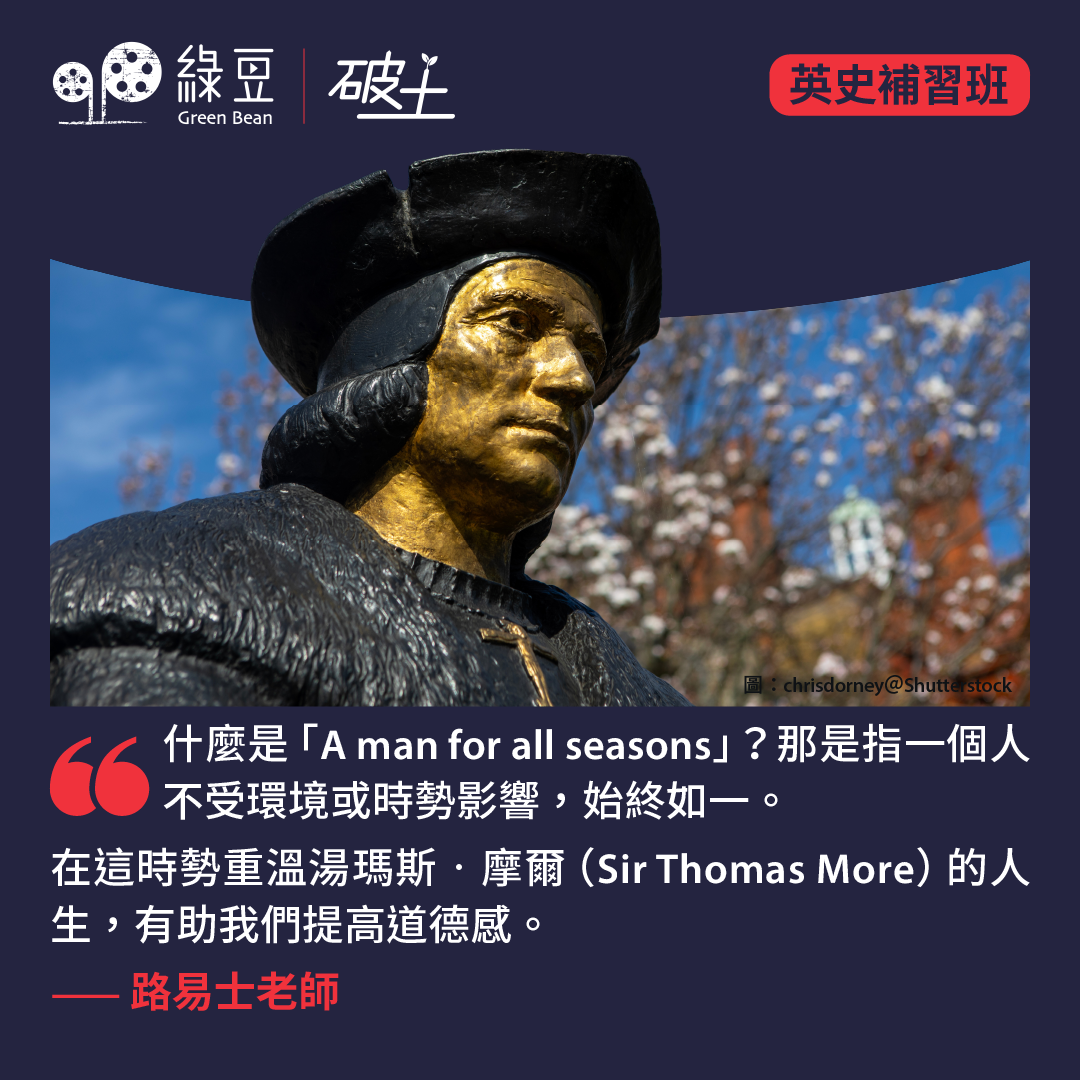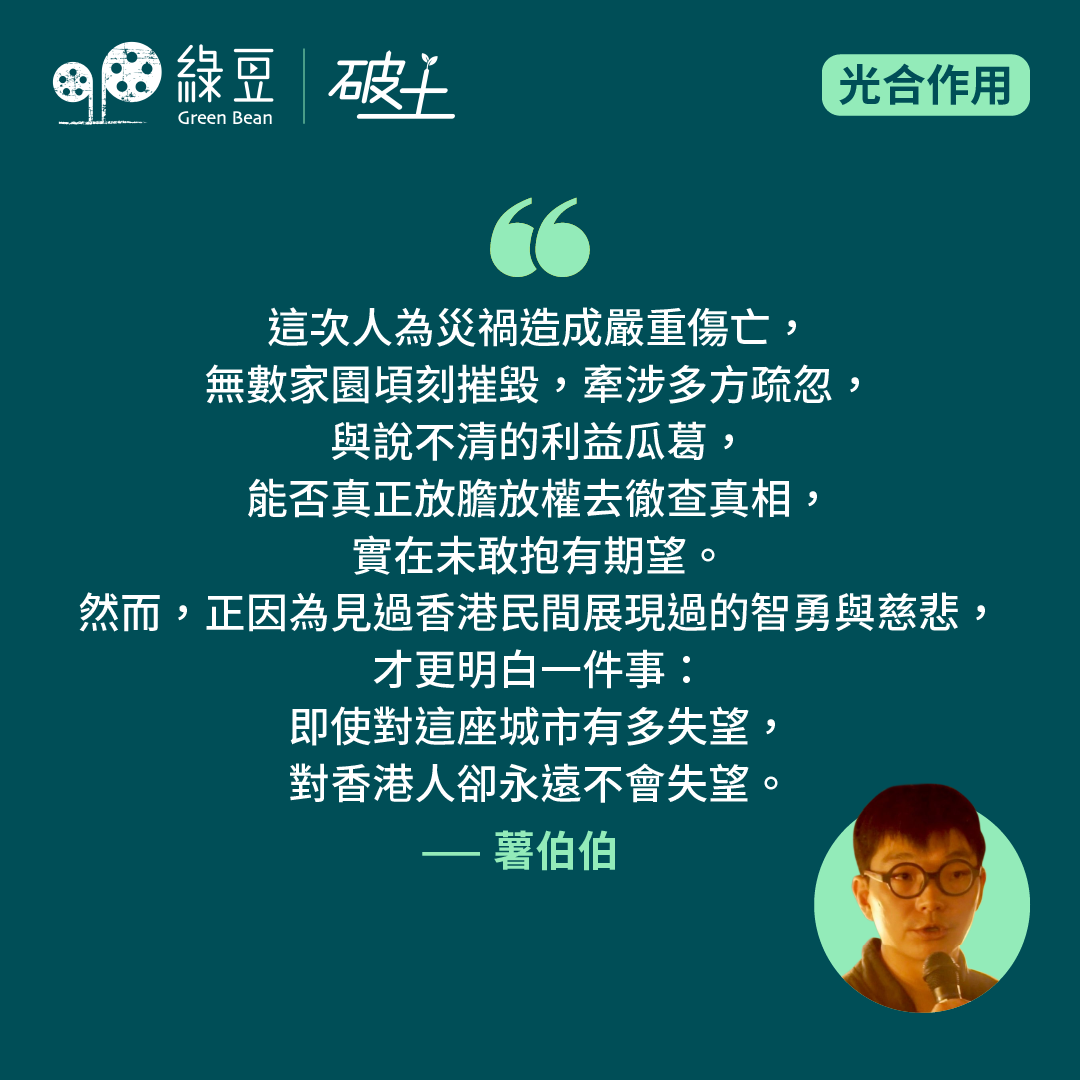過去三年半,美聯儲以量化緊縮(QT)方式「收水」,讓手上資產自然到期「蒸發」,形同把銀行體系中的水慢慢瀝走。直至2025年12月1日,QT結束,連主席鮑威爾也承認:儲備仍算「充裕但不再過剩」,緩衝位愈見薄弱。 水壓漸降之際,本周二至周三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會議焦點在於「檢驗水管」。表面上,決定的當然是利率——市場尚押注再減四分一厘。然而真正影響深遠的是何時啟動「儲備管理買入」(RMP)、怎樣調配常設回購工具(SRF),以及如何消化財政部愈來愈「短兵相接」的發債策略。 QT落幕RMP登場:技術操作還是暗渡陳倉? 量化緊縮自始就是走鋼線。當銀行儲備如海水般汪洋,一點半點收縮不會引起波瀾;但水位下降至「充裕但偏緊」,每逢報稅、結算、標售,便足以掀起回購與聯邦基金利率的激烈波動。眼下,市場正處於這敏感地帶。 RMP(儲備管理買入)本為穩壓工具,其做法刻意和QE拉開距離——不碰長年期,不干預曲線,只買短期國庫券,單純確保隔夜利率聽話停留在政策區間中間,不因儲備被稅收或財政部賬戶吸走而下滑。 但華爾街自然讀到弦外之音。美銀策略師認為RMP最快明年1月啟動,且每月買入量本身就是政策暗號——若月度超過400億美元便屬「偏鴿且偏暖」;低於300億美元則「純屬技術操作」。高盛相對「含蓄」,預測月買入約200億美元,剛好抵銷MBS繼續流失後的儲備不足。摩通更保守,料月度約80億美元,純屬維穩。...
我乘車由斯洛伐克前往波蘭,安排在窗口旁的位置。上車時發現走廊座位坐着一位拿著拐杖的女士,見她行動不便,問是否想坐窗口位,答沒關係。只見她頗為艱難地站起來,讓我跨到窗口位置。 坐下交談,她是斯洛伐克人,丈夫來自波蘭。她懂說德語、波語及斯語,但我通通不懂,只好用翻譯軟件溝通。期間拐杖無處可放,只能插在前座椅子之間的縫隙,一直搖晃,不斷掉落,她連聲道歉。 我靈機一動,從背包取出「膠化」(Gaffer tape,又稱「布基膠紙」)。這次我只帶了 19 公升的背包,精簡且輕便,但常備膠化。用一支外賣木筷子捲成一筒,隨身攜帶。膠紙可以徒手撕開,黏性極強,而且除下時不留膠漬,除非是中國製造。 我熟練地拉出約20...
距離本專欄文章更新只是十多天,筆者和眾多移英港人心情卻有如過山車。 先是離散群體關注了半年的,被稱為50年來英國對合法移民機制最大改革的諮詢文件,終於面世。執政工黨內政大臣馬曼婷終於明確表明,循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即BNO簽證申請永居的港人,將沿用「五加一」程序完成整個過程,並不納入今次諮詢當中。及後不變的框架之中卻包含基本要求的提升,港人群體和關注團體、獨立記者四出求問、求證,和代議士在國會討論中再次申訴、尋根究底。走筆至此,見到不少街坊鄰里在怨懟之後,努力盡一己之力寫信、向國會議員講解改變之不公和有如為難為避秦而至的移民和尋求庇護者。 今次諮詢文件強調「公平的入籍途徑」,但對永居申請者,包括英國公民家屬及BNO簽證持有人,都列入新訂立的基本規定要求。大多港人仍然沉著,透過民主制度、諮詢程序賦予的空間,要求政府落實對港人的人道和道義承諾,釐清灰色地帶。各方的論據和努力,在此不重覆了。但因入籍要求諮詢出台,得以跟本地人對談,卻也讓我這移居者感到溝通、對話,會令社群之間了解更深,也令移居者境況更令本地人明白。 疾風一代的借鑑 我們一家幾口子來英四年,參加本地英語教會的崇拜和侍奉都有三年了。教會內本身已儼如聯合國,所以我們早前都有就港人移民面對工黨政府欲把入籍「五加一」路徑延長至「十加一」分享,本地教友都有為港人、烏克蘭等人道途徑的移居者祈禱。 11月20日內相公布維持BNO持有人「五加一」路徑時,牧師發短訊給我說:「太好了。我一直都相信英國政府對香港人原有的承諾不應該有變。我還記得2021年英國多個堂會一同禱告和結集力量,動員本地教會接待從香港來的朋友。我祈求上帝的平安和應許不變。」 我們澄清,政府的建議還有很多灰色地帶,或會阻礙不少港人的永居申請。另一位教友、一位已是花甲之齡的牙買加裔居民就擁抱著我,說:「要好好把你們的需要和關注分析清楚給政府知道,也要預備好自己的文件。我的父母輩是『疾風一代』(Windrush...
特首近日就大埔火災事件宣布成立獨立委員會,公開表示政府會「調查到底,認真改革,化悲憤為改革力量,讓真相水落石出,讓公義得到伸張,讓逝者安息,讓生者安心。」並用上「必定會嚴肅查明真相,嚴格跟進問責」等強硬字眼,強調其決心全面查明事故成因及責任。此番說話旨在向市民釋出訊息,政府已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並希望透過獨立機制回應公眾關注。 然而,社會上亦有不少聲音關注政府沒有選擇成立法定的獨立調查委員會(Commission of Inquiry,下稱COI)。值得指出的是,這些討論固然重要,但不必因而貶低獨立委員會的價值,因為它無疑比一般的跨部門檢討小組更具獨立性與公信力。兩者的最大差異及成效,主要取決於其職權範圍(terms of reference)、成員組成以及法定權力,而後者尤其是公信力的關鍵。 按慣例,兩者一般皆由高等法院或以上的現任或退休法官主持。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尚待確定,但根據目前披露的資訊顯示,特首傾向要求獨立委員會「審視大埔宏福苑火災的起火和迅速蔓延的原因及相關問題」。這些相關問題尚待確定,特首的發言,似乎會觸及一些制度性的問題,如不當的相關利益、貪腐圍標、監管和檢測制度,以及相關人員包括政府部門及專業人士的責任承擔等(但似乎未提及政府高官的問責)。...
大埔宏福苑的五級大火造成最少159人死亡,逾千人痛失家園,全球媒體均大篇報道,多國元首致詞慰問,特區政府宣布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又設立基金協助居民善後,中央政府負責港澳工作的大員也親臨深圳督導。連日來事態發展顯示,這次人禍涉及多個制度漏洞,特區政府能否透過公平、公正、公開的調查,找出這些漏洞並一一堵塞,關乎民眾對香港未來的信心,關乎香港是否一座安全宜居的城市,這次火災善後考驗的是香港特區的全部底蘊。 大火剛發生不久,特區政府官員便面對傳媒和市民尖銳質詢,因為不是一幢大廈起火,而是七幢正在維修的大廈相繼起火。大廈外搭了棚架,棚架上了圍網,火勢沿著棚架棚網迅速蔓延,傳媒的提問很自然就落在棚網是否符合阻燃標準。保安局長鄧炳強公開表示棚網符合防火安全標準,但四日後便被迫改口。廉署調查顯示,部分棚網樣本經測試不符標準,懷疑承判商使用了廉價的不阻燃棚網。 傳媒調查又發現,由同一承判商負責的其他地盤,大廈外的棚網無端下架,市面上符合阻燃標準的棚網被搶購一空,更有傳媒調查發現,這類棚網多源自內地,防火檢測證書也是內地單位簽發,向來存在信用疑竇,供應商與檢測公司的資料數據無法對上,外界查證困難。 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的工程公司可以很容易買到廉價的非阻燃棚網,與合標準的棚網混合使用,遇到政府人員查詢,只要出示內地發出的棚網安全證書,便可蒙混過關。面對這樣巨大的制度漏洞,建築商和維修商能抵受引誘,堅持使用較昂貴的阻燃棚網嗎?市民今後看到建築物外牆搭了棚架、上了防沙塵外揚的圍網,能夠相信這些棚網安全嗎?難道要政府部門不斷抽樣檢測,來確定每張棚網都安全嗎?怎樣確保棚網上的安全證書標記不造假? 刑事調查無法堵塞制度漏洞 怎樣確保今後地盤用的棚網安全合規?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極不容易,因為它涉及內地的生產商和檢測單位,也涉及香港的工程公司和各級判頭,這條供應鏈上每一環都有可能弄虛作假。特區政府原本以為只要棄用竹棚,改為使用金屬棚架,便可消除棚架導火風險,但這次大火顯示,竹棚主因論不足為憑,就算竹棚被金屬棚架取代,若棚上圍網不阻燃,火勢迅速蔓延的風險仍在。刑事調查可以懲處個別黑心工程商,卻無法堵塞制度漏洞,恢復市民信心。 除了棚網,火災迅速升級的另一個原因,是承判商在大廈窗戶外,用了易燃的發泡膠物料遮擋窗戶,避免外牆工程震碎玻璃窗,這個漏洞太過顯而易見,到場巡視火災的官員很早便注意到這個問題。然而,傳媒和公眾一直無法明白,承判商為何如此大膽,在窗戶這樣當眼位置蓋上使用易燃物料?更加難以解釋的是,勞工處曾16次巡查宏福苑維修地盤,為何一直沒有發現如此明顯可見的漏洞?只要有一個地盤工人舉報,檢查人員拿一塊回去檢驗,就能發現整幢大廈被蓋上極多塊易燃物,這樣巨大的安全漏洞,該如何解釋,可如何補救?...
到 1529 年底,摩爾接替失勢的沃爾西,成為大法官,負責維護英格蘭的宗教一致性。兩年後,即 1531 年 11 月,他又一次來到切普賽德(Cheapside)的聖保羅大教堂——十年前沃爾西焚書的地點。這一次,投入火焰的不再是書籍,而是人:理查‧貝菲爾德(Richard...
大埔歷史性火難,死傷枕藉,相信很多身處海外的香港人和我一樣都會問自己:我能做些什麼?特別是看見留港的朋友奔赴現場,快速組織各種社區互助支援,身在千里之外獨自看著螢光幕,難免倍感無力,甚至質疑自己為何未能在關鍵時刻貢獻家園。這種情緒並不難理解,但海外港人不應因為不能一同搬運物資而感到氣餒,留港離港本來就有不同崗位,海外港人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還有很多。 超渡生人 首先,我們應正視災難之下對參與其中的渴望,本來就是正常人應有的反應,對社群亦可帶來正面作用。災難之可怕,在於把生命的不確定性赤裸裸的呈現在我們的眼前,而參與災難應對的其中一個作用,正正是重新建立自主性,找回效能感,避免陷入無力的漩渦,是重建信心的重要方式。套用黃子華的說法,「生人也要超渡」,而行動就是最實際的方式。 參與災難應對也可重建社會連結與互助支持,對抗創傷產生的孤立,帶來歸屬感與「一起面對」的情緒,有助撫平悲傷。當大家在互助中看見彼此,也有助情感的正常化與降低污名,鼓勵更多怕被看見的人站出來接受援助,讓更多人能被接住。最重要的,是參與帶來的社會連結,可以建立目的和強化集體韌性,甚至為未來作準備,最少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 在地不是唯一參與方式 以上的參與,有時會以在地的方式呈現,例如到災難現場獻花。有些社群體現的模式,也是通過在地參與連結呈現,廣福邨平台和大埔墟火車站的物資站是例證。但在網絡時代,在地參與不是唯一的參與模式,各種遙距參與的空間也被擴展出來。 在火災發生後,已立即見到許多海外港人自動補位,向世界各地的媒體推送詳細的背景信息,甚至接受身處當地的媒體採訪說明事發因由。很不幸,一開始的時候不少國際媒體把火災的原因連結到竹棚之上,沒看到維修工程本身已經歷了為時數年的各種爭議。這些媒體把觀眾的目光投到陌生和獵奇的角度,無疑是東方主義(如果不是種族主義)的潛意識投射,也說明了文化識讀的問題並非知識份子的無病呻吟或矯枉過正。幸好許多海外港人立即站出來,向這些媒體點出問題所在,報道角度也隨之有所調整。...
大埔的火光熄滅了,但悲傷仍在蔓延。撰寫此文之時,社交媒體上正傳來一位又一位身穿素服的香港人,默默前往大埔靜靜悼念的景象。遠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一夜又一夜緊盯著屏幕,等待各種最新消息:有人在工作間偷偷刷新手機,有人在海外城市的清晨默默祈禱,有人的社群聊天一整天都停留在那幾張令人心碎的照片上。即使相隔萬里,人們依然深深牽掛。那份牽掛,是人與人之間最原始、最柔軟的連結。 這場大火,再次把我們拋回一個古老而迫切的問題:我們究竟在給下一代示範一個怎樣的世界?我們又希望孩子在怎樣的價值觀中長大? 面對巨大傷痛,我們往往覺得無力;但正是此刻,我們的一言一行、一個念想、一份態度,都悄悄塑造着下一代眼中的人性與社會。若我們希望孩子成為有溫度、有責任、有判斷力的人,那我們作為成年人,作為上一代,就是如此這般的成為孩子學習的模樣。 我們都是人:承認無力、擁抱情緒,才是力量的開始 很多人不願承認,但這樣的災難讓無力感如巨浪般襲來。我們會悲傷、會崩潰、會憤怒,也會在深夜看見新聞時突然落淚。這些反應並不丟臉,它們提醒我們,我們還有感覺,還在乎! 對下一代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我們表現得多堅強,而是我們願不願意承認情緒需要被照顧。孩子從大人身上看到的,不應是壓抑,而是如何面對情緒、整理內心、在脆弱中尋找前行的力量。讓孩子知道:悲傷是可以的,哭是可以的,停下來照顧自己更是可以的。真正成熟的大人不是不會倒下,而是倒下後還願意重新站起來。這樣的榜樣,比「我沒事」更有力量。 互助的本能:我們之所以叫作「社會」...
以前未曾離開香港生活,總是說不清楚為甚麼喜歡我城;直到真正走出外地,才恍然明白香港確實與眾不同。山野近在咫尺,不用片刻便可徒步登山,飽覽世界級景致;轉個彎下山,隨意步行已能找到各式美食,或走進戲院看一場好戲。這種幾乎無縫銜接的大都會與大自然共存的格局,在其他城市從未遇上。 有次與拉達克的好友聊天,他問我最喜歡香港甚麼,我笑著回答:「我最喜歡在香港搭電梯時,不用刻意跟人打招呼。」自問性格偏向所謂的「I 人」,有時打開門看見鄰居在門口等候電梯,會假裝有事在身,寧願錯開一程。常聽說外地不少社區街坊十分親切,表面聽來溫馨動人,但設想若長期置身其中,對於習慣保留私人空間的我而言,其實頗感吃力。 不少人覺得香港人冷漠、性急,曾幾何時,我也有此印象。直至風風雨雨,才明白其實香港人並非無情,而是本能地尊重彼此的界線與私隱;日常話不多,但一方有難,八方總會自發伸出援手。 近乎本能的慈悲心懷 有些經歷已不宜再公開細寫,免得再捲入無謂風波,惹來文革式批鬥。然而只以疫情期間經歷為例,香港民間自發,展現出驚人的守望相助精神。互不相識,姓甚名誰皆不得而知的街坊,會主動提供口罩、酒精、藥物等物資,默默照應身邊人。 最難得的是,疫情過後,大家又自然回復原本淡然的距離,各自生活、互不打擾。我感激這份無私的真摯互助,又不趁機逾越對方的生活界線。君子之交淡如水,志趣相投,交往不涉利益,並非只屬古書所說的高尚情操,而是不少香港人確切的日常實踐。我最喜歡香港之處,正是這種微妙而珍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