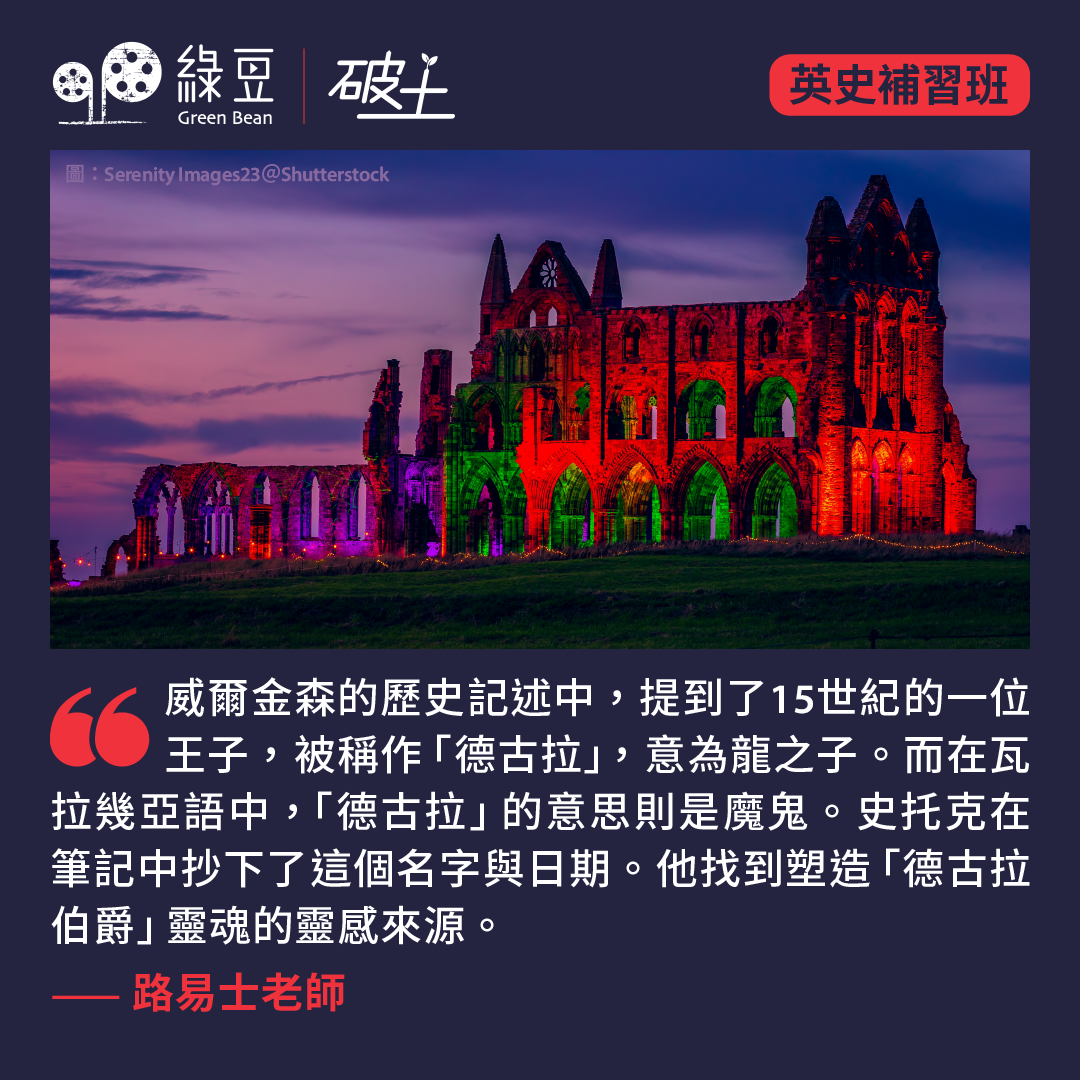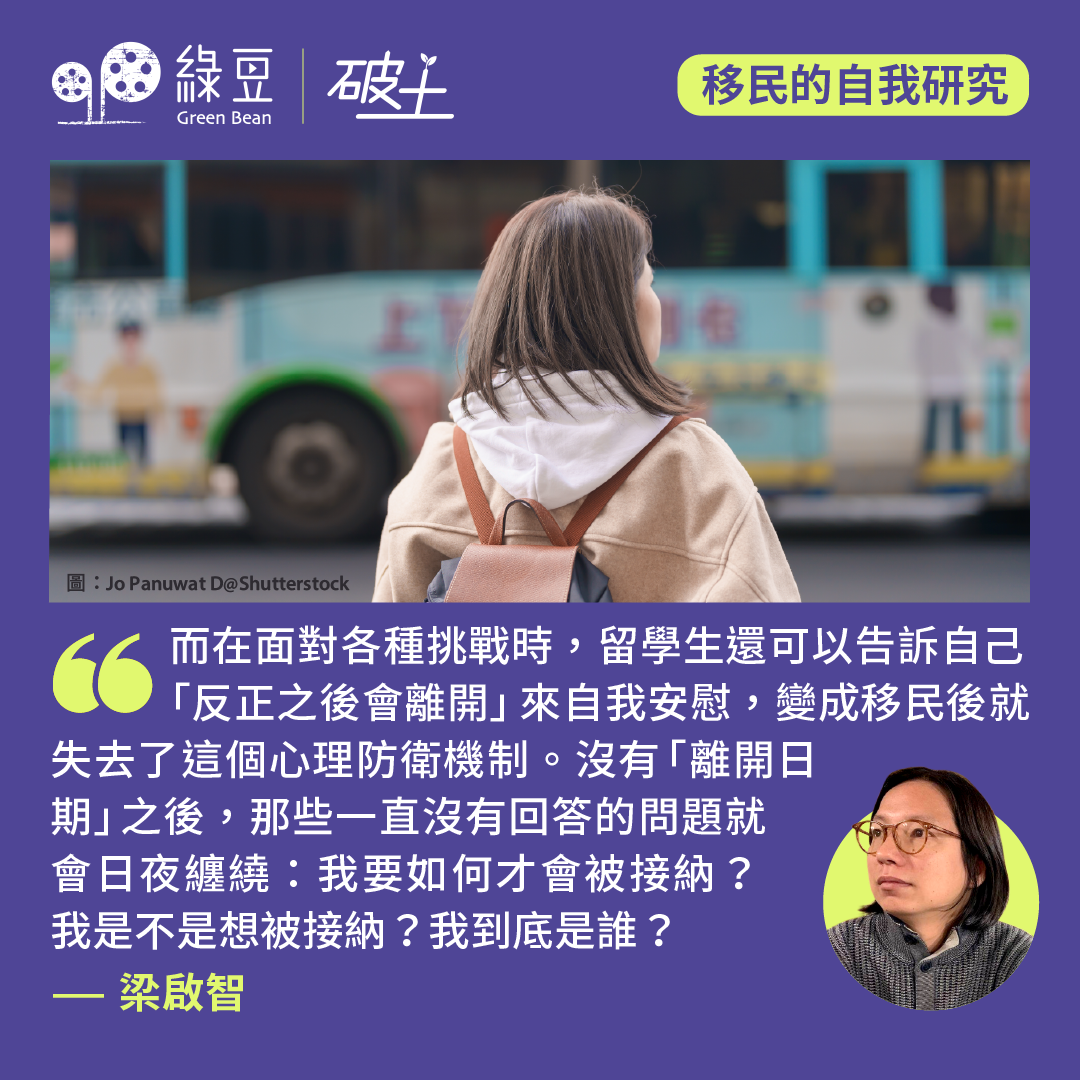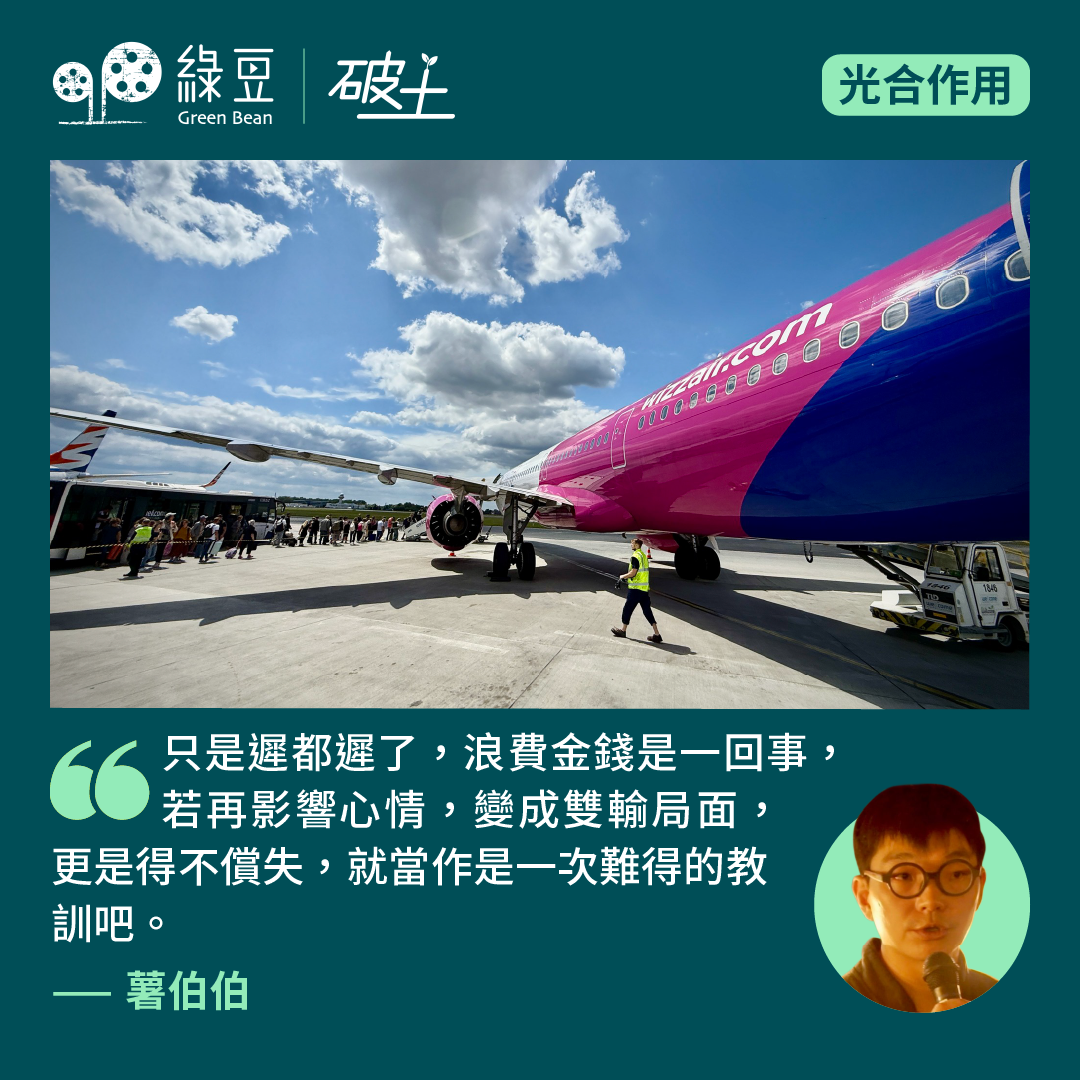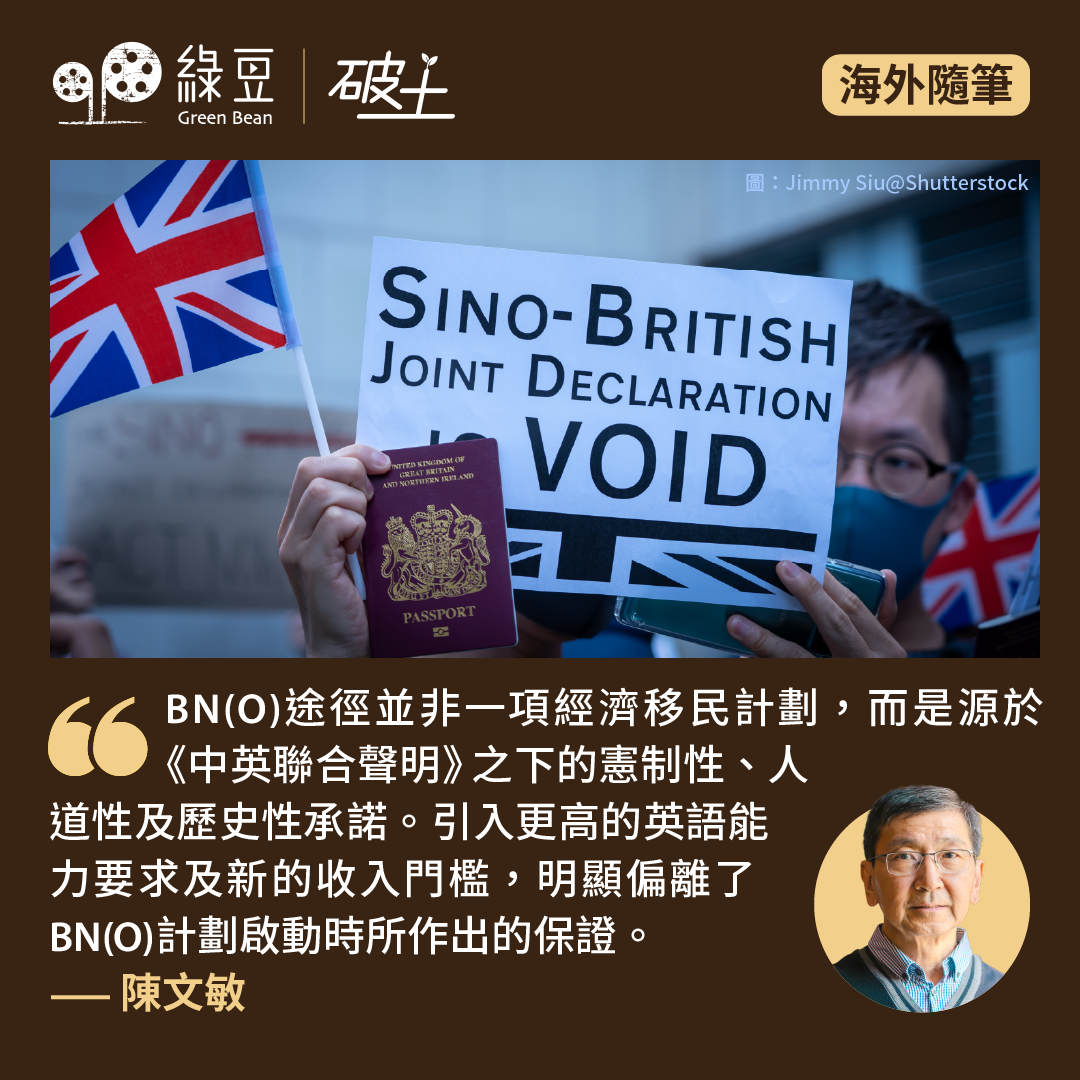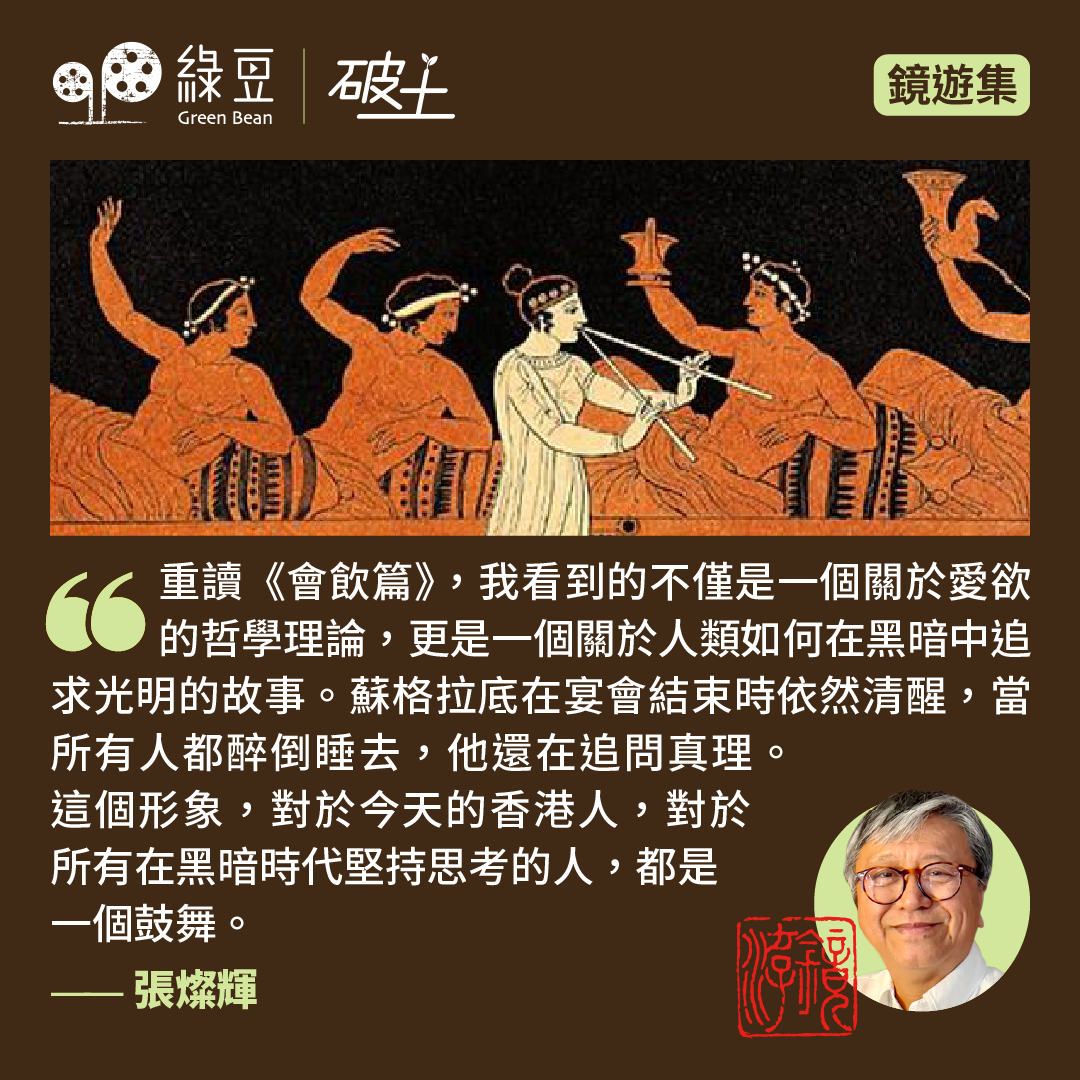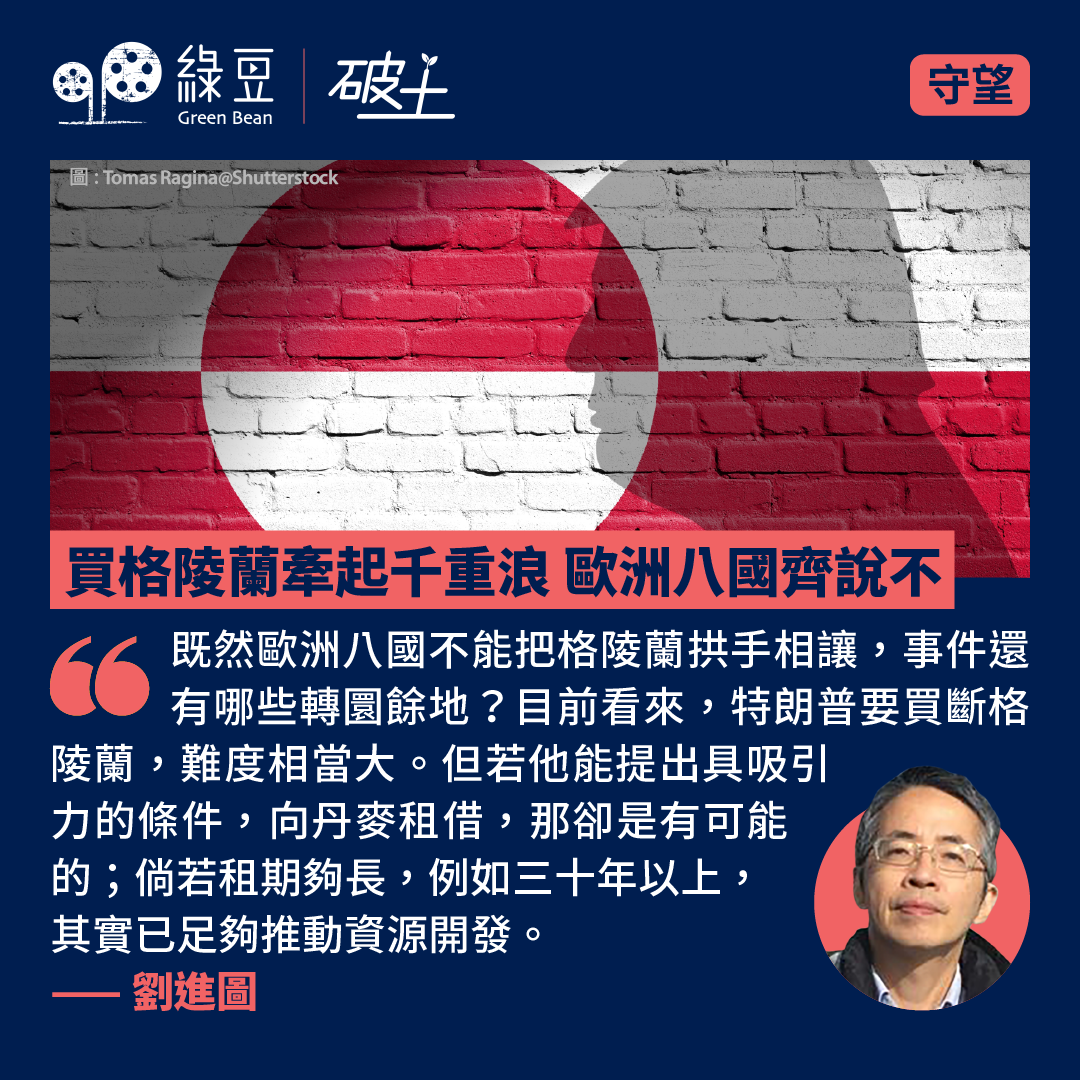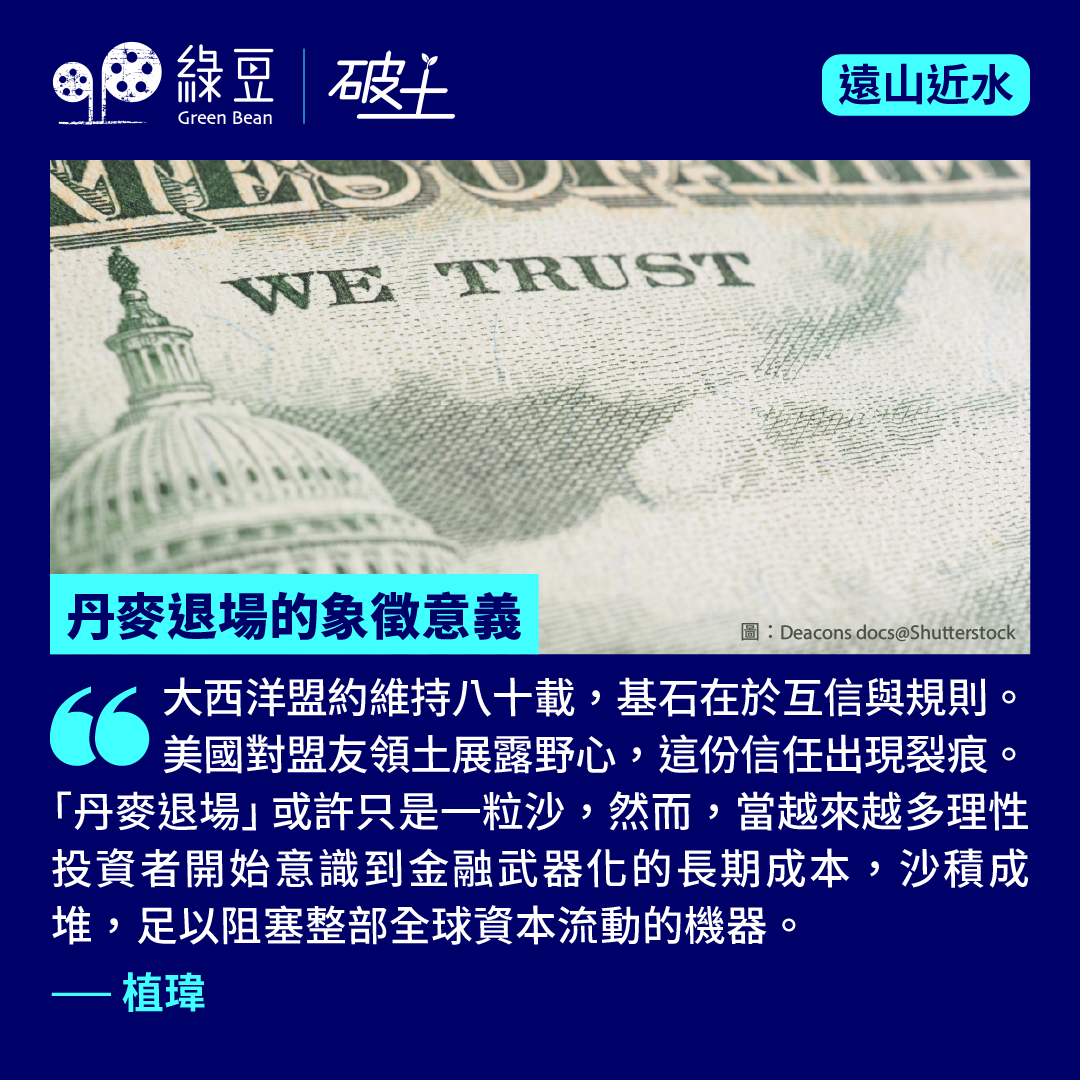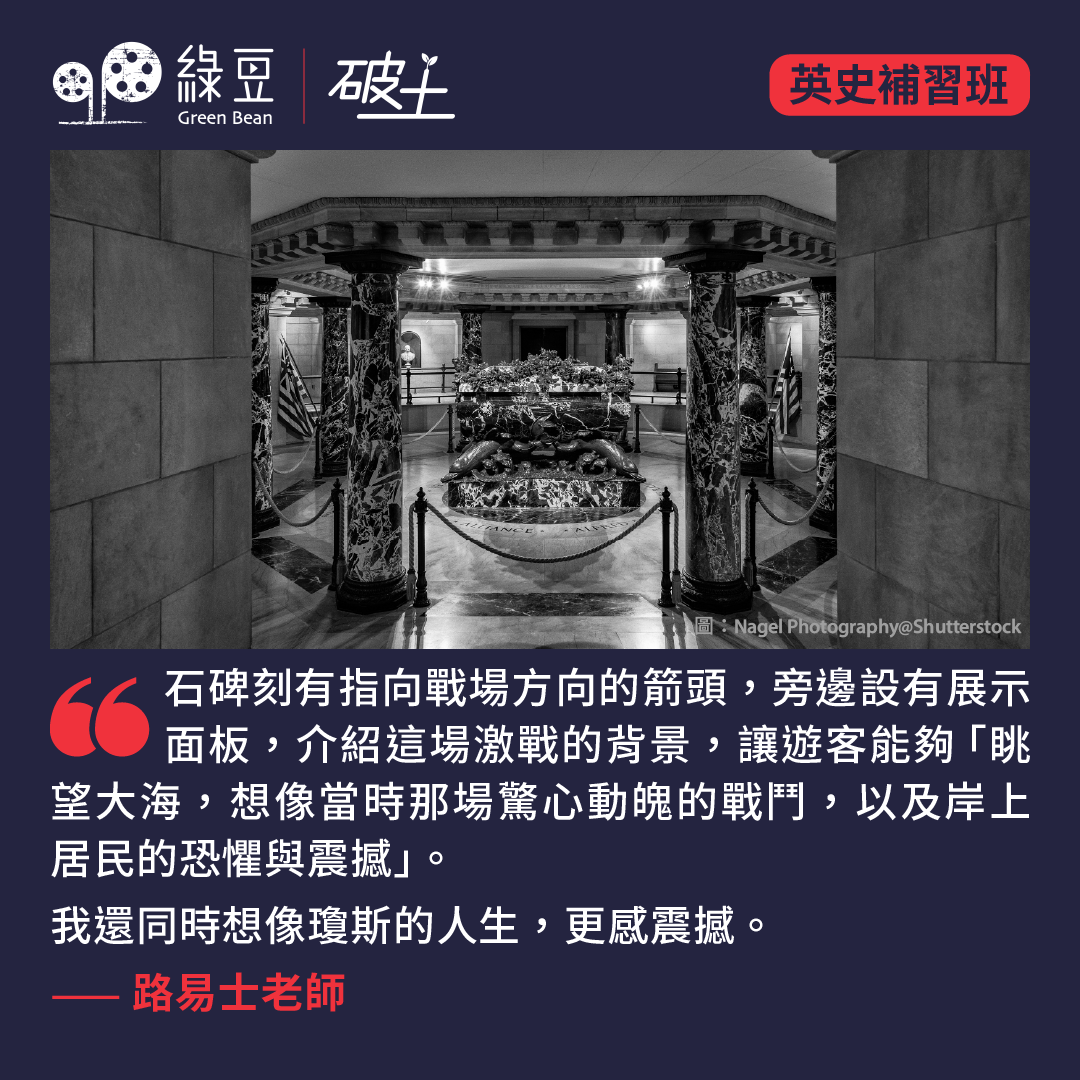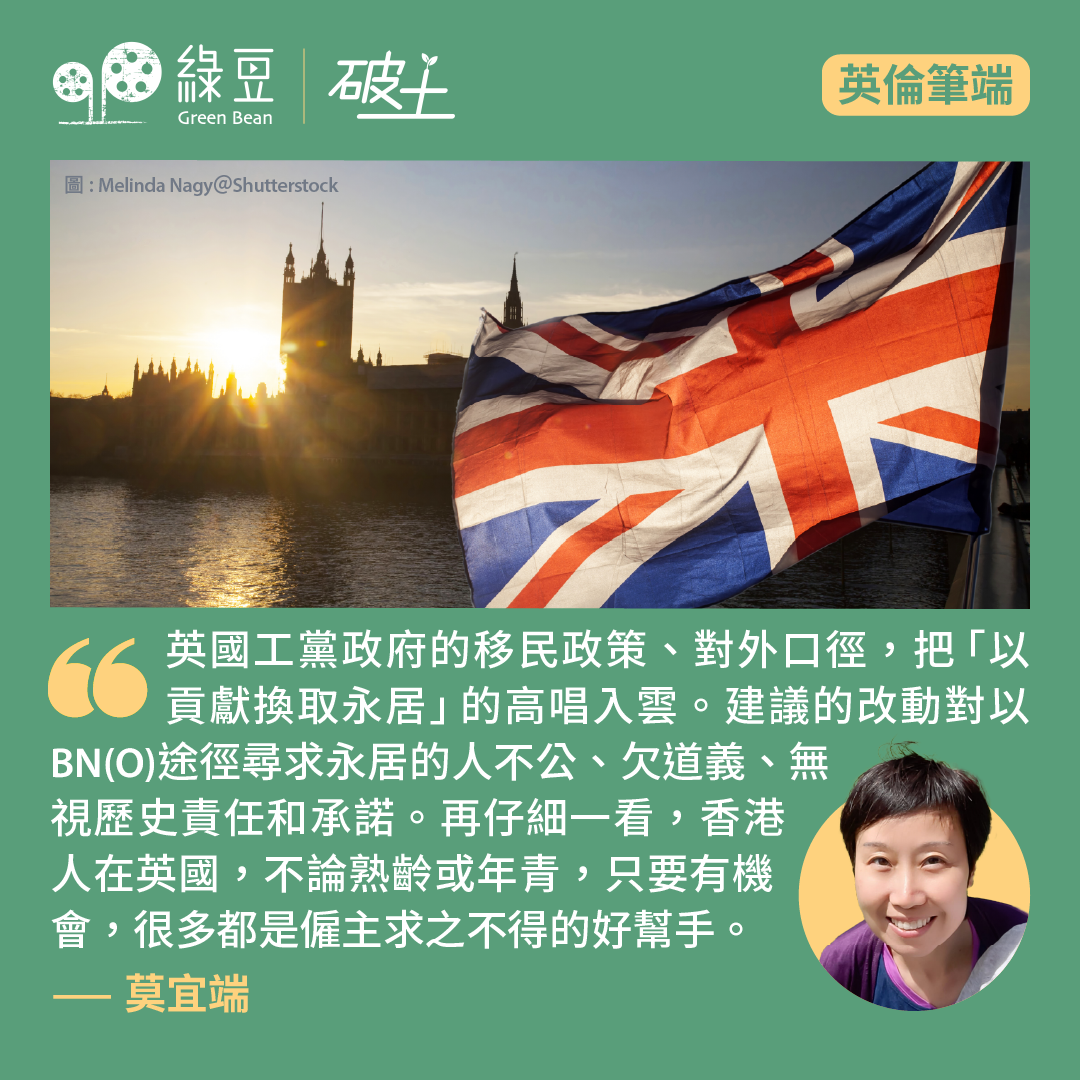在弗蘭伯勒(Flamborough)只留了一會,朋友說要帶我們到惠特比(Whitby)。我們去約克郡(York)前全無準備,怎會知那兒是什麼地方呢。朋友很懂賣廣告,說《德古拉》(Dracula)一書就是在此地創作的呢。 弗拉德三世 這完全符合我的興趣,加上最近看了一齣半紀錄片,講述鄂圖曼帝國與德古拉伯爵之關係。德古拉伯爵的原型是弗拉德三世(Vlad III),又稱「穿刺公(Vlad Țepeș)」或「德古拉(Drăculea)」,他是 15 世紀中葉(約...
最近因為工作關係,收到一些香港來台留學生的履歷。從香港移民來台灣,留學是其中一種方法,雖然這樣路現在已不太好走。認識不少通過留學移民的年輕人,在轉換身份的過程中都遇都不少問題。從留學到移民,不是一條純粹的直行路。 留學生算是移民嗎?如果放在傳統意義下對移民作為單向遷移的理解,那就當然不算。但現實往往複雜很多,很多時候出國留學的那一刻沒有想過要在當地留下來,結果因緣際會,可能是找到喜歡的工作,可能是有異地姻緣,也就誤打誤撞留下來了。反過來,也有不少人一開始就想移民,留學是其跳板:香港就有不少中國大陸的學生是這樣留下來的;也有不少香港人因政治因素需要離港,而來台留學對他們來說是最容易的方式,儘管他們本來並無意欲留學。 對未來的想像 從留學變成移民,身份轉變會帶來時間觀的改變。留學是暫時的,你知道自己有回去的一天,於是很多影響比較長遠的決定都不會做,最起碼不會為住處添置大件傢俱,最好一個皮箱隨時來去自如。決定留下來了,不再是數年內便會離開,道理上就可以開始想得比較長遠。 只不過,時間觀在拉長的同時,也可以變得更不確定。身為一個學生,每日每月每年的作息是有清楚規劃的,時間往往可預期且被制度化:上課下課有時間表,學程有明確年限,未來被想像為「完成學業後再說」。一旦留下來了,除了開始要為以後的時間規劃,也要面對這個未來是何等的難以規劃。即使當了幾年的留學生,不等於就對當地的職場文化和不同業界的發展前途有任何認識,也沒有多少人可以依靠,剛畢業踏進社會的不安感比本地人更如浮萍。 然後是工作簽證的年限、居留資格的更新,還有移民政策的變動,使得生活規劃不再圍繞學期論文和考試的定時規律,而是被行政程序與政策風險所切割。你發現「原來一畢業才知,一世我也要考試」;只是這些考試不再有評分表和天書,酌情權全在移民官手上,你做足所有要求不等於你的申請會最快得到審批。 另一個時間觀改變的後果,是因為過去的居留被定義為是臨時的,無論是自我或外在對於融合的期望也會比較低。留學生通常被置於一個相對清楚、甚至受到保護的制度位置;因為位置是暫時的,邊緣性也被合理化。口語說得不好?沒所謂,留學生嘛;但身份變成移民後,期望就不一樣了:你既然要成為本地人,你就要變得像一個本地人。儘管正如本欄多次強調,「何謂本地人」從來沒有客觀標準可言。...
這趟歐洲之旅,由於各站點距離相對較近,我主要以巴士代步,間中改搭火車。從波蘭華沙飛往英國倫敦,選擇了一程短途廉航,機票只需數十歐元。 搭乘廉航有個重要原則——出發前務必細閱所有規定,特別是行李限制。我刻意只攜帶一個重量在 7 公斤以內的背囊,以免被抽查。 可是這次還是老貓燒鬚,犯了一個低級錯誤。雖然提早了兩個多小時抵達機場,但到場時才猛然想起尚未辦理網上登機手續。我本以為時間尚算充裕,馬上用手機登記,但屢試不果。手機程式顯示須到櫃台辦理,那刻已心知不妙。 原來 Wizz...
《重讀經典:與人文和自然對話》 狄俄提瑪的教導:愛欲的哲學本質 狄俄提瑪(Diotima)的教導構成了《會飲篇》的哲學核心。她系統地回答了關於愛欲的三個根本問題:愛欲是什麼?愛欲的目的是什麼?如何正確地愛?這些教導展現了柏拉圖(Plato)成熟期的哲學思想,特別是他的形式理論的萌芽。 愛的精靈本質 當蘇格拉底(Socrates)承認愛既不美也不善時,他像阿伽通(Agathon)一樣立即推論說愛欲必定是醜陋和邪惡的。狄俄提瑪糾正了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她指出,在美與醜、善與惡之間存在著中間狀態。愛正是這樣一種中介性的存在。 狄俄提瑪講述了愛神厄洛斯(Eros)誕生的神話。在阿芙洛狄忒(Aphrodite)誕生的慶典上,機巧之神波洛斯(Poros,即「富足」)和貧困女神佩尼亞(Penia)躺在一起,生下了厄洛斯。因此,愛繼承了雙親的特性:他始終貧困、粗糙、赤腳,居無定所;但同時他又勇敢、機智,不斷追求智慧和美好事物。 這個神話揭示了愛的辯證本質。愛永遠處於擁有與匱乏之間。他不是神(因為神是完滿的),也不是凡人(因為他永恆存在),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精靈(daimon)。同樣,他處於智慧與無知之間:這正是哲學家的處境。...
特朗普宣布對八個歐洲盟友實施額外關稅制裁,除非他們在六月一日前促成美國收購屬於丹麥的格陵蘭。歐洲八國一致表示不會屈服,醞釀採取反制措施,令美歐原已簽定的關稅協議可能被廢,觸發環球金融市場震盪:周二全球股市普遍下跌,金價則創新高,美債被沽售,美元匯價疲軟。 特朗普周三出席瑞士達沃斯經濟論壇,臨行前說他將會就格陵蘭達成讓北約盟友和美國都高興的交易。在論壇上,他說希望立即與丹麥作收購格陵蘭談判,但強調不會動武,並放棄對八國加徵關稅。 軟硬兼施誓取格陵蘭 特朗普為什麼想要格陵蘭?過去本欄曾簡略作分析,格陵蘭位處北極圈,是箝制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略之地,特朗普說美國出於國防需要必須取得此地。其次,昔日格陵蘭海域大部分時間冰封,無法通航,但自全球暖化後,該處海域已可通航,令油氣及礦物勘探、開採和運輸變成可行,經濟吸引力大增。特朗普在瑞士說,二戰時丹麥被德國攻佔,格陵蘭等如淪陷,全靠美國打敗德國,奪回交給丹麥,美國是西半球領袖,可獨力守住格陵蘭。 丹麥和歐洲盟友提出,在北約共同防衛框架下,美歐向來共同承擔格陵蘭的防務,美國想派多少軍隊去,丹麥都支持,北約盟友也願意貢獻兵力。若只是為了加強國防應對俄中威脅,沒必要逼丹麥出讓格陵蘭主權,強取乃侵犯丹麥主權及領土完整,以武力奪取更意味一個北約成員國攻擊另一北約成員國,會導致北約解體,最大得益者是俄羅斯。 特朗普較早前不理會丹麥和其他北約盟友反對,堅持要取得格陵蘭,並且不排除軍事手段。他之後又表示要購買,逼丹麥盡快談判讓美國收購安排,丹麥當時對策是邀請瑞典、挪威、芬蘭、德國、法國、荷蘭和英國這歐洲七個盟國,到格陵蘭軍事演習,合共派了三十五人,宣示歐洲共同守護格陵蘭,特朗普勃然大怒,對丹麥在內的這八國宣布制裁,二月一日起徵10%關稅,到6月1日加至25%。 背後動機...
周二正值農曆二十四節氣之「大寒」,北歐財金界亦透出一股蕭殺之意。丹麥專職人士退休基金(Akademiker Pension)正式宣布,將於本月底前悉數清空其投資組合中的美國國債。這家管理約250億美元資產的養老基金,其拋售額雖僅約1億美元,在28萬億美元的美債汪洋中不過是滄海一粟;然則,天下大勢,波瀾往往起於青萍之末。這場「丹麥退場」(Danish Exit)行動,實則是對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美債零風險」神話,投下質疑票。 美國的財政壓力並非新鮮事。真正令人不安的,是華盛頓對此展現出的從容,甚至近乎理所當然。白宮近日提出,擬將年度國防預算推高至 1.5 萬億美元。表面上,這是地緣政治緊張下的「必要之惡」;但從財政角度看,卻是一場豪賭。 「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CRFB)估算,相關計劃將在未來...
不知是幸還是不幸,老師跟學生最喜歡的不是返學,而是放假。我總想起同事half term 前最後一天放學時那個「四萬咁口」的笑容。 我當然也喜歡holiday,特別是可以放假出外走走。今次我們打算去列斯,但最後去了約克 (York)。約克的見聞,稍後才跟各位分享。今次想談談海邊的歷史。 說起海,雖說英國是島,但要走到海邊並不是易事。不像在香港可以很快親親海邊,至少我們有維港啊。所以朋友說要帶我們到海邊,立即說好,更何況有海豹(seal)可看。 去看海豹的地方是弗蘭伯勒(Flamborough)。「弗蘭伯勒」(Flamborough)是一個位於英格蘭東約克郡(East...
( 編按 : 此專欄內容均為真實處境,旨在反映家庭、婚姻及個人之間的複雜性,以文字與大家一起走過荊棘。專欄文章經編輯在文字上修改處理,確保內文提及的人士身分保密。) 一家人舉家移民英國,卻在落腳後不久遭逢巨變——父親因病離世。失去丈夫與父親的傷痛,靜靜地籠罩著這個家庭。媽媽美雲與兩個女兒相依為命,陪伴彼此走過那段最艱難的日子。 時間慢慢流逝,兩姊妹先後完成大學課程,踏入人生的新階段。大女兒 Miche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