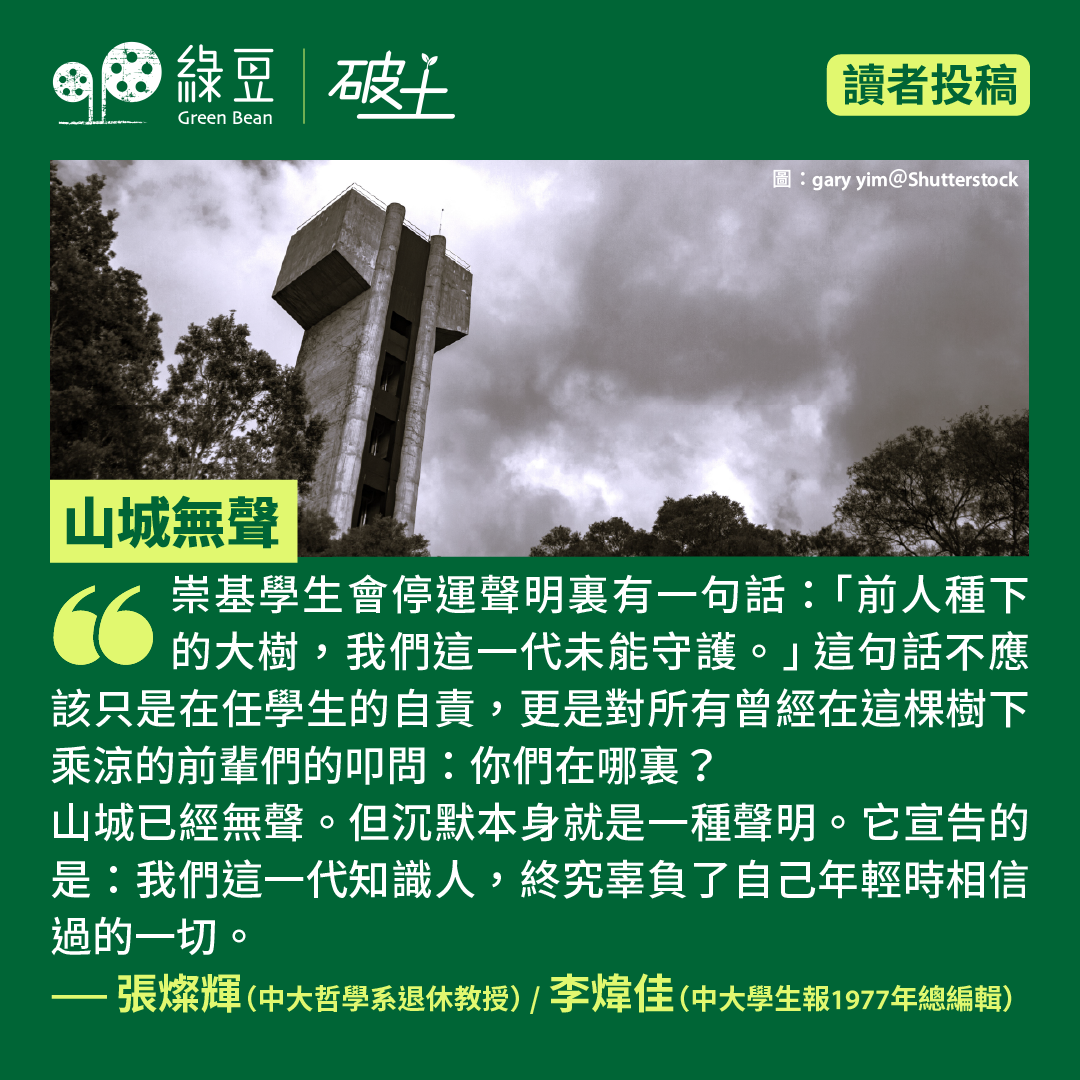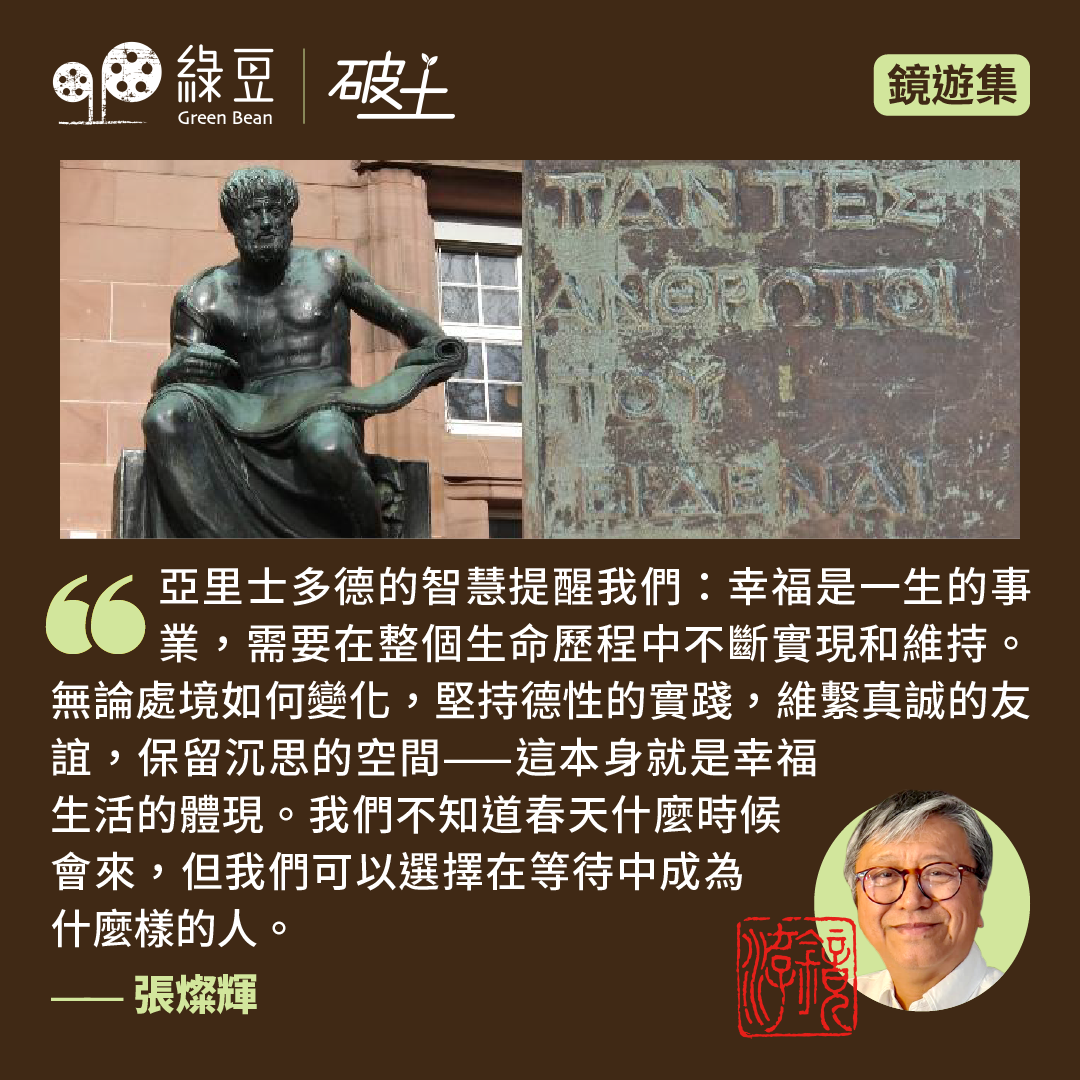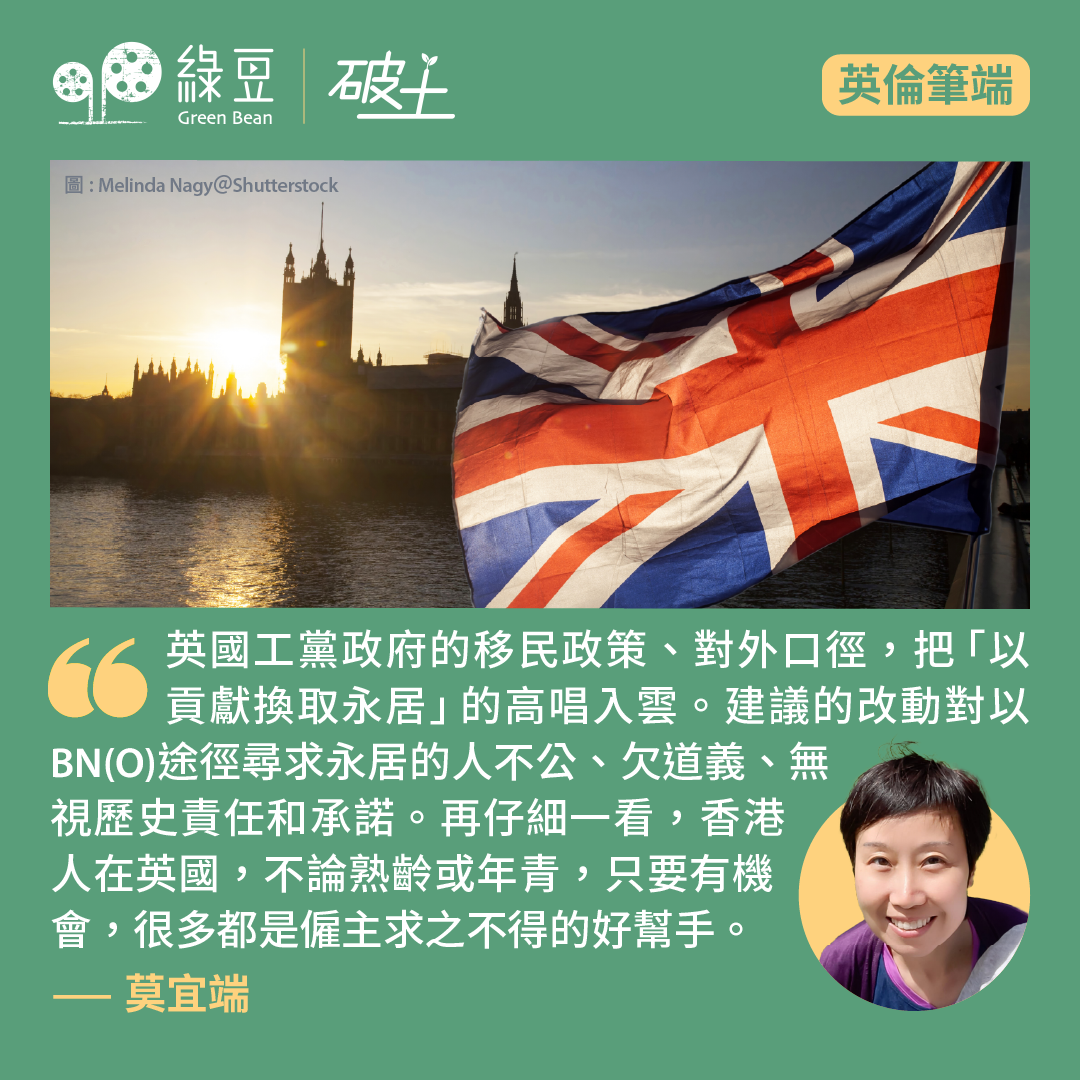《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因串謀勾結罪被重判20年,報社編採主管也判坐牢6年9個月至10年,此案量刑之重,遠超英治時期香港對政治異見者判刑,引起西方社會廣泛抨擊。另一邊廂,日本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解散國會重選,替自民黨取得史上最大勝利,拿下國會下議院逾三分二席位,足可通過上議院不支持的法案及推動修憲。 黎智英的最大罪名 《蘋果日報》案備受西方社會關注,定罪裁決被指為不公平,量刑裁決被視為不人道,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黎智英等人除了發表不利中共的言論,並沒有具體危害香港或中國的行動。在西方社會眼中,他們是因為政治言論得罪當權者而受迫害。 在2020年香港國安法生效前,黎智英曾公開呼籲西方國家制裁北京,也資助鼓勵一些香港青年,游說西方政府發動制裁,認為這樣有利於爭取香港自治與民主,當時這些言行沒有牴觸香港任何法律。 2020年中,香港國安法頒布,呼籲境外勢力制裁中國或香港列為非法,黎智英及蘋果諸人停止了公開呼籲,避免觸犯刑法。但控方以串謀勾結罪起訴,把國安法生效前的言行列為犯罪背景證據,指眾被告在國安法生效後,腦海裡仍然繼續此圖謀,促使西方制裁中國。《蘋果日報》一些批評北京政策的文章,成了控方指眾被告仍在隱晦實施串謀的證據,黎智英與西方政客的私下通訊,也被控方拿來推論他依舊在串謀促使西方制裁。 從定罪及量刑裁決發布後北京官方評論來看,黎智英的最大罪名,其實是北京認定他乃2019年反送中社運引發持續騷亂的幕後黑手,是配合西方在中國境內策動「顏色革命」的罪魁禍首,必須檢控及重判他以儆效尤。換言之,國安法審訊是對他的秋後算帳。 難以與西方保持正常關係...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78歲)去年12月被裁定串謀刊印及發布煽動刊物,以及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共三罪罪成。法官今指考慮到本案罪行屬「罪行重大」,再考慮到案件性質,將量刑起點提高至15年,而由於認為黎智英是各項串謀的幕後主腦和推動者,最後重判黎入獄20年。 法官在判刑理由中提到,《國安法》第29條的處罰條文訂明:「犯前款罪,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據呂世瑜案,法庭認為立法原意是,假若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涉及外國實體,一般會被視為較嚴重,理應判處更嚴厲的刑罰。 而在界定案件是否屬「罪行重大」,法庭考慮了馬俊文案所列明眾多因素,因應《蘋果》案作調整後,相關因素包括:當時的社會氣氛;犯案手法,包括方式、行為、措詞、媒介或平台;犯案次數、時長及持續性;罪行規模;有否預謀犯案;有否涉及武力或以武力威脅;涉及人數;請求制裁的目標及對他們的潛在影響;是否成功導致外國制裁,或制裁的風險和迫切度;罪行對香港及中國帶來的實質或潛在影響等。 法庭強調《國安法》不具追溯力,在《國安法》實施前發生的事,只構成犯案背景的一部分。而法庭考慮證據後認為相關罪行屬「罪行重大」,判處的刑期不應少於10年。 就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庭認為有關串謀「不僅經精心策劃,且是早有預謀的,並涉及使用網上平台,觸及本地及海外受眾」,並指「請求外國實施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的呼籲,無論是公開進行或者隱晦行事,都確實促成了外國政府針對香港特區以及針對中國及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採取上述措施」。每項串謀的量刑起點為15年監禁。至於串謀刊印及發布煽動刊物罪,法庭認為有關串謀屬最嚴重級別,以21個月監禁作為量刑起點。...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78歲),去年12月被裁定串謀刊印及發布煽動刊物,以及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共三罪罪成。法官今指,黎智英在本案的三項控罪中,均是主謀及核心推動者,其角色與其他被告有本質上的層級差異,因而須承擔最重刑責,遂重判他入獄20年,當中 18 年與其欺詐罪刑期分期執行。至於六名《蘋果》高層,前壹傳媒行政總裁兼《蘋果》前社長張劍虹入獄6年9個月、前《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入獄7年、前總編羅偉光入獄10年、前執行總編林文宗入獄10年、前英文版執行總編馮偉光入獄10年、前社論主筆楊清奇入獄7年3個月。至於早前承認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並出庭作供的重光團隊成員陳梓華和李宇軒,則分別被判入獄6年3個月及7年3個月。黎智英從2020年12月31日起已還柙超過五年,其餘各人也被還柙四年半至接近五年。 ...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以及 6 名蘋果日報高層的國安案,將於香港時間星期一上午10時判刑,眾人至今已被還押 4 年半至 5 年不等。上月案件進入求情階段,旁聽巿民提早...
收看節目 已解散的支聯會及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鄒幸彤,被控在2020至2021年間「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件歷時四年多,三名被告長期拒保還押,將於1月22日正式開審。 法律學者陳文敏分析指出,控方的檢控基礎幾乎完全建立於「結束一黨專政」這一口號,並將其等同「結束共產黨領導」及違反中國憲法,毋須具體非法行為,爭議已推至思想定罪的極限。影片深入拆解預審爭論、程序公義問題、特委法官制度如何導致審訊延誤,以及此案在《國安法》實施後的象徵性意義。 節目內容: ⚖️ 支聯會案背景...
收看節目 美向歐八國徵稅至取得格陵蘭美國向8個歐洲國家徵收額外10%關稅,直至美國能購買格陵蘭,懲罰他們不支持美國。八國共同聲明指此舉破壞跨大西洋關係。特朗普否認格陵蘭問題因失意諾獎挪威首相史托爾透露,特朗普因未獲諾貝爾和平獎,認為除非完全掌握格陵蘭,否則世界無真正安全。史托爾強調和平獎由委員會頒發,非挪威政府。特朗普則堅稱挪威操控獎項,但他不在乎,只關心拯救生命。特朗普赴世界經濟論壇致詞特朗普週三將赴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致詞,討論格陵蘭問題,美方擬提99年租借。歐洲準備930億歐元關稅反制。特朗普將與多國領袖會面,並強調美國經濟空前良好。《和平委員會》被指意欲架空聯合國達沃斯會議將關注加沙重建。白宮公布NCAG成員。特朗普另設「和平委員會」監察加沙,並計劃擴展範圍,遭評論指意圖架空聯合國。聯合國堅稱委員會僅限處理加沙事務。特朗普自任主席,普京獲邀,並揚言向拒絕加入的馬克龍徵收高關稅。台記者涉諜報被控違國安台灣中天記者林宸佑涉嫌違反國安法、貪污、洩密,與5名軍人同被收押。檢方指林向現役軍人收買情報轉交大陸,涉嫌行賄數百萬台幣,換取防空設施操作手冊及參數等機密。案情嚴重。中國人口持續下降老化加劇儘管中國鼓勵生育,人口連四年下降至14.05億,出生率創1949年新低,結婚數字大跌。老化加劇(60歲以上近1/4),養老金系統承壓,當局已將退休年齡提高3歲。日首提前眾議院選舉望過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任3個月,宣布解散眾議院並提前於下月8日大選。她希望藉高達78.1%的支持率,助自民黨議席過半,以利政策推行和預算通過。但其挺台言論及高國防開支,可能使擔心中日關係的選民卻步。歐盟與南美5國簽訂歷史經貿協議歐盟與南錐共同體(Mercosur,成員包括烏拉圭、阿根廷、巴西等)經逾25年談判,終簽署歷史性經貿協議。歐盟主席馮德萊恩指協議構成全球最龐大的自由貿易區,涵蓋7億人市場,貿易額接近全球總生產力1/5。西班牙火車出軌相撞數十亡西班牙南部可多華省發生火車出軌相撞事故,造成至少40人死亡,逾150人受傷,40多人失蹤。一列高速火車脫軌後撞向另一列南下火車,總共逾500名乘客。事故疑因路軌接駁點損壞,加上山區位置令救援緩慢。
「罪行重大」,是否只看案件本身,而毋須考慮被告在案中的角色?本周的西九龍裁判法院內,這個問題落在一眾被告身上。《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以及六名《蘋果日報》高層,以及陳梓華及李宇軒,早前被裁定或承認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成,案件於本周進入求情階段。隨着法官就量刑分級多番提問,代表被告的大律師小心翼翼回應,牽動被告、家屬以至旁聽人士的情緒。▌「罪行重大」是否只看罪行本質、不看角色?今次案件牽涉的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控方援引《港區國安法》以及《刑事罪行條例》中有關串謀的本地法律條文提出檢控。根據《港區國安法》第 29 條,「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設有兩級刑罰:一般情況下可判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則可判處...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裁定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串謀刊印煽動刊物三罪罪成,法官星期一開始聽取黎智英連同其餘八名被告的求情陳詞。就本案的量刑原則,法官李運騰多次提到本案量刑只有考慮被告是否「罪行重大」一個條件,關乎罪行本身,沒有提及「首要分子」,顯示各被告在案中角色似乎對量刑影響不大,這或將直接影響案中其餘被告的刑期。 黎智英上月被裁定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串謀刊印煽動刊物共三罪罪成,而六名前高層包括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蘋果》總編輯羅偉光、《蘋果》副社長陳沛敏、執行總編輯林文宗、主筆馮偉光及主筆楊清奇,以及律師助理陳梓華及李宇軒則分別承認一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 ▌重大罪行刑期10年或以上 控方今陳詞指,本案所牽涉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庭須考慮被告是否「罪行重大」。 法官李運騰指,「罪行重大」字眼分別在《國安法》的三條條文出現,包括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以及勾結外國勢力罪條文,而前兩者涉及三個分級,即「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積極參加」、「其他參加」。前兩者的被告似乎只要符合「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條件,就可被判處終身監禁或 10...
收看節目 黎智英案進入求情階段,三位國安法官早前裁定黎智英三項罪名成立,頒下 855 頁判詞。《綠豆》法律篇,就法院定罪理據,逐項詳細分析,探討達致定罪的理據是否合理,並從法律觀點上,指出判詞未能令人信服的地方。講者: ▌陳文敏|香港大學前法律學院教授 ▌黃瑞紅|大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