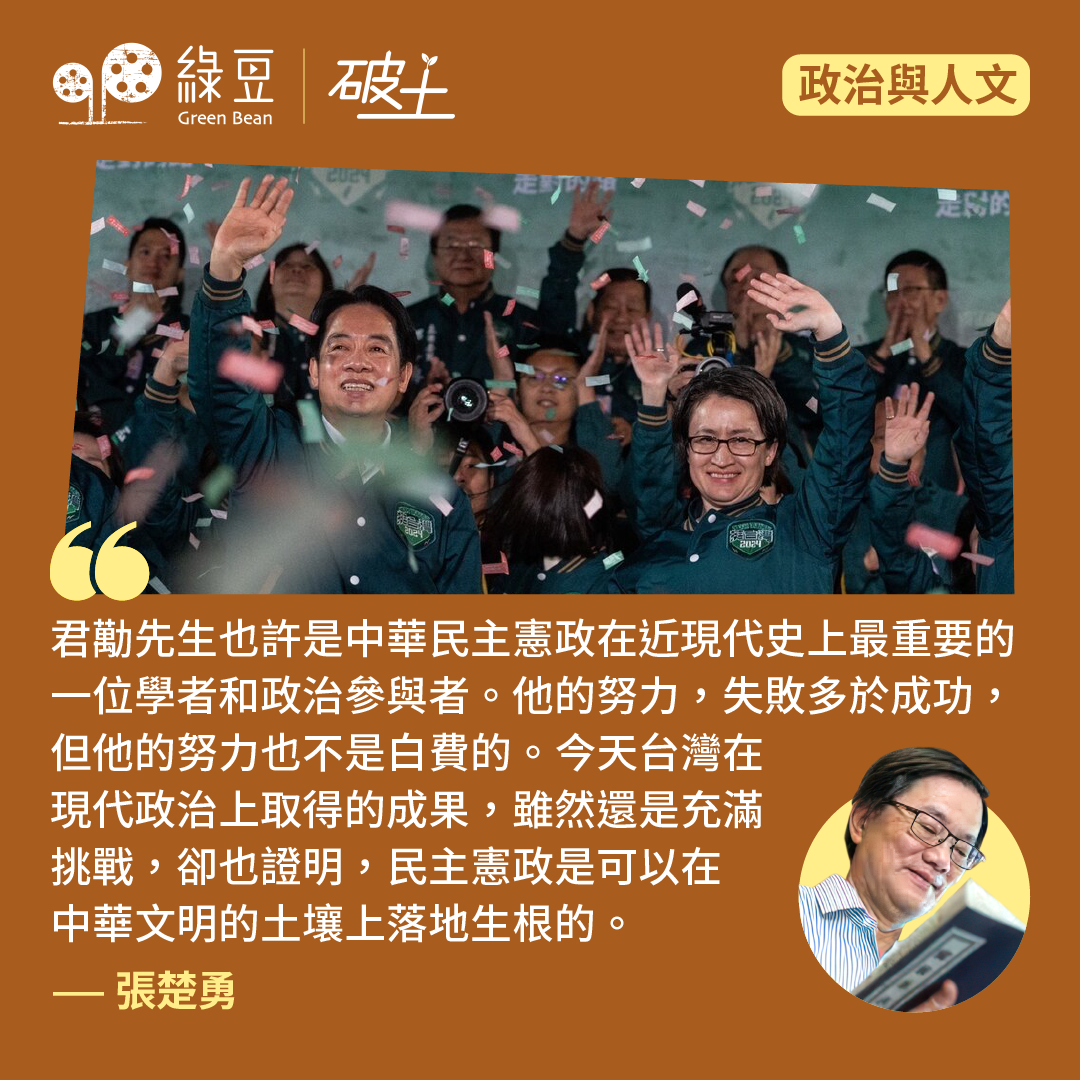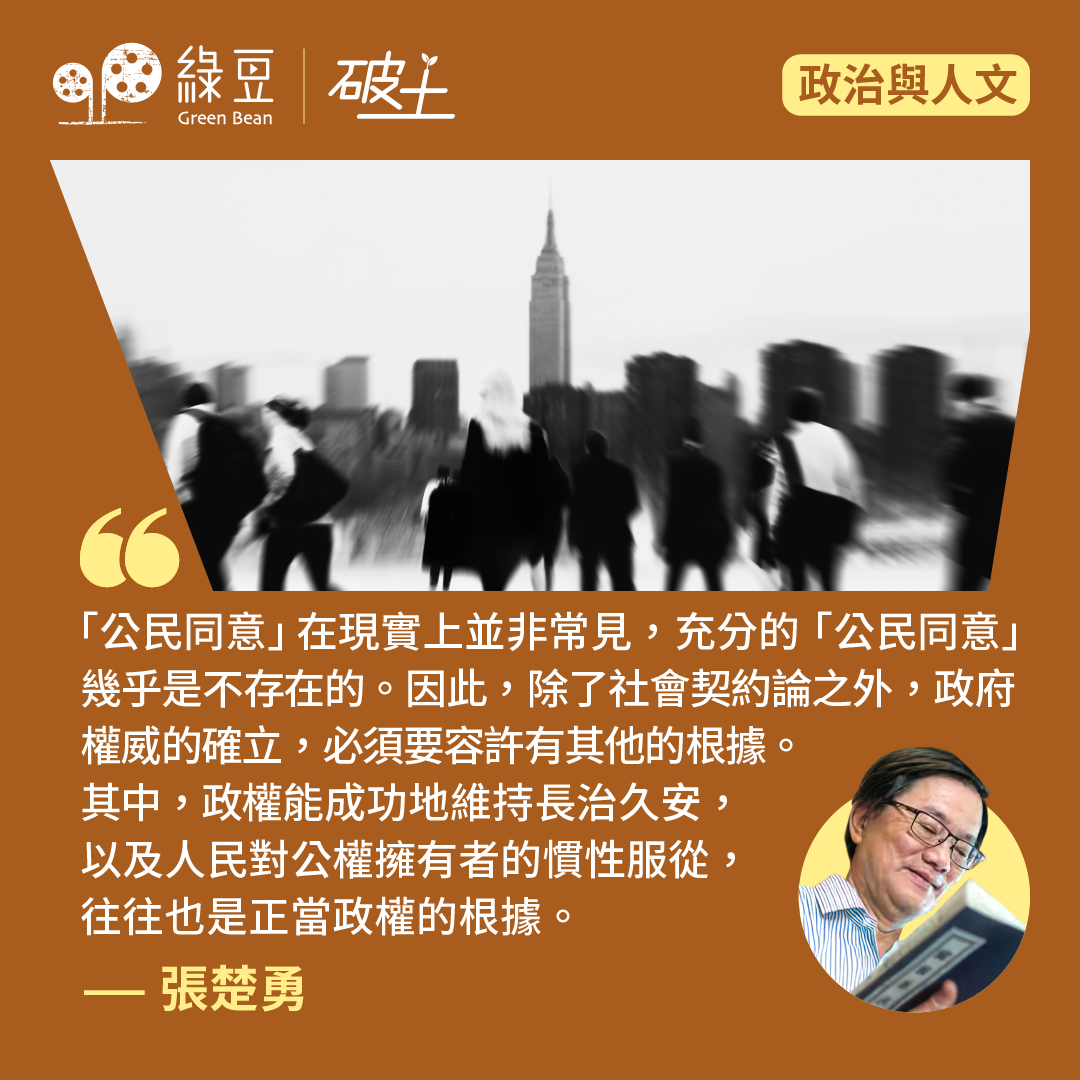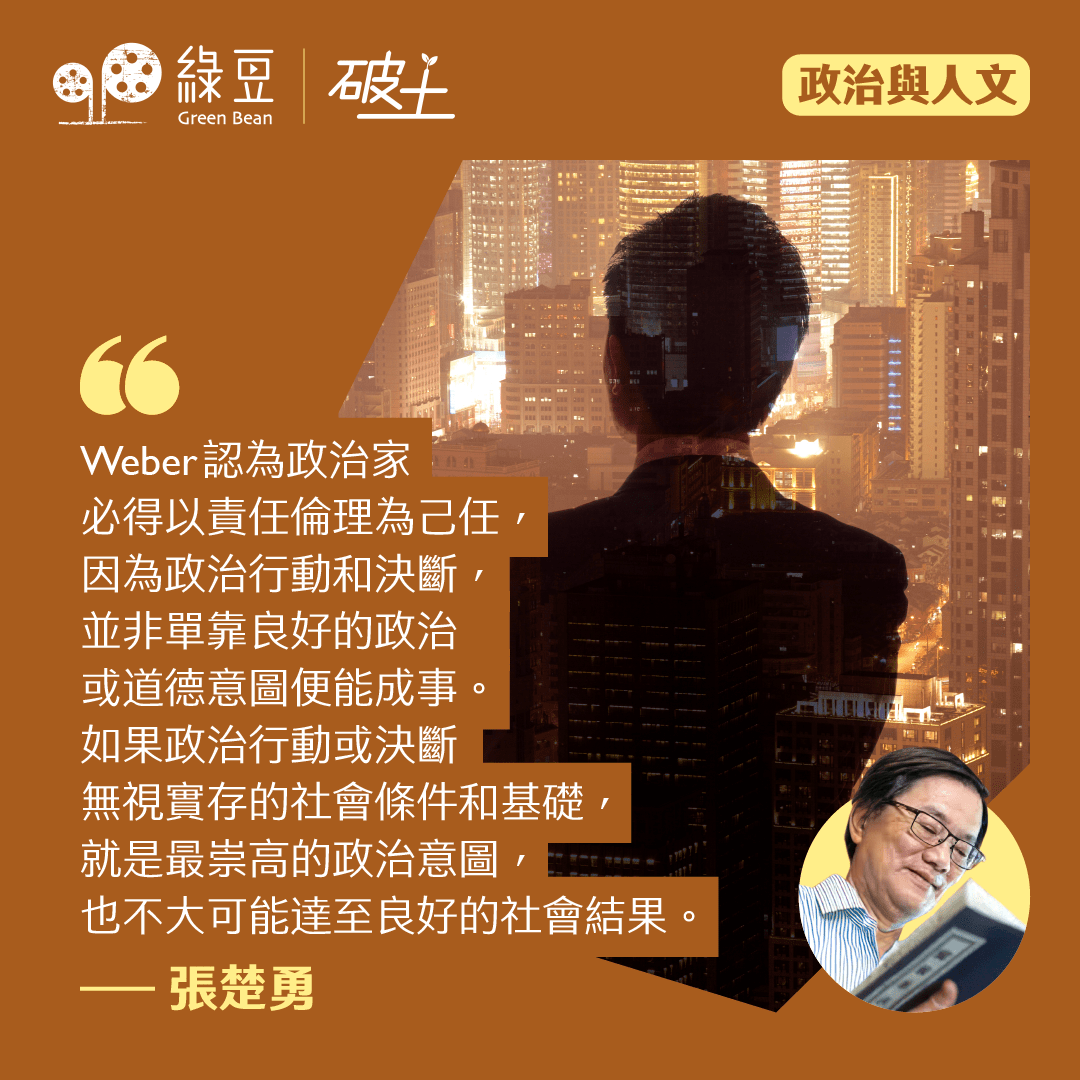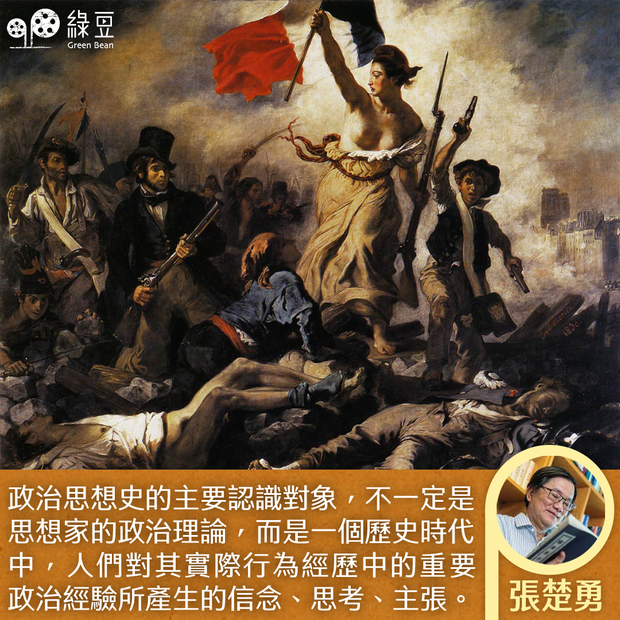20世紀英國學者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形容哲人是「受思辨所害的不能自拔者」(victim of thought)。他的意思是說,哲學思辨是一種對所有思想內容背後的根據或前提的假定,不斷進行尋根究底式的知性拷問。任何結論,在哲學上都是臨時的。因為除非我們停止思考,否則,所有思辨在過程中達至的有關結論,其背後的根據或前提的假定,總是可以作出進一步和更深一層的探索。因此,嚴格說來,哲學思辨是個無涯涘的追尋。哲人對思想的拷問,是一種不斷啟航的知性釐清和加深認識的行為。哲人在這旅途到達的所有目的地都是過客。因為哲人會對到達了的目的地可能引發出的、未被探索的新路徑或潛在的通道產生不能自拔的好奇,於是便不能自已的再走上思辨拷問的征途,邁向無涯涘的思考。 哲人如果不能在他生活的所在地進行哲學思辨,或者他那不斷尋根究底式的知性拷問活動,受到了掌管公權者的禁制、懲處,甚至迫逼其思辨活動服務於當權者的政治目的,那麽,哲人為了忠於其無涯涘知性的追尋,便有可能被迫流亡。否則,哲人很可能從「受思辨所害的不能自拔者」,變成是被政治迫害成為工具者,因而無法繼續進行真正的哲學思辨。 被迫流亡在外的先輩 我和本書作者張燦輝都是在戰後香港成長的一代。張燦輝是我的學長輩,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我自己則畢業於香港大學,修讀的是哲學和政治學。我們這些在戰後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看到香港1949年後,成為了來自中國大陸不少哲者學人和文化先輩的流亡地。這些華夏知識人,基於種種政治或文化的因由,其思想或作為不容於掌控公權的黨國體制,因此只能避秦於這大陸南端的英國殖民地,否則便不能繼續他們在思想上和文化上自主的追尋。...
撰寫這篇文章時,紀念1911年辛亥革命的雙十節剛過去了。 辛亥革命是中華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這場革命結束了中國維持了數千年的君主制。雖然革命後建立出來的中華共和國並不是很有良政善治的實效,但其政治意義卻標緻著中國從此脫離了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帝皇集權制,進入了邦國公民主權為中心的現代政治文明經驗。 宣揚發展及落實憲政 辛亥革命的初心,是要推翻滿清的專制皇權,在中華大地建立憲制民主的共和國。1912年清帝和平遜位後至今的一百多年的政治經驗卻說明,憲政民主的發展在中國是荊棘滿途,期間更經常受到來自邦國救亡和民族復興的需求所挑戰。因此,憲政民主之道在近現代中國的努力,總體而言,是並不成功的。到今天唯一例外的,是目前民主的台灣。而台灣當下的憲政民主制的其中一個重要根據,便是在1946年主要由張君勱先生為國民政府草擬,在1947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 也許,在近現代中國,在宣揚、發展中華憲政思想和在現實政治中推動和落實憲政這一重要的範疇內,君勱先生的貢獻是最突出的。年輕的君勱先生,在晚清和民初時便已跟隨梁啟超主張憲政。他生平發表的第一篇著作,便是在1906年留學日本期間,刊登於梁啟超流亡在外時主編的《新民叢報》的〈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John Stuart Mill...
極右政治對西方自由民主邦國的挑戰,除了間或爆發像今年7、8月間,在英國多個城市因惡意散播假消息引發的反移民暴力騷亂之外,更為根本的是,傾向極右政治的政黨及其政治,在今天這些邦國中,似乎已日漸成為主流和常規政治的一部分。最近期的一個例子,是今年9月1日德國的地方選舉,其極右政黨AfD(德國另類選擇黨)在東部的Thuringia邦成為得票最多的政黨,取得88個邦議會議席中的32個,成為該邦的最大黨,比佔第二得票最多的中間偏右的CDU(基督民主黨)多出9個議席;在鄰近的Saxony邦,AfD的得票率也僅以些微的差距屈居第二,取得120個邦議會議席中的40個,比排首位的CDU僅少了一個議席。AfD在德國東部兩個邦各取得約三分一的選票,比不少主流政黨還要多。這更是自納粹德國以來,首次有極右政黨在德國的議會選舉中,成為得票最多的政黨。數天前奧地利極右的Freedom Party(自由黨)在全國大選中取得29%的選票,成為得票最多的政黨。這一發展比AfD在德國的地方選舉勝出更具意義。此外,今年6、7月在法國國會大選的二輪投票中,極右的RN and allies(國民集結及聯盟) 贏得了超過37%的選票,也是比其他單一政黨都要多。雖然上述這些極右政黨未能取得過半數的選民支持,加上其他政黨聯手在議會中拒絕與他們結成執政聯盟,這些極右政黨因此未能執政。但如果我們判定,現在極右政治已在這些地方變成了主流政治的一部分,似乎已是不爭的事實。就是在英國,相對激進的右傾政黨Reform UK (英國改革黨) 在今年7月的國會大選中,也取得了超過14%的選票,成為繼工黨和保守黨外得票第三最多的政黨。其會員人數,在大選後也以倍數的增幅達至8萬人,使傾向極右的政治在英國也變得愈來愈重要。愈來愈跟主流政治分不開以研究極端政治為主的歐洲學人Cas...
極右民族主義的民粹政治和擁抱多元文化的普世政治,自18世紀以來,一直處於緊張關係。 上世紀30年代,極右民族主義中的納粹和法西斯政權的崛起,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場慘烈大戰的結果,是納粹和法西斯政權的全面潰敗,而這些政權在執政和戰爭時期犯下的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例如對數以百萬計猶太人進行有系統的種族屠殺,使在戰後重建世界政治秩序的主要邦國,決心要避免重蹈覆轍(即當時大家用英文說的"never again”),不能讓這些納粹和法西斯政治死灰復燃,因此積極地在國際間和邦國內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成立以保障世界和平為目標的聯合國、在日本通過放棄軍國主義的和平憲法、在聯合國制定國際人權公約、以及在被納粹和法西斯政權統治及佔領過的邦國内,把納粹和法西斯的主張和政治組織列為非法等等,希望杜絕這些極端而暴力的民族思想和政治。 可是,傾向極右民族主義的主張、思想、政治,甚至政黨和政權自此消失了嗎?答案很遺憾是否定的。 今年7月底,3個英國女童,在英格蘭中西部的海濱市鎮紹斯波特(Southport) 一個暑期舞蹈班上,涉嫌被一名患有自閉症的17歲黑人青年殺害後,爆發了在英格蘭和北愛爾蘭各地近一個星期接連的極右分子的暴力騷亂,這清楚地提醒人們,極右民族主義的情緒和力量,在英國是不容忽視的。他們今次能牽起這些暴力騷亂,肇因之一,正是通過網絡上刻意散播行兇者是一名在英國尋求政治庇護的穆斯林青年這一假消息所造成的。 極右領袖得勢...
17至18世紀的啟蒙運動,是歐洲知識界一次劃時代的文化運動。這運動在科學、理性、宗教、信仰、政治、經濟、文藝、技術等多個領域上,塑造了現代的文明、價值與人的心靈。啟蒙運動更通過當時崛起的歐洲強國,把這種文明、價值和心靈,輸出至全世界,成為至今仍然主導人類認知和社會發展的一種重要文化資源。1919年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揭櫫要打倒孔家店,追求「民主」和「科學」,正是這種現代世界的文化運動大潮下的一股巨浪。不少人因此稱五四運動為中國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中最有代表性的其中一句格言,是德國哲人Immanuel Kant在〈甚麽是啟蒙〉一文中所說的「敢於思考」這句說話。16、17世紀的歐洲,隨著個人從封建制度關係的逐步解脫、科學知識的建立和傳播、理性思辨的抬頭,在知識界慢慢形成一種深具批判力的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著重運用理性思維,以確立辨別是非對錯的標準和方法。這種標準和方法對傳統的信仰、道德、知識、政治、社會等權威造成了愈來愈重大的挑戰,新的知識精英日益認為,這些傳統權威如果經不起理性標準和方法的批判考驗,那便是代表這些權威只是人們的迷信或偏見,既不能反映客觀真實的世界,而且更阻礙理性認知的建立和人類心靈的進步,使社會發展未能朝向更文明更開放的道路邁進。要改變這種現狀,知識界和社會的進步精英便得為社會大眾進行啟蒙,而啟蒙的要點,正在於個人必須採納理性的標準和方法,敢於思考,挑戰未經啟蒙考驗的傳統權威,為人類和社會帶來福祉。啟蒙運動的輸出歐洲17、18世紀不少的傑出思想家、科學家、文化人對啟蒙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其中法國和英國知識精英的貢獻尤其突出。Rene Descartes、De Voltaire、Baron de Montesquieu、Marquis de...
2024年5至6月期間,我有機會前往台北參與一些學術活動。抵達台北的5月20日,正好是他們新當選總統的就職典禮。臨行前我在家中想到,不如帶上張君勱在1946年為推廣中國當時制憲的努力而寫成的《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一書,在旅途中重讀一遍。 追尋民主憲政的沉重代價 1946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憲法》在南京國民政府主催下,於國民大會三讀通過,張君勱是主要的草擬者。憲法在1947年底正式在中國實施。後來國民政府在內戰連連失利,最後敗走台灣,蔣氏政權於國共兩黨軍事對峙下,以緊急法令凌駕了此憲法的部分條文,變相繼續實行威權統治。 但隨著1980年代後台灣的黨禁解除,民主化逐步在當地推行以來,張君勱草擬通過的這份憲法,在經過歷次重大修正後,至今還是台灣民主政治上的憲政根據,也是自晚清以來130多年的中華立憲史上,唯一成功通過和仍在實施的中華民主憲法。張君勱因此被稱為是「中華民國憲法之父」。 民主憲政的追尋,在中華大地上不單是荊棘滿途,投身者往往更要付出重大的代價。張君勱這位為國民政府立憲的中華憲法之父,在1949年內戰勝負分明時,便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為頭等戰犯。敗走台灣的國民政府對他也並不友善,例如在立憲以前,因為他的主張、組織政黨活動和言論等,國民政府便曾派遣國民黨特務人員把他禁錮了一個多月。張君勱也曾經受到當權者的暗殺威脅和軟禁等對待。追尋憲政民主者被執政者視之為是公敵,這在近現代的中華大地,屢屢發生。 劃時代的成果 如果我們不只以短期現實政治的得失論一個人的成敗,我覺得張君勱先生在近現代中華政治歷史中,他對民主憲政的堅持及所取得的成果,可以說是劃時代的。...
現代政治的一個主流論述,是政權的正當性得建基在「公民同意」之上。「公民同意」的理據,簡要說來是這樣的。政府之所以有權作出強制性的集體決定,例如立法、制定政策、推行政令,是因為政治社群中的個人,為了有穩定的秩序,讓大家和平共存,便得在社會上實施集體而共同的規範使大家遵行,以避免沒完沒了的衝突、糾紛、緊張失序等無政府狀態。大家因此同意,放棄部分個人與生俱來的自由,並推舉一些人有權去行使公權,掌管公職,以便公正地保障社群各成員的安全和促進社群的福祉,制定法律和規範性措施,以應付集體所面對的問題和挑戰。 社會契約論根據這種看法,正當政權的建立,正是從這基礎引伸出來的。社群中的每一個成員據此同意服從政府為集體所作的決定,並承認其權威和公權力。我們一般稱這種說法為社會契約論。社會契約論把政權的公權力及其權威建基在「公民同意」之上。但是,假如政府未能履行社會契約中的要求,公正地保障公民的安全、生命、財產、權利等等,公民便沒有義務繼續服從政府,嚴重者公民更有反抗的權利,革掉暴政的命。社會契約論處理的根本政治課題是多樣而繁複的。有關的哲學和理論論述更是博大精深,是任何想認真了解現代政治的學人必須好好地去鑽研。我這篇短文,自然無法對這些課題和論述觸及於萬一。有留意西方現代政治思想發展的讀者大概都知道,與社會契約論有關的幾位最重要的經典理論家,是英國的Thomas Hobbes和John Locke,以及法國的Jean-Jacques Rousseau。不少論者認為,這理論開啟了現代政治的範式(paradigm),因為人類政治的重點,從此由集體轉向個人,以個人同意、權利、自由等為公權力和政治權威正當性的根據,取代了以前的君權神授論的基礎,也把優良管治的要求,從追求至善的社會,轉移到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保障,從而開創了現代個人主義式的民主自由政治的格局。 「公民同意」是否必須?對於社會契約論中「公民同意」的一個直接而重要的批評,也許可以簡述如下:假如政權能有效地為政治社群帶來穩定和秩序,使各成員和平共存,遵守共同的規範,避免沒完沒了的衝突、糾紛、緊張失序的無政府狀態,那麼,「公民同意」是否必須的呢?就算「公民同意」在正當政權的建立中是可取的,但「公民同意」是否唯一的正當政權的根據?對上述這些問題的思考,讓我們看看18世紀蘇格蘭的重要思想家David Hume在他的名著 Of the Original Contract (〈關於原初契約〉)...
早些時候,我在本欄的《威權政治與法治:現代邦國的兩種形態》一文中,介紹過英國20世紀政治思想家Michael Oakeshott關於法治邦國和威權邦國的論述。今天,我想談談他對歐洲政治思想史的一些重要貢獻。我根據的文本,是2006年出版的《政治思想史講座》(Lectures in the History of...
《通向奴役的路》(The Road to Serfdom) 在1944年3月和9月二戰期間先後在英、美兩國出版。出版後,始料不及的,是該書即時使英籍奥地利裔思想家 Friedr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