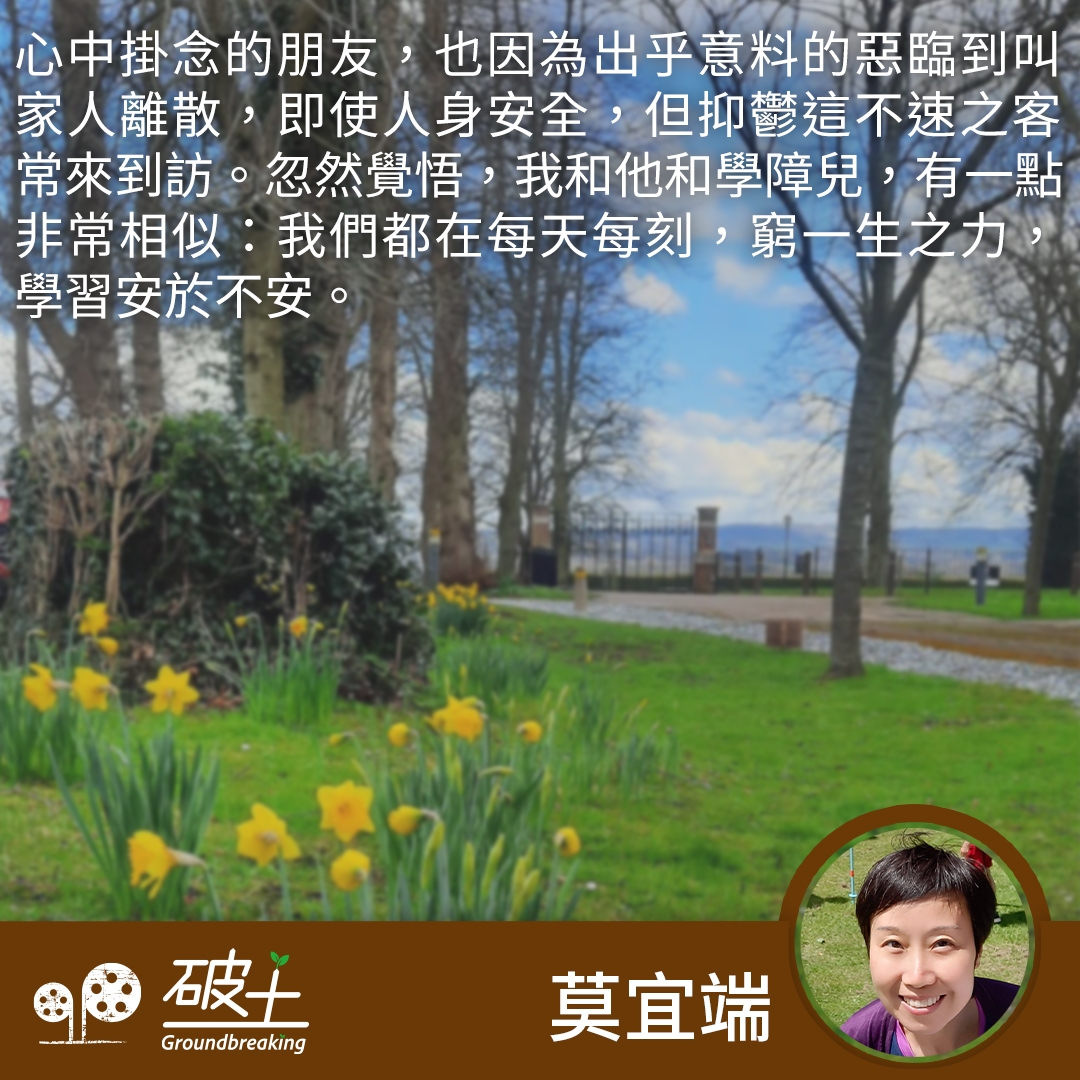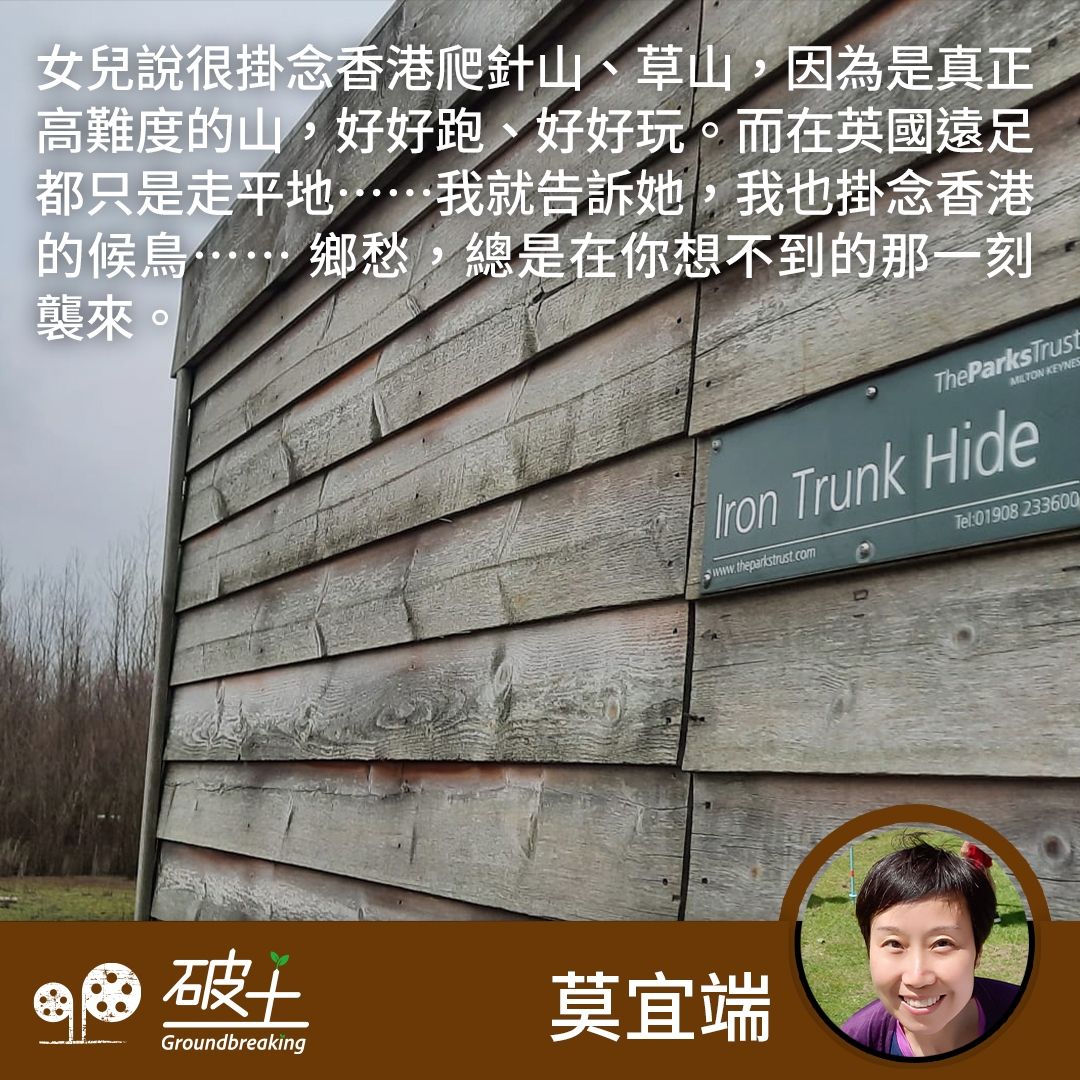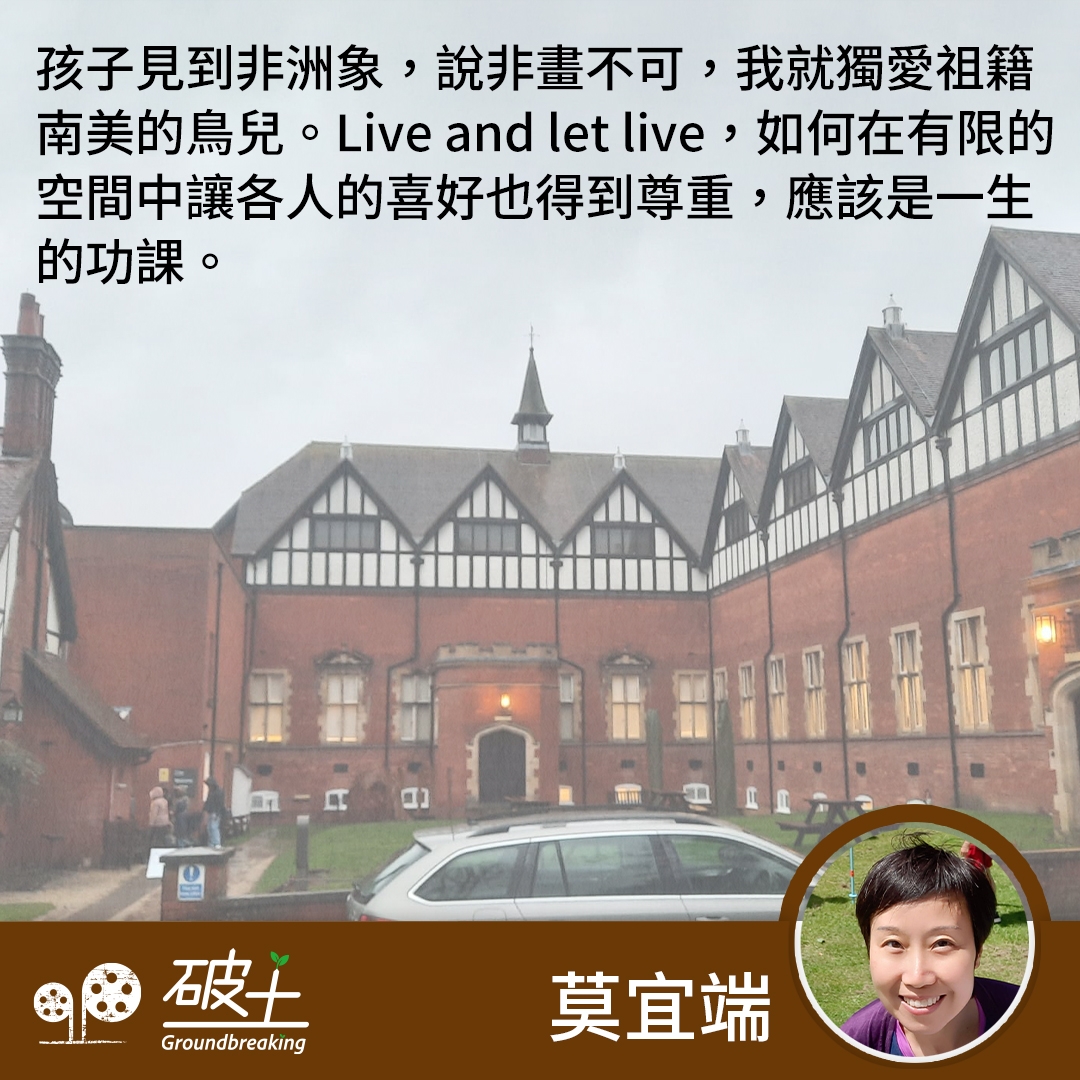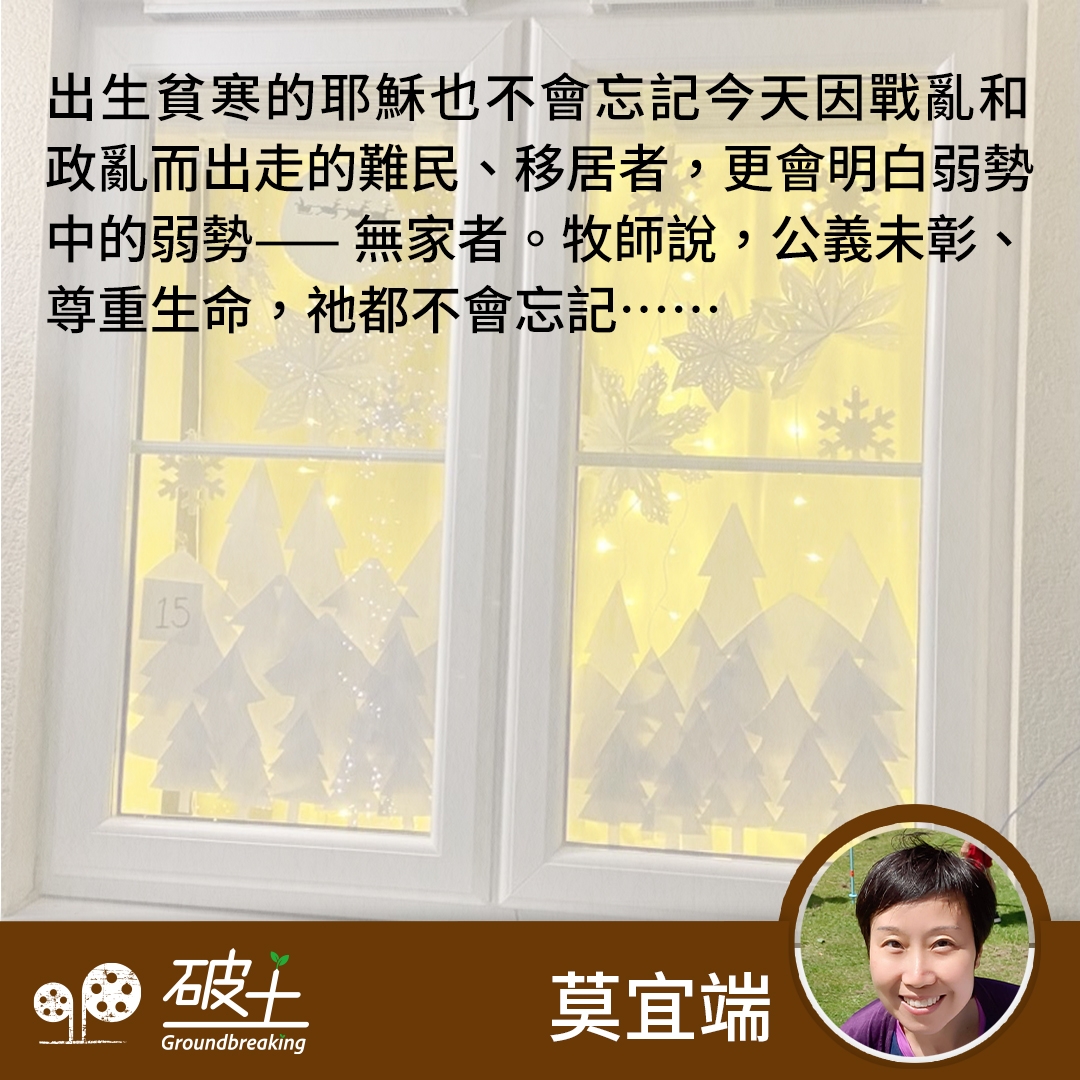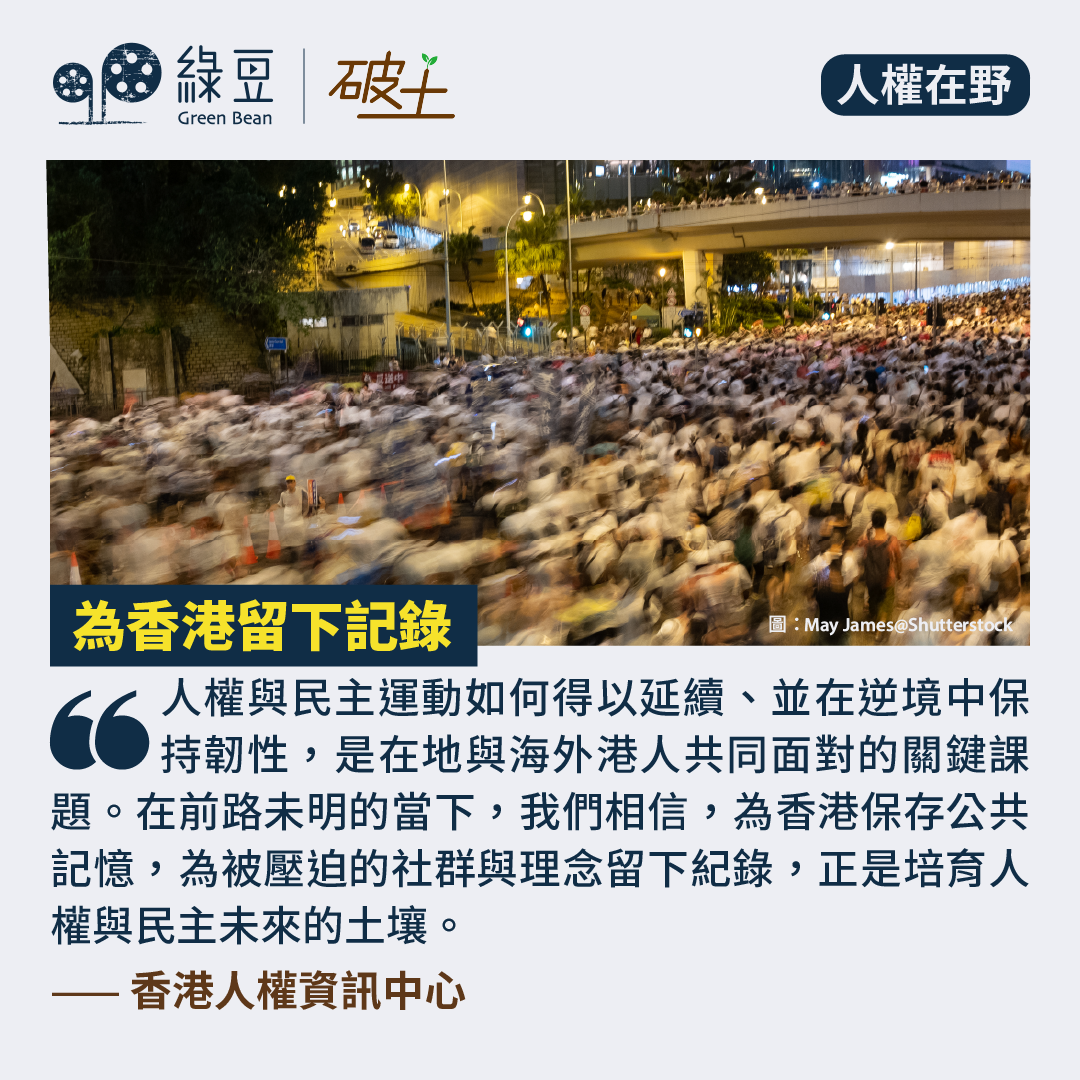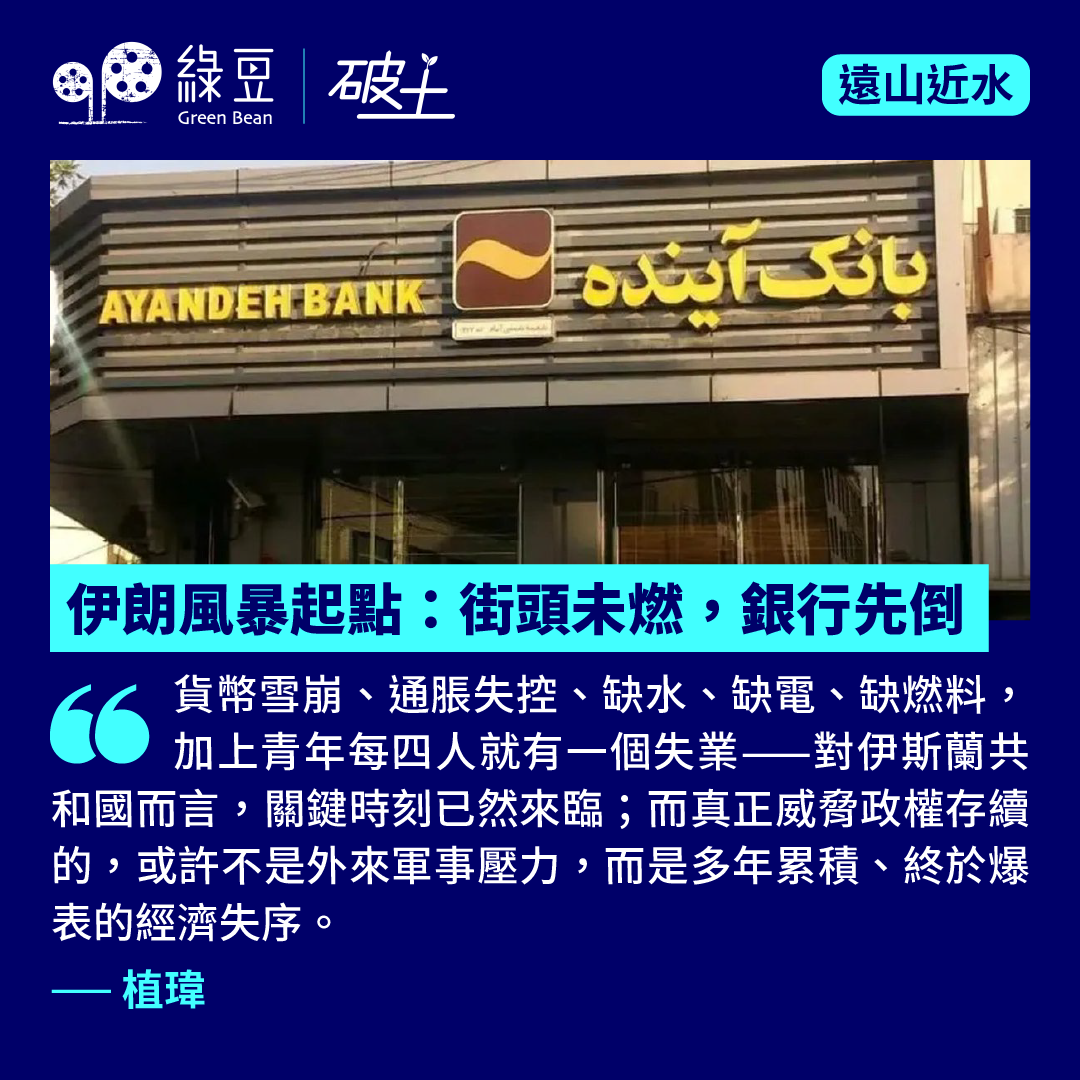有人問,在英格蘭做言語治療師,是否比在香港舒適?會準時收工?不會寫報告寫到手軟? 我的答案是:時間安排和作息的確是比香港人性化,也準時收工,但報告和文書工作不會少(其實要求可能更嚴緊、量會更多)。 或許曾做助人專業的香港朋友,如教師、心理學家、治療師也會有類似的感覺,就是這兒高舉對受助人的權利,所以若未完全理解這兒的人本想法,做教師、教學助理或入校的專業支援同工,想必會對接觸的SEN兒童/青少年心存畏懼,交流和教導期間步步為營。不過,若能不太快對有身心障礙的學童下結論,一步一腳印,讓SEN學童/青少年因我的同行體現作為一個人的權利和價值,不僅得到彰顯也能被真正看重,那種畏懼感自然會減少,工作亦能更投入。 於我,從少年人的反應中,我學到的更多。我或許透過不同的實證方法,有條理地提升他們這樣那樣的溝通技巧;但學生言行給予我的,有時更是有著醍醐灌頂的感受。 勇敢說不 還記得一位同學T,祖家是非洲一多難之邦。10來歲、沒有口語能力的自閉和過度活躍症兒,更是從小就跟家人以難民身份來到英國,接著住過不同的寄養家庭,也經歷創傷。T在這寄宿學校已有幾年時間,非常喜歡跟人互通,與他做訓練不愁冷場或欠缺反應。不過,相處了兩個月,發覺T雖然用其輔助溝通軟件(Alternative...
收看節目 在香港連根拔起,來到英國落地重生。找工作應是大部分移英港人遇到的問題。「英文程度不賴,又高學歷,在這裡工作就沒有煩惱?」莫宜端告訴你,即使是重操香港的故業,這些其實都是假象。 搵工要有一份「屢敗屢戰」的念力,有工做的,亦要學「做鹽」,香港人,加油! ...
二月,聽本地人說Snowdrops雪鈴花盛開,代表濕冷冬天終於來到尾聲。所以即使返工未能像上一份工作般,可跟學童一齊放假,但趁學校half term完結之前,都走到白金漢郡的莊園田地,追蹤雪鈴花的蹤影。 漫山片野的小白花,象徵春天真的不遠了,令人心存盼望。這也剛好是返新工滿三個月的日子,又剛搬了屋,借賞花親親大自然,當是慶祝。 郵遞中心通宵更 說起工作,做人最緊要是有希望。最近與相熟的朋友聊天,都感覺找工作並非易事。特別是跟我們一樣,並非住在大城市的,要找到合適的工作確是需要耐性,也需要一份「屢敗屢戰」的念力。就像外子和一些男性朋友,本來在香港均具專業資格,來英大半年忙於展開生活,顧好衣食住行,或許未急於搵工。不過,有孩子的,待子女學校、社交圈子慢慢適應下來、手上盤川越來越少、物價騰飛,總希望投入職場,半職兼職都好,掙最低工資也好,總比整天只忙著家頭細務踏實。 外子為了遷就現在做全職的我,目前只可找兼職的差事。原本有專業身份的他,試過面試超市倉務、理貨員,又申請過工業區貨倉工作。最後找到在市內一郵遞中心通宵分發郵件的臨時工。他為了日間可以照常包辦子女的接送,心口掛「勇」字返通宵更。還記得第二晚他晚上九時許出門開工,女兒見著父親離開的身影便哭起來,我摟著她,她說想到自己可以睡覺,但爸爸卻要做工,好傷心。翌日,做父親的頻說「不辛苦」、「不打緊」,還繼續一星期兩天,到博物館做維修義工,但另一邊廂,卻說頸痛腳軟,因為推著車,不斷來回運送大大細細的包裹,對做開文職的他確有點吃不消。...
收看節目 莫宜端與家人響應Big Garden Bird Watch雀鳥普查活動,到離家不遠的人造濕地觀鳥。母女在附近走走,女兒說懷念可以在香港爬高難度的山,莫宜端則記掛米埔的黑臉琵鷺,即使觀鳥時看到以前在林村河都常見的小白鷺,但數量差之千里,難抵突然來襲的鄉愁。 ...
收看節目 英國天氣變化莫測,周不時因風大雨大而要停止戶外活動,但不阻莫宜端帶孩子外出的決心,更讓她找到離家不遠一處隱世動物標本王國。王國隱藏於一座維多利亞式大宅內,原是一個猶太裔富家子21歳的生日禮物。單是大宅本身,已有相當的故事。
以前在香港,每年的農曆年前後,我家都會留意米埔自然保護區何時有開放日或導賞活動。因為每年這個時候,都是觀賞由西伯利亞到香港過冬的候鳥的好時機。前幾年,還買了雙筒望遠鏡,似模似樣的細看雀鳥的形態。一想起遠在英倫,未能再探米埔的黑臉琵鷺,就心有戚戚然。連在城門河畔、林村河都常見的小白鷺,現在也少見。就在這時,大兒子說,學校響應皇家保護雀鳥協會(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
自大學時代拜訪倫敦South Kensington的自然歷史博物館,當人們簇擁著出名的恐龍化石和骸骨,我總愛看不同的動物標本——絕種的、未絕種的、大型的、細小如蜂鳥的。總是覺得做得細緻的標本,就像一隻活著的動物向人們說話,很美,很有故事。不過,倫敦知名博物館總是遊人如鯽,DODO鳥標本前的人海,不下於羅浮宮蒙羅麗莎前,以我的高度,真的連條羽毛都看不到。於是,我這個留學生總是鑽去一些少人去看的標本堆中慢慢欣賞。 今日今時,住在城鄉之交,要滿足我這個博物館癡原來也非難事,只是不能常去名氣大的地方。2022年最後一天,雨天、風大,戶外活動要暫停。搜索一下,得知自然歷史博物館原來離我家大半個鐘車程有一個分館,也是免費的,只需要網上預約。心想反正曬不了太陽,去看看在Tring的自然博物館,也是消磨時間的好地方。 去到這個維多利亞時代建成的動物標本王國,真是驚為天人!它展示的標本、物種之多,及館藏原擁有人的故事、動物標本的背景,煞是豐富。 21歲的生日禮物 位於白金漢郡Tring小鎮的這座維多利亞式大宅,原屬猶太裔銀行世家Rothschild家族所有。Walter...
收看節目 來到英國一年多,莫宜端轉工了,她獲聘到一間特殊寄宿學校任駐校言語治療師。她提到上工開初,要參加多個令人望而生畏的新員工訓練課程,但後來發現課程彩蛋處處。 《破土》原文見綠豆Patreon:bit.ly/3WTSuYU ...
收看節目 莫宜端聲音導航,提到跟孩子到約克York的國家鐵路博物館(National Railway Museum)的大發現。原來鐵路博物館不單只是坐坐小火車,還包含英國段段歷史,以及背後有血有肉的故事。 ...
臨近聖誕,不論是孩子同學的家長,抑或為人父母的同事,都互傳訊息找一些又經濟又有節日氣氛的活動。在英國很多城鎮都有聖誕市集,也有專為兒童而設,把農場或古宅打造成的聖誕村,吸引大人細路到訪。只是大部份的聖誕熱門活動,都主打聖誕老人、飄雪場景。聖誕那個生於馬糟的耶穌,似乎消失在鋪天蓋地的商業噱頭中。還是在本地基督教會,和相關的鄰舍連結中,才令人真正細味聖誕的因由。我上的教會剛成立於新建社區,是浸信會背景。12月伊始,教會的崇拜時間搖身一變成為MESSY CHURCH(非一般教會)主日,早幾星期已經在社區宣傳,希望更多鄰居認識教會、認識聖誕慶祝的唯一原因 —— 主基督的降生、犠牲和救贖。MESSY CHURCH——顧名思義,就是借不同的活動,讓人大細路不怕凌亂、放心放膽玩創作、做手工,教會的信徒就分享信仰,邀請大家一同紀念聖誕。但是,籌備過程中一位教友真是字字珠璣,他說:「有人的地方,就必然會亂。每個人每個群體都是非常messy,加起來根本就是罪人一群,這就是messy church的最重要一點。我們有幸能在一起敬拜、互相尊重,只是靠上主的恩典,不是出於自己的德行或功勞。有這種覺悟,就會更坦誠地分享,是甚麼令我們messy但不會crazy,還可以有盼望。」My worries經這位朋友這樣一說,像點通了我們任督二脈,不再介意自己來教會只幾個月,連孩子都說要幫手負責手工檔,一同事奉。於是我們一家就跟大伙兒一起,跟新朋友聊聊天,玩遊戲。我負責的攤位豎立了一隻紙版驢仔,因為當年大肚馬利亞就是騎驢作交通工具。紙版驢仔駄著兩個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