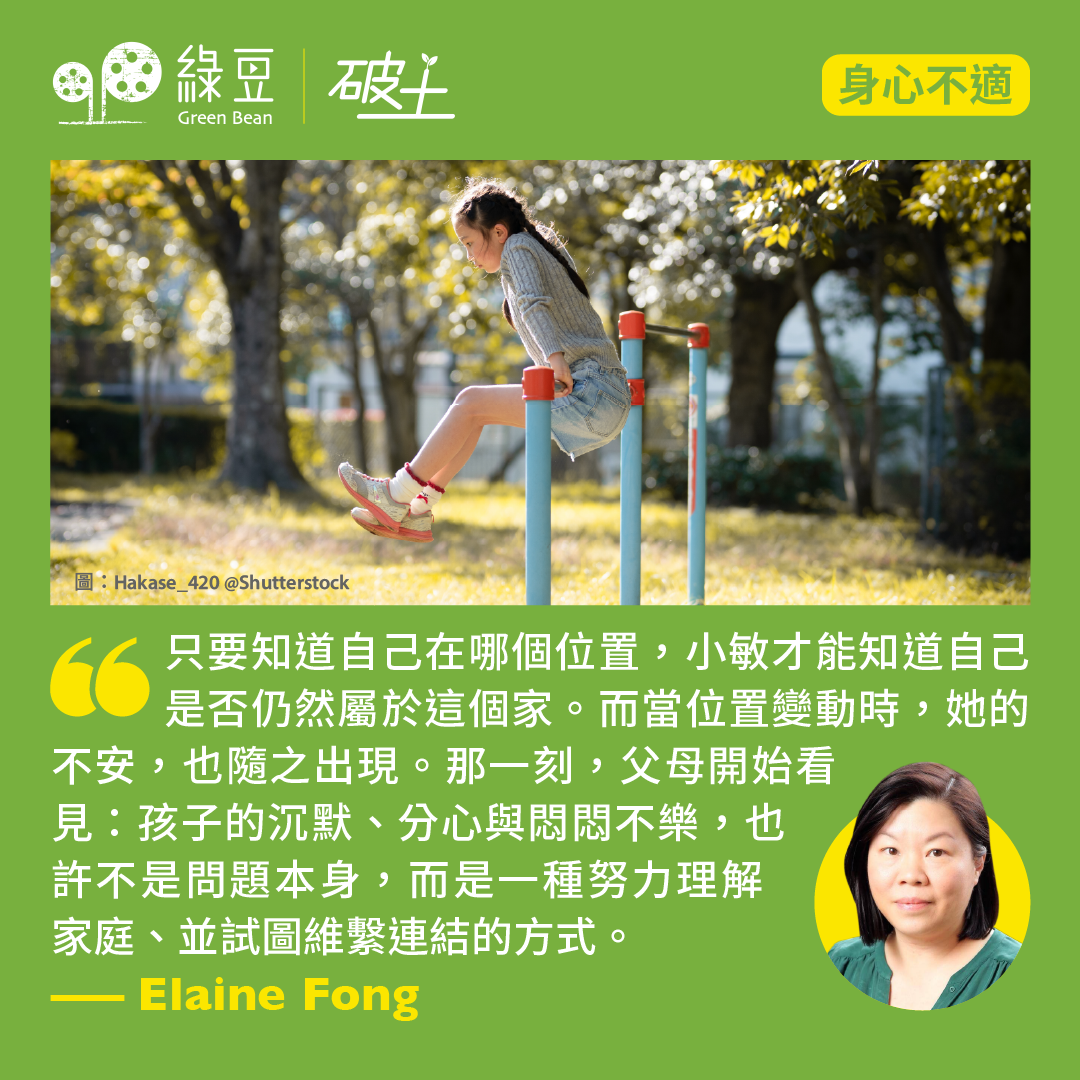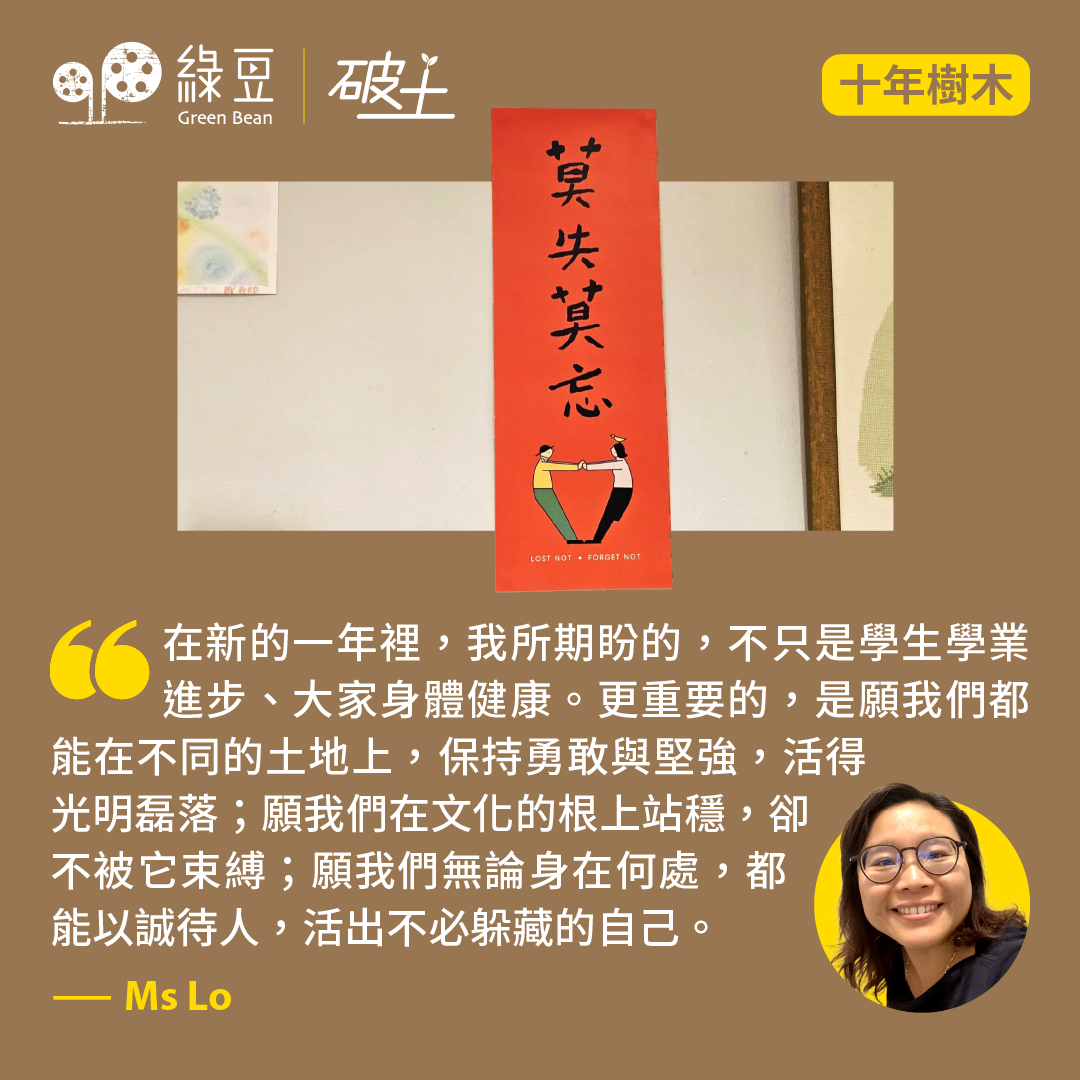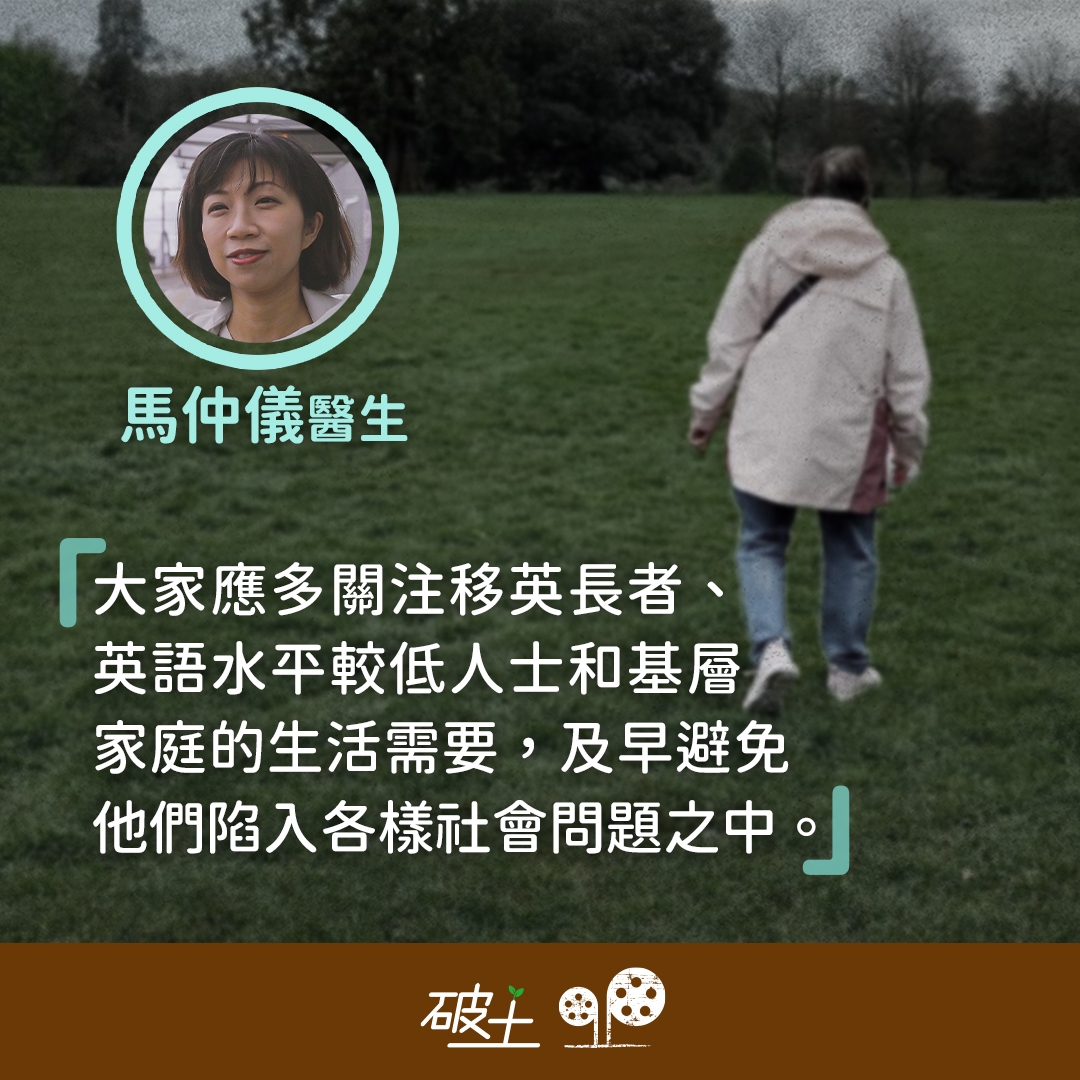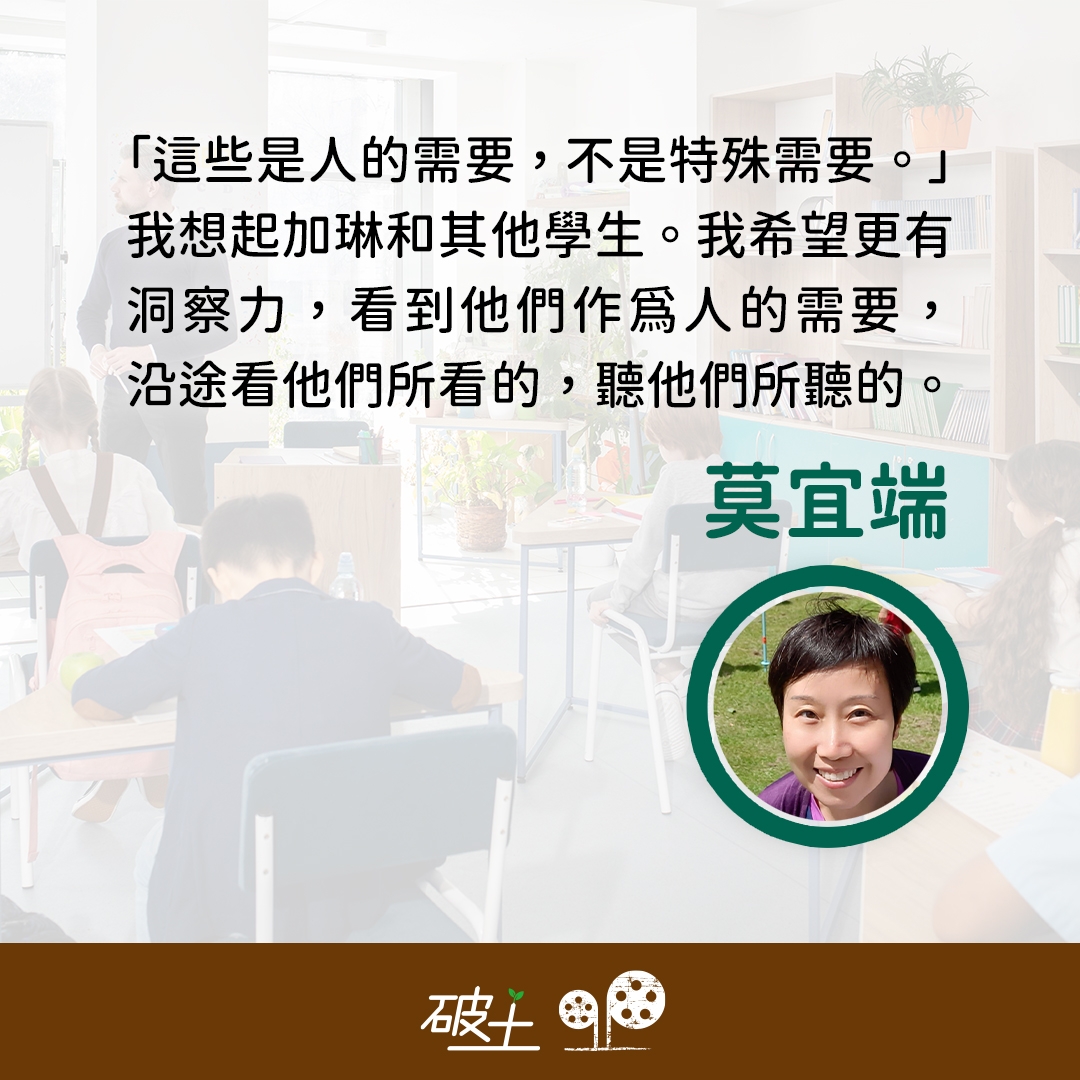貨幣政策的「酒碗」與選舉政治的「重鎚」 ——談聯儲獨立性的危機與鮑威爾的歷史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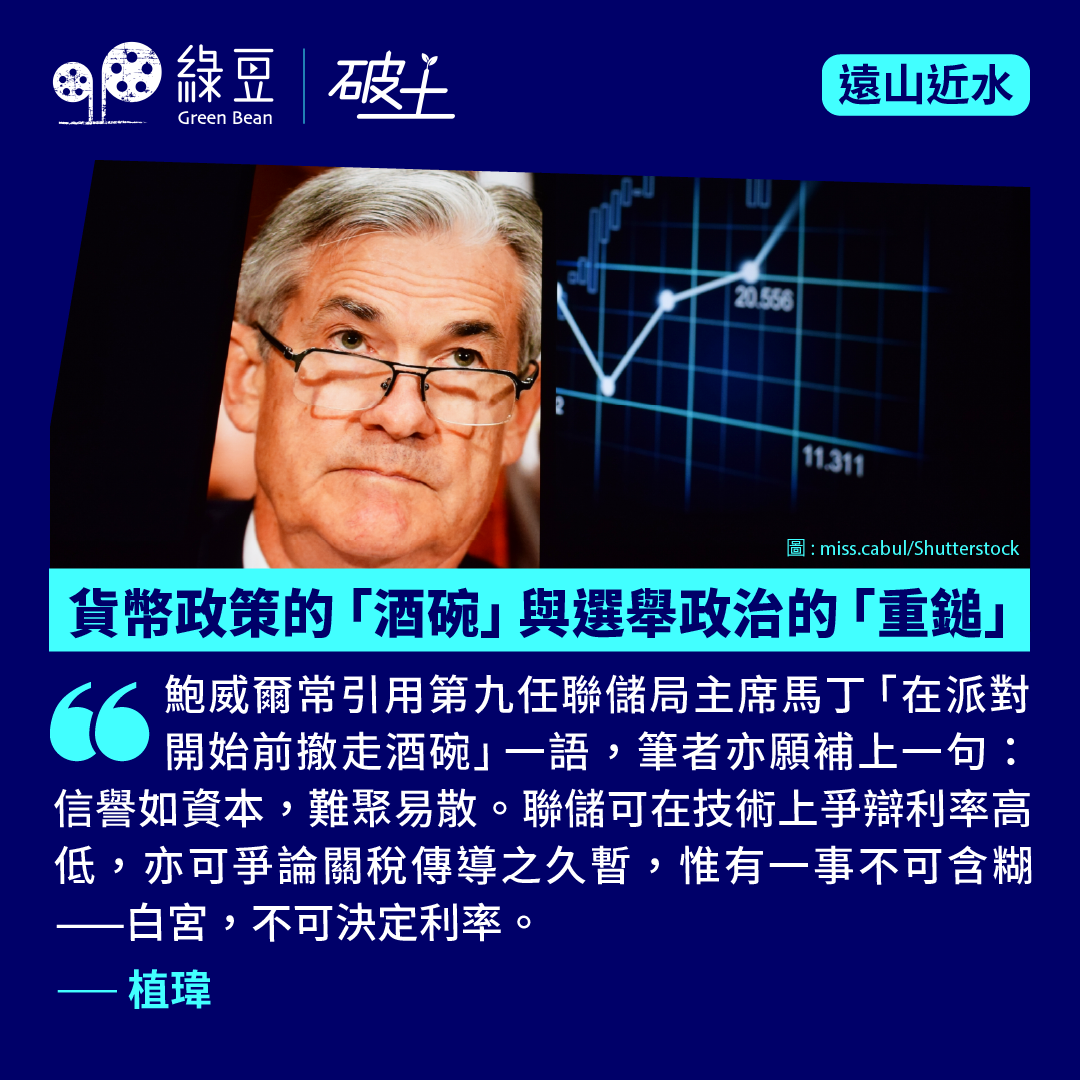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將於本周二、三(7月30日至31日)召開例會,市場焦點無疑是聯邦基金利率會否下調0.25厘。惟較利率決定更受關注者,乃聯儲局能否維持其「制度性中立」地位,抵禦來自白宮愈趨急切的政治壓力;鮑威爾(Jerome Powell)此役乃是為後伏克爾(Paul Volcker)時代延續數十載之貨幣政策獨立性立下最後防線。
若說利率是技術操作,獨立性則為制度根本。今次會議不過是市場對美國央行「能否一如既往堅守原則」的公開大考。
四分一厘之外的真風險
表面看來,是減息與否的技術爭論;實則背後隱伏的,乃市場對政策決策機制信心的鬆動。假若投資者開始相信利率變動不再純以通脹與就業數據為依歸,而轉由總統競選節奏所驅,則四分一厘的實際影響,遠不及信譽損失來得深遠。
屆時,美債長端收益率的期限溢價或急速攀升,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穩定預期亦將動搖,而聯儲的「2%通脹錨」將淪為空談,市場將重新評估央行意志是否堪信。
此類「信念危機」一旦萌芽,便難根除。投資者之疑心,非四分一厘可息。
委員意見分歧 白宮干預頻仍
7月中旬,兩位聯儲理事分別發聲,立場迥異:沃勒(Christopher Waller)認為近期通脹放緩、工資增幅下降、就業動能疲弱,足以構成減息理據;庫格勒(Adriana Kugler)則認為關稅傳導尚未完全顯現,企業目前仍以舊價出貨,價格上漲尚在路上。紐約聯儲總裁威廉斯(John Williams)則折衷表述,指現時影響尚屬溫和,但未來兩三季關稅將逐步推升通脹達一個百分點。
這種「一數多解」的經濟形勢,容許技術上出現「可減、可不減」的模糊地帶,正因如此,貨幣政策決策過程的「純潔性」愈發重要。須明確讓市場看到,若減息,是因應經濟模型,而非總統脅逼。
然而,7月23日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ant)一句話,猶如投下政治震撼彈。他直言:「政府已同步物色鮑威爾及庫格勒的接任人選。」此言一出,形同暗示「不聽話便換人」。雖然美國總統擁有提名權,但市場期望的是制度運作之正常節奏,而非選舉考量凌駕政策判斷。
歷史教訓:央行從政,代價沉重
歷史上,聯儲局並非從未受政治擺佈,惟後果皆慘烈。1972年,尼克遜政府要求時任主席伯恩斯(Arthur Burns)壓低利率以刺激選情,結果令通脹預期全面失控。至1979年,聯儲局幾乎淪為白宮之下屬機構。為重塑公信力,伏克爾上任後大幅加息,導致經濟衰退與失業率急升。
再早者,1951年《財政部—聯儲協議》正是央行與財政部脫鈎的歷史分水嶺。當時聯儲局為戰後赤字融資而強壓國債利率,通脹惡化之餘,制度亦幾近崩潰,最終雙方簽署協議,重建央行獨立性。
美國固非土耳其,更非阿根廷,不至於一夕貨幣崩潰,但制度信譽一旦動搖,美元的「過度特權」便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聯儲局若不能堅守自身角色,美國的貨幣體系亦難以長久維持其全球錨定地位。
關稅迷霧與預期轉變
當前困局,更由關稅政策增添不確定性。關稅在短期內或許對通脹影響不大,哈佛商學院的研究顯示消費者僅承擔三分之一的成本,其餘由外國供應商與本地進口商吸收。但中期而言,庫存週期與合約結構變化終將使成本轉嫁至消費者。紐約聯儲五月調查亦指出企業反應各異,有的完全轉嫁、有的部分吸收,有的甚至「不知所措」,可見價格機制亦受資訊摩擦影響。
若未來數季關稅成為滾動式成本推力,則「一次性提價」將變為「連續性上升」,通脹預期調整亦屬必然。此情況下,聯儲即使按兵不動,亦需表明政策為對抗通脹而非對應選情。
統計雜音與預測困境
再看增長數據。第二季GDP將於7月30日公布,雖受技術性反彈支持,惟私營部門需求(PDFP)恐續呈放緩。第一季GDP按季折年率為-0.5%,當中淨出口因關稅拖累近5個百分點。第二季數據若未見明顯改善,市場將進一步質疑增長動能。
此時決策難免落入「非左非右」的泥沼——減息,易被批評屈從政治;不減,又被視為政策過緊。鮑威爾若欲突圍,必須善用「政策框架檢討」之機,向市場明確表述決策邏輯與獨立精神。
小錯變大災的代價
或有人曰:聯儲以往亦屢受批評,未見市場崩潰。然今日緩衝條件已然不同。
其一,通脹預期不再堅定錨定。長期預期仍在2%附近,惟市場隱含預期顯現飄忽,反映投資者對中性利率與財政可持續性的懷疑。
其二,全球貨幣秩序已現裂痕。歐洲仍試探財政擴張底線,日本放棄殖利率曲線控制(YCC),中國則於資本管制下自救,美國作為唯一「正統」央行,其穩定性攸關全球。
其三,聯儲傳訊工具仍在改革中。點陣圖與經濟預測摘要愈發繁複,未必提高透明度。是次檢討,若為政治所染,即使合理亦難具信服力。
信譽之於央行,猶如資本之於銀行
央行資產負債表上雖無「信譽」一欄,然其運作之本,實賴信譽為支撐。歷史上,聯儲曾在伏克爾時代頂住通脹,金融危機時忍辱施救,亦曾於2022年承認錯誤並急轉政策——每一次,皆是向市場提款或存款。
數據導致減息,是一筆存款;總統施壓而減,是一筆提款——且遠非區區四分一厘之微。
鮑威爾常引用第九任聯儲局主席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在派對開始前撤走酒碗」一語(to take away the punch bowl just as the party gets going),筆者亦願補上一句:信譽如資本,難聚易散。聯儲可在技術上爭辯利率高低,亦可爭論關稅傳導之久暫,惟有一事不可含糊——白宮,不可決定利率。
7月30日,全球市場將逐句審讀FOMC聲明、點陣圖與異議票;唯獨一項訊號最為關鍵——鮑威爾與其同僚是否仍然堅守原則、以法定使命為唯一決策準則。若然,這份信號,其價值將遠超任何25基點的舉動。
市場真正需要的「減」,是政治干預與貨幣政策之間,一刀乾淨俐落的切割。否則,全球孳息率曲線之上,信任將日復一日流失,要止血,殊不容易。
▌[遠山近水]作者簡介
清風明月本無價 遠山近水皆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