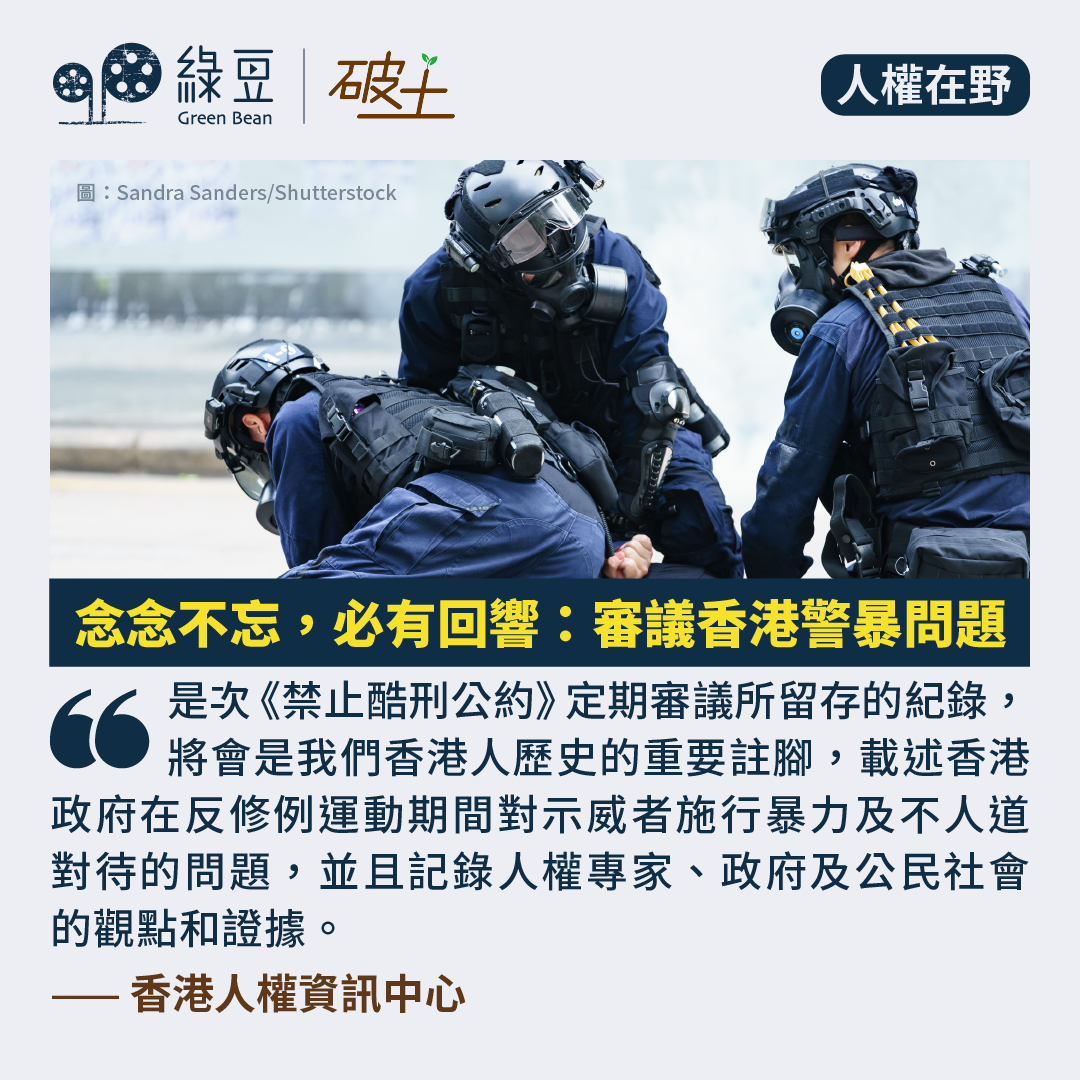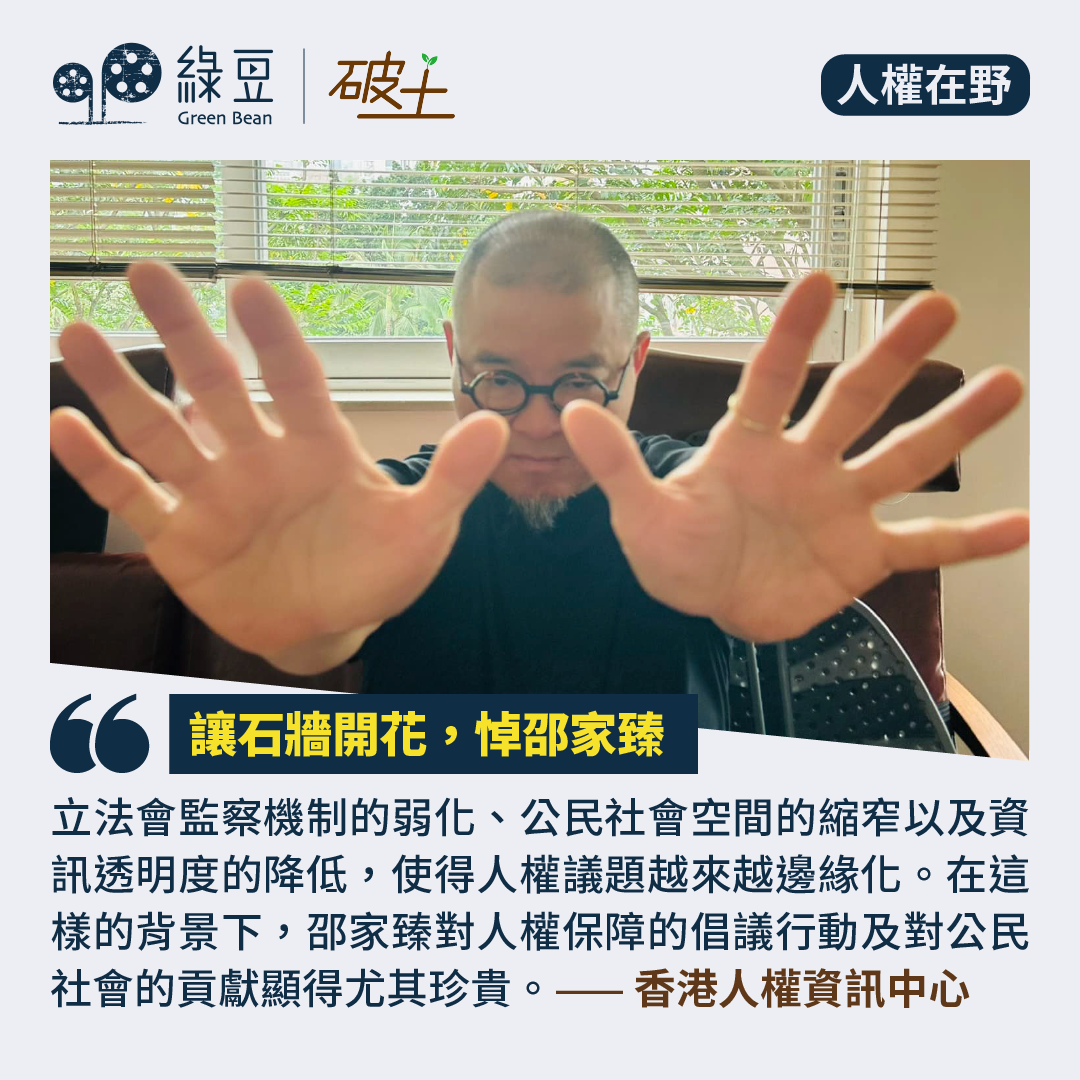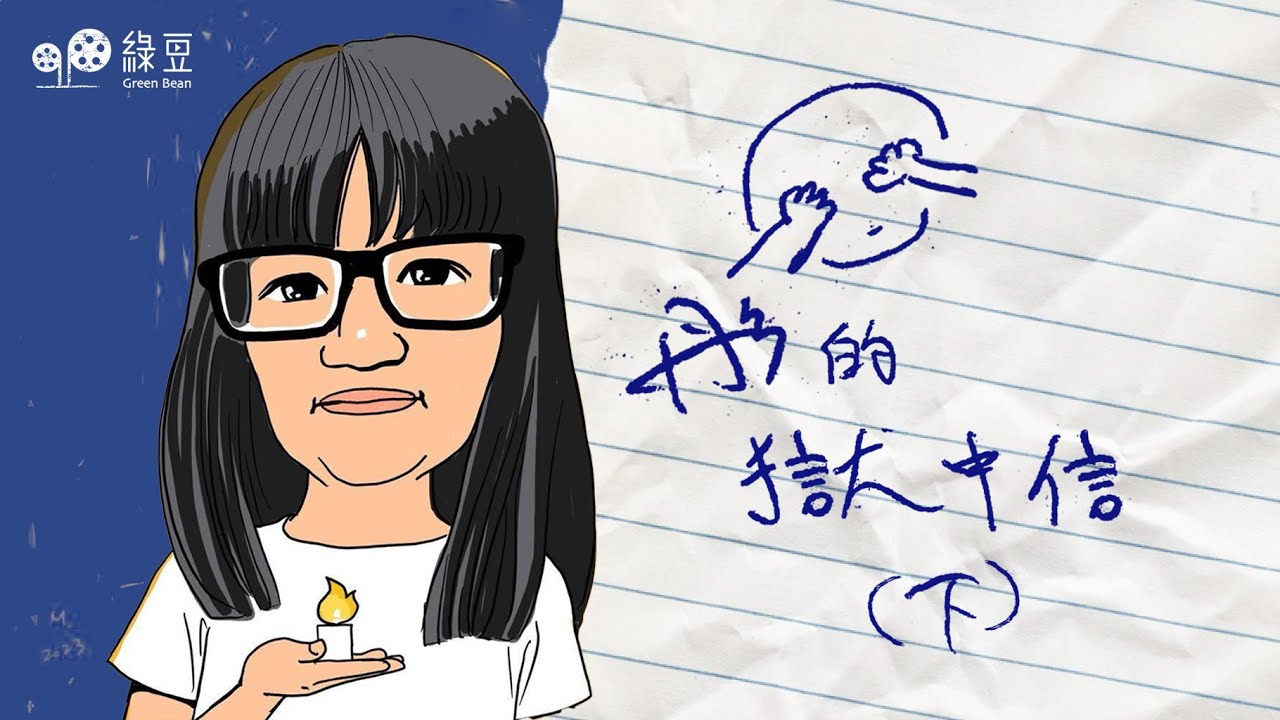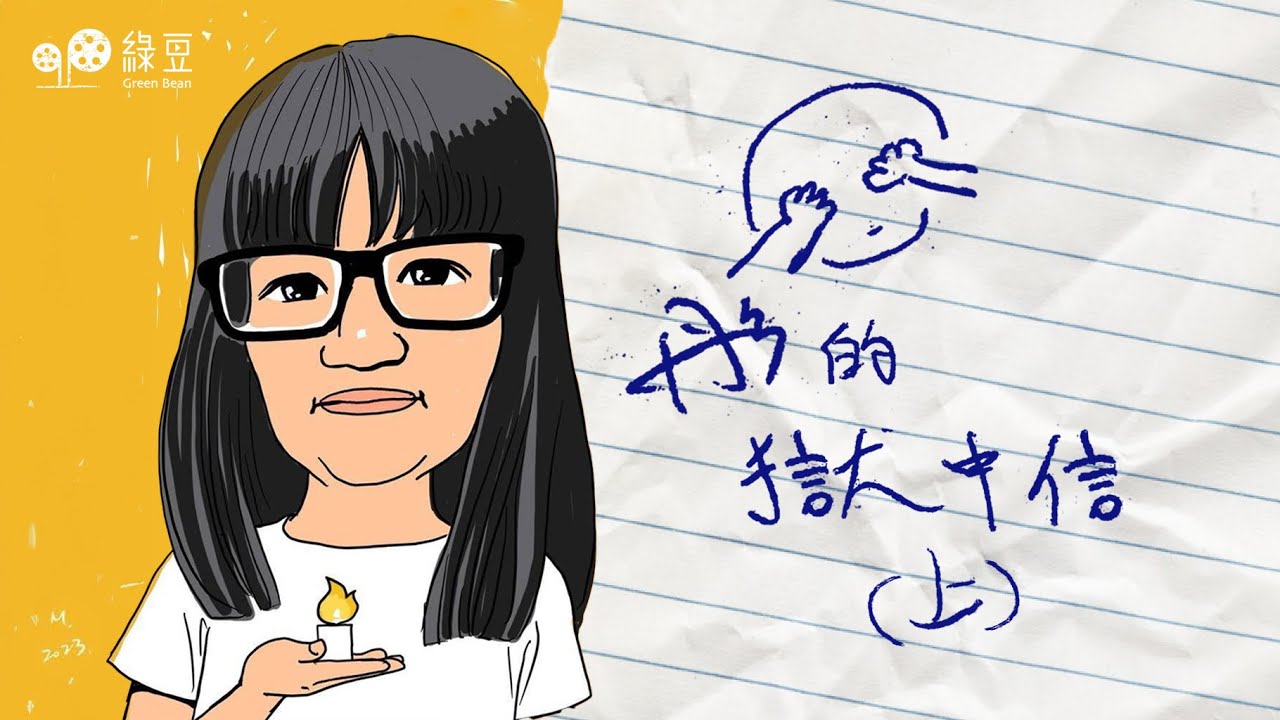(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歡迎各方讀者投稿。) 2025年12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頒下了一份長達855頁的判詞。三名由行政長官欽點的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李運騰及李素蘭——裁定黎智英「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串謀刊印煽動性刊物」共三項罪名全部成立。法官在判詞中指,黎智英「自成年以來一直懷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怨恨與仇恨」,其「唯一意圖」乃「尋求中國共產黨的覆滅」,法庭並用上比喻:黎智英的行為「類似於一名美國公民,以幫助加州為藉口,向俄羅斯求助以推翻美國政府」。 這段判詞值得逐字細讀。它把一個人數十年來在報章專欄、公開演講和國際場合所表達的政治觀點,重新界定為刑事罪行。判詞的語言與其說是法律推理,不如說是一套敘事策略:先把被告的動機歸結為「仇恨」,再把他的行為界定為「勾結」,然後把他所訴求的言論自由與選舉民主悄然轉譯為「外國勢力干預」。整個過程乾淨俐落,沒有血跡。...
我們於去年11月發表《 香港酷刑和不人道處遇報告 》(註一)指出中國當局,包括香港政府,未有根據《禁止酷刑公約》提交國家報告,逾期已近五年。我們並致函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要求作出跟進,以督促締約國履行公約義務和維持聯合國人權機制的完整性及監督的功能。 今年二月,中國政府終於向委員會提交報告,有關香港的報告 (註二)及相關文件已於近日上載至聯合國網頁。按照程序,禁止酷刑委員會將展開審議中國、香港及澳門執行《公約》的情況。我們預計,是次審議有望於2026年進行。《禁止酷刑公約》是以防止及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對待及處罰作為保障人權的公約,締約國或適用地區需要交代政府如何在法律、政策及實務中防範及禁止酷刑及相關行為。故此,香港政府在2019至2020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對示威者施行暴力及不人道對待的問題,將會面對聯合國人權專家的審視及質詢。2019年反修例運動雖已事隔六年,但追究香港政府的責任,制止警察濫權行使暴力的人權倡議,絕不應該停止。 政府迴避指控 公民社會仍有可為...
在香港夏季的潮濕酷熱中,女性囚犯被迫穿長褲參與日間活動,而男性囚犯則可以換上短褲。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針對這一政策提出司法覆核,認為懲教署的服裝規定構成性別歧視,不僅違反平等原則,還因加劇酷熱環境下的不適而涉嫌不人道對待囚犯。她提出的挑戰提醒我們,囚權不僅是免於酷刑的權利,更是在監禁中獲得公平與人道待遇的基本保障。 國際人權標準:囚權的法律基石 囚犯權利的保障根植於國際人權法。《世界人權宣言》第5條禁止酷刑及不人道或侮辱性待遇,奠定了人性尊嚴的基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7條重申此原則,第10條強調即使是被剝奪自由者亦應受人道對待,第26條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禁止基於性別的歧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要求消除女性在監禁環境中的不平等待遇。 1990年聯合國通過的《囚犯待遇基本原則》第1條已明確表示規定,囚犯應享有與自由人同等的核心人權,除非因監禁必要性受限;第2條亦同樣提出禁止任何因性別等身份施加歧視。2010年制定的《聯合國女性囚犯待遇準則》(Bangkok Rules)針對女性囚犯,第19條要求服裝適應氣候並尊重尊嚴,避免性別差異加重負擔。 梁國雄的長髮 鄒幸彤的司法覆核並非孤例,梁國雄(長毛)亦曾因男性囚犯須剪去長髮而入稟申請司法覆核。梁國雄於2011年衝擊立法會遞補機制論壇,2014年被裁定刑事毀壞及擾亂秩序等罪成,判囚4周,入獄時被剪去長髮。根據懲教署《工作守則》第41-05條,男性囚犯頭髮須「盡量剪短」,而女性囚犯無此限制。他被迫剪去標誌性長髮,遂提起司法覆核,指控政策違反《基本法》第25條(法律面前平等)及ICCPR第26條,構成性別歧視。...
前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囚權倡議組織「石牆花」創辦人邵家臻,於2025年1月10日因胃癌離世,享年55歲。他積極參與公民社會,為人權保障、尤其是囚權議題,作出重要貢獻。隨著《國安法》的實施,香港政治環境急劇轉變,人權保障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立法會監察機制的弱化、公民社會空間的縮窄以及資訊透明度的降低,使得人權議題越來越邊緣化。在這樣的背景下,邵家臻對人權保障的倡議行動及對公民社會的貢獻顯得尤其珍貴。 人權倡議與立法會的質詢權 邵家臻在擔任社福界立法會議員期間,發表《改善香港在囚人士權利及監獄環境建議書》及《懲教署檢討投訴及監察機制建議書》,為香港在囚人士的權利及懲教制度的監察,作出了多項深刻及詳盡的建議。例如針對監獄環境的酷熱問題,懲教署加速安裝風扇、為在囚人士提供飲用冷水,以及容許囚友自費購買散熱毛巾等,這些具體改善工作歸功於他鍥而不捨的跟進,以及在社會上持續引起公眾對囚權的關注。而去年發生的囚犯被虐事件,亦反映邵家臻及張超雄要求政府成立監察懲教署的獨立機制並非無的放矢。 邵家臻多次在立法會上針對人權相關議題提出口頭及書面質詢,要求政府正面回覆和公開相關的數據。包括在2018年旺角衝突案後,向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問,會否就事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以及2020年就政府外判員工的待遇向政府提出書面質詢。即使邵曾於2019年因「佔中」案被裁定兩項煽惑罪罪成,判囚8個月,他在獄中仍嘗試就「過勞死」的議題向立法會提出口頭質詢。 提出質詢的權力 立法會議員擁有向政府官員提出書面及口頭質詢的權力,這一機制是監督政府行為、促進政策透明的重要工具。通過質詢,議員可以要求政府公開相關數據,揭示潛在的人權問題,並推動政府採取改進措施。例如,針對監獄制度中的酷刑或不人道對待,議員的質詢能夠迫使政府披露實際情況,從而引發公眾關注並促進相關政策的改革。 對於人權研究及倡議而言,「可取得的信息」是釐清事實、揭示真相的重要前提。立法會的質詢權在這個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沒有議員的積極質詢,許多政府數據以及關於監獄和執法部門的問題將被官方報告遮掩,難以進入公眾視野。這些官方數據不僅是民間監察政府的重要依據,也為國際人權組織和本地團體提供了實證基礎,推動人權議題在全球討論和探索應有的保護措施。...
從2019年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到《香港國安法》的落實,再到俗稱「23條」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這五年間香港的人權狀況歷經了各種挑戰與變化。期間,聯合國人權機構及國際社會屢次發聲關注香港的人權狀況。五年過去,不少人可能疑惑:國際社群的目光是否已經轉移?香港的人權議題仍受國際關注嗎? 事實上,聯合國人權條約機構仍對香港的人權發展保有相當程度的監察和評估。而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工作小組等「特別程序」更是頻繁發表聲明或致函政府,密切追蹤香港的人權狀況,包括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少數群體平權以及勞工與婦女保障等各大領域。 聯合國特別程序的公開信與聲明 自2019年起,香港多次成為聯合國特別程序關注的焦點。這些特別程序包括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s)以及工作小組,透過聯合通報、聯合意見函或意見書等形式,就個別議題或事件向香港特區政府及中國政府提出具體人權疑慮。特別報告員以及工作小組是各個人權範疇的專家(例如言論自由、任意拘留、法官與律師獨立性等),他們在信函中引述《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等的國際人權標準,直接點出香港政府現行的法例或執法行動對人權造成的傷害。過去五年,聯合國特別程序已就香港的人權狀況發表19次公開信,當中包括: 以《香港國安法》或其相關法例作檢控的擴張性問題 特別報告員們數度致函香港政府,就國安法在實際執行層面,是否出現「過度闡釋」或「恣意擴張」的情況提出疑問。例如2023年的聯合通報,既質疑針對自我流亡的數名民主派人士發出通緝令的合法性,也表明此等「跨境追訴」恐怕與國際上慣常認定的國家管轄範圍有落差。同樣,2024年有關《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的聯合信函,亦一再強調立法過程應保持透明度及包容性,並避免進一步收緊言論及出版自由。...
「初選47人案」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最大規模的案件,亦是香港政府清剿民主派政治力量的關鍵一步。案件由檢控至判刑橫跨三年八個月,45人被裁定「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兩人脫罪。超過一半被告遭審前拘留,截至判刑日被還柙超過三年。案件日前判刑,45名被告中,戴耀庭遭判10年監禁,其餘分別被判處四年兩個月至七年監禁,總刑期合共245年。 我們指出,香港政府武器化法律,執意以嚴刑峻法打壓民主運動及公民參與的權利。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強調,表達自由、和平集會和結社自由是受人權保障的行為,但香港的國安法律將行使這些權利視為犯罪,並對公民社會的其他成員造成重大寒蟬效應。高級專員呼籲上訴法院應依照香港特區所承擔的國際人權義務,仔細審查這些定罪和判刑,推翻不符合人標準的案件。 這幾年間港府大張旗鼓將初選定調為「串謀顛覆國家政權」,將47名被告形容為「不理香港市民死活,挾持民主、自由的旗號」的罪人。我們應如何面對政府對初選案被告的負面標籤?以及如何看待這些為香港民主運動而坐牢的人? 思想有罪?良心犯的定義 1961年5月28日,英國律師Peter Benenson於《觀察家》(The Observer)發表題為〈被遺忘的囚犯〉(The...
我們早前發表了一份關於香港的酷刑和不人道處罰和待遇的報告,直指中國及香港當局未有履行《禁止酷刑公約》的義務,已逾期五年沒有向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提交國家報告;報告同時揭露在國安法新時代下的人權和法治問題,包括未審先囚越見普遍,2024年的還柙人士的監獄人口比例與十年前相比,增加超過一倍,達38%。長期的未審先囚令被告人屈服認罪,影響司法公正;律政司對酷刑罪避而不用,以較輕的控罪檢控涉嫌施行酷刑的人員。我們在報告中警告,香港本地制度內防止酷刑和不人道對待的保障措施正被系統性地削弱,使不同的弱勢群體面對酷刑及不人道待遇的問題,誠邀讀者下載報告細閱:https://hkchr.org/archives/2723 在國安法新時代下,我們撰寫人權報告可說是自找麻煩,吃力不討好。研究團隊要重覆細閱、覆核每一宗我們引述的資料,當中包括濫權、酷刑事件的詳情,就如不斷重覆旁觀受害者的遭遇,對研究員的情緒帶來很大的負擔。此外,我們發表報告,更要有心理準備會遭香港政府以煽動罪、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報復, 因我們在報告中對政府直斥其非,要求聯合國、國際社會就香港的人權問題進行問責。事實上,香港政府早前已向傳媒回應報告,對我們作強烈譴責,並指報告是失實言論和污衊抹黑。 國際人權法像一種信仰 筆者在進修國際人權法時,教授曾打趣說:「國際人權法像一種信仰」。這說法相當準確道出了國際人權法的特質:第一層的解讀是指國際人權法宣揚了普遍的人權標準,成為了一種信念或理想的體現。同時,亦把人的權利成為了家傳戶曉的概念。例如,當我們為「民主選舉」、「言論自由」而吶喊、上街,我們未必知道這是建基於哪一條國際人權公約的條文,但我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我們應有的權利,並願意為此去努力爭取。這些不同的人權公約建構了我們作為人類的道德、價值和原則,並成為一種力量,支撐我們的良知、推動我們為爭取正義、公平和人的尊嚴而努力。將追求人權或國際人權法視為一種信仰,這說法也不失為過。 第二層的解讀是帶點自嘲的意味。國際人權法有時會被視為信念和理想,多於在現實中有具體的影響。因為大部分的國際人權法欠缺強制性,條文的落實依賴國際共識、各國的法律制度和具體的執行機制,而這些在現實中往往存在挑戰和局限。國家違反人權法的條文可以沒有後果亦難以追究,大大弱化了其作為法律的實際作用,國際人權法在某些時候亦不能當成具體的法律工具去使用。 條約機構審查...
收看節目 壹傳媒已被清盤,但相關消息未完結。《路透社》報導,「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主席Mark Clifford及前《華爾街日報》發行人Gordon Crovitz,兩人以前壹傳媒董事會成員身份,向總部設於法國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出投訴信,指控全球第五大的會計師事務所立信德豪(BDO),非法協助香港政府清盤解散壹傳媒,違反人權標準。由於立信德豪母公司在英國,根據經合組織規定跨國企業必須「預防或減輕與其業務活動直接相關的不利人權影響」,並「進行人權盡職調查」。而母公司須對海外子公司的所有行為負責,因此,英國政府作為經合組織成員國,必須監督組織指導方法的實施,負責處理投訴的英國商貿部稍後將公開報告,決定是否進行仲裁。想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請收看EP110《兩邊走走》的編輯推介。 ...
收看節目 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獄中兩年幾,期間獲頒發至少 5 個國際人權獎項。她不能夠出席頒獎禮,但在獄中為每一個獎項都撰寫致辭,一字一句寫下萬言書,再透過親友在網上公開。我們透過聲演繹,讀出鄒幸彤最新的兩篇人權獎致辭,了解這位身陷囹圄的大律師怎樣思考人權和法治,怎樣思考香港和世界。 ...
收看節目 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獄中兩年多,期間獲頒發至少五個國際人權獎項,但她自己在獄中的人權狀況又是怎樣? 根據她親友統計,鄒幸彤過去半年經常被罰在「水飯房」單獨囚禁,累積達 78 日之多。她被隔離、被剝奪戶外「放風」、被限制閱讀書籍、被取消福利,甚至很多信件也被寄失。但她從沒有停止過寫作。我們透過聲演繹,讀出鄒幸彤在網上公開的信件及致辭稿,呈現這位人權獎得主在獄中的所思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