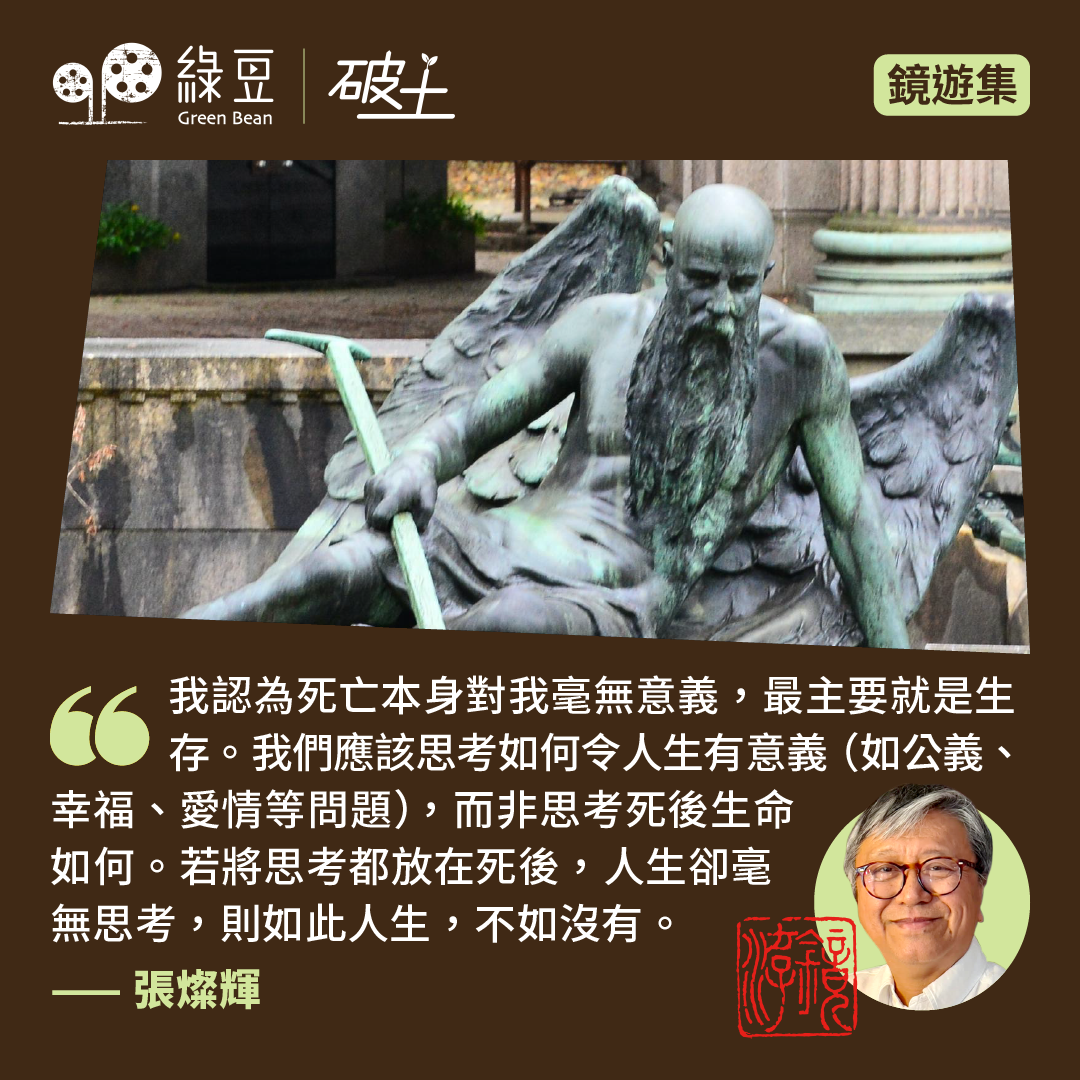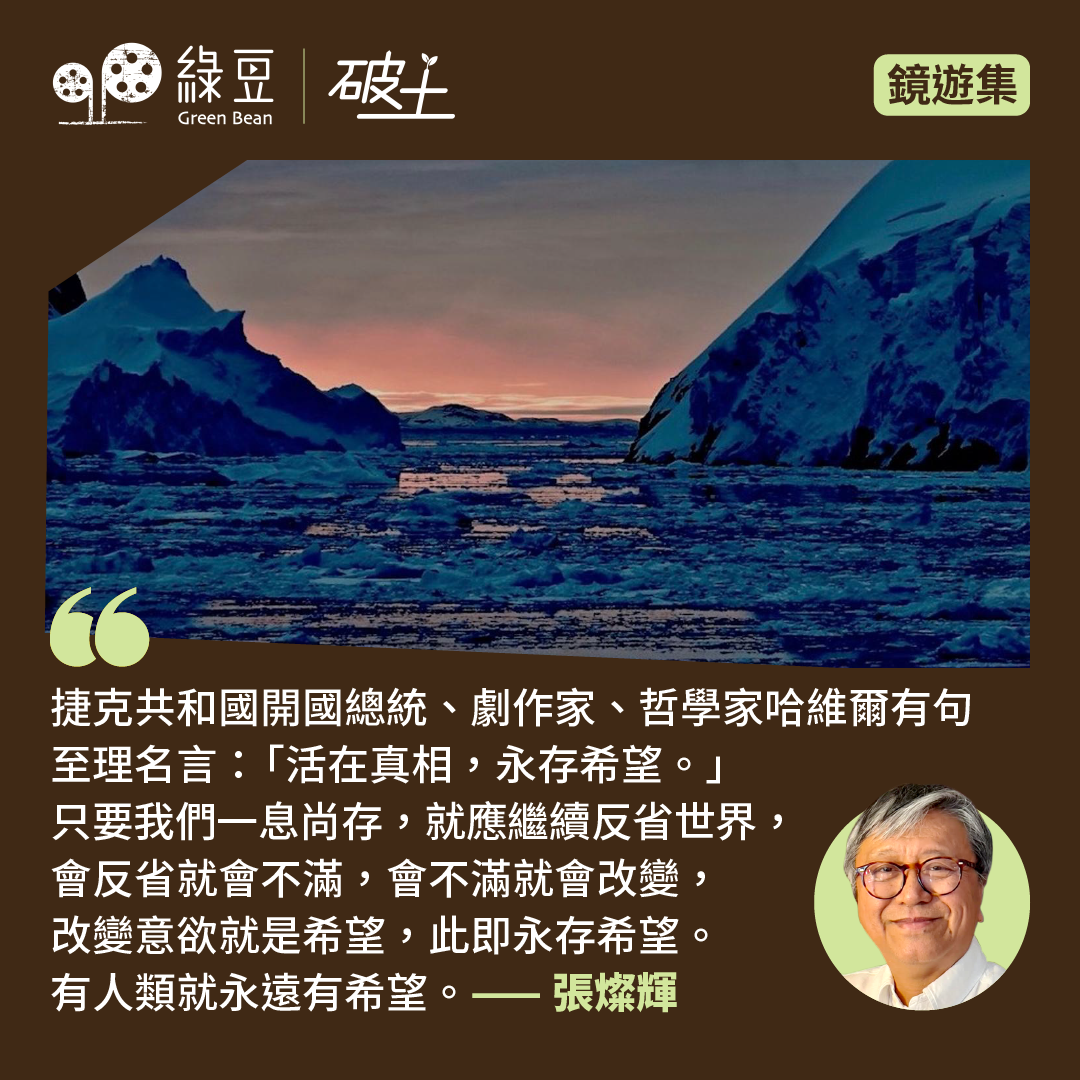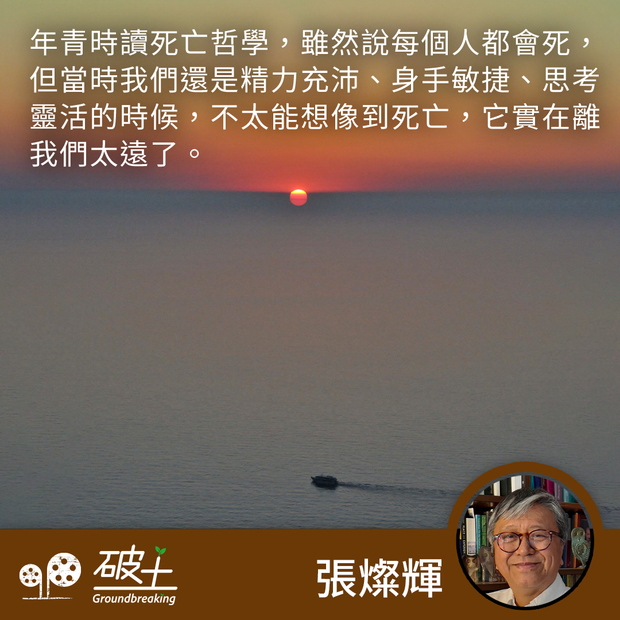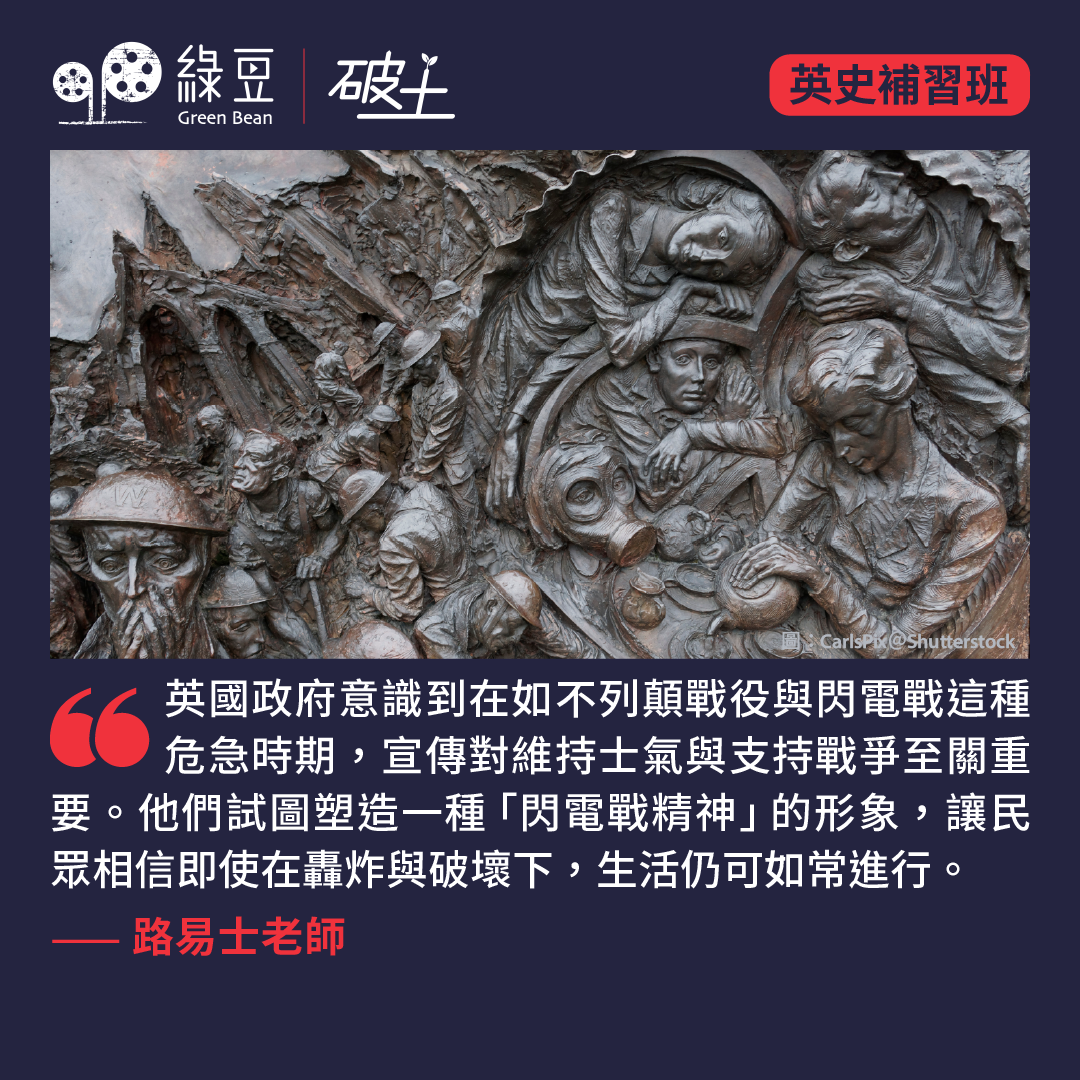第十五封信 15.2 明慧, 現在,回到你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生活?我認為,即使我的課程計劃失敗了,但其背後的哲學洞察仍然有效。我們不能等待理想的外在條件來實踐真正的閒暇,我們必須在現有的條件下開始。 現有條件下實踐閒暇 首先,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我們對時間的態度。不要將退休後的時間視為「空閒」或「剩餘」,而要認識到它是「我們擁有的最重要的時間」。這意味著有意識地保護和規劃我們的時間,就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不是為了工作而休息,而是為了閒暇而工作。...
生.死.愛.欲 去年我在台灣出版一套上下兩冊的《生死愛欲》,分別是《從希臘神話到基督宗教》及《從中國傳統到近現代西方》兩部分。這套書是我在中文大學歷年來思考與著述的總和,以東西方文化比較的方式處理相關問題。 《從希臘神話到基督宗教》由柏拉圖講起。處理死亡問題,我們需要透過柏拉圖所著的《自辯》來理解化死亡為哲學問題的第一人──蘇格拉底──其想法如何;同樣,處理愛欲問題,亦需由柏拉圖入手。在古希臘文明中,愛欲之神愛洛斯 (Eros)與死亡之神桑納托斯(Thanatos)乃一對密不可分而極重要的概念。故本書何以名為《生死愛欲》,為何「生死」會與「愛欲」相提並論,原因即在此。 亞里士多德將「愛」起碼分為三種,即欲愛(eros)、德愛(philia)、聖愛(agape),它們是「愛」的三種最主要形式,其中「philia」又被視為 「最高形式愛」。這套觀念深刻影響西方人「愛」的觀念,直到現代仍然如是。 柏拉圖在《饗宴》(Symposium)中提出,最重要的就是欲愛,這與亞里士多德看法微異。所謂愛,就是欲,就是追求,追求不在我自身裡面之對象。因為該對象不在我裡面(不屬於我),所以我欲,我追求,這就是愛。對象可以是任何事物,自然亦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抽象觀念,如真、善、美。柏拉圖所說的欲愛,乃單向而不對等之愛;與此相反,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德愛,則為雙向而對等之愛。他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八及九卷中論之甚詳,於此不贅述,大家可自行參閱。 聖愛,主要發揚自基督教的《新約聖經》,這種愛已達乎追求世界和平的大愛、博愛、明愛(caritas),類似佛家慈悲與儒家之仁。因此很明顯,聖愛絕非一般男女情欲的愛。但是基督教這種聖愛精神,並非鐵板一塊,首尾相貫,即使回歸到最純粹的研究上,對比《舊約》與《新約》如何看待聖愛問題,亦會發覺彼此之間看法亦不同。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又需要另費一番功夫,才能梳理出雄踞西方文明上千年的基督教,對於「愛」乃作何想法。 《從中國傳統到近現代西方》這部分,源自我有種想法,認為過去三十多年在雅正中文世界裡,甚少人寫而且頗為避諱相關主題,愛情或情欲既不能寫,死亡問題亦甚少觸及。因此,我立志要重新整理華夏文明對這些主題如何看待及處理。華夏與西方處理相關問題的方式與態度截然不同。正如上述,古華夏並無「愛你」這種觀念,儒家「仁者愛人」及墨子的「兼愛」,與所謂男女之愛毫無關係,在華夏古文獻中,西方文明那種「愛」,基本上不存在。面對如此現象,我們必須要問,為何這樣?這也是我試圖回答的一大問題。 西方自上古伊始,歷經文藝復興與浪漫主義風潮,迄今為止,對於「愛」所作反省與發展,屢有突破。譬如現代心理分析認為,欲望對人類這種存在相當重要,我們所欲所求,皆從心理變化而來。此說影響甚大。基於相關研究理論,他們不禁對眾哲學家提出質疑:哲學家果真了解愛情嗎?不少哲學家,如柏拉圖、尼采、叔本華等,皆終身未婚,因為愛情太麻煩。而康德更是當中佼佼者。當然,已婚或有過愛情經驗的哲學家亦不乏其人,如海德格與漢娜.鄂蘭,以及沙特和波娃,他們都是哲學家。不過,身為哲學家,他們能否依憑自身體驗,就愛欲問題提出哲學主張? 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耳聞「此愛非真愛」之類言語,然而,如果有所謂真實的愛(authentic love),則到底何謂真愛?真愛應該具備何種條件與狀態?若追根究柢,我們甚至要問,何謂真?我這部書其中一項所要表達的訊息即在此。 出版這部書,追本溯源,可追溯到我年輕時所出版過的另一本小書:《將上下而求索:給明慧的二十封信》。正如我在《生死愛欲》開首時所說:它是我歷年來思考與著述的總和,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正因為在這個耗盡一生以「上下而求索」的過程裡,我明白到生命問題並非容易回答,因此希望將這些思想果實化為著作,留給後人,希望多少有所裨益。 我一生在香港生活,未嘗受戰火洗禮與暴政蹂躪,從未意識到,無論中國抑或台灣,一直處於各式災難中,受盡荼毒折磨。昨日與朋友參觀台北景美白色恐怖紀念館,認識到自五○年代以來,台灣人如何在白色恐怖的壓力下,力爭民主,對抗暴政,並為此犧牲無數仁人義士的性命。如今白色恐怖在台灣已成過去,然而在香港,它卻處於現在進行式。香港如今已然巨變,但這種變化,對我們反省生命是否無意義與價值?大家不妨思考一下。 以上所述這部《生死愛欲》,我希望透過不同方向,探討人生問題,而非知識、理論、學科問題,因此切勿將此書當作歷史或理論哲學書閱讀。這部書既作為我歷年來思考與著述的總和,自然與我多年來所嘗試的教育方法以及各式著作,具有某種一致性(consistency),亦即有一條主軸貫徹始終,而這條主軸,就是人類處境與生命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每個人所給出的答案,並沒有任何一個可自詡為永恆而絕對。大家的答案,皆僅供他人參考,作為養分,以刺激更多思考與答案。人類處境與生命問題,乃實存問題 (existential problem),而非理論問題(theoretical problem)。實存問題不只要思考,更要處理,是我們無法避免、必須面對的問題。 年老哲學去年,我曾在網上開課講授死亡與年老哲學。談論死亡哲學者甚多,談論年老哲學者亦不少,但將兩者相提並論者則鮮。對於死亡與年老的關係,就我而言,不過是「若非早死,就要老去,別無選擇」。年輕時,我們極少想到年老與死亡的問題;到年老時,我們才會發覺自己既未早死,且逐漸老去,此時才會意識到這句話的存在。然而,老去既非必然之事,在我們的世代之前,更非常態。過去由於醫療尚不夠好,人多短壽,故古人有所謂「六十不稱夭,七十古來稀」之說,因此,過去大部分人都難以體驗老去,即使帝王將相亦然;但是,如今人類隨便都可活個八、九十歲,除非自殺,否則死亡不易降臨。...
哲學與人生問題 2021年,我曾出版《為人之學:人文、哲學與通識教育》一書,當中講述我如何看待哲學教育及通識教育。我從哲學與生命角度切入,發現通識中心甚少有課程觸及這個人生最重要的問題。以哲學思辨生命,並非單純講述自身故事,而是如何運用學問,探討及解決自身所面對人生問題。必須注意,運用學問並不代表你必須讀通康德或亞里士多德等人博大精深的學術巨著,你大可完全不明白他們的學術思想,不過卻要學習他們如何看待生命的方式。出於以上想法,因此將生命哲學放入通識教育範疇,作為實踐自身教育理念的基石。 正如上述,我們要向眾哲學家學習,如何看待生命。但他們所講的問題絕非具體問題,而是若干人類必然會遇到的共同問題,並尋求普遍意義的解決方法。就我自身能力所及,將眾多人類必會遇到的共同問題中的五種,納入講學範圍,後來遂發展成「死亡與不朽」、「愛情哲學」、「性與文化」、「幸福論」、以及「烏托邦思想」五門科目。以下我逐一講解這些科目的內容與意義。 五個人生共同問題死亡與不朽,乃人生最重要、亦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基督教徒強調,信耶穌,得永生。然而,何謂永生?何謂不朽?柏拉圖講靈魂不朽(immortality of the soul)與耶穌所謂肉身復活(resurrection of the body)有何分別?凡此種種,當我們面對生命與死亡時,實無可避免,必須處理。 人生另一主要問題就是愛情哲學。試問誰不渴望愛情?然而,何謂愛?何謂情?將「愛」與「情」化作人生經驗,該如何處理?表面上大家都在談情說愛,但若問他們何謂愛情,被問者大抵皆無言以對。華夏文明本無「我愛你」的概念,在座各位可否於1900年前任何一部古籍中覓得此三字?起碼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找到。為何在我們的傳統中,並沒有任何概念可對應「I...
20世紀英國學者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形容哲人是「受思辨所害的不能自拔者」(victim of thought)。他的意思是說,哲學思辨是一種對所有思想內容背後的根據或前提的假定,不斷進行尋根究底式的知性拷問。任何結論,在哲學上都是臨時的。因為除非我們停止思考,否則,所有思辨在過程中達至的有關結論,其背後的根據或前提的假定,總是可以作出進一步和更深一層的探索。因此,嚴格說來,哲學思辨是個無涯涘的追尋。哲人對思想的拷問,是一種不斷啟航的知性釐清和加深認識的行為。哲人在這旅途到達的所有目的地都是過客。因為哲人會對到達了的目的地可能引發出的、未被探索的新路徑或潛在的通道產生不能自拔的好奇,於是便不能自已的再走上思辨拷問的征途,邁向無涯涘的思考。 哲人如果不能在他生活的所在地進行哲學思辨,或者他那不斷尋根究底式的知性拷問活動,受到了掌管公權者的禁制、懲處,甚至迫逼其思辨活動服務於當權者的政治目的,那麽,哲人為了忠於其無涯涘知性的追尋,便有可能被迫流亡。否則,哲人很可能從「受思辨所害的不能自拔者」,變成是被政治迫害成為工具者,因而無法繼續進行真正的哲學思辨。 被迫流亡在外的先輩 我和本書作者張燦輝都是在戰後香港成長的一代。張燦輝是我的學長輩,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我自己則畢業於香港大學,修讀的是哲學和政治學。我們這些在戰後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看到香港1949年後,成為了來自中國大陸不少哲者學人和文化先輩的流亡地。這些華夏知識人,基於種種政治或文化的因由,其思想或作為不容於掌控公權的黨國體制,因此只能避秦於這大陸南端的英國殖民地,否則便不能繼續他們在思想上和文化上自主的追尋。...
既然我們要以知識層面理解希望及烏托邦,將哲學導入希望,則我們首先需要知道,哲學與希望關係是什麼。正如上述,過去不少哲學家認為「世界為一已完成的封閉實體」,故他們始終以被動沉思而非主動行動的態度,來理解希望,導致理解無法突破既有框架。 布洛赫指出,哲學(philosophy)這個概念本身,已經揭示這些哲學家思想方向有誤。眾所周知,「philosophy」希臘文是「Φιλοσοφία」,「φίλος」(philo)是「愛」(love),「σοφία」(sophia)是「智慧」(wisdom),故「哲學」原意為「愛智慧」。觀此原意,則可知哲學絕不是智慧,而是追求智慧。是以「愛」是種欲望,所以有欲望,實由於尚未得到或達成。因此,愛智慧便是尚未得到智慧,把握智慧,故追求。基於此前提,則哲學不可能是將「視世界為已完成的封閉實體」作思考基礎,此即這些哲學家思考方向所以有誤之由。 愛欲與希望 根據古希臘神話所言,人與神之間最大分別,就在於後者不朽。但柏拉圖卻將此說法扭轉,他說人有一部分可以不朽,就是靈魂,此即靈魂不朽論(immortality of the soul)。何以人類靈魂不朽?因靈魂具備自我昇華能力,可憑藉理性,提高到理念(eidos)層面,而追求如此境界的欲望,就是理性推動力所在。理性使人類一步步昇華,最終擺脫肉體束縛,化為完全精神之存在。凡此,皆由於欲望。...
第七封信 7.2 明慧, 中文大學變成為政權服務的知識工廠,我們為此而感到悲傷和難過。但是我們有沒有想到,21世紀的大學,不只是中文大學,差不多全世界的大學,根本上已經是學術產業和知識工廠?我之前所談到的大學之道,其實已經是過去的理想,現今並不重要。所有強調學術自主自由,追求真理的想法是不實際的。 現代研究型大學再不是如中世紀時的大學,少數精英教授和學生聚集學習和研究的地方,不是傳統中國書院私塾的規模,而是龐大的機構,由數以十計的學院和學系組成,設置學科以千計,學生成千上萬,教授和行政人員有數百位以上。這巨大組織經費來自政府,或由私人基金或捐贈而運作,是政治經濟的學術投資!這裡不是象牙塔,可以無憂無慮教學和研究學問,大學要向社會負責。教授和學生除了學術世界之外,仍有政治經濟環境去面對。...
第六封信 6.4 明慧, 我大半生在中文大學渡過。從事學術、研究、教學和行政工作,有幸受到不少老師的錯愛和鼓勵;朋輩的支持和幫助。業師沈宣仁院長在崇基本科一年級教授大學理念和他的教學熱誠,尤其是他對人文和自然知識的追尋,是「文藝復興人」的典範,使我終生受益良多。何秀煌老師對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肯定和規範性之確立,使我從他手中接任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工作時,可在堅實的基礎繼續工作。但在我理解大學和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實踐上,最重要的是受金耀基教授開啓性的影響。他的《大學的理念》一書為所有華人大學通識教育工作者必備的經典。我思考大學精神和通識教育的課程發展,很多方面從他的思想引發出來。 14年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工作可算是我教學生涯中較滿意的一部分。中文大學通識教育有這樣的成就,主要原因是在於各崗位參與者的無私奉獻,熱誠參與。任期中多次課程改革和變更,沒有校方和同事的支持,根本不可能成功。金耀基校長和楊綱凱副校長對通識教育的執著,是中大通識教育改革成功的首要條件。沈祖堯校長對通識教育基礎課程的信心至為重要,但最難得的是大學通識教育部上下同事積極的參與才能推動。其中特別要致謝的是梁美儀教授、崔素珊女士、吳曉真小姐和趙茱莉博士。和他們共事多年是我的榮幸。(註一)...
第五封信5.1明慧,讀哲學,所為何事?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哲學家的思想,如果不能治愈人的痛苦,則是徒然的話語。正如醫學不能消除身體上的疾病一樣,是沒有用處的;如果哲學不能消除心靈上的痛苦,也沒有任何好處。」如果自由是哲學的根基,則反叛精神是哲學的表現。我於1970年唸哲學本科,1982年獲頒德國哲學博士,然後任教哲學系成為教授。但我不是哲學家;儘管我讀了多年海德格哲學,我不是海德格思想專家!因為我沒有研究他所有的著作,有不少思想我還不理解。我仍然只是一個哲學學生和哲學老師。當然我也算是「學者」,作為大學教授定要寫哲學學術論文,出席學術研討會,根據學術基礎去授課。從助理教授升等為正教授需要一定學術程序,沒有實質資格不能勝任。但這些不是我最關心的事宜,因為我認為哲學博士學位只是進入大學任教的基本要求,是職業的需要,與生活和生命意義沒有一定關係。唸了一生哲學,對我的生命有什麼意義和影響?我讀過不少哲學經典和研讀中西哲學家思想,對我有影響的哲學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海德格和佛洛伊德。我在這篇文章無意詳細討論他們的哲學,這不是學術分析的場合。海德格思想令我知道所有以前中西人性論的偏差,人沒有必然的「本質」,人不是「什麼」而是「如何」,即是説人是透過他或她如何生活建構自己。人不是一種物件或動物,其獨特處是人對其存在有一種領悟,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是一個「我」同時知道我之外的他人和種種事物的存在。我和世界是不可分割的,但我的生命從出到死亡都是「拋擲」在預定的歷史文化世界中,「沉淪」在他人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少數時間我會面對自己,尤其是面對自己的死亡外,大部分時間我和其他人是以「非本己」的狀態生活著。海德格思想當然不是一言兩語可以講清楚,在此只是略説一二,作為我開展如何將哲學放在生活中的背景。第二個重要的影響來自佛洛伊德。他的精神分析理論告訴我,理性不是主導人類行為最主要的原則,而是我們的無意識。慾望不能被理性控制,而演變為種種連自己都不明白的行為。如果理性和道德是決定人類行為的原則,如果每個人都是理性的,則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思想早已落實在人類文明中,獨裁和專制便不會出現。可惜人類歷史文化不是順理性道德發展,三千多年來人類的悲劇不斷重演,自由、公義、平等和和平生活只是人類烏托邦的想像而已。明慧,我當然沒有足夠識見和智慧去解決這些大問題,但嘗試去了解這些問題是什麼的問題,去審視過往思想家如何分析和提出建議,是我能力範圍內,但重要的是我如何根據多年來的哲學研讀回應《將上下而求索》內的人生問題。我在第一封信提過這本年輕時代的小書只説出一些方向性的意見,沒有更深入討論和研究。以哲學去反省和理解我們的存在問題便是如何「實踐」哲學。我比很多朋友都幸福和幸運,能夠以學術興趣為生,不需要每天出賣時間去做一份與自己興趣或跟學問無關的職業,而是將興趣放在工作中。更幸運的是我在中文大學開設的課程全是自由自主去創立。二十多年來沒有任何審查內容,只要系務會議同仁通過,符合學術標準便可開課。為回應《將上下而求索》,我構思一系列通識/哲學課程。存在和生命意義問題絕對不可以簡單回答,而需要認真在中西哲學和思想史中尋求解答。我們可以不知道什麼是相對論或資本論,不需要探討創世論和進化論的矛盾,但我們不能不面對作為人存在的種種問題:生老病死、情慾、友誼、幸福、痛苦、人生意義和價值等問題。我正在這特殊空間和時間,有幸在學術自由的中文大學任教,哲學系又容許我發展這「存在問題」課程。上世紀末已經開出五門哲學課放在通識教育課程內。五個通識科目著重處理人生的意義,同時彼此亦有緊密的關聯:《死亡與不朽》探討的是生命的問題,是對生命價值、人生方向的醒覺和理解。我們從死亡中探索人生的意義,當中必涉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情愛」問題因此而起。愛情是人生重要的課題,同時也是年青同學的最大關懷。而《愛情哲學》就希望同學能對愛情或情愛有所反省,掌握中西文化對愛情的不同觀念;既理解柏拉圖之愛慾、西方浪漫之愛,也領悟到中國之「情」,從而取得啟示。談到「愛」,自然要提及「性」。「性」是現今社會很重要的問題。《性與文化》就是要從中西文化的不同角度,探討「性」在文化上建構的意義和其中的演變、傳統中西方對男女性別的看法。此外,我們還會討論「性」在當前文化中趨向商品化,成為消費品的問題。現今社會以物質享受為主流,以享樂為人生目的,但是人生價值是否就是如此?幸福的意義是甚麼?《幸福論》嘗試從不同角度探討快樂與幸福的問題,追尋幸福之道。從個人幸福推展至社會及世界層面,那就是烏托邦思想的課題。《烏托邦思想》嘗試從人類歷史以及哲學思想的角度,探究完美社會和理想世界的問題。及至中大哲學碩士學位課程成立,我將這些課題提升到碩士班程度:《生死愛欲》、《情、愛、性的哲學》、《痛苦與快樂》、《烏托邦及其不滿》和《死亡與年老哲學》,分別在長達十七年的教授碩士學位課程中展開。以上列出的課程,我在求學時期從未上過,沒有老師教授我有關生死愛欲等問題。《死亡與不朽》沈宣仁老師似有教授過,後來沈老師指定我開拓此課。《幸福論》是何秀煌老師請我發展的。也由於老師的鼓勵和支持,我可以提出這「存在問題」的課程。整體來說,我之前沒有一位老師開授這系列,之後也可能沒有。相信我在香港是第一個教授這系列存在課題。明慧,我在這封信開始時問讀哲學所為何事?就是為了解答我們作為人面對的種種存在問題,我覺得我從未有確定的答案,是以我仍然是哲學學生,仍然需要繼續研讀和思考;與此同時,我是哲學老師,將我所讀所思和同學分享,提供哲學理論,協助他們自己理解這些議題。但我沒有真理,從沒有教導任何「正確」的生活方式。從古希臘哲學開始,「認識自己」 (Know Thyself) 是讀哲學的任務。哲學有沒有用處,在乎你和我如何認識自己,不是一個抽象的自己概念,而是有血有肉,苦樂參半和充滿矛盾的自己。明慧,如此將哲學運用在生命問題便足夠嗎?我仍需要進一步思考和分析。待續▌[鏡遊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
第四封信 4.2第三期:本土哲學系上世紀80年代,除了香港中文大學以外的另一家哲學系就只是香港大學。不過,這只是殖民地的哲學系,當中不單沒有對中國的關懷,更遑論對香港的關切。記得80年代香港大學哲學系教授曾對我說,香港大學從未聘用過中國人和女性為教授,並引此感到驕傲。依我的觀察,香港大學只算是英國大學哲學系的分店,哲學系教授是將香港工作當成是悠長假期,既不用寫學術文章,亦不需要做課程檢討,生活在自己的象牙塔內,無論他們在波士頓、倫敦、紐約的大學教授康德都是一樣,沒有對時代文化和社會關懷的哲學,與其他自然科學沒有分別,學術和生活都是毫不相關。中大前兩期的哲學老師都是關心中國文化的,儘管唐先生牟先生對香港及香港文化不大重視,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懷抱是不容置疑。當我由港大轉到中大哲學系讀書時,發覺中大哲學教授,唐先生或牟先生,不單是講哲學思辨的技術,也不會把哲學當成純知識或商品,而是蘊含深遠的文化關懷。日後勞先生的「香港前景研究社」,是面對香港97回歸而創立,對共產黨的感受遠比香港大學的英國教授那種對香港無關痛癢,形成很大落差。1998年劉述先退休,當時系主任石元康下放權力,關子尹成為第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擔任中大哲學系系主任。這是個重大改變,亦是香港哲學系本土化的開始,加上劉國英於1995年從法國回港。「劉關張」出現,一度成為中大哲學系的「傳説」。當時系中的老師,超過一半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在中大唸本科,然後到歐美澳洲,獲得博士學位回來任教。第一次由香港人主政的哲學系,改變了一路以來哲學系的發展格局。1996年是重要的一年,我們舉辦了首次的現象學國際會議,是哲學系發展的重要里程,令我們覺得現象學可以有所發展。早於80年代中,勞先生曾經主辦在香港第一次涵蓋中港台政治社會經濟的聯合學術會議。大陸當時仍處於文藝復興期,時任中共國務院學者嚴家其都有獲邀出席。勞先生任命我為會議統籌員,負責會議一切的行政安排,這次活動的經驗對我們日後舉辦各種學術會議及研討會打下很好的基礎。作為本土人做哲學系領導,我們關心的是香港在此特殊環境下可以做些甚麼?當時的香港大學、嶺南和浸會沒有一個哲學系系主任是香港人,他們沒有關心哲學在香港發展究竟有著甚麼可能性,香港沒有「香港哲學」,只有「哲學在香港」。要哲學在香港有所發展,大學裡如何「做」是很重要的。因此,關子尹出任系主任,我全力支持他的,劉國英回港加入團隊亦很重要,那時「劉關張」的合作,勞先生對此感到驕傲。此時的哲學系開始以三條腿走路:中國哲學、分析哲學和現象學。關子尹90年代出任系主任8年,我於2005年接任此職位,學系著重學術在國際與香港方面的連繫。2004年我們偶然得到超過二千萬港元的捐助,為哲學系的發展打開缺口,多了資源我們可以在通識教育、中國哲學和現象學學術研討會及出版等投入更多的工作,慢慢地中文大學哲學系並不只局限於香港,而是放眼世界。二千年後陸續成立的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和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國際會議開個不停。2003創辦的唐君毅訪問教授計劃更令不少著名哲學教授來中文大學訪問一個月。我們希望讓世界認識及接受香港現象學和中國哲學的研究。香港的大學教育在港英殖民地年代,和97年回歸後的首20年仍享受著學術自主和自由。是以我們透過學術會議和出版將中港台日韓英美哲學界連接起來,不到十年中文大學哲學系慢慢被世界學術界接受和肯定。但重要的是這期在哲學系擔任主要教學和行政的老師,差不多全部是香港人或從美國研究回來的華人學者。在這期間,外國教授只有兩位。從1998年開始到2018年左右,相信應該是中大哲學系的黃金時期。創新嘗試 • 哲學碩士兼讀課程如果不是哲學系的本科生,在上世紀90年代的香港,要進修讀哲學有一定的困難。我在「香港哲學會」接觸到的民間社會,不少朋友都對哲學很感興趣, 很努力的尋找不同渠道修讀哲學,可惜苦無機會,被拒諸於哲學的門外。當年唯一可以選讀的是中文大學或香港大學校外進修部有關哲學的課程。香港政府從來沒有提供任何輔助課程,修讀人士亦沒有專業的哲學老師指導,很多人都不得其門而入。見到社會有這個情況,我們希望可以為對哲學有興趣的在職人士提供機會,讓他們能夠修讀哲學,我們參照了倫敦大學校外哲學課程開設學士學位課程,初時中文大學沒有興趣開課, 後來香港大學接受了我們的意見,...
第一封信 1.2人的「有限性」人生第三階段所要面對的第一個哲學問題,就是上世紀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所說的「有限性」。人的生命都是在一定的時間內,我們知道這個時間的「有限性」涵意就是死亡。年青時讀死亡哲學,雖然說每個人都會死,但當時我們還是精力充沛、身手敏捷、思考靈活的時候,不太能想像到死亡,它實在離我們太遠了,我們覺得自己仍有數之不盡的時間,還有很多事情想做未做,我們不大相信死亡是會出現的。現在,我們到了如孔子所說的七十「從心所欲」階段,不過,你發覺很多與自己同齡的人已經相繼離去。父親54歲過世,未能經歷我們現時的這個階段。在這第三階段裡,我們可以感受到人生的開放性、自由性。退休後,突然多出許多時間,從前未能做的,現在都有時間去做。不過,在這開放性裡面,你又會發覺自己正走到前方的一道閘,慢慢接近,而閘門很快就會關上,這就是我們的第四階段,亦即是終站,就是要落車的地方。生命中的LOSS由第三階段通往第四階段的路程中,我們的身體慢慢變化,變得遲緩、變得衰老。我們的一切已不像從前,我們走路的步伐、思考的速度、運動的能耐等,每況愈下,這都在告訴你人生已經走上另一個階段。年老並非一個概念,年老是我們從身體狀況深切感受得到的,慢慢衰退、老化,很多事情逐漸力不從心。上世紀法國女哲學家西蒙波娃在《論老年》(1970)(英:The Coming of Age/法:La Vieillesse)中就曾經提到,年老同時也是他人告訴你的:巴士上有人讓座給你、有人叫你一聲阿伯、每天照鏡,額上的皺紋多了、眼皮垂了、視力聽力都逐漸衰失。除了肉體上的衰退,還有精神方面的退化:記憶力模糊、話到口邊的詞彙說不上來、以前想過的問題現在都忘記了、曾經寫過的東西亦記不起了。整體來說,在這個記憶力失去的過程中,我們感覺到最大的就是loss,就是喪失,喪失了我們的能力,喪失了我們曾經擁有的東西。無論你從前如何叱咤風雲、身居要職、位高權重,慢慢的,當你離開之後,這些一切的風光都會隨你而去。這個loss,亦包括你身邊的人。你的朋友可能比你死得更早、你的父母及親人都可能已經不在。我可以大膽講一句,到了我們這個年紀,很多人都已經成為孤兒,因為爸媽早已過世,70歲的時候如果父母親仍健在,想必他們都十分老了,而且更接近終點,好快就要落車。同樣的,我們的伯父、姑母、叔叔,一個一個的長輩先後走了,到最後全部都離我們而去,你會發覺家族的生命鏈戛然斷裂,無聲無息,在上再沒有可親近的長輩,再不能像往日過年時到他們家中拜年,聚聚熱鬧。你面對的景況,心底深處再次感受到loss。此時,你看到的未來,已經不再是年輕人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