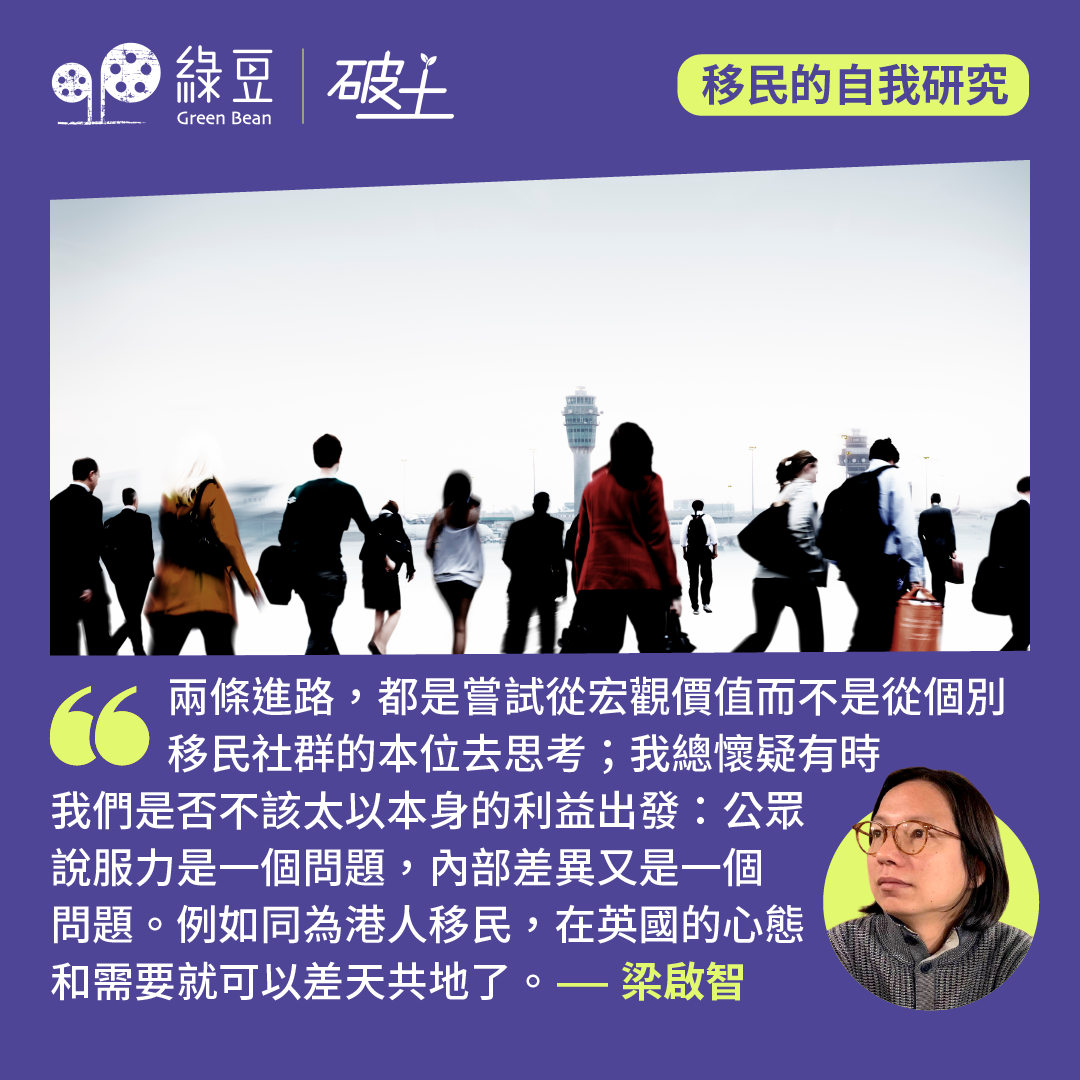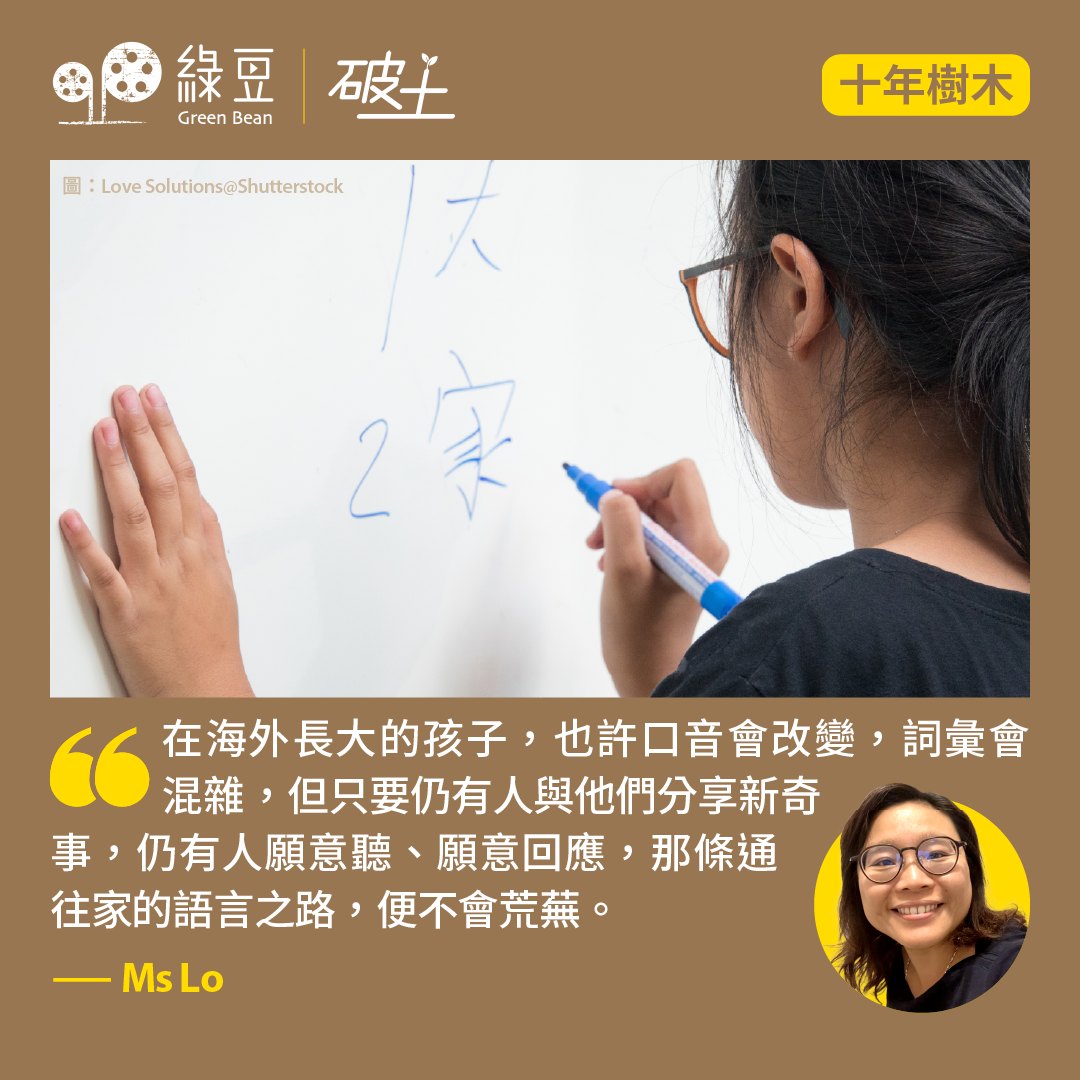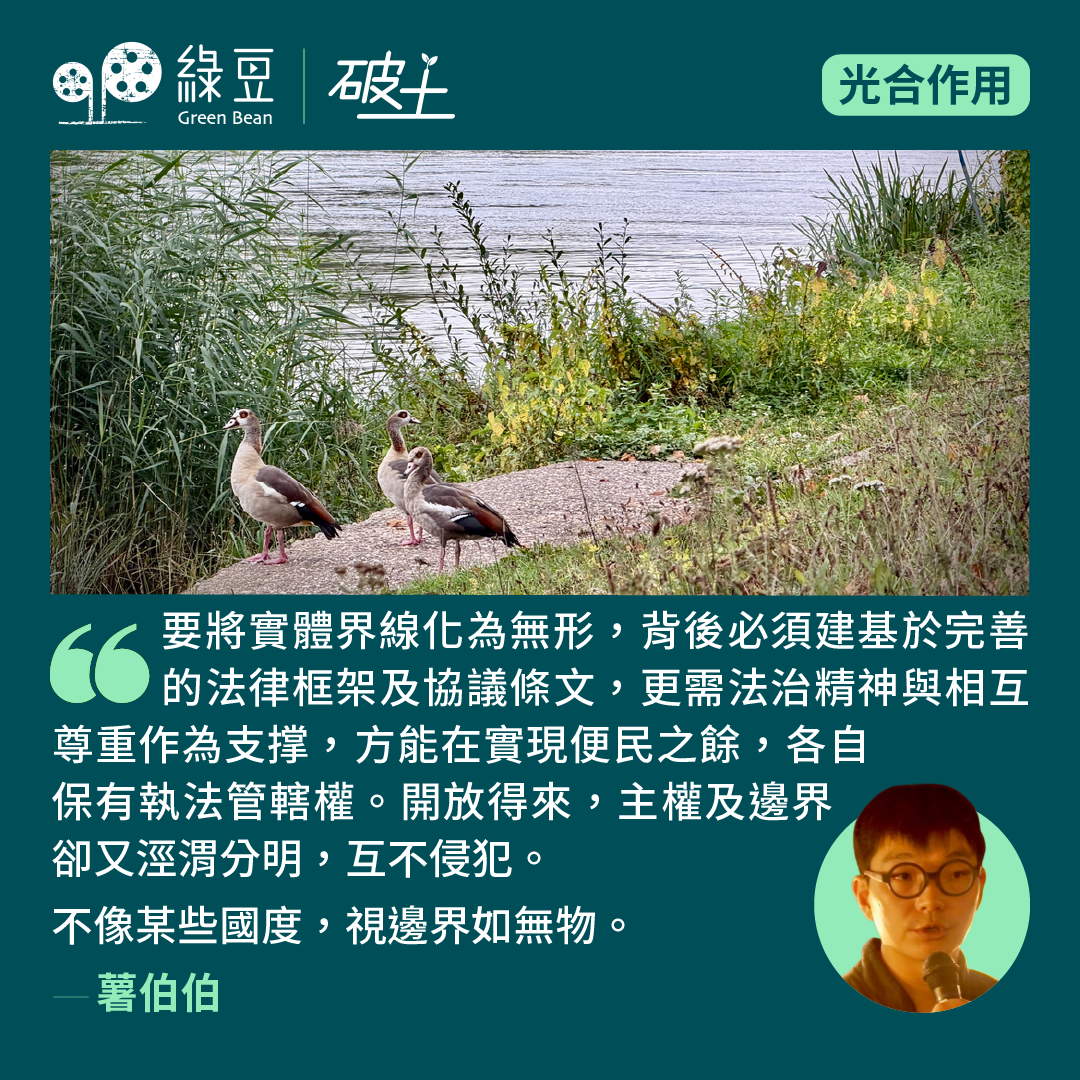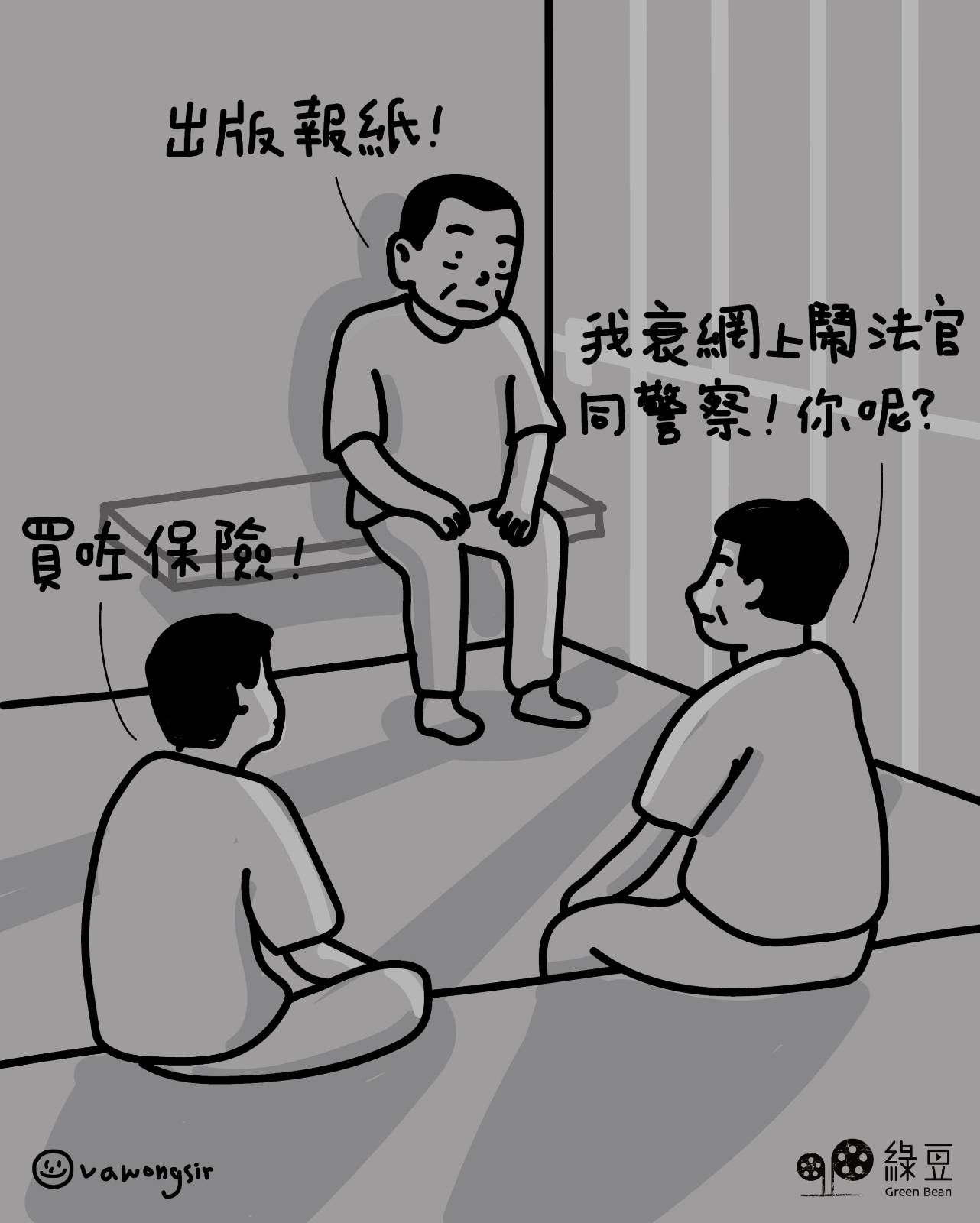收看節目 Henry是香港執業多年的註冊中醫師,飄洋過海舉家移民加拿大,為「儲鐘」放下身段化身超市執貨員,並考取加拿大中醫執照,在數間學院擔任中醫科導師,身兼數職只求一步一步「做回本行」。皇天不負有心人,Henry最終在溫哥華開了自己的中醫診所,成功重遊舊夢。 Henry剛剛到埗加拿大時一邊在超市工作儲鐘,一邊考中醫牌,目標非常清晰,就是希望可以「做回本行」。一年前,他終於得償所願在溫哥華開始中醫診所,並沿用香港診所的名稱,寓意在這裡重新開始。 「其實由未過嚟加拿大嘅時候,呢度已經係定咗嘅一個目標,因為香港本身自己經營一間診所,我係好想喺呢邊可以可以重新開始返嘅,因為作為一個傳承啦,至少我可以將以往一路做緊而恆之有效而幫到人嘅一個事業喺香港嗰邊結束咗,都會想喺呢邊可以重新做返同類型嘅嘢。」 ...
平等(equality)與公平(equity)是社會政策議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兩者的分別,在於如何對待少數。移民研究要處理的正正是少數外來者要如何在大社會當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自然難免會涉及平等和公平的問題。 簡而言之,平等強調對所有的人相同對待,公平強調對不同的人差別對待,以達至現實上的平等。例如對於要坐輪椅的人,我們的社會不會說「所有人都要走樓梯」才是公平,而是會刻意多花成本設立輪椅專用的通道,讓他們也能在後果來說得到公平。當然,正如本欄過去多次提到,「相同的人相同對待,不同的人差別對待」的原則聽起來十分簡單,但要分辨出在哪些時候應該差別對待卻十分困難。雖然法律上常見「受保護階層」(protected class)的概念,列明膚色、宗教、性別、康健、年齡等類別的特殊地位,但實際應用上還是會有數之不盡的矛盾,告上法庭或要求修法的聲音亦是無日無之。 千萬種差別對待的理由 移民在許多地方作為可見的少數族群,在這問題中當然不能倖免。而更麻煩的事情,是移民社群本身存有巨大的內部差異,同一套邏輯對某一個移民社群有利,對另一個移民社群則可變成不利。大學入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我們純粹追求平等,那十分簡單,十萬考生回答同一份考試卷,最高分的一百名考生入學,大學入學處除了考生編號之外甚麼都不知道,這樣最少看起來就是完全平等待遇。但世界不是這樣的,我們從來都會有各式各樣的差別對待,例如有身心缺陷的考生我們會給他們多一點時間完成試卷,畢竟他們往往不見得自願的,一般人認同社會有補償的必要。然而一旦我們開始考慮各種「不自願」的缺陷,則出生在一個因為歷史和政治原因而教育資源貧乏的原住民社區,又算不算是一個提供差別對待的理由?如是者,有些社會又產生了「原住民加分」的制度,彌補社會過去的不公。 很明顯,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些做法。當大學入學(或任何需要競爭的機會)不再只考慮冷酷無情的測試和分數,而開始考慮當事人的處境(特別是種族)的時候,就會吵得特別厲害。有些人是原則上反對,有些人則說現在的社會已經很公平所以不用再考慮。來到移民社群,一方面有移民社群會因為相關政策而得益,但也有不少例外。例如亞裔移民來到歐美社會,父母特別會強迫子女讀書考試,如果大學入學只看考試分數的話便全部都是亞裔學生,大學於是實施配額減少亞裔學生的比例;那麼在亞裔考生的角度出發,則會寧願不要基於族裔的差別對待了。...
如果你已經移民他方,但仍在掙扎之中,以下有些勵志小故事,或許能為你在聖誕佳節當前打打氣。 七十歲的掙扎 吳老太跟隨兒子一家到英國生活,70多歲的她,不會說英語,也不懂用智能電話,初來到時非常開心興奮,但很快問題已經出現。吳老太說:「我從小到大都沒有這樣委屈過,兒子、新抱最初對我還不錯,但一家人一起生活總有衝突,每次都是我讓步才平息。我為甚麼要這樣委屈?」吳老太不能適應英國的生活,一直嚷着要回香港,但香港已沒有家人,丈夫在幾年前過身。兒子也不知如何是好。 事實上,也不單是吳老太的適應,兒子及新抱也是在適應中,而且他們還要努力找工作,照顧孩子。當初只是希望一家人可以一起生活,互相照顧。經歷一年多的掙扎,大家學習改變、互動模式也開始不一樣,慢慢接受不適應才是正常的過程。 最近又再見到他們一家,關係已有明顯改善。兒子解釋:「我們總算安頓下來,過往不習慣講自己的感受,經過這一年的改變,明顯大家也多了說自己的想法,有甚麼不滿也可以說出來。」吳老太也補充:「我跟自己說,後生的已經要顧及很多事情,我也要努力學習,不要只是依賴他們。我現在會好好安排自己時間,出外喝咖啡,叫兒子寫上我要的Latte,遞給店員看,又解決了問題。 不會說,就用身體語言補充一下。我也幫忙照顧孫兒,新抱沒時間煮飯,我便幫忙,大家相處舒服開心。不關我事的,也學會不再多事。 」...
前文提到,一般來說中產於移民後被迫向下流動,往往被視為正常現象。畢竟之所謂社會身分,來來就必然嵌入在個別社會當中,無論是專業證照、街頭智慧還是人脈關係,一旦離開了便很可能會隨之失去,要在移居地重新累積。不過,在全球化底下,近年亦不難見到一些逆向現象,移民後還可以保持原來的社會地位,甚至因為移民而開創出新的事業。 各個移民因由 在解釋新現象之前,先說明一點:為什麼有下流風險,不少中產仍然甘心移民。這兒不外乎出於三種情況。第一,是原居地的情況正在變差,包括精神價值或是物質條件,以致潛在的移居者推算就算移民後會向下流動,留下來可能更糟糕,移民實為兩害取其輕。所以對於那些聲稱「多搵幾年錢才移民」的人,到了發現香港經濟明顯轉差的時候,就是考驗是否真正坐言起行的關口。 另一個古今中外常見的理由,就是移民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下一代。因為不想子女要在受限制的環境下成長,寧願犧牲自己的事業也要帶子女移居他方,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中各次移民潮的其中一個最基本的因素。按黃子華在《秋前算帳》中的說法,如果沒有下一代,其實我們是不用移民的。 最後,就是移居者本身擁有豐厚金錢資本,所以移民後就算失去本來的專業工作,也無損其社會身分。香港寸金尺土,許多中年的中產人士本身在香港已有物業,如果早兩年趁香港樓市高峰期的時候出售,移民後已基本上高枕無憂,可以過半退休生活,時間拿來料理家務種花養狗。曾經遇過資產豐厚的移英港人選擇做貨倉,只是為了打發時間,還說現在因為上班不用過於動腦筋而十分快樂。如果選擇去一些性價比較高的地方,例如台北以外的台灣,則實行成本更低。 向上流動機會 不過對於較年輕的移居者,無論是為了自我認同還是有實際的經濟需要,移民後總會希望重拾向上流動的機會。這點對這一波的移民來說又確有不少可能性。...
按照經典的社會理論,中產在移民後往往會經歷社會經濟地位下跌。在這一波移民潮當中,身邊也見到數之不盡的案例。不過與此同時,可能是時代變遷,又或香港移民本身的特質,也遇到不少例外情況,移民後仍然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以前更風生水起。 傳統來說移民後社會經濟地位下跌,往往是和工作相關。現代人的身份地位如果不是含金鎖匙出世,很多時候都是來自他們的工作;尤其是中產,他們不少都是專業人士,不單收入比較高,在社會上很多時候也較受尊重。移民對他們的衝擊可以十分直接,畢竟甚麼是專業本身就因地而異,香港很吃香的專業例如金融服務在某些地方可能是沒有需求的,反而某些在香港不被重視的工作如維修通渠,在當地才是真正專業人士。 專業資歷認證 另一個常見的原因,則是專業資歷要靠政府認定,移民後原有的資歷不一定能帶過去,當地很多時候會不予承認。沒有資歷認證,便做不了原本的工作,本來的專業人士要轉做能力錯配的工作,於是工作和社會地位都會下降,亦是移民後向下流動的常見案例。 資歷未能獲認證原因可以有很多:最常見的說法是當地專業有保護主義,不歡迎外來人士爭飯碗。不過這說法可能只是部分事實,後面通常還會有些實際理由。例如在美國,即使是在國內,許多州份的律師資格也不互通,畢竟每個州份的法律都不太一樣,更別說要到別的國家。律師要看法例,但許多專業也是和法律打交道的,醫生和工程師都要知道當地的監管制度才能有效工作,移民後資歷難免無法自動承認。 即使不看法律的部分,各地對專業內容的要求不一樣,有些知識或技能在當地看得很重要,在香港考牌時卻未必有考,也難怪當地要花時間釐清是否合適。又或者有些專業在香港本身也經歷過轉變,以前取得比現在要容易;當地查看過後,不接受某些持有舊資歷的香港申請人也有他們的道理。 當資歷不被承認,那可以怎麼辦?最直接就是重新考牌,但現實上有時還有迴旋的空間。舉個例,駕駛執照在國際間不時會有各種不協調,甲地的駕照和乙地不能互換,但甲地和丙地可以,而丙地又和乙地可以,於是便有人會繞個彎避開本來的資歷阻隔。有些專業資格國際上原來也有類似的情況,也見過有港人移民通過第三地取得移居地的資歷。至於當利用這方法的人越來越多,當地的監管機構會選擇「堵塞漏洞」還是索性直接開方便之門,則很大程度按各行各業的具體環境而定。例如英國就決定開放授予海外教師「合格教師身分」,為許多移英港人教師帶來重執教鞭的希望。...
( 編按 : 此專欄內容均為真實處境,旨在反映離散對個人和家庭帶來的衝擊,以文字與大家一起走過荊棘。專欄文章經編輯在文字上修改處理,確保內文提及的人士身分保密。) 這是我第一次跟這個家庭見面,他們是一致地沒有表情,頭頂看似有一朵黑雲跟著他們每一個人。16歲的女兒手上拿着手機,獨自坐在一旁;張爸爸也找到另一角落坐下;張媽媽看看他們各坐一邊,想一想便走近女兒坐下來。 張媽媽先開口:「我們來到這裡差不多三年了,但我們的關係愈來愈不妥當。特別是女兒跟她爸爸的關係,我夾在中間不知如何是好。」女兒目無表情地看着手機,問一句答一句;張爸爸也跟女兒一樣,不願意說話。 張媽媽嘆道:「雖然我們三人都同意移民,但來到了卻各顧各,我快要爆炸了!」...
近年到美加澳紐等地的大學參與學術交流活動,不時會聽到主辦單位在開場之前會先做一個「原住民土地確認」(Land Acknowledgement),向參與者說明活動所在地點的歷史。一般的宣言會包括「我們今天相聚的地方是(當地原住民民族)的傳統及未被割讓的領土」等字句,說明今天大家來開會的會場歸根究底是從原住民手上強搶而來的。 這種宣言大約是近十多年來開始流行,用意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表達對原住民的尊重。有在加拿大的港人組織也在網站上展示類似的宣言,鼓勵赴加港人多認識加拿大原住民的歷史。對於這些做法,有些人認為是對歷史的尊重,但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無論是開明派或保守派,都有反對聲音:雖然出發點未必一樣,但都認為這些儀式只是門面功夫,做出來自我感覺良好而已,口惠實不至。 對此,我問過一些當地朋友,卻又未至於完全反感,反而頗肯定其作用。面對白人主流對可見少數族裔的歧視,這些做法起碼可以警剔那些白人優越主義者:別忘記,你們自己也是移民後裔,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並不是你們。 「自古以來」 沒錯,在美加澳紐等移民社會,除了原住民以外,所有人某程度上都是移民或移民後代。因此,所有今天針對新移民的說法,對當地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同樣適用。例如說墨西哥裔移民到了美國之後繼續說西班牙語,建立只說西班牙語的小社區,引來不少批評;但是別忘記美國本身沒有法定語言,那些批評新移民沒有轉用英文的,也不見得自己有學會美洲原住民的語言。如果說擔心移民會取代原有的生活模式,則不得不說白人才是這方面的模範生。在此脈絡下,批評者不是真的關心文化承傳,只不過是害怕自己的主宰地位不保。 也有論者把類似的議論延伸到台灣。過去台灣常有「省籍之爭」,即「本省人」和國共內戰後遷台的「外省人」之間的問題。有評論就認為要把時間尺度拉闊,所謂的「本省人」也是從中國大陸移居來台,只是再早幾百年而已,然後延伸出台灣有七代移民的說法。...
( 編按 : 此專欄內容均為真實處境,旨在反映離散對個人和家庭帶來的衝擊,以文字與大家一起走過荊棘。專欄文章經編輯在文字上修改處理,確保內文提及的人士身分保密。) 你家中有沒有怪獸?怪獸的特徵是很難跟別人相處,一不順意便會發脾氣,亦不能接受生活上些微改動,好像一個長不大的孩子,但同時又會不斷向別人訓話,對方不同意的話,又會是另一場爭執。敏儀跟丈夫二人移民到英國,大家只想嘗試在新環境生活。在香港的時候,兩人周末各自約朋友,偶而一起吃飯去旅行,相處上沒有太大問題,惟來英不久,問題卻出現了。 為甚麼你變了?敏儀說:「現在像困獸鬥般,大家在一起快要窒息,我想自己出外走走也難。」丈夫卻不解的說:「以前的你,不是這樣對我的。來了英國後,你整個人變了。以前我有甚麼要求,你也會順着我的意思,不會像現在處處頂撞我,甚至不聽我的話。」敏儀看起來是一個很有能力的女士,見面時候也悉心打扮,反觀丈夫卻像沒精打彩。問敏儀他們何時開始出現問題,她說:「其實一直以來我對他很遷就,他要怎樣,我都會跟著做,因為我很怕衝突,不想吵架。但現在到了在新環境,一切都改變了,我也不能每樣事也跟足他的想法去做,而且他的方法不一定好。但當我不同意他的想法,他就會發脾氣,我受不了每天跟他吵架,但我又不能再事事跟著他的想法去做。」丈夫不解:「我真的不明白,在香港時,你事事也會問我意見,而且好像很依賴我,為甚麼來到這裡卻像另一個人?」敏儀嘆氣說:「在香港,我們沒有太多改變,為免跟你吵架,我選擇沒有自己意見,讓你作主。但在這裡你又不喜歡出外,只想留在家,我想自己出外走走,你也不高興。」 怪獸是如何養成原來一直以來,也是敏儀遷就丈夫,覺得很多事也是小事沒有所謂,便沒有出聲跟著做。久而久之,丈夫也覺得妻子跟隨他的方法去做是理所當然,沒有想過原來只是她不想有衝突,並不是她同意自己的做法。敏儀再說:「有時只是稍不同意你說的一句話,你就會不斷地向我訓話。上一次差不多說了兩個鐘,所以我寧願不說出自己想法,或許大家關係會好一點。」丈夫聽到敏儀這樣說,確實不是味兒,好像他是一隻怪獸一樣,不受歡迎,別人也怕了自己。 敏儀再說:「你的朋友、妹妹也不想跟你說話,每一次也像被訓話似的,只有你說,你察覺不到嗎?」敏儀丈夫成為家中的怪獸,是怎樣養成的?敏儀語帶激動大聲道:「我有份做成的。 如果不是我怕衝突,我不會過分遷就他。我就算受了氣,也只會跟朋友見面散散心,以為這樣我們便可以相安無事走下去, 我不應該這樣縱容他到這個地步,沒有人想接近他。我真的在考慮分開是否對大家來說會好一點。」丈夫一臉無奈,他答應一同來接受輔導治療,全因害怕敏儀真的要離婚,現在聽到妻子這樣說,也不知道究竟要怎樣處理。 貴乎真誠溝通移民過程,對關係中的角色、責任甚至界線,也要重新定位。...
( 編按 : 此專欄內容均為真實處境,旨在反映離散對個人和家庭帶來的衝擊,以文字與大家一起走過荊棘。專欄文章經編輯在文字上修改處理,確保內文提及的人士身分保密。) 家明今年14歲,去年跟隨父母到英國,對移民也有著很大期望,特別是香港功課壓力大,更覺得移民是一個重生的機會。 來了已經一年了,跟父母的關係卻愈來愈差。家明跟爸媽差不多隔天便吵架,吵的多為了日常生活事,例如很晚也不睡覺、不洗澡、不做功課、不同枱吃飯,父母看不過眼便出口罵,見家明不作聲,父母更手足無措,變得更激動,只好吵鬧更大。 這時的家明,便會比父母更大聲的用粗口大罵,媽媽只好不作聲在一旁痛哭,爸爸見狀就更激動,有時雙方甚至動起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