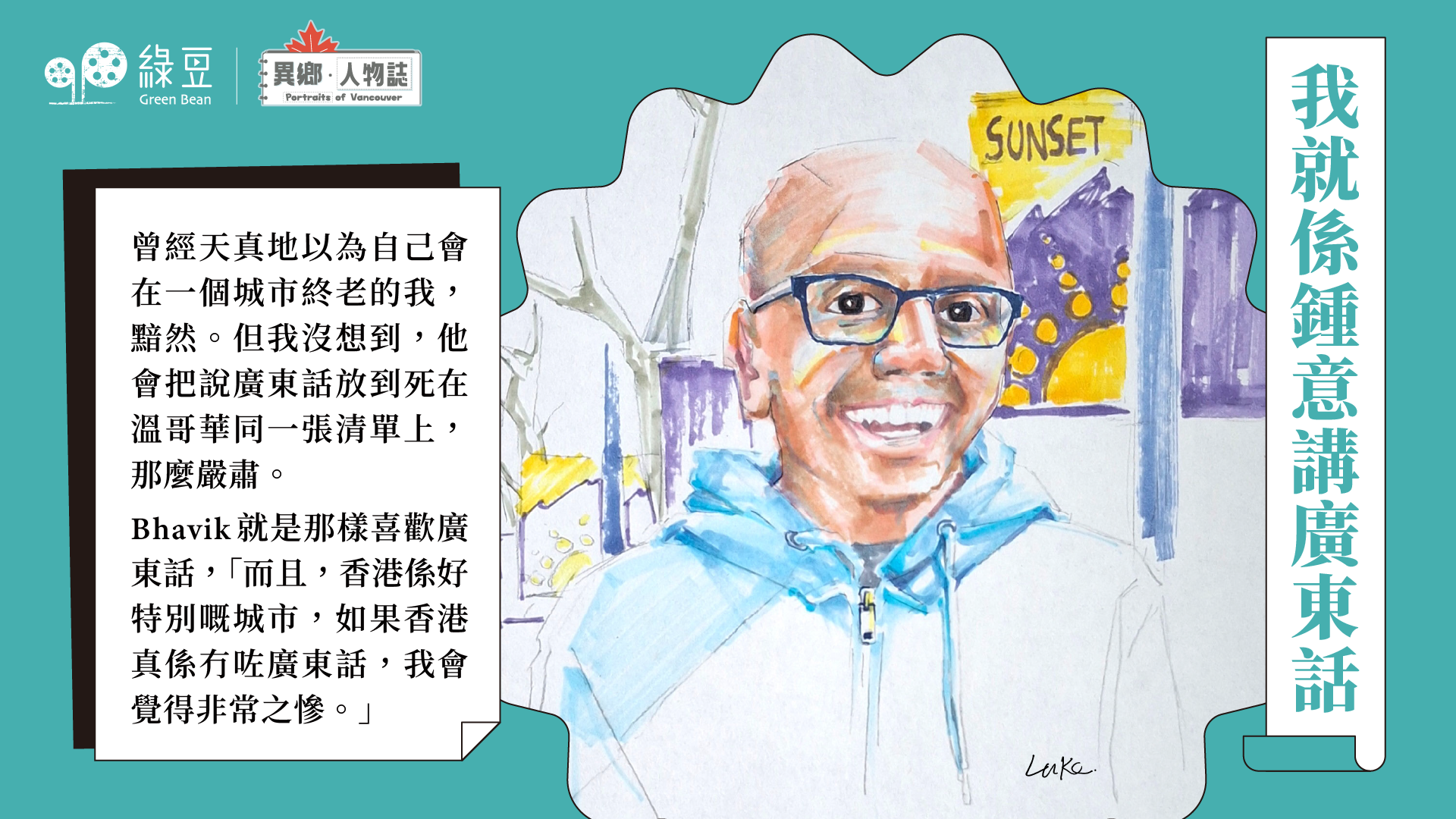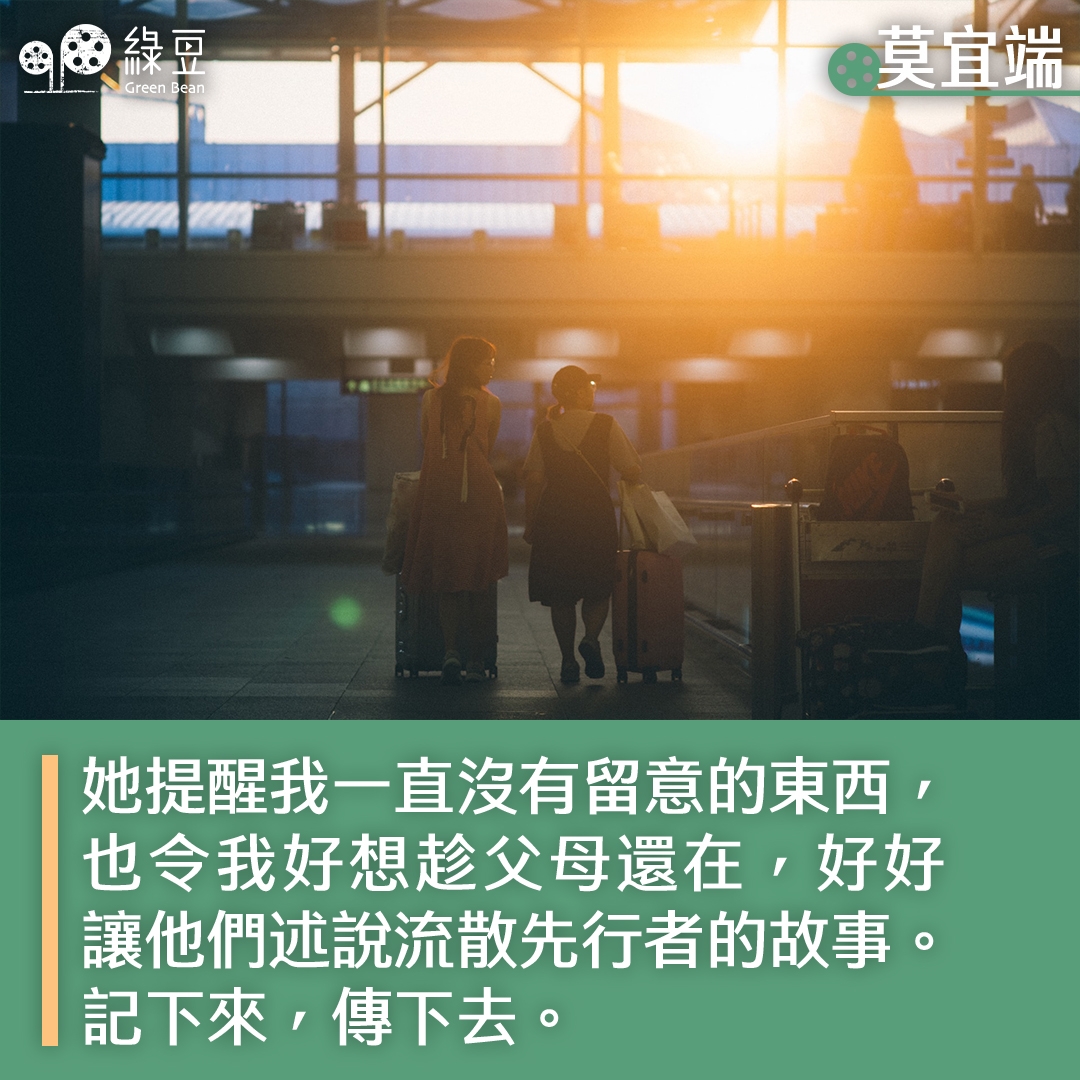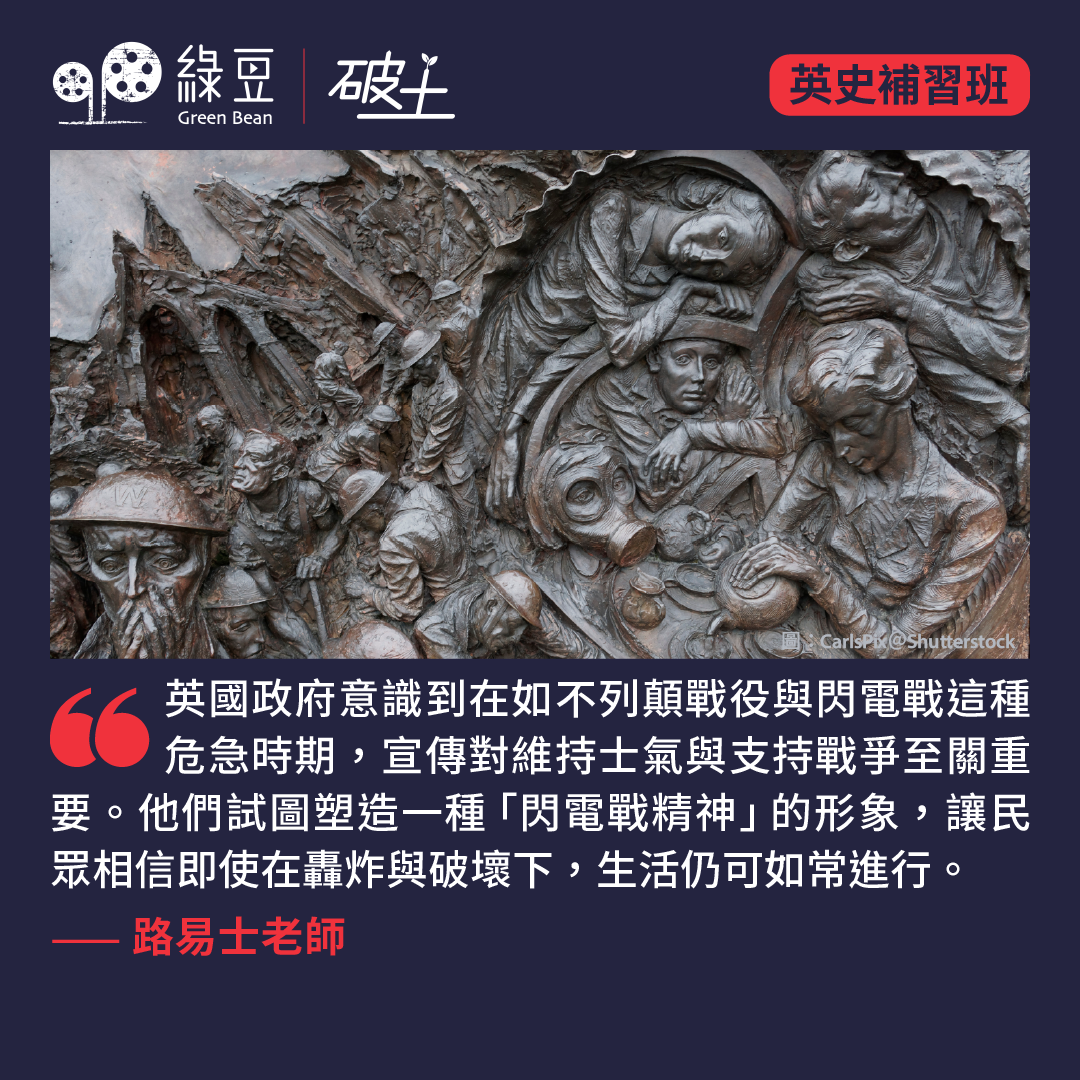每隔一段時間,離散港人社群好像都會爭吵一次「香港已死」這題目。我理解為什麼很多人覺得這議題重要,畢竟它關係到社群本身的角色,例如各種對承傳香港文化和價值的想像。不過要討論香港到底是否已死,又或離散港人社群到底要承傳什麼,難免必先回答香港本身是或不是什麼。然而回頭再想,關於香港本質的爭議在離散港人這概念出現之前已經有過不止一次。如果把每次爭論都算進去,香港可能已經「死」了很多次,又或者已經輪迴轉世了很多次。 離散港人如持有「香港已死」的觀點,後面不少都預設了香港必然要有某些內容或特質,這個香港才有「資格」被稱為「香港」,否則就是虛有其表,行屍走肉。同一邏輯下,也聽過不少離散港人聲稱「要離開香港才能當香港人」,後面也是假設了香港不止是一個地理位置,而是一種實踐。 「什麼是香港」 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出發,「香港是什麼」向來是一條難解的問題,並在九七前後出現過好幾波的爭論。這些爭論往往是在香港面對挑戰的時刻出現,因為大家很擔心香港正在消失,所以覺得很有需要定義清楚「什麼是香港」,讓我們得以釐清要捍衛的是什麼,要排除的又是什麼。 例如2010年以來的本土思潮,當中有一些比較教條主義的訴求,曾經聲稱只有在香港出生的(甚至是只有在九七前的香港出生的)人方可被稱為是香港人。當然,這說法很快受到質疑,因為不少著名的本土思潮領袖,本身也是九七後在中國大陸出身,後來才移居到香港。 於是又有另一種聲音認為香港代表了一系列的制度和社會價值,例如法治精神和公民參與,要認同這些制度和社會價值才算是香港人。問題又來了:以前的選舉有最少四成選民會投票給不太捍衛這些制度和社會價值的政黨,他們又算不算香港人?這些制度和社會價值在香港的歷史也不是那麼長,不少最少要在1970年代之後才普及,那難道在此之前的香港就不是香港?更別說在「虛擬自由主義」的審視下,這些價值恐怕本來都甚為無根和脆弱,以此作為香港價值的標準是否有點兒戲? 過往的論述...
我在「溫哥華街坊會」的行山活動上認識Bhavik。參與者多是幾年間落腳溫哥華的香港人,大夥兒在Seymour山上拉成長長的隊伍。那些話語碎片散落山頭,旋律高低起伏,節奏緊促跳躍;都是流落異鄉的港式廣東話。印裔的Bhavik加入了這幅豐富的聲音畫布。 「我之前唔係咁鍾意學語言,但係宜家唔單只想練好廣東話,仲好鍾意講。佢嘅聲音好好玩,好explosive(爆炸性),其他語言冇咁特別。」Bhavik的廣東話說得慢但清晰,除了夾雜了幾個零星的錯調外,稱得上道地。他在溫哥華出生,是移民第二代,平日在家用英文和印度母語Gujarati夾雜着溝通,原本沒打算學第三種語言,沒想到2018年加入一間香港人開的電子公司半工讀,天天被新語言轟炸,從此打開了廣東話耳朵。他突然發現,自己已在不知不覺間撿到幾個單字,像是「一二三」和「呢度、嗰度」。他自忖如果用心學、趁機學,應該會學得快,於是報讀廣東話小組,一學就是兩年,愈學愈喜歡,「譬如我都幾鍾意成語,好多時會講『言出必行』,我又鍾意講『落狗屎』,因為溫哥華冬天成日落雨,好有feel。」 有趣是,Bhavik說不同語言時,自我感覺會產生微妙變化——說廣東話時直腸直肚,「有嗰句講嗰句」;說英文時禮貌周周,從不爆粗;Gujarati介乎兩者之間,也是親人間獨特的話語。Gujarati是印度廿二種官方語言之一,在溫哥華說的人少,Bhavik只在家裡說,所以說不流利。對他來說,最能表達心意的不是母語,而是英文;但他視英文為溝通工具,沒建立起情感結連。Bhavik真正放在心上的,是廣東話,「將廣東話學到呢個程度,係我其中一個好大嘅achievement(成就),我用好多力氣去維護佢,想要投入呢種語言嘅生活。我唔想退步,所以同人傾偈好重要。」...
收看節目 莫宜端經常帶我們在英發掘寶藏,正當期待著她分享暑假有甚麼好玩的搞作時,她欲告知夫婦兩人暑假都要工作,沒有road trip沒有探險。不過這個暑假她仍是找到寶藏——孩子在家的成長。她還提醒,一家由香港移居到外地這場大遷徙,永遠不單止是大人的事,孩子其實已「升呢」,成為你的同路人。《破土》莫宜端|英倫筆端|大遷徙的同路人|原文見綠豆Patreon https://bit.ly/3ZjBz3J ...
收看節目 莫宜端經常帶我們在英發掘寶藏,正當期待著她分享暑假有甚麼好玩的搞作時,她欲告知夫婦兩人暑假都要工作,沒有road trip沒有探險。不過這個暑假她仍是找到寶藏——孩子在家的成長。 她還提醒,一家由香港移居到外地這場大遷徙,永遠不單止是大人的事,孩子其實已「升呢」,成為你的同路人。 《破土》莫宜端|英倫筆端|大遷徙的同路人|原文見綠豆Patreon https://bit.ly/3ZjBz3J...
收看節目 莫宜端跟上司談起家族故事,原來對方父母是柬埔寨華僑,經歷赤柬政權,逃離出生地,輾轉在澳洲落地生根。但兩人從沒有向子女提及半點在柬埔寨的事情,莫的上司曾經埋怨及質疑父母,後來長大了才明白父母不願提,或許是不想掀起中心的傷口。 作為同樣是流散的家庭,我們呢?還有,比我們還早已經歷流散的上一代,其實他們也是流散的先行者,聽聽他們的故事,或許可以互相療傷。 ...
人們常說,時間能沖淡一切。但對於移民的人來說,時間究竟是要沖淡,抑或是用來累積雜陳的五味,為自己、為下一代積累抵禦暗黑的溫度和熱度?最近跟一個流散者後代的對談,對這個令人糾結的想法,又清晰了一點。很多時,學校只有一個駐校言語治療師,雖然團隊會有其他同事,如職業治療師、教師、音樂治療師、社工等,但若有專業上的難題或疑問,並不容易找到行家請教。所以能得到僱主協助或向一位有心的資深治療師學師,實在是極之幸福。更開心的是,可以奉旨出城受培訓,還有督導同行。機會難逢,又怎會只請教臨床事宜?我就乘機跟我的督導多聊多學多想。不能提的故鄉督導Jane(假名)的父母是柬埔寨華僑,原本是小商人,但自赤柬掌權,兩人眼見一些親朋摯友失蹤的失蹤、逃亡的逃亡,於是兩人逃離出生成長的地方,去到越南,然後再遠走澳洲,Jane和她的兄長就是在澳洲出世的。她說,父母好緊張子女還會不會用中文寫自己名字,於是在澳洲要孩子每周上中文學校學中文。不過,青少年期的她非常不明白,一堆問號全沒被解答,包括:為何父母在人前絕口不提自己來自柬埔寨?為甚麼在社區活動和鄰里間介紹自己族裔時,不提柬國、不提華裔,一概只答自己是「海南人Hainanese」?何解每每問及父母少時在柬的生活時,他們總是支吾以對?不知道,不明白,加上踏入青春期,就常因為父母對過去不說不講而惱恨、埋怨。Jane說,直到自己讀大學了,心想他們不想講那借來的時間、回不了去的地方,也就算吧,但自己一直好想到柬埔寨遊歷。於是大學畢業時跟媽媽詳談了一遍,說很想去柬國逗留幾個月尋根,希望他們提供些少基本時、地、人、事的資料,好讓她自己到這兒看看,那兒走走。這樣,她的第一次尋根之旅就完成了。淌血的傷口我問她,尋根後呢?三個月就如走馬看花吧。她說。總算親身到了父母成長的地方,去過已重建的村落,知道長輩已逝親人的一些故事。不過,對她來說,最重要的是,對父母的有口難言,多了體諒和同理心。說言語治療一定要涉獵心理健康、創傷治療的皮毛,她說,終於,她明白到父母其實一直未從逃難的創傷中治癒過來,所以只想從新生活、教養兒女中忙忙忙,就會不用回頭,觸摸淌血的傷口。Jane回到家中,沒有長篇大論,但可能父母見有女初長成,卻沒有因為他們暗黑的前半生而有何負面影響,眉頭也放鬆了。已婚的Jane說,這個暑假,會帶父母和新婚丈夫,一同到柬埔寨旅遊兩周,是第一次與父母同遊這地呢!太好,Jane有一雙好耳朵,愛父母所以想知他們是如何成為今天的他們,再靜下心來傾聽,終於對自己的過去有所發現。對比之下我發覺,在外子和我輩不少朋友中,不知怎的,卻好像對長輩的過去所知不多……流散先行者前陣子,幾個昔日社關路中的戰友相聚英倫,他們在周日跟我家參加主日崇拜。我們教會有個習慣,就是牧者會先讓大家分小組,討論一個跟當天講道有關的問題,然後才開始講道。今次,投影片的問題是 :「你的父母是做甚麼職業的?祖父母又是以甚麼為生的?」有的教友提到祖家幾百年都是農夫,族譜寫得清清楚楚。到我們幾個在香港出生成長的人分享時,不約而同對祖父母輩的生活近乎一無所知。我算是答得最清晰的了,但因為祖父在父親幼年已在三反五反中遭難,家族其他的經歷都已難以細究了。送走朋友後,我仍在想,流散,我們的長輩才是先行者。或許是流散確實有太多讓人很難過的事情,父母總不想痛苦在我們這一代延續,又總以為忙忙忙就會忘掉不快事,所以情願欺哄、情願掠過?!將流散者故事傳下去噢,跟阿Jane的談話還未完。她問我一家人來英一年多,適應如何,孩子有問起香港的傷心事嗎?我說有,還告訴她孩子其實不小,所以幾年來出生地的變化和失去,他們都應該知道。就在那刻,Jane很認真地、直直的望著我說:「Don’t assume that they know.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