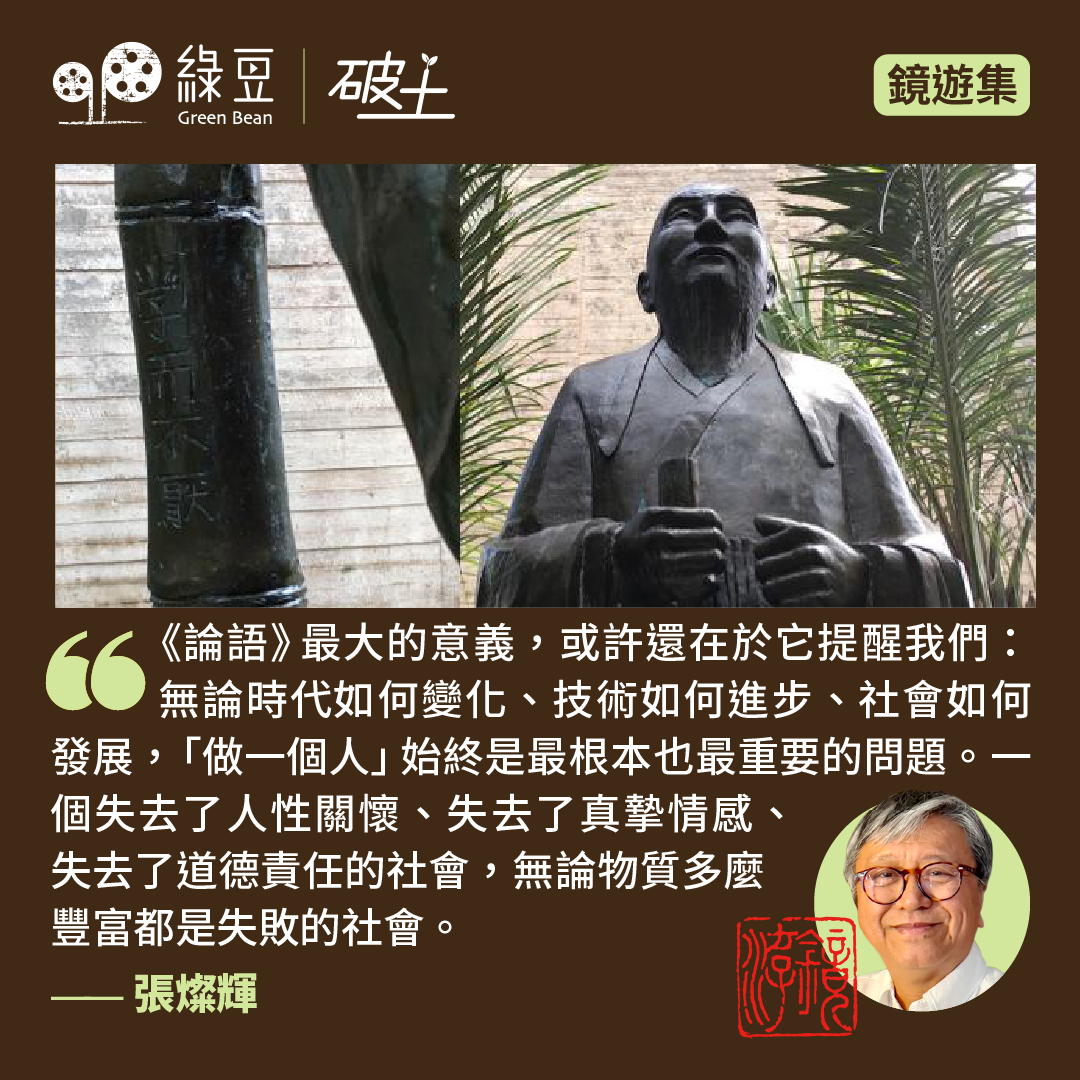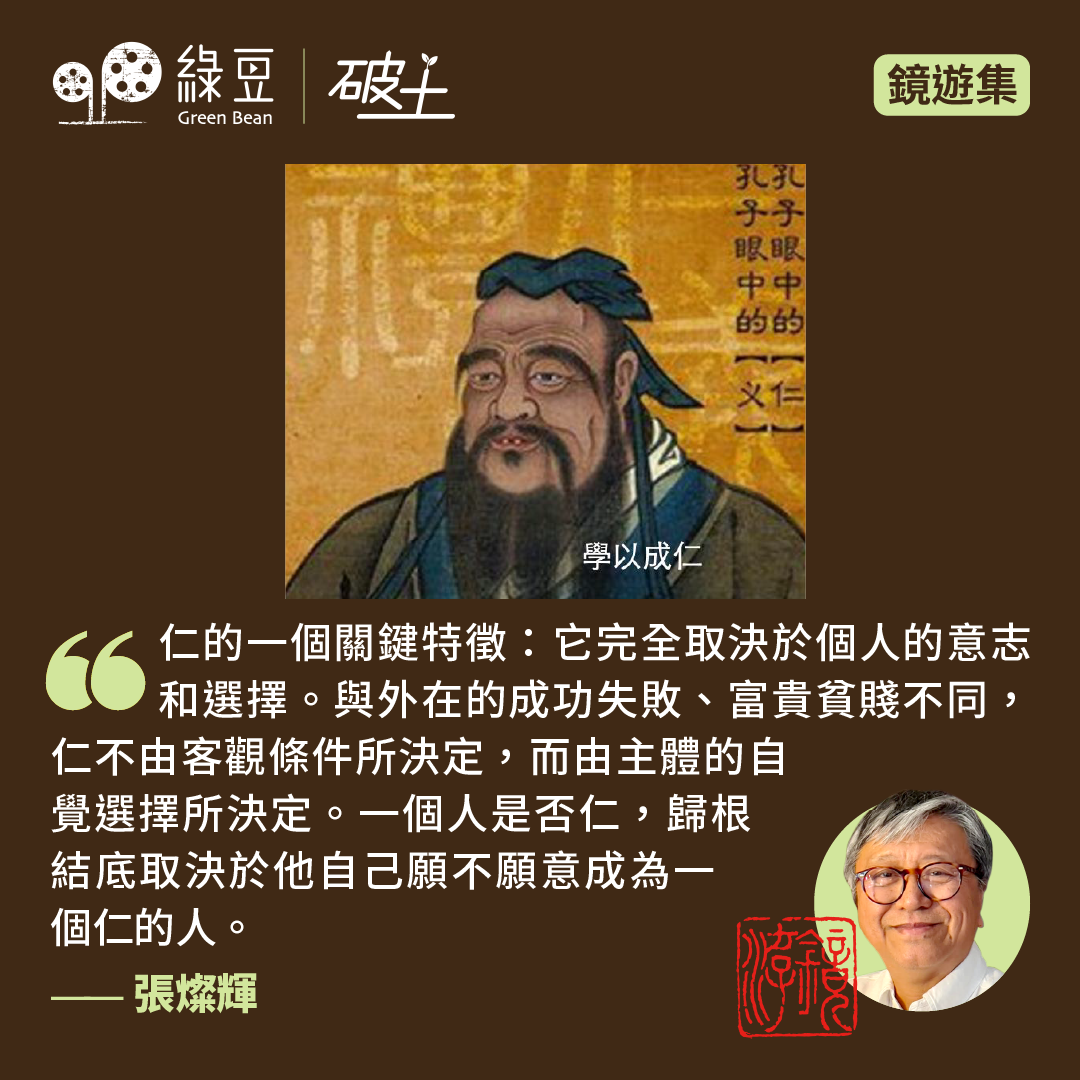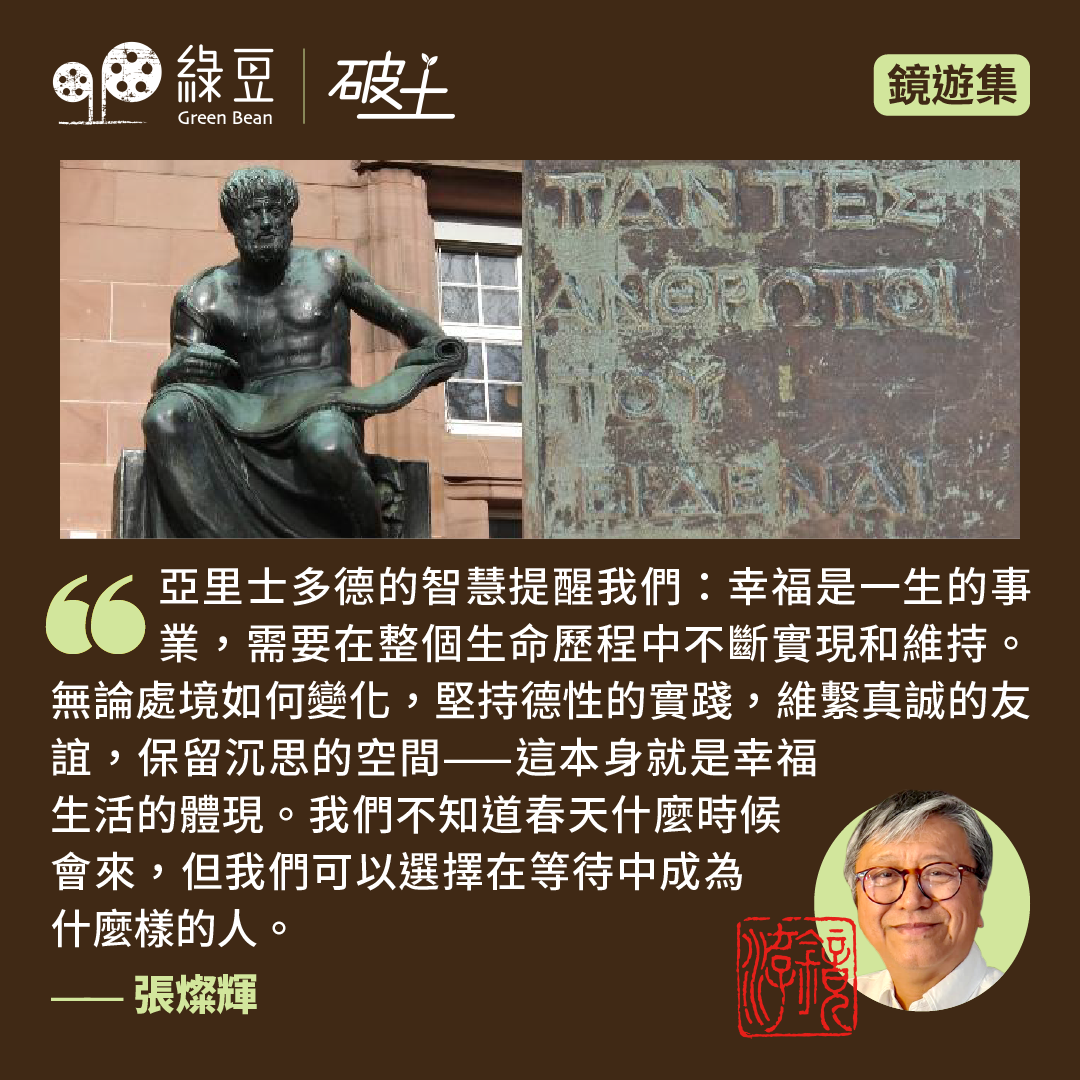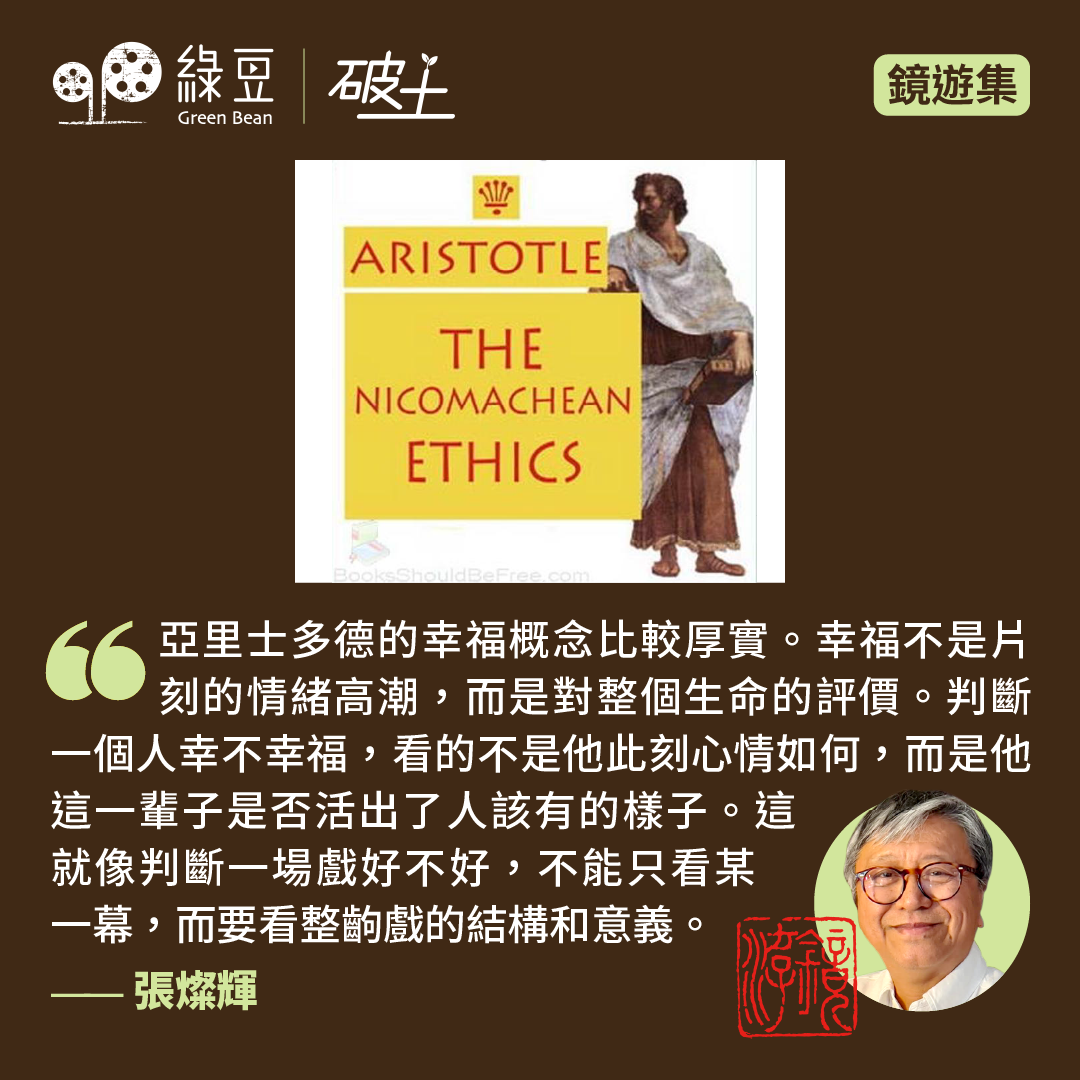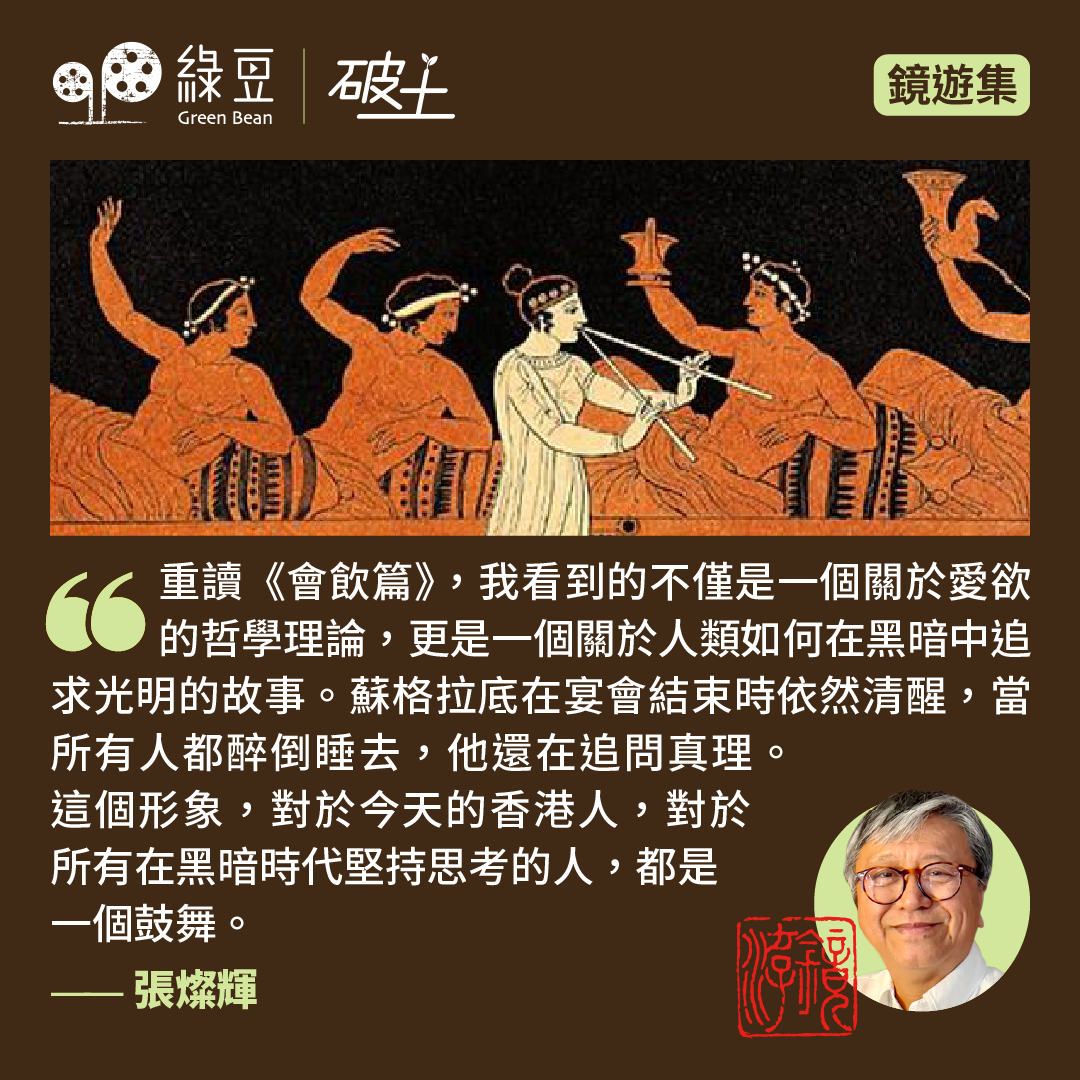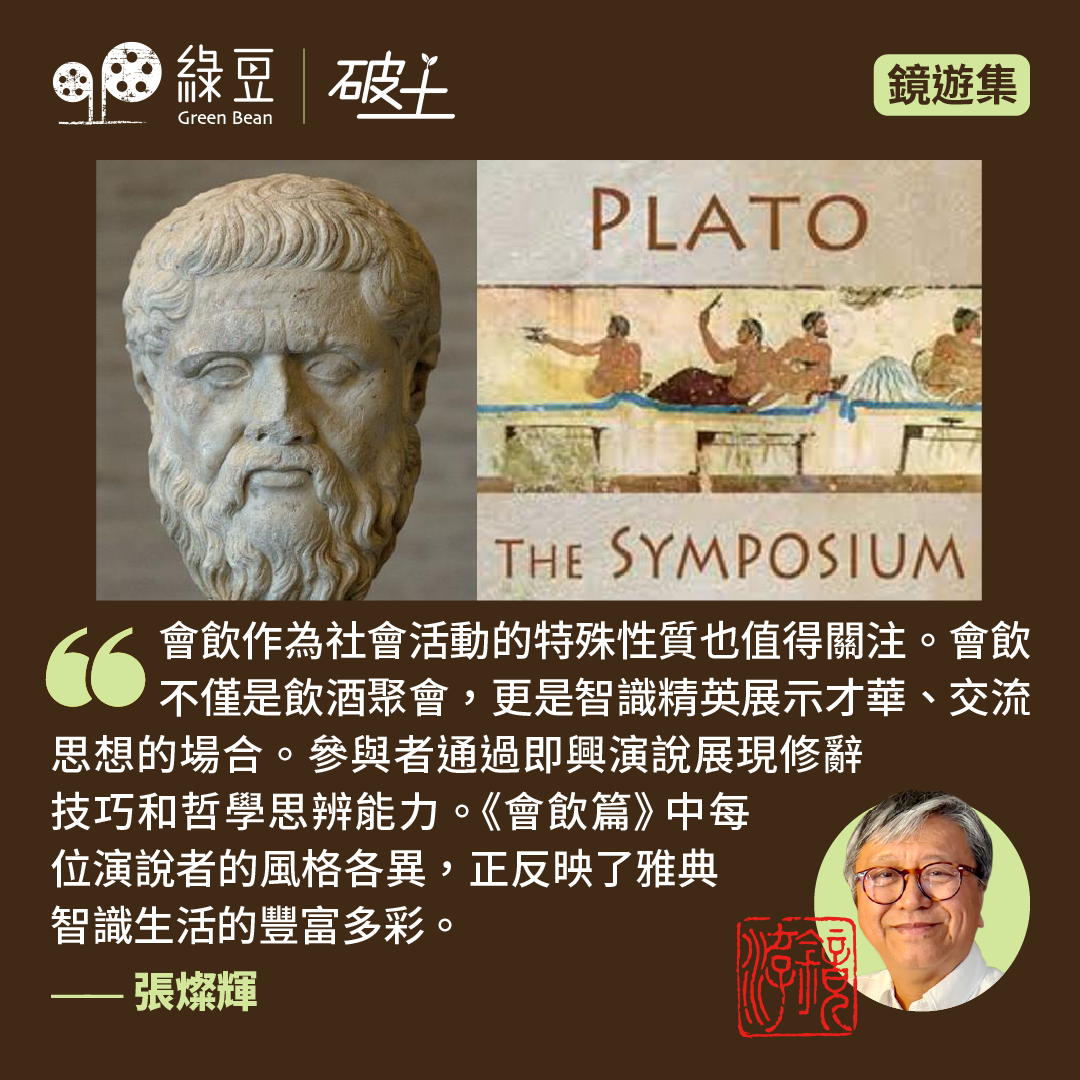儒家的人倫關係 理解了仁的核心意義之後,可以進一步探討儒家如何處理具體的人倫關係。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從具體的人際關係出發來談論道德,而非從抽象的原則出發。這種思路使得儒家倫理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可操作性。 以情為基礎的人倫觀 儒家的人倫觀以真實的情感為基礎。這與西方某些倫理學強調理性、義務或契約的進路有所不同。儒家認為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連結不是理性的計算或法律的約束,而是自然的情感。 一個人處於多重人際關係之中:對內有與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及其他親戚的關係;對外有與師長、朋友、同學、同事、鄰居、公職人員的關係。這些關係構成了一個複雜的網絡,而每一種關係都有其特定的情感基礎和行為規範。 這種人倫觀的特點可以用「中情西愛」來概括。西方文化強調「我愛你」的直接表達,而中國文化更注重「有情人」、「相思」這類涵蓋面更廣的情感。儒家所說的「仁」,就包含了親情、友情、愛情等多種情感,而不限於某一種特定的情感。 這種以情為基礎的人倫觀體現在儒家對「孝」的理解中。如前所述,孔子批評那種只知供養卻不知孝敬的做法,因為真正的孝必須包含發自內心的敬愛之情。同理,真正的友誼、夫婦之愛和兄弟之情,都必須建立在真摯情感的基礎上。...
儒家的根本問題 要深入理解《論語》,首先需要把握儒家思想關注的三個根本問題:人禽之辨、義命分立、仁禮之辨。這三個問題構成了儒家人生哲學的基本架構,也是理解「仁」這個核心概念的必要前提。 人禽之辨:為甚麼要做一個人? 儒家思想的起點,是對人之所以為人的追問。孟子說過:「人之所以異於禽於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下》)人與禽獸之間的區別其實只有一點點,普通百姓把它丟掉了,君子卻把它保存下來。這「一點點」的區別,就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所在。 在《論語》中,孔子通過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種區別。子游問什麼是孝,孔子回答:「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2.7)如今人們講孝,不過是說能夠養活父母就夠了。然而犬馬一樣能得到飼養,倘若不存心孝敬,贍養父母和飼養犬馬又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例子深刻地指出,人之為人,不僅在於外在的行為,更在於內在的情感與態度。單純的物質供養構不成真正的孝道,因為那只是生物性的需求滿足。真正的孝必須包含發自內心的敬意與關愛,而這種情感正是人與禽獸的根本差異。 孔子對此的態度非常堅定。當長沮、桀溺兩位隱士譏諷孔子「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勸子路跟隨他們避世時,孔子失望地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18.6)人不能和鳥獸同群,我不同人打交道又同誰打交道?天下太平的話,我也就用不著提倡改革了。...
幸福與友誼的內在關聯 在理解了幸福和友誼各自的本質之後,我們需要探討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繫。亞里士多德明確提出了一個問題:幸福的人是否需要朋友?這個問題的答案對於理解幸福的完整圖景至關重要。 有人認為,既然幸福的人是自足的,他們就不需要朋友,因為他們已經擁有了善的事物。歐里庇得斯(Euripides)的詩句也表達了這種觀點:「當命運對我們微笑時,何需朋友?」然而,亞里士多德認為這個結論是荒謬的:「如果我們將所有善歸於幸福的人,卻不給他朋友,這看起來很奇怪,因為朋友被認為是最大的外在善。」 「將完全幸福的人表現為孤獨者是荒謬的,因為沒有人會選擇獨自擁有世界上所有的善,因為人是社會性動物,天性就是要與他人一起生活。」這個論證揭示了自足概念的微妙之處。自足並不意味著完全的獨立或孤立。相反,它包括了與父母、子女、朋友和同胞公民的關係,因為人天性上是社會性動物(zoon politikon)。 亞里士多德進一步論證:「善的朋友本質上對善人來說是可欲的。因為自然之善對善人來說本身是善和愉快的。」、「既然善人對朋友的感覺就像對自己的感覺一樣,因為朋友是另一個自己——如果所有這些都是真的,那麼對一個人來說,朋友的存在就像自己的存在一樣可欲,或幾乎一樣可欲。」 使自己的存在可欲的是對自己善的意識,而這種意識本身是愉快的。因此,一個人應該同樣意識到朋友的存在。亞里士多德指出:「這可以通過共同生活和交談、分享想法來實現——因為這似乎是共同生活在人類意義上的含義,而不是像牛一樣在同一片田野裡吃草。」這裡亞里士多德特別強調,人的共同生活不同於動物。人的共同生活涉及思想和言語的交流,涉及意義和價值的分享。...
(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歡迎各方讀者投稿。) 2025年12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頒下了一份長達855頁的判詞。三名由行政長官欽點的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李運騰及李素蘭——裁定黎智英「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串謀刊印煽動性刊物」共三項罪名全部成立。法官在判詞中指,黎智英「自成年以來一直懷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怨恨與仇恨」,其「唯一意圖」乃「尋求中國共產黨的覆滅」,法庭並用上比喻:黎智英的行為「類似於一名美國公民,以幫助加州為藉口,向俄羅斯求助以推翻美國政府」。 這段判詞值得逐字細讀。它把一個人數十年來在報章專欄、公開演講和國際場合所表達的政治觀點,重新界定為刑事罪行。判詞的語言與其說是法律推理,不如說是一套敘事策略:先把被告的動機歸結為「仇恨」,再把他的行為界定為「勾結」,然後把他所訴求的言論自由與選舉民主悄然轉譯為「外國勢力干預」。整個過程乾淨俐落,沒有血跡。...
(筆者按:我在2023年初在綠豆《鏡遊集》刊出第一封給年老明慧的信,差不多要三年才完成二十封信,最後結集成書,今年二月台北國際書展面世。這篇短文是我一些反省,也在此感謝綠豆給我空間發表我的文章。) 一九七七年我和周兆祥合寫《將上下而求索》,那時我二十八歲,剛從中大哲學系畢業不久,正準備赴德國攻讀博士。我們虛構了一個叫明慧的年輕人,把自己對人生的困惑與思索寫成二十封信。那本書後來成為香港高中的參考讀物,陪伴了幾代年輕人走過迷惘的歲月。 近半世紀過去,我在英國聖奧本斯的書房裡再次提筆。窗外是異鄉的樹林,不是馬料水的山色。我已過七十,父母早逝,師長凋零,連我深愛的城市也面目全非。這一次,我要寫給年老的明慧——也就是寫給同樣走到人生晚年的讀者,寫給我自己。 書名從屈原換成了晏殊。「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是少年的壯志,前路無盡,時間充裕,什麼都可以慢慢來。「夕陽西下幾時回」卻是暮年的喟嘆,日頭已斜,問的不是路有多遠,而是天黑之後還有沒有明天。 兩本書的距離不只是五十年 當年寫《將上下而求索》,我談人生處境、痛苦幸福、生命意義、愛情本質、自由超越,題目很大,口氣也大。那時候我相信人可以選擇面對命運的態度,可以在荒謬的宇宙中自我賦義。存在主義的教科書都是這樣說的,我也這樣轉述給明慧聽。 但那些話說得輕巧,因為我還年輕。死亡對二十多歲的人而言是抽象的概念,是哲學課堂上的議題,不是每天早上照鏡子時逼視你的現實。我父親五十四歲死於車禍,我當年以為那是意外,是命運的捉弄。現在我比他活得更長,才明白死亡從來不是意外,而是必然。差別只在於你什麼時候真正意識到它。...
《重讀經典:與人文和自然對話》 狄俄提瑪的教導:愛欲的哲學本質 狄俄提瑪(Diotima)的教導構成了《會飲篇》的哲學核心。她系統地回答了關於愛欲的三個根本問題:愛欲是什麼?愛欲的目的是什麼?如何正確地愛?這些教導展現了柏拉圖(Plato)成熟期的哲學思想,特別是他的形式理論的萌芽。 愛的精靈本質 當蘇格拉底(Socrates)承認愛既不美也不善時,他像阿伽通(Agathon)一樣立即推論說愛欲必定是醜陋和邪惡的。狄俄提瑪糾正了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她指出,在美與醜、善與惡之間存在著中間狀態。愛正是這樣一種中介性的存在。 狄俄提瑪講述了愛神厄洛斯(Eros)誕生的神話。在阿芙洛狄忒(Aphrodite)誕生的慶典上,機巧之神波洛斯(Poros,即「富足」)和貧困女神佩尼亞(Penia)躺在一起,生下了厄洛斯。因此,愛繼承了雙親的特性:他始終貧困、粗糙、赤腳,居無定所;但同時他又勇敢、機智,不斷追求智慧和美好事物。 這個神話揭示了愛的辯證本質。愛永遠處於擁有與匱乏之間。他不是神(因為神是完滿的),也不是凡人(因為他永恆存在),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精靈(daimon)。同樣,他處於智慧與無知之間:這正是哲學家的處境。...
《重讀經典:與人文和自然對話》經典02 文本自 Symposium / Plato《與人文對話 - 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讀本》第一版,2011,頁105-158導論:柏拉圖其人其學柏拉圖的生平與時代柏拉圖...
《重讀經典:與人文和自然對話》 佩涅洛佩的堅守——智慧與忠誠的化身 困境中的抵抗 在《奧德賽》(Odyssey)的敘事中,佩涅洛佩(Penelope)大部分時間沒有出現在冒險的場景中,但她是整個故事的精神核心。她的處境極其艱難:作為奧德修斯(Odysseus)的妻子,她必須保持對丈夫的忠誠;作為伊薩卡(Ithaca)的王后,她需要維持某種政治平衡;作為母親,她要保護兒子不受傷害。這三重身份使她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 一百零八位求婚者的壓力日益增大。他們霸佔王宮、揮霍財產、威脅兒子特勒馬科斯(Telemachus)的生命。佩涅洛佩沒有軍隊、沒有武力,在古希臘社會中作為女性也缺乏公共權力。然而她用自己的方式進行了長達二十年的抵抗,展現出不亞於丈夫的智慧和堅韌。 最著名的是織布的詭計。她告訴求婚者,必須等她為奧德修斯的父親拉厄爾特斯 (Laertes)織完壽衣,才會選擇新的丈夫。然而她白天織布,夜晚又偷偷拆掉,如此持續了三年,直到被侍女出賣。這個情節充滿深刻的象徵意義。編織在古希臘文化中是典型的女性活動,象徵著女性的智慧和美德。但佩涅洛佩的編織卻具有顛覆性——她不是在創造,而是在拖延;不是在完成,而是在拆解。她的織布機成為了抵抗的工具,她用女性的傳統技藝來對抗男性的求婚壓力。這種巧妙的抵抗方式展現了她與丈夫奧德修斯相似的智慧——不是正面對抗無法戰勝的力量,而是使用計謀來爭取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