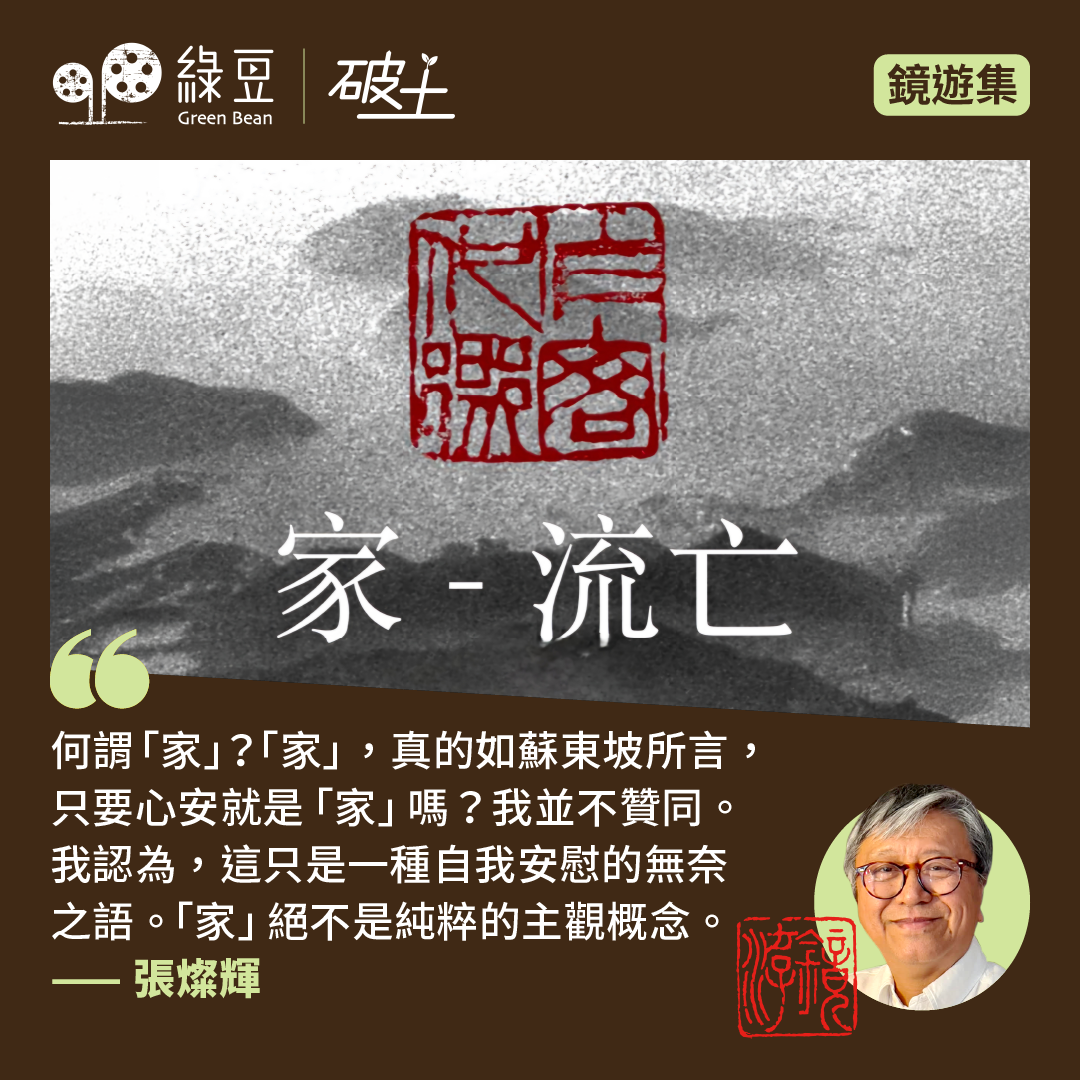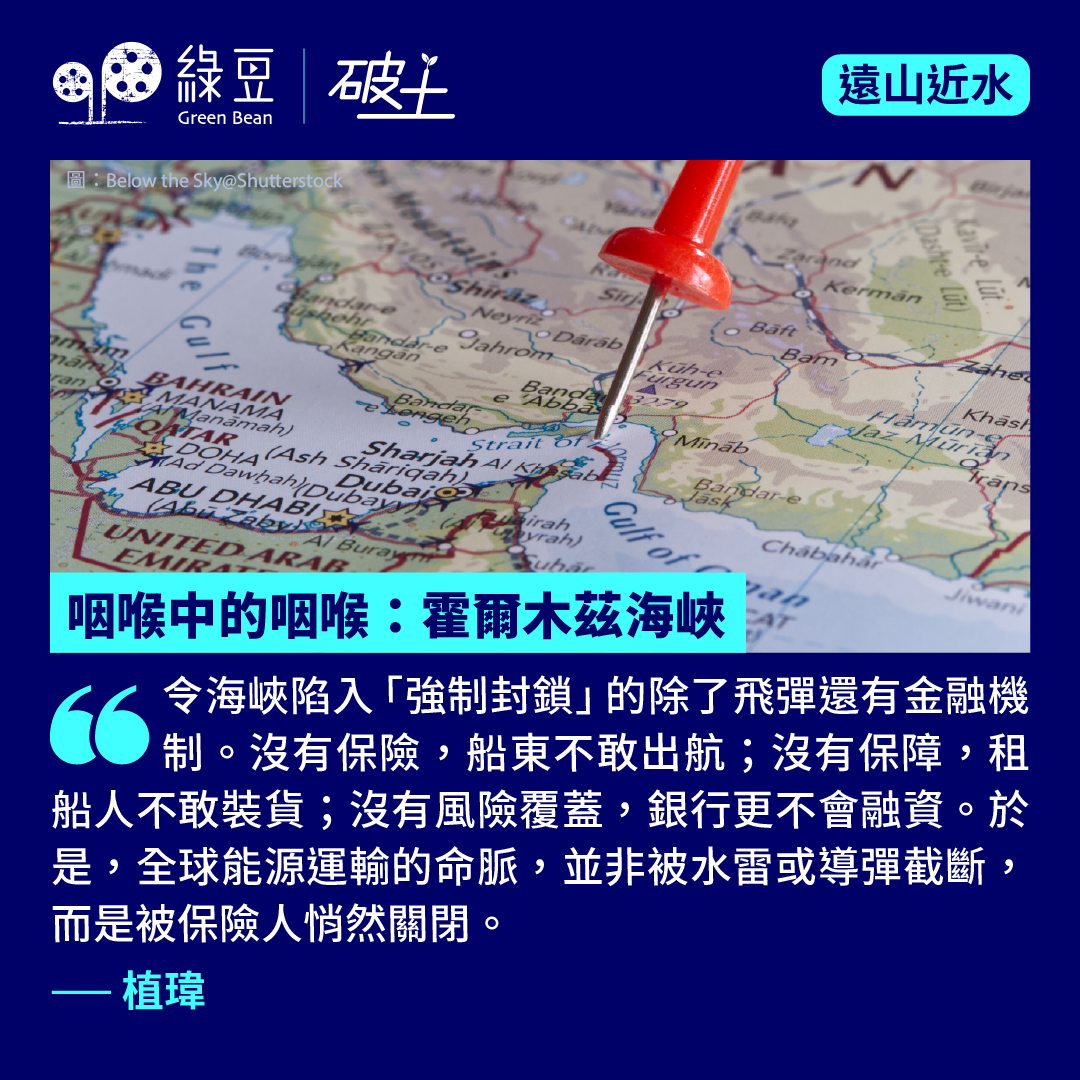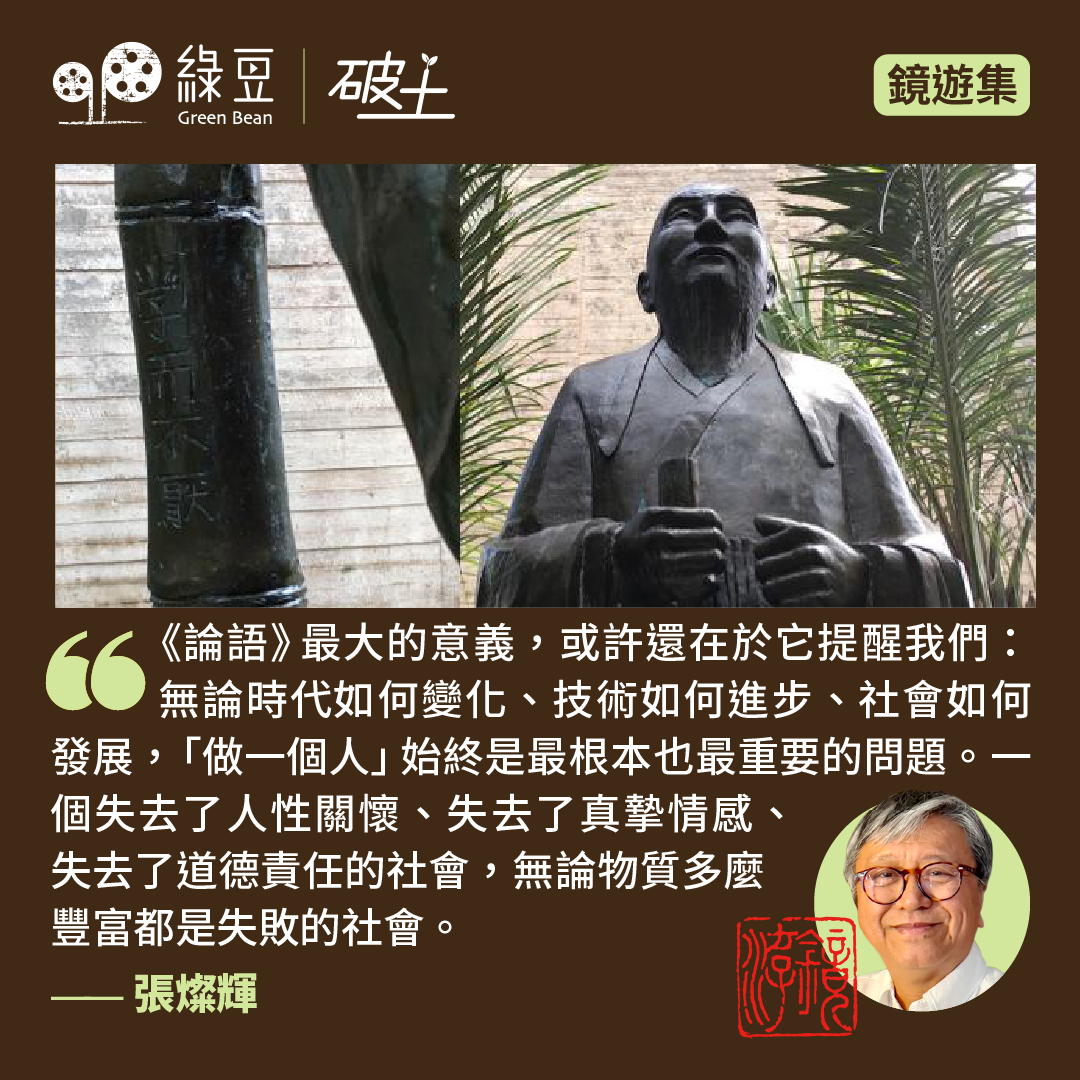「家」的概念也涉及空間的問題,這一觀點無疑受到海德格的影響,特別是在理解「居所」(Dwelling)方面。除了感受,「家」還與環境息息相關,這並非僅限於物理層面,而是透過存在於世(Being-in-the-world)以及世界作為意義網絡(world as a web of meaning)來理解。 海德格認為,人類之所以不同於其他生物,正是因為我們關心自身存在的問題,意識到存在是一個問題,並且這與世界息息相關。他因此創造了「此在」(Dasein)這一術語,「此在」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人類」(man),因為這個詞涉及對「人」的根本理解。「此在」屬於非反思(non-reflective)的狀態,世界也並非「存在集合」(collection...
(作者按 : 此文發表於2024年6月22日在台灣國立清華大學舉辦的「家。流亡 —— 哲學對談」研討會。由鄭栢芳同學筆錄編寫,經我修訂而成這文稿。現分兩星期刊出。) 流亡是上世紀相當重要的社會與文化現象。美國紐約有一所私立大學,名為新學院(The New...
業師勞思光有異於唐先生,他1955年來港,至1989年受邀於李亦園教授而返台,執教於清華大學;之後往返香港和台灣之間,直到2012年於台北逝世。他在香港生活長達57年。勞先生家庭背景相當顯赫,他祖上勞崇光,歷仕道光、咸豐、同治三朝,先後出任雲貴及兩廣總督,1860年,代表清廷與英國簽訂《九龍條約》。勞先生父親勞競九,為革命黨人,與蔣介石似乎關係匪淺。因此,勞先生可謂貴族出身,屬於上流社會人士。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勞先生亦跟隨其父赴台。勞先生自始至終,都對於共產黨的專制相當警惕,並不斷反省,故此其時他離開中國,前往台灣,多少亦有不願生活於專制政府治下的因素在內。順理成章,他亦不可能願意在蔣介石政府威權統治下生活。當時台灣仍處於大殺異己,鎮壓民眾之白色恐怖年代,故勞先生於1955年,離開台灣前往香港。 殖民地究竟是殖民地離開時,他寫下《六年心倦島雲低》一文。六年,就是1949到1955年,在此六年間,他生活於台北與台南,而無論在南還是在北,他只覺得這地方政治壓力太大,所以他必須離開。對於香港,他又作何感想?他認為自己「不是長住香港的人」,而且與唐先生一樣,「殖民地究竟是殖民地」,殖民地先天就有問題,是個原罪。似乎當時在避秦南來的知識份子眼中,沒有誰會覺得殖民地是好地方。殖民地就是殖民主義(Colonialism),就是邪惡(evil),這是他們的見解。香港雖然市里井然,街道漂亮,但勞先生不為所動,這個地方對他影響不大。不過,亦與唐先生相同,因為此地允許他自由生活,故其餘一切原罪、邪惡、問題,就瑕不掩瑜了。此外,從另一角度觀察,香港自1842年變成英國殖民地後,影響中國發展極大,康有為與孫中山都是住在香港。孫中山就讀於香港大學醫科,他之所以萌生革命念頭,正因為他身歷目見英國政府治理香港之良。可見香港對現代中國發展,影響何等巨大。正如上文所引述余英時之言,香港不止有自由,還有法治(rule of law),這是最重要。儘管香港沒有民主,但其整套制度,基本上屬於保護群眾,而非保護政府。不過,勞先生當初畢竟認為,香港「雖信美」,「卻非吾土」,故「何足以少留」。當然,勞先生1955年寫此書信時,絕不可能知道,往後57年,他都會留在香港。這基本上與唐先生相同。《六年心倦島雲低》一文情理皆備,是理解勞先生當時的心境最好的文章。 「家」的看法勞先生出生於西安,在北平長大,後來輾轉去過成都與台北,再來香港。談到成都,則不得不談其《憶巴州》一篇短文。勞先生曾在四川巴州住過一年,他認為此地是他生平居住過最寧靜、寫意、舒適的地方,其餘任何地方都不能比擬。在此文章中,勞先生雖未提及,但已隱然透露出他對於流亡與「家」的看法與情懷。在巴州,雖然如是其寧靜、寫意、舒適,但這種寧靜、寫意、舒適,決非現代化大都市那種。他在文中提到,巴州沒有汽車,出入都用滑竿,而在城內都是騎馬,不過通常以步行為主;巴州亦沒有供電,只有由燈草點燃的桐油燈;房屋沒有地板,全部是濕土地。身為世家子弟,又常年居住在西安與北平等名都大都,養尊處優,按道理,勞先生應甚不習慣巴州生活。然而,從其文章可見,並非如此。他在這些不便中,尋找出種種樂趣。例如,沒有汽車,馬匹亦不多,只能以步行為主,他就養成與二三鄰里踏青郊遊的新生活方式。由此可見,勞先生雖處於流亡中,似乎無一處是家,然其隨遇而安的性格,卻使他所在皆是「家」。這與唐先生不同。唐先生流亡到香港,從不以 為家,他一直認為,其家在中國,祖籍四川宜賓,他希望回去,儘管一生都再沒回去。勞先生一生去過不少地方,最後定居於台北市,長眠於宜蘭櫻花陵園。我必須再次強調,勞先生並不覺得任何一處是其家,因而處處可以為暫時的「家」。 痛批香港青年正因為處處是其家,所以對香港問題,勞先生比唐先生有更多關懷。他曾著有《歷史的懲罰》一書,我認為這本書實是勞先生最上乘作品。他對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青人,曾作出最痛切評論:「今日海外最與中國接近,同時知識青年較多的地方,應是香港。我們就香港來看,香港青年很少有願意獻身於政治運動。這自然有思想、環境、生活種種原因。香港是殖民地,一切社會標準都十分不正常。已成熟的人在香港生活,尚不免有迷眩之感;眾青年無論是外來或本地,在這個環境中度過童年,他們的人生觀已受了這個環境雕塑,而成為一種香港型青年。香港型青年最顯著特徵,就是缺乏理想性,缺乏犧牲精神,沒有遠大抱負。就研究學問說,他們不願面對有關文化價值的大問題,而只要學謀生技術;就實際工作來說,他們只要求有較好待遇,以便有較好生活享受。他們不切實感到國家危難,也不明白今日人類無法苟安。他們一味只構造個人小世界。談到政治運動,他們只在職業性或甚商業性考慮下,方有興趣。說到奮鬥犧牲,則他們會笑你是傻瓜。」基於這種看法,則勞先生絕難以置信,何以2014年會有雨傘革命,自然更不可能想像到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 「香港前景研究社」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香港九七回歸問題出現,勞先生思考如何面對香港從自由開放的國際城市回歸大陸的極權統治。正因如此,所以他在1982年時,創辦「香港前景研究社」。他知道當年英國透過《北京條約》,向清廷租借香港九十九年的大限已到,故想方設法保存香港。勞先生指出,考慮香港問題,必須從實際角度出發,而香港之於中共國,其最大用處,就在於經濟以及現代化,我們應從這裡切入,思考如何保存香港在中共國的位置。不過,他亦深明,在中共國與英國之間,香港人從無置喙餘地,甚至連立足處也沒有。故此,他自始就斷定,一國兩制是騙局,至今其言可謂大驗。所謂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其實是經濟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它是藉控制香港的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以成就中共國經濟發展;而讓香港人保持其原有生活方式,只是達成這個目的下,不得已接受之副作用。可是政治控制,卻一步步加強,因而說到底,香港絕不會有真正民主,勞先生早於一九九七年前已明言。他一語道破一國兩制的騙局:「由這兩面看 ,我們已經可以知道九七後的香港,除了在經濟方面可能有表面的『繁榮安定『,其他優點皆難保持。尤其在以後,中共當權人士很明確地將香港看成一個『顛覆基地』,又將一切抗拒專政統治的觀念與行動,與所謂外國的『陰謀』混在一起,結果必使香港民意及輿論受到強力壓制。總之,香港九七後只能在中共壓力下勉強苟全,再不能發揮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作用了。」在前景研究社時期,勞先生再三強調香港九七問題必須有香港人參與:「最後,我想總結上面所談各點,說說我認為香港居民對於香港前途問題應該作甚麼努力。第一:決定香港前途的權力在中國,但香港居民自有根據事理,表達意見的權利;所以,我認為在香港經濟未嚴重惡化以前,香港居民應當面對問題,形成一種代表香港人意願的共同主張。第二:香港現在對中國大陸的正面功能,本來是中國當局所了解的;但是他們對於『一九九七問題』,以及更長遠的香港地位問題等等,了解上仍然有許多隔膜;為了使香港問題獲得一個有益於中港兩方的解決,香港居民應該盡量運用言論,使中國當局對這些問題充分了解。第三:關於最後形成甚麼可行的方案,雖然不是可以由香港人單獨決定的;但香港居民仍然應該主動研討,形成一些草案,並作出實際的推動工作。總之,香港的前途要由香港人主動爭取;香港問題的解決要符合中國與香港雙方的利益。這就是我看香港問題時的主要意見。」很可惜,英國和中國共產黨當然對勞先生在前景社的一切努力,視如敝屣,毫不在意,香港人始終沒有參加處理自己命運的權利。是以當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刊出後,勞先生已經知道維持香港前途的努力已成泡影,前景研究社即時解散。所以中國共產黨答應台灣的一國兩制(而近來馬英九大力附和),若大家相信,若你果真相信,就正如勞先生所說,完全天真與無知。他深知共產黨絕不會放棄任何權力。故此,何以中共如此害怕香港,因為它害怕為香港所顛覆,它永遠視香港為顛覆基地。結果到2019年,就知道中共所害怕者,並非全無道理。最終勞先生離開香港,因為他絕不能生活於專制統治下。 一生都在流亡至於他到台灣教書,正如他自己所說,也只是隨緣,他再次流亡。他一生人都在流亡。勞先生雖然「所在即其家」,然而到頭來,實在沒有家。儘管他在香港五十餘年,亦有結婚生子,但這絕非其理想。1980年代,老師已然諄諄教誨我們,「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是無可奈何的事,但至少不做幫兇、不助紂為虐、不阿諛奉承、不搖旗吶喊。」而最重要的一句話是,「共產黨絕不可信。」對於這番話,當時我們好像聽不懂。香港對勞先生很重要,作為大學教授和公共知識人,也盡了責任;在重要時刻敢言批判時事,為香港人在97問題上發問。不過我覺得他最關心的是香港這個城市淪陷後,他失去自由開放的空間思考和寫作。但他並不關心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的努力,對香港人自己命運問題也沒有任何建議。他自始至終知道香港人一切努力都是白費的。是以他九七後已離開香港,大部時間獨自在台灣教學生活,回香港只是探望親人和見學生而已。香港不是他真正的家,勞先生一生都在流亡。2012年在台灣祝賀勞先生85壽慶時,也是他辭世的一年。有朋友聽到他一句感慨説話:「一生是苦多於樂。」果真如此,先生漂泊一生,四處可暫時寄居,但無一處真的為家,安身立命之所。(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