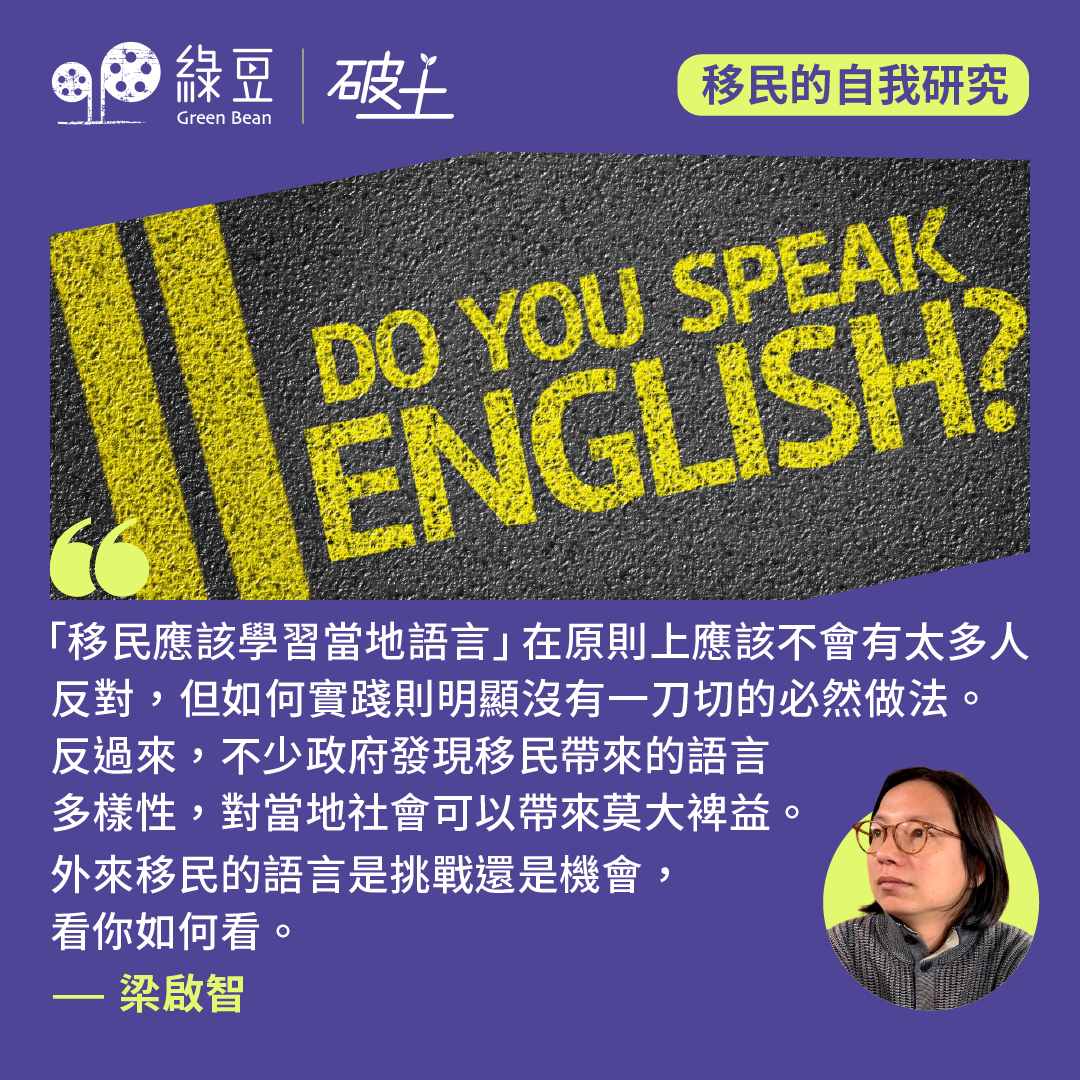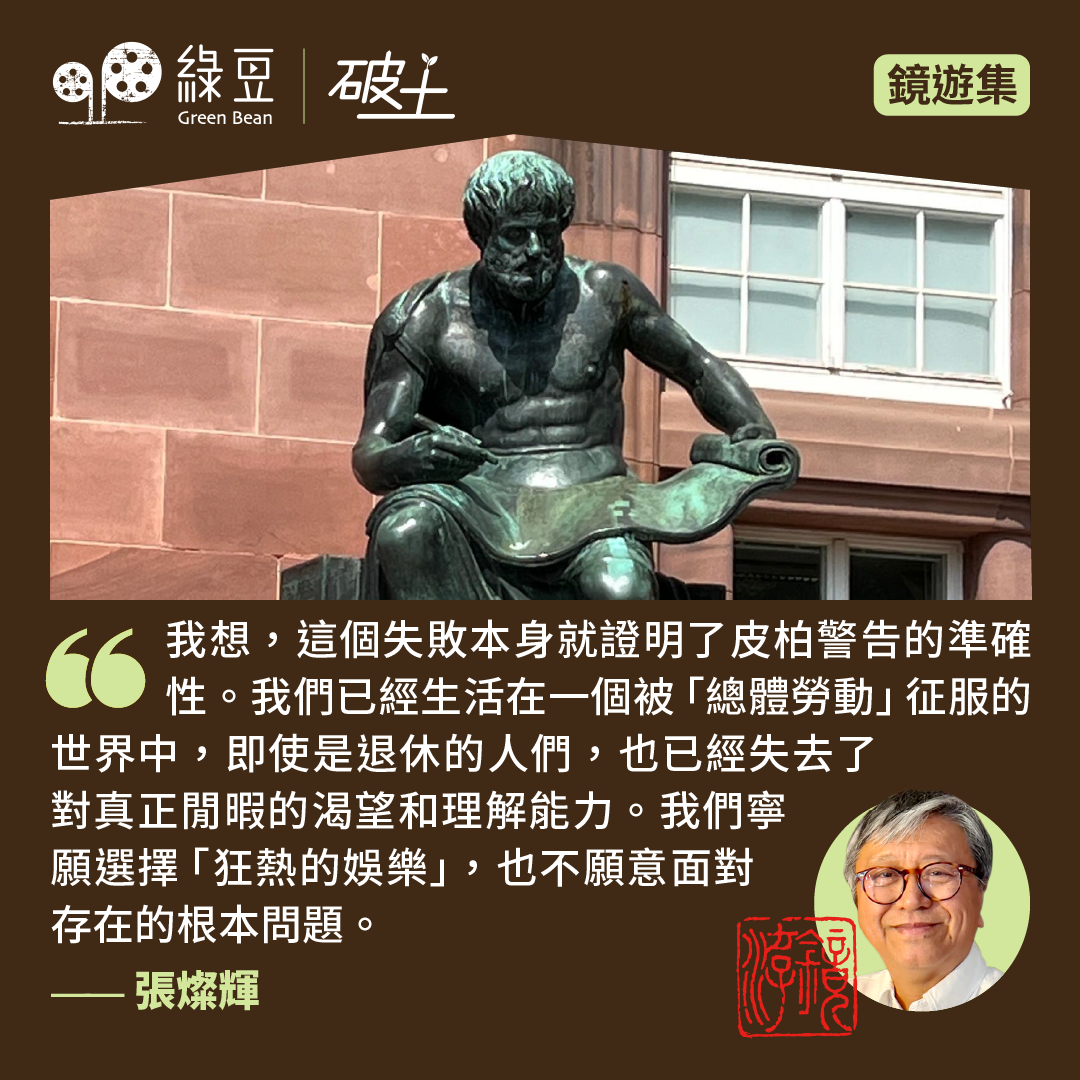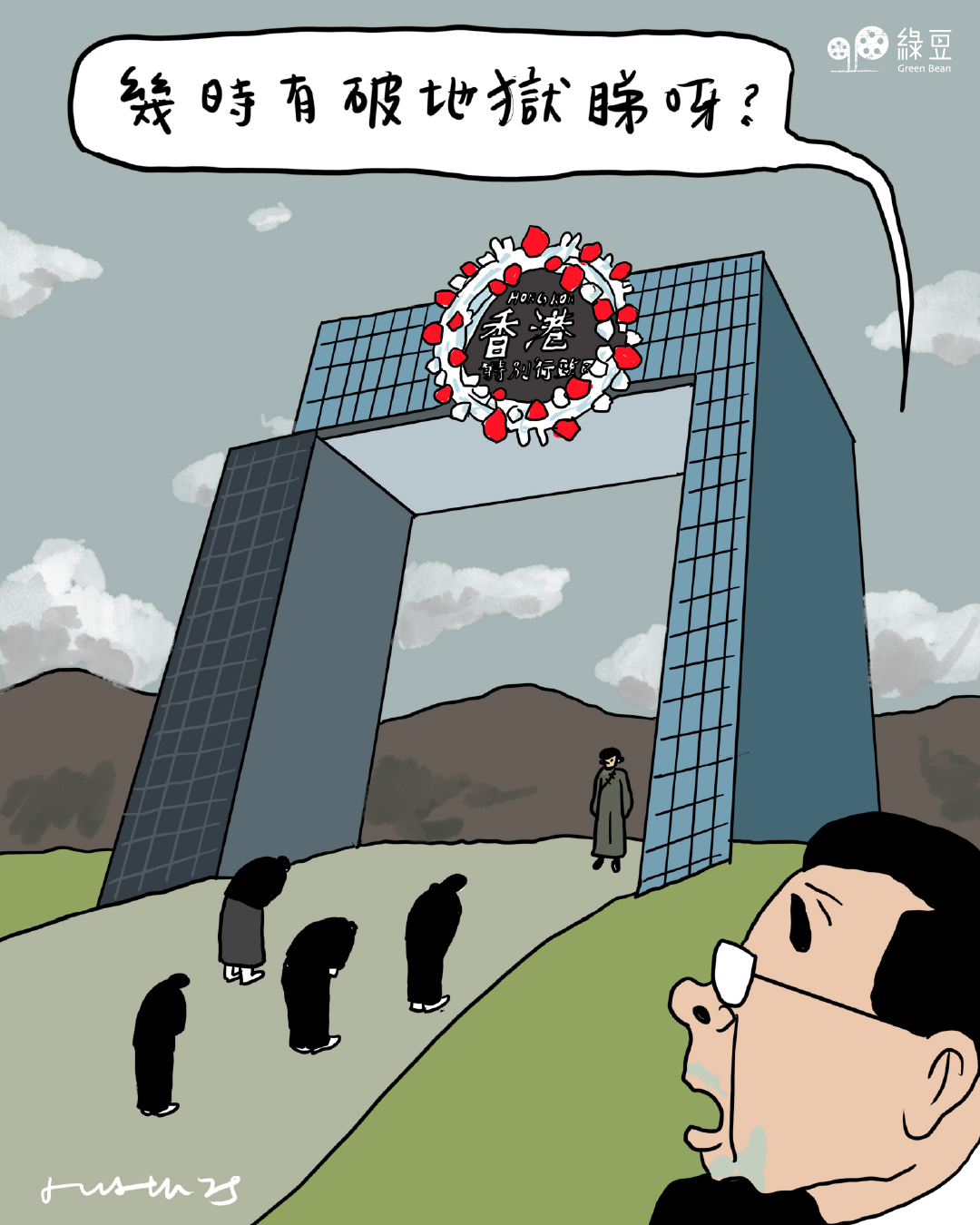原自香港的美國諧星 Jimmy O Yang 日前回港並在紅磡體育館表演多場棟篤笑,風頭一時無兩,有評論稱之為移民美國後的「衣錦還鄉」。與此同時,其移民和港人身份也引發了不少議論:他說的段子和香港本土文化有多大的距離?他還算不算是香港人?這些問題並不獨特,每一位移民第二代都要面對。風潮面前,各地港人移民也不妨趁機提早思考:如果你的孩子要當Jimmy O Yang,你會怎麼想?...
美國洛杉磯爆發反對移民執法的示威,總統指派國民警衛隊和海軍陸戰隊入城,被指濫權及破壞聯邦與州政府之間的分權。這場爭端也蔓延到海外港人社群,支持反對雙方各執一詞。然而經歷了一個星期的觀察,我越來越懷疑爭執的重點並不是移民議題,甚至乎不是公共政策;而背後的走向,相對於移民議題本身的分歧,恐怕更需要警惕。 在談我的觀察之前,先說說公共政策的爭議本來應該是怎樣的。如果我們想解決問題,而不是純粹發洩情緒,那麼我們需要的應該是細緻思辨。甚麼是細緻思辨?就是不要非此即彼,不要一刀切。例如在台灣,我支持或反對賴清德政府,不等於我必須同時支持或反對他的能源政策;就算我支持核能發電,也不等於我必然支持某一所核電廠的存廢。有常理的人,應該能夠把各條問題切開,逐項討論。 回到當前的移民爭議,反對或支持特朗普政府,和反對或支持當前針對移民的執法行動,可以是兩回事。反對當前的執法行動,也不等於就支持永遠不對移民執法,或者大開邊境以後不管合法非法,世事不用這樣滑斜坡。簡單把討論分為「撐移民」和「反移民」,然後對當前的執法行動提出質疑的一律扣為「撐移民」,那是思辨的懶惰。套用某著名港人時事評網紅的慣用說法,未免有點「小農DNA」,非現代人所為。 爭論的實證 那我們可以如何細緻一點?有些時候,公共政策的爭議會涉及原則問題,後面是價值觀的辯論;也有些時候,爭論的焦點是實證命題,可以通過現實社會中的經驗去回答。我們可從這分野開始。 舉個例,台灣的一大公共政策的爭議是死刑存廢。有些人認為「一命償一命」,是原則問題,那要爭論的就是這句話的含義,為什麼「一命」可以「償」另外「一命」;也有些人的觀點認為保留死刑可以阻嚇犯罪,那就是要實證的命題。例如香港和新加坡的社會文化經濟背景水平相近,都承傳了英國的司法制度,但是香港廢除了死刑,新加坡卻沒有;那麼香港在廢死後有沒有如某些反廢死論者所言,觸發出狂兇極惡的連環殺人事件?也沒有。 美國移民政策的討論也可以這樣分。有些爭論可以實證:例如說「非法移民沒有交稅」,實情是美國政府有向所謂的「非法移民」徵稅,紀錄十分齊全;又例如說「非法移民帶來犯罪」,實情是所有的移民(無論「非法」與否),在全國、州、縣、鄰里層面的暴力或非暴力犯罪率,都要比美國出生的低。這類問題很簡單,肯去找數據就會有答案。...
早前獲邀到國立政治大學演講,題為《臺港互視中的認同、歷史與未來》。接到這題目的時候心中有點忐忑,因為近來在社交媒體看到太多台灣和香港網友之間的對罵,看起來好像是兩地關係已變得很糟糕。身為一位兩年前才拿到台灣護照的香港人,夾在兩個地方之間,見到這些爭吵難免會感到有點氣餒。 先說明一點,我相信那些網上對罵並不代表台港關係的主流,我仍然相信兩地的民間關係相當友好。在台灣,許多人都是看周星馳的電影長大,電影中的對白你只要說一句大家都懂得接下一句。在香港,一般人對台灣人也十分友好,網上流行說台灣人到香港旅行有「通關密語」,只要說出「我是台灣人」之後店員的服務態度就會180度變好。再看許許多多「香港人在台灣」或是「台灣人在香港」,專門介紹兩地生活文化異同的網上專頁,留言區絕大多數都是鼓勵的說話,感受不到半點敵意。 話雖如此,儘管香港和台灣的距離十分之近,兩地交往頻繁(桃園來往赤鱲角是全球最繁忙的國際航線),但我總懷疑我們有點過於高估台港之間互相認識的程度。台灣的大學鮮有關於香港的課程,今天在香港要開關於台灣的課恐怕也是難上加難。兩地生活習慣不盡相同,當以為雙方很了解,突然發現原來其實並不了解的時候,落差就特別大。 「支語」之爭 近期見到的爭執,不少是出於言詞上的誤會。例如有台灣人問香港人會不會說中文,香港人聽到這句說話往往不明所以。在香港的語境,中文是書寫系統,常見相對應的口語有廣東話和普通話。在台灣的語境,中文則是國語的意思。這本來只不過是語言習慣之別,沒有什麼好爭吵的。如果說台灣人把國語等同中文是片面,那麼同樣邏輯下香港人把自己的慣用語言稱之為「廣東話」何嘗不也是片面?畢竟準確來說香港人使用的應該稱為香港粵語,而粵語還有其他分支,從四邑話到蜑家話不等,廣東不止一種「話」,人家也可以投訴我們的片面。 說來說去,這些爭執的內容是其次的,問題總是出於當誤解被上綱上線成為政治立場之爭,那麻煩就大了。近年來不少台灣人認為台灣正面對中國大陸的文化入侵,對日常生活中的台灣用語被中國用語取代特為警惕,對許多疑似中國用語標籤為所謂的「支語」。然而這過程往往有如獵巫,不少在香港已用了數十年的港式用語也被誤中副車,引發不少香港網民的不滿。這時候,又會有台灣網民宣稱反正香港已經被全面中國接管,不用分得那麼細,再進一步激發強調香港獨特身份認同的港人不滿。 不如多做有益身心的事情...
英國執政工黨提出移民定居年期要求從5年延長為10年,雖然未有說明BNO簽證持有人會否受影響,亦未知何時才會生效,但已引起移英港人廣泛關注。早前保守黨亦曾提出移民制度改革,雖然澄清建議不適用於於BNO簽證,本欄當時已指出不能對後續政治影響掉以輕心,結果僅僅三個月後便見到執政工黨跟進。 早點看破免站錯隊 回想當保守黨提出建議的時候,一些移英港人以「反正保守黨又不是執政黨」來自我安慰,但從宏觀來看已經敲響警號。英國社會整體向右轉,極右的改革黨在民調和地方選舉中節節勝利,保守黨要回應,工黨同樣也要回應。各黨的具體建議或有分別,但在社會大勢之下,朝向收緊恐怕是大勢所趨。 一些移英港人雖然自己也是移民,卻支持限制移民的政策,甚至是極右的改革黨,通常提出的理由都是認為自己是「模範移民」,改革黨反對的是破壞社會安寧的「非法移民」,並會拿出該黨的政綱佐證。每次看到這些討論我都感到十分奇怪,畢竟這些港人移英前在香港又不是未見過選舉,政客在選舉前後說一套做一套應該不會陌生,許多政黨總會在選舉前「溝淡」某些極端政見,當選後才故態復萌,這在香港也屢見不鮮,為何到了英國卻又能對這些選舉語言如此受落? 且看大西洋彼岸,特朗普當選前也得到某些少數族裔社群的支持,到要承受他當選後的鐵拳時已後悔不已。現在特朗普政府的排除移民政策已擴展到持有合法身份的移民,甚至是綠卡持有人。當然,他們每新增一批針對的對象,總會找到某些說詞來支持。只是當被針對的範圍越來越廣,拿着「模範移民」的幻想以為自己可以免疫,未免有點自欺欺人。如此類堆,千萬別以為英國工黨限制正規移民是搞錯對象。不,他們非常清楚他們在做些什麼,因為他們非常清楚選民底裡想要的其實是什麼。政治語言都分「前台」和「後台」,人前說一句,人後又說另一句,早點看破也就少一些機會站錯隊。 不安情緒的出口 移民政策評論有「薛定諤的移民」這比喻,諷刺反移民政客說詞表面上的前後矛盾。「薛定諤的移民」來自物理學思想實驗「薛定諤的貓」(Schrodinger's...
近來數個港人移民的熱點都有選舉,除了英國的地方選舉,澳洲和新加坡也舉行了國會選舉,而最受關注的則應該是加拿大的國會選舉。移加港人在這次加拿大選舉中的參與,特別是鄭敬基的國會議員競選,的確十分值得關注。 在網上看到不少移加港人因為這場選舉吵架,其中不少已經移居加拿大多年的港人移民,不滿新近赴加港人的政治立場,認為他們過於依賴個別港人網紅的政論解讀,輕視主流加拿大人的判斷,未能表現與加拿大社會的融合。 其實即使同一族群,選舉中有不同立場本來就正常不過。新舊移民的判斷不一樣,也是在所難免;老移民過去當過新移民,新移民有天也會變成老移民,不妨「放長雙眼」讓時間作證。唯一要介意的,是對民主制度的捍衛:難得千里迢迢來到一個民主社會,如果胡亂相信甚至散播一些破壞民主制度的言論,例如對選舉公正提出欠缺證據的指控,則這些人恐怕真的不值得留下來。 移民參政的難度 說回鄭敬基的國會議員競選,這次他代表保守黨參選,不過沒有被派到他一直經營的社區,而要他到一個保守黨本來支持度較低的選區出選,引起一些移加港人朋友的議論,被認為是當了「砲灰」。政黨出選機制從來都是選舉中的難題,由黨中央主導往往帶來黑箱作業的批評,但如美國一樣採取黨員民間初選則容易走向極端,讓奇形怪狀的候選人出線。移民要走上參選之路,不單止得花心思時間摸清當地選舉模式的實際操作,最後往往依靠天時地利人和加持才能順利出選。相對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來說,移民要參政,難度可不少。 第一個門檻是能不能夠參與。不少選舉制度事先排除了移民的參選權,例如美國《憲法》規定總統必須要是「天生美國人」才能出任,後來入籍的都不可以;所以除非修改相關條文,否則移民成為美國總統的機會是零。美國的開國先賢要這樣設限,背後固然有其時代背景的考慮。 今天的台灣亦有類似的情況:本來按《港澳條例》規定港人在台設有戶籍滿十年便可以參選公職,不過近期台灣政府解讀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也算「外國國籍」,而港人大多因為《基本法》而自動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加上中國政府不接受取得中華民國身份為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原因,如是者大批移台港人也就因「雙重國籍」而自動失去了參選權。...
曾經和一些早已在外國落地生根的港人移民組織者討論新一代港人移民的情況,常常會聽到一種說法:這一波的港人移民還是太過「新」,對當地的理解往往仍存有各種幻想,又或仍未能處理理想和現實的落差。但他們往往還會補充一句:雖然港人移民或者還未完全認識或適應身為移民的文化身份,但他們的下一代將會不一樣;亦因如此,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之間,長遠必有隔閡。 舉個例,不少港人移民會自以為「榮譽白人」,假設自己理所當然會被當地社會接納,各種針對移民和少數族裔的排外情緒與他們無關;最新就聽說還有移英港人推動「反移民聯署」,好像忘記了自己也還未入籍似的。這些港人移民之所以會擔起各種在「舊移民」眼中甚為奇怪的價值觀,原因倒也不難理解:他們當中不少人都未有甚至不需要和當地社會有深入交往,只體會到移民後的好處,當地社會對移民的不滿或歧視卻未感受得到。如果他們資本足夠豐厚,甚至可以一直活在自己的「幸福泡泡」當中。 對家長的提醒 但他們的下一代就不一樣了。尚未成年便隨父母離港的移民,以至在當地出生的港人移民後代,面對的社會環境和他們的父母有巨大差別。他們的成長過程和當地社會的融合遠遠來得徹底和直接,無論是學校或朋輩交往,他們身為少數的身份會無時無刻被提醒。而相對於他們的父母,原來自香港的生活記憶又遠遠不如。他們最重要的身份不再是港人或港人移民,而是在當地社會的少數族裔;這差別看似微少,卻十分重要。 舉個例,Crazy Rich Asians(港譯《我的超豪男友》)在香港和在美國的上映,雖然是同一齣的電影,但對兩邊的觀眾來說就是活脫脫的兩回事。考慮到早年荷里活電影的各種種族歧視,包括由白人飾演亞裔角色或只安排亞裔演員擔當配角,完全由亞裔演員領銜主演的...
早前邀請李立峯教授來台演講,提問環節有一條問題讓我久久不能釋懷:在移民世代,離港和留港者之間的裂痕該如何修補? 李立峯以研究社會運動和傳播理論聞名,他提到很多研究關心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中間那五年發生的事受到的關注則較少。他研究2014年和2019年之間的轉變,特別是香港人如何從雨傘後的大分裂走到反修例運動的「和勇不分」,認為這過程值得仔細說明。讓我千頭萬緒的觀眾提問,是:「來到今天的香港,已不用再談和勇之分,那麼新的裂痕是什麼?該如何修補?」李立峯認為離港和留港者之間的分歧是新的裂痕,而要修補恐怕並不容易。 從拆大台到和勇不分 回到十年前,雨傘運動在許多人眼中被視為「失敗」告終,而其中一個重點爭議是暴力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激進派認為傳統溫和派拖了後腿,各種「拆大台」的呼籲無日無之,引發反對陣營的嚴重內訌。激進與溫和之間的矛盾,在2016年農曆新年的旺角衝突推到高峰,如何理解示威者襲擊前線警員成為新一輪的爭執焦點。 那麼香港的反對力量是如何從撕裂走到「和勇不分」的呢?中間發生了三件事。第一,激進派有調整他們的語言。激進本土派參與2016年初的新界東補選和九月的換屆選舉,在選民面前無可避免地需要尋找公眾可接受的政治論述,作一定程度的自我重新發明;與此同時,香港眾志的成立亦為激進本土和主流民主派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中介。第二,香港政府對激進和溫和反對派作出無差別的打擊,例如在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事件當中,不止激進派的議員被取消資格,溫和派的也一樣,無異促使兩派敵愾同仇。最後,來到2019年,警察暴力的大規模升級,以及前線示威者面對警察和「白衣人」暴力時的巨大犧牲,為團結帶來了巨大的道德力量。 新的裂痕 來到今天,「港區國安法」訂立已差不多五年了,無論「和」或「勇」的抗爭也難成氣候,亦談不上成為內部矛盾的來源。相對來說,離港和留港,恐怕才是這世代的矛盾主軸。過去數年,見過太多這樣的爭拗:某些離港者批評留港者「沒有看清現實」,拒絕離開;當香港政府政策失誤時,則嘲諷「留港值得擁有」。當然,不是每一位留港的都是自願,也不一定認同離港者的批評,亦有些會對離港者作出(不一定有道理的)反擊。當兩者的日常生活經驗越來越遠,難免夾縫也越來越大。...
近日台灣移民署因應有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鼓吹武力統一,取消其居留許可並限令離境。這宗新聞對許多港人移民來說大概會覺得是事不關己,如果不是幸災樂禍的話。然而細想之下,港人移民其實也是時候想想如何應對針對移民社群的疑慮;在台港人固然要想,到其他地方的亦不見得可以免疫。 言論自由從來不是沒有限制,危害社會的言論在各地都會被明文禁止。不過言論自由的界線,和許多社會規範一樣,都是各處鄉村各處例。移民在此的第一重困難,自然是對紅線的掌握。這點對港人移民同樣適用。有些港人在香港的時候自恃是多數,習慣各種帶有種族歧視的言論而不自知,移民到了因為經歷過種族撕裂而對相關言論特別敏感的社會,如果仍然保持自己的一套然後聲稱當地的要求是「玻璃心」,則未免沒有入鄉隨俗。見到一些港人移民在歐美社會因為歧視言論而遇到麻煩,還要反過來指責當地是「左膠國家」,只好慶幸不是人人會讀中文,否則惹當地人討厭的程度只怕和上述的台灣案例相距不遠。 政府執行政策的尺度 當然,台灣的案例還有其特殊性:移民的原居地政權或移民所代表的群體,和當地的主流社會衝突,以致移民本身被視為潛在的疑慮對象。在台港人恐怕在這件事情上感受至深。2019年的時候台灣政府有過許多「撐香港」的言論,然而隨著中國政府對香港政府運作的介入日深,台灣政府難以再把香港和中國大陸作差別對待,港人移台無論是政策或執行上亦出現不少波折。 成為被疑慮的對象,過程不一定很有道理,要作辯解往往亦不容易。早兩年有不少港人因為「國安疑慮」而定居台灣遭拒,其中不少個案的解說相當無厘頭,例如在公立大學短暫工作也成為拒簽原因;雖然這些案例後來被監察院查明,原來只是移民署「為爭訟便利」而沒有詳細說明所有原因,例如投資移民本身的個案問題,但在港人社群中帶來的誤解和傷害已難挽回。 面對衝突,移民本身固然應當尊重當地社會的紅線,凡事有所分寸。與此同時,政府若要把紅線變成政策,主管機關的解釋必須有理有節,不作過度干預。近日台灣的案例得到輿論普遍認同,皆因台灣政府這次劃出的紅線十分清晰:談統談獨都可以,但不能「鼓吹戰爭」,並援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相關條文為此原則背書。換句話說,政府表明不是要針對個別移民社群,也不是要針對思想,而是「鼓吹戰爭」此一特定行為,也就是說對事不對人。這樣的界線普遍輿論認為適度合理,相關案例在此也是證據確鑿,沒有冤枉好人。 反過來說,當政府執行政策的尺度不一,被針對者難免會感到不服氣。例如當移台港人發現自己被視為潛在風險,另一方面卻見到退休軍官將領能到中國大陸出席統戰活動,不免懷疑所謂對國安疑慮的重視到底是真是假。相對來說,早前賴清德總統提出檢討港人移台政策,是放在十七條針對社會各階層的因應策略中提出,港人移民並非唯一針對的對象,就未有引起相關政策研究者的普遍反彈。...
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簽署行政指令,聲稱指定英語為美國的官方語言,背後相信針對美國社會對移民文化影響所謂美國主流文化的憂慮。語言從來都是移民研究的重要議題,本欄早前也討論過「發夢也是用當地語言」如何被視為徹底融入當地社會的界線,以及由此期望延伸出來的許多疑問。移民到達新的社會,學好當地語言固然對日常生活大有幫助;不過說到官方語言政策,問題又要複雜得多。 首先,特朗普的官方語言指令和他的很多政策一樣,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往往更像是做場戲出來給死忠粉絲歡呼喝采。就好像是他在競選首任時也有豎立墨美圍牆,還有「墨西哥付鈔」的豪言壯語;結果圍牆的新建部分只得數十英里(用的是美軍經費),拍張照片便自稱勝利。說到法定語言,美國《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當然也保護使用各種語言的權利;行政指令不是法律,只能影響聯邦行政機關,而特朗普指令其實只是推翻了克林頓年代加強政府協助非英語人士的要求,沒有禁止政府部門繼續提供現有各種語言的服務。所謂指定英語為美國的官方語言,很大程度只是又一次特朗普式的標題黨。 官方語言與本地文化 美國聯邦政府沒有法定語言,各州政府倒有不少對此作出要求。有超過30個州列明英文為該州的官方語言,但同時也有數個州把當地原住民語言定為官方語言:夏威夷州規定英語和夏威夷語同為官方語言,南達科他州則認可了拉科塔語、達科他語和拉科塔語,阿拉斯加州法例更在英語以外列出20種當地語言為官方語言。 原住文語言的案例說明了在美國談語言的尷尬:如果說外來人口應該尊重本地文化,那麼英語本來就不是美洲大陸的本土語言,其實也是外來文化。而在外來文化當中,英語也不應視為特例;新墨西哥和路易斯安那在成為美國領土前,分別當過西班牙和法國的領地,影響遺留至今,兩地政府的官方文件分別仍有使用西班牙語和法語。美國領土也不限於50個州,波多黎各也是美國領地,九成四的居民說西班牙語;當地人口超過三百萬,人口排名比18個州還要高。如若真的要求美國各地政府以後只用英語,恐怕是天方夜譚。 美國的情況也許比較極端,但同樣的歷史思考和由此而來對少數的尊重也可見於其他地方。台灣華語雖然現實上是台灣的通用語言,但台灣從歷史到現在尚有許多其他語言:原住民語、台灣台語、客語以至日語等,華語的通用地位是歷史和政治產物。今天的《國家語言發展法》僅說明「所稱國家語言,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嚴格來說台灣華語沒有更高一層的地位。《大眾運輸工具播音語言平等保障法》則要求「除國語外,另應以閩南語、客家語播音」;而在歸化國籍的基本語言能力標準當中,口試部分也有「華語、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語擇一應試」的選擇。 是挑戰還是機會...
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國總統,教育部限令學校停止DEI(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多元公平共融)相關的政策,否則將失去聯邦資助。港人移民在各地雖然應算是少數族裔,卻同時不乏反對DEI的聲音,認為違反唯才是用的原則。道理上,用人唯才當然是好事。不過怎樣才算是用人唯才,卻有不少值得仔細思考之處。 香港人認同唯才是用,本身十分合理,畢竟這期望符合大多數港人的成長經歷,甚至視為香港的成功基石。回想過去數十年香港經濟起飛時期,社會各行各業急需人才,而很多出身底層的年輕人都得益於社會流動改善生活。這一段經歷,在香港主流論述中被理解為港人只要有能力、敢冒險,自然就可以出人頭地。事實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往往以大學入學試作為社會流動門檻,相對於中國大陸講究階級成份或政治忠誠來分配資源,無疑相對來說要公平開放得多。 當然,如果我們深究下去,昔日香港那個「獅子山下」的故事其實有眾多盲點。例如少數族裔的語文政策問題,很大程度打擊了他們在公開試中公平競爭的機會。聲稱香港是個唯才是用的社會,往往忽視了「沒有相同起跑線」這個事實,純粹站在終點宣告比賽公平。只因受負面影響者屬社會少數,唯才是用的迷思才得以留存。 DEI破壞了公平? 道理上,當港人移民到外地,從社會中的大多數變成可見少數之後,應該更有可能理解少數的弱勢地位,對補償少數的社會政策更為支持。事實卻不一定如此。相反,港人移民後不一定會覺得自己是被邊緣化的少數,不少覺得自己是所謂的「模範移民」,認為那些補償少數的社會政策反而會對他們不利,甚至覺得反對這些政策才能更讓主流社會接納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