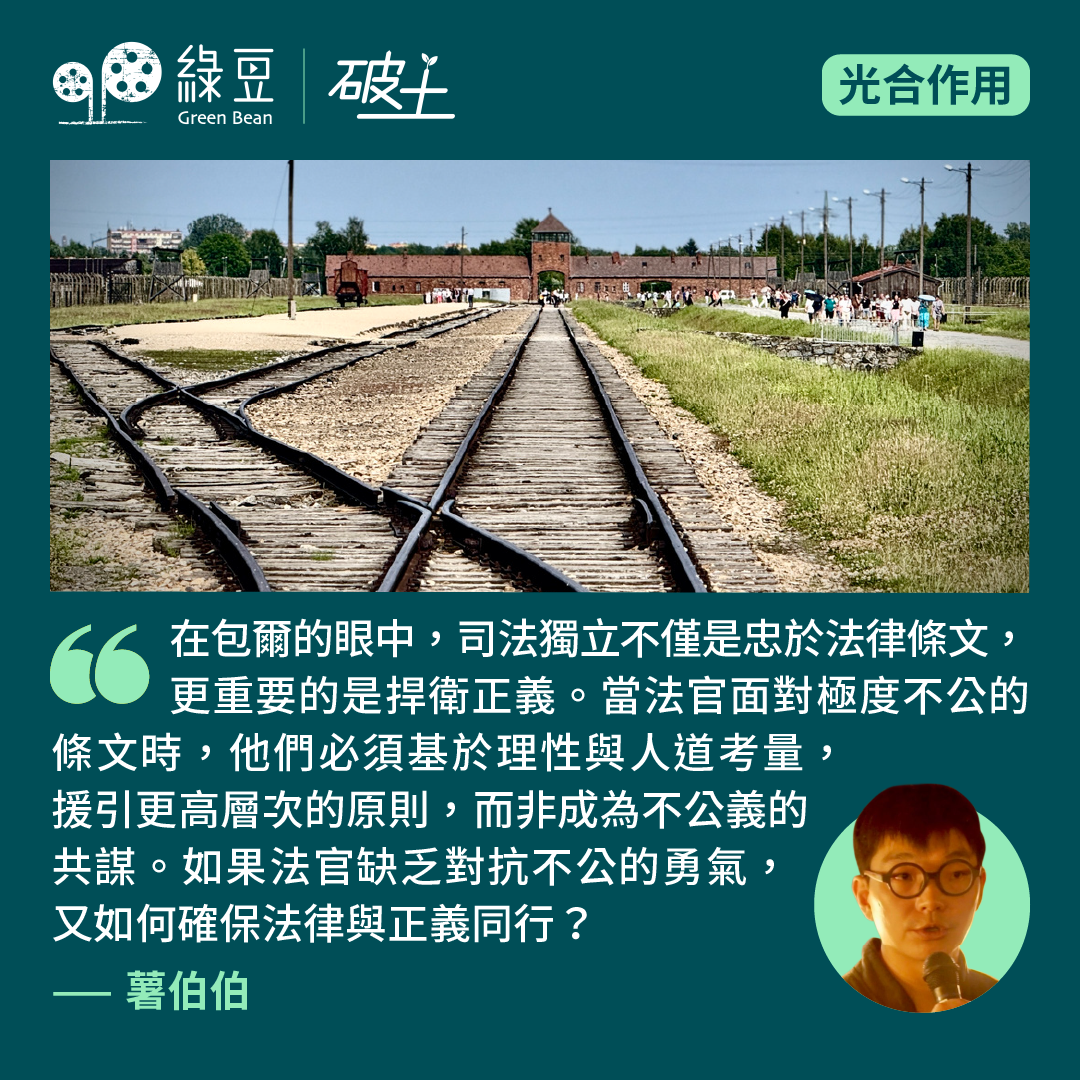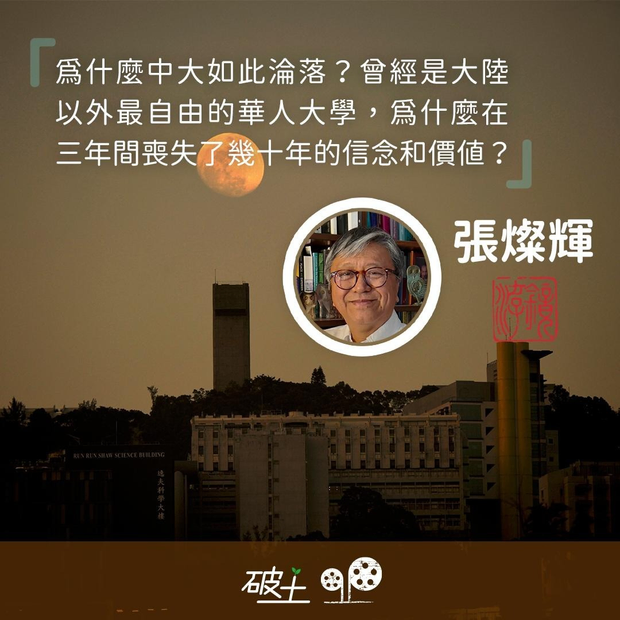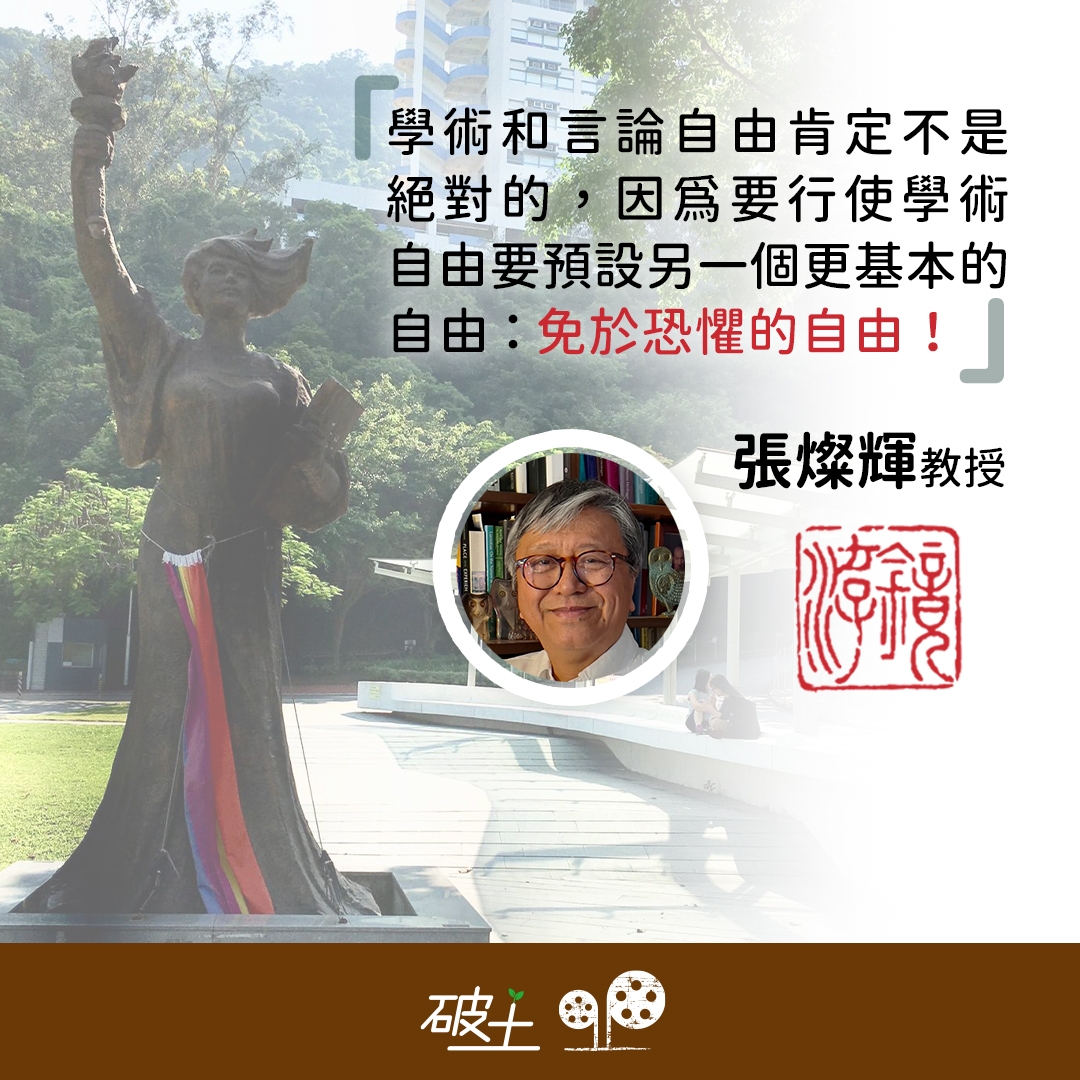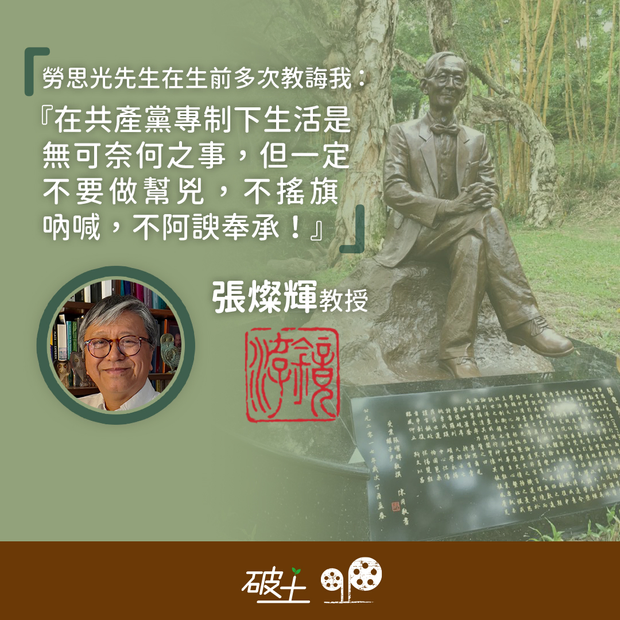我們還有家嗎?家與流亡之哲學反思 (下)

「家」的概念也涉及空間的問題,這一觀點無疑受到海德格的影響,特別是在理解「居所」(Dwelling)方面。除了感受,「家」還與環境息息相關,這並非僅限於物理層面,而是透過存在於世(Being-in-the-world)以及世界作為意義網絡(world as a web of meaning)來理解。
海德格認為,人類之所以不同於其他生物,正是因為我們關心自身存在的問題,意識到存在是一個問題,並且這與世界息息相關。他因此創造了「此在」(Dasein)這一術語,「此在」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人類」(man),因為這個詞涉及對「人」的根本理解。「此在」屬於非反思(non-reflective)的狀態,世界也並非「存在集合」(collection of things)或「一切存在的總和」(summation of all things),而是對「此在」開放的,因為世界是一個完整的意義網絡。因此,我們不需要為自身的存在、所居之所乃至於整個世界進行反思,而是透過日常性(everydayness)來呈現。
家:事事就手
由此可見,人類絕非僅僅存在於物理空間的物理存在,而「家」作為居所的需求,不僅涉及空間,還包括集體回憶、價值觀和人情等。人類從原始狀態中創造文化,我認為,這同時也是生活環境從最初的單純物理空間,通過建築轉變為「家」的過程。空間與「家」的區別在於,後者是具文化呈現的居所。文化造就居所,而居所又呈現文化,彼此互為因果。「家」使我們意識到,我們不僅是存在於世(being in the world),而且是生活在家中(being at home)。
我目前居住在清華大學的宿舍,每次外出後回來,與他人告別時,我都只說「返宿舍」(回宿舍),而不是「返屋企」(回家)。無論其設備如何不足,即使設備足夠,我也不認為純粹由房間、客廳、廚房和洗手間組成的空蕩蕩空間可以稱為「家」。更何況,我明白在這裡的時間有限,終將有離去之日,因此不願意多添置物品;這種情況和心態使我無法視其為家。如果我真打算長期居住在這裡,自然會設法讓這裡變得適合我居住,從而成為「家」。
何謂適合居住?至少,它應該令你在其中感到(Ready-to-hand),完全為你的習慣而設。與我較熟悉的朋友們應該知道,我在香港的家書房十分凌亂,妻子經常要整理,但我卻拒絕,因為即使凌亂,卻也亂中有序,我在其中掌握一切,事事就手。這種掌握與就手的感受,屬於非反思的、日常性的,理所當然(Taken-for-grantedness),它們共同構成了「家」。每次回到家中,你都知道「家」會為你保留並提供什麼,這一切都是恆定、必然和可知的。同樣的道理,為何我們住酒店時不會將其視為家?因為一方面它具備宿舍的特質,我不會長期居住於此,而是暫時改變自身的習慣以適應它;另一方面,它不具備日常性、非反思性、理所當然性以及事事就手等「家」的特質,因為它不會遷就我的習慣。
「家」必然有「情」
「心安即是家」這一說法雖然無誤,卻只是自我安慰的表達,因為人類並非獨立存在。正如海德格所說,人類同時是為他人存在(being for others),即社會關係的體現。因此,「家」不僅僅是自身的居所,還包括所處的社會,而這個社會也具備一定程度的日常性、非反思性、理所當然性和事事就手的特質,這就是所謂的集體回憶與人情。例如,我在香港生活久了,自然知道哪家麵店的水準高、何處購買螃蟹最為划算,以及中文大學裡哪三四十家餐廳的奶茶和奶油多士最為出色,這一切都構成了我在香港七十年生活的回憶,它們都是「家」的一部分。

如果沒有這些,試問「家」還剩下什麼呢?因此,「家」必然有「情」的存在。於是,我們又找到了「家」之所以為「家」的另一個要素,而宿舍和酒店都不具備這一要素,那便是「情」。我常常說,人類是「授情者」,我們不僅為自身的生命賦予意義,也為他人的生命賦予「情」,而「情」正是在海德格所提到的「為他人存在」中所建立的關係中自然產生的結果。因此,社會是「家」的重要構成部分,而社會又因「情」而聯繫,因此「情」必然是「家」的要素。
談到「情」,我們不得不提到語言的問題。語言是「家」的另一個構成要素。為何我對台灣缺乏歸屬感?因為這裡並非以廣東話為主。語言是人類情感交流的主要媒介,若語言不通,或者不能使用母語暢所欲言,那麼「情」的建立自然會受到阻礙,從而使「家」無法圓滿形成。
流亡:主動卻不自由的狀態
粗略談過流亡的定義、「家」的定義及流亡與「家」的關係後,接下來我將進一步探討移民、放逐和流亡三者之間的不同,以及流亡所衍生的各種哲學問題。
移民並不需要反思,且隨時可以返回故鄉,隨著全球化的日益成熟,移民在二十世紀已成為普遍現象;放逐則是因政府迫害或犯罪而遭驅逐,這是一種身不由己的懲罰;流亡則是因為我自覺與當權者的立場不同,同時我的言行也不被政府所容忍,因此自願離開,並可能永遠無法回去。由此可見,流亡既不同於放逐的被動性,也不同於移民隨時可以回鄉的自由。換言之,流亡是一種主動卻不自由的狀態。
我的師長們,如唐君毅和勞思光先生,皆是從極權的中國或專制的台灣流亡來到香港。香港為他們提供了自由的空間,讓他們能夠發展學術事業,因此兩人都在香港度過大半生,唐先生最終在香港去世,而勞先生則在晚年離開香港返回台灣。我生於香港,正如開頭所述,於2020年決定離開,勞先生曾表示,除非共產黨與國民黨有所改變,否則他絕不再踏足中國和台灣的土地,我也同樣有此心態。這就是流亡者的態度。

「喪家」於世
1970年代,我仍在德國就學,那時德國的台灣人非常多,我有不少台灣同學都反對國民黨。其中一位同學在德國待了八年,卻始終未能畢業。我問他,為何不盡快完成博士論文以便畢業?他回答道:「寫完博士論文後,我去哪裡?」當時我並不明白這句話的悲哀之處,如今我已然明白,因為當時我取得學位後,香港是我的家,我可以回去。但他卻無家可歸。如今我自己成為流亡者,回想起他的話,才真正體會到其中的淒涼與悲慘。
在這個意義上,流亡並非只是喪失「家」,而是「喪家」於世。不僅是離開了「家」這個空間,而是與此地的一切情感、回憶和關係都被迫切斷,讓你在世上找不到回去的地方。以往無論外出旅行或公幹,都知道總有歸期,但自從2020年這次出發後,我明白這次可能永無歸期。我的這位德國同學雖然未明言,但顯然他也持有流亡之心,對於不變的台灣,他誓言不再回國。
確實,香港已經死去,如今的香港不再是Hong Kong,而只是Xianggang,就如上世紀神州大地從古華夏淪為中國一般。以前我們不曾知道香港的重要性,如今失去後,才明白它的珍貴。香港人正因為無家可歸(existential homelessness)而陷入存在危機(existential crisis)之中。這場危機在於,我們的存在同時受到外界與內心的批判與挑戰,既遭他人質疑,也自我懷疑。儘管流亡者因放棄家園而獲得了自由,尤其是思想與言論的自由,但也因此深陷存在的疑惑中,無法自拔。當然,留在香港的人並不代表擁有「家」,他們也失去了「家」,因為香港已死,如今他們所居之地僅僅是叫做香港,因此他們是在自身家園中流亡;同時,他們也沒有自由。
汪洋中的錨
談到存在的疑惑,讓我想起我曾讀過不少存在主義的書籍,存在主義者不斷質疑存在本身:人存在於世是否有意義?難道生命不是毫無意義(Meaninglessness)、空虛(Emptiness)、無聊(Boredom)、焦慮(Anxiety)、不真實(inauthentic)、缺乏安全感(Insecurity)、隨時可能死亡、未知的嗎?而最重要的問題是,為何有而非無?(Why is there anything at all, rather than nothing?)這是哲學中最根本的問題。種種疑問,皆是海德格所欲知並追問的內容。至於如何解答,則是哲學的責任。
與海德格相同,唐君毅先生也簡明扼要地描繪了現代人如何陷入存在疑惑的困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外不在人,內不在己。神明道隱(上不在天)、自絕於大自然(下不在田)、對人際關係或文明一無所獲(外不在人)、不自知為何物(內不在己),這便是所謂的四不掛搭,完整地道出了現代人的苦況。
面對這四不掛搭,唐先生雖然對於花果飄零感到感慨,但並未讓自己陷入疑惑與空虛之中,而是努力思考與生活。雖然他失去了四川宜賓的家,但他開放心胸,放眼整個華夏作為他的家,而他的所有著作也皆以過去的事物為依歸。這就如同在茫茫汪洋中找到一個錨,讓自己在驚風駭浪中穩立。唐先生借此悟得生命的真諦,哲學幫助他尋找到解惑脫困的道路。
如今的香港人正面臨著前人曾經遭遇的問題,我們的家園被侵略者以暴力手段摧毀,這導致了我們在自身存在上的困惑,身份受到質疑與挑戰。我們應該如何面對自己?又應該如何面對流亡的現實?前人的經驗與智慧,或許能為我們帶來一些啟示,成為我們思索人生的指路明燈。
最後,針對本次主題,做一個簡短的總結:「家」與「流亡」在當今的香港,正體現出無家可歸的流亡狀態,無論是對於留港者還是流亡者而言,情況皆是如此。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