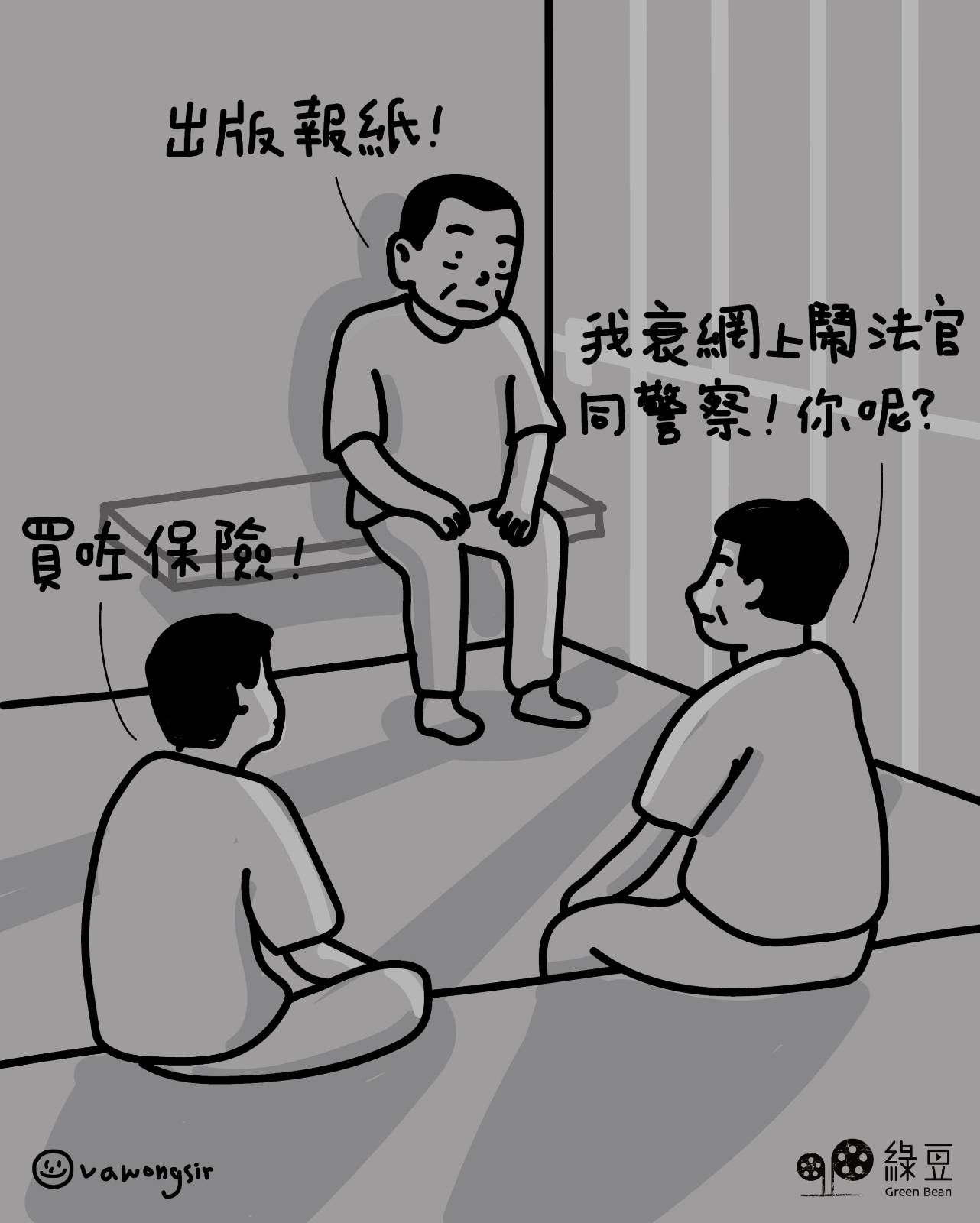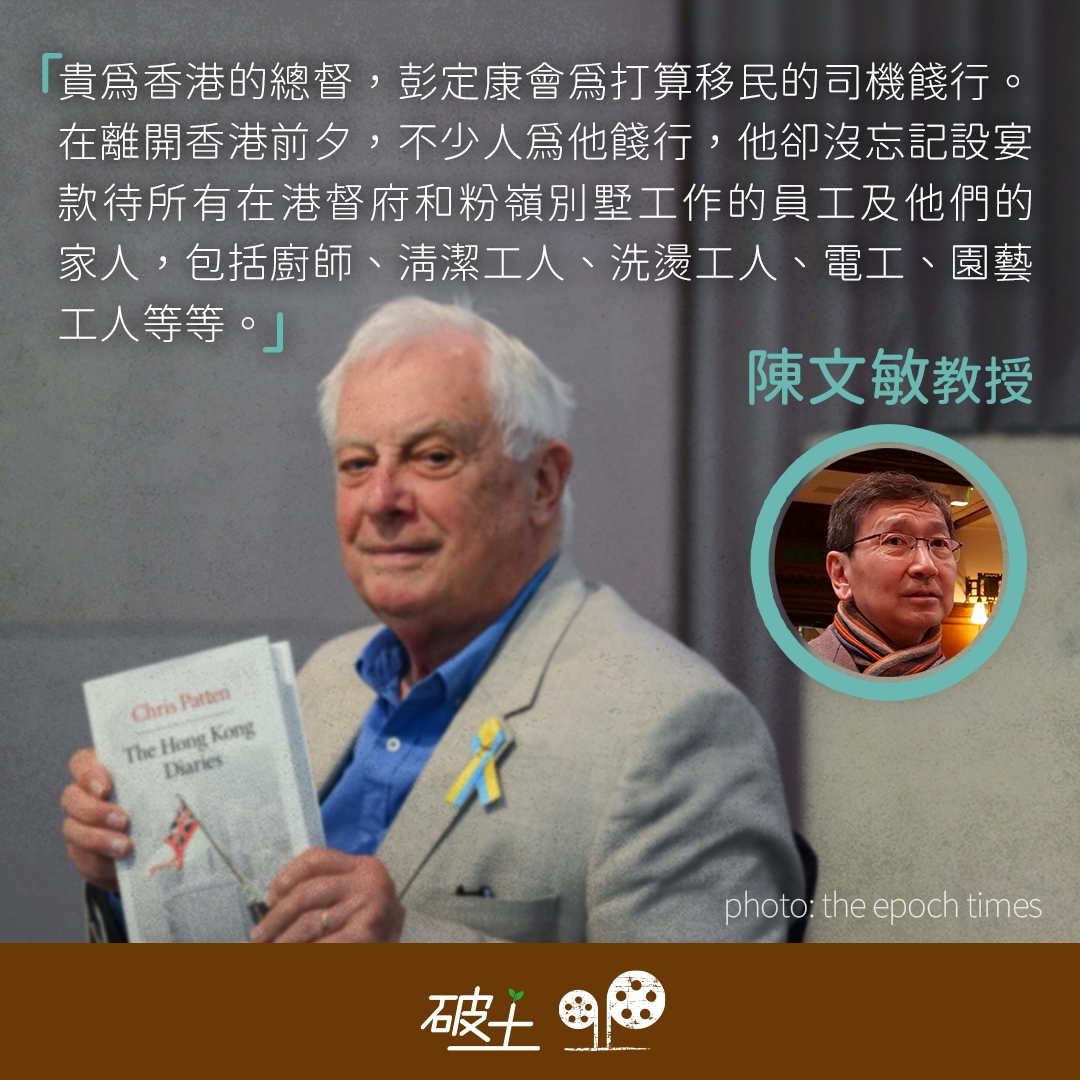從張敬生減刑案看近期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

當公眾的焦點仍聚集於「立場案」的判決和量刑時[1],大約同時間一宗人身保護令的判決似乎遭到忽略,但這宗案件對香港的司法獨立和法治的影響,絕不下於立場案。[2]
2021年7月1日晚上,銅鑼灣崇光百貨公司外,一名男子突然持刀從後襲擊一名當值警員,令該名警員身體嚴重受傷。該名男子隨即以刀刺向自己心臓自殺,送院後證實不治。警方其後將事件定性為孤狼式恐怖襲擊,並警告其後往現場獻花的市民可能觸犯煽動恐怖主義罪。
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在事件後通過動議,表揚支持七一刺警案疑兇。雖然他們隨後收回議案並向公眾道歉,但時任主席張敬生等四人仍遭檢控一項《國安法》下的宣揚恐怖主義罪,及一項《侵害人身罪條例》下的煽惑他人有意圖傷人的交替控罪。他們後來承認交替控罪,被判囚兩年,2024年九月中獲上訴庭減刑至15個月[3]。
隨後張敬生稱他因為在獄中行為良好,按他被判刑時的《監獄規例》,應該獲得三分之一刑期扣減,可即時獲得釋放,但懲教署繼續羈留他。他遂向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要求即時獲釋。懲教署署長其後根據新修訂的《監獄規例》作出決定,不信納張敬生獲假釋後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法院最終駁回人身保護令的申請。
案中的關鍵問題是在張敬生服刑期間,政府修訂了《監獄規例》,令到某些罪行會有不獲假釋的假定,並註明該修訂具追溯效力。新的修訂是否適用於這個案?這本來可以只是一個法律解釋的問題,但隨後的發展令案件變成一個法治和司法獨立的問題。
《監獄規例》的修訂具追溯效力
在文明社會,刑事罪行一般不會有追溯效力,這是要保障市民不會因今天法律的修改,令昨天原來合法的行為在今天變為不合法而受到法律的懲罰。同樣地,一名被告在昨天所觸犯的罪行,不會因為法律在今天加重了該罪行的刑罰而被判更重的刑罰。這原則受到《人權法案》的保障。
根據《監獄規例》第68條,若在囚人士完成三分二的刑期後,懲教署署長可因應在囚人士於在囚期間行為良好而給予假釋。雖然是否獲得假釋是由懲教署署長酌情決定,但在一般情況下,只要在獄中行為良好便可獲三分一的刑期減免,這是眾所周知的慣例。這慣例亦令監獄較易管理,為在囚人士提供誘因,在服刑期間盡量表現良好,以求獲得刑期減免。
2023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修改了假釋的規定,對觸犯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士,除非懲教署署長信納他們獲假釋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否則不得獲假釋。這修訂引進了一個不獲假釋的假定,而要推翻這假定,囚犯要提交足夠證據去推翻一項負面的假設 (a negative state of affairs ),即他獲假釋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這是非常高的門檻,幾乎等於一旦新例適用的話,即使在囚人士在獄中行為良好,仍是相當難獲假釋。這規定具追溯力,適用於已在服刑的在囚人士。
何謂「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這新規定有兩個具爭議的地方:第一是修例的適用範圍?新例適用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法例對「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定義,除了包括《國安法》、《國安法執行細則》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的控罪外,還包括「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但何謂「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則沒有任何定義。
於是,若被告觸犯的控罪並非《國安法》,而是《公安條例》下的控罪,例如暴動、非法集會、組織或參與未經批准的公眾參會、甚至襲警的罪行,那這規定是否適用?在執行這規例時,懲教署署長需要闡釋何謂「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他所採納的解釋,可能擴闊《監獄規例》的適用範圍。那懲教署會如何演繹這一規定?國安和公安如何區分?國家安全應有別於公共安全,若政府選擇不以《國安法》提出起訴,法院按《公安條例》作出判刑,那在決定假釋的時候,該罪行便不該當作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否則公安和國安的界線便會變得很模糊,令人難以適從。
但事實是否如此?懲教署的回應是:「署方會根據法律行事,不存在自行擴闊修例的適用範圍」。但這顯然沒有解釋,當法例沒有作出定義時,懲教署如何決定哪些控罪屬「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懲教署署長又能否交待,在新例生效後,有哪些罪行因這一規定而不獲減刑?這決定是如何作出?法治的一個基本原則是法例的要求需要合理地清晰,市民有權知道,觸犯那些罪行會引致失去獲假釋的機會。
實際延長了剝奪人身自由的時間
第二個爭議點是追溯効力的公平問題。懲教署稱:「減刑是酌情權,不行使酌情權並沒有增加刑罰。」然而,在修例前,若被告行為良好,懲教署署長並沒有太大的空間不給予減刑,新例改變了這個遊戲規則,起點是被告不會獲得減刑。政府當然可以改變遊戲規則,但當新例具追溯效力時,對一些已在服刑的人士,或因考慮減刑因素而決定認罪的在囚人士,在他們作出決定後才改變遊戲規則,這是否公平?《人權法案》第12條的核心價值,便正正在「公平」二字。
在2000年的「呂達恆案」[4],《監管釋囚條例》賦予監管釋囚委員會權力,於囚犯在假釋期間,因違反假釋條件或可能進行犯罪行為而召回釋囚,條例具追溯效力。申請人在條例通過前已獲假釋,他不滿召回的權力亦適用於他,遂提出司法覆核。原訟法庭在駁回他的申請時指出,即使在假釋期間,申請人在法律上仍在服刑,故不存在他的權利受到侵犯,並強調相關條例的目的在協助釋囚更新,重新融入社會,召回的權力只是支持有效落實更新計劃,並非用於懲罰釋囚,因而認為即使有追溯效力亦沒有違反《人權法案》。
技術上而言,即使被告獲得假釋,法律上他仍是在服刑,但實際上他已是重獲自由。一個被判九年監禁的囚犯,在舊例下,若在囚期間行為良好,可以在服滿六年刑期後便出獄,但在新例下卻可能不獲假釋而須服滿九年的刑期。對在囚人士而言,新例的效果是延長了囚犯被監禁的時間,不管那三年在法律上如何定義,在囚人士實際上被奪去人身自由的時間是被延長了。歐洲人權法院便傾向採納一個較現實的理解,認為在這情況下已構成剝奪人身自由,若拒絕假釋的機制具追溯效力或是出於懲罰性的考慮,那便可能違反《人權法案》的保障。
此外,在「呂達恆案」中,召回的權力並不影響在囚人士獲得假釋的機會,只是釋囚在假釋期間仍受監督,並在特定的情況下可能被召回監獄繼續服刑。相對而言,《監獄規例》的修訂,卻是取締或剝奪獲得假釋的機會,而且有别於舊例,新例是以在囚人士不能獲得假釋為出發點。因此,「呂達恆案」的判決未必適用於新的規定。
在這方面,懲教署只是重申國家安全的重要,完全沒有回應為何新例需要有追溯效力,以及有追溯力是否公平的憂慮。「呂達恆案」的技術性判決是否合理仍有爭論的空間,而該案強調具追溯效力的法例的目的是協助釋囚更新,但新的《監獄規例》,即使在囚人士在獄中行為良好,但卻因為案件的性質而可能失去獲得假釋的機會,目的似乎是出於懲罰多於更新的考量。
張敬生人身保護令案
新例是否適用?
張敬生服滿三分二的刑期,在獄中行為良好,但仍遭懲教署繼續羈留,他遂於2024年9月20日單方面提出人身保護令的申請(ex parte application)。當值法官認為需要聆聽署方的解釋才能作決定,遂將案件押後至9月23日(接著的周一), 由負責審理憲法及行政法案件的專責法官高浩文審理。
但到了9月23日開庭時,案件改由國安法指定法官黎婉姫審理。法院解釋,在過去的周末,特首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115條發出證明書,指該案涉及國家安全,高院首席法官遂將案件轉介由一名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
上文指出,新修訂的《監獄規例》適用範圍模糊,因為除了《國安法》以外,該規例還適用於「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但這會包括甚麼罪行和以甚麼準則來決定?張敬生被判的是《侵害人身罪條例》下的煽惑他人意圖傷人罪,這並非《國安法》下的罪行,是否因為涉及警察便成為國家安全罪行?
原來,這決定是由特首作出,特首在開審前夕發出證明書,指該案涉及國家安全,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115條,在特首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可以就某行為或事宜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某材料是否涉及國家秘密的認定問題發出證明書。「張敬生案」並不涉及任何國家秘密,只是一宗普通的襲警案,特首是根據甚麼理由認為該案會涉及國家安全?然而,特首的證明書不單令案件需要由一位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並同時處理了《監獄規例》的適用範圍,這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特首不用解釋,證明書亦不受法院挑戰。
於是,一個法律上本來應該由懲教署署長作出、受法院監督的決定,變成一個由特首作出、不需提出理據,亦不受任何約束的決定。
國安委的介入
懲教署反對人身保護令的申請,它指張敬生應循司法覆核提出質疑,但司法覆核是針對行政機關的某個決定,而當時署方的代表律師亦承認,懲教署署長仍未就假釋問題作出決定,故根本沒有可供司法覆核的決定。懲教署亦稱未能信納若張敬生獲假釋後不會作出危及國家安全的行為,但在法官連番追問下,署方律師仍無法提出證據支持這説法。
由於法院就人身保護令的申請需要排期聆訊,故張敬生提出要求,在等候聆訊期間暫准獲得保釋。署方反對,指稱《國安法》關於保釋的條款適用於本案。法官指出當日張敬生被控包括《國安法》控罪的兩項控罪時仍獲保釋,故法官傾向准許保釋,但會收緊保釋條件,最後署方代表律師指需要向懲教署就保釋條件索取指示,法官同意將案件押後一天處理保釋,及安排於10月3日就人身保護令的申請進行聆訊。
翌日甫開庭,懲教署便向法院提交兩份文件,一是國安委的決定,二是懲教署署長就假釋的決定,兩項決定似乎都是在案件被押後當天(即9月23日)才作出。國安委認為若張敬生獲得減刑,不利於國家安全。懲教署署長則表示,考慮了「評委會」的報告和意見、警務處國安處的意見,並徵詢了國安委的判斷和決定,及所有相關資料和因素後,他不信納張敬生獲得減刑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因此根據新例,不准予以假釋。由於國安委的決定對法院有約束力,並考慮了懲教署署長的決定,法院認為毋須再處理保釋申請,並同時撤銷人身保護令的申請,及勒令張敬生須支付署方的訟費。
人身保護令申請至此終結,張敬生要繼續服滿餘下的刑期,但案件卻留下最少四個疑問:
追溯效力是否公平?
第一,新規例是在張敬生服刑後才通過,當日他被控《國安法》下的宣揚恐怖主義罪,後來控辯雙方達成協議,被告承認交替控罪,控方則同意不對被告作出《國安法》的檢控及同意撤銷《國安法》的控罪,法院因此撤銷了《國安法》下的宣揚恐怖主義的控罪。
於是,被告只是面對一項控罪,他被判刑的是《侵害人身罪條例》下的煽惑他人有意圖傷人的控罪。很明顯,被告當日承認該控罪以換取控方同意撤銷《國安法》下的控罪,判刑的長短和按當時的法例,行為良好可獲三分之一的刑期減免,肯定是承認控罪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當被告因此認罪,並在服刑近一年後才改變遊戲規則,控方當日同意撤銷《國安法》下的控罪,現在卻將被告刻意選擇,並獲控方接納的非國安法控罪,納入新規例的適用範圍內,這樣公平嗎?
國安委的介入
第二,國安委的文件全文如下[5]:
「國安委就此考慮了囚犯張敬生在監禁期間的實際情況、國安委獲得的所有相關資料和因素,作出的判斷和決定。
本秘書處現將國安委的判斷和決定,通知署長如下:
(1)基於案件的性質、事實及情況,囚犯張敬生在此案中所被定罪的罪行,即「煽惑他人有意圖傷人」罪,涉及國家安全,屬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及;
(2)若該囚犯獲得減刑,不利於國家安全。」
國安委的決定只有結論,並無提出任何理據,這決定對懲教署署長有約束力,在國安委作出決定後,懲教署署長根本不可能作出相異的決定。故此,懲教署署長的決定,只是從形式上去符合《監獄規例》的要求及落實國安委的決定,並沒有實質意義,甚至不存在署長可以獨立作出決定的可能性。
同樣地,國安委的決定對法院具約束力,亦不容法院覆核或質疑。該決定第一段的意思是新的《監獄規例》及《國安法》適用於本案,前者涉及假釋,後者涉及保釋。第二段則説張敬生獲減刑不利於國家安全,所以不該給予假釋,基於同樣理由,亦不該給予保釋。至此,法院經已是無事可判,只能駁回人身保護令及保釋的申請。
但國安委是否有權介入這宗案件?國安法第14條界定國安委的職責,即:
- 分析研判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形勢、規劃有關工作、制定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政策;
- 推進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建設;
- 協調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工作和重大行動。
第一和第二點均屬政策層面的工作,分析研判形勢、規劃工作、制定政策、推進法律制度及執行機制建設,第三點則是協調一些重點工作和重要大行動,也是一些策略性的工作。
這三方面的工作均不包括在個別案件中,向懲教署署長提供署長應如何行使法定酌情權的意見。但在這案件中,國安委所處理的正是法院在訴訟中要裁決的事項,而國安委的決定,實際上已取代法庭作出結論,而且不需給予理由,不能提出上訴或司法覆核,法院淪為橡皮圖章。若國安委可以隨時介入任何具體個案的司法程序,司法獨立還有空間嗎?
評委會的法律基礎?
第三,懲教署署長在作出決定的時候,考慮了一個「評委會」的報告和意見。懲教署署長所指的評委會又是一個甚麽機構?在接受傳媒查詢時,懲教署並無作出解釋。早前在「馬俊文案」,新的《監獄規例》在馬俊文服刑還有五天便服滿三分之二刑期之日通過,令他要繼續服刑近五個多月才可獲釋。他已提出司法覆核,申請書稱他當時收到署名「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在囚人士評審委員會」的便箋,表示考慮了他在獄中的表現、更生進度及心理狀況評估,認為「現階段沒有任何資料表明,如果對馬先生給予減刑,馬先生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
這相信便是懲教署署長在「張敬生案」所指的「評委會」,但這評委會有何法律基礎?有甚麼權力和成員?根據甚麼程序作出評估?受影響的在囚人士有何參與或答辯的機會?這些問題涉及程序公義,但卻沒有任何透明度或澄清。
訟費
第四,法院駁回人身保護令的申請後,應署方要求勒令張敬生須支付懲教署的訟費,這決定頗難令人信服。張敬生在9月20日提出人身保護令的申請,當時他被判刑的罪行並非涉及國家安全的罪行,而他已服刑超過三分二的刑期,獄中行為良好,但懲教署並沒就他的假釋作出決定,並繼續羈押他,故當時他有表面證據及理由提出人身保護令的申請。
9月23日的聆訊,法官亦表示傾向批准保釋,當時署方仍未能提出任何書面證據反對申請。直至9月24日的聆訊,署方才首次向法院提交國安委和懲教署署長的決定,而兩個決定皆是在9月23日才作出,雙方律師也是在9月24日開庭前才收到這兩份文件,而這兩份文件正是案件的轉捩點。
在這情況下,較公平的裁決應該是各自負擔己方的律師費。一名尚未畢業的大學生,所犯的事並非傷天害理或大奸大惡,已經服刑十多月,出獄後恐怕亦前途盡毀,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他提出的人身保護令亦非全無道理,但署方仍要求張敬生支付署方龐大的訟費,而法院竟然批淮,這就是所謂公義嗎?
結語
即使張敬生不獲假釋,他也只需服刑多四十天左右便刑滿出獄。他所觸犯的罪行只是在時任港大評議會主席時通過一項議案,這行為是魯莾和未經深思熟慮,事後亦已隨即收回並向公眾道歉,就這事要提出刑事檢控已經是極為荒謬,最後被判入獄兩年(後改為15個月 )。及後其行為被指涉及國家安全,令新的《監獄規例》適用,繼而動用國安委的決定,再次確認這一點及否決張敬生獲假釋,架空法院,所採用的手段完全超出比例。申請人只是一名學生,是否要這樣咄咄逼人地去摧毀一名大好青年的前途!
更令人擔憂的是對司法制度的破壞,在新的《監獄規例》下,懲教署署長要決定新例是否適用、若張獲釋是否不利於國家安全,這是法例賦予他的權力和責任,而他的決定受到司法監督。現在,國安委基本上代懲教署署長作出決定,他根本沒有不跟隨國安委的決定的餘地;繼而國安委亦取代法院,在司法程序中作出法院要裁決的問題,令法院根本沒有裁決的空間,更遑論司法獨立。
國安委本來該是一個政策性的機構,但它已取代行政和司法,在「張敬生案」,國安委的介入,將法院淪為橡皮圖章;在「黎智英海外律師代表案」[6],終審法院批准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 QC代表黎智英,國安委則指示入境處拒絕發給Tim Owen入境簽證,間接推翻終審法院的裁決。國安委既可決定宏觀政策,亦可介入具體案件,即使它的權力只限於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但國家安全的概念已是無遠弗屆,而且是由國安委自行界定,任何國家認為重要的事情或利益均可以是涉及國家安全;亦不只限於刑事罪行,例如在民商糾紛或執行仲裁判決,若涉及國家利益時,亦不難想像國安委會介入案件[7]。國安委的地位在法律之上,而它的決定,毋須解釋,亦不受任何約束,這就是新香港下的法治!
註:
[1] 就「立場案」的評論,見陳文敏:評立場案 (1-4): https://greenbean.media/category/ground-breaking/%E7%A0%B4%E5%9C%9F%E5%9C%96%E6%96%87/%E6%B5%B7%E5%A4%96%E9%9A%A8%E7%AD%86-%E9%99%B3%E6%96%87%E6%95%8F/
[2] 「張敬生 v 懲教署署長」,HCZZ75/2024 (CACC201/2023; [2023] HKDC 1463。
[3] 上訴法院於2024年9月13日推翻原審時的兩年監禁,認為原審法官以35個月作為量刑起點太嚴苛,改為15個月監禁。完稿前法院尚未頒下詳細的書面判詞: https://www.jurist.org/news/2024/09/hong-kong-appeals-court-reduces-sentences-of-4-former-student-leaders-convicted-of-glorifying-police-attacker/
[4] Lui Tat Hang v The Post-Release Supervision Board [2000] 1 HKC 297.
[5] 「港大評議會案張敬生爭提早獲釋失敗」,法庭線,2024.09.24: https://thewitnesshk.com/%e6%b8%af%e5%a4%a7%e8%a9%95%e8%ad%b0%e6%9c%83%e6%a1%88%e5%bc%b5%e6%95%ac%e7%94%9f%e7%88%ad%e6%8f%90%e6%97%a9%e7%8d%b2%e9%87%8b-%e5%9c%8b%e5%ae%89%e5%a7%94%e4%bb%8b%e5%85%a5%e4%bd%9c%e5%87%ba%e6%b1%ba/
[6] Re Tim Owen [2022] HKCFA 23; 黎智英隨後就入境處拒發簽證提出司法覆核,但遭法院以無權覆核國安委的決定而駁回:Re Tim Owen [2023] HKCFI 1382.
[7] 例如在「國家豁免特權案」(F 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 v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2011) 14 HKCFAR 95),這是一宗民事執行仲裁判決的案件,涉及剛果民主共和國,雖然根據普通法,一個主權國家的商業行為並不享有豁免特權,這稱之為「相對國家豁免特權」 (relative state immunity),但因涉及中央政府在非洲的龐大經濟和政治利益,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改變香港的普通法,以「絕對的國家豁免特權」 (absolute state immunity),取代普通法的「相對國家豁免特權」。
▌[海外隨筆]作者簡介
陳文敏,前香港大學公法講座教授,2021年退休後,旅居英國,並出任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客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