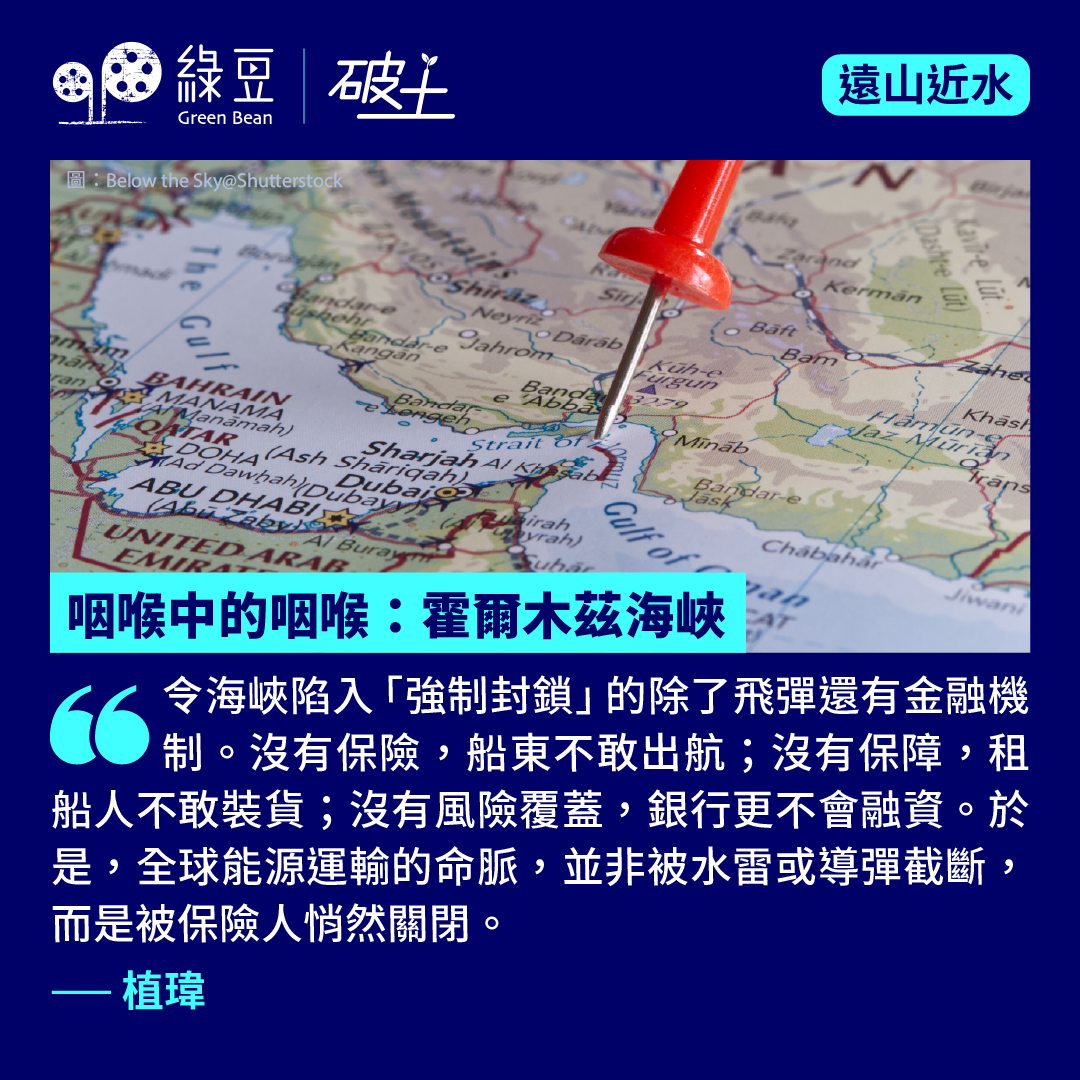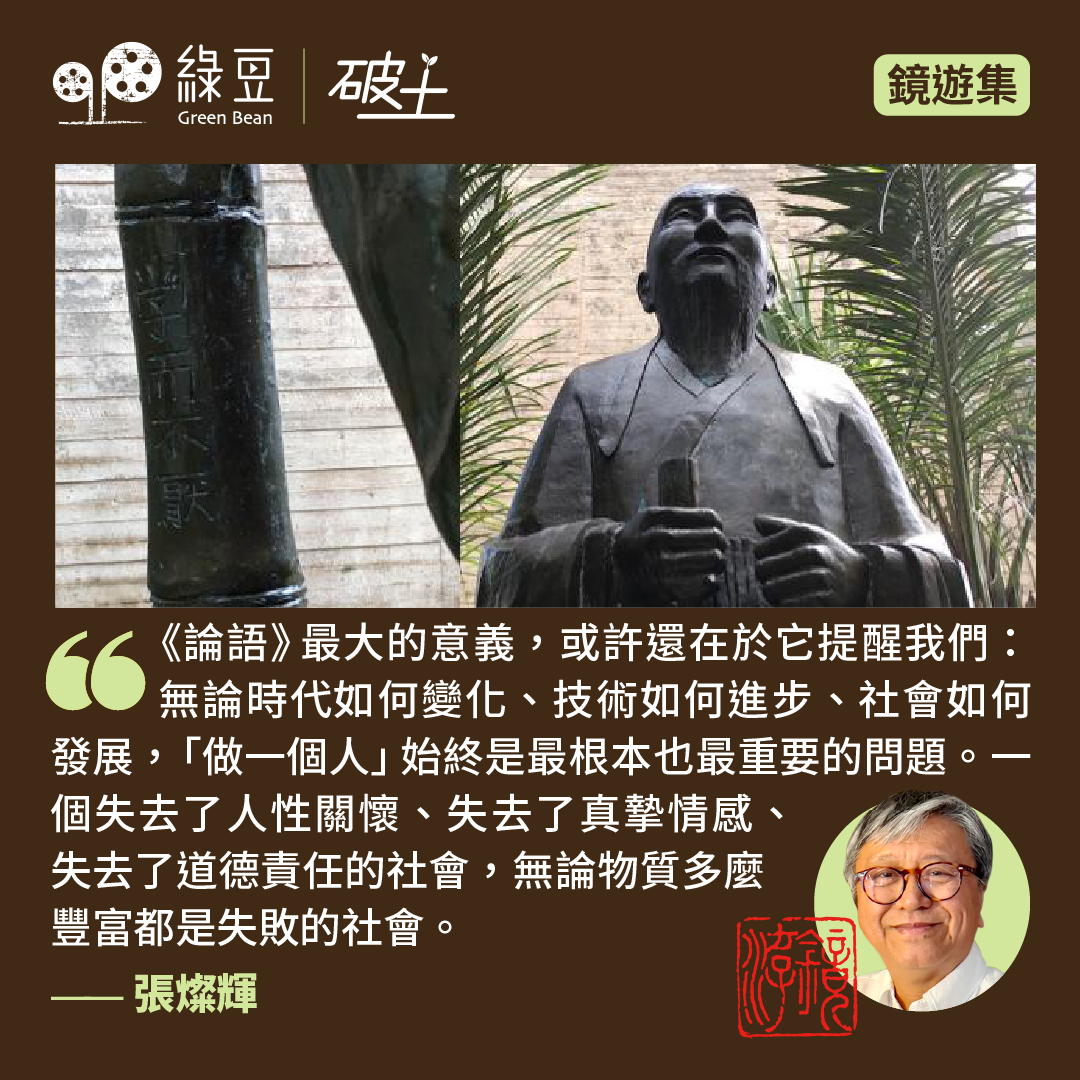《奧德賽》中的成長、返鄉與堅守(上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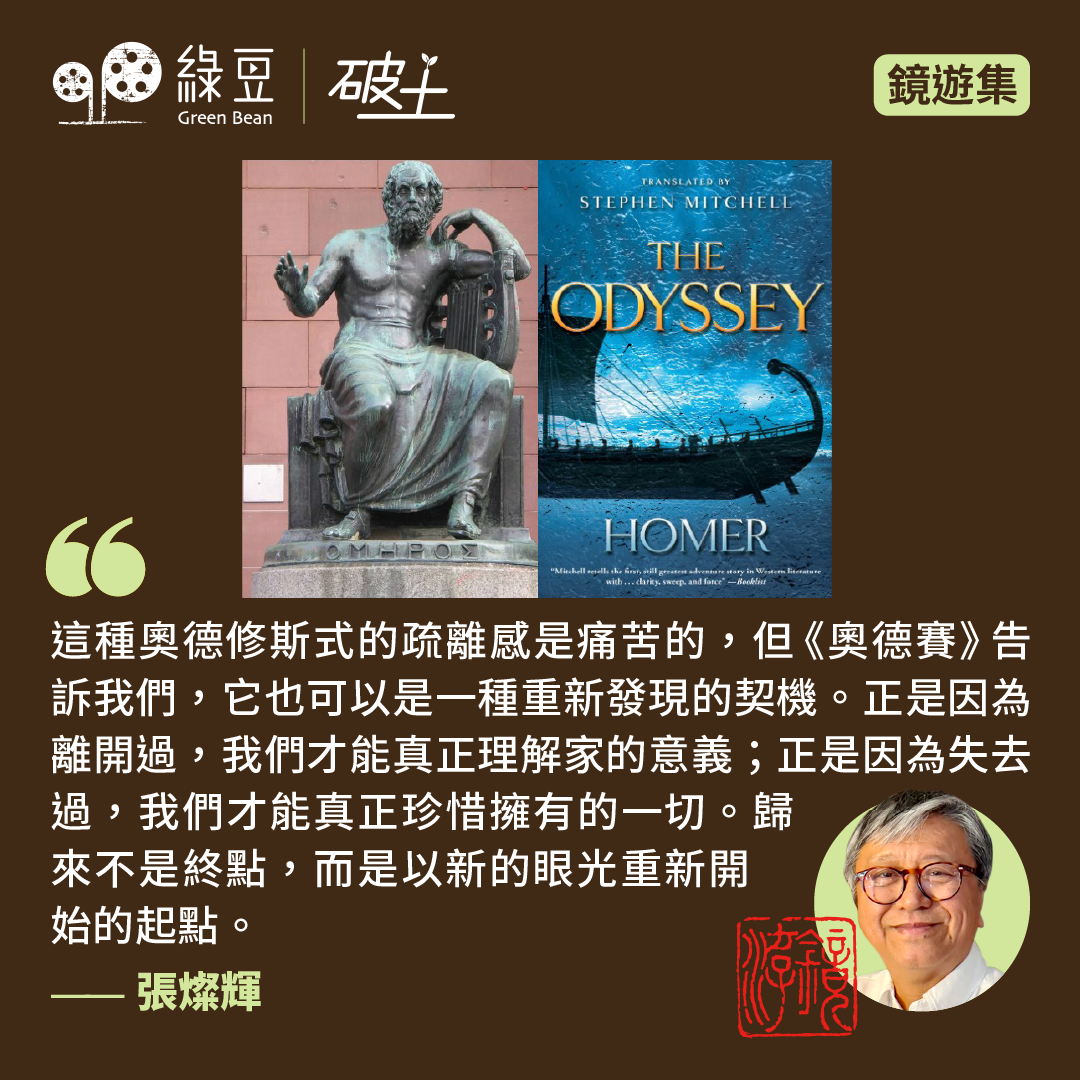
《重讀經典:與人文和自然對話》
經典01 文本自Odyssey/Homer
《與人文對話 – 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讀本》 第一版,2011,頁7 - 104。
荷馬 (Homer)——西方文學的源頭
荷馬其人與其時代
在西方文明的漫長歷史中,沒有任何一位詩人比荷馬更具有根本性的影響。這位生活在約公元前八世紀的古希臘遊吟詩人,被後世尊為「詩人中的詩人」,他的名字本身就成為了史詩藝術的代名詞。關於荷馬的生平,古代流傳著許多傳說,其中最著名的是說他是一位盲眼詩人,來自愛奧尼亞 (Ionia)地區。雖然現代學者對這些傳說的真實性存有爭議,甚至有人懷疑荷馬是否真有其人,但沒有人能夠否認以他之名流傳下來的兩部偉大史詩——《伊利亞特》(Iliad)與《奧德賽》(Odyssey)——對整個西方文明產生了無可估量的影響。
荷馬生活的時代,正是古希臘從黑暗時代走向古風時代的過渡期。這個時期,希臘人開始從腓尼基人(Phoenicians)那裡學習字母文字,口頭傳唱的史詩逐漸被記錄下來。荷馬站在這個歷史的關鍵節點上,他繼承了數百年來遊吟詩人口耳相傳的史詩傳統,同時又以其天才般的藝術才能,將這些材料重新組織、提煉、昇華,創造出兩部結構宏偉、主題深刻、語言優美的不朽傑作。
古希臘人視荷馬為「教育者」,他的史詩是每個希臘公民必須學習的基本教材。柏拉圖雖然在《理想國》(Republic)中批評詩歌對靈魂的負面影響,主張將詩人逐出理想城邦,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認荷馬是「希臘的教師」,是塑造希臘民族精神的最重要人物。亞里士多德在《詩學》(Poetics)中以荷馬為分析悲劇與史詩的最高典範,認為荷馬在敘事藝術上達到了無人能及的高度。
《伊利亞特》(Iliad)與《奧德賽》(Odyssey ):戰爭與歸途
荷馬留給後世的兩部史詩——《伊利亞特》與《奧德賽》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敘事循環,共同講述了特洛伊(Troy)戰爭及其後果的故事。這兩部作品既相互獨立,又彼此呼應,分別從不同角度探討了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
《伊利亞特》以特洛伊戰爭第十年的一個片段為中心,講述了希臘聯軍統帥阿伽門農(Agamemnon)與最偉大的戰士阿喀琉斯(Achilles)之間的衝突。阿喀琉斯因為榮譽受到侮辱而憤怒地退出戰鬥,導致希臘軍隊節節敗退。當他最親密的戰友帕特羅克洛斯(Patroclus)被特洛伊王子赫克托爾(Hector)殺死後,阿喀琉斯重返戰場,為朋友復仇,最終殺死了赫克托爾。史詩以赫克托爾的葬禮結束,但特洛伊城的陷落和阿喀琉斯的死亡已經隱約可見。
《伊利亞特》探討的核心主題是戰爭中的榮耀與悲劇、憤怒與和解、生命的短暫與不朽的渴望。阿喀琉斯是一個典型的悲劇英雄,他明知自己命中注定要死在特洛伊城下,卻仍然選擇短暫而光榮的生命,而非漫長而平庸的人生。他的憤怒是史詩的開端和動力,而他最終對普里阿摩斯(Priam)國王的憐憫——將赫克托爾的屍體歸還給這位悲傷的父親——則標誌著他人性的回歸和昇華。
相比之下,《奧德賽》則將視角從戰場轉向歸途,從集體的戰爭轉向個人的旅程,從外在的征服轉向內在的成長。這部史詩講述了希臘英雄奧德修斯(Odysseus)在特洛伊戰爭結束後,歷經十年艱辛、穿越無數險阻、最終回到故鄉伊薩卡(Ithaca)的故事。如果說《伊利亞特》歌頌的是阿喀琉斯式的英雄主義——以武力和激情著稱,那麼《奧德賽》則展現了另一種英雄典範——以智慧、忍耐和對家庭的忠誠為核心。
兩部史詩的對位與互補
《伊利亞特》與《奧德賽》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對位關係。首先,在主題上,前者關注戰爭與死亡,後者關注歸家與重生;前者展現的是集體的命運,後者則聚焦於個人和家庭的經歷。其次,在英雄類型上,阿喀琉斯代表了力量、速度和不妥協的激情,而奧德修斯則以多謀善斷、隨機應變著稱。在《伊利亞特》中,奧德修斯已經是希臘軍中最足智多謀的將領,但他只是眾多英雄中的一個;到了《奧德賽》,他成為了絕對的主角,他的智慧成為克服一切困難的關鍵。
最能體現兩部史詩對話關係的,是奧德修斯在冥界與阿喀琉斯靈魂的相遇。奧德修斯稱讚阿喀琉斯生前在勇士中最受尊敬,死後在亡靈中地位最高。但阿喀琉斯的回答卻令人震驚:「光榮的奧德修斯啊,不要對我說死亡的安慰話。我寧願活在地上,作為一個窮人的長工,侍奉一個無田無產的人,也不願在這裡統治所有的死者。」這段話是對《伊利亞特》英雄觀的深刻反思。阿喀琉斯在生前選擇了短暫而光榮的生命,但在死後卻後悔了這個選擇。這種反思為《奧德賽》的主題奠定了基調:生命的價值不在於榮耀或不朽,而在於真實的生活、與所愛之人的團聚、以及履行自己的責任。
荷馬對西方文化的深遠影響
荷馬史詩對西方文化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持久的、無可替代的。在文學上,荷馬開創了史詩這一偉大體裁,確立了敘事詩的基本範式。從古羅馬維吉爾(Virgil)的《埃涅阿斯紀》(Aeneid)到中世紀但丁(Dante)的《神曲》(Divine Comedy),從文藝復興時期塔索(Torquato Tasso)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Delivered)到彌爾頓(Milton)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所有偉大的史詩都以荷馬為楷模。現代文學中,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直接以奧德修斯的拉丁名字為書名,將荷馬史詩的結構移植到二十世紀都柏林(Dublin)的一天之中,證明了荷馬敘事模式的永恆生命力。
在哲學上,荷馬史詩提出了關於人類處境的根本問題:什麼是真正的英雄?人應該如何面對死亡?榮譽與生命孰輕孰重?家庭與責任的意義是什麼?這些問題被後來的希臘哲學家們反覆討論,成為西方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的重要源頭。在藝術上,荷馬史詩中的場景和人物成為繪畫、雕塑、戲劇的永恆題材,從古典時代到現代,無數藝術家從荷馬那裡汲取靈感。
荷馬史詩還塑造了西方人對英雄、命運、神祇、家庭等基本概念的理解。它們不僅是文學作品,更是文化的根基,是西方人認識自身和世界的基本框架。正如英國詩人雪萊(Shelley)所說:「我們都是希臘人。」而要理解希臘,首先必須理解荷馬。
特勒馬科斯(Telemachus)的覺醒——從無力少年到成熟男子
伊薩卡(Ithaca)的危機與少年的困境
《奧德賽》開篇即將讀者帶入一個充滿危機的世界。奧德修斯離家已近二十年 ——十年征戰特洛伊,又十年漂泊海上 —— 伊薩卡王宮內外早已不復往日秩序。一百零八位來自伊薩卡(Ithaca)及周邊島嶼的貴族青年長期盤踞在奧德修斯的宮殿中,他們名為追求佩涅洛佩(Penelope),實則肆意揮霍王室財產,每日宰殺牛羊,痛飲美酒,將奧德修斯(Odysseus)的家產視為己有。
這些求婚者的行為不僅是對奧德修斯家族的羞辱,更是對古希臘社會待客之道的公然違背。在古希臘文化中,主客關係受到神聖法則的保護,由宙斯(Zeus)親自守護。客人應該受到款待,但也必須知所進退,不可久居不歸,更不可覬覦主人的財產和妻子。然而這些求婚者卻完全顛覆了這一神聖傳統,他們不是過客而是侵佔者,將奧德修斯的宮殿變成了自己的歡宴之所。
年輕的特勒馬科斯正處於人生最尷尬的境地。史詩描繪他坐在求婚者中間,內心悲傷地想像著父親突然歸來、驅散這些入侵者的場景。這個場景揭示了特勒馬科斯面臨的核心困境:他已不再是孩童,卻尚未成為真正的男人。他能夠感受到羞辱,能夠憤怒,卻缺乏採取行動的能力和權威。在古希臘社會,男性身份的確立需要通過具體的行動來證明——在戰場上的勇武、在議事會中的雄辯、在處理家族事務時的果斷。但特勒馬科斯既無父親的指導,也無實踐這些美德的機會。求婚者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他男性身份的否定:他們的在場表明,這個家庭缺少一個有力量的男性保護者。
雅典娜(Athena)的啟蒙與成長的開始
正是在這個危急關頭,智慧女神雅典娜以奧德修斯老朋友門特斯(Mentes)的形象出現在特勒馬科斯面前。這次神性介入標誌著特勒馬科斯成長之旅的正式開始。雅典娜與特勒馬科斯的對話充滿了教育意義。她不是直接解決問題,而是啟發少年自己去思考和行動。
雅典娜首先肯定了特勒馬科斯身上繼承自父親的特質。她說:「朋友啊,我看你無論身形還是相貌,都不像一個懦弱的人。看來你確實是奧德修斯的兒子——你有他那樣的頭顱和美麗的雙眼。」這種肯定對特勒馬科斯至關重要。在一個父親缺席的環境中成長,他一直缺乏男性身份的榜樣和認同。雅典娜的話語讓他意識到,他身上流淌著英雄的血液,有能力也有責任繼承父親的遺產。
接著,雅典娜給出了具體的行動建議:召集伊薩卡的議事會,公開譴責求婚者的行為,然後出海前往皮洛斯(Pylos)和斯巴達(Sparta),尋訪父親的消息。這個建議包含了兩個重要的成長儀式:公開演說和遠航。在古希臘社會,能夠在公共場合發表演說是成年男性的重要標誌,而遠航冒險則是英雄必經的考驗。「門托爾」(Mentor)這個名字後來在西方文化中成為「導師」的代名詞,正是源於雅典娜在特勒馬科斯成長過程中發揮的關鍵作用。
議事會的挫折與遠航的收穫
在雅典娜的鼓勵下,特勒馬科斯召集了奧德修斯離開後的第一次議事會。清晨,他手持父親的權杖,在傳令官的陪同下來到集會場所。他坐上「父親的座位」,象徵著他開始承擔父親的角色和責任。雅典娜賦予他超凡的魅力,使所有人都驚奇地注視著他。
然而,特勒馬科斯的第一次公開演說並不算成功。他控訴求婚者的傲慢和暴行,呼籲伊薩卡人民主持正義,但求婚者的首領安提諾俄斯(Antinous)巧妙地將責任推到佩涅洛佩身上,指責她用織布的詭計欺騙他們。議事會最終沒有取得實質成果,求婚者們拒絕離開,伊薩卡的人民也不願意或不敢干預。
然而,這次經歷對特勒馬科斯來說是寶貴的。他學會了在公共場合發言,經歷了求婚者的反駁和嘲諷,並且在社群面前確立了自己作為奧德修斯兒子和繼承人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他沒有因為議事會的失敗而氣餒,而是決定執行雅典娜建議的第二部分:出海尋訪父親的消息。
特勒馬科斯的航行與傳統英雄冒險有所不同。他不是去屠龍或奪取寶物,而是去尋找關於父親的消息,去學習如何成為像父親那樣的人。在皮洛斯(Pylos),智慧的老國王涅斯托耳(Nestor)讚美他的口才,說他說話的方式非常像奧德修斯;在斯巴達,墨涅拉俄斯(Menelaus)和海倫(Helen)講述了奧德修斯在特洛伊戰爭中的英勇事蹟:他如何偽裝成乞丐潛入特洛伊城探查情報,如何在木馬中控制住想要回應妻子聲音的希臘士兵。這些故事展示了父親的機智、忍耐力和自制力——這些都是特勒馬科斯現在需要的品質。
父子相認與並肩作戰
當特勒馬科斯遵照雅典娜的指示回到伊薩卡,來到忠誠的豬倌歐邁俄斯(Eumaeus)的小屋時,他不知道偽裝成乞丐的父親就在那裡。雅典娜安排了父子相認的時刻:她讓奧德修斯恢復真實的樣貌,從衣衫襤褸的老乞丐變成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壯年男子。
特勒馬科斯最初不敢相信,他以為這是神祇的顯現。但奧德修斯對他說:「我不是神祇。我為什麼讓你把我當作不朽的神?不,我是你的父親,為了他你受了這麼多苦,忍受了這麼多暴行。」這個時刻是整部《奧德賽》最動人的場景之一。父子二十年來第一次相見,而兒子已經從嬰兒成長為青年。他們抱頭痛哭,史詩用飛鳥失去幼雛的悲鳴來比喻他們的哭泣——他們不僅為重逢而哭泣,也為失去的二十年而哭泣,那些無法挽回的歲月,父親錯過了兒子的整個成長過程,兒子在沒有父親指導的情況下艱難長大。
在接下來的復仇行動中,特勒馬科斯展現出他的成長和勇氣。他與父親制定計劃,在合適的時機武裝自己,與父親並肩戰鬥。當奧德修斯的箭矢用盡時,是特勒馬科斯跑到儲藏室取來盔甲和武器。雖然他在匆忙中犯了一個錯誤——忘記鎖上儲藏室的門,讓叛徒得以為求婚者取來武器——但他能夠坦然承認錯誤並立即採取行動補救。這種誠實和負責的態度,正是成熟的重要標誌。
當故事結束時,特勒馬科斯已經不再是那個無力的少年,而是能夠獨立判斷、果斷行動的男人,準備好繼承父親的遺產。他的成長之旅告訴我們:成熟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而是通過一系列的考驗、失敗和學習逐漸實現的。
奧德修斯的苦難歸程——人性與命運的搏鬥
卡呂普索(Calypso)島上的抉擇
奧德修斯的返鄉之路充滿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苦難與掙扎。在史詩開始時,我們看到英雄被困在俄癸吉亞(Ogygia)島上,這是女仙卡呂普索的領地。奧德修斯已經在這裡度過了七年時光,而在這之前,他還經歷了無數的冒險和災難。
卡呂普索深深愛著奧德修斯,她為他提供了一切:美食、美酒、舒適的住所,以及不朽的愛情。她甚至承諾,如果奧德修斯願意留下,她將使他長生不老,讓他永遠保持青春和活力。這是凡人難以拒絕的誘惑——誰不想逃脫死亡的命運呢?在古希臘神話中,凡人獲得不朽的機會極其罕見,這是連最偉大的英雄也夢寐以求的恩賜。
然而,每當卡呂普索在洞穴中準備晚餐時,奧德修斯卻坐在海邊的岩石上,眺望著大海的方向,流下思鄉的眼淚。史詩這樣描繪他:「白天他坐在岩石和沙灘上,用眼淚、嘆息和悲傷折磨自己的心,他望著茫茫大海流淚。」這個形象非常動人。奧德修斯不是被物理上的鎖鏈囚禁,而是被情感和處境所束縛。卡呂普索愛他,但這種愛對他來說是一種監禁,因為它阻止他回到真正的家。島上的一切都很美好,但這不是他的生活,他渴望的是伊薩卡的貧瘠土地、他的妻子和兒子、以及他作為國王的責任。
當宙斯最終命令卡呂普索放奧德修斯離開時,女仙再次向他提出誘惑。她說自己比佩涅洛佩更美、更年輕、而且不朽,凡人怎麼能與不朽的女神比美貌呢?奧德修斯的回答非常巧妙。他首先謙卑地承認卡呂普索確實比佩涅洛佩更美,但接著說:「但即便如此,我仍然日日夜夜渴望回家,渴望看到返鄉的那一天。即使神祇在暗紫色的海上再次打擊我,我也會忍受,因為我的心已經習慣了苦難。」
這段話揭示了奧德修斯選擇的核心:他選擇的不是更美的女人或更舒適的生活,而是他自己的生活——儘管充滿苦難,卻是真實的、有意義的。在卡呂普索的島上,時間是靜止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但也是虛幻的。奧德修斯渴望的是有限卻真實的人類生活:成長、衰老、死亡,但也包括愛、責任和歸屬。這個選擇體現了《奧德賽》的核心主題之一:人性的價值勝過神性的誘惑。
海上的磨難與考驗
奧德修斯的海上歸程是一連串災難和考驗的集合。海神波塞冬(Poseidon)對他懷有深仇大恨,因為奧德修斯刺瞎了他的兒子獨眼巨人波呂斐摩斯(Polyphemus)。每當奧德修斯接近家鄉時,波塞冬就會掀起可怕的風暴,將他吹向更遠的地方。
與獨眼巨人的遭遇充分展現了奧德修斯的智慧,但也暴露了他性格中的缺陷。當他和部下被困在巨人的洞穴中,眼看著同伴一個個被吃掉時,奧德修斯設計了一個巧妙的計謀:他用美酒灌醉巨人,告訴巨人自己的名字叫「無人」(Nobody),然後用燒紅的木樁刺瞎了他的眼睛。當其他巨人來詢問時,波呂斐摩斯說「無人傷害我」,其他巨人便以為他發瘋了。第二天,奧德修斯和部下綁在羊肚子下逃出了洞穴。
然而,當船隻已經安全離開時,奧德修斯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出於驕傲和憤怒,他向正在岸上的波呂斐摩斯大聲喊叫,揭示了自己的真實身份:「獨眼巨人,如果有人問是誰弄瞎了你的眼睛,你就告訴他是伊薩卡的奧德修斯!」這種傲慢導致了波塞冬的詛咒,成為奧德修斯後來所有苦難的根源。這個故事揭示了英雄主義的危險面——為了榮譽而危及實際安全,為了個人驕傲而犧牲同伴的福祉。
在女巫瑟茜(Circe)的島上,奧德修斯面臨另一種考驗。瑟茜將他的同伴變成了豬,但奧德修斯在赫爾墨斯(Hermes)神的幫助下抵抗了她的魔法,迫使她恢復同伴的人形。然而,他們在島上一待就是整整一年,沉迷於女巫提供的舒適生活,幾乎忘記了返鄉的使命。最後是同伴們提醒他:「朋友啊,現在是時候想想我們的祖國了。」這表明即使是最堅強的英雄,也需要同伴的支持和提醒,才能抵禦各種形式的誘惑,堅持自己的目標。
塞壬(Sirens)女妖的誘惑更加微妙。她們用甜美的歌聲吸引水手,承諾給予「一切知識」。對於渴望智慧的奧德修斯來說,這是幾乎無法抵抗的誘惑。他命令水手用蜂蠟塞住耳朵,卻讓自己被綁在桅杆上聆聽歌聲。當塞壬唱起歌時,他瘋狂地掙扎,示意同伴鬆開繩索,但同伴們遵守命令,將繩索綁得更緊。這個故事探討了知識與危險的關係,以及人類對於「知道一切」的慾望。奧德修斯的解決方案是智慧的:他承認人類的慾望和弱點,但通過預先設置限制來克服它們。
最大的悲劇與最後的考驗
奧德修斯旅程中最殘酷的時刻,是他不得不在斯庫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之間做出選擇。海峽一側是六頭怪獸斯庫拉,另一側是吞噬一切的漩渦卡律布狄斯(Charybdis)。瑟茜警告他,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會吞沒整艘船,而斯庫拉只會抓走六個水手。奧德修斯選擇了斯庫拉一側,這意味著他必須眼睜睜看著六個忠誠的同伴被怪獸吃掉。
史詩描述了這個場景的悲慘:「斯庫拉從船上抓走了六個手腳最強壯的同伴。當我轉向快船和同伴時,我看到他們的手和腳已經被舉到空中。他們大聲呼喊我的名字,那是最後一次……這是我在海上受苦受難時見過的最可憐的景象。」這不是光榮的戰鬥,而是無助的犧牲。奧德修斯被迫做出一個道德困境中的選擇,而這種責任將永遠困擾他。
最後的災難發生在太陽神的島上。儘管奧德修斯再三警告,他的同伴們在飢餓的驅使下宰殺了神聖的牛群。宙斯降下雷霆,擊沉了船隻,奧德修斯失去了所有同伴,獨自抱著桅杆漂流到卡呂普索的島上。這是他冒險的最低點——他失去了一切,只剩下求生的意志和回家的渴望。
當奧德修斯終於回到伊薩卡時,他沒有衝動地揭示身份,而是耐心地偽裝成乞丐,忍受求婚者的羞辱和虐待。當牧羊人墨蘭提俄斯(Melanthius)踢他時、當安提諾俄斯(Antinous)用腳凳砸他時、當他坐在妻子面前卻不能相認時,他都強忍住憤怒。他的眼睛「像鐵或角一樣」固定,隱藏住眼淚。這種自制力是他經過二十年苦難後獲得的最重要能力——不是不能行動,而是選擇不立即行動,等待最佳時機。
歸家的悲喜與家的重新發現
然而,《奧德賽》最深刻的洞見或許在於:回家並不是故事的終點,而是另一種考驗的開始。奧德修斯踏上伊薩卡土地的那一刻,並沒有立即感到喜悅和解脫,反而經歷了一種奇異的疏離感。雅典娜用迷霧遮蔽了島嶼的面貌,使奧德修斯醒來時竟然認不出自己的故鄉。他悲傷地以為自己又被欺騙,被拋棄在另一個陌生的土地上。這個細節意味深長:二十年的漂泊不僅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歸來者本身。家還是那個家,但凝視它的眼睛已經不同了。
這種歸來的陌生感是所有長期離家者的共同經驗。奧德修斯離開時,特勒馬科斯還是襁褓中的嬰兒,如今已是能夠並肩作戰的青年;佩涅洛佩的容顏刻上了歲月的痕跡;老狗阿爾戈斯(Argos)躺在糞堆上奄奄一息,只剩下認出主人的最後一絲力氣。最令人心碎的是那條老狗的場景:阿爾戈斯在奧德修斯離開前還是一隻矯健的獵犬,如今已被遺棄、衰老、瀕死。當牠認出偽裝成乞丐的主人時,只能搖搖尾巴、垂下耳朵,隨即便死去了。奧德修斯不敢流露感情,只能悄悄擦去眼淚。這個場景凝聚了歸來的全部悲愴:時間無法倒流,失去的歲月無法彌補,即使最終回到家,許多東西已經永遠改變了。
回家的喜悅與悲傷就這樣奇異地交織在一起。奧德修斯渴望了二十年的重逢,真正來臨時卻必須隱忍、等待、偽裝。他坐在自己的宮殿裡卻是一個乞丐,看著求婚者揮霍他的財產,聽著僕人的嘲諷,甚至面對妻子也不能相認。這種「在家中流亡」的處境,比海上的漂泊更加煎熬。在海上,敵人是明確的——風暴、怪獸、女妖;在家中,一切都曖昧不清——誰是忠誠的,誰是背叛的,甚至妻子是否還在等待,都需要一一試探和確認。
然而,正是這種艱難的歸來過程,使奧德修斯重新發現了家的真正意義。家不僅僅是一個地點,不僅僅是宮殿、土地和財產。家是那些在漫長歲月中仍然記得你、等待你的人。是老狗臨終前的搖尾,是老奶媽歐律克勒亞(Eurycleia)摸到傷疤時的驚呼,是豬倌歐邁俄斯不知情時對舊主人的懷念,是佩涅洛佩在絕望中仍然保持的一絲希望。家是這些關係的總和,是記憶與忠誠編織成的網絡。
更深刻的是,奧德修斯必須通過行動來「重建」他的家。僅僅回來是不夠的,他必須清除侵佔者,恢復秩序,重新確立自己作為丈夫、父親和國王的身份。這個過程是痛苦的,甚至是血腥的,但也是必要的。家不是被動地存在於那裡等待你回來,而是需要你去守護、去維繫、去重新創造。奧德修斯在復仇之後,還必須面對求婚者家屬的報復,必須與憤怒的伊薩卡人和解。史詩的結尾,雅典娜介入調停,宣布和平,但這和平是脆弱的,需要所有人的努力來維持。
這樣看來,《奧德賽》講述的不僅是「回家」的故事,更是「重新認識家」的故事。奧德修斯經歷了漫長的漂泊,見識了世界的廣闊和人性的複雜,最終回到那個貧瘠的小島。但這個「回來」的他,已經不是當年離開的那個年輕國王。他帶著傷痕、智慧和對生命有限性的深刻理解,重新審視這個他曾經視為理所當然的地方。伊薩卡的價值不在於它的富饒——卡呂普索的島嶼遠比它美麗——而在於它是他的,是他的根所在,是他的故事開始和應該結束的地方。
對於現代讀者來說,這個主題具有特殊的共鳴。在全球化的時代,許多人離開故土,在異鄉建立新的生活。當他們回到家鄉時,往往會經歷奧德修斯式的疏離感:熟悉的街道變得陌生,童年的朋友已經不認識,甚至自己的家人也似乎成了另一個世界的人。
這種奧德修斯式的疏離感是痛苦的,但《奧德賽》告訴我們,它也可以是一種重新發現的契機。正是因為離開過,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家的意義;正是因為失去過,我們才能真正珍惜擁有的一切。歸來不是終點,而是以新的眼光重新開始的起點。
待續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