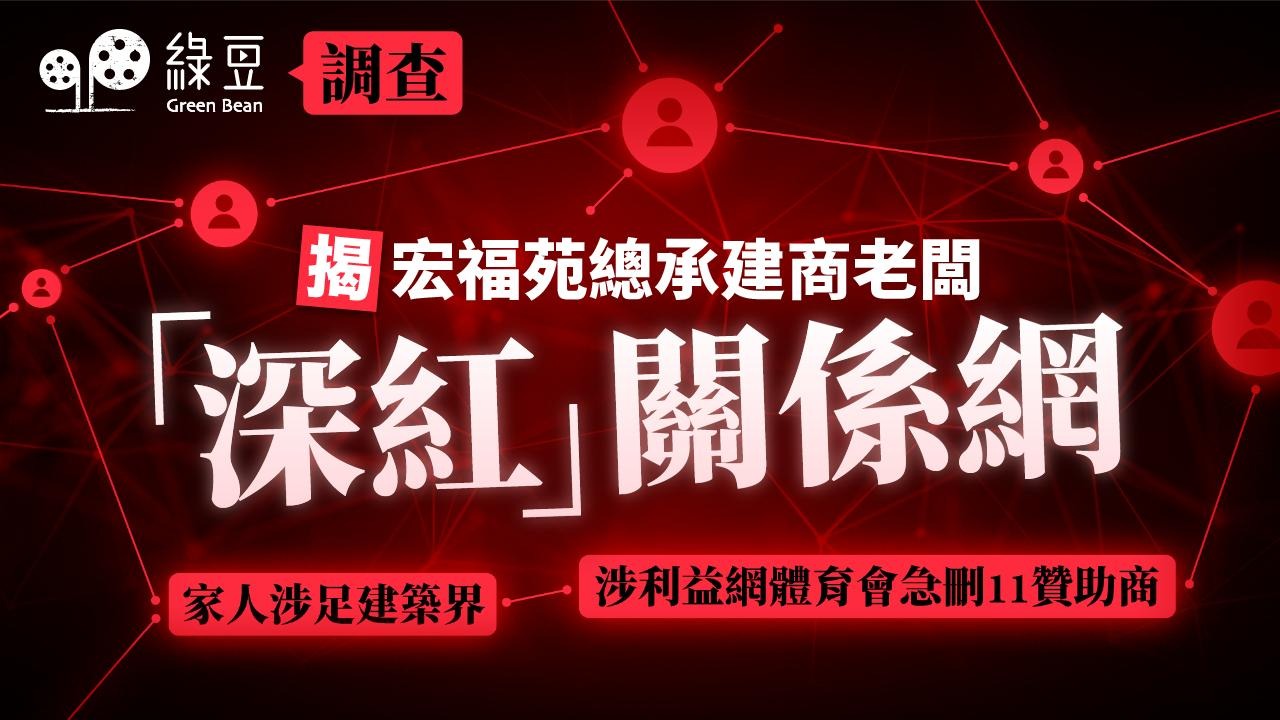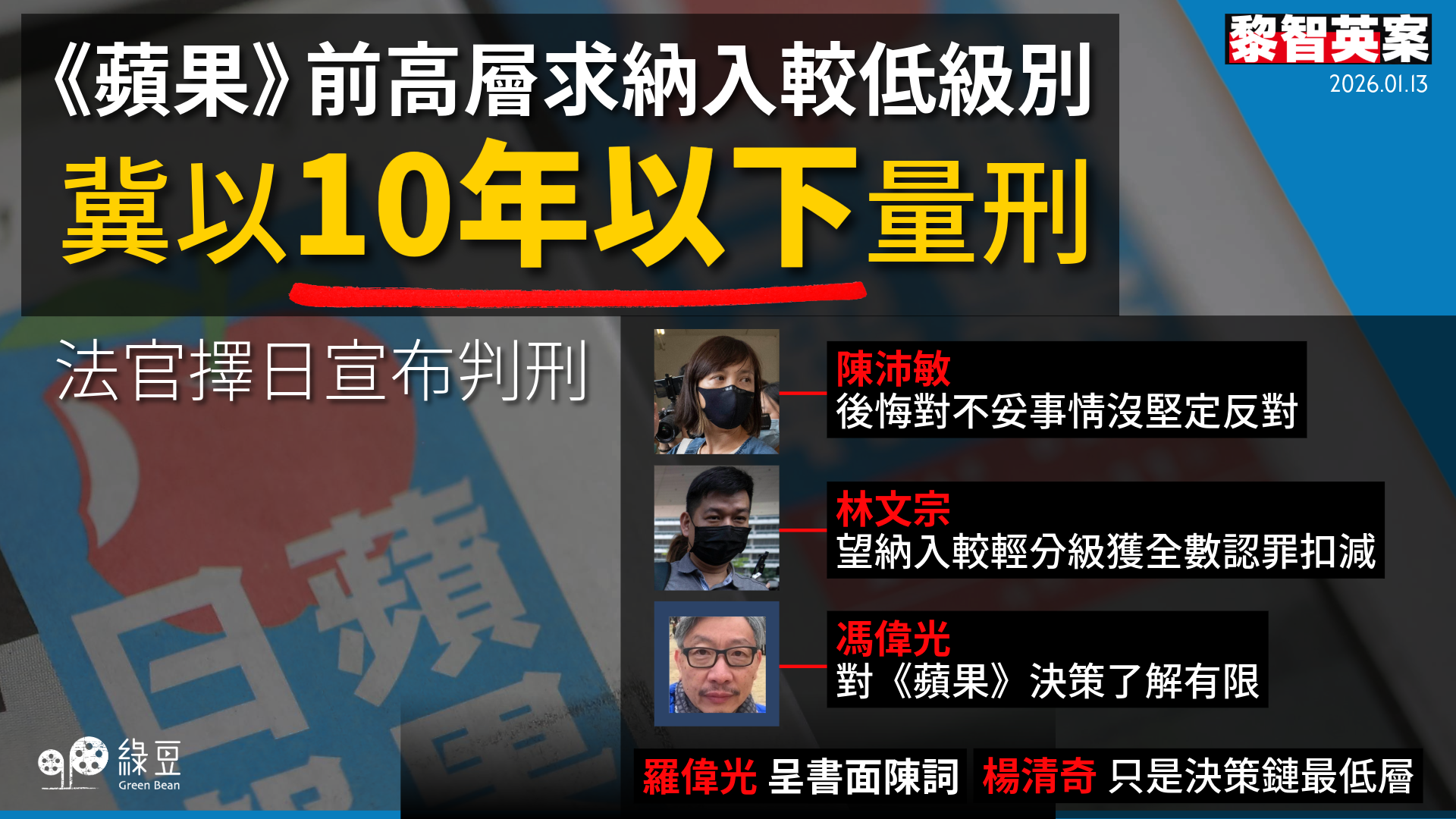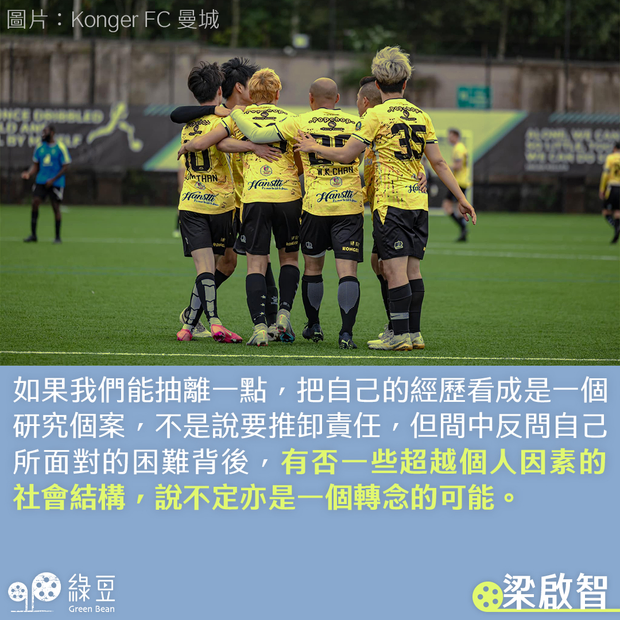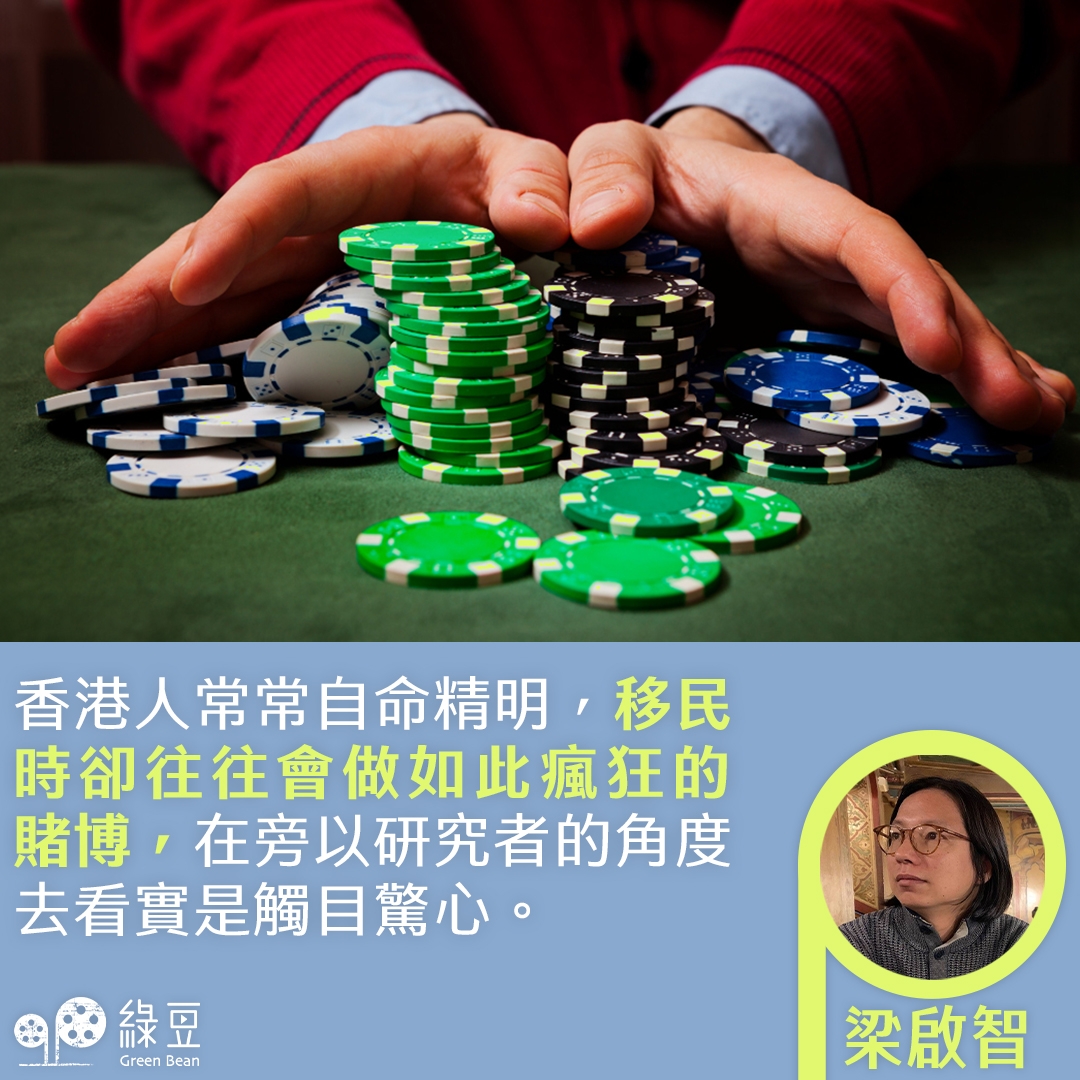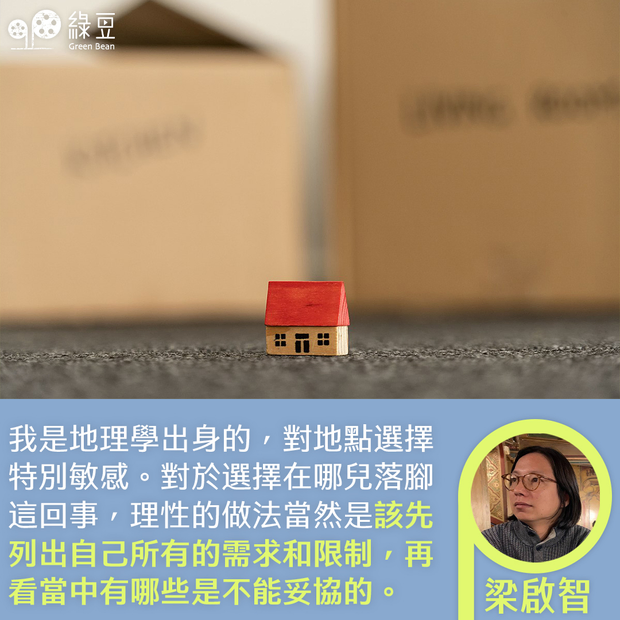移民第二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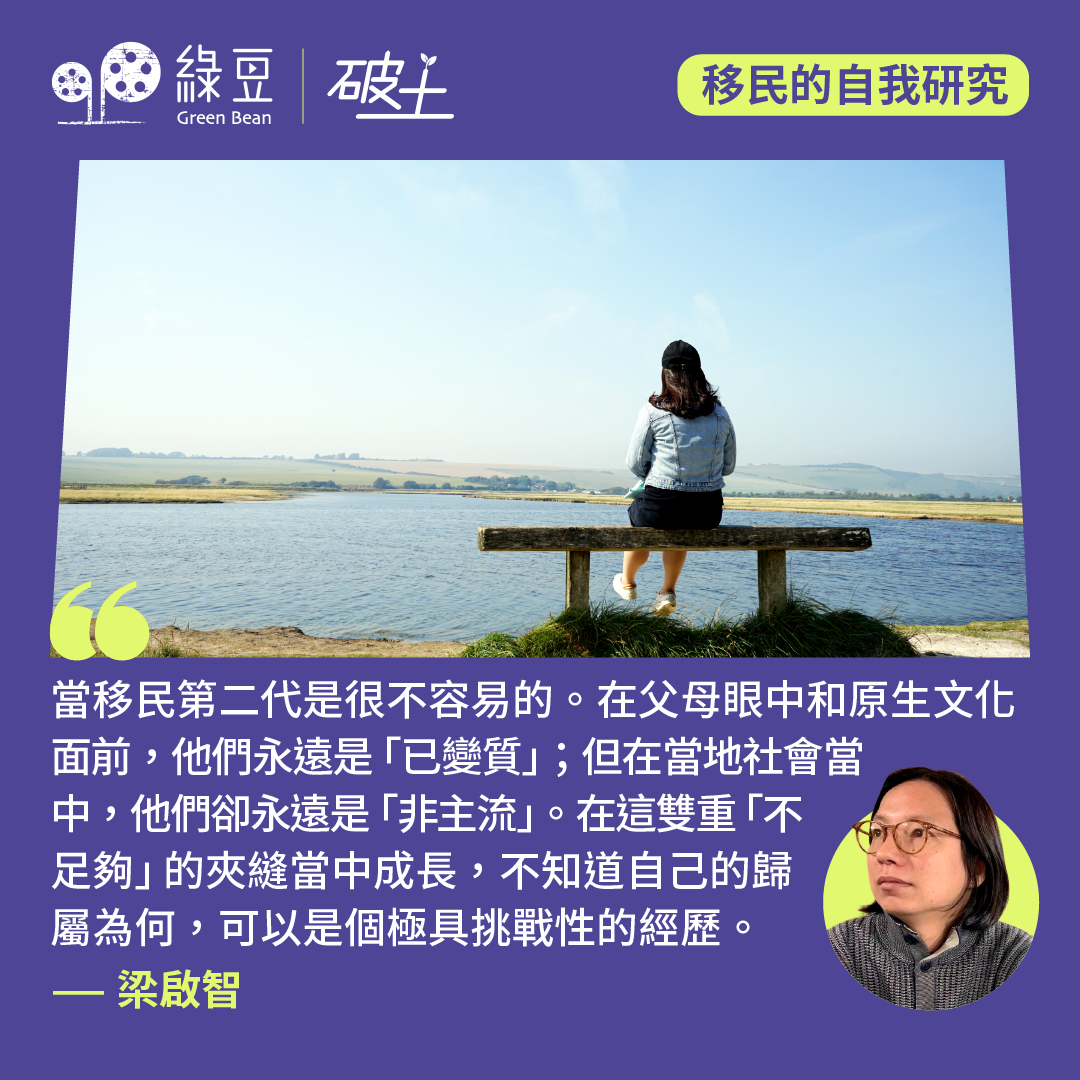
曾經和一些早已在外國落地生根的港人移民組織者討論新一代港人移民的情況,常常會聽到一種說法:這一波的港人移民還是太過「新」,對當地的理解往往仍存有各種幻想,又或仍未能處理理想和現實的落差。但他們往往還會補充一句:雖然港人移民或者還未完全認識或適應身為移民的文化身份,但他們的下一代將會不一樣;亦因如此,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之間,長遠必有隔閡。
舉個例,不少港人移民會自以為「榮譽白人」,假設自己理所當然會被當地社會接納,各種針對移民和少數族裔的排外情緒與他們無關;最新就聽說還有移英港人推動「反移民聯署」,好像忘記了自己也還未入籍似的。這些港人移民之所以會擔起各種在「舊移民」眼中甚為奇怪的價值觀,原因倒也不難理解:他們當中不少人都未有甚至不需要和當地社會有深入交往,只體會到移民後的好處,當地社會對移民的不滿或歧視卻未感受得到。如果他們資本足夠豐厚,甚至可以一直活在自己的「幸福泡泡」當中。
對家長的提醒
但他們的下一代就不一樣了。尚未成年便隨父母離港的移民,以至在當地出生的港人移民後代,面對的社會環境和他們的父母有巨大差別。他們的成長過程和當地社會的融合遠遠來得徹底和直接,無論是學校或朋輩交往,他們身為少數的身份會無時無刻被提醒。而相對於他們的父母,原來自香港的生活記憶又遠遠不如。他們最重要的身份不再是港人或港人移民,而是在當地社會的少數族裔;這差別看似微少,卻十分重要。
舉個例,Crazy Rich Asians(港譯《我的超豪男友》)在香港和在美國的上映,雖然是同一齣的電影,但對兩邊的觀眾來說就是活脫脫的兩回事。考慮到早年荷里活電影的各種種族歧視,包括由白人飾演亞裔角色或只安排亞裔演員擔當配角,完全由亞裔演員領銜主演的 Crazy Rich Asians 在美國亞裔圈子牽起了風潮。但對於活在亞洲的香港觀眾來說,沒有相對應的文化歷史背景,就不會感到同樣的震撼,甚至反過來覺得電影就像是美國唐餐館的菜色那樣「有點怪怪的」。
因此,移民海外的家庭必須時刻提醒自己,不要理所當然地把家長自身的各種文化社會期望放在子女身上。畢竟他們在當地長大,會有他們對自我身份認同的迷惑和探索。
夾縫當中成長
關於移民第二代,學術界的研究如恆河沙數。最基本的,是語言能力的差別。第一代移民集慣的還是原來的語言,第二代則完全在當地語境中成長,並且往往會極力擺脫原有口音所帶來的歧視問題。父母一輩視乎有多介意原有文化的散失,或會介懷子女不再說母語(雖然我懷疑某些港人父母對粵語文化本身有多大的重視)。一個常常被忽視的問題,是當父母與子女出現「語言不通」,則連較深入的情感交流也做不到,子女對父母更感到陌生和欠缺支持。
而在移民家庭當中,各種期望落差又特別容易爆發。之前提過,移民家庭往往對子女期望和要求特別的高,因為父母覺得自己因為移民所作出的「犧牲」都是「為子女著想」,如果子女沒有好好珍惜在當地的機會就等於背叛了父母的期望。更麻煩的情況,是萬一父母在移民前沒有和子女溝通,甚至整個籌備移民的過程是在隱瞞子女的情況下發生,子女到達後則更容易變得更為抗拒。如果這時候子女提出寧願回流返港,則恐怕會誘發家變收場。
當移民第二代是很不容易的。在父母眼中和原生文化面前,他們永遠是「已變質」;但在當地社會當中,他們卻永遠是「非主流」。在這雙重「不足夠」的夾縫當中成長,不知道自己的歸屬為何,可以是個極具挑戰性的經歷。父母應多與子女溝通當初離港的原因,亦不要把自己對移民的喜或憂都投射到子女身上。最怕因為自身在移民的路上遇到障礙,便在子女的經歷當中尋找討厭當地的理由,合理化自身的憂慮,則恐怕更會把子女越推越遠。
( 圖 : Shutterstock )
▌[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
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