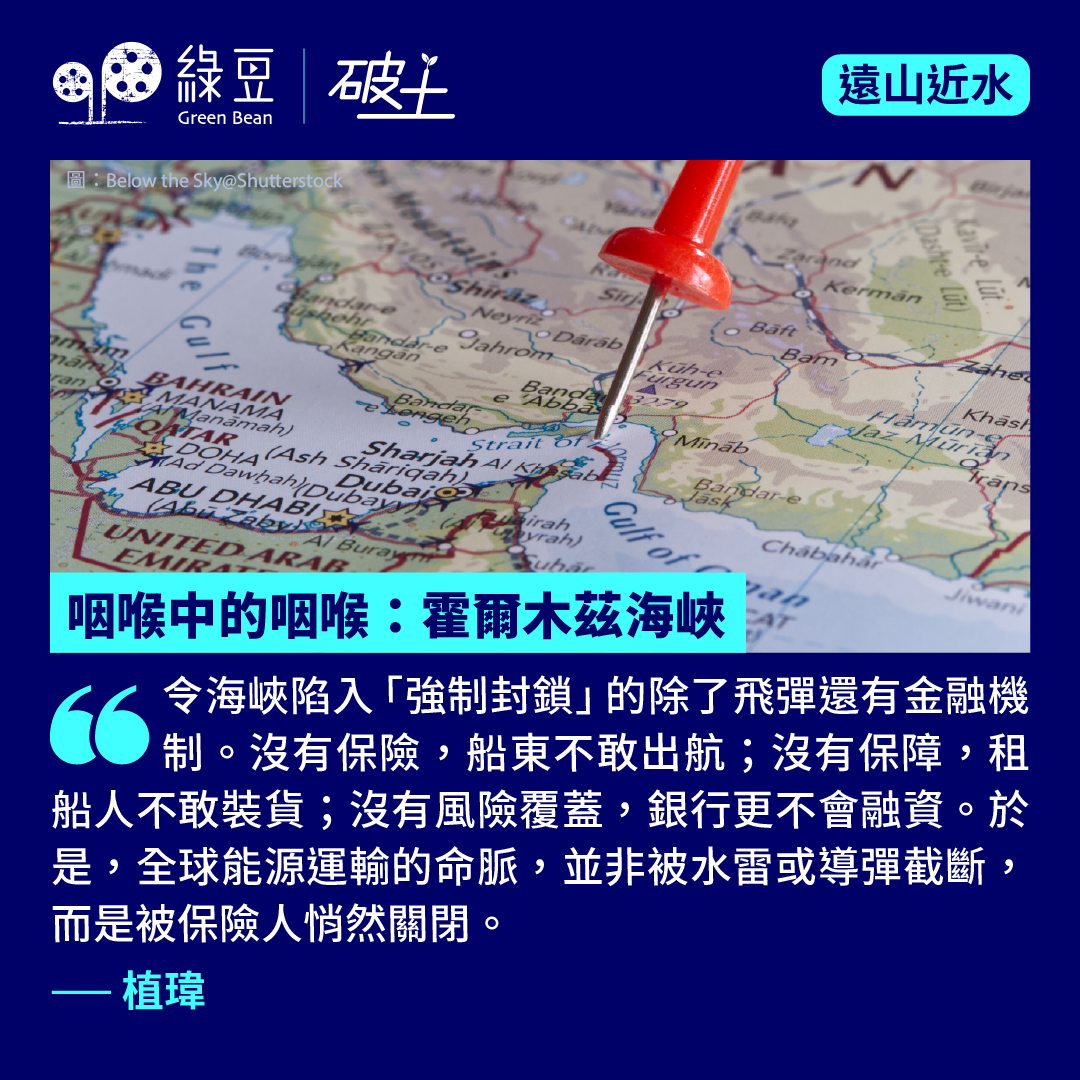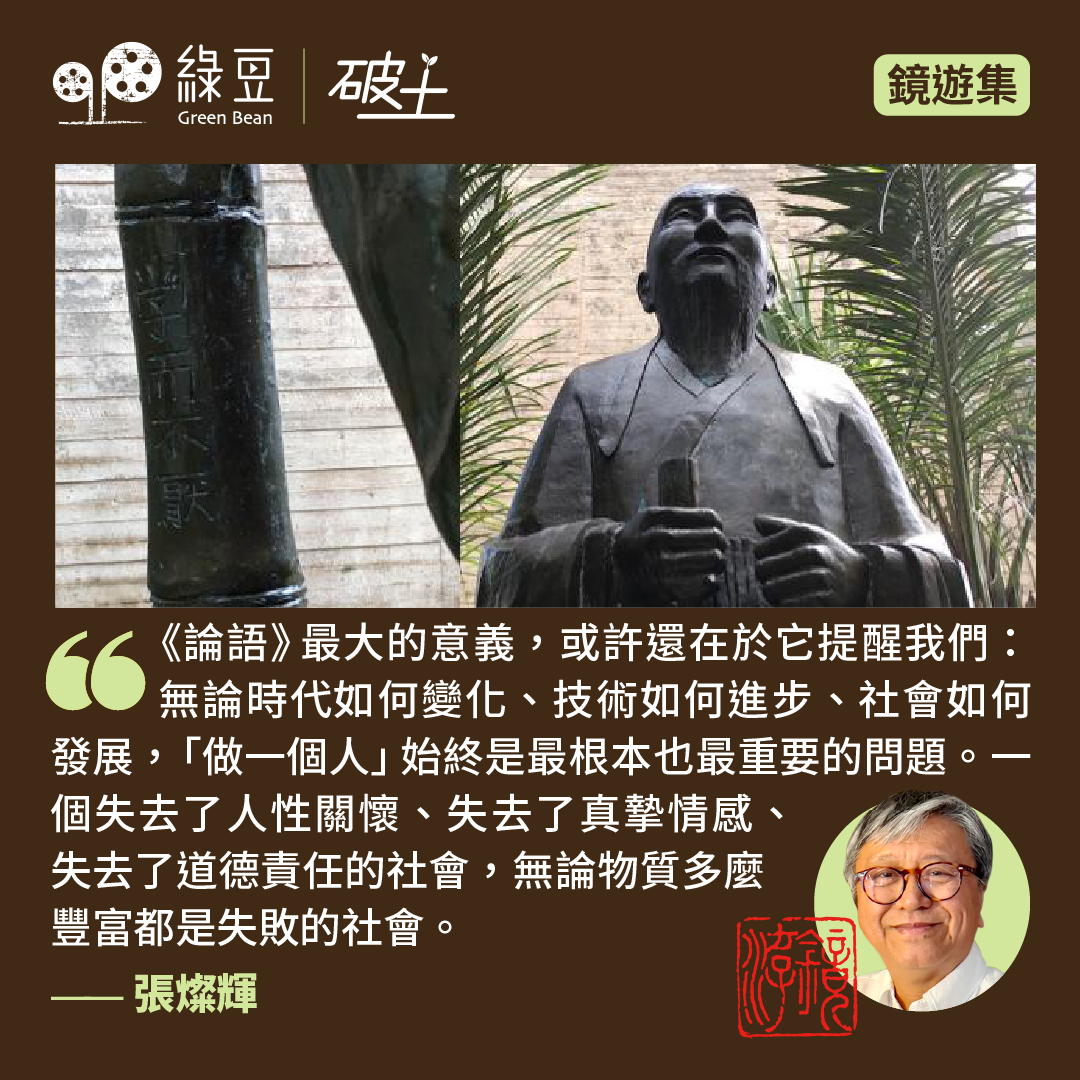柏拉圖《會飲篇》:愛欲的本質與蘇格拉底的智慧 (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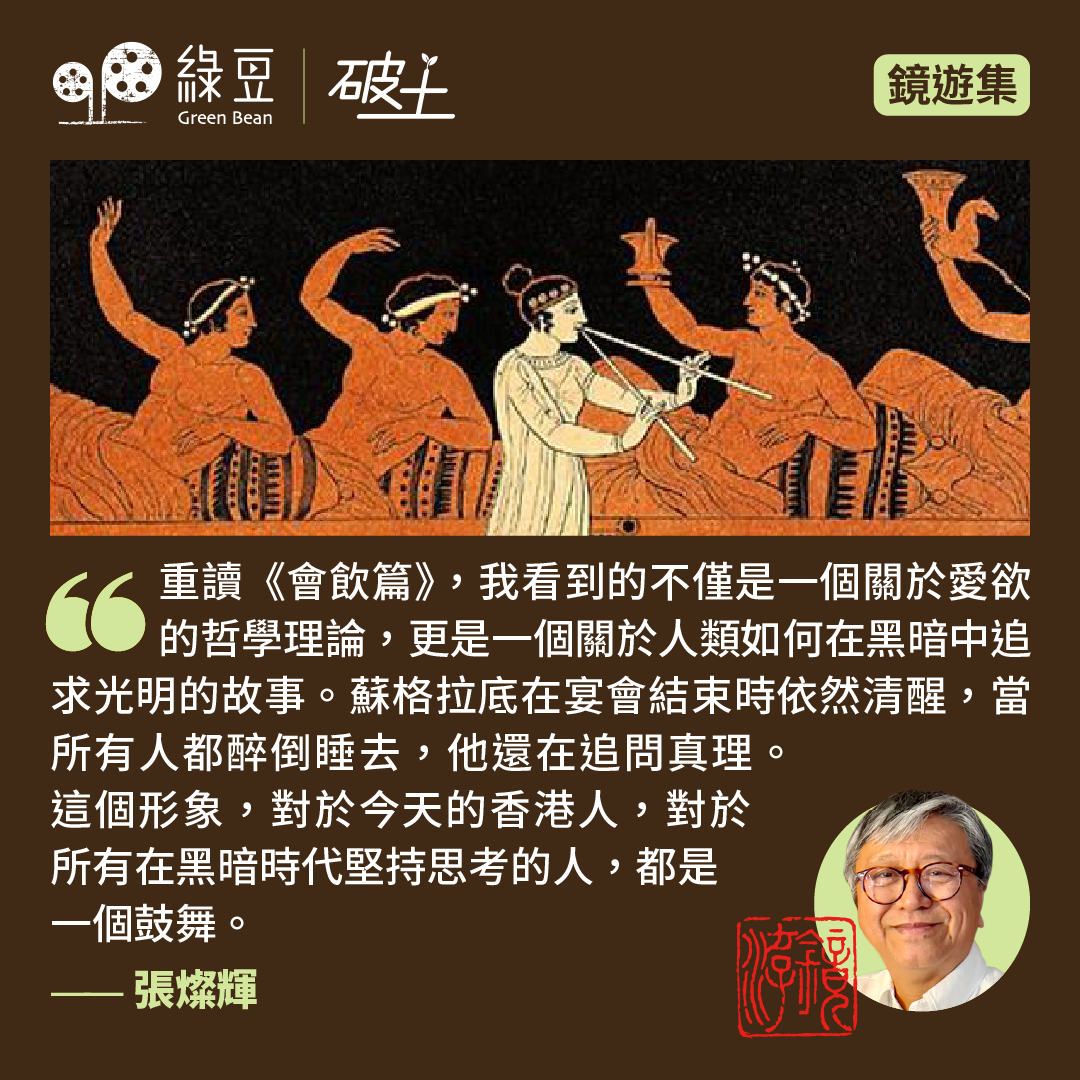
《重讀經典:與人文和自然對話》
狄俄提瑪的教導:愛欲的哲學本質
狄俄提瑪(Diotima)的教導構成了《會飲篇》的哲學核心。她系統地回答了關於愛欲的三個根本問題:愛欲是什麼?愛欲的目的是什麼?如何正確地愛?這些教導展現了柏拉圖(Plato)成熟期的哲學思想,特別是他的形式理論的萌芽。
愛的精靈本質
當蘇格拉底(Socrates)承認愛既不美也不善時,他像阿伽通(Agathon)一樣立即推論說愛欲必定是醜陋和邪惡的。狄俄提瑪糾正了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她指出,在美與醜、善與惡之間存在著中間狀態。愛正是這樣一種中介性的存在。
狄俄提瑪講述了愛神厄洛斯(Eros)誕生的神話。在阿芙洛狄忒(Aphrodite)誕生的慶典上,機巧之神波洛斯(Poros,即「富足」)和貧困女神佩尼亞(Penia)躺在一起,生下了厄洛斯。因此,愛繼承了雙親的特性:他始終貧困、粗糙、赤腳,居無定所;但同時他又勇敢、機智,不斷追求智慧和美好事物。
這個神話揭示了愛的辯證本質。愛永遠處於擁有與匱乏之間。他不是神(因為神是完滿的),也不是凡人(因為他永恆存在),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精靈(daimon)。同樣,他處於智慧與無知之間:這正是哲學家的處境。
狄俄提瑪進一步解釋說,沒有神會追求智慧,因為他們已經是智慧的;完全無知的人也不會追求智慧,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缺乏智慧。只有那些意識到自己無知的人,才會成為「愛智者」,即哲學家(philosopher)。厄洛斯正是這種哲學追求的化身。
這個分析將愛與哲學緊密聯繫在一起。哲學不是已經擁有的智慧,而是對智慧的愛戀。哲學家像厄洛斯一樣,永遠處於追求的過程中,永不滿足,永不停歇。愛欲的精靈本質就是哲學活動本身的寫照。
愛的目標:善的永恆佔有
狄俄提瑪接著探討愛的目標。愛欲求美好的事物,但這還不夠精確。更準確地說,愛欲求佔有美好的事物。但為什麼要佔有美好的事物呢?因為佔有美好的事物能使人幸福。
然而狄俄提瑪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愛要永恆地佔有美好的事物?因為愛本質上不僅欲求善,更欲求善的永恆佔有。這裡引入了時間維度:愛不滿足於暫時的擁有,而追求永恆的佔有。
這個洞見具有深刻的存在論意義。人類是有限的、會死亡的存在,但愛求永恆。這種矛盾如何解決?通過生育和創造。狄俄提瑪說,所有人都在身體和靈魂上處於孕育狀態,當達到適當的年齡,我們的本性渴望生育。
生育是凡人通向永恆的方式。通過繁衍後代,個體的生命得以在種族中延續。但這種生物學意義上的永生仍然是間接的、有限的。更高形式的生育是精神上的創造:詩歌、法律、科學、藝術作品。這些精神產物比肉體後代更加持久,帶來更大的榮耀。
狄俄提瑪舉例說,荷馬(Homer)和赫西俄德(Hesiod)通過詩歌獲得了永生,梭倫(Solon)和萊庫古(Lycurgus)通過立法流芳百世。這些精神創造是靈魂的後代,比肉體的子女更加值得珍視。任何人都寧願擁有這樣的精神後代,也不願只是生育凡俗的孩子。
這個理論解決了愛欲與死亡、有限與永恆的張力。愛欲不是對已擁有之物的守護,而是通過創造性活動超越死亡的努力。真正的愛欲指向永恆,其實現方式是創造不朽的善。
愛的階梯:從感性到理性的上升
狄俄提瑪教導的高潮是著名的「愛的階梯」理論。她描述了一條從具體到抽象、從感性到理性、從眾多到唯一的上升之路。這不僅是愛情的道路,更是整個哲學教育和精神修養的歷程。
第一階段,年輕人應當首先愛上一個美麗的身體。在與這個美麗個體的接觸中,他學會欣賞身體的美,並在這種愛中創造美好的言論和思想。這是愛的啟蒙階段,感性經驗是不可跳過的起點。
第二階段,他應當認識到美不僅存在於一個身體中,所有美麗的身體在某種意義上是同一的。他應當成為所有身體之美的愛者,從而超越對單一對象的執著。這是從個別上升到普遍的第一步。
第三階段,他應當認識到靈魂的美比身體的美更加珍貴。即使某人身體不那麼美,如果他的靈魂美好,愛者也應當愛他,並努力創造能使年輕人變得更好的言論。這是從外在美轉向內在美的關鍵轉折。
第四階段,他應當觀照活動和法律中的美,認識到所有這些美是相通的。從而他會看輕身體的美,轉向更廣闊美的領域。法律、制度、社會規範中體現的美,代表了群體智慧的結晶。
第五階段,從行為規範他應當轉向各門知識,觀照知識的美。這時他將面對廣闊美的海洋,創造出許多美好而壯麗的言論和思想,在哲學中顯示不竭的愛。知識的美是普遍的、客觀的美。
最後,經過這長期而艱苦的訓練,他將突然瞥見一種驚人的、本性上美的東西。這就是美本身,永恆的、不生不滅的、不增不減的美。這種美不會在某個方面美而在另一個方面醜,不會時而美時而醜,不會相對於某些事物美而相對於其他事物醜。這種美不以面容、手足或身體的任何部分的形式出現,也不以言論、知識或存在於他物中的形式出現,它自身獨立永存。
所有其他美的事物都分有這種美,但當那些事物生滅變化時,美本身絲毫不增不減,保持永恆不變。這就是柏拉圖的理形論的核心:存在著超越感性世界的永恆形式,它們是一切現象事物之所以為其所是的根據。
這個上升的歷程不僅是認識論的,更是存在論的轉化。愛者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淨化自己的欲望,提升自己的存在。從對個別美好身體的愛戀,到對美本身的直觀,這是靈魂的完全轉向,從生成的世界轉向存在的領域。
狄俄提瑪最後說,只有在這個階段,當人直觀美本身時,生活才真正值得過。在那裡,他不是創造美的影像(現象世界中的美好事物),而是創造真正的德行,因為他接觸的是真理。創造真正德行的人,為神所愛,如果有任何人能夠不死,那也正是這樣的人。
這個理論具有深遠的影響。它將愛欲經驗哲學化,將哲學追求愛欲化。愛欲不再僅僅是個人的情感體驗,而是人類存在的根本動力,是推動靈魂上升、達到智慧和德行的力量。同時,哲學不再是冷冰冰的理智活動,而是充滿激情的愛欲的追求。
阿爾基比亞德斯的闖入:理論的實踐檢驗

正當蘇格拉底講完狄俄提瑪的教導,眾人沉浸在哲學沉思中時,外面傳來喧嘩聲。政治家阿爾基比亞德斯(Alcibiades)醉醺醺地闖入宴會,頭上戴著花環,手持笛女和一群狂歡者。這個突然的轉折為對話增添了戲劇性的維度。
阿爾基比亞德斯是雅典最富有、最英俊、最有才華也最具爭議的年輕人。他曾是蘇格拉底的追隨者,對蘇格拉底懷有深厚的愛慕之情。他的到來將抽象的愛的理論拉回到具體的人際關係中,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案例研究。
對蘇格拉底的愛慕
阿爾基比亞德斯不知道之前關於愛的討論,他提議讚頌的對象不是愛神,而是在場的蘇格拉底。他的演說與其說是讚頌,不如說是傾訴,充滿了愛戀、困惑、怨恨和崇敬交織的複雜情感。
阿爾基比亞德斯首先將蘇格拉底比作薩堤洛斯(Satyr)雕像和西勒諾斯(Silenus):外表醜陋但內藏神像的盒子。蘇格拉底確實貌不驚人:塌鼻子、凸眼睛、禿頂大肚,完全不符合希臘人的美的標準。但當你打開這個醜陋的外殼,裡面卻蘊藏著令人驚嘆的美。
蘇格拉底的言論也是如此。表面上看起來可笑——他總是談論皮匠、鐵匠、廚師這些卑微的主題;但如果深入其中,就會發現這些言論充滿神聖的內容,蘊含著對德行的真知。
阿爾基比亞德斯描述了蘇格拉底如何用言論迷惑了他。當聽蘇格拉底說話時,他的心跳加速,眼淚奪眶而出,整個人陷入激動。蘇格拉底的言論像科律班忒斯(Corybantes)的音樂一樣,使他神魂顛倒。蘇格拉底指出他的生活方式錯誤,使他羞愧,恨不得逃走又捨不得離開。
被拒絕的誘惑
阿爾基比亞德斯接著講述了他如何試圖誘惑蘇格拉底的故事。憑藉自己的美貌和地位,阿爾基比亞德斯相信他可以用肉體換取蘇格拉底的智慧。他創造各種機會與蘇格拉底單獨相處,期待蘇格拉底會像其他愛人那樣對待他。但令他困惑的是,什麼都沒有發生。
最後,阿爾基比亞德斯採取了大膽的行動。在一次訓練後,他邀請蘇格拉底共進晚餐,然後留下過夜。他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意圖:願意把自己的美貌和身體交給蘇格拉底,以換取智慧和德行的提升。
蘇格拉底的回答充滿了反諷。他說,如果阿爾基比亞德斯看到了他內在的美,想要用青銅換黃金(荷馬史詩中不公平交換的典故),那實在是聰明的買賣。但阿爾基比亞德斯應當仔細審視,不要自欺欺人。也許蘇格拉底什麼也沒有。而且,理智的視力是在肉眼的敏銳性開始衰退時才開始變得敏銳的。
儘管如此,阿爾基比亞德斯堅持留下來。他們共眠一榻,阿爾基比亞德斯將自己的外衣蓋在蘇格拉底身上,擁抱著這位他認為值得敬重的智者。但整夜過去,什麼都沒有發生。早晨醒來時,就像和父親或兄長睡了一夜一樣。
阿爾基比亞德斯說,在那之後他的處境極為尷尬。他感到被羞辱,卻又無法怨恨蘇格拉底,因為蘇格拉底並沒有做錯什麼。他既不能擁有蘇格拉底,又無法離開他。這種折磨比任何其他的愛戀都更加強烈。
蘇格拉底的非凡品質
阿爾基比亞德斯接著描述了蘇格拉底在軍旅中的表現。在嚴寒的波提狄亞(Potidaea)戰役中,當其他人穿戴厚重時,蘇格拉底仍然穿著平常的薄衣,赤腳在冰上行走。士兵們懷疑他是在故作姿態,但實際上蘇格拉底對身體的不適完全不在意。
更令人驚訝的是,有一天黎明時分,蘇格拉底開始思考某個問題,站在那裡沉思。到了中午仍未得出結論,他就繼續站著思考。士兵們注意到了,驚訝地告訴彼此。到了傍晚,他還在站著。最後,幾個愛奧尼亞人(Ionians)把睡墊搬到外面(那是夏天),既是為了乘涼,也是為了觀察蘇格拉底是否會站一整夜。蘇格拉底確實站到黎明,太陽升起時,他向太陽祈禱後才離開。
在戰鬥中,蘇格拉底也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在德利翁(Delium)的撤退中,當雅典軍隊潰敗時,阿爾基比亞德斯騎馬遇見正在撤退的蘇格拉底。蘇格拉底鎮定自若,從容地環顧四周,清楚地表明,如果有人碰他,他會堅決抵抗。正因為這種態度,他和拉刻斯(Laches)安全地撤離了。敵人不會攻擊這樣從容的人,而是追趕那些驚慌失措的逃兵。
阿爾基比亞德斯還提到蘇格拉底對飲酒和寒冷的抵抗力。沒有人見過蘇格拉底喝醉,雖然這個晚上他的能力將受到考驗。
最後,阿爾基比亞德斯強調蘇格拉底的獨特性。你可以將其他演說家與過去的雄辯家相比,但蘇格拉底無與倫比。你找不到任何古今之人可與他相提並論,除非將他比作薩堤洛斯和西勒諾斯——不是在外表上,而是在他的言論和整個人格上。
欲的多重維度:《會飲篇》的哲學啟示
《會飲篇》通過多重視角和敘事層次,呈現了愛的極其豐富和複雜的本質。從斐德若(Phaedrus)的神話讚頌到狄俄提瑪的形而上學理論,從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存在論神話到阿爾基比亞德斯的個人見證,這部對話錄構成了一個關於愛的完整光譜。
愛欲的層次性
《會飲篇》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揭示了愛欲的層次結構。愛欲不是單一的、同質的現象,而是具有質的差異的多層次現實。從最低層次的肉體欲望,到中間層次的情感依戀和道德關懷,再到最高層次的智慧追求和形式直觀,愛欲經歷了一個上升的序列。
這種層次性不是簡單的價值排序,而是揭示了愛欲的內在辯證結構。較低層次的愛欲並非全然錯誤,而是通向更高形式的必要階梯。狄俄提瑪明確指出,愛欲必須從對一個美麗身體的愛欲開始。如果沒有感性經驗的啟蒙,靈魂就無法開始其上升之旅。
同時,這種層次性也是一種淨化和轉化的過程。愛不是被壓抑或否定,而是被提升和轉化。從對個別對象的執著,到對普遍形式的直觀,這是欲望能量的重新定向。柏拉圖並非禁欲主義者,他承認欲望的積極作用,但主張應當引導欲望朝向更高的對象。
愛欲與知識
《會飲篇》的另一個核心洞見是將愛欲與知識緊密聯繫在一起。愛欲不僅是情感或欲望,更是一種認識活動。愛欲推動靈魂超越表象,穿透現象,直達本質。
蘇格拉底的提問方法本身就體現了這種愛欲的認識論。他不是冷漠的邏輯機器,而是充滿激情的真理追求者。他「愛」那些與他對話的人,正是這種愛欲使他不能容忍對方停留在錯誤之中。蘇格拉底式的反詰不是攻擊,而是一種愛的行為——幫助對方擺脫無知的產婆術。
反過來,真正的知識也只能通過愛欲來獲得。認識美本身不是通過抽象推理,而是通過長期的愛的修煉。狄俄提瑪說,只有當一個人經歷了所有階段,最後才能「突然」瞥見美本身。這種直觀不是概念分析的結果,而是整個存在轉化的頂點。
這種愛欲與知識的統一,哲學與激情的融合,是柏拉圖思想最具原創性的貢獻之一。它超越了理性與情感的二元對立,展示了完整人性的理想。
愛欲與創造
狄俄提瑪關於生育和創造的理論,揭示了愛欲的根本動力學。愛欲不是被動的接受或靜態的佔有,而是積極的創造活動。無論是身體的生育還是精神的創造,都是愛欲實現自身的方式。
這個理論具有深刻的存在論意義。人類作為有限的、會死亡的存在,通過創造性活動超越了死亡。個體的生命雖然短暫,但通過後代、作品、制度,個體的生命獲得了某種永恆性。愛欲是人類對抗虛無、創造意義的根本力量。
在精神層面,這種創造性在哲學活動中達到最高形式。哲學家不是創造具體的事物,而是創造真正的德行——符合美本身的靈魂狀態。這種創造最為持久,因為它直接觸及永恆的形式。
愛欲與自我實現
《會飲篇》提出了一個關於自我的深刻問題:自我是已經給定的實體,還是需要通過愛欲來實現的可能性?阿里斯托芬的神話暗示,真正的自我是分裂的、不完整的,需要通過與他者的結合來恢復完整。
但蘇格拉底的理論提供了不同的答案。自我不是通過找到失落的部分來完成,而是通過向上的超越來實現。真正的自我不在過去(原初的完整狀態),而在未來(對美本身的直觀)。自我實現不是回歸,而是提升。
這兩種理論代表了關於自我的兩種基本模式:一種是本質主義的、回溯性的,另一種是存在主義的、面向未來的。柏拉圖通過狄俄提瑪的理論,挑戰了阿里斯托芬神話的普遍吸引力,提出了一種更加動態和開放的自我概念。
然而,阿爾基比亞德斯的存在提醒我們,這種哲學化的愛欲的理論在實際生活中面臨著困難。阿爾基比亞德斯無法理解蘇格拉底的拒絕,因為他仍然停留在較低層次的愛愛欲的理解中。他想要的是傳統意義上的愛情關係,而蘇格拉底提供的是哲學的轉化。
愛與節制
蘇格拉底對阿爾基比亞德斯的拒絕,體現了愛欲與節制的複雜關係。表面上看,節制似乎與愛欲相對立 — 節制意味著克制欲望,而愛欲是欲望的表達。但在更深層次上,真正的愛欲需要節制。
蘇格拉底並非不愛阿爾基比亞德斯。相反,正是因為真正的愛,他拒絕了肉體的結合。如果蘇格拉底接受了阿爾基比亞德斯的誘惑,他就會確認阿爾基比亞德斯對愛欲的錯誤理解——認為智慧可以通過身體交換獲得。蘇格拉底的拒絕本身就是一種教導:真正的愛欲不是佔有對方,而是幫助對方成為更好的人。
這種節制不是壓抑或否定欲望,而是引導欲望朝向正確的對象。蘇格拉底並非對美無動於衷 — 阿爾基比亞德斯的見證表明,蘇格拉底經常被美少年環繞,對他們表示興趣。但蘇格拉底的興趣不停留在肉體層面,而是指向靈魂的美。
這種愛欲的節制也是哲學家自我掌控的體現。在德利翁的撤退中,蘇格拉底的從容不是來自身體的強壯,而是來自靈魂的秩序。一個能夠統治自己欲望的人,也能在外部危險面前保持鎮定。
柏拉圖與香港:流亡者的哲學沉思
蘇格拉底之死與香港學人的沉默
重讀《會飲篇》,我不禁想起蘇格拉底的命運。公元前399年,這位哲學家被雅典民主法庭以「不敬神明」和「腐蝕青年」的罪名判處死刑。今天的香港,雖然沒有毒鴆,卻有《國安法》;雖然沒有公開審判,卻有無形的白色恐怖籠罩著每一個曾經敢於發聲的知識人。
蘇格拉底選擇了留下,飲鴆而死,以身殉道。他的學生柏拉圖卻選擇了離開,先是流亡,後來才返回雅典建立學園。這兩種選擇,在今天的香港語境下,都有了新的意義。留下的人,有些選擇沉默,有些被迫噤聲;離開的人,散落在世界各地,成為離散社群的一員。
我在中文大學任教通識教育課程「與人文對話」與「與自然對話」多年,引領學生重讀柏拉圖、荷馬(Homer)、聖經等經典。2020年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當《國安法》的陰影籠罩校園,學術自由成為奢侈品,「腐蝕青年」的罪名可以套用在任何啟發學生獨立思考的教師身上,我不得不問:蘇格拉底若在今日香港,會有怎樣的下場?
愛智者的流亡:從雅典到香港
柏拉圖在《第七封信》(Seventh Letter)中回憶,蘇格拉底之死令他對雅典政治徹底幻滅。他寫道,原本以為民主制度會帶來正義,結果卻是民主殺死了城邦中最正義的人。這種幻滅,對於經歷過2019年後香港巨變的人來說,並不陌生。
我們曾經相信,香港的法治、自由、開放會得到保障;「一國兩制」會讓香港保持其獨特性;大學是真理的堡壘,學術自由是不可侵犯的。然而,這些信念一一破滅,正如柏拉圖對雅典民主的信念在蘇格拉底飲鴆那一刻破滅一樣。
柏拉圖的回應是建立學園,在政治之外尋求真理。他的哲學轉向了理型世界,那個超越現實政治的永恆領域。這是逃避,還是另一種抵抗?我認為是後者。當現實世界被不義所統治,對永恆價值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種抵抗。當權力可以扭曲事實、篡改歷史、壓制異見,堅持真理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反抗。
洞穴喻與香港的「新常態」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的洞穴喻,對今天的香港有著驚人的適切性。想像一群人從小被囚禁在洞穴中,頭頸被縛,只能看著牆壁上的影子,以為那就是真實。這不正是今天香港的寫照嗎?
當媒體被收編、教科書被改寫、公共討論的空間被壓縮,人們所能接觸到的「真實」越來越只是牆上的影子。那些操控火光的人,決定了什麼影子可以被看見,什麼影子必須消失。而那些曾經走出洞穴、見過陽光的人,若膽敢回來告訴洞中人外面的世界,會被視為瘋子,甚至被視為危險人物。
蘇格拉底就是那個走出洞穴又回來的人。他試圖喚醒雅典人,告訴他們所見的不過是影子,結果被判處死刑。今天香港的處境何其相似:那些試圖揭示真相的人,拒絕接受官方敘事的人,堅持記憶的人,都面臨著各種形式的懲罰。
欲愛與香港人的精神追求
《會飲篇》告訴我們,欲愛(Eros)不僅僅是男女之情,更是人類對真善美的根本追求。這種追求源於我們的不完滿,源於我們知道自己有所欠缺。正是這種欠缺感,驅使我們超越當下,追求更高的價值。
香港人在2019年所展現的,不正是這種欲愛嗎?那不僅僅是對民主制度的追求,更是對尊嚴、正義、自由這些永恆價值的渴望。當百萬人走上街頭,當年輕人願意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代價,那是人類靈魂中最深沉的欲愛在躍動。
柏拉圖的「愛的階梯」理論告訴我們,真正的愛會引領我們從個別上升到普遍,從有形上升到無形,最終瞥見美本身、善本身、真理本身。香港人的抗爭,從最初對具體不義的反抗,逐漸上升為對普世價值的捍衛。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哲學的實踐,一種靈魂的上升。
流亡作為哲學處境
作為一個流亡哲學人,我在柏拉圖的思想中找到了慰藉,也找到了使命。
柏拉圖告訴我們,哲學人是居於神與凡人之間的存在,永遠在追求而從未完全擁有。流亡者的處境何其相似:我們居於故土與異鄉之間,既不完全屬於這裡,也無法回到那裡。這種「之間」的狀態,既是痛苦的根源,也可以是智慧的泉源。
狄俄提瑪說,厄洛斯是豐盈與貧乏之子,永遠處於有與無之間。流亡者也是如此:我們失去了故土,卻獲得了距離;失去了熟悉的一切,卻獲得了重新審視的可能。這種失去與獲得的辯證,正是哲學反思的起點。
我離開香港,不是因為懦弱,而是因為我相信,有些事情只有在外面才能做。當香港的學者被迫沉默,流亡者有責任繼續發聲;香港的記憶被系統地抹除,離散社群有責任保存和傳承;香港的年輕人失去了接觸真正通識教育的機會,我們有責任在別處延續這個傳統。
重讀經典作為抵抗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與人文對話」課程多年,帶領學生閱讀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聖經》、《論語》等經典。這門課程的精神,正是蘇格拉底式的:不是灌輸知識,而是啟發思考;不是提供答案,而是學會提問。
今天,這種教育在香港已經越來越困難。但經典的力量在於,它們超越時空,在任何處境下都能對我們說話。柏拉圖在兩千四百年前寫下的文字,今天讀來依然振聾發聵。這就是經典的意義:它們提供了一個阿基米德點(Archimedean point),讓我們可以站在那裡,審視當下的處境。
重讀《會飲篇》,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關於愛欲的哲學理論,更是一個關於人類如何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故事。蘇格拉底在宴會結束時依然清醒,當所有人都醉倒睡去,他還在追問真理。這個形象,對於今天的香港人,對於所有在黑暗時代堅持思考的人,都是一個鼓舞。
不朽的追求與歷史的審判
柏拉圖式的欲愛,最終指向不朽。狄俄提瑪告訴蘇格拉底,人類追求美善,是因為我們渴望永恆。身體的生育讓族群延續,靈魂的生育讓精神不朽。
對於香港,這意味著什麼?我相信,那些在2019年及之後所展現的勇氣、犧牲、團結,那些為自由而付出代價的人們,他們的精神將會不朽。當權者可以囚禁身體,卻無法囚禁靈魂;可以壓制聲音,卻無法消滅記憶;可以扭曲歷史,卻無法逃避歷史的審判。
蘇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處死刑,但歷史的審判卻完全相反:蘇格拉底成為了西方哲學的聖人,而那些判他死刑的人,除了作為殺害蘇格拉底的兇手被記住之外,已經被歷史遺忘。柏拉圖在《申辯》中記錄了蘇格拉底的預言:「你們判我死刑,但懲罰會降臨到你們頭上。」這個預言應驗了。
我相信,香港的歷史審判終將到來。那些壓迫者、告密者、助紂為虐者,終將面對歷史的審判。而那些堅持正義、追求自由、保持尊嚴的人,他們的名字將被銘記。
哲學作為生活方式
最後,我想說的是,柏拉圖的哲學不僅僅是一套理論,更是一種生活方式。蘇格拉底用他的一生,乃至他的死亡,展示了什麼是哲學的生活。那不是書齋中的玄思,而是在城邦中與人對話,追問什麼是正義,什麼是美德,什麼是值得過的人生。
對於流亡者來說,這種哲學的生活方式尤為重要。當我們失去了物質的根基,精神的追求就成為存在的支柱。當我們無法改變現實政治,對永恆價值的堅持就成為最後的抵抗。當我們感到孤獨和絕望,與古人的對話就成為慰藉的泉源。
我將繼續重讀經典和書寫,在可能的地方教學。這是我作為一個流亡哲學人能做的事情。柏拉圖在蘇格拉底死後,用餘生書寫對話錄,讓老師的精神得以不朽。我當然沒有柏拉圖的才華,但我可以效法他的精神:用書寫對抗遺忘,用思考對抗愚昧,用愛智對抗犬儒。
《會飲篇》最後,當黎明來臨,蘇格拉底起身離去,「像平常一樣度過這一天」。這個結尾看似平淡,卻蘊含深意:哲學不是特殊時刻的激情,而是日常生活的堅持。在最黑暗的時代,保持清醒,繼續追問,像平常一樣度過每一天,這本身就是一種英雄主義。
願我們都能像蘇格拉底那樣,在黑暗中保持清醒,在喧囂中堅持追問,在絕望中不忘希望。願香港的精神不朽。願自由終將歸來。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