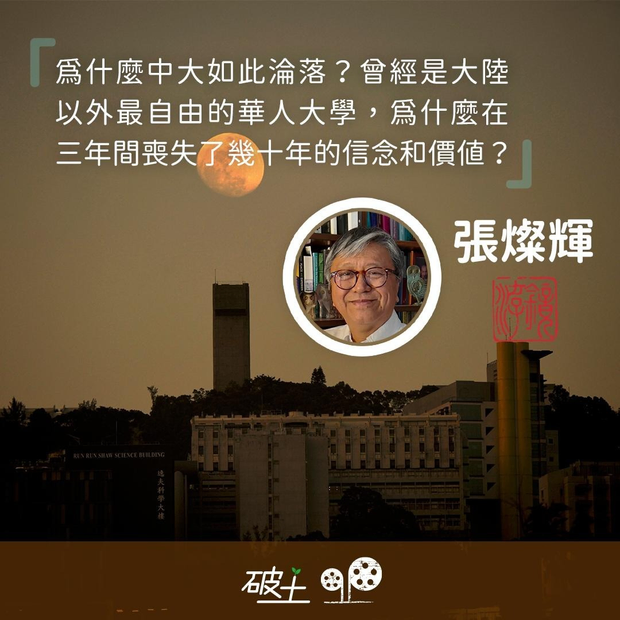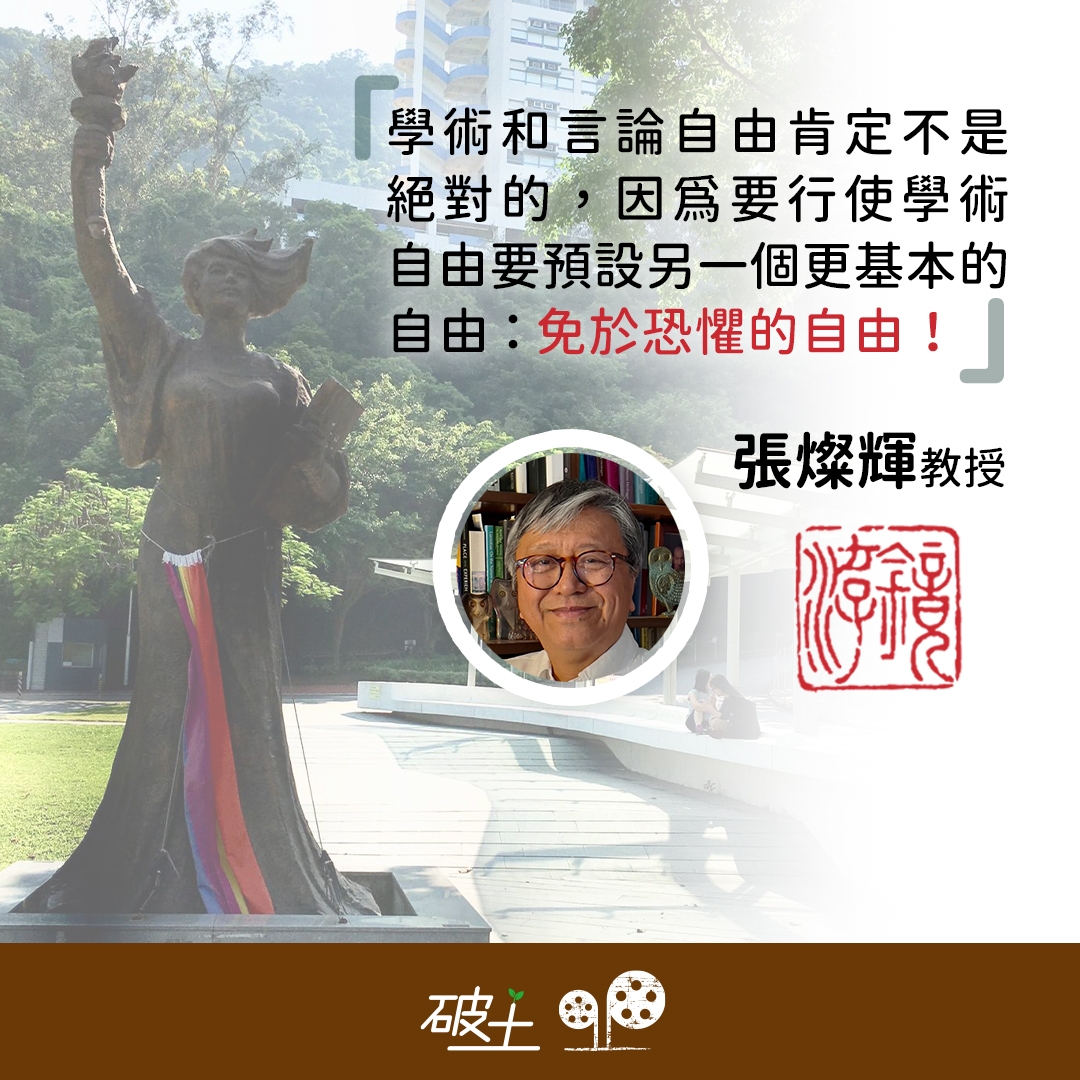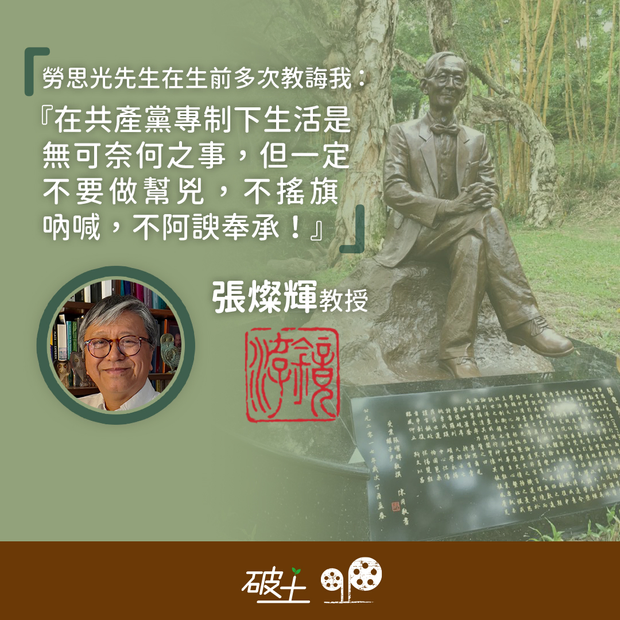閒暇的哲學思考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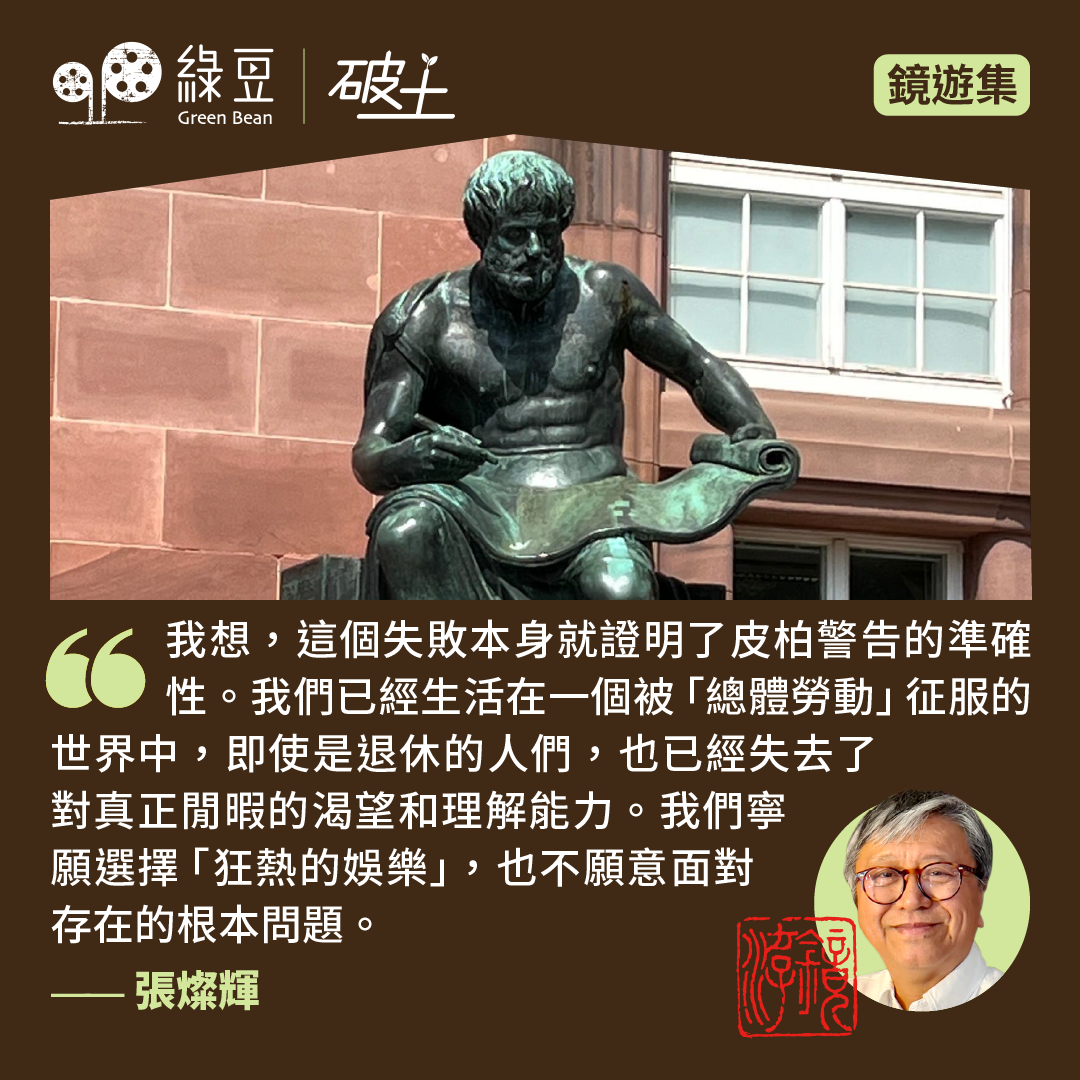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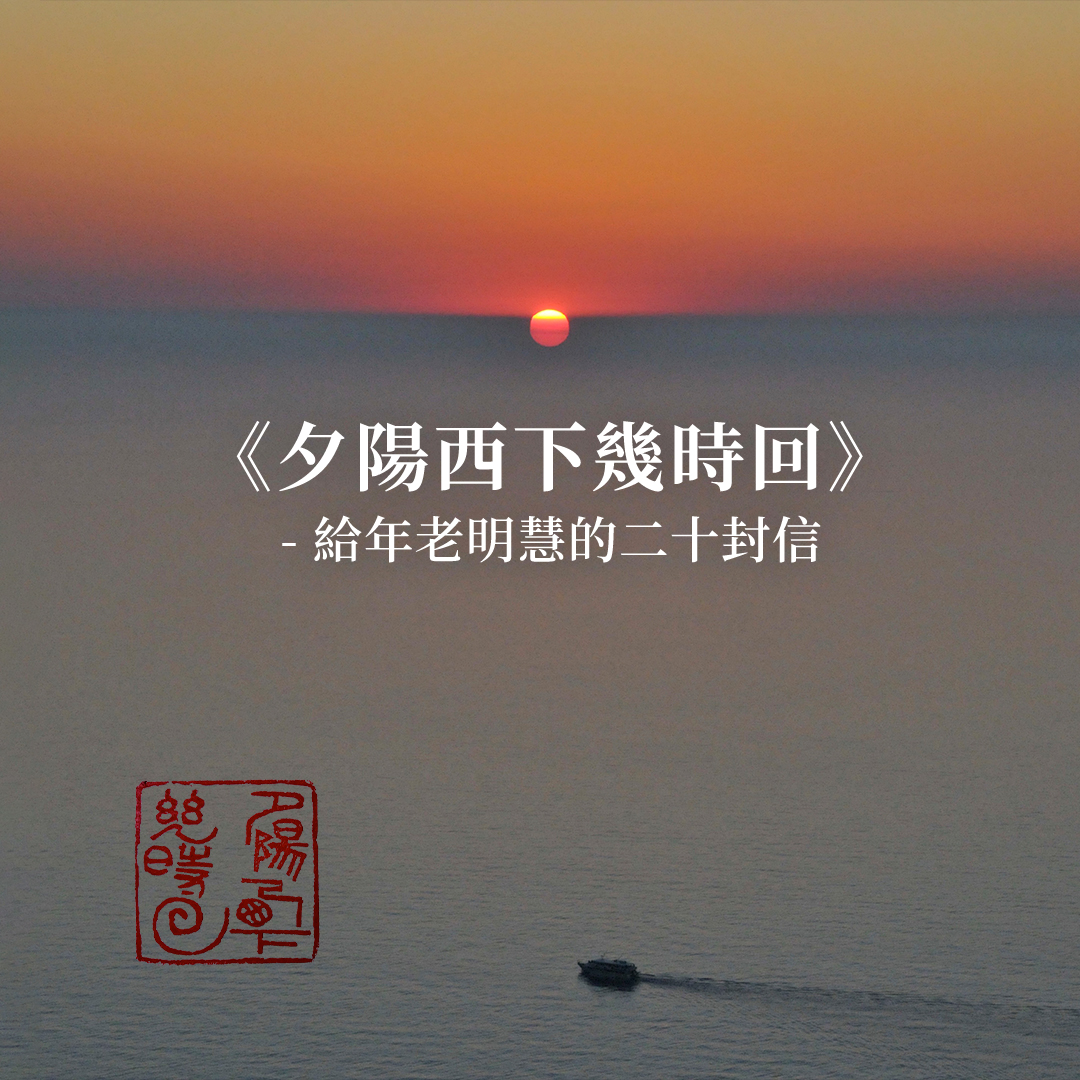
第十五封信 15.1
明慧,
收到你的回信,我深深感受到你對生命意義的困惑與焦慮。你說前面的兩封信可能太沉重了,讓我想起尼采曾經說過的話:「我的靈魂過於驕傲,不願被安慰,但它有時需要安慰,正如強者有時需要酒一樣。」也許我們都需要在這人生的黃昏時分,和面對政治打壓的處境,找到一種既不逃避現實,又能超越痛苦的生活態度。
我以尼采「愛命運」(amor fati)的思想來引導自己,但正如你所說,這只是一種領悟,我們更需要行動。哲學確實是一種生活方式(a way of life),而不僅僅是書本上的智慧。但我認為,正是這種對生命的深入反思,才讓我們有機會真正理解什麼是有意義的生活。
你提到的日常生活循環 —— 工作、吃飯、週末娛樂、旅遊、退休、最終離世—— 這確實是現代人普遍的生活軌跡,但這真的就是我們生命的全部嗎?尼采的「愛命運」並非要我們被動地接受這種機械化的存在,而是要我們學會在命運中創造意義。
真正的「閒暇」
當我從中文大學退休下來的時候,我當時的感覺是:太好了!我不用再開那些無聊的會議、不用每天到辦公室上班、不需要和不喜歡的人應酬吃飯,我重新解放了,我有大量時間!但是不用工作,每天都是放假,這就是幸福的生活嗎?
這個問題讓我陷入了深思。表面上看,我獲得了自由,但這種自由如果沒有方向和內容,很快就會變成空虛。正如尼采在《快樂的科學》中所說:「我想要學會越來越多地將事物中必要的東西看作美的;這樣我就會成為那些使事物變美的人之一。愛命運(Amor fati):讓這成為我從今以後的愛!」
但是,愛命運不是消極的接受,而是積極的轉化。我們不是要愛痛苦本身,而是要在痛苦中找到成長的可能,在限制中發現創造的空間。這種態度的轉變,需要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是真正的「閒暇」(leisure)。
2016年我設計了一個課程給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課程是專門為退休人士而設,名為「第三齡人文學術課程」(Scola Humanitatis for the Third Age)。這個課程經過嚴格審核通過了,但推出後報名人數太少,結果要取消。這是我一個失敗的嘗試,但這個失敗讓我更深入地思考工作和閒暇的關係,以及第三齡長者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當我重新審視古希臘哲學家們的智慧時,我發現了一個被現代社會遺忘的深刻洞察。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一句至今仍震撼人心的話:「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和平,工作的目的是為了閒暇。」這句話在今天聽來幾乎是反直覺的,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將工作視為生命核心的社會中,但亞里士多德的洞察指向了一個更深層的真理。
你知道嗎,「學校」(school)這個詞來自希臘語「scholē」,而「scholē」的原意就是「閒暇」。這不是巧合,而是揭示了一個重要的文化觀念:真正的學習、思考和人格發展,只有在閒暇中才能實現。
亞里士多德認為,閒暇不是工作的對立面,也不是簡單的休息或娛樂。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他明確指出:「幸福被認為依賴於閒暇;因為我們忙碌是為了能夠有閒暇,我們發動戰爭是為了能夠生活在和平中。」真正的閒暇超越了功能性的放鬆,它是一種生活態度,是「為了自身而進行的活動」。
閒暇與人類繁榮
現代學者研究亞里士多德的閒暇概念時發現,scholē實際上是幸福(eudaimonia)的前提條件。這不是說閒暇本身就是幸福,而是說沒有閒暇,我們就無法達到真正的人類繁榮。為什麼會這樣呢?
首先,閒暇為沉思(contemplation)提供了空間。亞里士多德認為,沉思是人類最高的活動,因為它不是為了其他目的而進行的,而是為了自身的價值。當我們在真正的閒暇中時,我們可以思考生命的根本問題:什麼是善?什麼是美?什麼是真理?這些問題沒有實用價值,但卻是使我們成為完整人類的根本。
其次,閒暇培養德性。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指出:「與閒暇相關的德性是必要的;因為正如多次說過的,和平是戰爭的目的,閒暇是事務的目的。但對閒暇有用的德性不僅是那些在閒暇時發揮作用的德性,也包括那些在事務中發揮作用的德性。」換句話說,閒暇不僅給我們時間來發展智慧,也給我們機會來培養品格。
第三,閒暇與自由的關係密不可分。亞里士多德強調,真正的閒暇是自由的標誌。只有自由人才能享有閒暇,這不是因為他們有特權,而是因為閒暇要求一種內在的自由——從物質需求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從外在強迫中解脫出來。
但這裡涉及一個深刻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如果真正的人類繁榮需要閒暇,那麼一個好的社會就應該為其公民提供享有閒暇的可能性。這不是奢侈品,而是人類尊嚴的基本要求。
真正閒暇意義
二十世紀的德國哲學家約瑟夫·皮柏 (Josef Pieper, 1904-1997)在他的經典著作《閒暇:文化的基礎》(Leisure:The Basis of Culture)中,更深入地探討了這些古典洞察對現代世界的意義。皮柏寫於1948年的這部作品,現在讀來比當年更加緊迫和相關。
皮柏的核心論點讓我深深震撼:「文化的存在完全依賴於閒暇,而閒暇反過來,除非它與崇拜(cultus)—— 與神聖崇拜有持久而因此活躍的聯繫,否則是不可能的。」這個觀點可能讓現代讀者感到困惑,但皮柏所說的「崇拜」不僅指宗教活動,更廣泛地指向對超越性價值的敬畏和追求。
更令人警醒的是皮柏的預言:「我們資產階級的總體勞動世界已經征服了閒暇,並發出驚人的警告:除非我們重新獲得寂靜和洞察的藝術,非活動的能力,除非我們用真正的閒暇來替代我們狂熱的娛樂,否則我們將摧毀我們的文化——和我們自己。」
當我讀到這段話時,我想起了你信中描述的現代生活模式。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已經忘記真正閒暇意義的「無閒暇文化」中。現代人面臨的問題不是缺乏空閒時間,而是不知道如何建設性地使用這些時間。
對於皮柏來說,真正的閒暇不是活動的停止,而是一種特殊的精神狀態。他寫道:「閒暇是一種心靈的態度和靈魂的狀態,它培養感知世界現實的能力。」這種態度的特徵是什麼呢?
首先,它是接受性的而非製造性的。在我們的工作導向文化中,我們習慣於通過行動和製造來定義自己的價值。但閒暇要求一種不同的存在方式 —— 允許事物向我們展現自己,而不是強迫它們符合我們的意志。
其次,真正的閒暇與沉默和內在寧靜相關。皮柏特別強調了沉默在現代世界中的重要性。在一個充滿噪音和干擾的世界中,我們失去了聆聽——聆聽自己內心聲音的能力,聆聽他人的能力,聆聽世界本身的能力。
第三,閒暇具有節慶的特性。皮柏認為節慶是閒暇的核心,因為它體現了對神聖的體驗。當我們真正慶祝時——無論是與朋友共進晚餐,參與音樂會,還是簡單地欣賞日落——我們進入了一種超越日常功利關係的存在模式。
這讓我想起了皮柏對用餐的深刻觀察。他寫道:「用餐具有『精神的甚至宗教的特性』。也就是說,它是一種奉獻,一種犧牲,也是——在最高層面——一種聖禮,從高處,從我們向其奉獻的存在那裡給予我們的東西。動物進食,但在它們的生活中沒有任何東西對應於『用餐』的體驗,作為對我們在地上生活的慶祝和認可。」
活在被「總體勞動」征服的世界中
正是基於這些哲學洞察,我設計了那個最終失敗的課程計劃。我想為「第三齡」的人們創造一個真正的「學堂」(scola),一個可以實踐古典意義上的「閒暇」的空間。
我在課程前言中寫道:「第三齡不是由60歲或65歲的年齡數字來定義,而是理解為一個階段,在經歷了第一齡的準備和教育,以及第二齡的工作、事業和家庭之後。第三齡是人類在多年工作後進入的階段,是自由和閒暇的時期。因此它不一定意味著退休,而是反思和重新思考自己生活的開放可能性。」
我深信,這些課程不應該按照普通大學的單一學科劃分為哲學或文學;它們都應該是跨學科的方法和存在主義的性質。課程不關心生產力、利潤或政治,而純粹關心用人文學科的財富來滋養心靈。它們要求學術嚴謹,由原始文本支持,達到研究生水平。它們被組織成講座、研討會,並在適當的情況下進行實地考察。它們不是「容易」的課程,而是需要在文本和對話中積極的智力參與,這樣才能實現心靈的「復興」:重新發現自我和世界,重新發現文化和社會,重新發現生命的意義。
我邀請了超過十位朋友同事學者,參與計劃這個課程,設計了二十門課程,涵蓋了從古希臘哲學到現代存在主義,從東方道教到西方基督教神秘主義的廣泛領域。每一門課程都旨在觸及人類存在的根本問題:衰老與生活的藝術、死亡與不朽、愛與性、幸福與痛苦、悲劇與喜劇、美與醜、社群與美好生活等等。
但是,這個計劃失敗了。報名人數太少,課程不得不取消。這個失敗讓我深深思考:為什麼在一個理論上應該對這種「閒暇教育」有需求的社會中,實際的回應卻如此冷淡?
我想,這個失敗本身就證明了皮柏警告的準確性。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被「總體勞動」征服的世界中,即使是退休的人們,也已經失去了對真正閒暇的渴望和理解能力。我們寧願選擇「狂熱的娛樂」——旅遊、購物、電視節目、社交媒體——也不願意面對存在的根本問題。
但是,這個失敗也讓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哲學作為生活方式的意義。哲學不能僅僅是學術活動,它必須與我們的日常生活互相融合。也許我的錯誤在於,我試圖在一個學術機構框架內重建古典的「閒暇」概念,而忽視了現代生活的實際條件和限制。
(待續)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