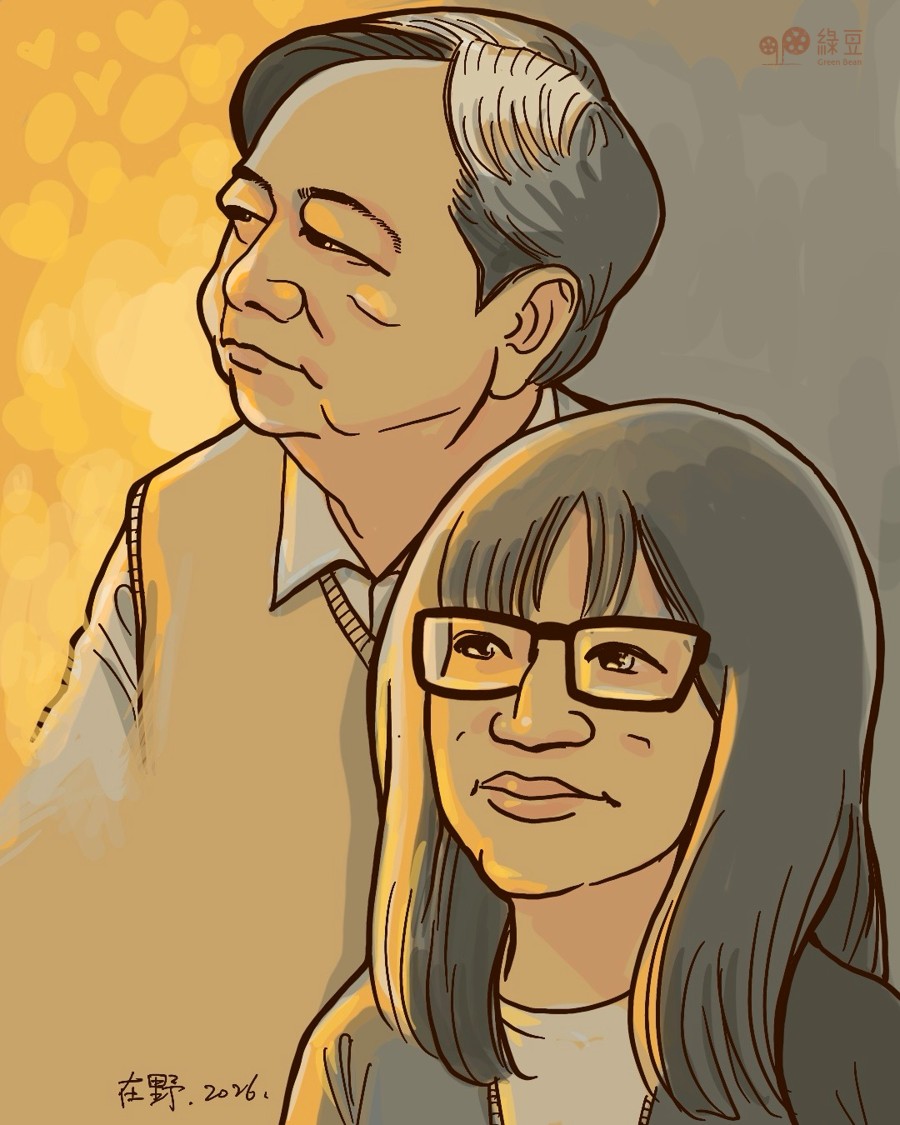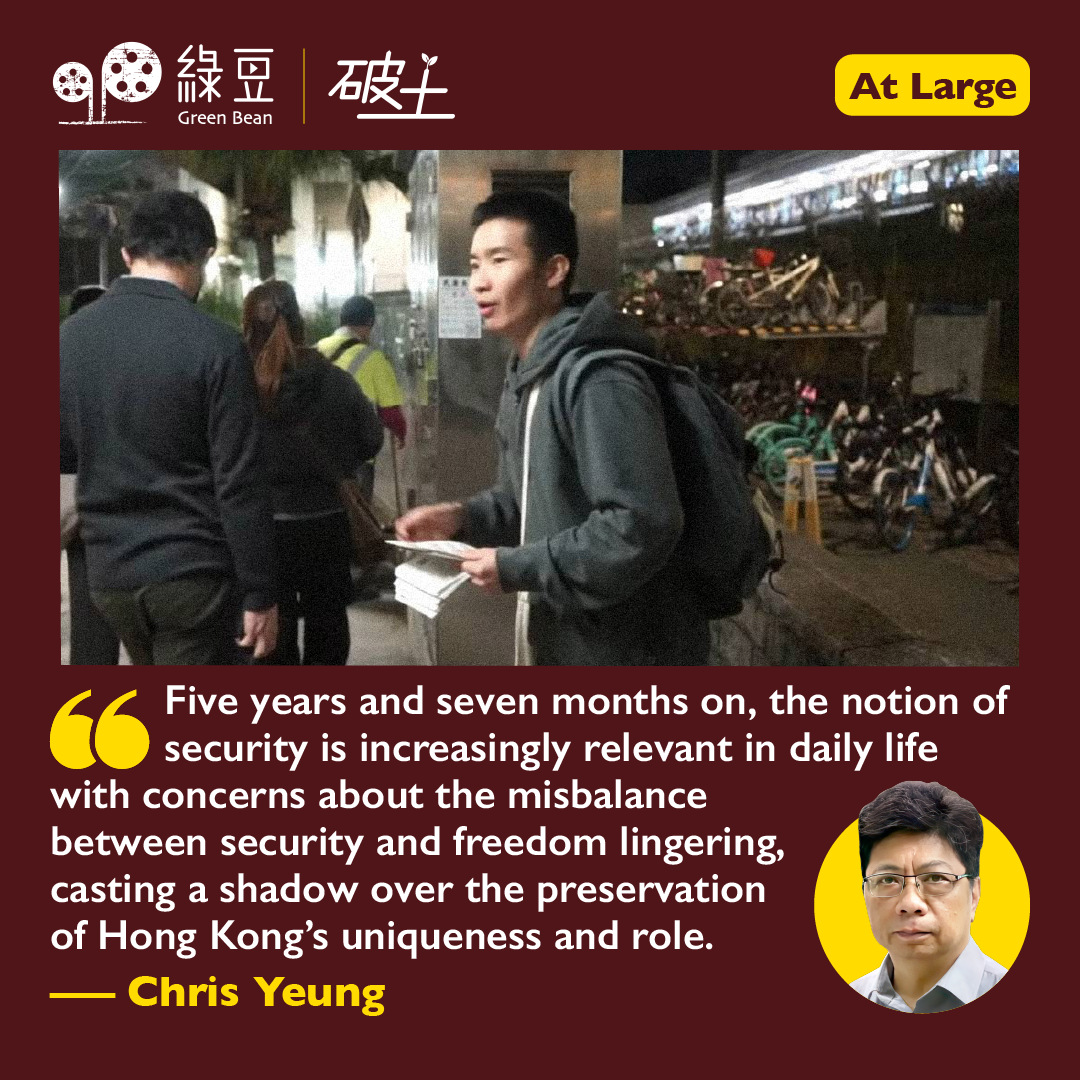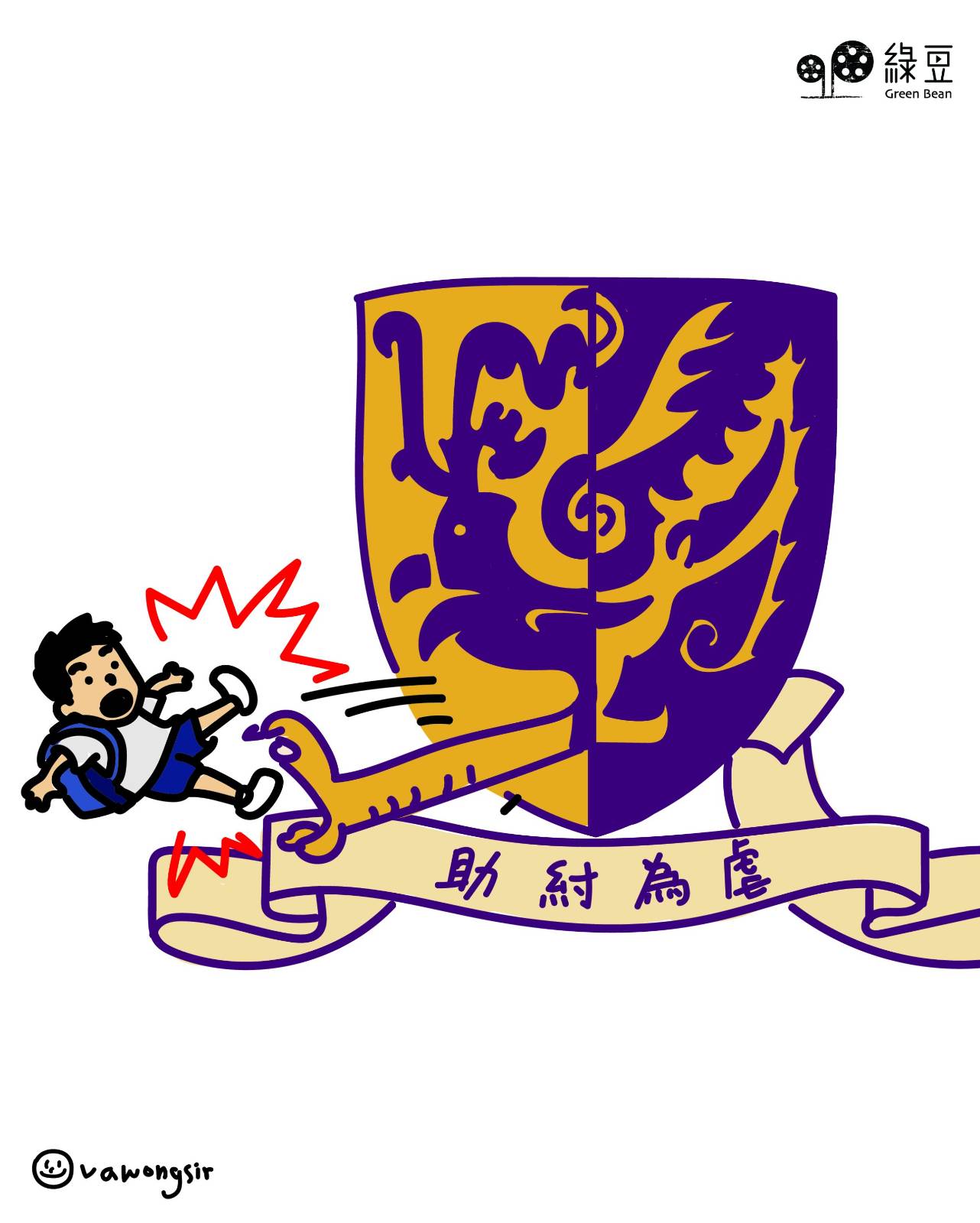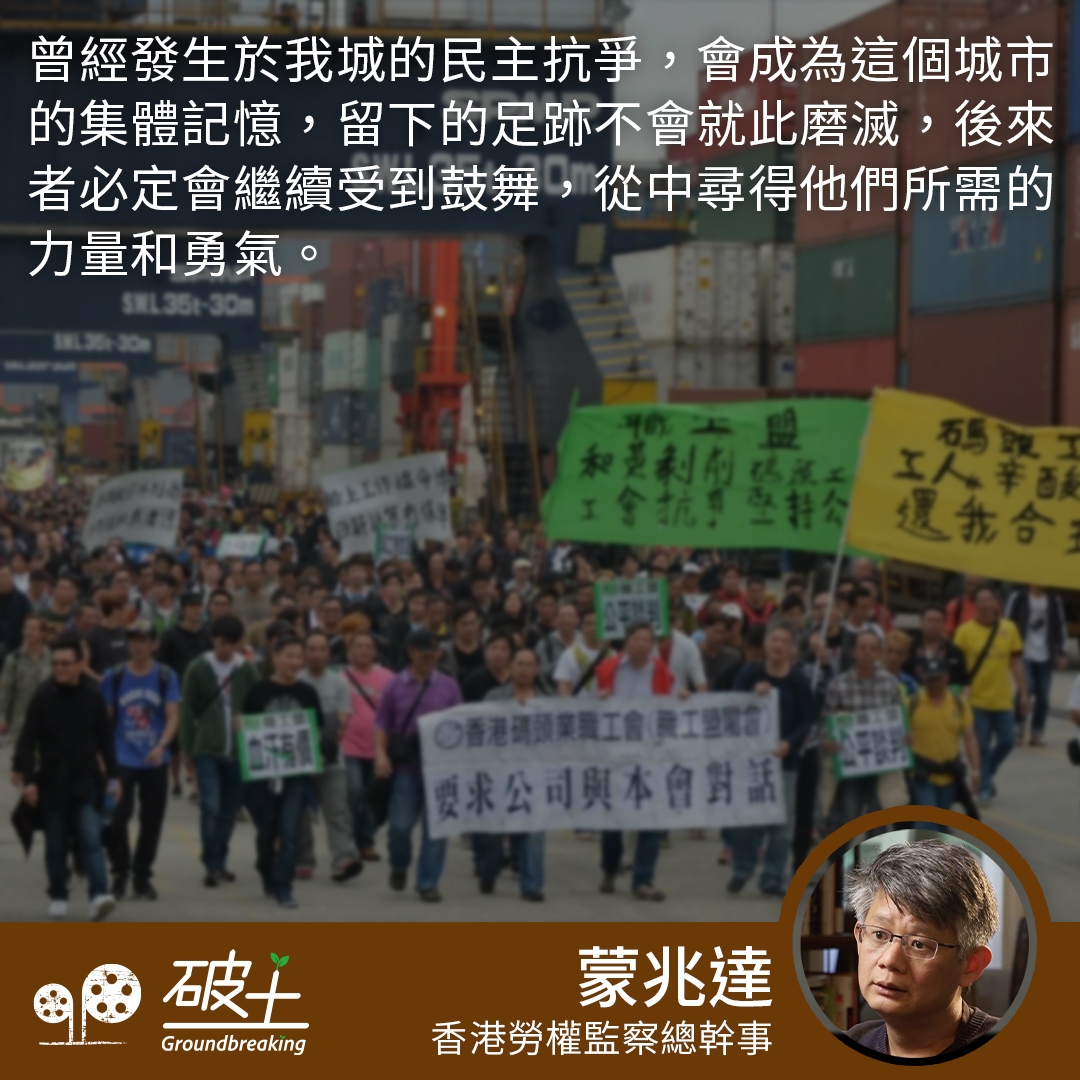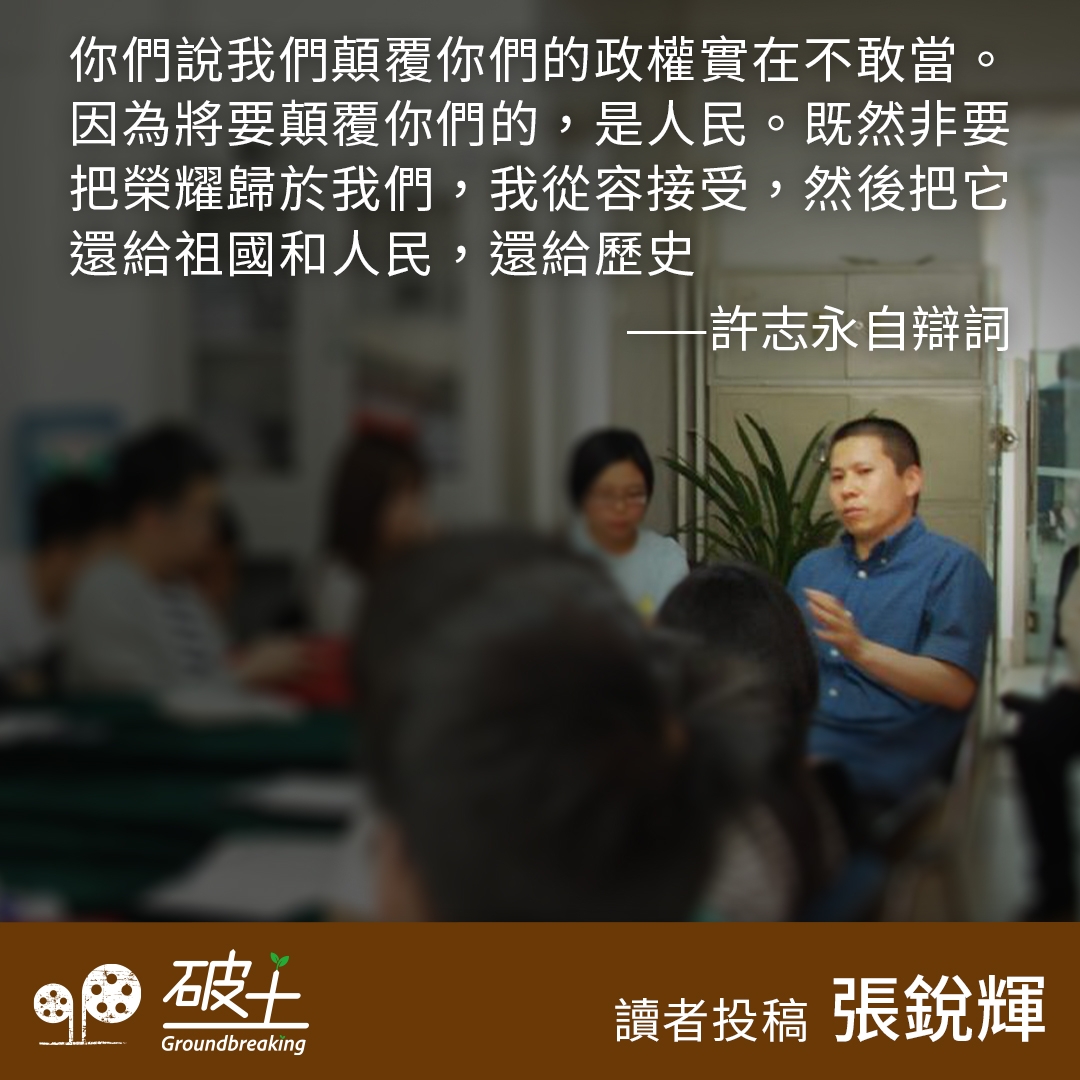當法律退位:司法越權、行政擱置與立法權的侵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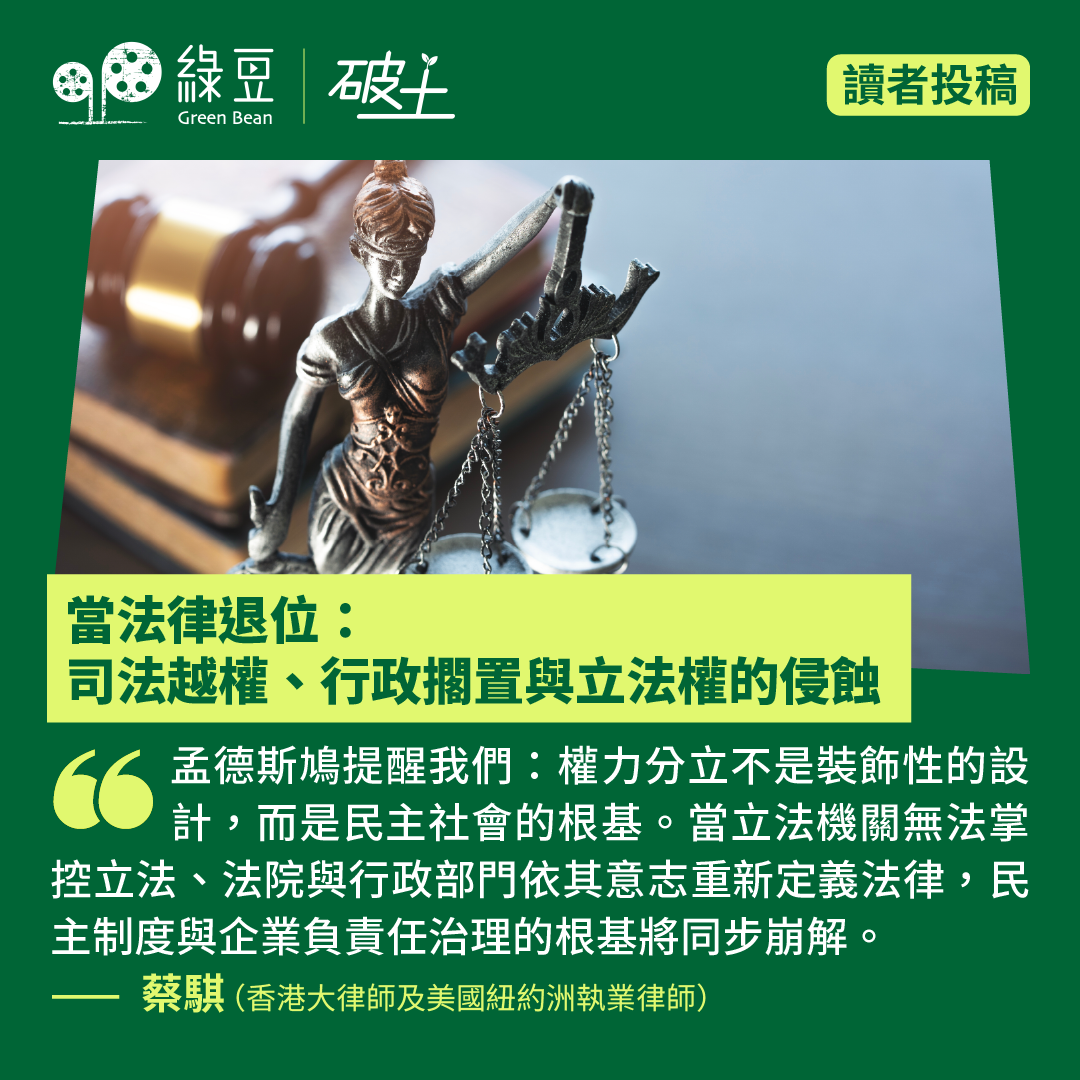
最近兩宗與反貪法相關的法律發展——一宗來自香港,另一宗來自美國——凸顯出不同法治體系中日益嚴峻的憲政困境:立法權是被擴張性司法詮釋與行政命令邊緣化?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林卓廷》一案中,香港終審法院恢復了林卓廷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30(1)條被定罪的裁決,罪名是披露廉政公署調查對象的身分。值得注意的是,該被調查對象所面對的指控 ——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並不屬於條例第二部分所列明的罪行。然而,法院以立法目的為依據,作出擴張性的詮釋,將刑事責任延伸至法條文本未涵蓋的範圍。
與此同時,在美國,一項總統行政命令暫停了《海外反貪腐法》(FCPA)的執行——這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反賄賂法例。行政命令的理由是保護美國在「戰略性產業」中的經濟與國家安全利益。此一決定未經國會討論、修法或廢止,就被行政機關單方面中止,形同擱置一整套根本性的法規體系。
超越國界:全球反貪趨勢的倒退
當前的全球不確定性因主要強權的路徑分歧而進一步加劇。在如中國這類威權體制中,反貪執法往往具備雙重功能:既用以強化黨紀,也常被視為清除政敵的政治工具。特定罪名在缺乏立法監督下透過司法解釋擴張,使外界擔憂反貪制度會否淪為政治打壓的手段,而非一個以法治原則為基礎的法制。
相對地,曾經是全球商業誠信典範的美國,如今卻透過行政手段鬆綁反賄賂體系,以換取經濟利益。這兩種極端——一方是政治化的過度執法,另一方是經濟導向的任意放寬——共同向國際商界傳遞出一個混亂且不安的訊號:合規的核心是否已不再是普世原則,而是對權力結構的策略導航?
結果是全球反貪合規版圖的碎片化,這勢必會為跨國企業帶來更高的法律風險、成本與操作複雜性。
法律詮釋與立法界線之間
在《林卓廷案》中,法院透過目的性詮釋擴張了法條適用範圍,雖從學理角度具正當性,卻引來強烈反對意見。持反對意見的法官令人思考法院此舉是否有僅扭曲了法律條文的意思,甚至擾亂了原有的立法權力平衡?爭論焦點並非立法原意是否重要(它當然重要),而是法院是否已越過了條文、案例與立法背景所容許的界限。同樣地,以行政命令擱置法例也突顯出行政機關在未經立法諮詢即行動,可能會引發憲政危機:行政部門是否可以透過行政命令使國會立法形同失效?
立法機關是否仍在正常運作?
這兩宗案件所引發的共同反思是:立法機關是否仍是法律制定的核心機構,還是正被司法與行政部門的擅自行動所架空?當法院將法條詮釋得面目全非,行政機關單方面停止法律的執行,我們所面對的將是:由民主協商產生的法律變成便利政治或經濟的工具。在企業環境中,這意味著更大的法律模糊空間、更難預測的執法風險,以及支撐商業道德的法治條件逐步被侵蝕。當立法權力的邊界被模糊、甚至被忽視時,對管治制度的信任亦隨之瓦解。
永恆的警示:孟德斯鳩的告誡
孟德斯鳩於1748年所著的《論法的精神》中發出了一個至今依然重要的警示:
「當立法權與行政權合而為一時……便不可能存在自由……若司法權不獨立於立法與行政權,也不可能存在自由。若司法者同時具立法權,人民的生命與自由將暴露於專斷的控制之下……萬事萬物將走向終結。」
孟德斯鳩提醒我們:權力分立不是裝飾性的設計,而是民主社會的根基。當立法機關無法掌控立法、法院與行政部門依其意志重新定義法律,民主制度與企業負責任治理的根基將同步崩解。
結語:一場制度重整的呼籲
全球反貪體系一直以來仰賴的是領導力、透明度與對制度的信任。如今,司法越權、行政擱置、立法程序被繞過的趨勢,正將這個體系推向風險邊緣。此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法律人、合規主管與制度領袖挺身而出,捍衛制度的正當性。我們不僅要依法行事,更要守護那些賦予法律正當性的憲政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