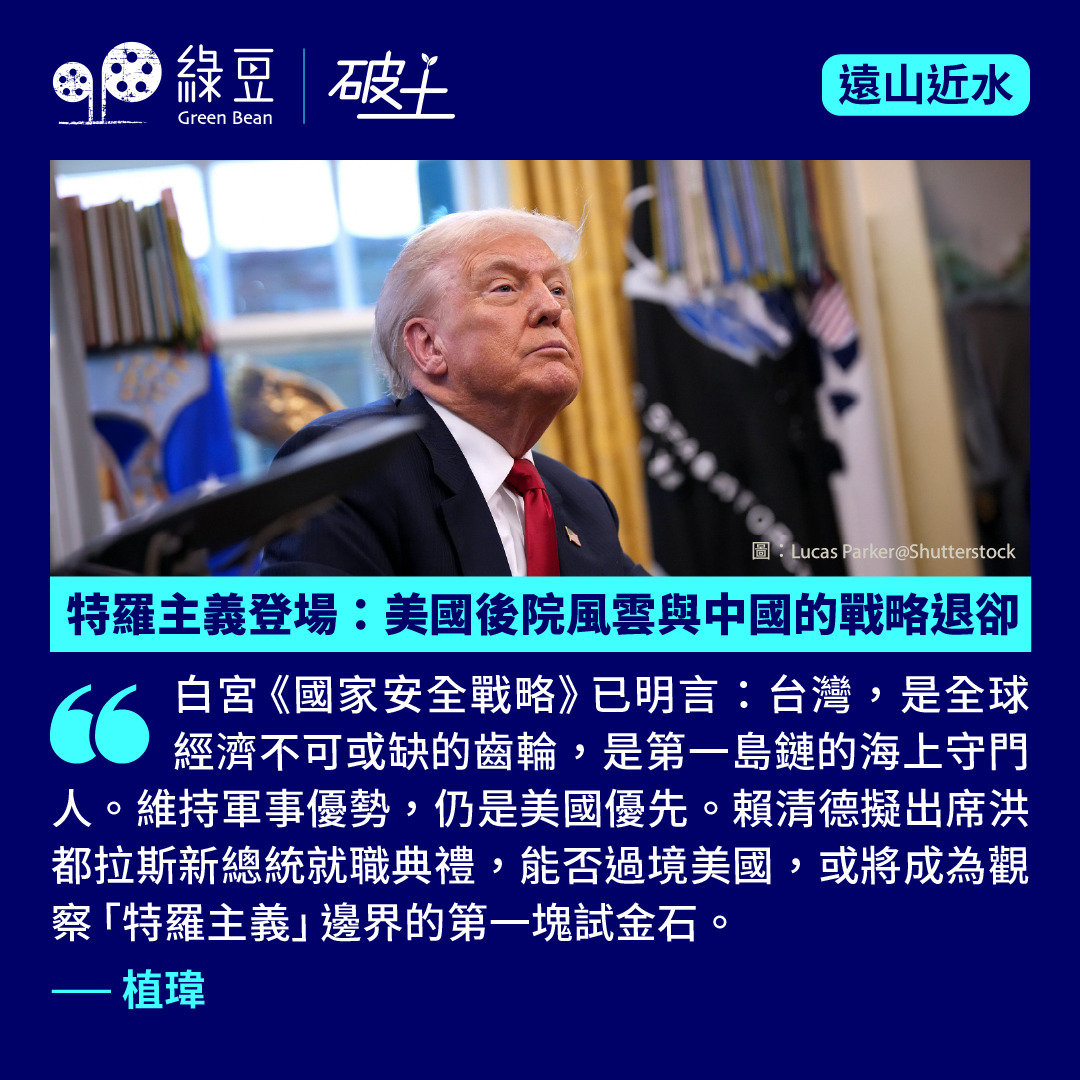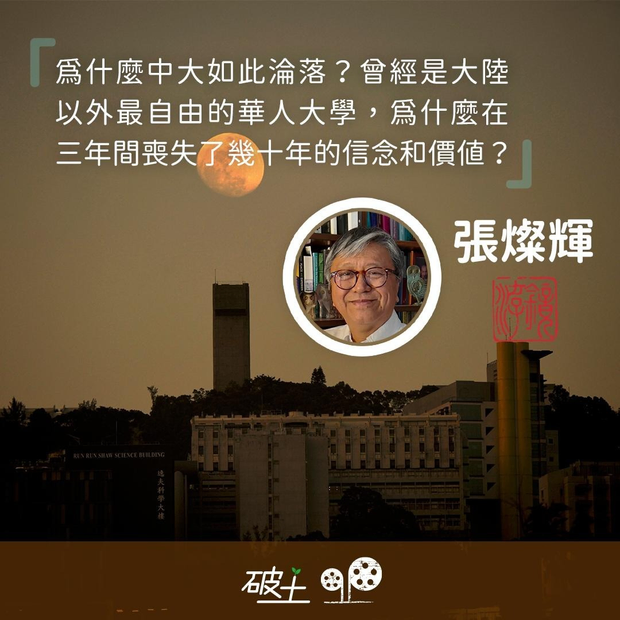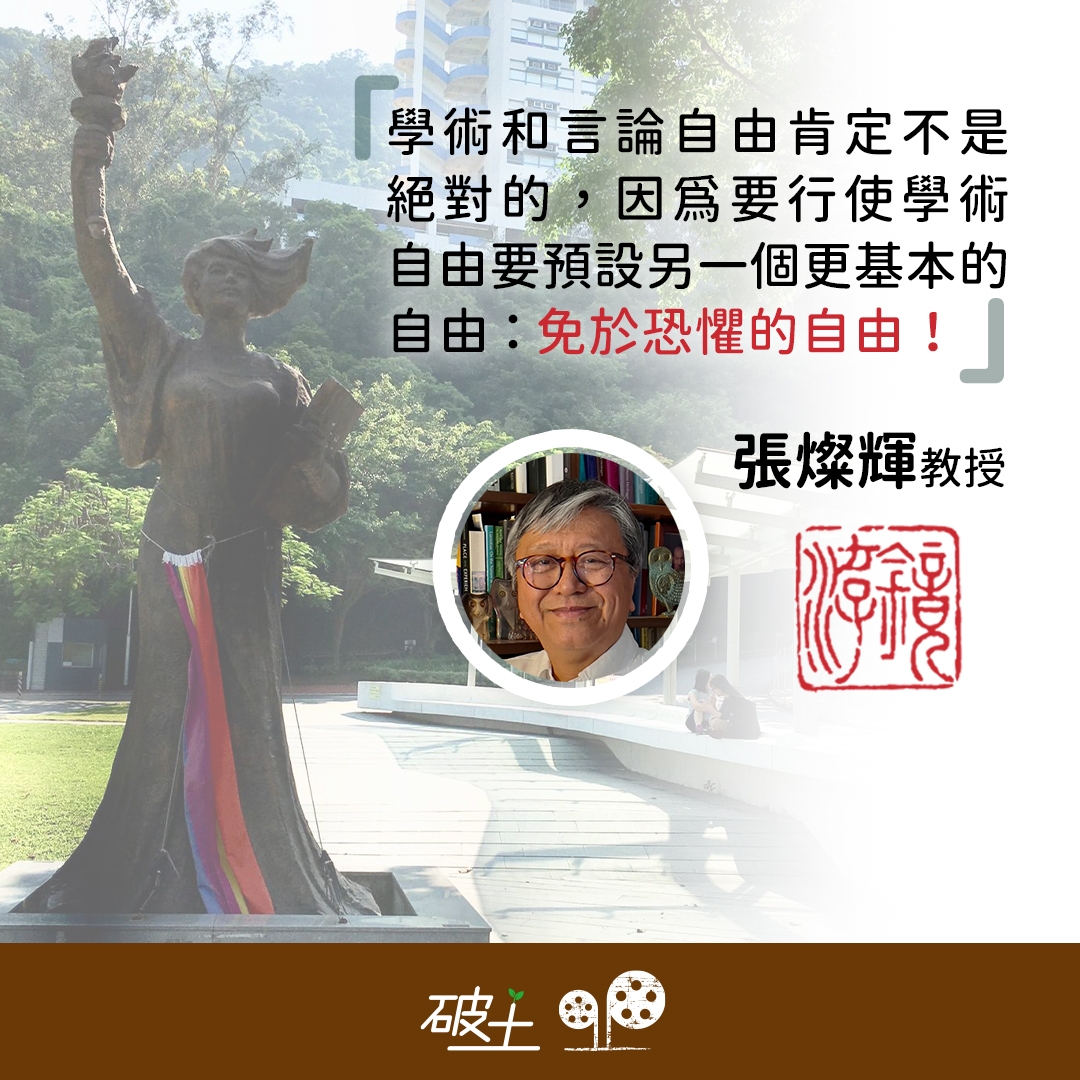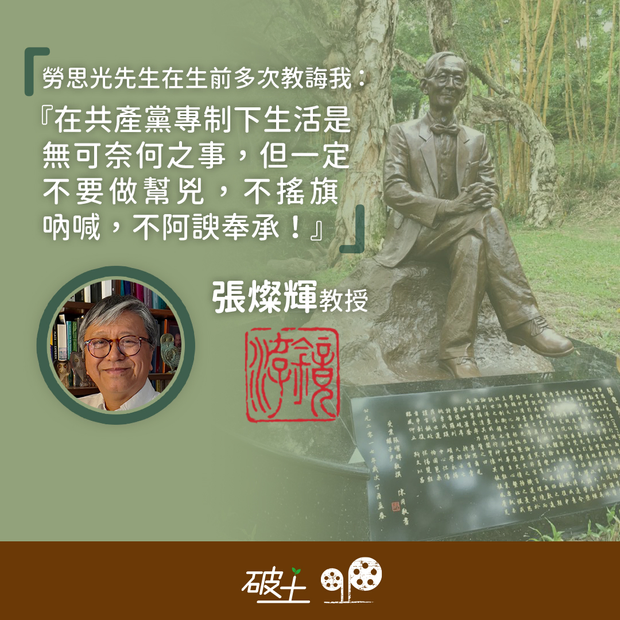夕陽西下-準備死亡與生命敘事的完成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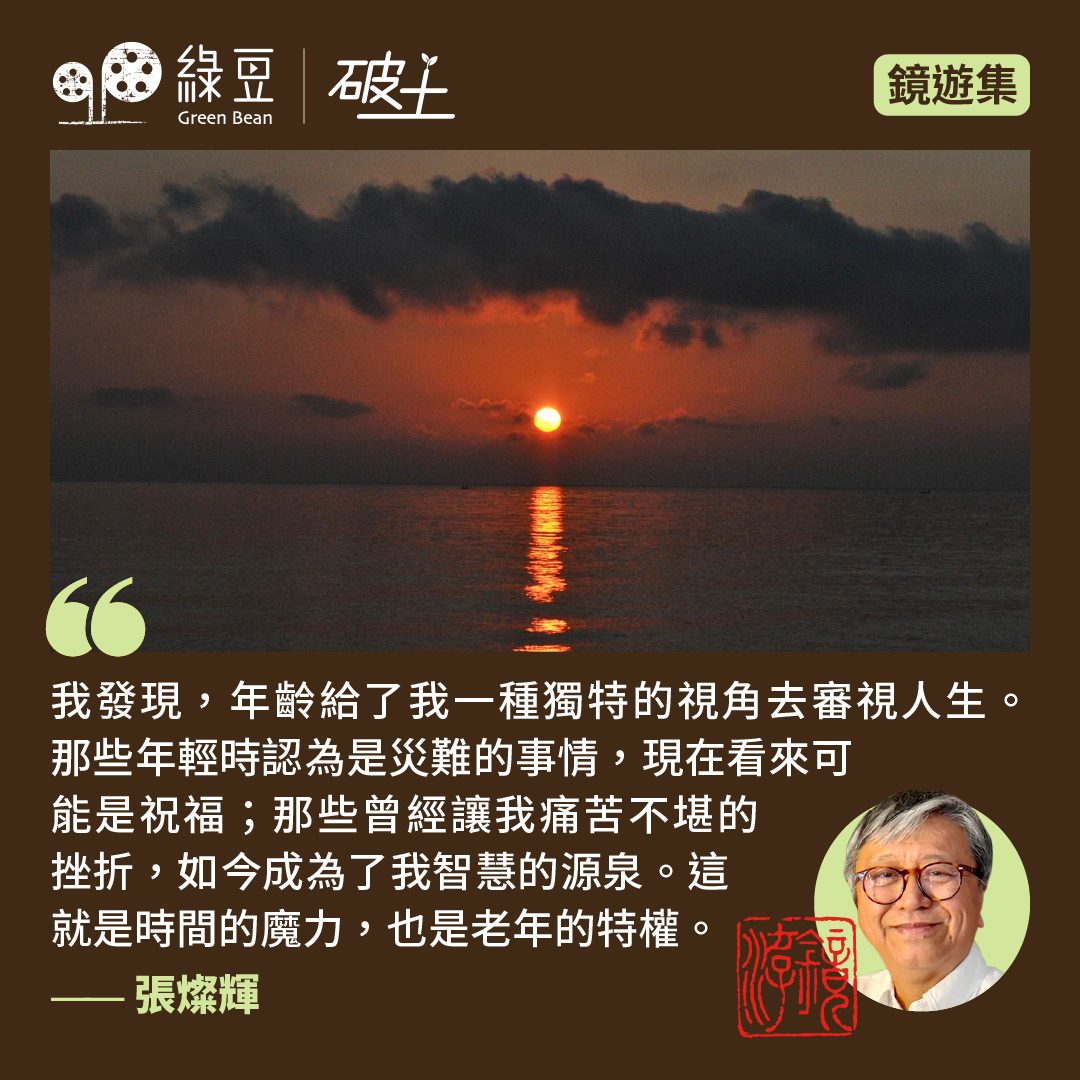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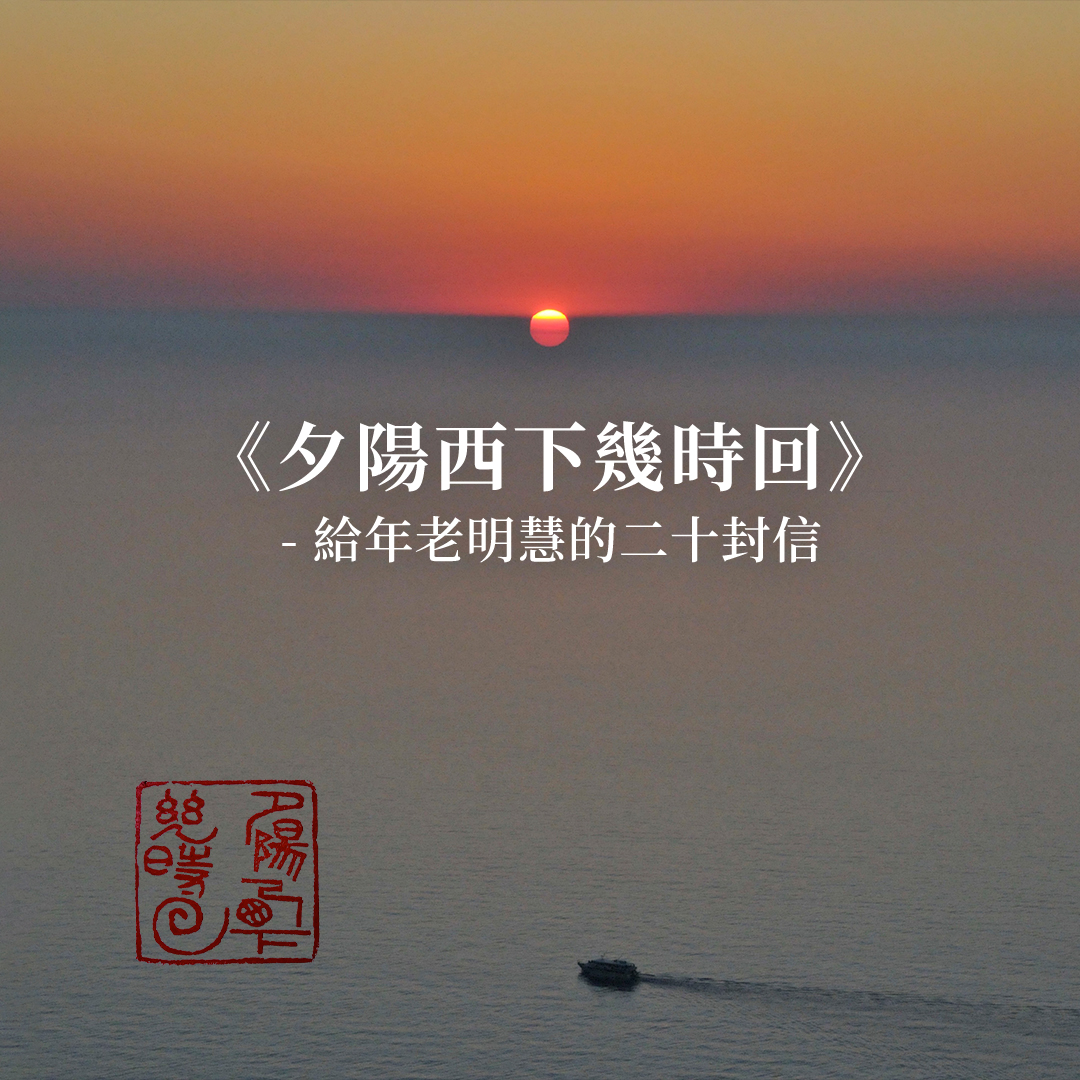
第二十封信 20.1
明慧:
五十多年前,當我還是二十多歲的年輕哲學學生時,曾在那個充滿理想與迷茫的年代給你寫信,談論人生的困惑與意義。如今,歲月如流水,我已屆耄耋,在這人間已生活七十多年,也已臨近離世之時。現代醫療雖能延壽,長命百歲亦非奢談,可真正重要的並非「活著」,而是「如何活得有意義與價值」。這正是蘇格拉底「未經省察的人生不值得活」的深意所在。
「人生七十古來稀」,杜甫昔日的感嘆,在今世已改換語境。醫療與營養的躍進,讓壽命攀升,但面對生命有限性,我們當以深刻與廣闊替代長度與數字,用每一刻的清醒與熱情去雕塑屬於自己的天地。
時光荏苒,回望這五十多年的歲月,我想起當年我們第一次相遇時的情景。那是在一個春日的午後,我們在尖沙嘴海運大廈的巴西咖啡店裡討論著存在主義的哲學問題。你當時穿著一件淡藍色校服,手中拿著一本沙特的《存在與虛無》,眼中閃爍著對知識的渴望與對生命的熱忱。那個午後的陽光透過窗櫺灑在你的臉上,你認真思考問題時微蹙的眉頭,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記憶中。
現在,當我坐在異鄉的書房裡,望著夕陽西下的天空,那些往昔的點點滴滴如潮水般湧來。我們曾一起走過香港的石板街、聽過維港的汽笛聲、在太平山頂看過萬家燈火、在廟街夜市品嚐過地道小食。那些歲月裡,香港正值黃金年代,一切都充滿了希望與可能。我們年輕的心靈裡裝著整個宇宙的夢想,以為時間是無限的,以為生命可以永遠年輕。
年老的雙重面貌:挑戰與智慧的交織
明慧,我們必須誠實地面對年老帶來的各種挑戰。當代研究顯示,約有14%的60歲以上成年人患有心理健康疾病、25%的老年人經歷社會孤立,大多數人都面臨著行動能力限制和慢性健康問題等重大身體變化。這些統計數字並非要讓我們沮喪,而是要我們清醒地認識到老年階段的複雜性。
我自己也深深體會到這些變化。曾經靈活的身體開始變得遲緩,記憶力不如從前,有時會忘記剛剛說過的話。夜晚常常因為身體的疼痛而難以入眠,白天又因為體力不濟而感到疲憊。這些都是老年不可避免的現實,我們無法逃避,只能學會接受。
但是,明慧,這只是故事的一面。研究同時顯示,50%經歷創傷的老年人最終會表現出創傷後成長。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擁有著年輕人所沒有的獨特優勢:我們有著豐富的人生經驗、有時間進行深度思考、也擺脫了年輕時的許多壓力。
當代對成功老化的理解已經超越了單純的無病狀態,而是包含了身體健康、認知功能、積極的生活參與、心理健康和社會連結等多個維度。智慧並不會自動伴隨年齡而來,但可以通過反思、整合生活經驗和意義創造等活動來積極培養。
我發現,年齡給了我一種獨特的視角去審視人生。那些年輕時認為是災難的事情,現在看來可能是祝福;那些曾經讓我痛苦不堪的挫折,如今成為了我智慧的源泉。這就是時間的魔力,也是老年的特權。
生命敘事的哲學:卡爾(David Carr)的洞察
在我探索年老意義的過程中,我拜讀現象學家朋友卡爾(David Carr)關於敘事認同的深刻思想。卡爾認為,我們的人生可以理解為一部不斷被書寫和重寫的自傳。這個洞察讓我豁然開朗:原來我們的老年不僅僅是時間的積累,更是我們能夠採納的關於生命整體性的視角。卡爾在《我們生命的故事:年老與敘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看法:人的獨特性不在於存活的年限,而在於我們具有「時間意識」——自知身處「現在」,並以回憶與期待串連成完整生命布幕。
明慧,你還記得我們年輕時那次激烈的爭論嗎?那時我們為了一個哲學問題爭得面紅耳赤,甚至一度冷戰。在當時,我認為那是我們友誼的危機;但現在回想起來,那次爭論實際上深化了我們的友誼,讓我們更加了解彼此的思想深度。這就是卡爾所說的敘事重構——同樣的事件,在不同的時間點,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自傳書寫者面臨兩個根本陷阱:連貫性不足,即生活事件缺乏有意義的連結;以及過度連貫,即對不同經驗強加人為的統一性。尋求連貫性等同於重寫故事,使敘事認同成為一個積極的、持續的過程,而不是被發現的真理。這個視角將年老從被動的衰落轉變為積極的創意綜合。
我發現,在我的七十多年人生中,我一直在不自覺地進行這種「自傳重寫」。年輕時的挫折,中年的迷茫,年老時的流亡,現在都成了我生命故事中不可或缺的章節。它們不再是痛苦的回憶,而是智慧的來源。
時間意識與存在的深度
卡爾的現象學方法特別強調,作為有意識的存在,我們與無生命的物體(比如一張椅子)的根本區別在於我們的時間意識。我們不僅存在於當下,更重要的是,我們意識到我們的存在,意識到過去和未來。這種時間意識在年老階段變得特別深刻。我們的記憶中承載著幾十年的人生經歷,我們的期望中包含著對剩餘時光的安排。但是,明慧,這裡有一個深刻的悖論:雖然我們的未來在客觀上越來越短,但我們對生命的理解卻越來越深。
每一個當下的經驗都是從未來湧現並註定要加入過去。每一個經驗的瞬間都預示著一個將來,而這個將來本身也會成為當下經驗的瞬間。這就是我們存在的時間性本質。在年老,我們對這種時間性有了更深的體會。我常常在黃昏時分坐在窗前,看著外面的世界慢慢沉入夜色。這個時候,我會感受到一種奇妙的時間感:過去的回憶如潮水般湧來,未來的不確定性如薄霧般瀰漫,而當下的這一刻卻如此清晰、如此珍貴。這就是年老帶給我們的時間智慧。
卡爾強調,我們的出生不是我們能記住的事情,我們的死亡也不是我們能最終體驗的經歷。但是,我們確實意識到出生和死亡。它們是事實,我們可以說我們知道它們,但我們對它們的意識超越了這一點。我們並不會想著它們;大部分時候我們不會。它們也不是我們會時不時被提醒的事實。它們模糊地作為我們經驗的邊界而存在,而這些邊界之間的東西就是我們所稱的生命。
年老的敘事特權:從積極生活到沉思生活
卡爾的分析指出,年老涉及個人和創造性的方式來思考個體生活尺度上過去和未來之間的關係。晚年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來理解早期經驗,而對有限性的意識則塑造了對過去事件的詮釋和對未來可能性的構想。生活經驗的積累允許越來越精緻的自傳推理形式,使年老本身成為一種敘事過程。
明慧,卡爾一個深刻的洞察:在年老階段,我們可以說是從「積極生活」(vita activa)逐漸轉向「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這不是因為我們變得懶惰或無能,而是因為我們獲得了一種新的自由——不再需要證明自己,不再需要追求外在的成就,而可以專注於內在的反思和理解。這種轉變給了我們一種特殊的敘事特權。我們有時間,也有經驗,去重新審視我們的整個人生。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年輕時看不到的模式,理解那些當時無法理解的事件意義。我們可以將看似混亂的人生經歷整合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
在生命的意義上,生命周期的規模或許保持不變,但推進的當下和不斷增長的過去將焦點從待活的生命轉向已活過的生命。這也可以被視為從積極生活到沉思生活的漸進轉變,只要是在越來越少的時間來實現變化計劃的意義上。但當我們接近終點時,雖然越來越少的東西可以改變,但越來越多的東西可以重新詮釋。這就是我們年老人的優勢:我們有更多的材料可用於卡爾所說的「意義創造」操作,即試圖形成一個關於自己生命的連貫敘事的自傳反思。雖然「理解生命」可能不是最高價值,但至少在這裡可以說我們有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善。
死亡哲學的思辨與接受
明慧,過去幾十年我花了不少時間去讀書和反思死亡這個課題,即將完成《死亡與年老哲學》一書,2025年底出版。我不怕死,這不是虛言,而是經過深刻哲學思辨後的結論。
從柏拉圖開始,西方哲學就將哲學與死亡緊密相連。柏拉圖在《斐多篇》中記錄蘇格拉底的話:「真正的哲學家為他們的信念而死,死亡對他們來說根本不足以引起恐慌」。西塞羅也說:「哲學家的整個生活,就是對死亡的默想」。蒙田更進一步指出:「哲學化就是學會死亡」。這些古代智者都認為,死亡的思考是哲學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但是,死亡究竟是什麼?維根斯坦說得很精確:「死不是人生的一個事件。人不可能體驗死」。這句話蘊含著深刻的哲學洞察。從主觀的角度看,我們永遠不會經歷死亡,因為當死亡到來時,「我」已經不存在了。這看似矛盾,實則揭示了存在的雙重性:客觀上我們必死,主觀上我們永遠活著。死亡是「我的死亡」、「我的有限性」,是存在問題而非理論問題。正因如此,我們才需要哲學思辨來理解這個悖論。
智慧傳統中的老年與死亡準備
斯多葛哲學和中國哲學傳統都為有意義的年老和死亡準備提供了深刻的資源,強調接受而非抗拒自然過程。斯多葛方法圍繞控制的二分法——專注於可以影響的事物(思想、態度、美德)而不是不能影響的事物(身體衰退、死亡時機)。
塞內卡 (Seneca, 4BCE-65CE)的洞察是,老年應該被珍惜,因為「如果一個人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充滿了快樂」,這體現了這種方法。老年人的斯多葛實踐包括每日死亡反思、將每一天視為「獎勵」、接受身體衰退同時培養內在美德。斯多葛派區分疼痛(不可避免)和痛苦(我們對疼痛的反應),表明即使身體衰弱,心理能力仍可保持敏銳以培養美德。塞內卡在《論人生之短暫》中寫道:「生命的長短不在於時間,而在於我們如何運用它」。他說:「我們不是時間太少,而是浪費太多」。這些古代斯多葛學派的智慧,在我們今天仍然適用。生命的意義不在長度,而在深度和廣度。
中國哲學傳統通過互補的視角來看待老年。儒家思想將年老視為「終生道德朝聖的頂峰」,在這裡積累的學習和道德發展使長者成為智慧的寶庫。道家強調自然轉化和無為,接受不可避免的事物而不是與自然過程作鬥爭。佛教方法認識到老年是基本的苦,同時通過理解無常和培養平等心來提供解脫。
這些傳統在幾個關鍵洞察上匯聚:智慧通過積累經驗自然地隨年齡發展;減少執著允許專注於精神發展;時間視角增強當下時刻的欣賞;長者在向年輕一代傳遞智慧方面扮演關鍵角色。我特別被莊子的一個故事所感動。莊子在妻子去世時,惠子發現他在敲盆唱歌,感到震驚。莊子解釋說,他意識到死亡只是自然變化的一部分,就像季節的變化一樣。這種對死亡的接受不是冷漠,而是智慧。
(待續)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