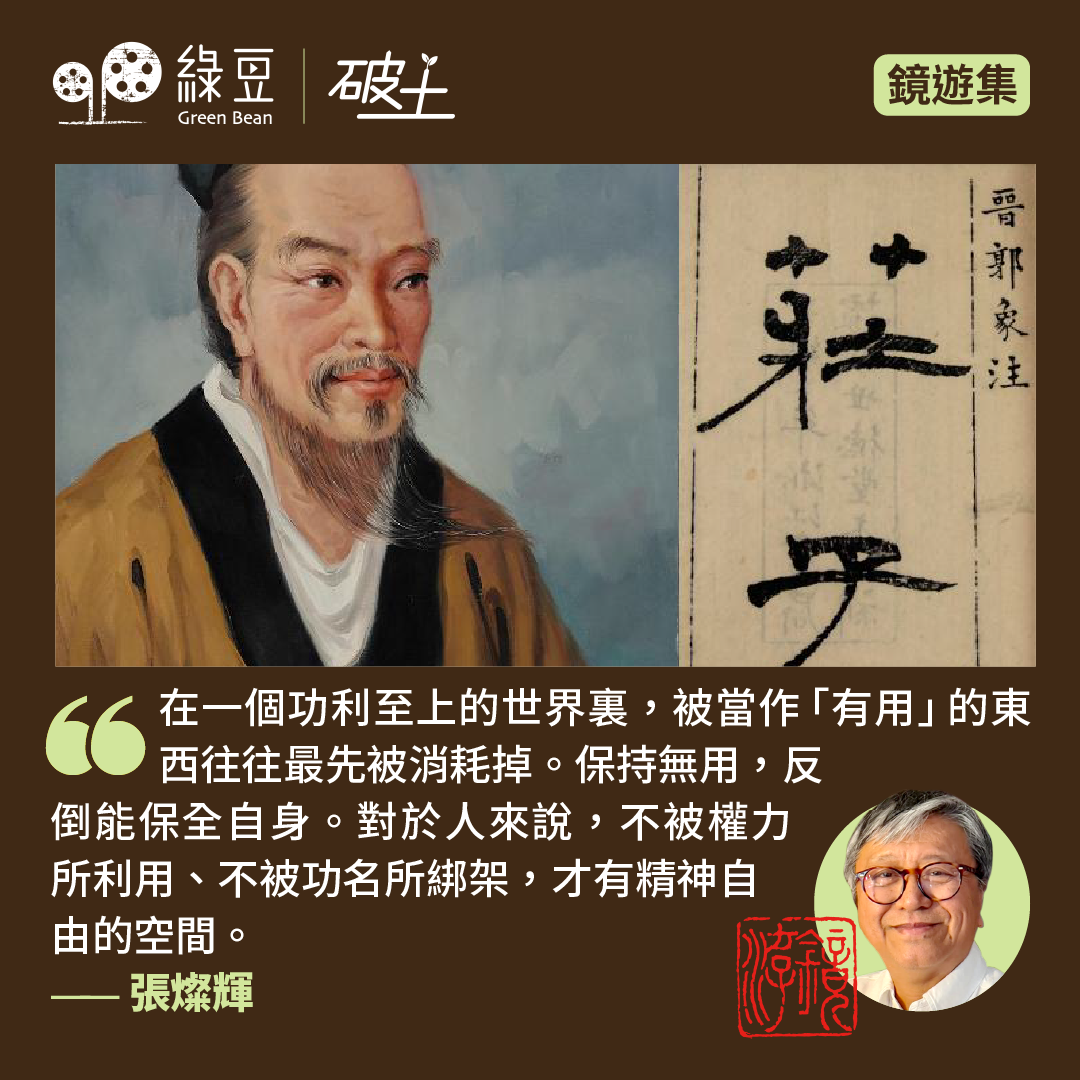《奧德賽》中的成長、返鄉與堅守 (下篇)

《重讀經典:與人文和自然對話》
佩涅洛佩的堅守——智慧與忠誠的化身
困境中的抵抗
在《奧德賽》(Odyssey)的敘事中,佩涅洛佩(Penelope)大部分時間沒有出現在冒險的場景中,但她是整個故事的精神核心。她的處境極其艱難:作為奧德修斯(Odysseus)的妻子,她必須保持對丈夫的忠誠;作為伊薩卡(Ithaca)的王后,她需要維持某種政治平衡;作為母親,她要保護兒子不受傷害。這三重身份使她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
一百零八位求婚者的壓力日益增大。他們霸佔王宮、揮霍財產、威脅兒子特勒馬科斯(Telemachus)的生命。佩涅洛佩沒有軍隊、沒有武力,在古希臘社會中作為女性也缺乏公共權力。然而她用自己的方式進行了長達二十年的抵抗,展現出不亞於丈夫的智慧和堅韌。
最著名的是織布的詭計。她告訴求婚者,必須等她為奧德修斯的父親拉厄爾特斯 (Laertes)織完壽衣,才會選擇新的丈夫。然而她白天織布,夜晚又偷偷拆掉,如此持續了三年,直到被侍女出賣。這個情節充滿深刻的象徵意義。編織在古希臘文化中是典型的女性活動,象徵著女性的智慧和美德。但佩涅洛佩的編織卻具有顛覆性——她不是在創造,而是在拖延;不是在完成,而是在拆解。她的織布機成為了抵抗的工具,她用女性的傳統技藝來對抗男性的求婚壓力。這種巧妙的抵抗方式展現了她與丈夫奧德修斯相似的智慧——不是正面對抗無法戰勝的力量,而是使用計謀來爭取時間。
等待中的煎熬與信念
佩涅洛佩的堅守不僅需要智慧,更需要非凡的信念。二十年是漫長的歲月,期間無數流浪者帶來關於奧德修斯的各種消息,有的說他死了,有的說他還活著,每一次希望都帶來更深的失望。她必須在完全不確定的情況下堅持等待,這種精神上的磨難或許比奧德修斯的海上冒險更加煎熬。
當偽裝成乞丐的奧德修斯終於與她對話時,她已經習慣了不相信。這個陌生人聲稱見過她的丈夫,預言他即將歸來,但佩涅洛佩只是悲傷地回應:太多流浪者為了得到款待而撒謊,她已經學會不再輕信。然而,她仍然善待這個乞丐,命令老奶媽為他洗腳——這種待客之道本身就體現了她對奧德修斯價值觀的堅守。
當她聽到乞丐詳細描述奧德修斯當年穿的衣服時,史詩用美麗的比喻描繪她的情感:「就像雪在高山之巔融化——東風融化了西風帶來的雪,雪融化後河流滿溢——佩涅洛佩美麗的臉頰就這樣被眼淚融化。」(卷十九,204-209行)堅冰之下仍有溫柔,二十年的等待沒有使她的心變硬。
床的秘密——最後的考驗與相認
復仇完成後,奧德修斯清理了血跡,洗浴更衣,在雅典娜的幫助下恢復了英俊的外貌。但佩涅洛佩仍然不敢相信。她沉默地坐在對面,仔細審視這個男人,內心充滿矛盾。特勒馬科斯責備她為什麼不擁抱歷經千辛萬苦回家的丈夫,但奧德修斯理解妻子的謹慎。
然後佩涅洛佩設置了最後的考驗。她假裝命令僕人將主臥的床搬到外面,這激起了奧德修斯的強烈反應。他憤怒地描述了那張床的秘密:它是圍繞一棵活的橄欖樹建造的,床柱就是樹幹本身,是不可能移動的。只有真正的奧德修斯才知道這個秘密,因為只有他親手建造了這張床。
這個考驗是佩涅洛佩智慧的最高展現。她沒有被外表或故事所欺騙,而是找到了一個只有真正的丈夫才能回答的問題。床的象徵意義深遠——它代表著他們婚姻的基礎,穩固、不可移動、深深扎根於土地。橄欖樹是雅典娜的神聖植物,象徵著和平與神的祝福。床圍繞活樹而建,意味著這段婚姻是有生命的、成長的,與土地和家園緊密相連。
當佩涅洛佩聽到這個答案時,她的膝蓋和心都軟了。史詩用另一個美麗的比喻描述她的感受:「就像陸地對於游泳者來說是可愛的,當波塞冬在海上用風浪摧毀他們的船,少數人游過灰色的海浪逃到岸上,他們的身體結滿鹽殼,但他們高興地踏上陸地——她的丈夫對她來說就是如此可愛。」這個比喻將佩涅洛佩比作遭遇海難後終於上岸的水手,而奧德修斯就是她的陸地和安全。具有深刻諷刺意味的是,奧德修斯本人就是那個在海上遭遇無數災難的人。現在,夫妻終於團聚,他們都從漫長的漂泊和等待中得到了拯救。
《奧德賽》的永恆意義
《奧德賽》探討了許多永恆的主題:家庭與歸屬、忠誠與背叛、智慧與力量、人性與神性。它提出了深刻的問題:什麼使一個地方成為家?什麼使一個人保持身份?如何在苦難中保持尊嚴?如何在誘惑面前堅守信念?如何在勝利後保持節制?
史詩給出的答案是複雜而富有啟發性的。家不僅是物理空間,更是關係和記憶的網絡;身份不是固定的,而是通過行動和選擇不斷建構的;尊嚴來自內在的原則,而非外在的地位;信念需要智慧和謀略來維護,而不僅僅是激情和衝動;節制是真正力量的標誌,因為只有強者才能選擇不使用自己的力量。
在所有這些主題中,最核心的是人性的價值。《奧德賽》歌頌的不是神祇般的力量或不朽的生命,而是人類的智慧、情感、責任和選擇。奧德修斯拒絕卡呂普索(Calypso)的不朽,選擇回到會衰老、會死亡的妻子身邊;阿喀琉斯在冥界後悔自己對榮譽的追求,寧願活在地上作為最卑微的人;佩涅洛佩用二十年的等待證明,忠誠和希望是比任何物質財富更寶貴的東西。
特勒馬科斯的成長故事告訴我們,成熟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而是通過一系列的考驗、失敗和學習逐漸實現的;奧德修斯的返鄉之路告訴我們,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從不犯錯的人,而是那些能夠從錯誤中學習、在苦難中成長的人;佩涅洛佩的堅守告訴我們,忠誠不是被動的等待,而是主動的抵抗和選擇。
荷馬通過《奧德賽》告訴我們,真正的英雄主義不是征服世界或獲得不朽,而是在有限的生命中實現自己的價值,履行自己的責任,愛護自己所愛的人,並最終找到回家的路。這個信息在兩千八百年後的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因為每個人都是某種意義上的奧德修斯,都在尋找回家的路,都在人生的旅程中面對各種誘惑和考驗,都在努力成為更好的自己。
《奧德賽》的結局是和解與和平,但它也暗示著新的開始。忒瑞西阿斯 (Tiresias)的預言表明,奧德修斯的旅程並未真正結束,他還將再次出發,帶著船槳走到不知海洋的地方。生命本身就是一場永不停止的旅程,每一次歸來都是下一次出發的準備。但無論走多遠,家永遠在那裡等待,成為我們存在的意義和行動的方向。
這就是荷馬留給西方文明最寶貴的遺產: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對家庭的珍視,對智慧與勇氣的歌頌,以及對生命有限性的坦然接受。兩千八百年來,每一代讀者都在《奧德賽》中找到自己的倒影,都在奧德修斯、特勒馬科斯和佩涅洛佩的故事中獲得啟發。這部偉大的史詩不僅是文學的源頭,更是理解人類處境的永恆指南。
《奧德賽》對現代世界的啟示——跨越時空的人生課題
身份認同與歸屬感:全球化時代的「回家」問題
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人口流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數以億計的人離開故土,成為移民、難民、流亡者或跨國工作者。對於這些現代的「奧德修斯」們來說,《奧德賽》所探討的核心問題——什麼是家?如何在漂泊中保持身份?——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奧德修斯拒絕卡呂普索的不朽誘惑,選擇回到貧瘠的伊薩卡,這個選擇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真理:家不僅僅是物理空間,更是關係、記憶和責任的網絡。在現代社會,許多人身處異鄉,享受著比故鄉更優越的物質條件,卻仍然感到一種深層的失落和渴望。這種「鄉愁」不是對某個地點的懷念,而是對歸屬感和完整身份的追求。
《奧德賽》還提醒我們,身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通過行動和選擇不斷建構的。奧德修斯在漫長的旅途中經歷了無數變化,但他始終記得自己是誰、來自哪裡、要回到哪裡去。這種對根源的堅持,與對新經歷的開放態度之間的平衡,正是現代人在多元文化環境中需要學習的智慧。
香港流亡者的《奧德賽》——有家與無家的悖論
對於2019年後離散世界各地的香港人來說,《奧德賽》不再只是一部古老的文學經典,而是一面照見自身處境的鏡子。然而,香港流亡者的經驗與奧德修斯的故事之間,既有深刻的共鳴,也存在令人心碎的差異。
奧德修斯的苦難在於他「無法」回家——波塞冬的詛咒、海上的風暴、女妖的誘惑,種種阻礙使他的歸途延長了十年。但他始終知道,伊薩卡還在那裡,佩涅洛佩還在等待,只要他堅持下去,終有一天能夠踏上故土。這種確定性是他苦難中的希望之錨。然而,香港流亡者面對的是一種更加弔詭的處境:家還在那裡——維多利亞港的輪廓沒有改變,太平山的剪影依舊,街道的名字仍然熟悉——但那個「家」已經不再是離開時的那個家了。這不是物理上的阻隔,而是本質上的斷裂。
這就是有家與無家的悖論:香港人並非沒有故鄉,故鄉卻已面目全非。奧德修斯的伊薩卡被求婚者佔據,但他可以通過復仇來恢復秩序;香港的改變卻是結構性的、法律性的、不可逆轉的。流亡者即使回去,面對的也不是可以驅逐的入侵者,而是一整套新的規則、新的禁忌、新的沉默。在這個意義上,香港流亡者比奧德修斯更加無家可歸——他們的家沒有消失,卻已經不再是家。
這種處境產生了一種獨特的鄉愁:不是對一個地方的思念,而是對一段時間的哀悼。流亡者懷念的不是香港這個地理座標,而是那個曾經存在、如今已經逝去的香港——那個可以自由言說的香港,那個六月四號晚上燭光不滅的香港,那個書店裡擺滿禁書的香港。這個香港已經成為記憶中的城邦,如同特洛伊陷落後只存在於歌謠之中。從這個角度看,每一個香港流亡者都是倖存的特洛伊人,攜帶著城邦的記憶在異鄉漂泊。
然而,《奧德賽》也為這種困境提供了某種啟示。奧德修斯在卡呂普索島上拒絕不朽的誘惑,選擇回到會衰老、會死亡的人間生活。他的選擇不是基於伊薩卡比俄癸吉亞更美好——事實恰恰相反——而是基於一種更深層的認知:意義不在於環境的完美,而在於那是「自己的」生活。對香港流亡者而言,這個洞見可以轉化為另一種理解:家的意義或許不在於能否物理性地回歸,而在於如何在心靈深處守護那個家的本質。
佩涅洛佩的形象對留守香港的人同樣具有啟示。她在重重壓力下用織布的方式進行無聲的抵抗——白天織、夜晚拆,在服從的表象下保持內心的忠誠。這種「弱者的武器」、這種以時間換取空間的策略、這種在沉默中堅守的姿態,正是許多香港人當下的寫照。他們無法像奧德修斯那樣張弓搭箭,但可以像佩涅洛佩那樣,在看似順服的表面下,保存記憶、傳遞火種、等待某種可能的轉機。
流亡本身也可以成為一種特殊的生存方式。先知忒瑞西阿斯在冥界告訴奧德修斯,即使回到家鄉、完成復仇,他的旅程仍未結束。他必須扛著船槳走向內陸,走到一個不認識大海的地方,在那裡向波塞冬獻祭,然後才能獲得真正的安寧。這個預言暗示著,奧德修斯的身份已經永遠被漂泊所標記,他無法回到那個從未離開過的天真狀態。同樣地,香港流亡者也許需要接受:無論最終身在何處,他們已經被這段經歷永遠改變。流亡不是生命的中斷,而是生命的另一種形態。
在異鄉建立新生活的過程中,流亡者面臨著身份的重新建構。奧德修斯在漫長的旅途中反覆被問及「你是誰」,他的回答方式隨著情境而變化——有時是「無人」,有時是克里特的商人,有時才是伊薩卡的國王。這種身份的流動性不是虛偽,而是生存的智慧。香港流亡者在英國、在台灣、在加拿大、在世界各地,也需要學習這種彈性:在新的環境中重新定義自己,同時不忘記自己從何而來。
最終,《奧德賽》教給我們的或許是:家不僅是一個可以回去的地方,更是一種可以攜帶的東西。奧德修斯之所以能在二十年的漂泊中保持自我,是因為他心中始終有伊薩卡 —— 不是作為地理位置,而是作為意義的座標。香港流亡者攜帶的,是一座已經沉沒的城市的記憶,是一種已經消逝的生活方式的回聲,是一個或許永遠無法實現的承諾。但正是這些東西,使他們在異鄉仍然是香港人,使流散各地的個體仍然構成一個共同體。
有一天,也許會有人像荷馬一樣,把這一代香港人的漂泊與堅守寫成史詩。在那部史詩裡,會有無數的奧德修斯在海上掙扎、無數的佩涅洛佩在沉默中抵抗、無數的特勒馬科斯在父輩缺席的世界裡尋找自己的路。而《奧德賽》這部來自近三千年前的古老詩篇,將繼續為這些現代的漂泊者提供慰藉和指引——不是因為它許諾了一個圓滿的結局,而是因為它見證了人類在失去與尋找之間那永恆的掙扎,並且告訴我們:這掙扎本身,就是人之為人的尊嚴所在。
結語:永恆的漂泊者與永恆的歸途
《奧德賽》的智慧在於,它沒有簡單地將誘惑描繪為邪惡的。卡呂普索真心愛著奧德修斯,她提供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瑟茜最終成為奧德修斯的幫助者;甚至塞壬的知識誘惑也具有某種崇高性。這種複雜性使史詩遠遠超越了簡單的道德寓言,成為對人類處境的深刻沉思。
每個人都是某種意義上的奧德修斯,都在人生的海洋上航行,尋找回家的路;每個人也都是特勒馬科斯,在成長的道路上尋找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每個人還可能是佩涅洛佩,在等待和堅守中展現忠誠和智慧。
荷馬的偉大在於,他用詩歌的形式將這些普遍的人類經驗提升到了藝術的高度,使之成為永恆的典範。閱讀他的作品,我們不僅獲得審美的愉悅,更獲得人生的智慧。這就是經典的意義 —— 它們不是博物館中的陳列品,而是活生生的對話夥伴,幫助我們理解自己,面對世界,走向未來。
後記:
本文對《奧德賽》的討論,僅是最初步的介紹,離開真正理解荷馬這部偉大史詩的深度和廣度,還有很長的距離。荷馬研究是西方古典學中最古老、最豐富的領域之一,兩千多年來積累了浩如煙海的學術文獻。
(筆者按:因篇幅問題,文中註釋和參考資料暫不放在內,留待在實體書中補上。)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