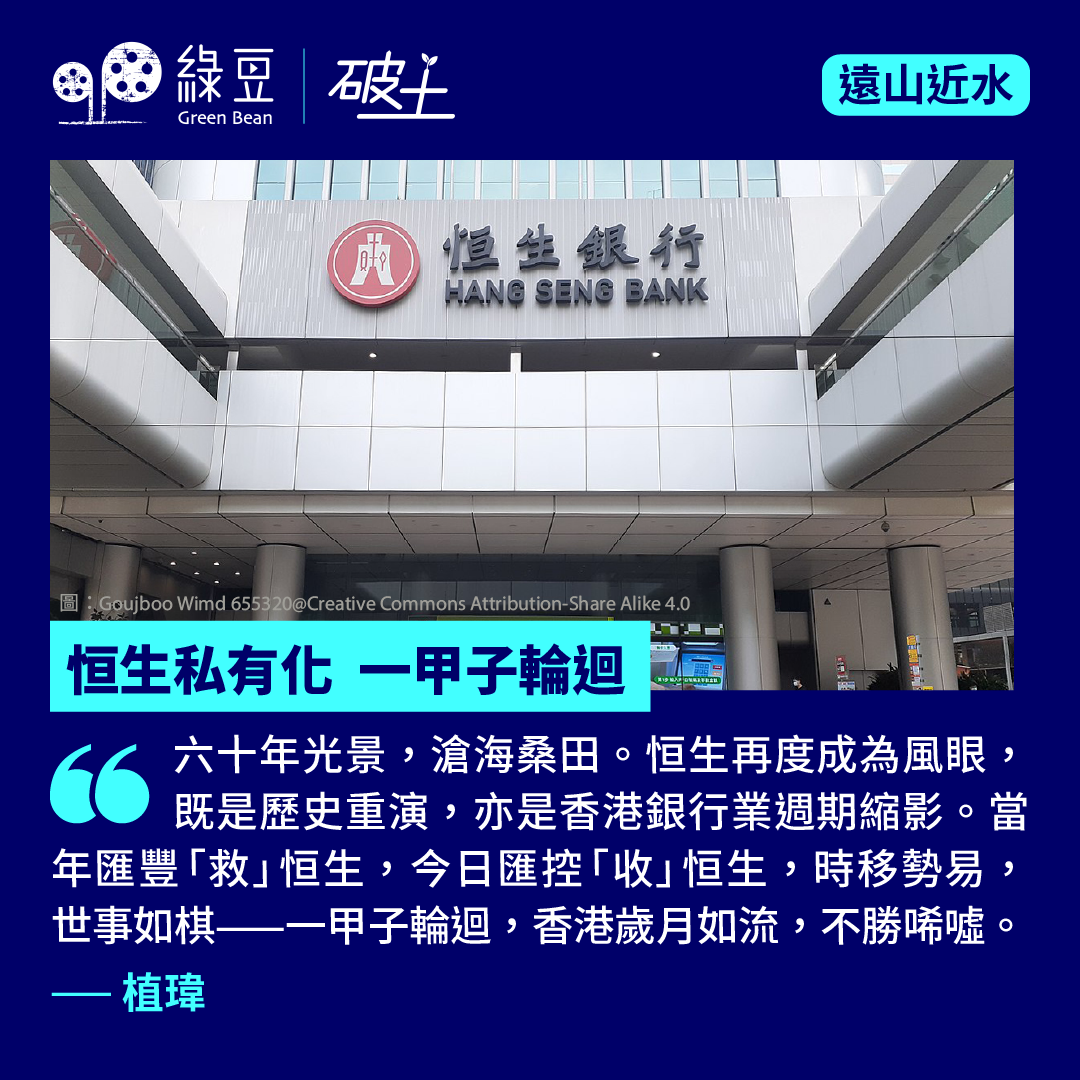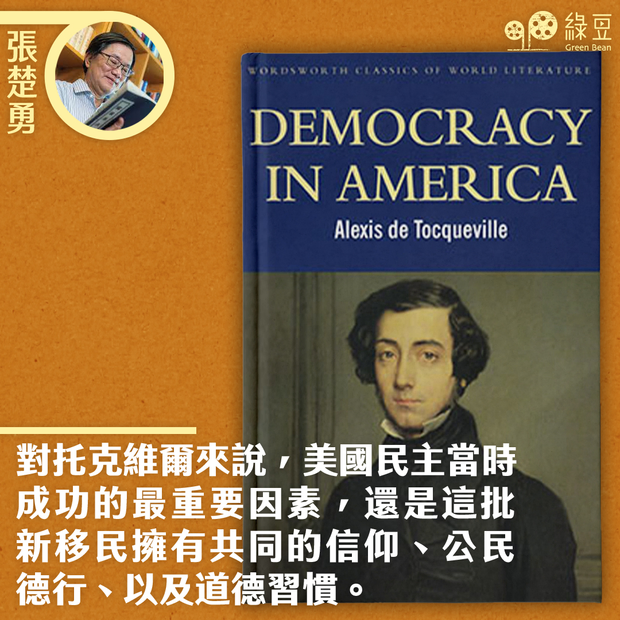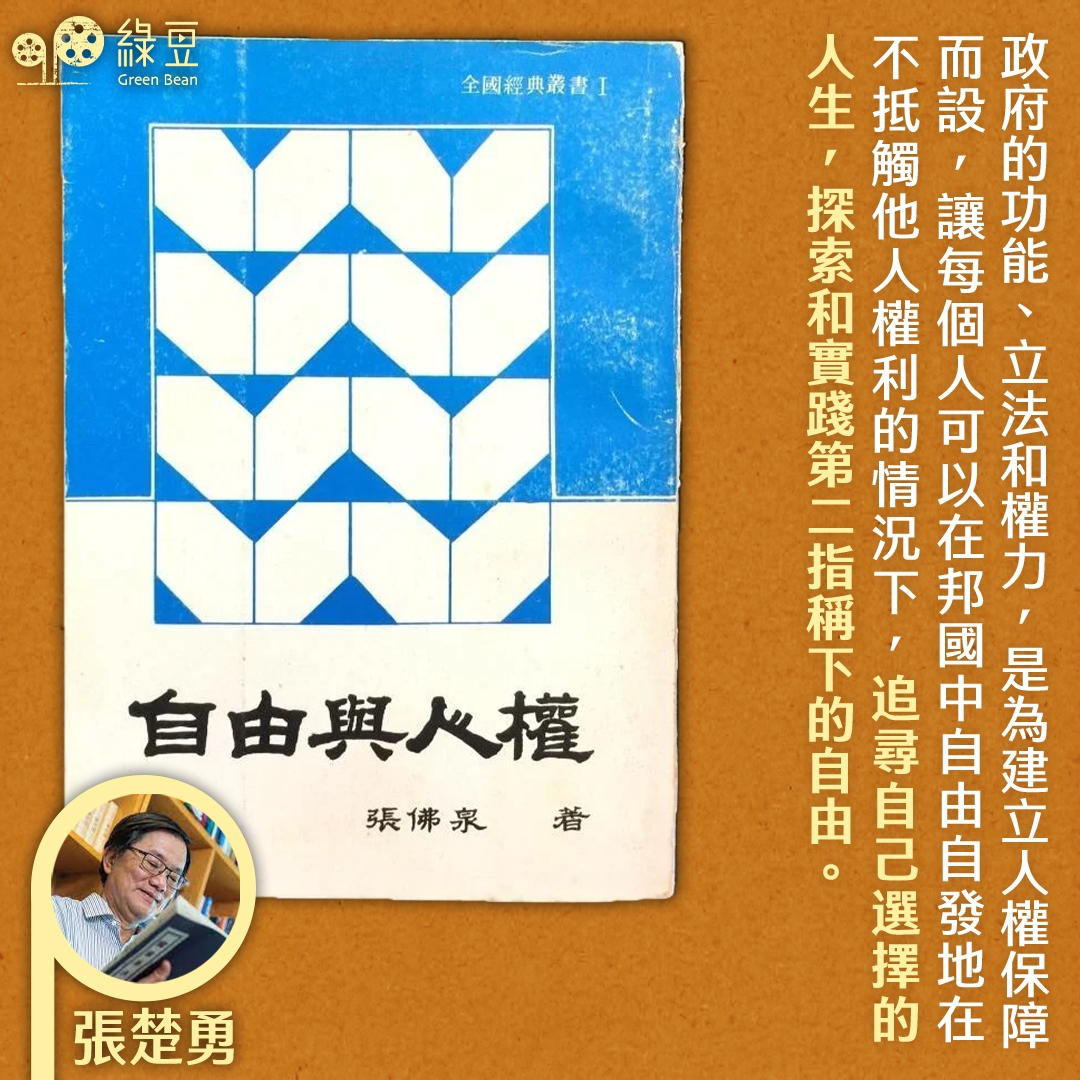世道紛亂:「敵人」與有限政治

我在上一篇〈世道紛亂:政治上的「敵、友」思考〉一文中說,施密特認為「敵、友」的界定,是邦國政道中最根本的政治決斷。如果從這個理論視野看今天紛亂的世局,對全球蒼生影響最全面的潛在「敵、友」分野,顯然是美、中目前在全球爭雄的競爭格局。有些論者認為,世界已經處於第二度冷戰的年代。
大國進行全球爭雄
一般對冷戰的理解,是核武超級大國進行全球爭雄,在關鍵地區通過代理人式的局部戰爭和衝突進行對峙的一種格局。核武的存在,使核戰一旦爆發,交戰各方將無一倖免,出現全面互毀文明的一種結局。因此,在核武年代,超級大國的理性爭鬥,便得通過戰略上關鍵的局部代理人式的戰爭和衝突,逐一挫敗敵方,以達致主導全球稱雄的局面。
如果美、中已處於冷戰,那麼,目前在烏克蘭的軍事衝突便是冷戰時期的典型代理人式的局部戰爭。其他關鍵的潛在爭鬥熱點,包括了台灣、朝鮮半島、南海等處。兩國在南太平洋島國和非洲諸國的外交競爭,也可以理解為雙方全球對峙的伸延。香港雖然是中國主權下的特別行政區,但因為種種原因,在1997年後很長的一段時期,是中國境內實質控制地區中最受西方價值影響,最容易局部挑戰中國黨國體制的一個國際大都會,因此也就成了美、中全球競爭的一個半熱點。
上述的分析雖然不無道理,但也有論者似乎還未認為世界已經第二度進入冷戰。基辛格在今年5月20日《經濟學人》的訪談中說,他認為目前中國的體制是儒家式的多於馬列式的。他說,中國決意要強大崛起,並不願意受制於二戰以來,美國主導的、以西方標準建立起來的「規則為本」的國際秩序。但他相信,中國不會像希特拉般要控制世界。
基辛格的判斷可能對,也可能錯。但他也看到,美、中雙方對對方的敵視和日益強硬的立場,正在威脅到彼此的和平共存,因此他同意,美國要加強軍備,以阻嚇戰爭爆發。
兩意識形態爭持
回到施密特的法理政治思想。他那「敵、友」的分野、政治決斷的論述,會如何看待今天的美、中競爭呢?首先,我想大概沒有太大爭議的一個分析,就是美、中兩國已把對方確定為是己方的首要假想敵,這假想敵威脅著本國的核心政治價值和利益。
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美、中的爭鬥可以理解成是繼蘇聯解體後,自由憲政的民主制和專政獨裁的黨國制的第二回合爭持。只是這個改良版的黨國制,在吸收了市場經濟的優勢後,變得比從前斯大林的黨國制難應付得多,特別是西方的民主制在經歷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和民粹政治的狂飆後,歐美邦國對自己的政經體制的信心已不如以前。加上中國開放改革後已成為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一部分,使雙方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壁壘分明,同時混集著經濟、貿易、金融上的難解難分,使這種「敵、友」關係,變得比先前的冷戰複雜得多。
正是這個意識形態上的壁壘分明,使美、中在這場全球爭雄的競爭中,儘管經貿金融上雙方格局難解難分,卻都付不起敗給對方的代價。試想如果美國不能阻止民主的台灣被中國大陸強行統一,美國對亞太和西方盟國的「軍事保護傘」承諾將會蕩然難存。與此同時,美國在世(特別是亞太區)的主導地位,難免在形勢上被中國取代。人們對自由民主制的信心,也自然大打折扣。同樣道理,西方不能坐視烏克蘭敗於俄國,正如中國不能讓普京政權崩潰,因為俄國落敗的結果,既使中國更難與美國爭雄,又失去一大制衡西方的屏障,大大加強美國對中國的直接威脅。
「敵、友」(起碼是假想敵)的論斷既然已經確立,那是否代表世界難免爆發第三次大戰呢?
儘管目前的局面是嚴峻的,但基辛格認為,世界還有5至10年的時間,通過有效和有遠見的政治領導和努力,使美、中雙方在其矛盾熱點上加強相互了解,務實地嘗試減少猜疑,增加互信,並建立雙方能接受的避免競爭和衝突升級的共同機制和規範,以期能達到均衡共存。
界定當中誰是「敵人」
曾經支持納粹德國,以「敵、友」關係為政道核心主軸的施密特,是否一個不斷製造政敵,並要把「敵人」趕盡殺絕,以致控制全局的思想家呢?以我對施密特法理政治思想的理解,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下這結論的理由,是建基於我對施密特關於「敵人」這概念的認識。
以「敵、友」關係為政道核心的思想,自然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善治式的思想大相逕庭。施密特提醒我們,常規憲政之外,在現實環境中,政治社群難免要應付非常態政治的挑戰。政治社群所作出的政治決斷,既是常規憲政的前提,也是面對危機或常規政治不能應付的挑戰時,不能不做的事,必要時甚至要作出生死攸關的交戰決斷,界定當中誰是「敵人」,誰是盟友。
但是,對施密特來說,政治上甚至戰爭中的「敵我」關係,並非是「漢賊不兩立」的。政治上和戰爭中的「敵人」,是就具體的分歧、紛爭、衝突而界定出來的。要解決或平息有關矛盾,國邦有時不惜訴諸戰爭,但當衝突平息後,曾經敵對的國邦還是可以繼續並立。
「敵我」雙方如果非要把對方趕盡殺絕,那便不再是只限定在政治領域或戰爭中的「敵我」關係,而是一種全面、抽象、無邊際的敵對關係。這關係除了把敵人完全殲滅或征服之外,在任何其他情況下,這敵對關係都不可能化解。如果是這樣,這種無邊際的絕對敵對關係的界定,是某種教條信仰的後果,這和必須審時度勢的政治決斷是相違背的。
大地和海洋兩種不同政治空間
不同的政治空間和秩序從法理角度來看,這種趕盡殺絕的做法,已不再把敵人當作是對等的人看待,也不承認敵國是擁有對等主權的國邦。這種對政治、公權不設限定的做法,施密特是不以為然的。因此,在《戰爭論著》(Writings on War)一書中,施密特說:「戰爭的公義、榮譽、價值,正是繫於敵人既非海盗,也不是集團罪犯這一事實上。實際上,敵人是個『國邦』,是一個『受國際法管轄的成員。』」(War owed its justice, honor, and worth to the fact that the enemy was neither a irate nor a gangster, but rather a ‘state’ and a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aw.)
施密特在他的《大地與海洋:世界史的一種沉思》(Land and Sea: A World-Historical Meditation)中,認為在現代政治裡,大地和海洋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空間和秩序。這本書在二戰時寫成,當中的論述或有過時的地方,但對了解施密特的法理政治觀,我認為還是有參考價值。在書中,他提到自16、17世紀起,歐洲大陸便分別出現了主權並立,劃地為界的眾多國邦;反之在茫茫大海,卻是政治邊界闕如,缺乏相互承認的一種法權狀況。
因此,施密特認為,在陸地發生戰爭,交戰各方都是主權國,屬國際法規管下的國邦關係。戰場上打仗的,是國邦的軍人,一般平民,除非參與戰鬥,否則應該既不成為軍事目標,也非戰爭敵人。海戰的邏輯卻大不相同。公海中軍事襲擊商船和民用船隻,以及向敵人的口岸進行不分軍事目標和不理平民死活的海面全線封鎖,卻是習以為常的事。因此,海戰是一種難有限定的狀態。施密特在《大地與海洋》一書中還說,通過海戰崛起的海上霸權,在過去三數百年間,在新大陸不斷侵佔擴張,並完全無視當地土著作為人的權益。他又認為,英美通過海上稱雄展現出的全球霸業和主導一統傾向,對世界局面是有潛在危險的。我相信這些危險,便是施密特所說的無邊際政治的泛濫和以普世標準之名實行國際政治單一化的壟斷。
政治上文明與野蠻之分野
與此同時,他在《游擊武裝理論》(The Theory of the Partisan) 一書中也說,儘管列寧和毛澤東把革命游擊戰爭的理論和實踐推到極致,但他們同時也把革命中的敵我關係全民化和絕對化,使到任何潛在的他者,一轉念便成為了絕對的敵人。因此,施密特在該書結束時警告說: 「否定了敵人是實實在在的話,將會是為趕盡殺絕一個絕對的敵人的做法,掃清了障礙。」(It is the denial of real enemy that will clear the way for the work of annihilation of an absolute enemy.)
施密特並不欣賞自由民主制。他雖然批評希特拉二戰時在征服了德國西面的敵人後繼續出兵攻打蘇聯,是無節制的殲滅性意識形態之戰,但他從1933年起對納粹德國總體的正面政治判斷,使很多人認為,他是極權政治的支持者。特別是在屠殺和反猶太人一事上,施密特的態度更多受質疑。因此,不少論者認為,施密特的法理政治思想是危險的。施密特曾經支持納粹是不容否認的。但光從理論觀點分析,我還是傾向認為,他的法理政治論述,可以理解成在理念上是支持有限政治,認為不管哪類模式的政治制度,如果走向極端,失去節制和限定,把政治上和戰爭中的「敵人」,變成是絕對而全面的敵人,將會帶來政治秩序的災難和崩潰。
也許,政治上的文明與野蠻之別,正在於後者是沒有節制,前者卻必須懂得自制。有節制的有限政治,可能有不同的存在形式,但都是人類社群和國際秩序的基礎。面臨第二度冷戰威脅的當今世局,敵友各方如何對今天的政局,作出有節制而有效的決斷,將是影響億萬蒼生的頭等大事。在此如果稍有差遲,後果將會是災難滅絕性的。
▌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