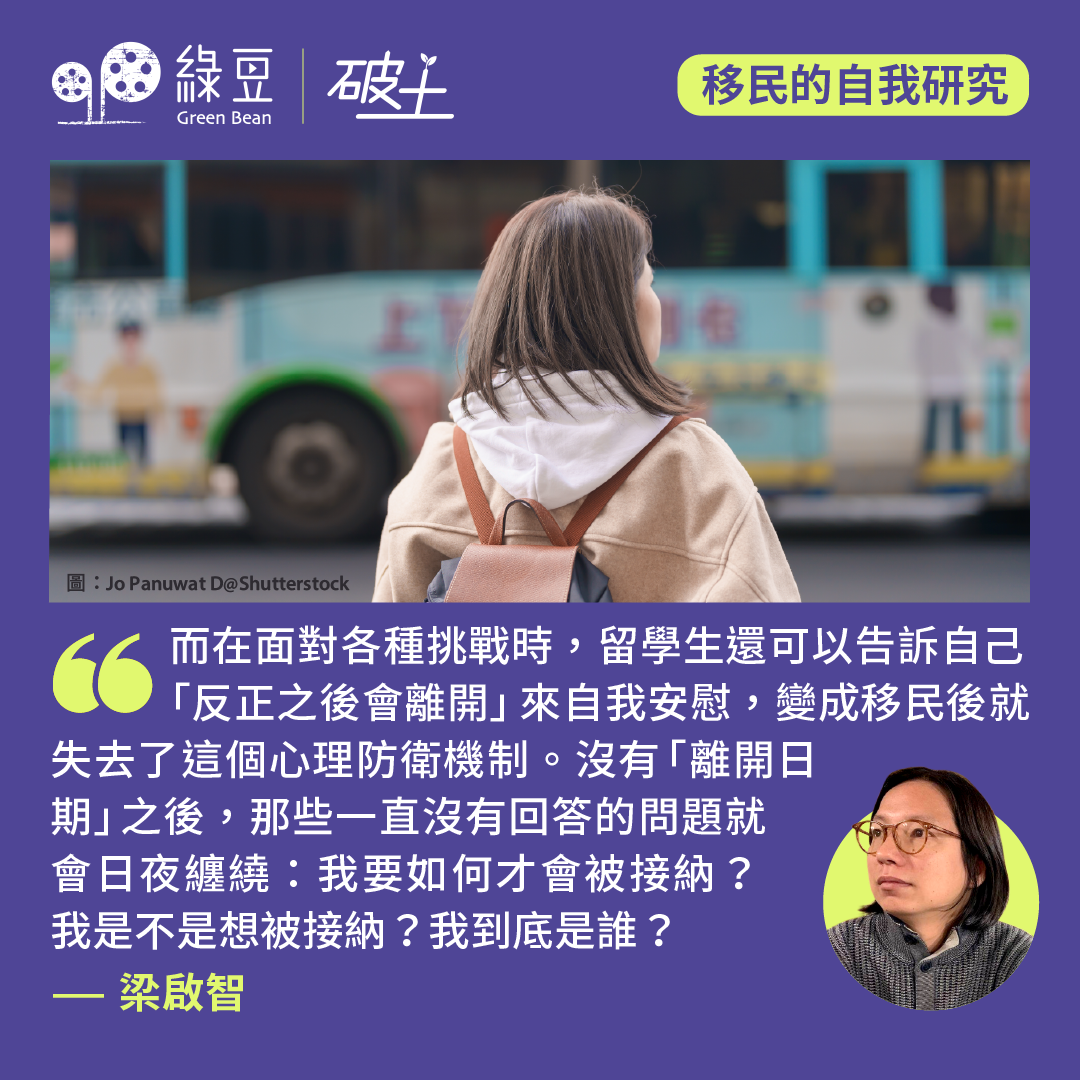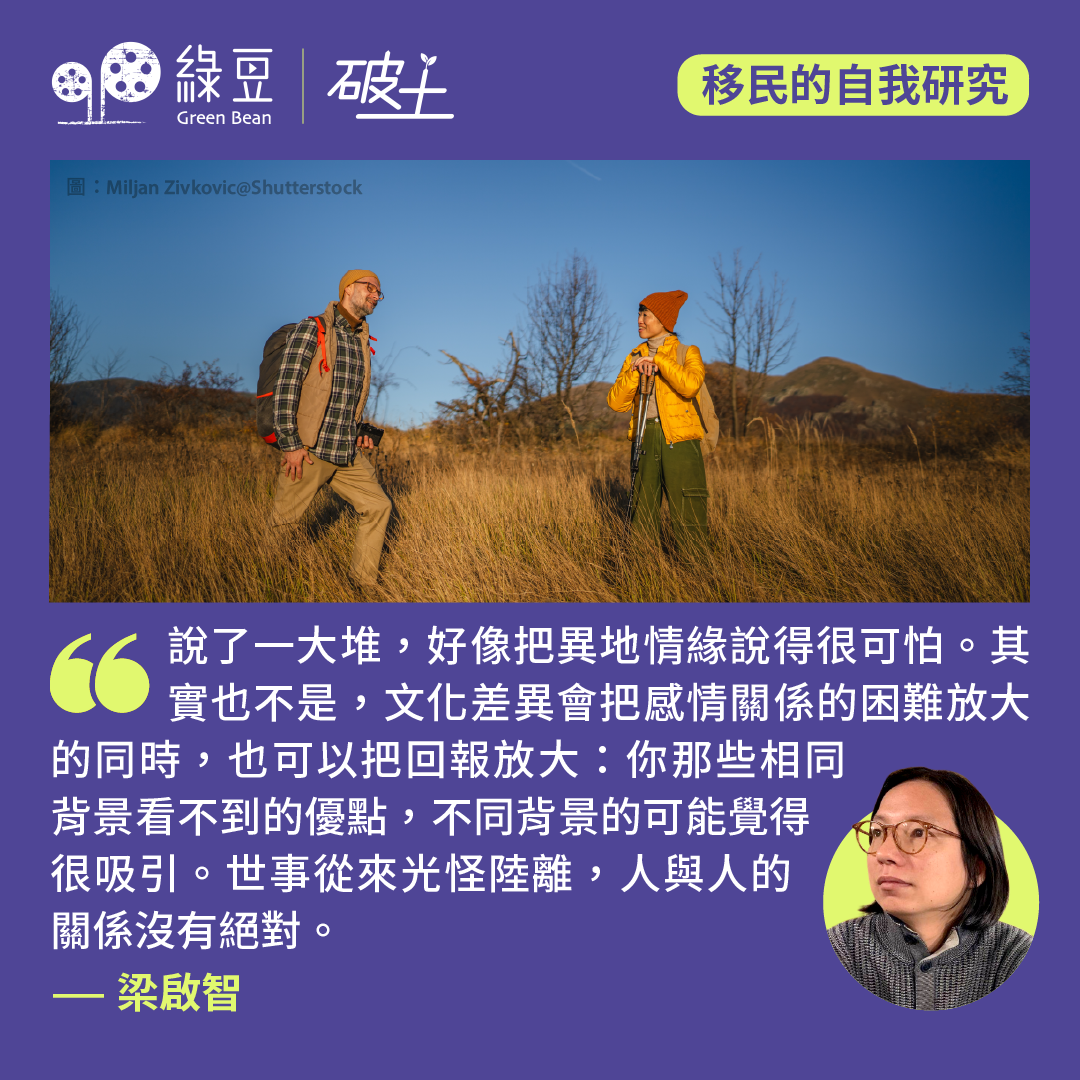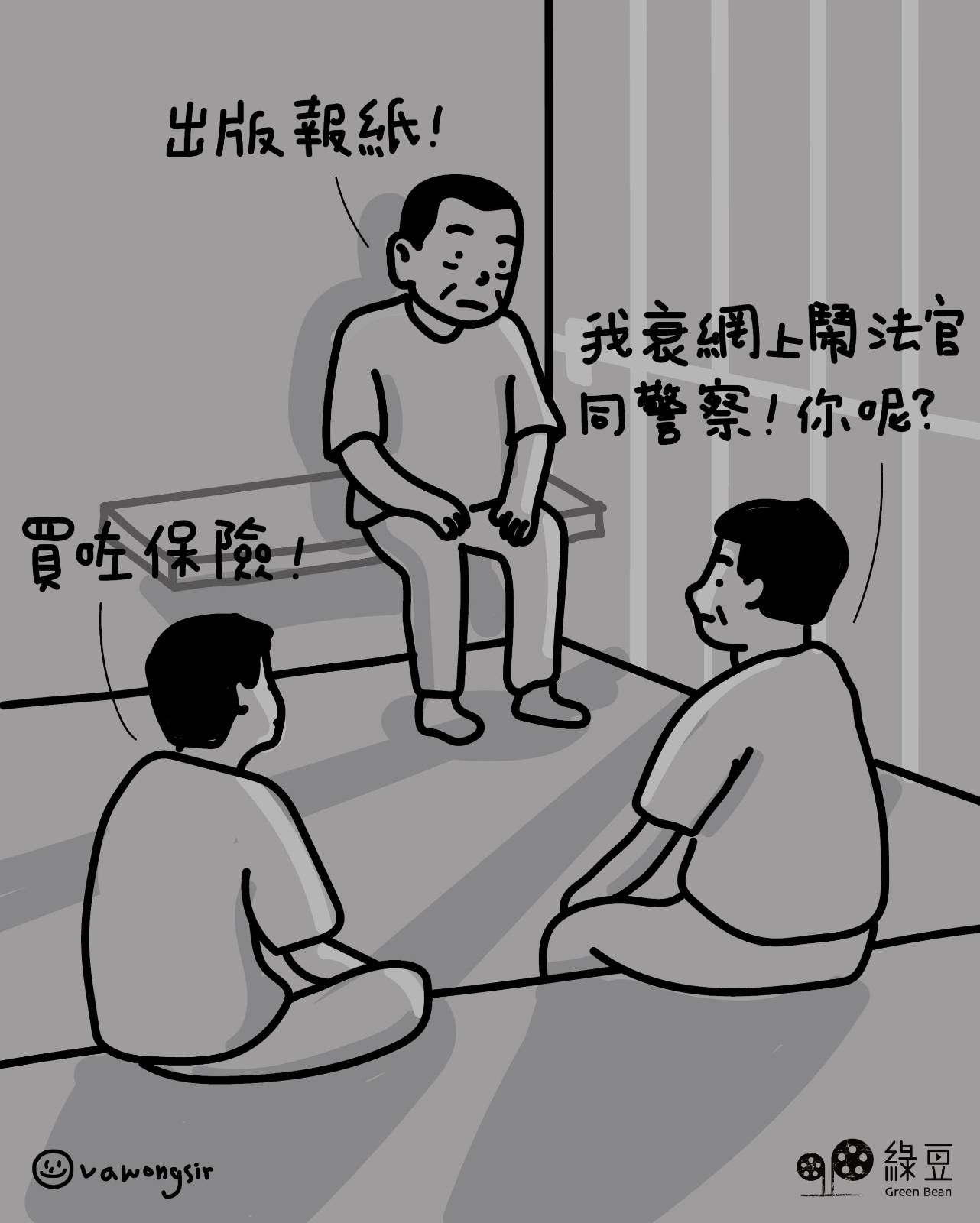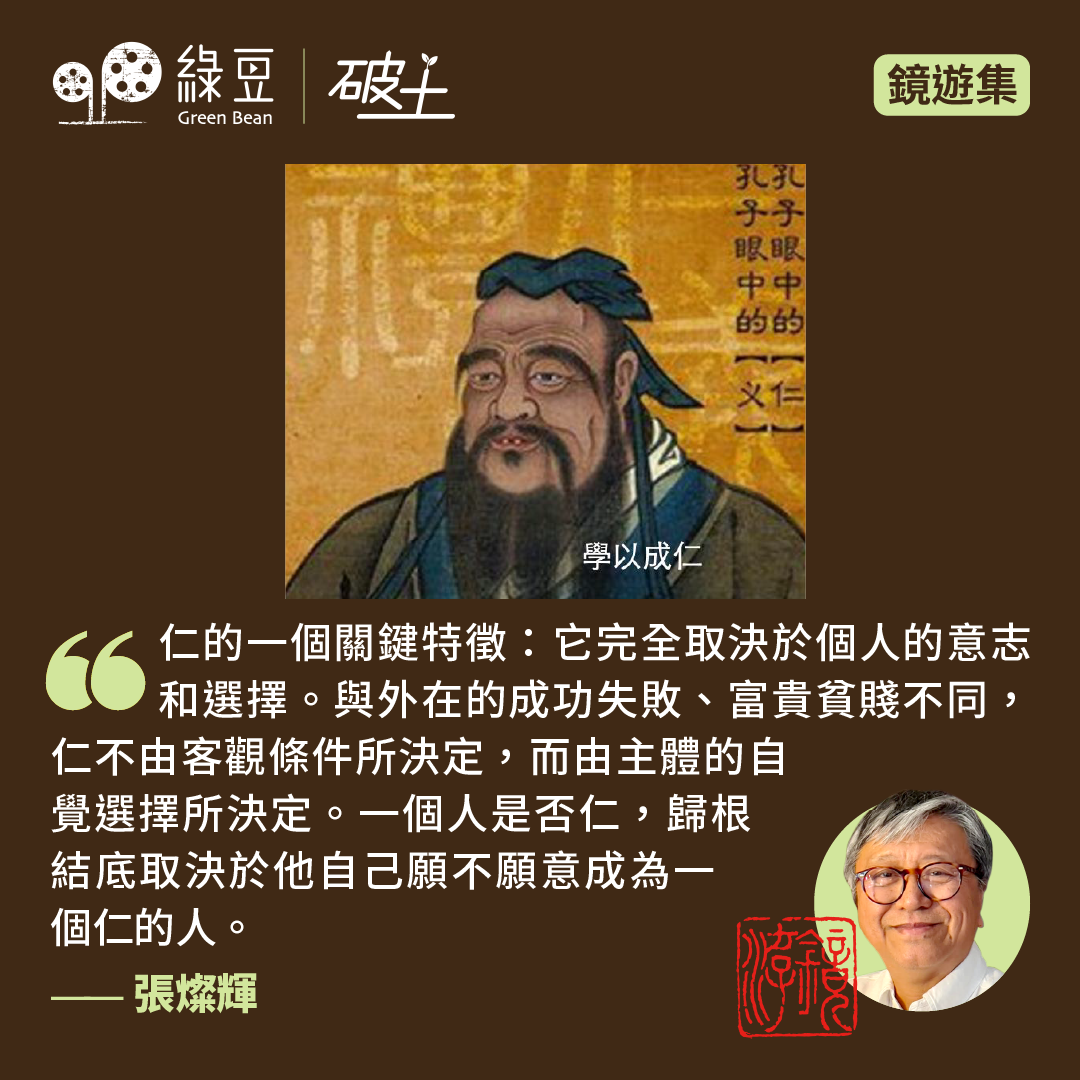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要求選民登記必須提供有效的美國公民身份證明。這項議案雖然在眾議院通過,但在民主黨反對之下,預期在參議院將無望闖關。對於許多香港人來說,投票要看身份證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對於美國會有這麼多人反對此項議案感到不明所以。其實在美國,相關的爭議由來已久,背後的邏輯和香港的情況也大相逕庭,很容易產生誤解。 法案背後 要求選民證明公民身份,言下之意就是擔心非公民會混進去投票,從而左右選舉結果。實際上,這件事情存在嗎?北卡羅萊納州在2016年選舉的審計當中,翻查選民名冊中480萬票的已投票紀錄,當中只有41票是由非公民所投。在往後八年,僅三宗個案被送檢控。在其他州份的類似審計當中,找到的案例都是個位數。這也不難理解:大多數移民最怕的事情就是被遣返,誰會為了選舉中百萬分之一的影響力去犯法,危及自己日後的入籍申請? 調查發現,大多數的非公民選民登記,都是工作人員不小心作業所造成:法例規定政府要協助申請駕照者順道完成選民登記,但不是所有申請駕照者都是公民,人有錯手之下便有少數非公民被登記了,根本不是什麼陰謀。這不是說選舉舞弊不能發生,有美國人甚至曾經成功為一隻狗登記選民,關鍵在於它能否成為普遍現象,左右選舉結果。 說到底,還是有些政治人物輸不起,輸了選舉便散播謠言說有數以十萬計的非公民投票,妄稱選舉不公。當政治壓力形成,議會便不得不立法去處理這個現實上不存在的問題。這些為了一己私利去破壞制度信任的行為,才是我們要譴責的對象。 類似的「不存在的問題」,還有所謂的冒充選民問題:會不會選民登記的資料是真的,但去投票的那個人是假的?因為美國的投票站往往不看身份證,選民自稱是誰就可以領選票,在許多香港人的眼中也是貌似兒戲。現實上,和上面說的情況一樣,也是十分難以發生。首先,你要知道某一名字是在選民登記冊之上;然後,你要確保你比真的那個人更早到達投票站,因為如果對方已經投票,甚至就排隊站在你前面,那你就會當場被捕。而同樣是,你只有一次機會,影響力百萬分之一。當然你可以不停去不同的投票站排隊投票來增加影響力,但投票日的時間限制不站在你的一邊;你也可以動員親戚朋友和你一起做這件事,但被揭發的風險同時倍增。 另一種選舉不公平...
回想起來,應該大概是一年前某次在赤峰街喝酒的時候,知道沐羽要寫在台港人移民群像。當時聽他說到其中一章的內容,已經覺得嘩嘩嘩不得了。今年書展,《代代》終於出版,第一時間課金支持,一晚看完。沐羽很稱職地為這一波移民潮的離散文學立下了典範。套用書中的說法,他有為離散港人社群「做啲嘢」。 得釐清,我是說沐羽對離散港人社群的描述很成功,不是說沐羽描述了離散港人社群的成功。2019年的港人抗爭精神換來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注視;但都2026年了,還繼續寫堅毅不屈承傳意志未免流於淺薄。現實的離散生活不是每天在想如何有朝一日光復舊地,更多時候的種種混帳糾纏甚至是遇人不淑;世上無聖人,香港人也不例外,革命熱情退卻後總要回到現實,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代代》所寫的,更多是離散下的種種荒謬。 離散社群中的各種光怪陸離 小說的設定場景是台北的一家港式茶餐廳,各篇的主角有老闆也有茶客,有金主也有伙記,有大學教授也有小學生。要寫在台港人移民群像,我首先想到的是《台北人》,也就是六十年代白先勇筆下隨著國民政府逃難而來的外省人;但半世紀後的香港人明顯有另一個樣貌,沐羽筆下的創作的「鴻記」,更讓我想起的是《18樓C座》的周記茶餐廳:在最尋常的場景,對世情提出最啜核的疑問。 沐羽說他是把《代代》想像成諷刺漫畫來寫的,身為讀者得說這部小說首先娛樂性甚高,笑到肚痛。部分原因,大概是因為自己也是在台港人移民的一分子,難免會在小說一眾角色當中找到認識的身影;畢竟就連我們在中央研究院辦的香港資料庫,也被轉化成為小說橋段之一。出版社大可以在書封加上一句:本故事純屬虛構,但如有雷同卻絕非巧合。相反,它很深刻地繪畫了離散社群中的各種光怪陸離;正如陳健民教授在書首介紹詞所述,讓人笑中有淚。 也不用真的去猜書中一眾角色的「真身」是誰。其一是「真身」可以多於一個,角色性格人設看來都是揉合而成;其二是人物本身不是重點,他們所代表的情感才是。例如茶餐廳的金主要出版回憶錄,最後變成滯銷倉底貨,那種不合時宜的自戀,我在台灣、在英國,在各地的離散社群都見過太多次。又例如流亡手足戰戰兢兢到東京的中國大使館換領特區護照,過程中的內心患得患失跌宕反省與自責,同樣是年輕尋求庇護者的必經心路歷程。 誠實地書寫離散...
最近因為工作關係,收到一些香港來台留學生的履歷。從香港移民來台灣,留學是其中一種方法,雖然這樣路現在已不太好走。認識不少通過留學移民的年輕人,在轉換身份的過程中都遇都不少問題。從留學到移民,不是一條純粹的直行路。 留學生算是移民嗎?如果放在傳統意義下對移民作為單向遷移的理解,那就當然不算。但現實往往複雜很多,很多時候出國留學的那一刻沒有想過要在當地留下來,結果因緣際會,可能是找到喜歡的工作,可能是有異地姻緣,也就誤打誤撞留下來了。反過來,也有不少人一開始就想移民,留學是其跳板:香港就有不少中國大陸的學生是這樣留下來的;也有不少香港人因政治因素需要離港,而來台留學對他們來說是最容易的方式,儘管他們本來並無意欲留學。 對未來的想像 從留學變成移民,身份轉變會帶來時間觀的改變。留學是暫時的,你知道自己有回去的一天,於是很多影響比較長遠的決定都不會做,最起碼不會為住處添置大件傢俱,最好一個皮箱隨時來去自如。決定留下來了,不再是數年內便會離開,道理上就可以開始想得比較長遠。 只不過,時間觀在拉長的同時,也可以變得更不確定。身為一個學生,每日每月每年的作息是有清楚規劃的,時間往往可預期且被制度化:上課下課有時間表,學程有明確年限,未來被想像為「完成學業後再說」。一旦留下來了,除了開始要為以後的時間規劃,也要面對這個未來是何等的難以規劃。即使當了幾年的留學生,不等於就對當地的職場文化和不同業界的發展前途有任何認識,也沒有多少人可以依靠,剛畢業踏進社會的不安感比本地人更如浮萍。 然後是工作簽證的年限、居留資格的更新,還有移民政策的變動,使得生活規劃不再圍繞學期論文和考試的定時規律,而是被行政程序與政策風險所切割。你發現「原來一畢業才知,一世我也要考試」;只是這些考試不再有評分表和天書,酌情權全在移民官手上,你做足所有要求不等於你的申請會最快得到審批。 另一個時間觀改變的後果,是因為過去的居留被定義為是臨時的,無論是自我或外在對於融合的期望也會比較低。留學生通常被置於一個相對清楚、甚至受到保護的制度位置;因為位置是暫時的,邊緣性也被合理化。口語說得不好?沒所謂,留學生嘛;但身份變成移民後,期望就不一樣了:你既然要成為本地人,你就要變得像一個本地人。儘管正如本欄多次強調,「何謂本地人」從來沒有客觀標準可言。...
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近日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槍殺公民一事,再次掀起對美國移民政策的爭吵。很不幸,這一輪的爭吵和以往一樣,只見大量的稻草人和潑髒水,還原問題本質的討論卻往往欠奉。 相對於逐格重播槍擊現場的短片,爭論那不到半秒的雙方判斷,重點應是這場街頭執法本來就不該發生。美國的移民問題是不可能靠這種街頭執法解決的,背後是政治問題,而香港人都知道:政治問題要政治解決。現在的所謂執法只不過是一場又一場血淚推出來的表演,最終只是用來騙選票而已。 別誤會我,在把我套上各種標籤之前,我得先聲明我同意美國有嚴重的移民問題,其中無證移民的大量湧現對於守法申請的移民無疑是有所不公。我不是要求明天取消全球邊界,大家手牽手世界大同。我只是要指出如果我們真心想解決美國的移民問題,那些街頭執法明顯不是務實手段。 現實的問題 按ICE自己的統計,2024年會計年度共遣返了約27萬人;與此同時,估計美國有超過1400萬名無證移民。換言之,就算人數從明天開始如魔術一樣不再有任何新增,單靠抓的話,抓數十年也抓不完。而魔術當然不存在,還是會有新的入境;其中的問題並不限於美墨邊境地區,就算把圍牆蓋高十倍也不會解決問題,因為有近半的無證移民是以逾期居留的方式生活,入境的時候是合法的。 說來說去,這明顯不是一個單靠執法就可以解決的問題。至於現實的解決方式,本欄過去也寫過很多次:拿走他們前往美國的誘因,自然就不會來了。移民需要工作,美國需要廉價勞工,有需求就有供應;要解決問題,你願意嚴懲聘用無證移民的僱主,把財路斷掉就行。那麼為什麼不這樣做呢?兩個字:虛偽。美國約百分之五的勞工是無證移民,一下子把全國百分之五的勞工趕走,企業便要大幅加薪才能找到員工,之後便物價飛漲,執政黨就會完蛋。 故事其實是這樣的:經濟全球化之下,貧富懸殊日益加劇,民眾不滿無處宣洩,於是政客便找來無證移民來當出氣袋;但又不能真的把他們都趕走,於是便讓全副武裝的執法人員在街頭巷尾巡邏,聯同媒體表演幾場抓人的大戲來吸引注意。因為是演戲,實效是其次的,最重要是看起來嚴厲,各種錯亂執法因此而起:一次又一次合法移民甚至公民被抓,最近還搞出出錯抓美國原住民的鬧劇...
經歷數年的移民潮以後,明顯見到香港人離港趨緩。與此同時,也不時聽到移民回流的故事。媒體標題中各種「敗走」之說或是為了煽動情緒,但現實是此波數十萬人移民當中總不可能每個人都對移居後的生活感到滿足,失意時思考是否應該「止蝕離場」也是人之常情。 回看兩三年前針對移英港人社群的研究,絕大多數受訪者表示不會回流。現在看起來,這個比例或有高估之嫌。首先,此波移民潮是在香港發生巨大震盪之下產生的,對移居者的推力十分強大;與此同時,他們大多剛剛到埗,對英國生活的各種問題仍未有切身感受,即使遇上也因為蜜月期而視而不見。經過數年的心理調整,當初信誓旦旦說不會回流的,今天即使有了新的懷疑亦不應意外。 為什麼要移民 引用最古典的經濟模型,移民是為了得到某些好處,當到埗後得不到這些好處,或發現背後的成本增加至不能接受,便只好回頭是岸。這說法當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因為它假設了移居者本來就很知道移民的目的和成本是什麼,實際上完美信息和理性決策者在現實社會中都不存在。不過反過來說,我們也可藉此追問:那些沒有想清楚為什麼要移民,或移民前沒有「做好功課」的,到埗後的經歷會否特別困難,是否更容易產生回流的念頭。 舉個例,有朋友聲稱是為了下一代而移民,但這句說話後面是甚麼意思?是為了子女入讀世界排名更高的學校,還是為了更開放自由的學習環境?這兩個目標不一定完全重疊,如果最初的目標只是為前者,那得不到自然就會感到氣餒;後者卻是相對普遍,因而也不會那麼容易失望。推而廣之,如果移民的目的是為了物質生活(例如「住大屋」、「前園可以種花」),則恐怕更容易被日常生活中大小事務的不便所擊倒。最怕就是很多港人本來對前宗主國就有不切實際的美好幻想,到達英國後發現不如現實便處處都看不順眼。 回想以前在美國讀書遇到中國留學生,當時中國發展迅速機會處處,留學生群體都流行說如果僅僅是為了物質生活,其實不應該前來美國,留在中國前路更廣。但如果你追求的不是物質生活,而是無法在中國滿足的文化社會體驗,則明顯對回流與否會有不一樣的判斷。當然,現在香港的經濟情況相對於二十年前的中國差距甚遠,即使為了物質生活回流也得認真考慮自身行業的兩地前景,無謂「兩頭唔到岸」。 世上無樂土,有時移民或回流與否,選擇並非在於尋找最理想的環境,而是要避免最差的情況發生,又或者是在面對逆境時有尋求一定的自主權。聽過不少移民後的生活困難,無論是飲食習慣或是工作機會,甚至是制度歧視等結構性困難,或多或少可以通過自助或群體互助應對。那麼當初把你推離香港的那個理由,又是不是同樣可以應對的呢?只怕有些人一開始移民的時候也沒想清楚原因,現在應該回流與否也無法衡量。而這些人如果不先搞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甚麼,則移民或回流也不見得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隨離散港人在外地的生活逐漸穩定下來,間中也會遇到有朋友開展異地情緣。相對日常生活與工作的接觸,感情關係的建立是另一層次的跨文化交流。而因為這些關係往往更為深刻和不易建立與維繫,帶來的回報和傷害也同樣可以更大。學術界對異地情緣有不少有趣的研究,值得在此情感路上的港人參考自省。 「相見好同住難」的放大加強版 異地情緣有時在移民前就已發生,又或移民反過來是異地情緣發展出來的結果。常見的例子是獨旅期間在路上遇到浪漫對象,確定關係後不想一直維持長期遙距戀愛,便決定移居當地共組家庭。有台灣學者就研究香港女孩來台旅遊結識到對象,及後決定結婚依親移民來台的經驗,相對有趣。簡單來說,因異地情緣而依親移民,往往是「相見好同住難」的放大加強版。即使一般在相同文化背景中長大的情侶,同居結婚後也會因生活習慣而爭執,跨文化關係則更甚。 首先,在旅途中觸發的戀情,往往都基於心情放鬆和身在異地警戒性降低下發生,換句話說就是帶有嚴重粉紅濾鏡下看對方;一旦離開了放假的心情,期望落差隨之而來,泡沫就會爆破。泡沫爆破的原因多不勝數,有個人的也有外在的。例如不少香港女性比較追求獨立自主,來到台灣才發現丈夫是個未長大的「媽寶」,對方家人還預期婚後會一同居住,新抱要服侍老爺奶奶……結果女方隨即拔足而逃。研究者還遇過一些嫁到台灣鄉郊的案例,對方家人對香港一無所知,在刻版印象下還以為香港女孩是貪錢還是詐騙才來到台灣,弄得女方哭笑不得。 說到刻版印象,也別忘記這事情是雙向的。有些港男受流行文化荼毒太深,幻想日台女孩必然都是溫柔體貼,歐美女孩必然都是熱情自由開放,那就是大錯特錯自找麻煩。僅僅是歐洲,東歐相對於西歐、北歐相對於南歐,交往文化已是大為不同。東歐與南歐仍然有相當傳統的交往文化,其中家庭的角色相對較深。與此同時,如果有港男抱有男尊女卑的性別定型走去結識視兩性平等為理所當然的北歐女孩,恐怕是沒搞清楚狀況。 故事反過來也一樣,有些嚴重大男人主義的歐美男性特別喜好亞洲女性(有時會被批評為「黃熱病」(yellow fever)),後面往往是假定了亞洲女人比較溫順、女性化、不會頂嘴,甚至乎是比較傳統、好控制等。學術討論中,這種族裔偏好(如果不是族裔性癖)的後面往往與殖民和冷戰歷史相關,建構於想像中的種族性別階序之上,甚至是白人男性把族裔本身當成主要甚至唯一吸引力。如果有亞洲女性明知對方有此想法還要走進這種關係當中,就要當心伴隨而來的結構性不對等,甚至是剝削關係。...
大埔歷史性火難,死傷枕藉,相信很多身處海外的香港人和我一樣都會問自己:我能做些什麼?特別是看見留港的朋友奔赴現場,快速組織各種社區互助支援,身在千里之外獨自看著螢光幕,難免倍感無力,甚至質疑自己為何未能在關鍵時刻貢獻家園。這種情緒並不難理解,但海外港人不應因為不能一同搬運物資而感到氣餒,留港離港本來就有不同崗位,海外港人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還有很多。 超渡生人 首先,我們應正視災難之下對參與其中的渴望,本來就是正常人應有的反應,對社群亦可帶來正面作用。災難之可怕,在於把生命的不確定性赤裸裸的呈現在我們的眼前,而參與災難應對的其中一個作用,正正是重新建立自主性,找回效能感,避免陷入無力的漩渦,是重建信心的重要方式。套用黃子華的說法,「生人也要超渡」,而行動就是最實際的方式。 參與災難應對也可重建社會連結與互助支持,對抗創傷產生的孤立,帶來歸屬感與「一起面對」的情緒,有助撫平悲傷。當大家在互助中看見彼此,也有助情感的正常化與降低污名,鼓勵更多怕被看見的人站出來接受援助,讓更多人能被接住。最重要的,是參與帶來的社會連結,可以建立目的和強化集體韌性,甚至為未來作準備,最少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 在地不是唯一參與方式 以上的參與,有時會以在地的方式呈現,例如到災難現場獻花。有些社群體現的模式,也是通過在地參與連結呈現,廣福邨平台和大埔墟火車站的物資站是例證。但在網絡時代,在地參與不是唯一的參與模式,各種遙距參與的空間也被擴展出來。 在火災發生後,已立即見到許多海外港人自動補位,向世界各地的媒體推送詳細的背景信息,甚至接受身處當地的媒體採訪說明事發因由。很不幸,一開始的時候不少國際媒體把火災的原因連結到竹棚之上,沒看到維修工程本身已經歷了為時數年的各種爭議。這些媒體把觀眾的目光投到陌生和獵奇的角度,無疑是東方主義(如果不是種族主義)的潛意識投射,也說明了文化識讀的問題並非知識份子的無病呻吟或矯枉過正。幸好許多海外港人立即站出來,向這些媒體點出問題所在,報道角度也隨之有所調整。...
每隔一段時間,離散港人社群好像都會爭吵一次「香港已死」這題目。我理解為什麼很多人覺得這議題重要,畢竟它關係到社群本身的角色,例如各種對承傳香港文化和價值的想像。不過要討論香港到底是否已死,又或離散港人社群到底要承傳什麼,難免必先回答香港本身是或不是什麼。然而回頭再想,關於香港本質的爭議在離散港人這概念出現之前已經有過不止一次。如果把每次爭論都算進去,香港可能已經「死」了很多次,又或者已經輪迴轉世了很多次。 離散港人如持有「香港已死」的觀點,後面不少都預設了香港必然要有某些內容或特質,這個香港才有「資格」被稱為「香港」,否則就是虛有其表,行屍走肉。同一邏輯下,也聽過不少離散港人聲稱「要離開香港才能當香港人」,後面也是假設了香港不止是一個地理位置,而是一種實踐。 「什麼是香港」 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出發,「香港是什麼」向來是一條難解的問題,並在九七前後出現過好幾波的爭論。這些爭論往往是在香港面對挑戰的時刻出現,因為大家很擔心香港正在消失,所以覺得很有需要定義清楚「什麼是香港」,讓我們得以釐清要捍衛的是什麼,要排除的又是什麼。 例如2010年以來的本土思潮,當中有一些比較教條主義的訴求,曾經聲稱只有在香港出生的(甚至是只有在九七前的香港出生的)人方可被稱為是香港人。當然,這說法很快受到質疑,因為不少著名的本土思潮領袖,本身也是九七後在中國大陸出身,後來才移居到香港。 於是又有另一種聲音認為香港代表了一系列的制度和社會價值,例如法治精神和公民參與,要認同這些制度和社會價值才算是香港人。問題又來了:以前的選舉有最少四成選民會投票給不太捍衛這些制度和社會價值的政黨,他們又算不算香港人?這些制度和社會價值在香港的歷史也不是那麼長,不少最少要在1970年代之後才普及,那難道在此之前的香港就不是香港?更別說在「虛擬自由主義」的審視下,這些價值恐怕本來都甚為無根和脆弱,以此作為香港價值的標準是否有點兒戲? 過往的論述...
人在異鄉,常常會提到「各處鄉村各處例」這說法。不過具體來說,各地法例的細微分別,有時是要生活了一段日子才會慢慢發現。畢竟許多法例在日常生活不會觸碰,不容易發現和香港有所不同。然而這些法律上的分野,往往反映出兩地價值觀和歷史脈絡的不同。我在台灣的這些年間,曾無意中聽說不少我眼中的「奇怪法例」,也算是對這地方另一層面的深度認識。 先說明,這兒說的「奇怪法例」都是指有在實際執行和有日常意義的法律。世上有不少看起來很不可思議的法例都是過百年前留下來的規定,只是在條文上沒有被廢除,也沒有被執行。亦有不少只是被過度解讀,本身並不是那麼不合理。例如美國俄勒岡州有法例規定「不可以在墳場打獵」,聽起來好像很無聊,實際上還是有一定意義,只是很難想像會有人觸犯(捉鬼應該不算打獵吧)。 遺產特留分 我想到台灣的「奇怪法例」,許多看來都和家庭與性別有關。台灣同婚作為「亞洲第一」,我一直以為在家庭與性別範疇的法例都應該是十分進步的,後來才發現是我想得太多。台灣在這些方面原來很多時候都十分保守,同婚反而是一個例外。 第一個要介紹的例子,是「遺產特留分」。所謂特留分,是指繼承遺產的時候,必須保留一定比例給不同類別的繼承人,即使有預立遺囑也不得違反特留分規定的範圍。按現有規定,逝者的子女、父母、配偶之特留分為應繼分的二分之一;兄弟姊妹、祖父母則為三分之一。 舉個例,如果某逝者只有配偶和三位子女,在沒有遺囑的情況下,按應繼分計算,四人應平均分配遺產,即每人四分之一。那如果有預立遺囑,全部只分給其中一位子女可以嗎?不可以;最多只可以分得八分之五,其餘八分之三還是要分給另外三人,每人八分之一。很複雜嗎?我還未把兄弟姊妹和祖父母算進去呢。 這規定明顯限制逝者遺囑自由,更平添家庭矛盾與訴訟糾紛,猜想大概來自古舊的家庭責任思維。可幸最近有民間團體提議修法,先把兄弟姊妹的特留分取消,政府也答應明年啟動修法,算是為脫離舊觀念邁出了第一步。...
本欄一直強調移民是極為多元的社會過程,世上一方面沒有單一的移民經驗,而你是哪一種移民也不是你自己說了算,亦要看當地社會如何看。要見證移民經驗的多元性,我建議大家留意最近在台灣十分火熱的網上節目《中文怪物》。節目中的一百位參賽者都是移民到台灣的外地人,而且背景都不太一樣,撞出各種火花。 《中文怪物》是由來自法國的網紅「酷」所策劃的大型節目,召集了一百位在台灣生活的外國人比試中文能力,勝出者可獲三十萬台幣獎金。第一集在一個月前播出,至今已近五百萬收看次數,最後一集亦已在早前播出。這節目可以討論的地方有很多,本文集中討論當中反映的移民經驗。 首先得稱讚節目組在尋找參賽者時花了很多心思。一百名參賽者固然有不少來自觀眾熟悉的國家,例如美國、日本和南韓等,但也包括許多平常提到「外國人在台灣」的時候未必會想到的國家,例如印度、烏克蘭和波蘭,拉闊觀眾對外國人的印象。也有一些參賽者來自中華民國現時或曾經的邦交國,例如海地、斯威士蘭(Eswatini)和岡比亞(Republic of the Gambia),說明台灣對外關係的特殊性。 擴濶一般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