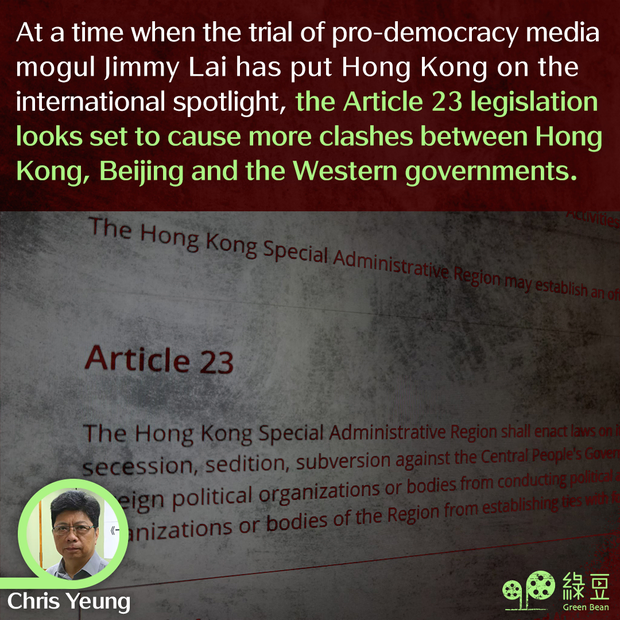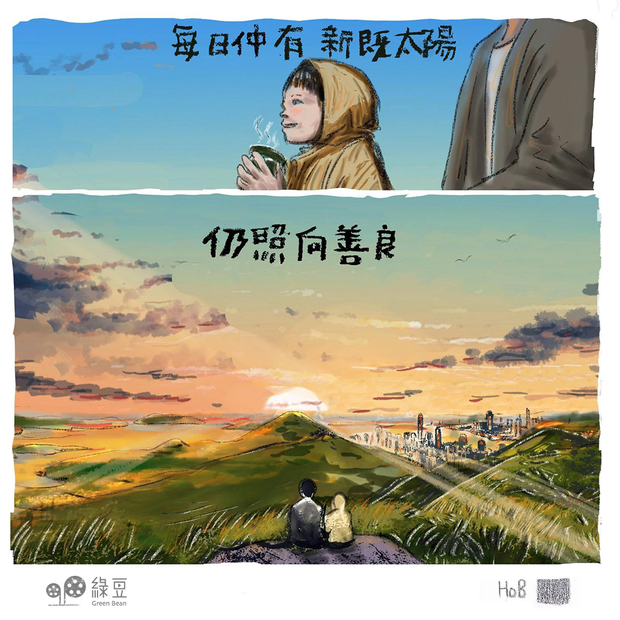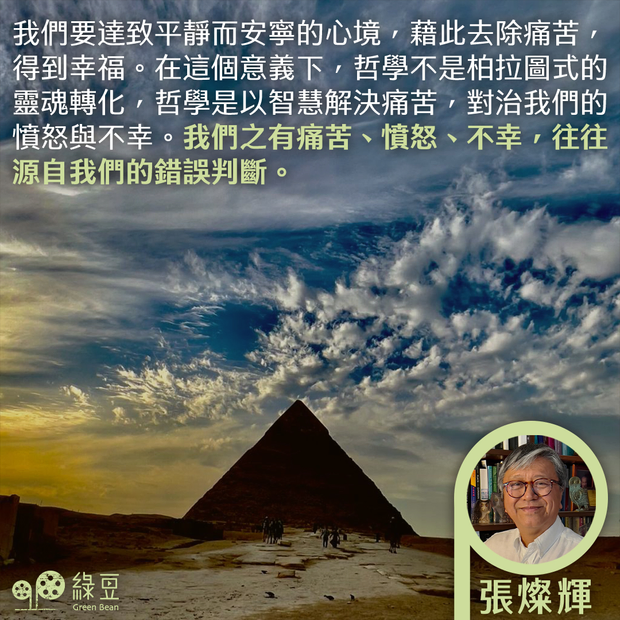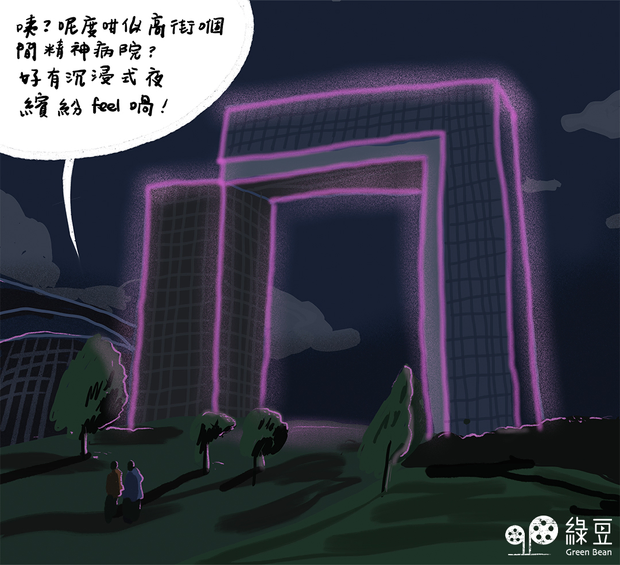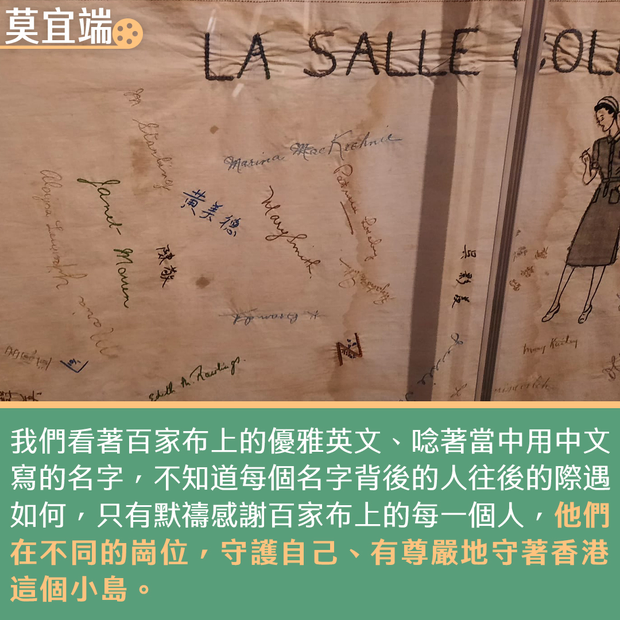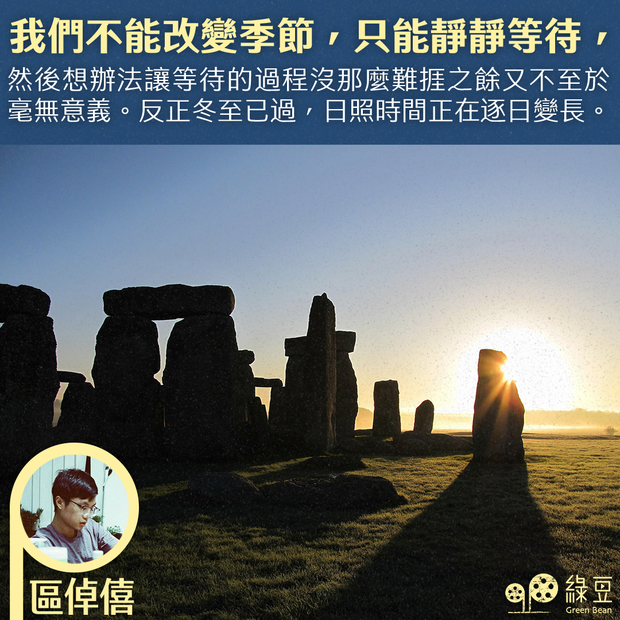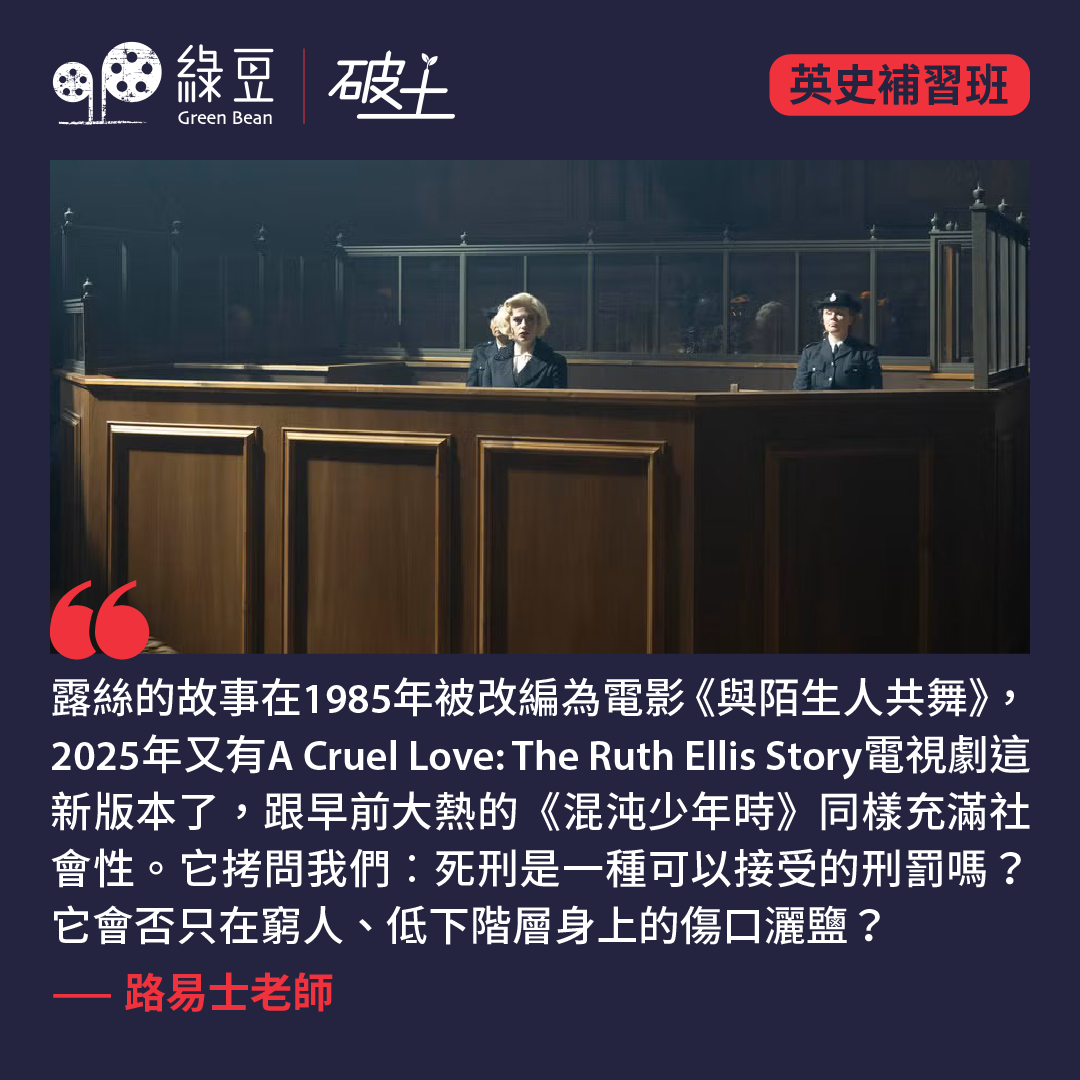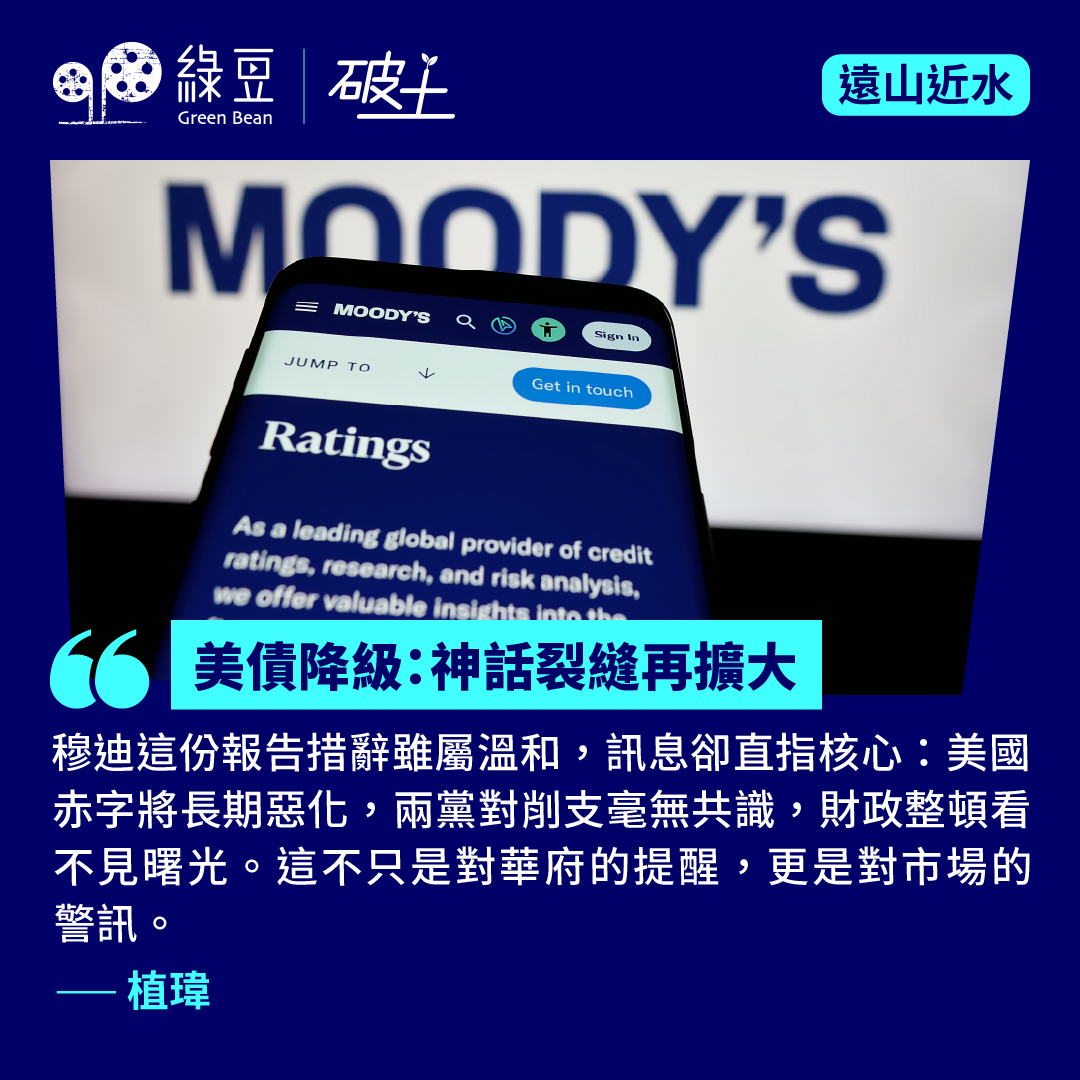《相印集》之前刊出了十輯墓園系列。十九世紀歐洲墳場是埋葬平民百姓,主教、神父或帝王將相則長眠於大教堂。 大教堂(Cathedral)是歐洲基督宗教的最要建築,多是教區大主教所在之地方。大教堂的建築時間,往往需時幾十年,甚至百年以上。長久以來,這標誌著那個城市的宗教輝煌成就,為其主要地標。基督宗教全盛時代,大教堂的崇拜儀式是每個基督教徒盼望參與其中,是以大教堂可容納上千以上的教徒。 惟基督宗教經過上兩個世紀的世俗化過程,昔日全盛時期已成過去。現代歐洲大城市的大教堂,已變成旅遊景點! 我想在《相印集》跟各讀者分享我到過的大教堂種種不同景象。首先從我現在身在英國聖奧爾本斯大教堂説起。聖奧爾本斯(Saint Alban)是英國第一個基督教殉道者,於公元4世紀為羅馬統治者所殺害,信徒於793年在此地建立教堂以紀念他。教堂自此輾轉發展一千多年,1877年成為大教堂。 大教堂的建築形式不是英國十一世紀以降最重要的歌德式(Gothic)建築,而是羅馬式(Romanesque)和後歌德式(late...
第十二封信 12.1 明慧, 抱歉沒有和你通信差不多兩個月,想你一切安好。2023年最後兩個月到了不少地方旅遊,增加很多以前不知道的見聞,對中歐、埃及與土耳其文化和藝術認識加深。 十二月中深夜由埃及旅遊回來。從金字塔、神廟、王帝谷到沙漠,給我從未有過的經驗。一方面讚嘆和敬佩四千多年前古埃及的文化成就,但這些偉大建築和藝術只是為了歌頌法老王和貴族的豐功偉績,無視無數人民的苦難和勞役!同時看到現今埃及的落後和貧困,交通的混亂難以想像!所有地方都要求小費!開羅和其他城市隨處可見爛尾樓,沿途有不少警察關卡。導遊跟我們説,2011年的和平革命雖然推翻了當時的總統...
▌[黑膠集]漫畫家簡介政治漫畫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07年起替報章及雜誌創作漫畫及插圖。其政治漫畫專欄《嘰嘰格格》於《明報》連載至今。出版作品包括《Hello World》,《Lonely Planet》,《大時代》,《新香港》等 。曾任教城大創意媒體學院及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 現定居英國。 ...
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是我極希望參觀的一個地方。在倫敦Lambeth的博物館現址,前身是一所醫院。1936年起用以收藏和展示戰爭物事,或許,意義上也儼如一個治療之所 —— 回顧一戰以來戰爭的旅程,細味瓦礫血肉之下人的恐懼、變通和淚水。 帝國戰爭博物館...
記得臨離開香港前,曾有朋友煞有介事地告訴我:「在英國的第一個冬天最難捱。」聽罷我卻不以為然,事關小弟從小怕熱,每年冬天都只會嫌不夠凍,到了外國恨不得可以過一個冰天雪地的冬天。 但抵英後隨著冬意漸濃,我開始感受到那個「難捱」真正的意義。 原來,天氣寒冷還算事小,真正難捱的是急劇變短的日照時間。記得初到埗英國的時候,晚上八點還可以看到太陽;過了十月,一轉冬令時間,即感受到日落時間逐日提前;至十一月的時候,基本上每天下午三點多就已經開始天黑,更甚的是,即使在日間,你也可能因為天陰下雨而看不到太陽。 以前生活在香港,從來不會覺得照不到陽光是甚麼大不了的事。但當接連好幾個星期都不太接觸得到陽光,身體開始出現反應。首先是沒有精神,就算前一晚睡飽了,第二日照樣可以呵欠連連。隨之而來的是失去做事的動力。好幾晚看著案頭上還未完成的工作和功課,儘管跟自己說今晚要好好努力,最後卻發現自己根本不能專心,只想賴在床上做些不太需要用腦的事情。 季節性抑鬱 後來學到原來這種情況叫做「冬季抑鬱」(Wi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