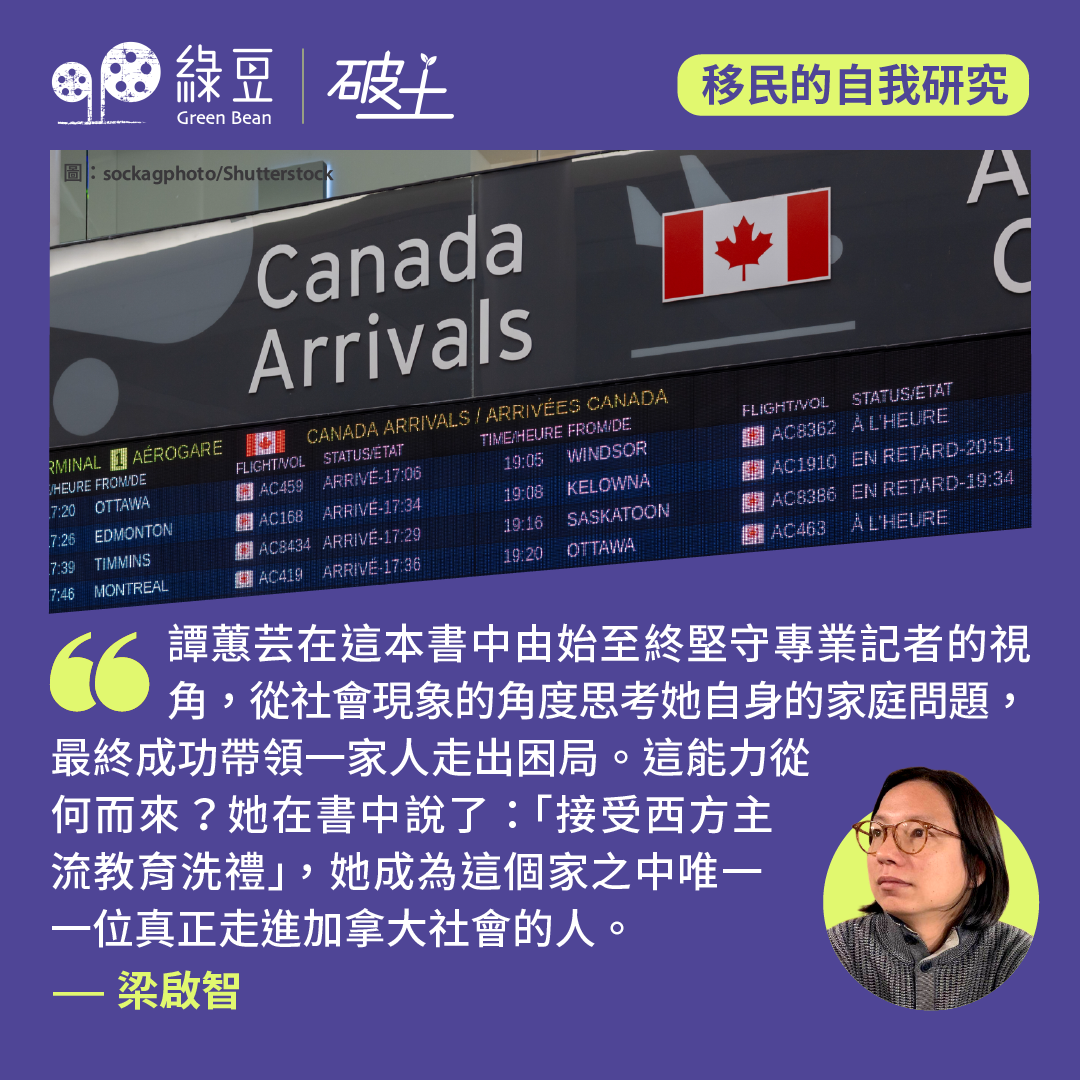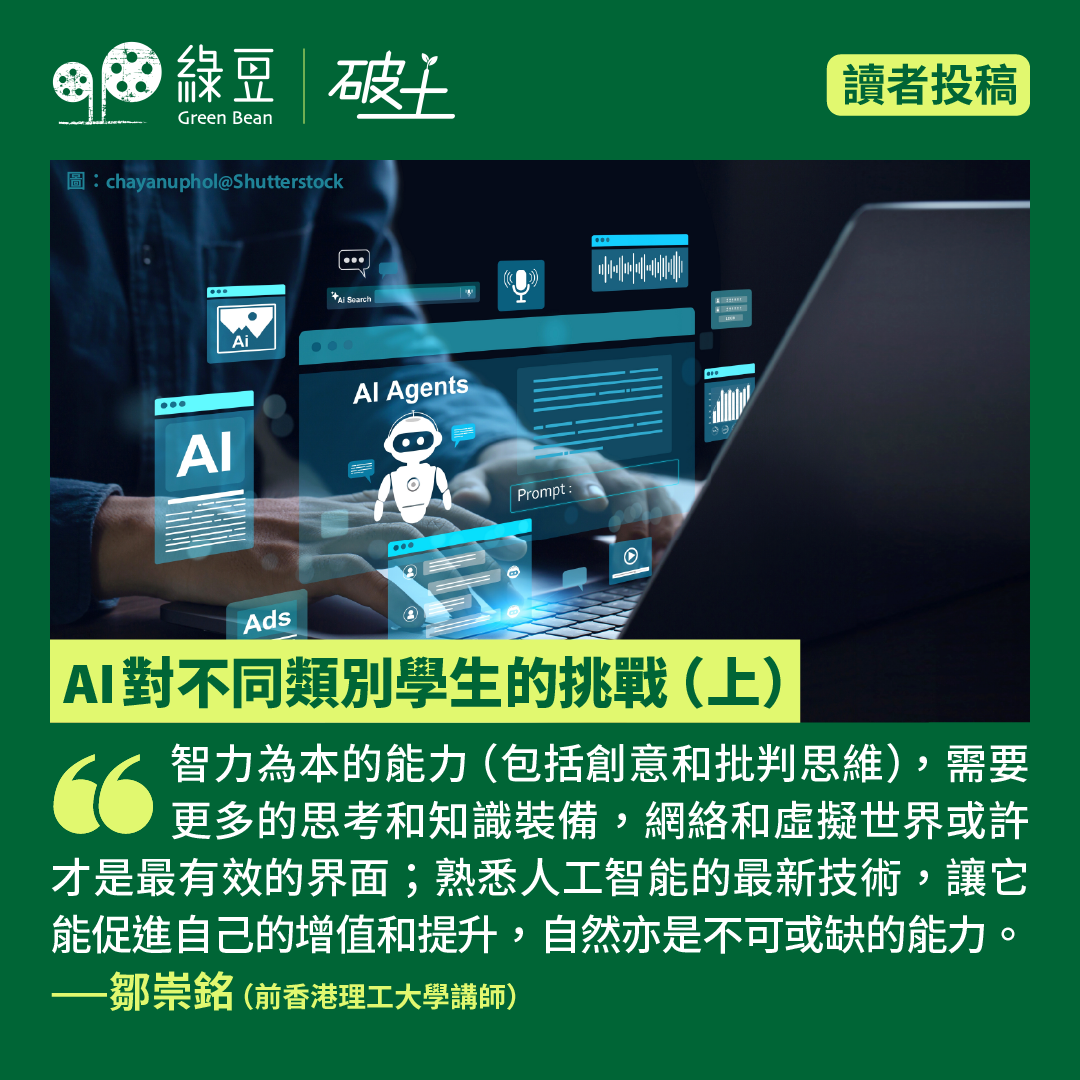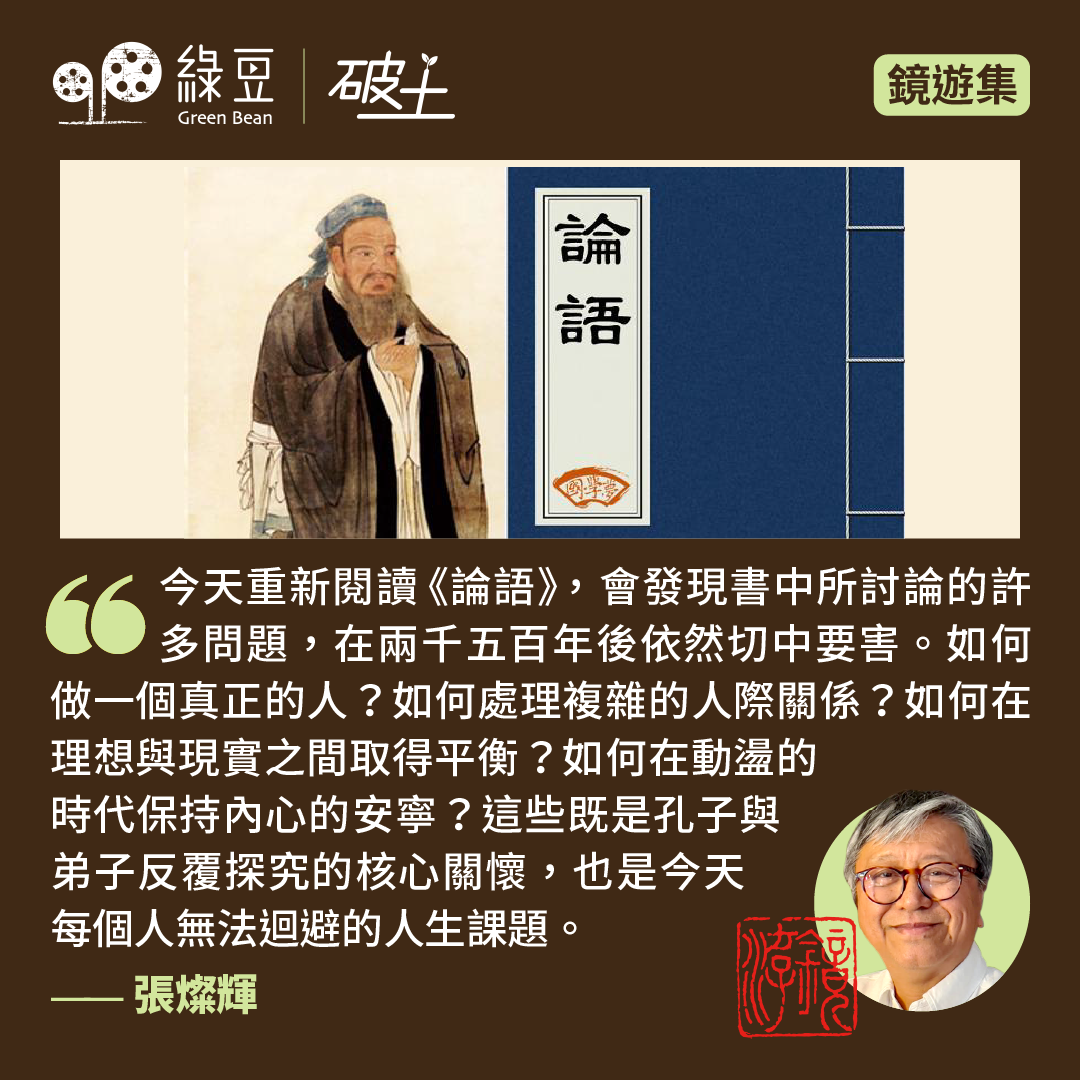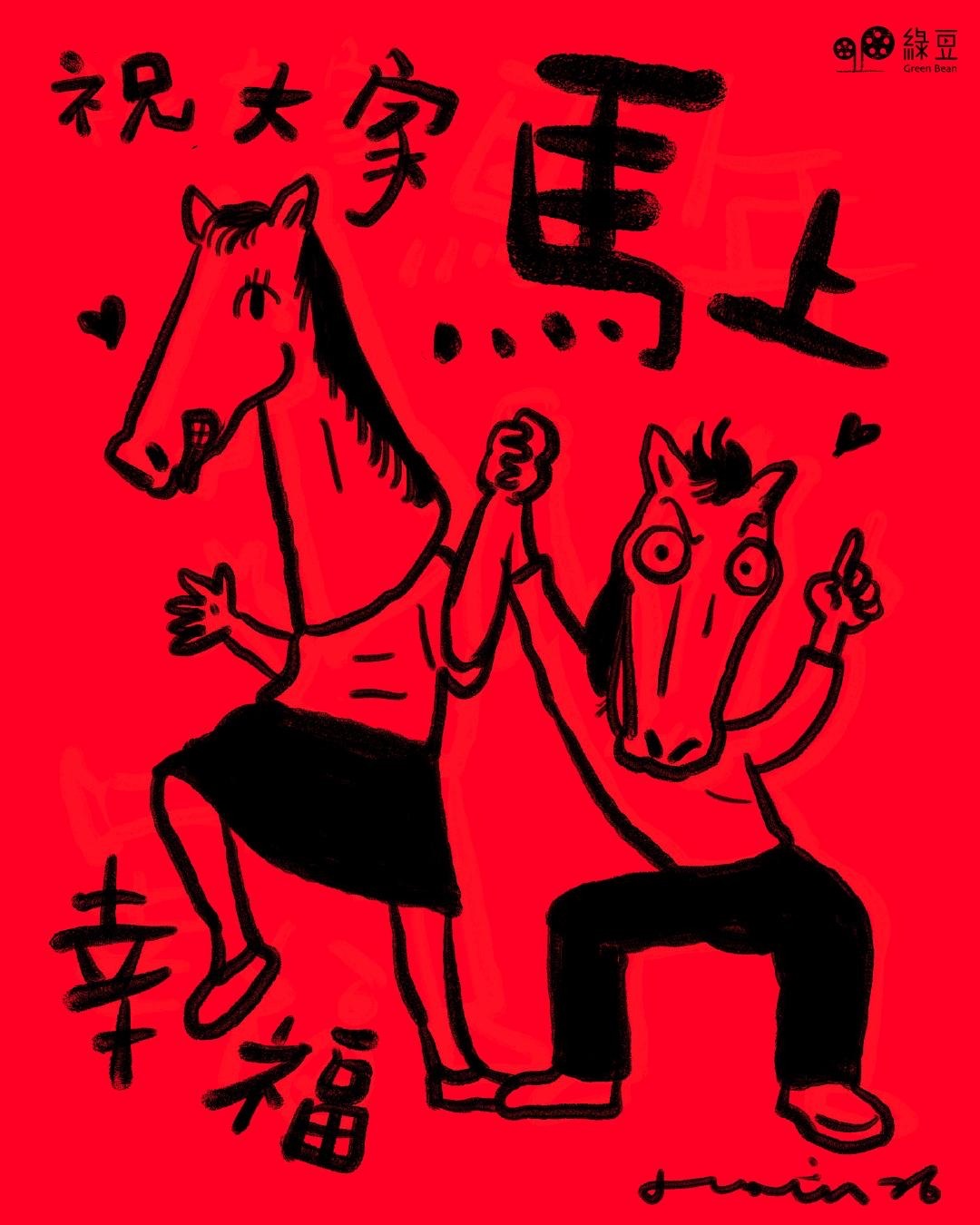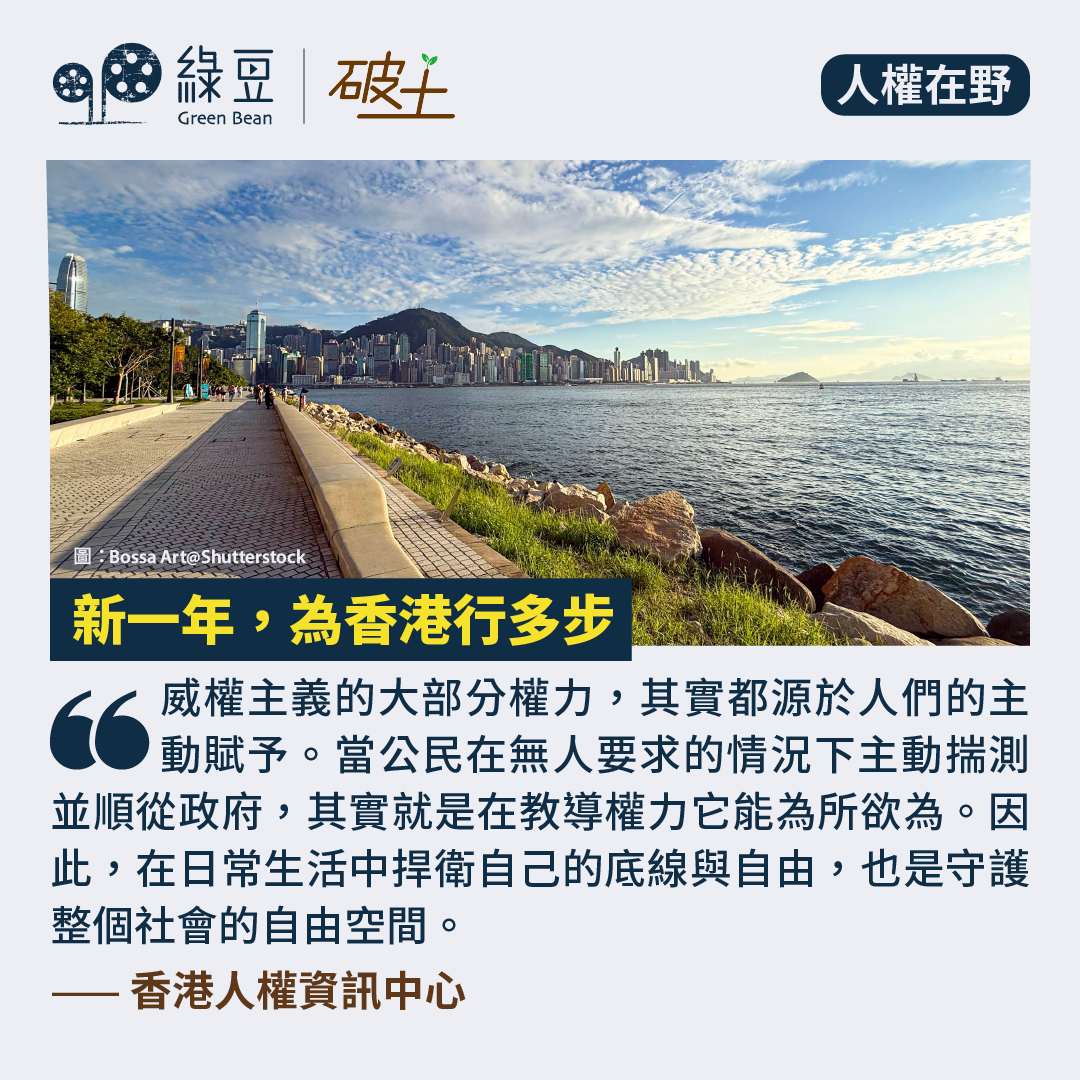友人譚蕙芸近日出版的新書《家鎖》廣受好評,送到各書店的首刷書均被搶購一空。早前她分別在台北和東京的飛地書店舉行新書發布會,兩場活動也是座無虛席。《家鎖》的副題是「華人家庭這個巨獸」,不少到場讀者也分享了他們與原生家庭的種種糾纏,說明此主題有強大的共通性。然而在新一波的移民潮下,此書也帶出了另一個重要的主題:移民的衝擊如何擴大原有的家庭矛盾。相對於「華人家庭這個巨獸」,要直視的還有「移民家庭這個巨獸」 過去熟悉的譚蕙芸,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同事,擅長於以輕鬆活潑的方式教授新聞寫作手法。在公眾領域的她,則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以細膩的筆觸,紀錄街頭和法庭的人與事。而在這本書當中,她打開了另一個被埋藏的身份:她有中風的父親、失智的母親,還有思覺失調的哥哥。在疫情期間,當香港人都在趕緊移民離開,她一個人把全家從加拿大搬回香港,找辦法活下去。 故事的起點是八九六四後,一九九七前的那一波移民潮。他們一家過去從來沒有離開過亞洲,一下子連根拔起移民到加拿大多倫多。然而哥哥在離港前已有的徵狀,在移民後進一步加劇,結果被診斷為思覺失調。可是他的精神健康卻沒有得到適切照顧,父母把他藏起來與社會絕緣,成為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移民環境成問題催化劑 事情發展至此,固然有華人家庭中的疾病污名和社會禁忌。然而在譚蕙芸的筆下,很明確看到移民家庭的環境如何加劇了各種問題,一步一步的走到無尾巷。 精神問題和其他身體問題不一樣,不能依靠外在儀器診斷,需要患者願意告知醫生潛在的徵兆;其中首要條件是建立和醫生的信任關係,在此之前又要先跨過語言的障礙。自問在台灣看醫生,明明已是說華語,有時要描述自己到底怎樣不舒服還是覺得隔了一層;換成英語,再加上各種沒聽過的醫學專有名詞,難度可想而知。書中就提到要在當地尋找懂粵語的精神科醫生的各種障礙,即使身處港人社群聚居的大城市也不易辦到,求醫路上又帶來更多拖延。 移民也會帶來家庭崗位的改變,而這點又可以延伸出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書中提到母親對家居整潔十分執着,移民後成為退休人士,一天到晚就在大屋中料理家務。對她來說,維繫這個家的整潔成為了她的「工作」甚至是生活價值,甚至演變成某種「控制慾」;然而兒子本來已是精神緊張,家中還要有各種規條,對病情沒有好處。可是也正正因為成為退休人士,她有時間照顧兒子生活所需,真的可以把兒子從社會中隔絕起來,雖然這也同樣不見得對病情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