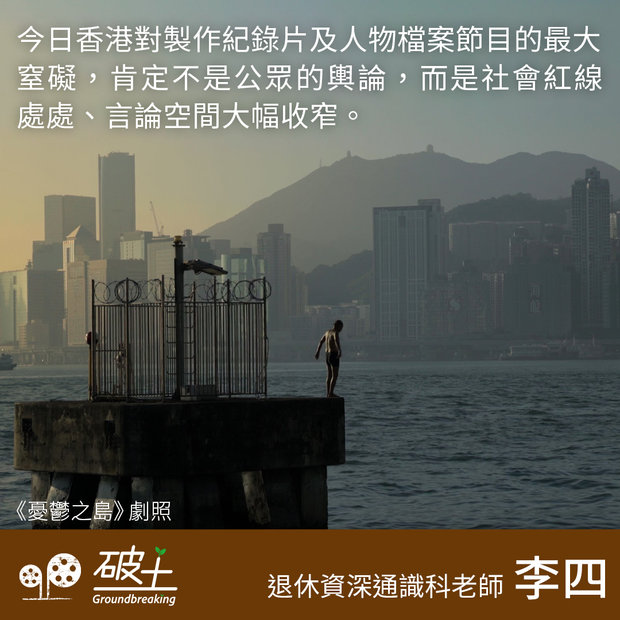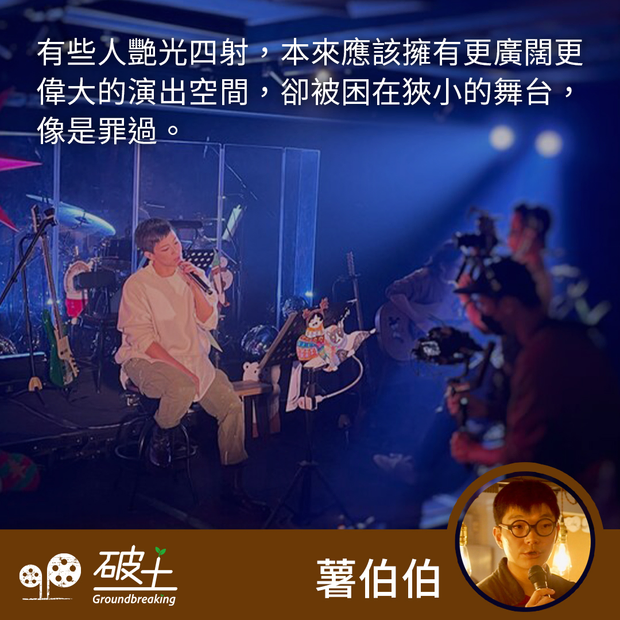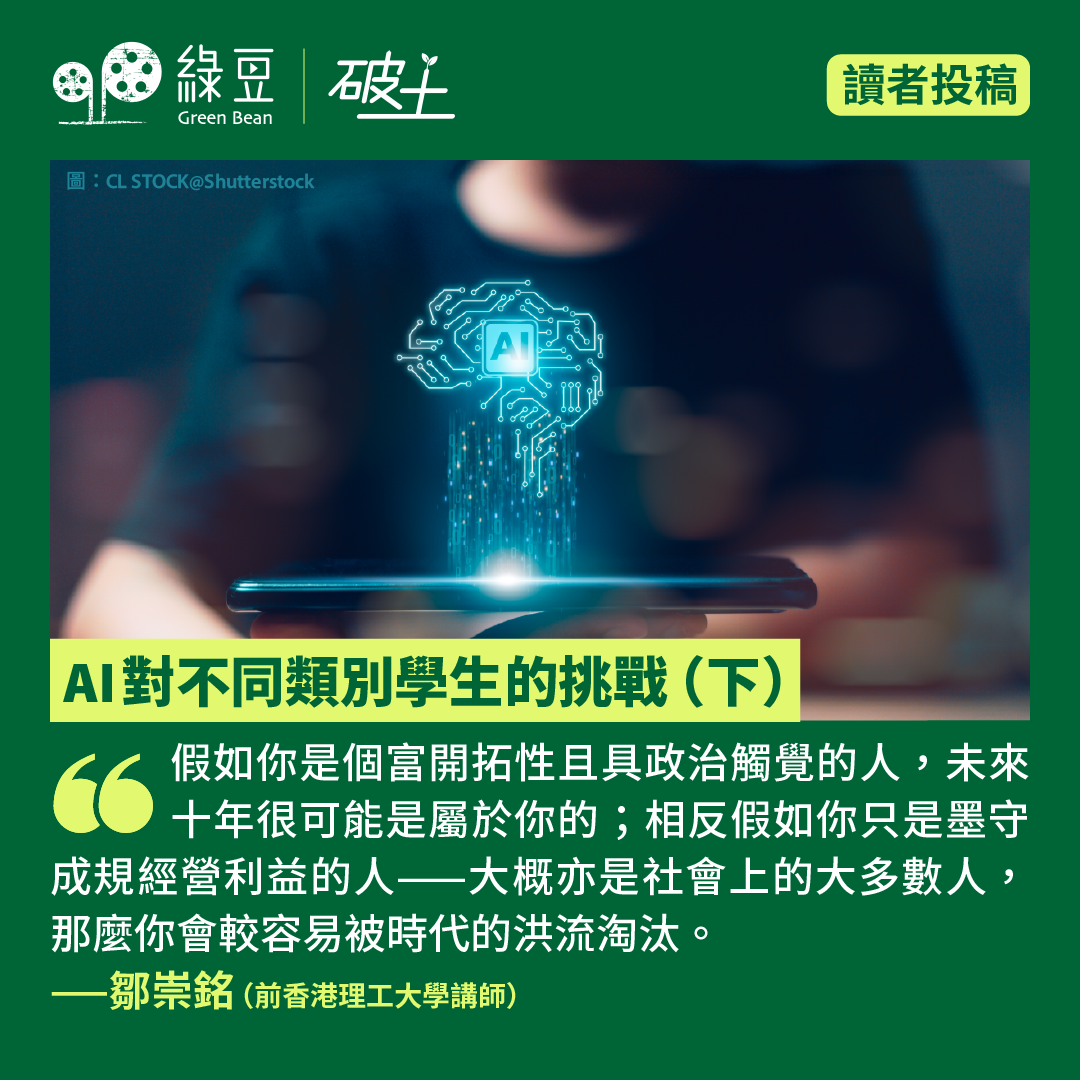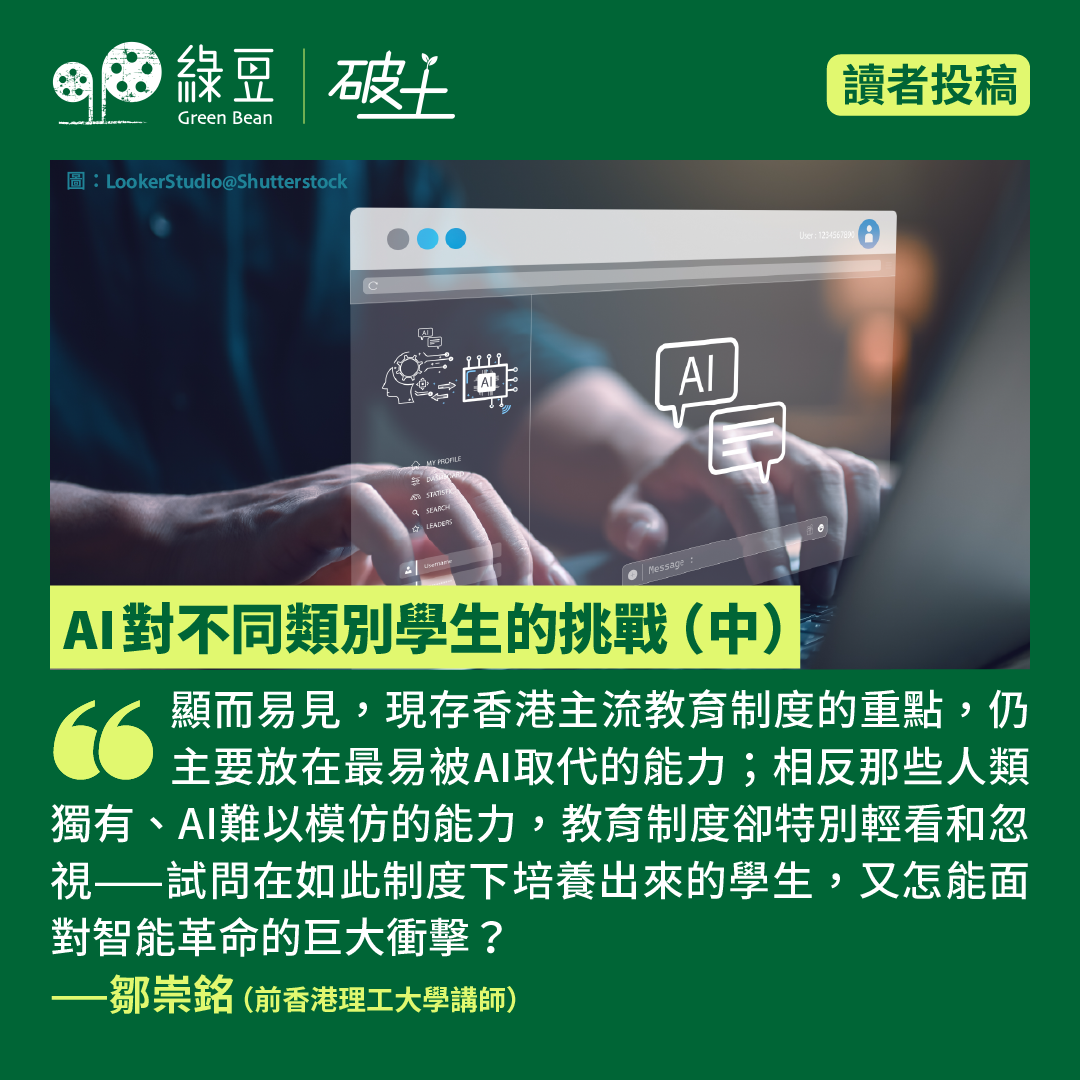發哥哀嘆,壓制創作自由,電影難有作為。長官:他胡說,年前頒布的禁令二十條,是為了讓業者增加創作自由,不是壓制。演員:是是是,重溫禁令,才知政府是一番好意。一禁「愛情劇不准太甜蜜」,容易得很,演員選用百歲以上人瑞,便不會太甜蜜了。編劇:二禁「同性戀題材,要把愛情改為友情」。這更容易,寫成他們未曾相愛已無情便是。導演:三禁「架空題材,虛構要徹底」;港片不用擔心犯禁,因為沒法拍得出《抗美援朝》的史實,編劇想像不到,單靠步兵,如何能打敗聯合國海陸空三軍?沒法做到「虛構要徹底」,不拍就不會犯禁了。影評人:四禁「拍壞警察」。電影《殺破狼》已從善如流,補拍了結局的內地版;死了的洪金寶忽然站起來,把執行私刑的壞警甄子丹拋下街中斃命。講真,九七之後,香港已無壞警察。長官:就是嘛,禁令二十條並不可怕,而且充滿正能量。
《給十九歲的我》從最初備受讚譽,到在爭議聲早停止放映,連日來已有大量的分析及評論。自己沒有機會觀看影片,及後從報刊中讀到兩位片中學生的訪問報道,隔著文字也能感受到兩位當事人的不忿與無奈,感到實在不應再觀看影片了,因而也難就影片的具體內容作細節評議。 鋪天蓋地的評論確實對製作人及受訪者都帶來了不小的壓力,但有論這些批評將會窒礙了未來香港紀錄片及人物檔案節目的製作空間,則似乎誤判了現時香港創作自由真正面對的問題。 自己曾經作為老師,也曾為學生安排過媒體拍攝一些個人生活紀錄。經驗中檔案節目的製作人(導演甚至是監製),都非常重視受訪者的信任。不要說這樣一個長達十年的拍攝過程,就算我以前經歷過的幾個星期甚或只是幾天的受訪拍攝,導演都會在正式拍攝前,先和接受拍攝的同學促膝長談,既更深入了解同學的想法,同時讓同學了解導演的拍攝目的。 假若製作人未能充份了解同學的心態與想法,最後同學對「出街」的節目感到不滿,即使事前簽了什麼同意書,不滿或質疑公開了,結果只會損害了影片或節目的公信力,這肯定不是製作人所願意見到的。因此,虛心聆聽受訪者的聲音,設身處地感受其關注及憂慮,是手執鏡頭及剪接刀大權的媒體工作者責任,若未能做到則難言專業了。 如果評論的焦點在於製作人有否刻盡紀錄片製作人(而不是戲劇製作)的專業,這應該是促進而非窒礙了專業發展。 其實今日香港對製作紀錄片及人物檔案節目的最大窒礙,肯定不是公眾的輿論,而是社會紅線處處、言論空間大幅收窄。許多優秀的紀錄片製作人,記錄了不少年輕人過去幾年的抗爭經歷、社會參與及心路歷程,受訪者也極希望其聲音能獲得聆聽,然而在香港今天窒息高壓的政治氣氛下,根本就沒有可能發放。...
近幾年過節之時,明知習慣上要說聲「快樂」,但話到嘴邊就變成「平安」——生日平安,中秋平安、聖誕平安、新年平安。原來當「平安」成為未知之數,快樂不是首選,平安才是難能可貴。不知大家有否相同感覺?經歷風風雨雨,人的要求雖然變得卑微,但卑微得來反而更為實在,沒參雜半點奢華。 身處香港,在只求平安的平安夜,聽何韻詩的演唱會。她是香港其中一位最能獨當一面的歌手,但在大氣候壓頂之時,堅持唱下去居然也要花足巨大勇氣。 演唱會開始,她唱《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隨著每個打擊,我會愈強」。她開玩笑說這次舞台終於有「台板」,而不是踏在平地上唱歌;現場有空調,不像上次令人滿頭大汗的「桑拿」。 結束之時,她唱《春夏秋冬》,「能同途偶遇在這星球上,是某種緣份,我多麼慶幸」,當離合變成日常,才更珍惜曾幾何時以為理所當然的相聚。 看著平安夜的演出,你會因她在此時此刻仍能找到舞台而高興;但當射燈映照在她的身上時,還是不禁感慨,感慨的不單是人之去留或時代變遷,而是有些人艷光四射,本來應該擁有更廣闊更偉大的演出空間,卻被困在狹小的舞台,像是罪過。 但願是晚在不同時空共同收看的朋友,會因為這場演唱會,在多年以後仍然記得2022年的平安夜。 原文連結:https://www.patreon.com/posts/76340599...
收看節目 創作人都知道,能否說好香港故事,並不取決於作者主觀意願;但只要以香港文化底蘊作本,反映香港時、地、人的經歷和思想,那個故事就會「好香港」。 你的香港故事,還記得嗎?創作自由對文化、藝術、學術界等十分重要,近年不少香港人選擇到更自由的地方發展,繼續理想。當電影、出版、劇場,來到自由土壤,可以在另一端開花,在異地裁種出來的,是香港文化嗎?離開熱愛的這片土地之後,還能拍出帶有本土情懷、真實反映香港的的創作嗎?英國製造,真的可以呈現港產味道? 《記香港人.話》來到第四話,嘉賓張燦輝教授、戲場監製列明慧、導演伍嘉良,將會分享人在英國與香港流行事物的聯繫;文化人編寫文章、攝影、舞台製作到拍攝電影,創作背後的動機,是愛還是責任,又或者兩者俱備?香港文化隨族群流散各地,又會衍生出怎樣的文化現象? 當小島被浪潮不斷洗刷,香港文化和每代人的集體意識亦會不斷演變、承傳。他們相信不必急於一時,沉澱過後,融合各自經驗,或許是英國版《秋天的童話》,或許是重新以英語演繹的香港人氣劇作,各地觀眾將會看到更多「好香港」的故事。 [01:35]...
收看節目 香港的淨人口移出,由2019年起到2022年上半年,累計達23.1萬。這個概念性的數字之下,其實是一個又一個獨立家庭,離開香港流散在異地各處。 BNO簽證移英潮經歷兩年,隨一批又一批港人先後落戶,這群因相若理由離開,擁有近似價值的人,開始在各地凝聚。 有前香港區議員在較少港人居住的地區,組建港人組織,延續「遍地開花」的精神,為凝聚香港族群,重建港人公民社會深耕細作。 無政治背景的移英港人,亦在自身的條件和能力下,為港人建立聚腳點,集散香港文化。...
收看節目 禁片《十年》金像奬電影人伍嘉良:移英不是移民,是延續要做的事;以電影連結流散港人,一同重建港人族群力量 在迷惘的時代,陌生的處境之中,《記・香港人》打算盡力去記錄一個又一個移居英國香港人的故事,希望他們的剖白和分享,可以讓大家在摸索的過程中找到一點啟發,或者一點精神上的支持。 第一集的人物伍嘉良,他的團隊創作了電影《十年》,在數年前預言了香港變局,不幸地在今天逐一應驗。2020年,他決定離開香港。2022年,他籌辦了英國香港電影節,推廣播放已被香港禁制的港產電影。 他相信這次離開,並不是放下某些東西,而是負上了額外的責任。因為那段共同經歷,令到不論離開或是留下的人,都已經成了一體。 「離開,並非想開展美好的生活或者美好的前途,並不是用一種移民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