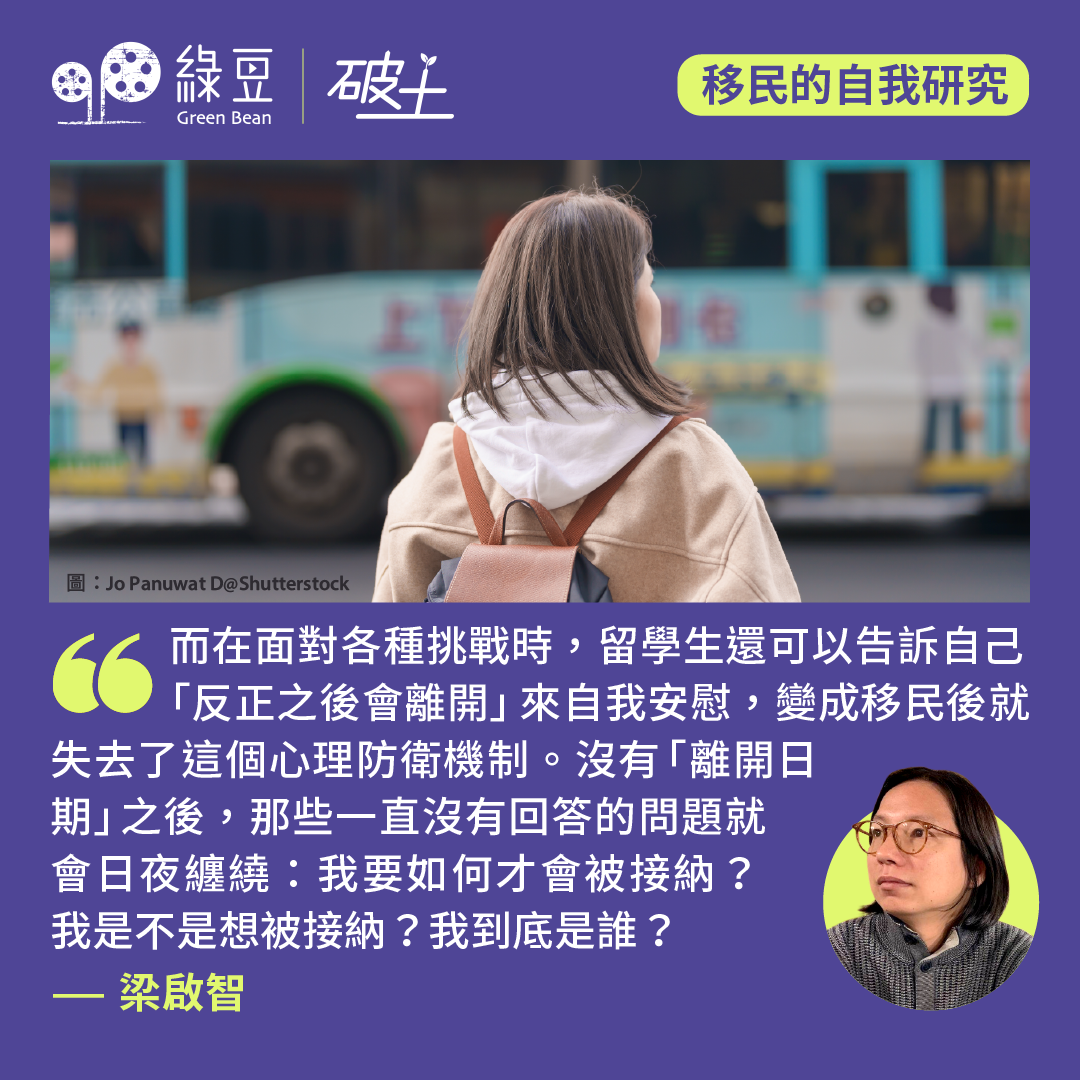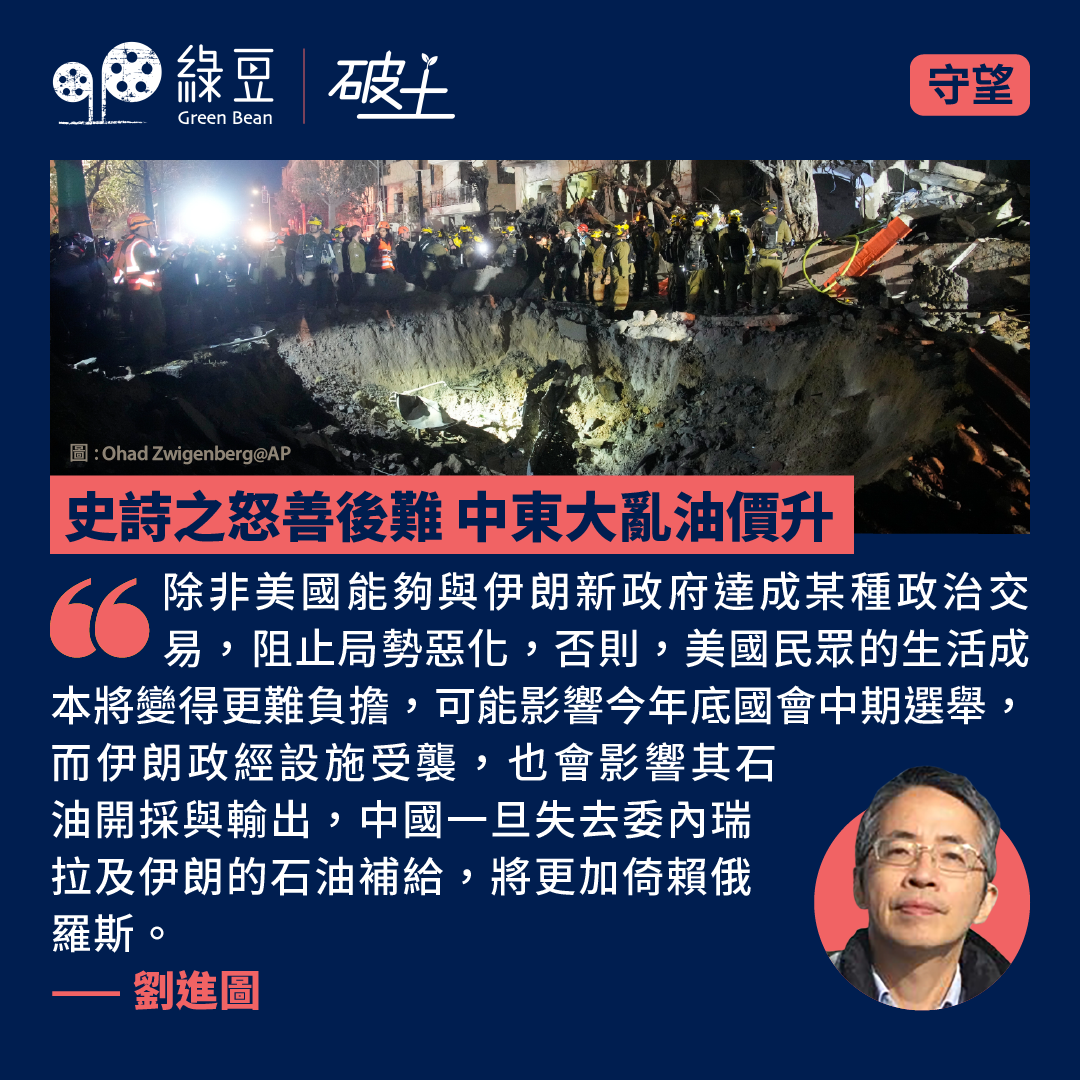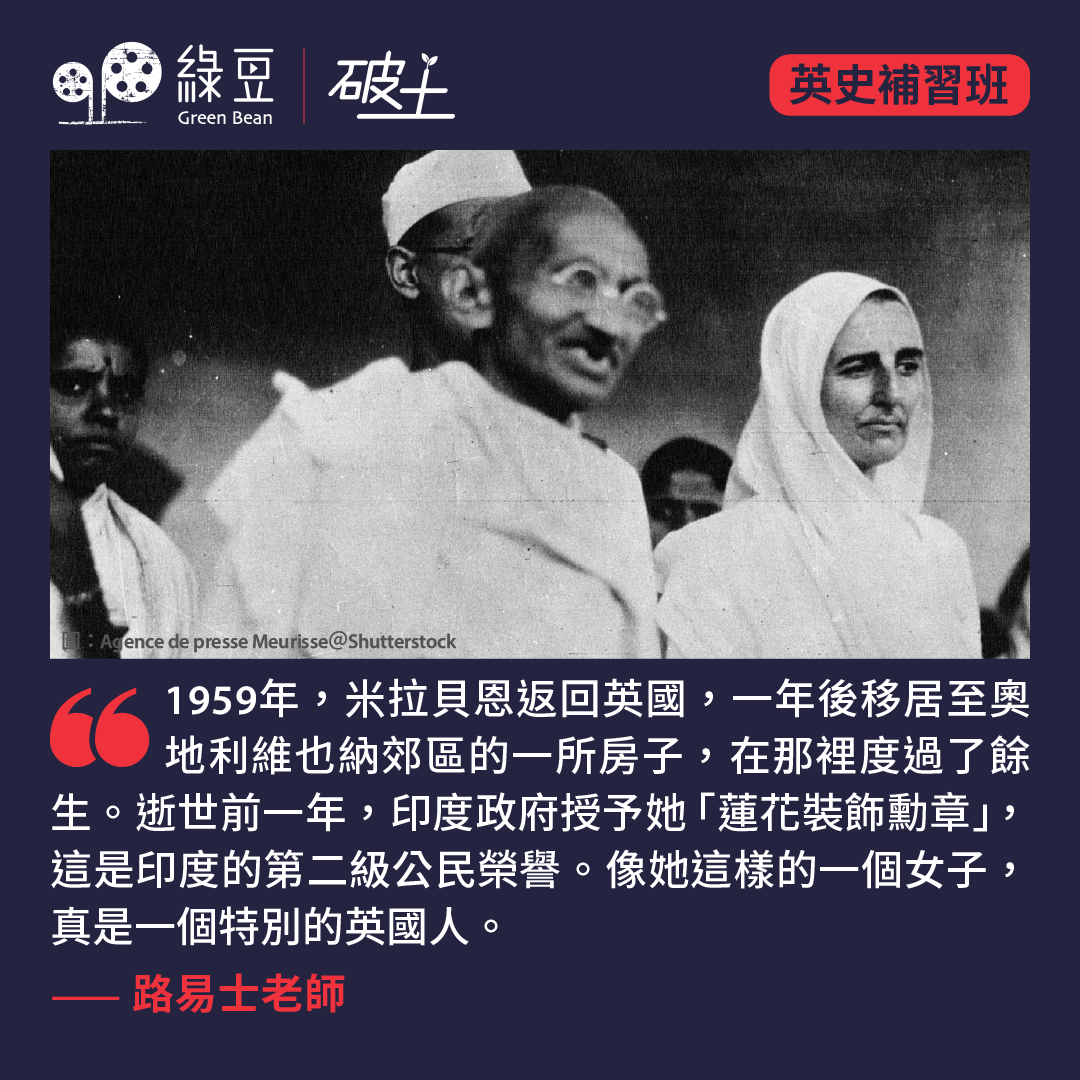最近因為工作關係,收到一些香港來台留學生的履歷。從香港移民來台灣,留學是其中一種方法,雖然這樣路現在已不太好走。認識不少通過留學移民的年輕人,在轉換身份的過程中都遇都不少問題。從留學到移民,不是一條純粹的直行路。 留學生算是移民嗎?如果放在傳統意義下對移民作為單向遷移的理解,那就當然不算。但現實往往複雜很多,很多時候出國留學的那一刻沒有想過要在當地留下來,結果因緣際會,可能是找到喜歡的工作,可能是有異地姻緣,也就誤打誤撞留下來了。反過來,也有不少人一開始就想移民,留學是其跳板:香港就有不少中國大陸的學生是這樣留下來的;也有不少香港人因政治因素需要離港,而來台留學對他們來說是最容易的方式,儘管他們本來並無意欲留學。 對未來的想像 從留學變成移民,身份轉變會帶來時間觀的改變。留學是暫時的,你知道自己有回去的一天,於是很多影響比較長遠的決定都不會做,最起碼不會為住處添置大件傢俱,最好一個皮箱隨時來去自如。決定留下來了,不再是數年內便會離開,道理上就可以開始想得比較長遠。 只不過,時間觀在拉長的同時,也可以變得更不確定。身為一個學生,每日每月每年的作息是有清楚規劃的,時間往往可預期且被制度化:上課下課有時間表,學程有明確年限,未來被想像為「完成學業後再說」。一旦留下來了,除了開始要為以後的時間規劃,也要面對這個未來是何等的難以規劃。即使當了幾年的留學生,不等於就對當地的職場文化和不同業界的發展前途有任何認識,也沒有多少人可以依靠,剛畢業踏進社會的不安感比本地人更如浮萍。 然後是工作簽證的年限、居留資格的更新,還有移民政策的變動,使得生活規劃不再圍繞學期論文和考試的定時規律,而是被行政程序與政策風險所切割。你發現「原來一畢業才知,一世我也要考試」;只是這些考試不再有評分表和天書,酌情權全在移民官手上,你做足所有要求不等於你的申請會最快得到審批。 另一個時間觀改變的後果,是因為過去的居留被定義為是臨時的,無論是自我或外在對於融合的期望也會比較低。留學生通常被置於一個相對清楚、甚至受到保護的制度位置;因為位置是暫時的,邊緣性也被合理化。口語說得不好?沒所謂,留學生嘛;但身份變成移民後,期望就不一樣了:你既然要成為本地人,你就要變得像一個本地人。儘管正如本欄多次強調,「何謂本地人」從來沒有客觀標準可言。...
Kevin Takahide Lee 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有一個有趣的說法:他既是 50%日裔與 50%華裔,也是百分百的加拿大人。作為土生土長的中日移民第四代,他始終與多重歷史同行,特別是二戰期間日裔移民被強制遷到集中營的一段。他曾參演講述早年移民足跡的舞台劇,也創立新移民合唱團,透過自己的演藝和聲樂專業,來回應和梳理自己的關注。 他所領會的加拿大,充滿創傷,但同時複雜而美麗。...
( 編按 : 此專欄內容均為真實處境,旨在反映家庭、婚姻及個人之間的複雜性,以文字與大家一起走過荊棘。專欄文章經編輯在文字上修改處理,確保內文提及的人士身分保密。) 近年不少香港人選擇移民到英國或其他地方。無論離開的原因是什麼,你可曾想像過二十年後的生活會變成怎樣?家庭之間又會出現什麼變化? Andy 的父母在他四歲時便分開了。三十多歲的媽媽帶著他離開家鄉,到英國重新開始。到了英國,只有母子二人,沒有親人,也沒有熟悉的朋友在身邊。媽媽的決定,是為了讓...
本欄一直強調移民是極為多元的社會過程,世上一方面沒有單一的移民經驗,而你是哪一種移民也不是你自己說了算,亦要看當地社會如何看。要見證移民經驗的多元性,我建議大家留意最近在台灣十分火熱的網上節目《中文怪物》。節目中的一百位參賽者都是移民到台灣的外地人,而且背景都不太一樣,撞出各種火花。 《中文怪物》是由來自法國的網紅「酷」所策劃的大型節目,召集了一百位在台灣生活的外國人比試中文能力,勝出者可獲三十萬台幣獎金。第一集在一個月前播出,至今已近五百萬收看次數,最後一集亦已在早前播出。這節目可以討論的地方有很多,本文集中討論當中反映的移民經驗。 首先得稱讚節目組在尋找參賽者時花了很多心思。一百名參賽者固然有不少來自觀眾熟悉的國家,例如美國、日本和南韓等,但也包括許多平常提到「外國人在台灣」的時候未必會想到的國家,例如印度、烏克蘭和波蘭,拉闊觀眾對外國人的印象。也有一些參賽者來自中華民國現時或曾經的邦交國,例如海地、斯威士蘭(Eswatini)和岡比亞(Republic of the Gambia),說明台灣對外關係的特殊性。 擴濶一般的想像...
移英港人近日很想講很想問但仍掃不走千個未知的,必定是當局對BNO簽證永居條件政策的走向無疑。 社群中不難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忐忑不安。其中一種忐忑,卻從社群中有人更大聲、更擁抱排外觀點中表現出來。 在一些短訊群組,總是有人仍隨一些網上意見領袖、或GB NEWS等新聞風向起舞,語不驚人勢不休地批評犯法的難民、又言語狠毒大罵工黨承認巴勒斯坦是鼓勵恐怖主義......。 坦白說,見到粗口橫飛,大貼標籤,我和大多數群組內的人,都轉趨沉默。當然在社交媒體上,仍有KOL散播對伊斯蘭的恐懼、或其他有色人種如何如何的更極端的說法,更有市場,更能讓人變一日或一刻英雄。於是具名不具名,一些移民港人都跟著極端政客或KOL說出更無底線的言論。 身邊的平凡人 不如,了解完每日新聞重點之後,關掉網絡,放眼四周,聽一聽、看一看身邊的鄰舍、同事,再想一想,默許甚至為更為排外的政策主張拍掌歡呼時,會影響哪些你關心、你珍惜的平凡人?...
友人譚蕙芸近日出版的新書《家鎖》廣受好評,送到各書店的首刷書均被搶購一空。早前她分別在台北和東京的飛地書店舉行新書發布會,兩場活動也是座無虛席。《家鎖》的副題是「華人家庭這個巨獸」,不少到場讀者也分享了他們與原生家庭的種種糾纏,說明此主題有強大的共通性。然而在新一波的移民潮下,此書也帶出了另一個重要的主題:移民的衝擊如何擴大原有的家庭矛盾。相對於「華人家庭這個巨獸」,要直視的還有「移民家庭這個巨獸」 過去熟悉的譚蕙芸,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同事,擅長於以輕鬆活潑的方式教授新聞寫作手法。在公眾領域的她,則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以細膩的筆觸,紀錄街頭和法庭的人與事。而在這本書當中,她打開了另一個被埋藏的身份:她有中風的父親、失智的母親,還有思覺失調的哥哥。在疫情期間,當香港人都在趕緊移民離開,她一個人把全家從加拿大搬回香港,找辦法活下去。 故事的起點是八九六四後,一九九七前的那一波移民潮。他們一家過去從來沒有離開過亞洲,一下子連根拔起移民到加拿大多倫多。然而哥哥在離港前已有的徵狀,在移民後進一步加劇,結果被診斷為思覺失調。可是他的精神健康卻沒有得到適切照顧,父母把他藏起來與社會絕緣,成為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移民環境成問題催化劑 事情發展至此,固然有華人家庭中的疾病污名和社會禁忌。然而在譚蕙芸的筆下,很明確看到移民家庭的環境如何加劇了各種問題,一步一步的走到無尾巷。 精神問題和其他身體問題不一樣,不能依靠外在儀器診斷,需要患者願意告知醫生潛在的徵兆;其中首要條件是建立和醫生的信任關係,在此之前又要先跨過語言的障礙。自問在台灣看醫生,明明已是說華語,有時要描述自己到底怎樣不舒服還是覺得隔了一層;換成英語,再加上各種沒聽過的醫學專有名詞,難度可想而知。書中就提到要在當地尋找懂粵語的精神科醫生的各種障礙,即使身處港人社群聚居的大城市也不易辦到,求醫路上又帶來更多拖延。 移民也會帶來家庭崗位的改變,而這點又可以延伸出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書中提到母親對家居整潔十分執着,移民後成為退休人士,一天到晚就在大屋中料理家務。對她來說,維繫這個家的整潔成為了她的「工作」甚至是生活價值,甚至演變成某種「控制慾」;然而兒子本來已是精神緊張,家中還要有各種規條,對病情沒有好處。可是也正正因為成為退休人士,她有時間照顧兒子生活所需,真的可以把兒子從社會中隔絕起來,雖然這也同樣不見得對病情有好處。...
( 編按 : 此專欄內容均為真實處境,旨在反映家庭、婚姻及個人之間的複雜性,以文字與大家一起走過荊棘。專欄文章經編輯在文字上修改處理,確保內文提及的人士身分保密。) 「我兒子失蹤了。」黃先生一見面便焦急地說。 黃先生身在香港,兒子則在兩年前移民英國,父子間一直每星期通電話,一切看似如常。直至一個月前,兒子突然不再接電話,訊息也不回。黃先生向女兒提起此事,女兒卻輕描淡寫地說哥哥一切安好,叫他不用擔心。 這樣的情況一拖就是一個月。黃先生終於按捺不住,準備訂機票前往英國問個明白。女兒才向他透露:哥哥暫時不想聯絡,希望有點空間。黃先生無法理解,也無法接受。他反覆追問自己是否做錯了什麼、說錯了什麼,卻得不到答案。後來在女兒的安排下,我與黃先生及其女兒進行了一次視像會面。...
台灣大罷免首波投票以罷方大敗落幕,社交媒體見到有台灣人發晦氣說要移民離開,引發其他網民熱議。這邊嘲笑對方之前說愛台灣是假的,另一邊則號召不能只有在贏的時候才愛台灣,要愛就要同時愛她的不完美。一時之間,各種道德判斷紛紛壓下來,好不熱鬧。 身為移民,對移民這件事情本身沒有多大的道德判斷。人不能選擇自己於何處出生,如能有機會爭取自己在何處生活也算是一種自我實現,把對原生地的愛說成責任並非吾等自由主義者所嚮往。驀然發現自己和所處的社會原來格格不入,那麼嘗試尋找新的居住地亦是人性所在。 而對於本來處於社會邊緣的人群,意外的選舉結果或政治變遷很可能預示未來環境的急速崩壞,提早規劃後路實是情理之中。你總不能說上世紀三十年代末離開歐洲大陸的猶太人或四十年代末離開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是不夠義氣。而從六十年代起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移民離開香港,後面也是同樣的道理。 台灣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沒有人能夠預知。這次選舉是否預示未來情況將會急速轉壞,有風險或有能力的人是否該開始想想後路,恐怕要由未來的歷史學者回答。不過我相信這刻會說這些話的人,出發點很可能是情緒發洩;而之所以引起不滿,是因為碰上其他同樣在巨大困擾和震撼中的人群,於是引發了更多的情緒。 多少人付諸實行 現實上,要作出移民這個決定還是沒有那麼即興的。就連處於移民潮中的香港,經常見到民意調查聲稱有兩三成港人計劃移民,但到目前為止真正離港的人口百分比應該還是個位數。有時人們對媒體或調查說自己寧願移民,很大程度上是要表達對現況不滿,而非真有計劃。 那麼每次選舉之後聲稱「這社會太可怕,還是早走早著」的人,實際上又有多少人付諸行動呢?美國人移民加拿大的數據或可幫助我們回答。過去兩次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都為不少美國人帶來震撼,紛紛聲稱要移民加拿大。從數據上看,確實見到有移民加拿大的美國人有所增加。按加拿大統計局的資料,在奧巴馬任內八年,每年移居加拿大的美國居民大約是一萬人;特朗普在2017年就任後,數字明顯增加,到2019年時最高峰時超過兩萬人。2020年的數字估計因疫情大幅減少,到了2021年拜登上任後仍維持於每年超過一萬五千人的水平。至於特朗普再次就任的影響,現在為時尚早,未有數據。...
近期聽到不少赴加港人不滿加拿大政府未能及時處理永居申請,導致大量案件積壓。類似的問題,之前赴台港人也經歷過,亦引發不少怨言。與此同時,赴英港人則面對永居申請門檻從五年增加至十年的陰霾。三地政治環境和當地政府背後的盤算固然各有不同,卻同時折射出這一波港人移民潮的一個核心問題:在當地政府眼中和在港人移民自己心目中,港人到底算不算「走難」? 這條問題重要,除了是心態不同外,更是現實政策問題:如果是「走難」,那當地政府該套用的政策邏輯應從人道及恩恤出發,看重的是香港情勢的特殊性;如果不是「走難」,則會比較從當地本身的需求出發,重視申請人本身的能力如學歷、專業能力和資本貢獻,而且不用談「道義責任」。我發現各地出現的爭議,往往源於兩種想像之間的模糊性,和港人對自身定位的游移與期望落差。 人道救援? 首先,不得不得說有些誤解是港人自己造成的。例如加拿大針對港人的「Hong Kong Pathway」,香港傳媒常稱之為「救生艇計劃」或「避風港計劃」,但這從來都不是加拿大政府的官方翻譯,直譯應該是「香港通道」。然而語言有影響力,許多赴加港人習慣了「救生艇」這情感豐富的說法,面對申請延誤時便出現了不少認為當地政府「背信棄義」的慨嘆,實情是政府從來沒用過如此形象化的說法來描述此政策。 話說回來,港人自己想不想被視為人道救援的對象,有時也顯得難以說清。例如早前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的網頁改版,...
曾經和一些早已在外國落地生根的港人移民組織者討論新一代港人移民的情況,常常會聽到一種說法:這一波的港人移民還是太過「新」,對當地的理解往往仍存有各種幻想,又或仍未能處理理想和現實的落差。但他們往往還會補充一句:雖然港人移民或者還未完全認識或適應身為移民的文化身份,但他們的下一代將會不一樣;亦因如此,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之間,長遠必有隔閡。 舉個例,不少港人移民會自以為「榮譽白人」,假設自己理所當然會被當地社會接納,各種針對移民和少數族裔的排外情緒與他們無關;最新就聽說還有移英港人推動「反移民聯署」,好像忘記了自己也還未入籍似的。這些港人移民之所以會擔起各種在「舊移民」眼中甚為奇怪的價值觀,原因倒也不難理解:他們當中不少人都未有甚至不需要和當地社會有深入交往,只體會到移民後的好處,當地社會對移民的不滿或歧視卻未感受得到。如果他們資本足夠豐厚,甚至可以一直活在自己的「幸福泡泡」當中。 對家長的提醒 但他們的下一代就不一樣了。尚未成年便隨父母離港的移民,以至在當地出生的港人移民後代,面對的社會環境和他們的父母有巨大差別。他們的成長過程和當地社會的融合遠遠來得徹底和直接,無論是學校或朋輩交往,他們身為少數的身份會無時無刻被提醒。而相對於他們的父母,原來自香港的生活記憶又遠遠不如。他們最重要的身份不再是港人或港人移民,而是在當地社會的少數族裔;這差別看似微少,卻十分重要。 舉個例,Crazy Rich Asians(港譯《我的超豪男友》)在香港和在美國的上映,雖然是同一齣的電影,但對兩邊的觀眾來說就是活脫脫的兩回事。考慮到早年荷里活電影的各種種族歧視,包括由白人飾演亞裔角色或只安排亞裔演員擔當配角,完全由亞裔演員領銜主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