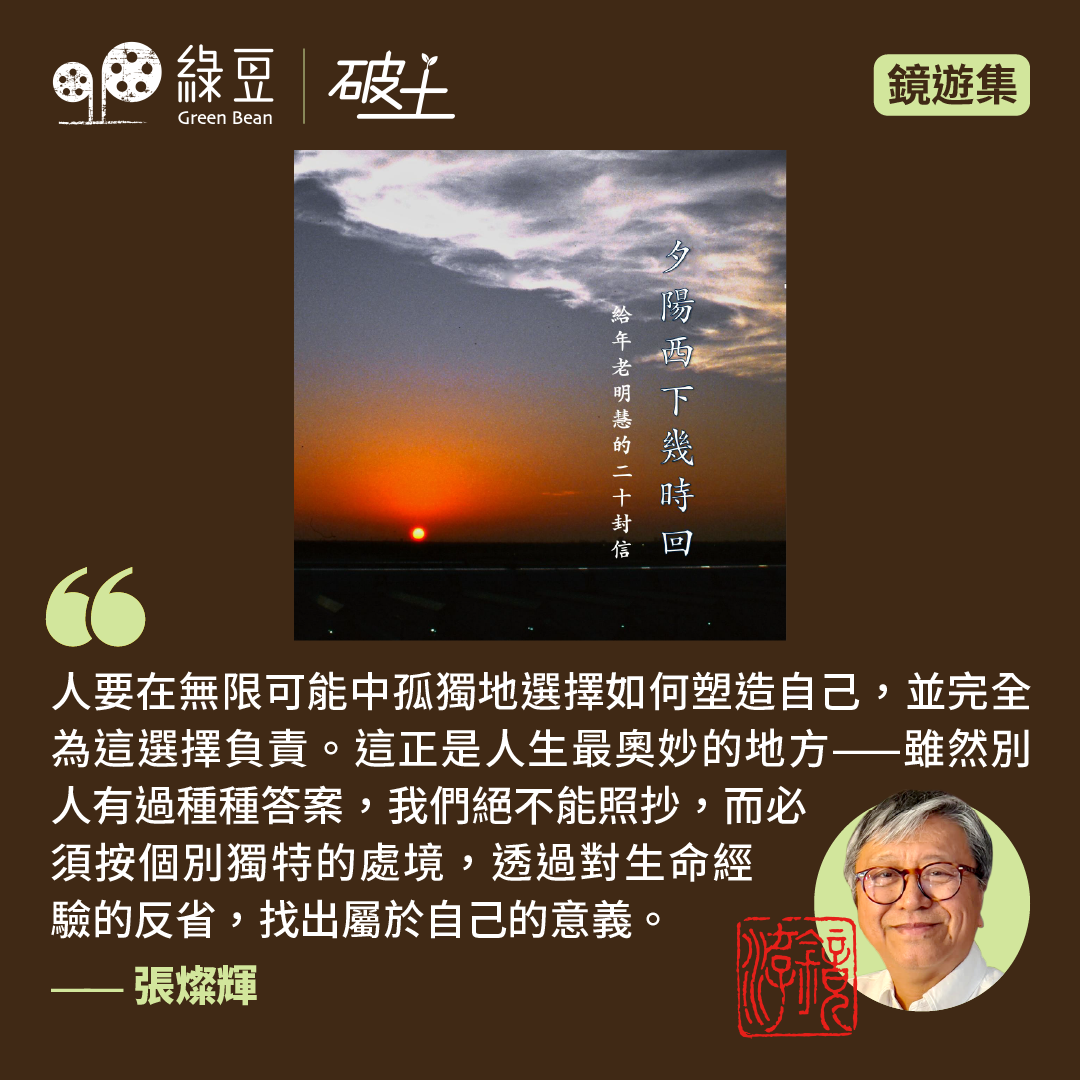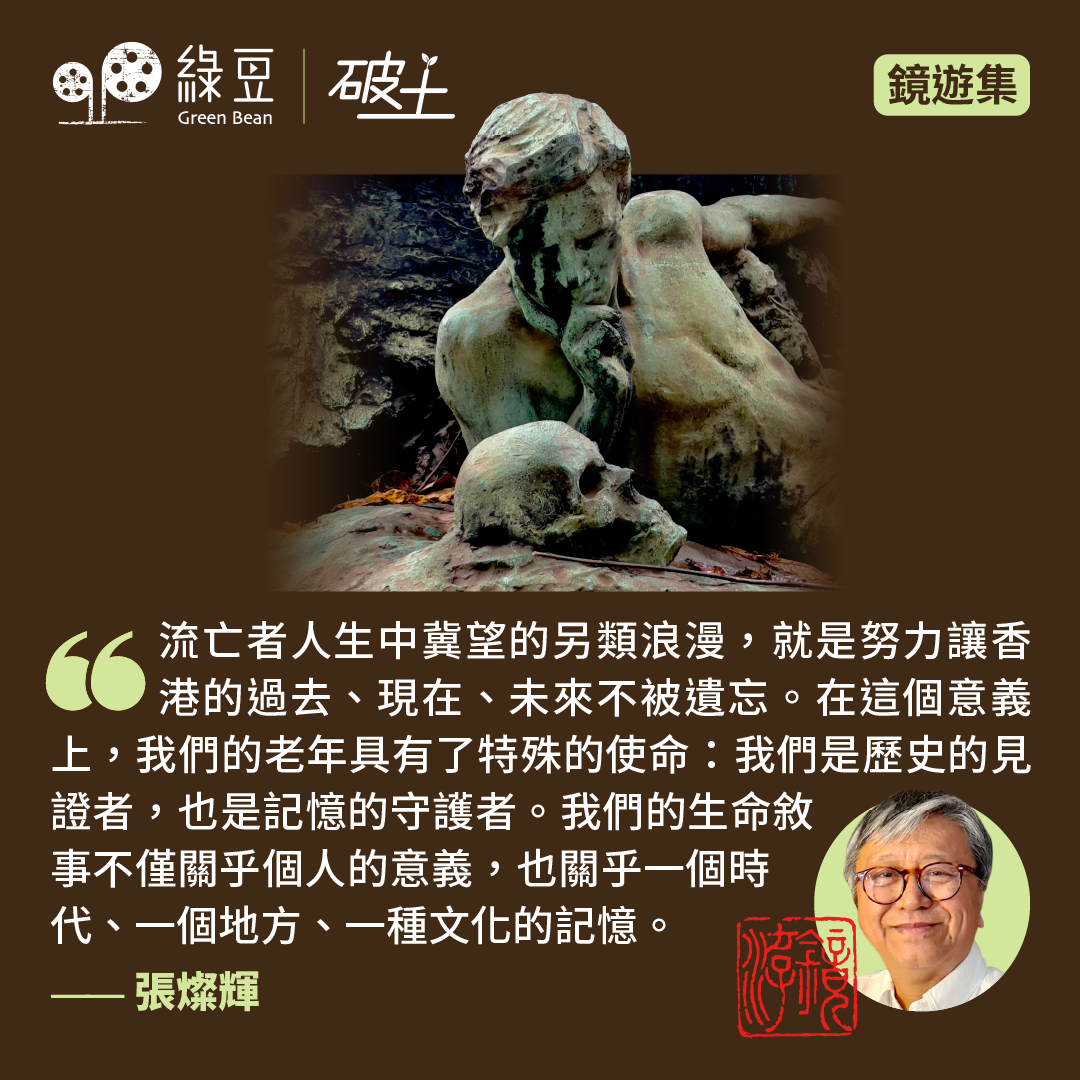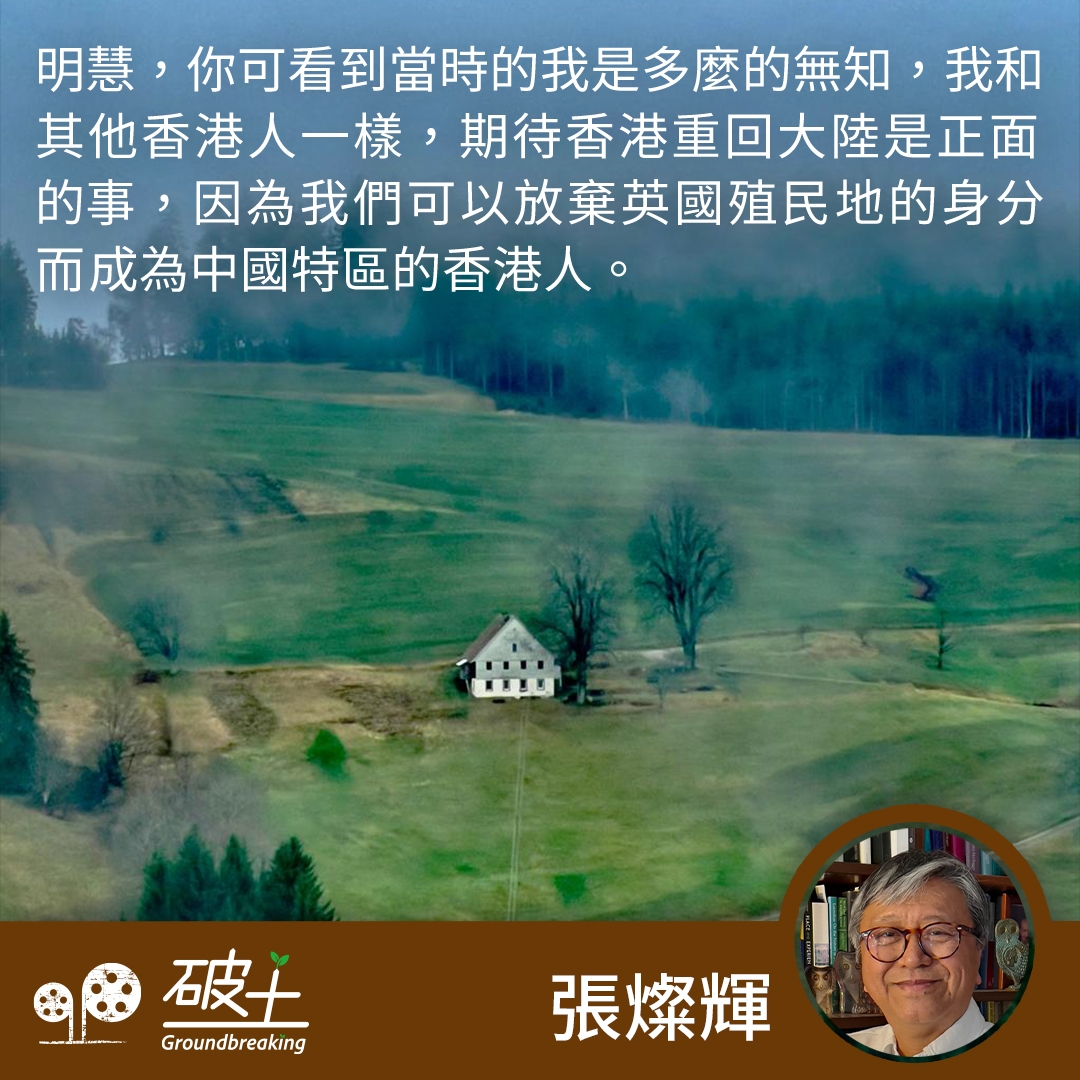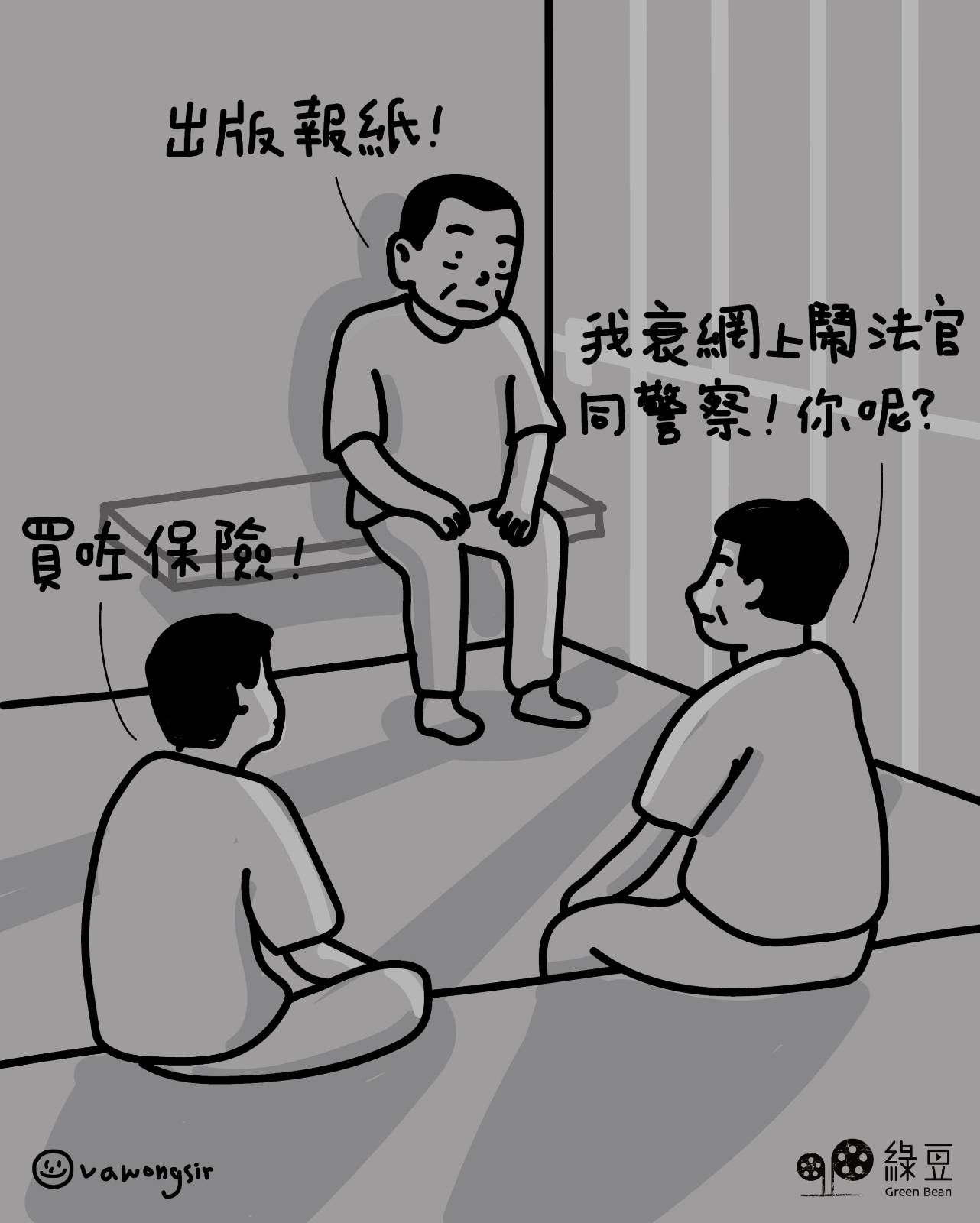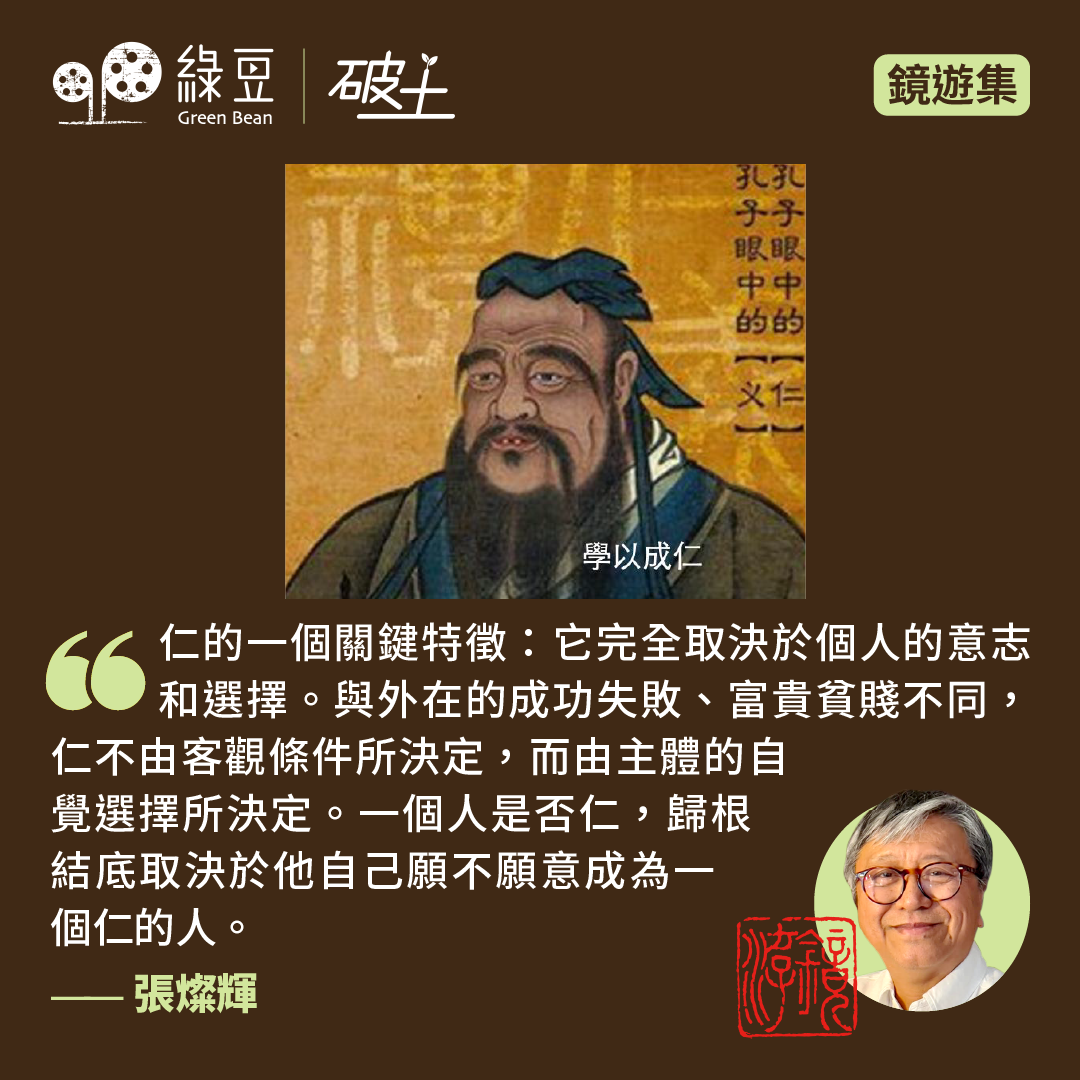(筆者按:我在2023年初在綠豆《鏡遊集》刊出第一封給年老明慧的信,差不多要三年才完成二十封信,最後結集成書,今年二月台北國際書展面世。這篇短文是我一些反省,也在此感謝綠豆給我空間發表我的文章。) 一九七七年我和周兆祥合寫《將上下而求索》,那時我二十八歲,剛從中大哲學系畢業不久,正準備赴德國攻讀博士。我們虛構了一個叫明慧的年輕人,把自己對人生的困惑與思索寫成二十封信。那本書後來成為香港高中的參考讀物,陪伴了幾代年輕人走過迷惘的歲月。 近半世紀過去,我在英國聖奧本斯的書房裡再次提筆。窗外是異鄉的樹林,不是馬料水的山色。我已過七十,父母早逝,師長凋零,連我深愛的城市也面目全非。這一次,我要寫給年老的明慧——也就是寫給同樣走到人生晚年的讀者,寫給我自己。 書名從屈原換成了晏殊。「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是少年的壯志,前路無盡,時間充裕,什麼都可以慢慢來。「夕陽西下幾時回」卻是暮年的喟嘆,日頭已斜,問的不是路有多遠,而是天黑之後還有沒有明天。 兩本書的距離不只是五十年 當年寫《將上下而求索》,我談人生處境、痛苦幸福、生命意義、愛情本質、自由超越,題目很大,口氣也大。那時候我相信人可以選擇面對命運的態度,可以在荒謬的宇宙中自我賦義。存在主義的教科書都是這樣說的,我也這樣轉述給明慧聽。 但那些話說得輕巧,因為我還年輕。死亡對二十多歲的人而言是抽象的概念,是哲學課堂上的議題,不是每天早上照鏡子時逼視你的現實。我父親五十四歲死於車禍,我當年以為那是意外,是命運的捉弄。現在我比他活得更長,才明白死亡從來不是意外,而是必然。差別只在於你什麼時候真正意識到它。...
(作者按 :《夕陽西下幾時回:給年老明慧的二十封信》構思開始於2017年,香港仍在「太平盛世」年代。我想退休之後,是回應《將上下而求索》的時候了。但真正執筆是2020年之後,幾經波折,至今才完成。 《鏡遊集》讀者不一定看過這本半世紀前的小書,是以將實體書《給年老明慧的二十封信》剛寫好的序和一封長信刊出,讓大家有比較全面的了解。實體書希望明年中在台灣出版。) 序 在時代裂縫中尋回人之為人 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遇見「明慧」,那時我們都年輕、倉皇,對世界充滿饑渴卻又不知如何張口;半世紀後,我遠走英倫,她依舊在風雨飄搖的香港守望。我們以書信重新搭起一座橋 ── 二十封長短不一的信札,鋪展成今日你手中的《夕陽西下幾時回...
第二十封信 20.2 生命回顧與個人歷史的重要性 明慧,讓我與你分享關於個人歷史保存重要性的一些思考。研究表明,個人歷史保存對心理健康、身份維護和代際連結具有根本重要性。個人歷史保存服務於多個關鍵功能:通過身份肯定增強心理健康,為家庭創造有形遺產,保存文化知識,並通過智慧傳播為老年人提供目標感。 生命回顧和回憶活動顯著改善老年人的抑鬱、生活滿意度和心理健康。這些益處通過整合生活經驗、解決過去衝突、增強連續感,以及從積累經驗中積極創造意義來運作。 現代遺產保存方法包括回憶錄寫作、口述史專案和數位多媒體方法。研究表明,回憶錄寫作刺激認知功能,同時創造有意義的家庭遺產。口述史專案對文化保存和可及性特別有價值。數位生活故事書即使對有記憶困難的老年人也顯示出積極結果,通過多感官參與強化自我感。...
第二封信下篇兩岸三地的際遇1977年我離開香港,初次見識到德國當地的學生運動,第一次經驗到他們的競選文化。同時期,香港的97問題還未出現,直至兩年後,香港前途始成為英國與北京的談判對象。但在這談判中,香港和香港人並不參與其中,我們香港人的命運不在我們自己的手裡。1997年中英租約期滿之後,英國再不能在新界有任何的統治權,在這個背景下,香港人為什麼從沒考慮這問題?在這環境下,香港究竟具備著甚麼意義?從少到成年,殖民地教育下,我們似乎自由的學習,在安樂窩中成長,但學校從來沒有真正的人文教育,香港歷史不是議題,中國和世界歷史和文化只是浮面的教過。在「借來的時間和地方」,我們「享受」這種割離大陸、台灣、亞洲和世界政治的「中立」環境生活。大部分當時的香港年輕人不知道也不太關心二次大戰後的政治危機、台海兩岸的戰爭狀態、冷戰帶來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大陸50年代的殘暴政治運動和台灣「美麗島」事件,這些似乎對我們是太遙遠的事。1967年暴動後的香港,是現代香港的起點,在港的年輕人開始感覺到自己身份的問題。我當然也是其中一個。當時在德國,香港人不多。香港留學生通常到英語世界攻讀研究院,來歐洲德國或法國,首先面對的是語言問題。在自由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 )唸哲學的亞洲學生,大多是日本和韓國人,他們慕名而來研究胡塞爾和海德格的現象學,但其中也有來自台灣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從台灣來的學生,有不少是台獨傾向。當時的台灣,仍是蔣經國的戒嚴時代,美麗島事件令很多台灣人受到很大的壓迫,反對國民黨便要離開家鄉到外地流亡。我當時便認識了幾位台灣朋友,有一位修讀博士學位的,讀了多年也未有完成,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不寫完博士論文,他帶一點悲傷的回答:「完成了博士,就要離開德國,但我沒有家可回!」那時我不明白他的感受,因為只知我拿德國政府獎學金,完成學位之後便可以回家!我不想留下成為德國人,因為有家人在香港等待我回來。到現在,我才明白這位台灣朋友的悲哀!香港淪亡了,再不能回去。我們是流亡海外的異見人士。隨後到了70年代後期鄧小平改革開放,逐漸有大陸來的朋友,他們是第一批文革後出國的內地人,在大陸以教德文為生,來西德(當時德國還未統一,仍分東,西德)考察德文作為外語教育。和幾位相熟,從他們口中得悉文化大革命對他們的傷害,殘酷政治鬥爭令他們生活在人間煉獄之中。1976年打倒四人幫之後,大陸似乎露出一點曙光,我的大陸朋友當時相信最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後來認識一位同行來西德進修哲學,但他回想起文革時的慘痛經歷欲哭無淚, 他親眼看見中學校長被紅衛兵打死、英文老師被批鬥後得了憂鬱症,最後吊頸結束生命,他也被下放到農村再教育,過著飢餓無助的生活。後來他克服困難,文革後重返學術世界,並且到德國留學,之後成為大陸一個重要的海德格哲學學者。比起這些台灣和大陸朋友,我這香港人幸福得多!我們習慣自由,有法治保護、個人權利受尊重。我們不理解在獨裁強權下生活是怎樣的。我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是看陳若曦的《尹縣長》而來,理論是從《七十年代》文章得知,但從這些朋友的敘述當中,文革災難是真實的,不是小説和報道。香港的政治打壓,從2014年雨傘運動到2019年,再到今天,未見減褪,而且力度愈來愈大,愈來愈高壓,這股政治低壓槽在過去幾十年的香港從來沒有出現過。香港一直得天獨厚,擁有和平、安全和穩定的環境,反之,與我同時代出生的人,無論是大陸或是台灣,他們所面對的經歷都是我們從未想過,從沒經歷過,他們所受的痛苦,是我們香港人無法想像的,他們面對的悲慘景況我們亦無從感之。當然,2019年之後,我們便知道,這慘痛悲傷我們不能避免,而今都在我們的面前! 公民參與塑造社會在德國我亦同時經歷了德國人的公民選舉,競選期間不同黨派的政治家和政客會走到大學及市集裡演講,給他們的選民講解自己的政綱和論點。在自由堡的競選演講,在電視看到國會的辯論等等,都是我在香港沒有經驗到的。那時我才發覺德國在戰後的發展裡,是一個真正民主模式的開放社會,公民參與政治這種現象我是從未感受過的。作為一名海外留學生,他們的政治活動我不能參與,但作為旁觀者,我深切明白到透過每個公民自身參與的重要性,讓德國人知道這個屬於人民的投票權可以如何改變整個社會。我還記得將近離開德國的時候,在電視中常看到當時西德總理舒密特Helmut Schmidt,在最後一天的國會演說中說:投票結果他的黨輸了,在他完成了這最後一天的德國總理工作後,第二天他就變回漢堡的一名普通公民。換句話說,參與政府工作的時候,他的身份是總理,當他完成總理的職責時,他就變回公民身份。他的這番說話對我感受殊深,至今依然歷歷在目,印象難忘。當權者是透過人民和憲法賦予權力,是要服務人民,而不是控制人民,更不能戀棧權貴。參與政治活動是德國人作為公民非常重要的部份,至今德國人對二次世界大戰為世界帶來無比災難和痛苦還存著深深的罪咎感。當時東西德還未統一,但前往參觀慕尼黑達豪(Dachau)集中營時,我發覺德國人從沒有忘記這段歷史。在對歷史不遺忘的同時,德國人對上世紀由專制政權製造出來的舉世災難、知識份子讓一個政黨以口號帶領人民步向災害,依然有所警惕,深深悔咎。現時德國境內還有不少集中營博物館開放予公眾憑弔:不能忘記歷史。獨裁者從來只是滿足一己的權力私利,永遠不會真正為人民建立自由和諧幸福的生活。中英談判下的香港一代我在80年代初中英談判開始時,對香港問題仍然一無所知,1979年到1980年期間我在德國才知道香港的情況,北京和倫敦即將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大學時代,唐君毅老師所說的花果飄零,再加上理解到過去一百多年來西方列強對中國帶來災難,我感覺到這個談判將會帶來一個結果,那就是香港是要回歸大陸:但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香港要回到共產主義的極權大陸。這如何可能?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