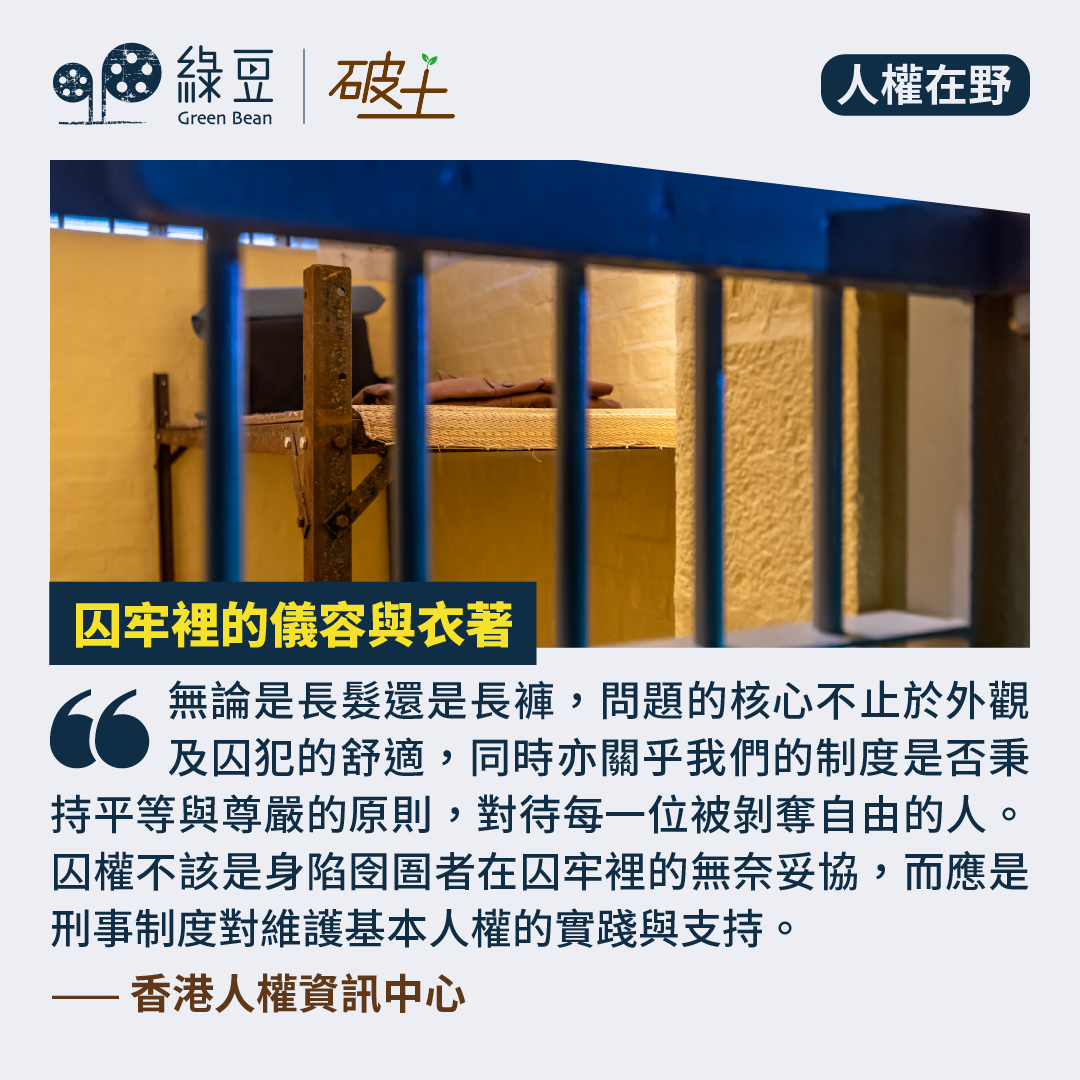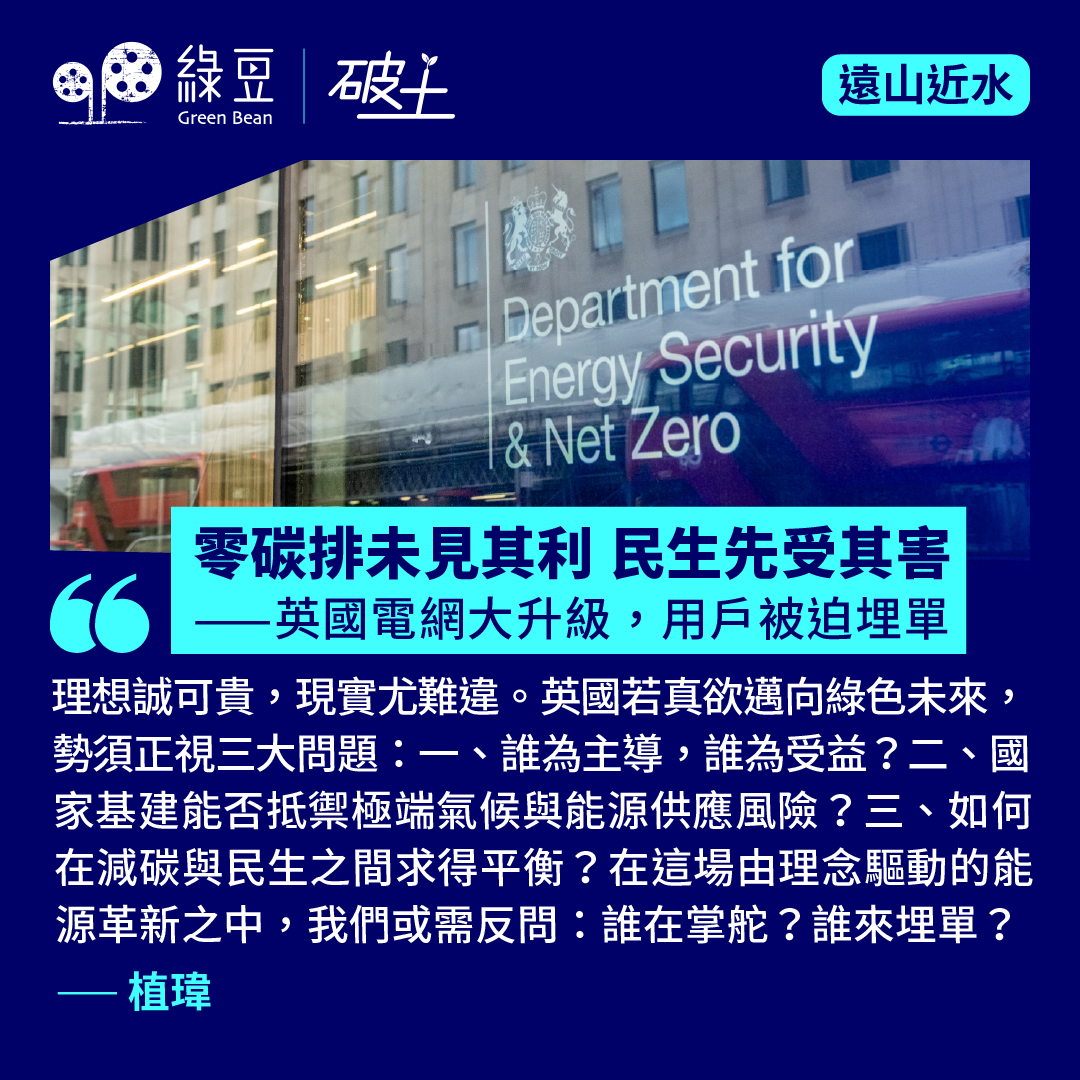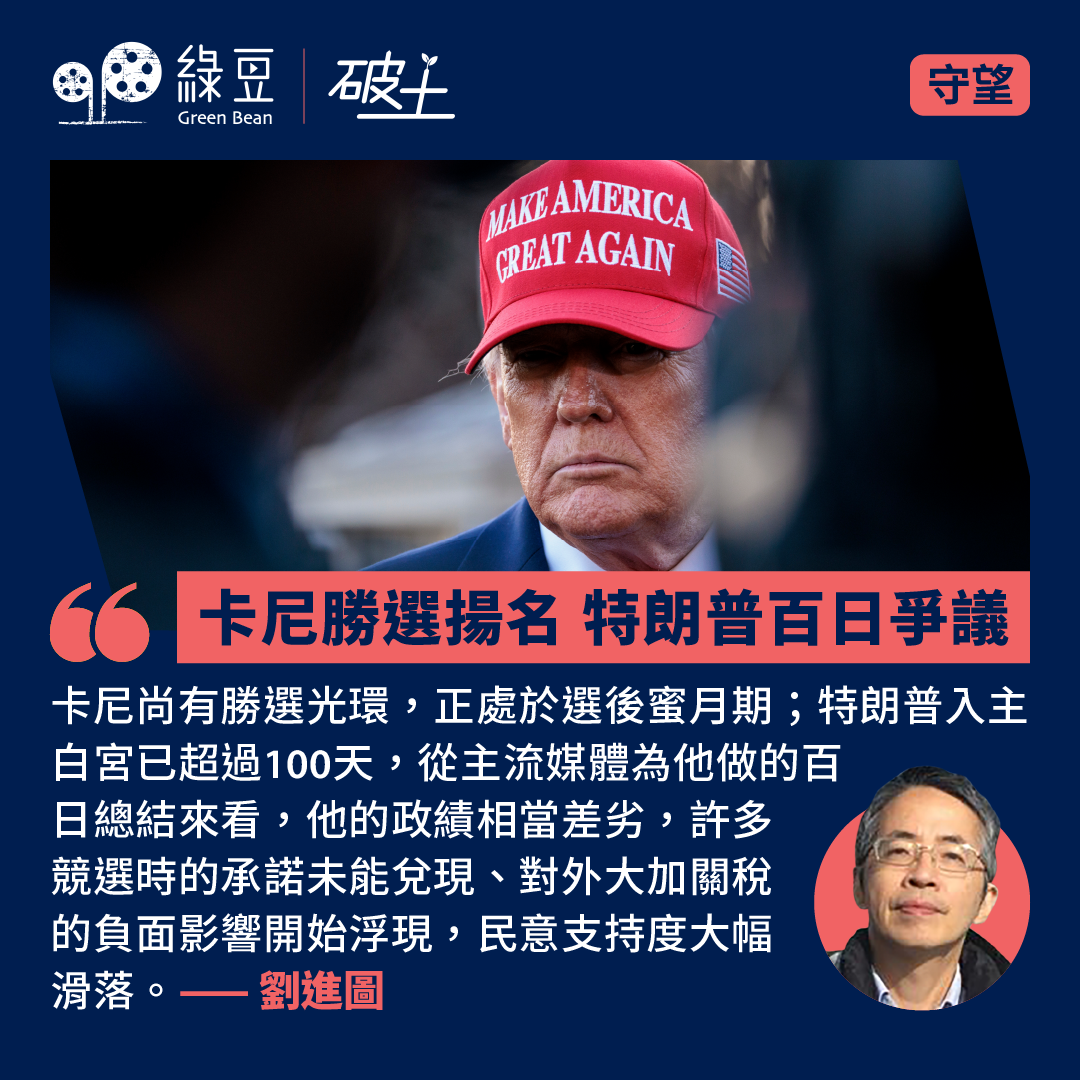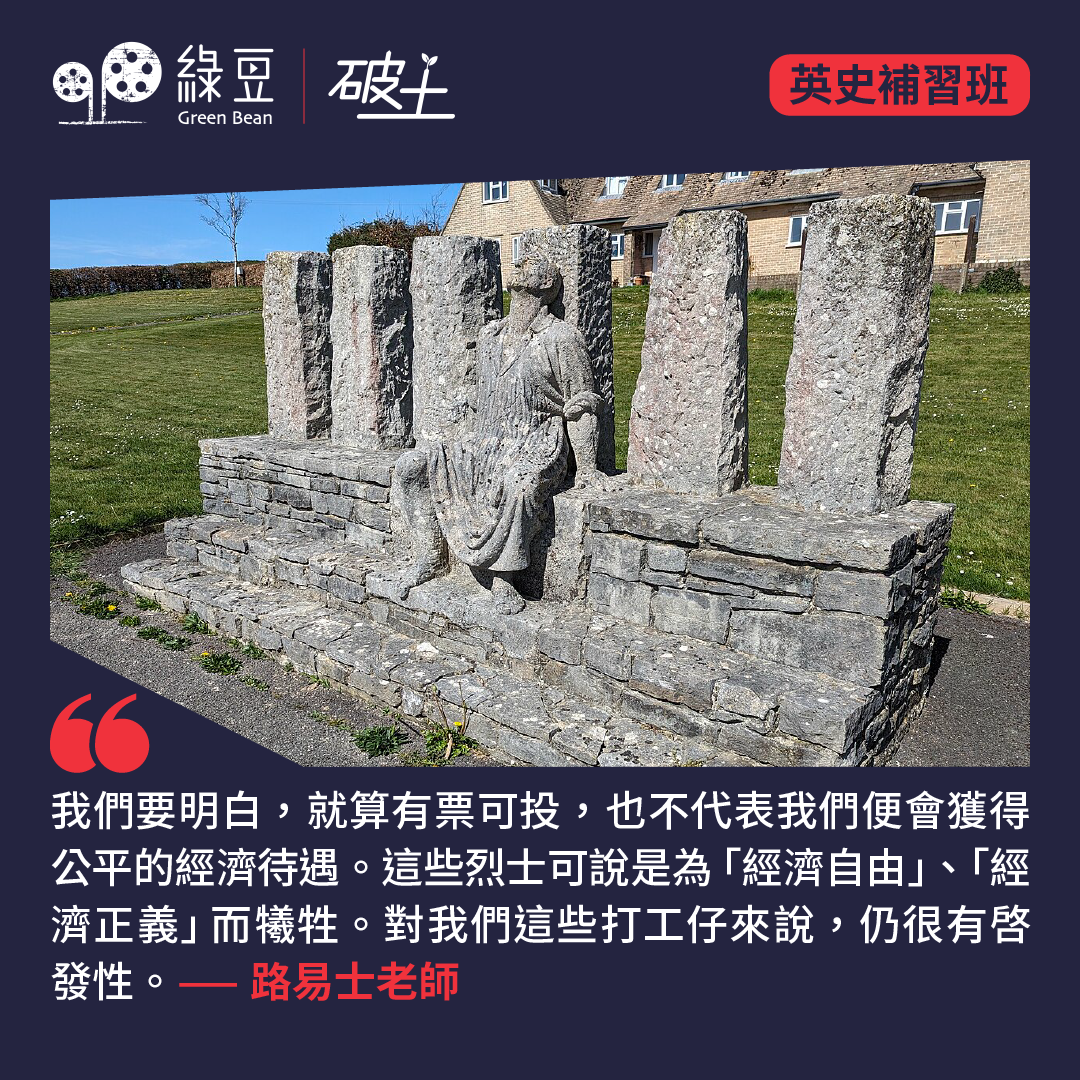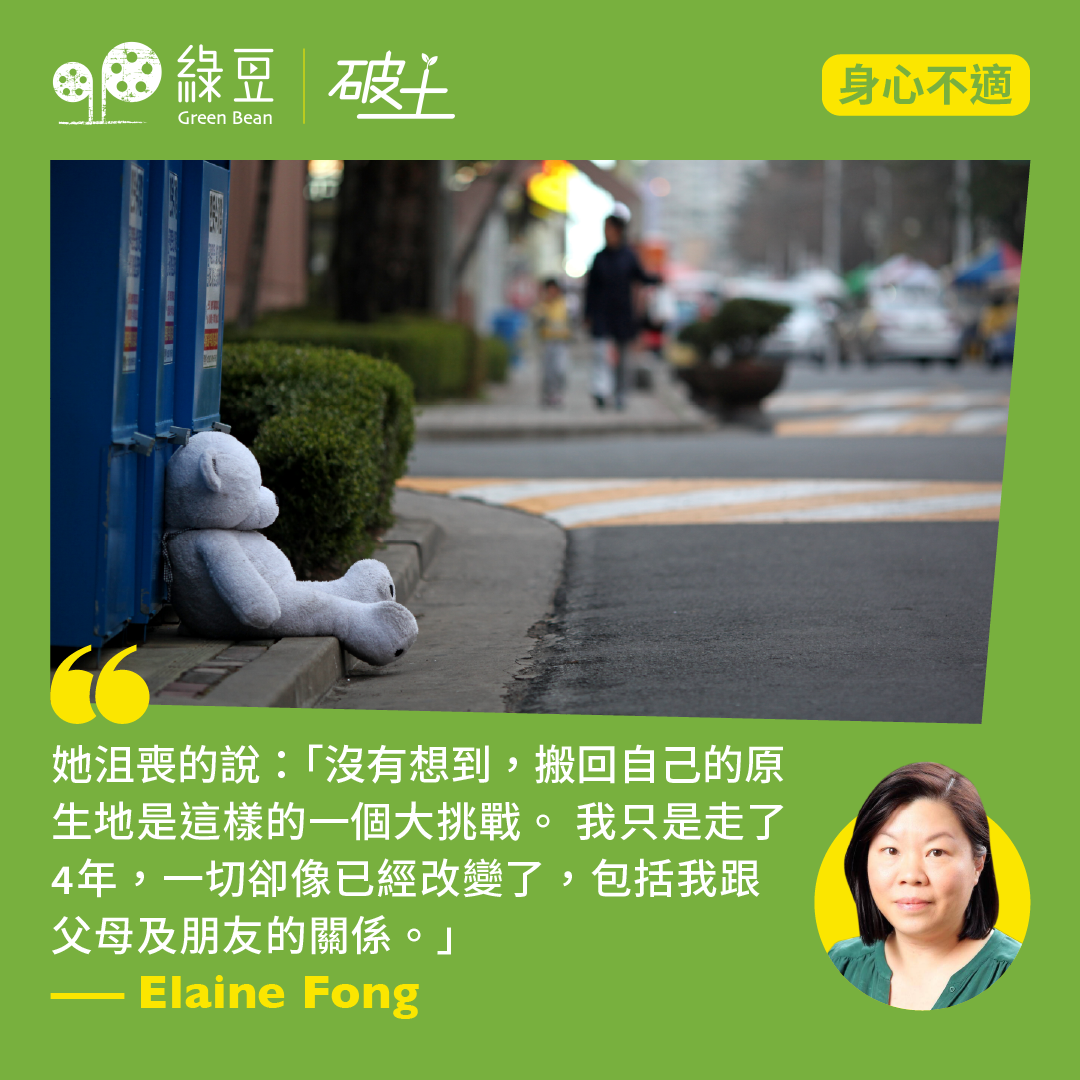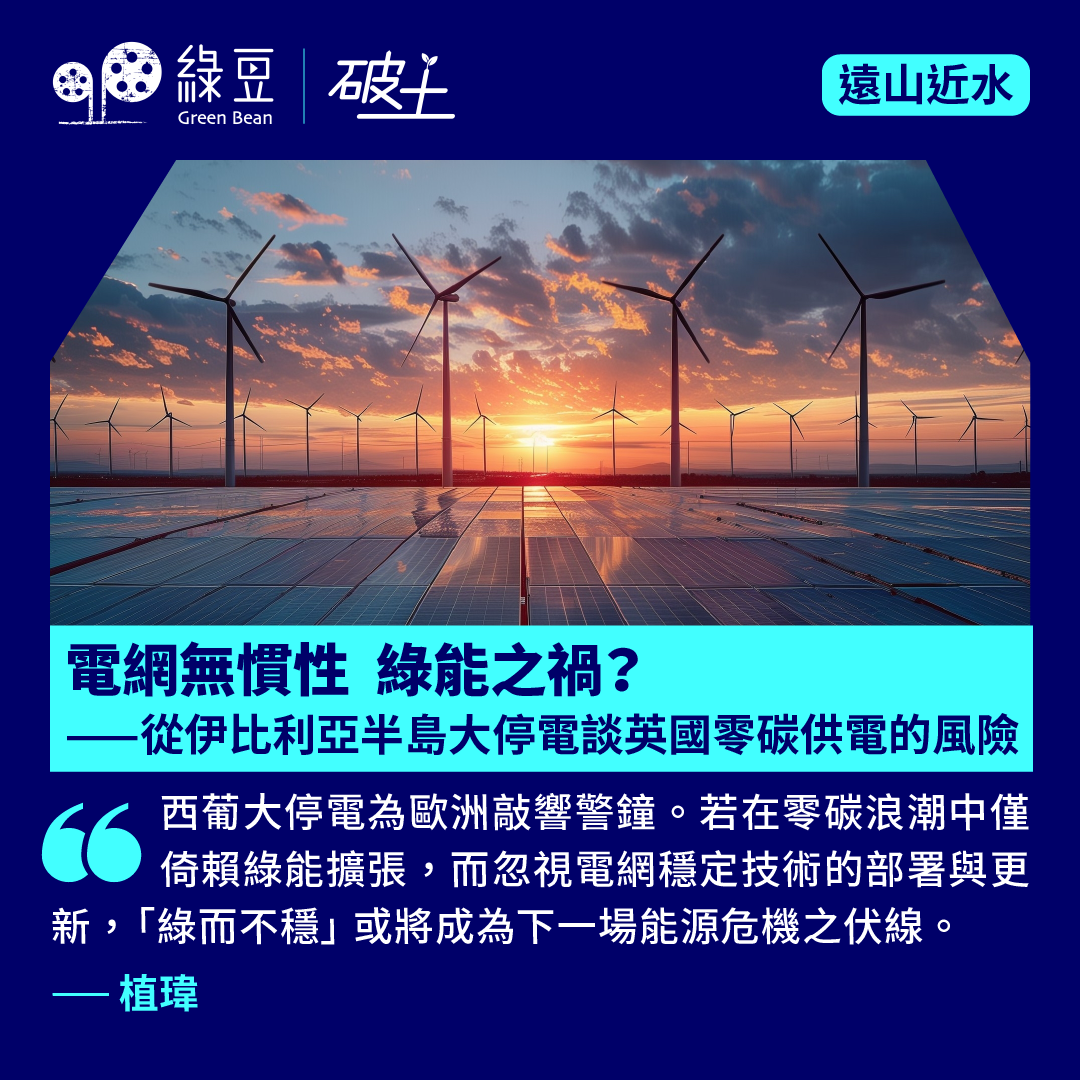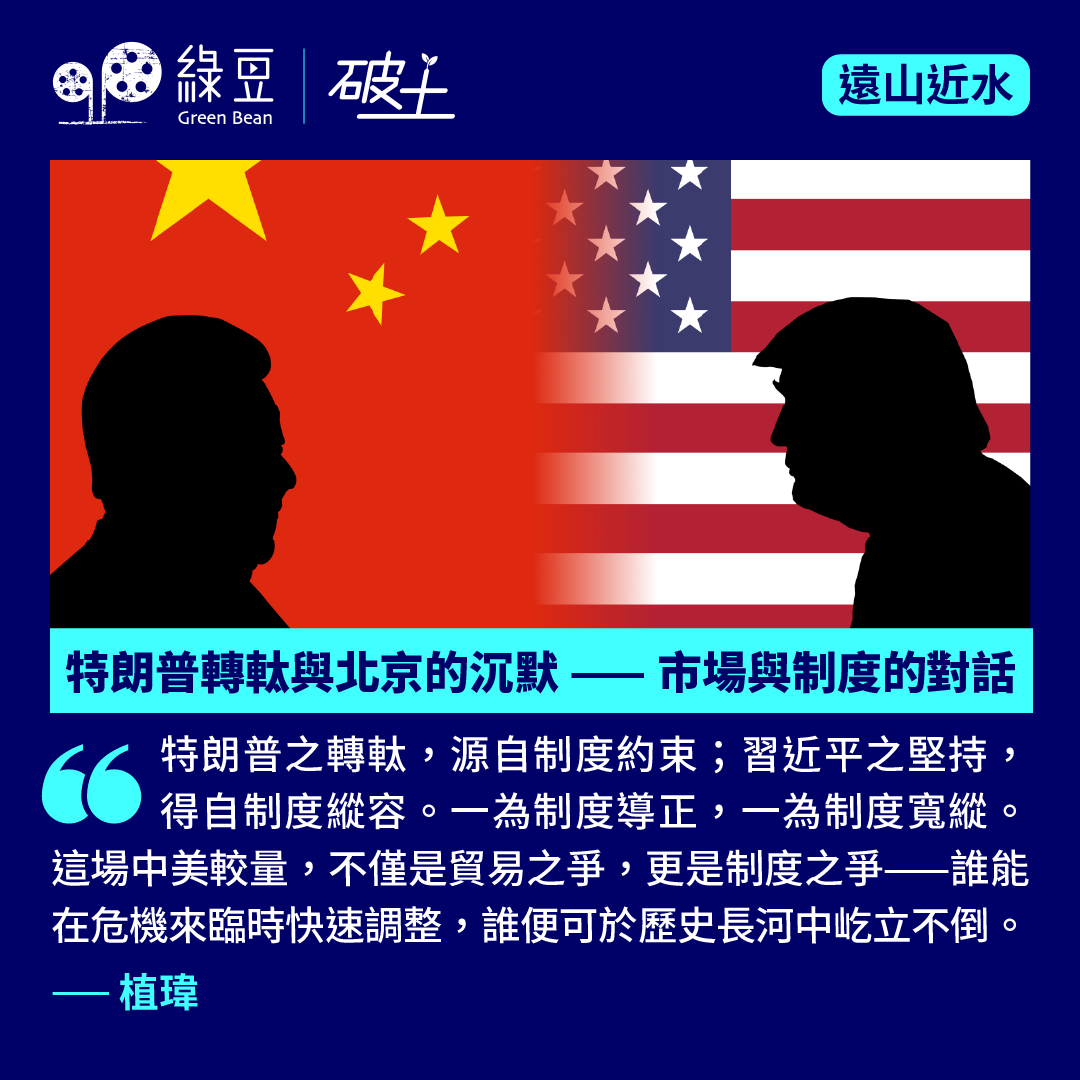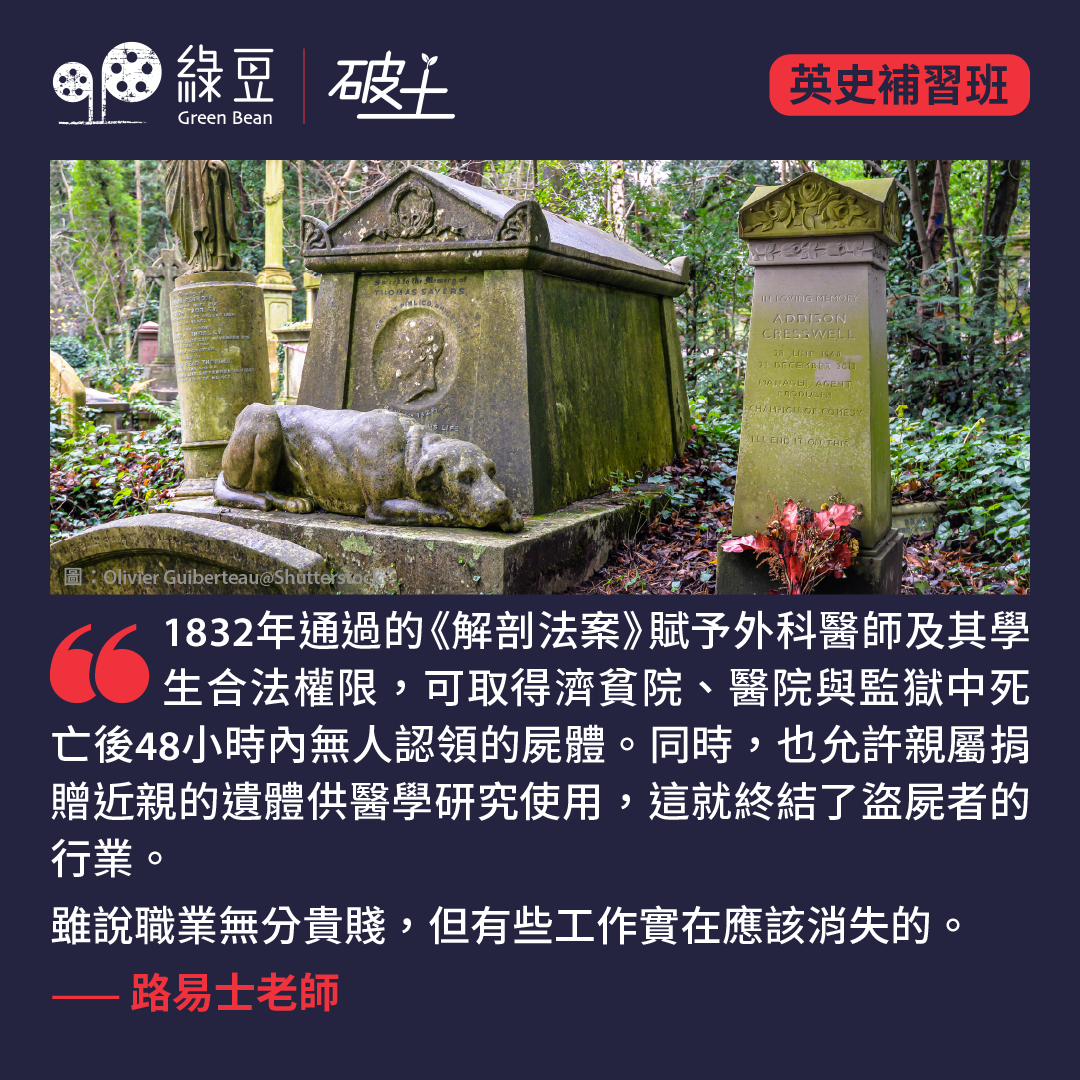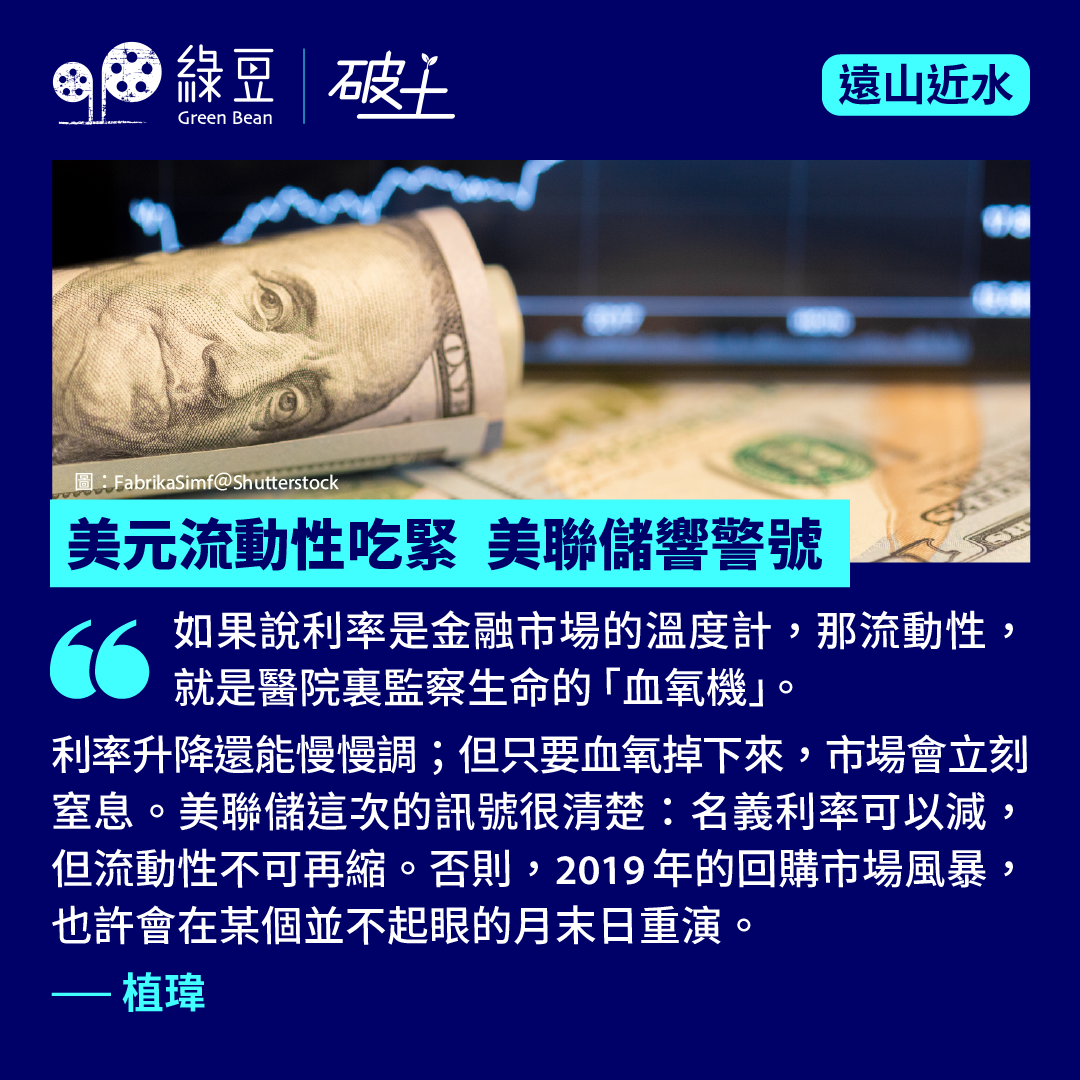在香港夏季的潮濕酷熱中,女性囚犯被迫穿長褲參與日間活動,而男性囚犯則可以換上短褲。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針對這一政策提出司法覆核,認為懲教署的服裝規定構成性別歧視,不僅違反平等原則,還因加劇酷熱環境下的不適而涉嫌不人道對待囚犯。她提出的挑戰提醒我們,囚權不僅是免於酷刑的權利,更是在監禁中獲得公平與人道待遇的基本保障。 國際人權標準:囚權的法律基石 囚犯權利的保障根植於國際人權法。《世界人權宣言》第5條禁止酷刑及不人道或侮辱性待遇,奠定了人性尊嚴的基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7條重申此原則,第10條強調即使是被剝奪自由者亦應受人道對待,第26條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禁止基於性別的歧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要求消除女性在監禁環境中的不平等待遇。 1990年聯合國通過的《囚犯待遇基本原則》第1條已明確表示規定,囚犯應享有與自由人同等的核心人權,除非因監禁必要性受限;第2條亦同樣提出禁止任何因性別等身份施加歧視。2010年制定的《聯合國女性囚犯待遇準則》(Bangkok Rules)針對女性囚犯,第19條要求服裝適應氣候並尊重尊嚴,避免性別差異加重負擔。 梁國雄的長髮 鄒幸彤的司法覆核並非孤例,梁國雄(長毛)亦曾因男性囚犯須剪去長髮而入稟申請司法覆核。梁國雄於2011年衝擊立法會遞補機制論壇,2014年被裁定刑事毀壞及擾亂秩序等罪成,判囚4周,入獄時被剪去長髮。根據懲教署《工作守則》第41-05條,男性囚犯頭髮須「盡量剪短」,而女性囚犯無此限制。他被迫剪去標誌性長髮,遂提起司法覆核,指控政策違反《基本法》第25條(法律面前平等)及ICCPR第26條,構成性別歧視。...
英國家庭電費將顯著上升,非因俄烏戰火重燃,亦非天然氣價格波動所致,而是為配合政府邁向「零碳排」的氣候政策,全國配電網絡須作大規模升級。工程浩大,開支以數十億英鎊計,惟政府無意由庫房或企業負擔,反將重擔轉嫁至民生——以電費加徵名目,普羅大眾被迫埋單。能源監管機構Ofgem日前公布新規,要求九家地區配電公司投資重建其網絡。此項升級計劃預定於2028年啟動,並持續至2033年,旨在為配合英國邁向2050年零碳排的氣候目標,應對因電動車及電力供暖普及而大幅上升的用電需求。預計至2050年,全國用電量將較現水平增加一倍以上。Ofgem網絡價格監管總監Steve McMahon估計,需投入數千億英鎊。電網收費將節節上升所謂「配電網絡」,即負責將高壓輸電系統輸出的電力,轉送至千家萬戶的地區性基建。這九家配電商分區壟斷,且多為外資掌控:倫敦與東南英格蘭由李嘉誠旗下長江基建持有的UK Power Networks掌管;東北則屬巴菲特的巴郡(Berkshire Hathaway)旗下Northern Powergrid營運;西北則屬日本關西電力;蘇格蘭兩區由西班牙能源巨擘Iberdrola旗下的Scottish Power經營;其餘地區則由SSE與National...
加拿大國會大選剛結束,執政自由黨在卡尼( Mark Carney )領導下勝出大選;在野保守黨成績沒預期那麼差,但黨魁在自己選區丟失議席;第三大的新民主黨大敗,黨魁引咎辭職。卡尼上台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打算如何與特朗普(Donald Trump )...
在英國,教師有工會且勢力頗大,路易士老師在此地就親身經歷過兩次為爭取合理薪酬的罷課。在香港則「罷課」仍不「罷學」,堅持要給學生公民教育,可見華人老師使命感特強,權利感則較輕。然而,當我們說英國工會真「厲害」時,也時會抱怨會費不輕。但細心再想,比起血,二三百英鎊其實又算什麼? 歷史就是血的教訓。其一個不能不說的案例是「托爾帕德爾烈士」(Tolpuddle Martyrs)。先說說背景: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法國君主制被推翻,統治階級被送上了斷頭台。英國的地主和政府看到這樣的情況後,對勞動階級產生強烈的猜忌,並抱持著集體意識,決心不擇手段鎮壓任何組織抗議的行動,更不容許勞動階級成立工會。 英國高速工業化和城市化,令部分人富起來,但也導致大量工人處身於貧窮,只能獲取低薪,他們開始組織工會(trade union)為自己爭取權益。政府擔心工人階級在英國發動革命,遂對他們的抗議行動進行了嚴厲的懲罰。政府尤其顧忌「大英國民綜合工會」(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 編按 : 此專欄內容均為真實處境,旨在反映家庭、婚姻及個人之間的複雜性,以文字與大家一起走過荊棘。專欄文章經編輯在文字上修改處理,確保內文提及的人士身分保密。) 初次跟小善見面,是她準備回去原生地 —— 韓國。大學畢業後她在家鄉工作幾年,偶然機會下找到來英工作的機會,便與丈夫和孩子離開家鄉到英國去。最初很理想地,她先好好工作,丈夫在家帶小孩。但隨著孩子長大及經濟有壓力,一個人的收入應付不了一家的生活開支,丈夫開始嘗試找工作,惟找了兩年也無果。最後,一家人決定離開英國,回到韓國生活。...
日前橫掃整個伊比利亞半島(Iberian Peninsula)的電力大停頓,震撼歐洲能源界。西班牙、葡萄牙兩國幾乎同時陷入癱瘓,交通燈熄滅、列車停駛、通訊中斷,醫院靠備用發電機勉強維持運作。起初,西班牙方面懷疑遭遇網絡攻擊,葡萄牙則歸咎於天氣異常,後來歐盟能源界專家指向一項更根本的結構性問題——綠色能源比重過高、慣性不足,導致電網抗壓力大減,一遇小故即全盤崩潰。 無慣性系統下的連鎖反應 電力系統的穩定,有賴於電網的「慣性」(inertia)—— 這是一種由旋轉機械(如燃煤、燃氣、水力發電渦輪)自然產生的動能緩衝,在遇上突發事故(如供電中斷、電壓波動)時,能以物理方式暫時維持頻率與穩定。問題在於,風力與太陽能發電均不具旋轉部件,因而無法產生慣性;系統一失衡即容易陷入故障。 據報,事故當日西班牙再生能源佔發電量高達八成,燃氣發電則因中午需求低迷而處於低負荷狀態,整體電網慣性極低。電壓或頻率一旦出現異常,反應時間大幅壓縮,營運商未及應變,已告失控,遂釀成連鎖式癱瘓。葡萄牙本土雖無直接事故源,亦因電網互聯而同步遭殃,電力一體化之下,風險亦成聯動。 電網的脆弱性...
Aimed at “improving” the electoral system, the...
日本當代著名建築師隈研吾的角川武藏野博物館是一個現代建築與雕塑藝術完美結合的範例。這座建築利用石塊作為外牆的主要材料,不僅展現了建築的堅固性和自然美,還充分體現了周圍環境的特性。隈研吾設計的這座博物館,放棄了他之前以木材作為建築元素,將石塊的質感與形狀巧妙地融入整體設計中,使建築本身成為一件藝術品。外牆的石塊排列不規則,營造出一種流動感,仿佛是在與自然環境對話。在雕塑藝術中,形狀和質感是兩個至關重要的元素。隈研吾在設計中運用石塊的不同紋理和色澤,使得整體外觀變得生動而不單調。每一塊石頭都有自己的性格,這些自然石材的呈現讓人聯想到大自然的力量與美感,從而引發觀者的情感共鳴。當陽光透過不同的角度照射在石牆上,形成光影的變化時,建築彷彿也在不斷地變化,散發著生命力。總結來說,隈研吾的角川武藏野博物館展現了現代建築作為雕塑藝術的可能性。藉由獨特的石塊外牆設計,建築從協調的視覺效果到和諧的環境關係,皆體現了他對自然和人文的深入理解。這樣的建築作品,既是功能的實施,也是藝術的探索。 ...
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素以言行反覆著稱,惟其近日於兩件事上的「轉軚」,尤顯耐人尋味:一是忽然收回罷免聯儲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之強硬態度,二是於中美貿易戰中釋出願意放緩關稅攻勢的訊號。這兩項看似策略性後退,背後原因卻明白不過——金融市場已響起警號,美國債、股、匯三市共振,合奏出一首特朗普不能不聽的市場交響曲。2026年是美國的中期選舉年,民意與選票使他不得不慎。 反觀北京方面,大可充耳不聞 —— 中國之政治架構,容許決策者既不需回應市場訊號,亦毋須向選票負責。特朗普須時刻關注美股表現、國債孳息與美元走勢,但習近平則可無視滬深兩市震盪、青年失業率攀升,甚至民企哀鳴。 美國的自我修正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