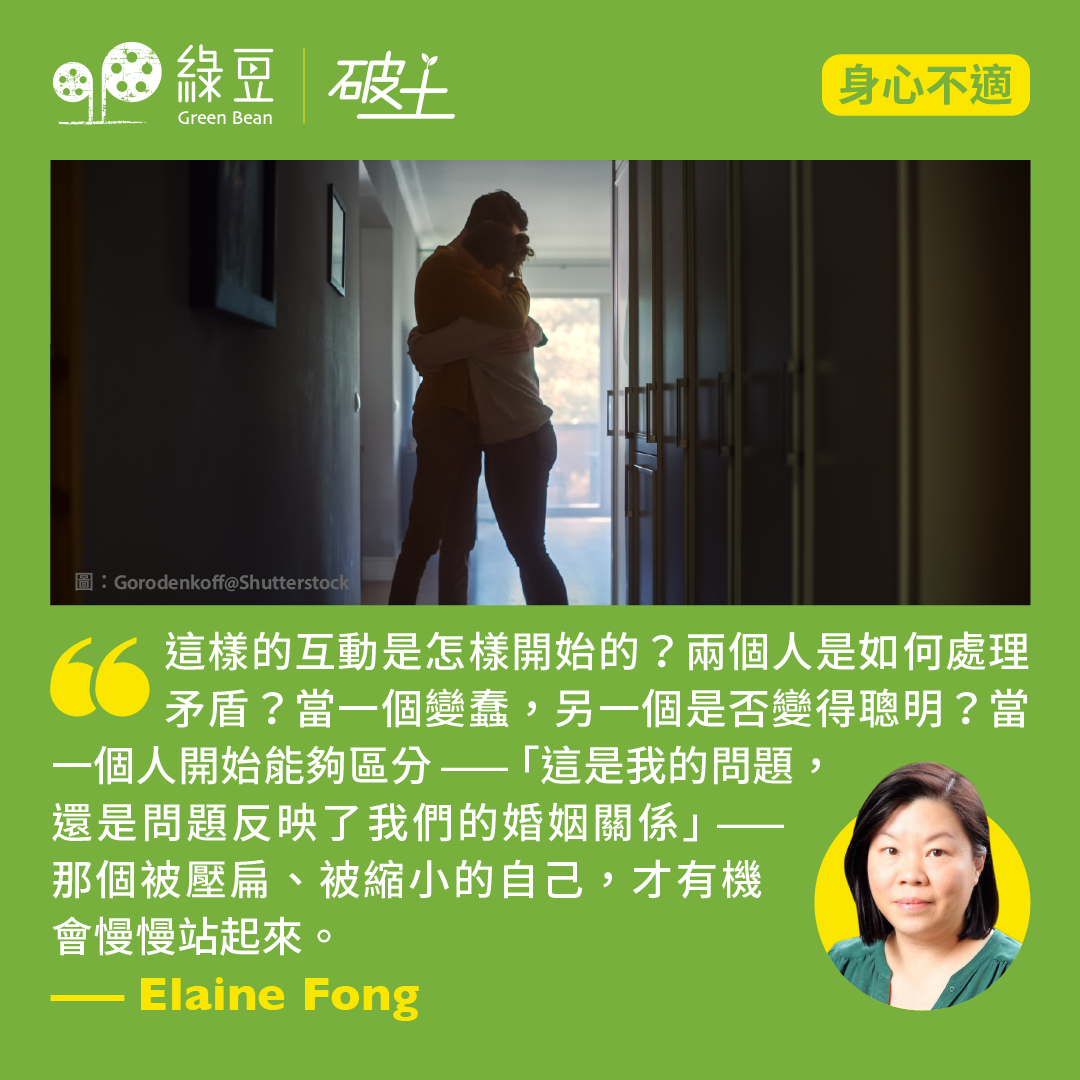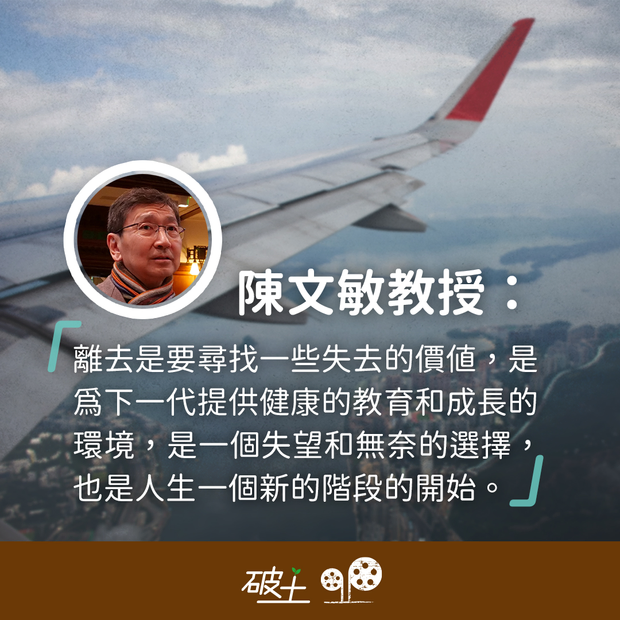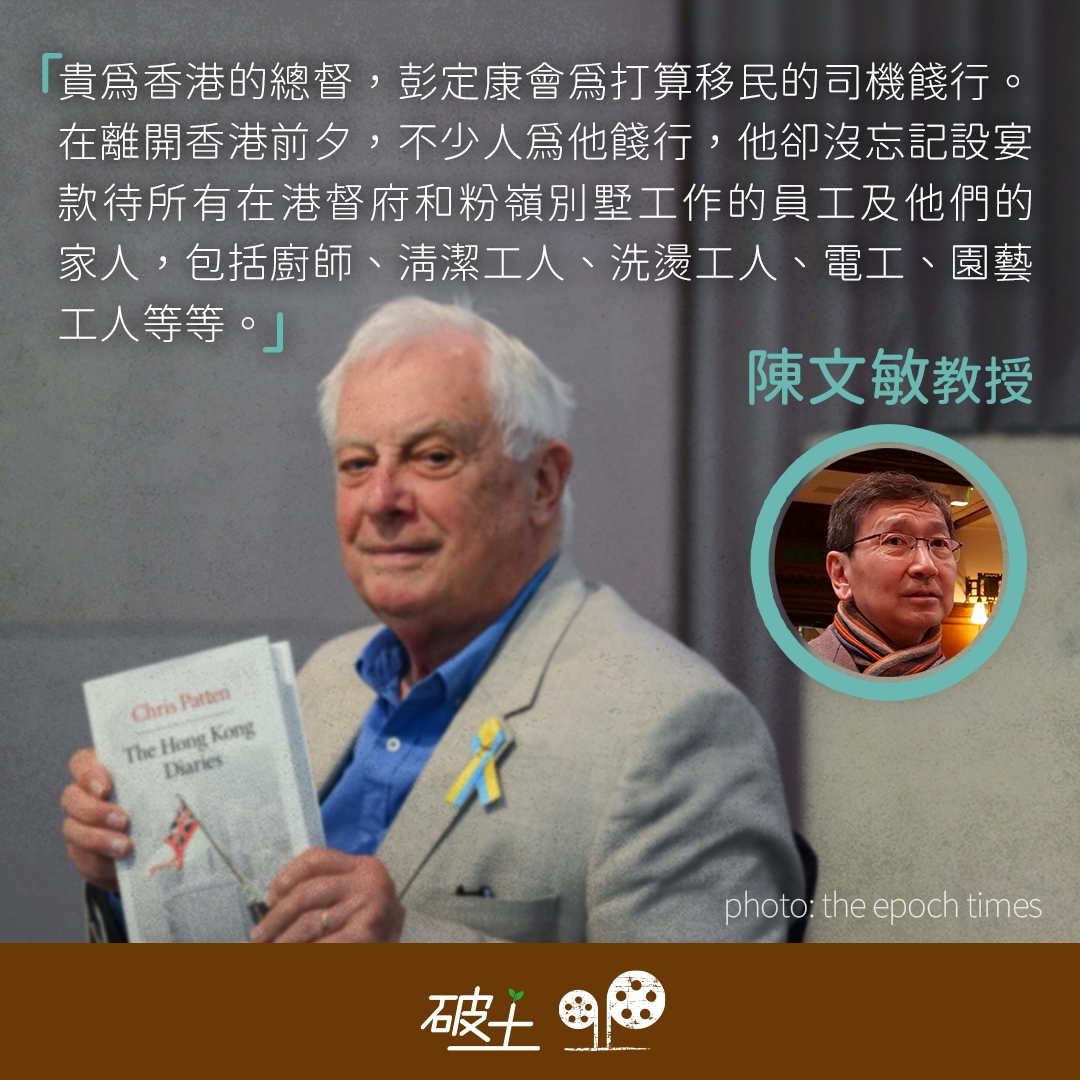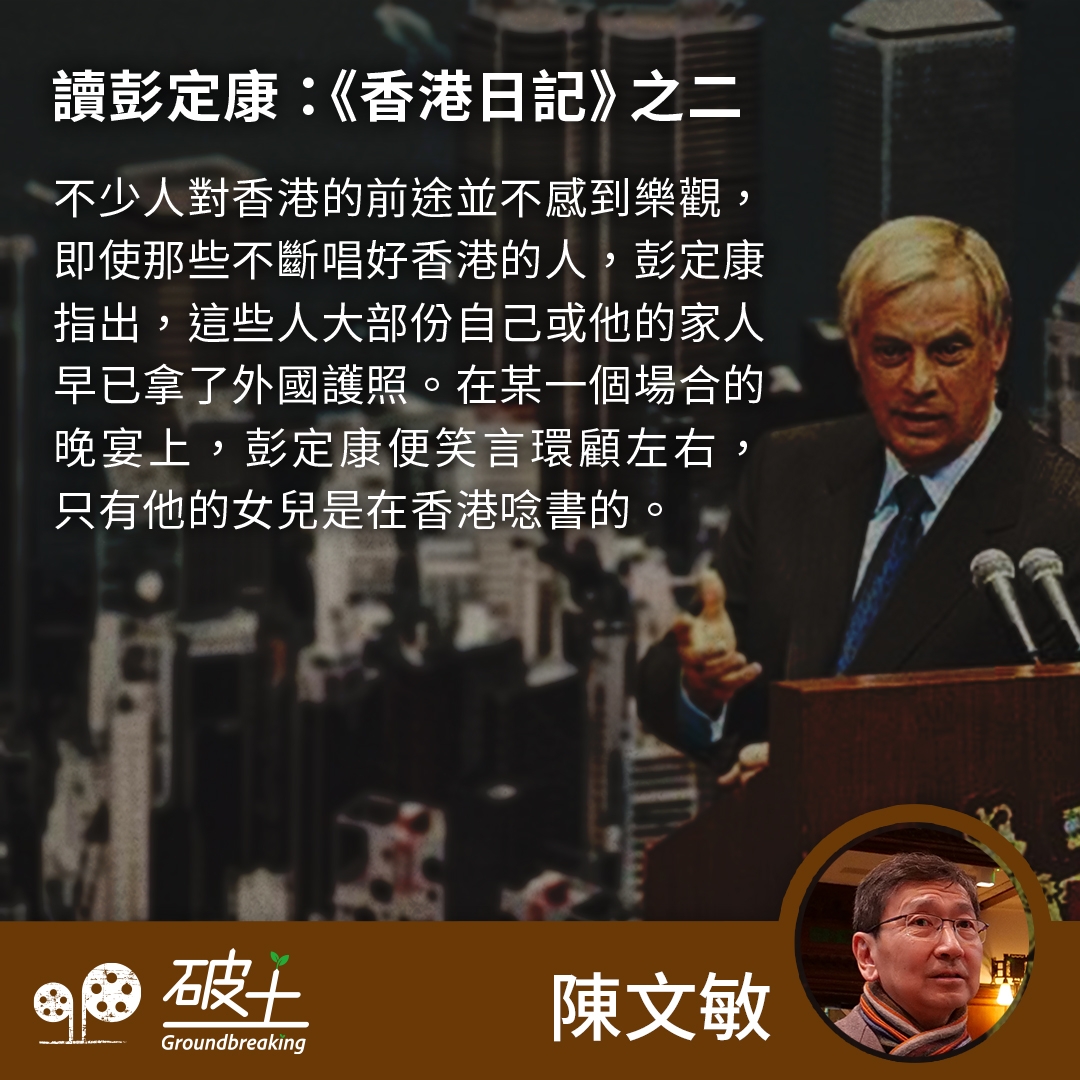否決《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與香港法治的憲制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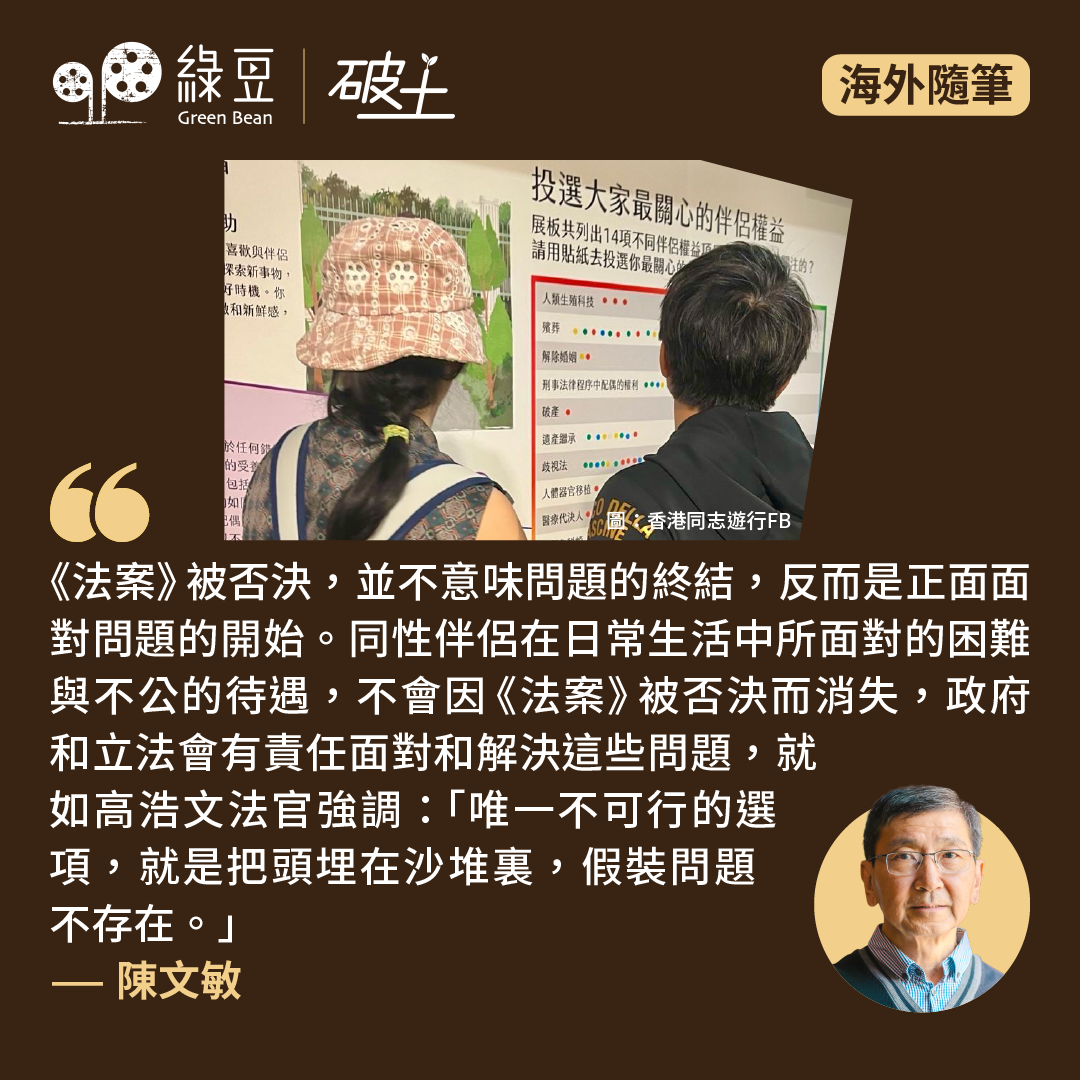
一、前言
2025 年 9 月,香港立法會以大比數否決了《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下稱《法案》)。[1] 該《法案》原本是政府為回應終審法院在《岑子杰》一案中的判決而提出。 [2] 該判決依《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下稱《人權法案》)第 14 條(保障私隱與家庭生活權利),要求政府在兩年內建立一個法律框架,以承認同性伴侶的關係。 然而,《法案》在寛限期屆滿前夕遭立法會否決,這發展引發一系列關於法治、憲制秩序與社會共識的問題。
本文將探討:(一)《法案》被否決後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二)法院判決之法律效力與立法會的責任;(三)否決《法案》引發的憲制問題,並回應有關「立法會不是橡皮圖章」的論述及其誤區;(四) 近日一宗關於同性伴侶爭取在孩子的出世紙登記為家長的案件;以及(五)未來社會與司法的路向。
二、法院判決與特區政府的責任
即使《法案》遭否決,有兩點仍是相當清楚:第一,終審法院的判決依然有效,同性伴侶在日常生活所遭受到的滋擾,令欠缺法律框架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情況構成侵犯《人權法案》所保障的私隱和家庭生活的權利,這法律原則仍然適用和有效。第二,政府有責任訂立法律框架保障同性伴侶的關係,這責任不會因立法會否決修例而告終,政府仍有責任繼續落實法院的判決。
政府早前已明確表示不會申請延長終審法院判決中所給予的兩年寬限期(period of stay)。 然而,政府在寛限期內未能完成立法,並不表示政府已完成了其法律責任。寛限期的意思是在寛限期內法院的判決未開開始生效,以使讓政府在寛限期內作出相應的措施,而不會在這段期間因未能落實法院的判決而被視為藐視法庭。寛限期結束,表示法院的判決開始生效,雖然目前仍未知政府將會如何跟進事件,但政府冷淡的回應多少反映了其執行判決的意圖。相比以往在一些政府重視的法案中政府所採取的積極游説和推動的態度,本案中政府為爭取立法會支持的努力,便顯得流於形式,態度亦可謂相對冷淡。例如修例在兩年寛限期的最後三個月 (還是在暑假開始時)才提出,亦未見政府對個別政黨或議員作積極游説,更未見有大型的公眾推廣活動,向市民及議員詳細解釋法院的判決。部分議員否決的原因是諮詢不足,亦有部分議員明顯誤解終審法院的判詞。
平情而論,政府確實曾提出法案,即使力度未如理想,但也算嘗試落實法院的判決,在這階段不能苛責政府,但法院判決所指的責任並非一次性,而是延續性的責任 (continuing obligation),一次做不成,不等如完成責任。兩年的寛限期屆滿後,若政府仍未落實法院的判決,即使因其曾作出嘗試未果而可能不涉及藐視法庭,但若政府就此罷手,仍有可能構成藐視法庭。法院的判決是要政府訂立法律框架保障同性伴侶關係,如何立法、一次立法還是分開立法、修改不同法例等,這些均交由政府決定,但不再嘗試立法則非選項。
政府可以再進行諮詢討論,尋求一個立法會和社會可以接受的方案,捲土重來。在爭取立法會的支持時,政府有責任作出更多解説,亦有責任尋找其他途徑落實法院的判詞,例如能否對《法案》作出輕微修改,以減低部分議員認為會衝擊傳統婚姻的疑慮,或修改一些其他法例,逐步落實法院的判決?
三、法院判決與立法會的責任
雖然宣告性判決 (declaratory judgment)在技術上僅對訴訟雙方具約束力,但法院對《人權法案》的詮釋本身即構成一項法律原則。由於《人權法案》對一切公共機關,包括立法會均具約束力,立法會有責任遵守《人權法案》下的法律責任。[3] 因此,否決《法案》不能説只是不同意《法案》的內容,而是未能履行其在《人權法案》之下的義務。
在立法會的辯論過程中,部分議員以「公眾反對」為由否決《法案》,他們認為社會上大部分人均不認同同性婚姻或同性伴侶登記。但第一,終審法院已多次指出,保障少數人士的權益,不能取決於大多數人的共識,否則少數人士的權利便永不會得到保障。第二,政府在草擬過程中並未進行充分的公開諮詢,議員所引用的「公眾反對」意見亦存在可靠性和客觀性的疑慮。
港大榮休教授卜約翰 (Professor John Burns)便撰文指出,這些所謂公眾意見,諮詢程序欠缺客觀和科學性,重點是收集人數反對修例,它們只是反映反LGBTQ活動者的動員能力,難以反映廣泛民意。[4]
相反,反對的議員完全漠視大量具科學基礎的調查。這些透過長時間和持續的調查,顯示社會對同性伴侶的接受程度有明顯的改變和顯著的支持率。2023 年由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及北卡羅來納大學共同進行的調查顯示,60% 的受訪者支持同性婚姻,僅 17% 反對。[5] 在 2013 年和 2017 年同期類似調查中,支持率分別為約 38% 和 50.4%。同時,該調查亦顯示支持立法禁止基於性向歧視的法律在 2023 年獲得約 71% 支持,比起 2013 年和 2017 年明顯上升。另一項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 於 2023 年進行的跨國調查則顯示,香港支持同性婚姻的比率為 58%,反對的約40%。[6] 此外,中文大學 2025 年針對 908 名 LGBQ+ 受訪者的研究亦發現,70% 的人表示希望或非常希望與同性伴侶結婚。[7] 這些數據均與部分議員所謂「多數人反對」的說法背道而馳。
立法會認為相關議題具爭議性,需要更多時間作深入討論,這一點無可厚非。亦即是説,否決《法案》只是開始,而非終結。立法會本身受法律約束,有責任落實法律的要求。立法會可以舉辦公聽會,聽取多方面的意見,秘書處亦可與學術機構合作進行科學和客觀的調查,研究承認同伴侶關係和維護傳統婚姻價值是否可以並存。
同性伴侶在社會上面對不少不公和歧視,這些問題始終需要解決,與其由同性伴侶就個別權利向法院提出經年累月的訴訟,是否可以有更有效和更能平衡社會各方利益和資源的解決方案?在這方面,立法會是責無旁貸的。
四、否決《法案》引發的憲制問題
部分媒體的評論,將立法會否決《法案》解讀為「證明立法會不是橡皮圖章」的例證。[8] 行會成員湯家驊亦在其面書專頁撰文認為否決《法案》並非憲法危機 [9]。然而,這些說法在憲制層面上存在謬誤。
法院對法例的解釋本身已是一項法律原則,在該原則未被推翻前,任何人包括立法會皆有守法的責任。立法會可以通過立法改變法院的判例原則,若判例的原則是法院對《人權法案》或《基本法》的解釋,那便只能透過修改《人權法案》或《基本法》才能改變法院的解釋。湯家驊的論點正犯上這個錯誤,忽略了本案的性質。立法會以法例改變普通法確是常見,但今次的判決並非一般的普通法,而是法院對《人權法案》下的責任的闡釋,立法會不能透過普通立法改變法院的判決,而是須要修改《人權法案》,更遑論立法會根本沒有通過任何立法,改變法院的判決。
倘若立法會因為「不同意」而漠視法院的法律詮釋,則意味立法會可以選擇性地遵守或拒絕遵守法律,這不是「各司其職」或「立法會不是橡皮圖章」的表現,而是立法會踐踏法治的行為。若將此邏輯推至極端,則立法會同樣可以選擇漠視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然而,無論是終審法院對《人權法案》的解釋,還是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均屬憲制性法律詮釋,對立法會具有約束力,制𧗾的途徑是修改相關法律,而非漠視相關判決。立法會將自己置於此憲制秩序以外,只會動搖法治的根基。
湯家驊的論點的另一值得商榷的地方是將法院的判決理解為《人權法案》的目標,他以2015年民主派否決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為例,認為這不能理解為違憲,但全面普選是《人權法案》明確指出的終極目標,法院的判決卻是當下政府的責任而非長遠或將來的目標。他引用2003年立法會否決特區政府提出的23條立法,解釋這是社會條件不足夠,並不能被視為違憲。這個論點有些莫名其妙,多年來,中央政府不是一直指責特區政府和立法會沒有履行第23條的憲法責任嗎?如果説沒有履行憲法責任不等如違憲,這恐怕只是玩弄文字!
在討論中,有意見認為交由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便可提供解決方案。然而,此說在此案中並不適用,因為並無任何憲制基礎讓人大常委會介入。本案判決的依據是《人權法案》第 14 條之「私隱與家庭生活的權利」,其最終詮釋權屬於香港法院,而非人大常委會。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只限於對《基本法》的解釋。其次,若要勉強扯上《基本法》,最接近的是《基本法》第37條對婚姻的保障與第30條對私人通訊秘密的保障,但《基本法》第37條保障的是婚姻自由和自願生育的權利,判詞已清楚指出,承認同伴侶關係的基礎出於對私隱與家庭生活的保障,這種關係有別於婚姻關係。至於《基本法》第 30 條,這一條僅保障「通訊自由與通訊秘密」而非普遍的私隱權,在性質上與《人權法案》所保障的私隱與家庭生活權利並不相同。 此外,承認同性伴侶關係明顯屬於香港特區的自治範疇,並無理據或法律基礎讓人大常委會以解釋方式介入。
五、另一宗近期判案
在立法會審議《法案》前夕,高等法院在《K(未成年人)訴 律政司司長》案中,[10] 裁定當局拒絕讓一名孩子在其出世紙上登記其基因母親為家長之一,構成違反《人權法案》第14條所保障的私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權利。
案中涉及一對女性同性伴侶,她們在南非註冊成為合法同性伴侶,其後希望育有自己的孩子。透過現代醫療科技,她們其中一方的卵子與一名捐贈者的精子在體外結合後,將受精的卵子植入另一名伴侶,懷胎十月後孩子誕生。兩名同性伴侶對孩子愛護有加,同時肩負家長的責任,是一個幸福的三人家庭。
孩子現今已四歲,在醫療、教育及其他生活方面很多時均需要出示孩子的出世紙,但出世紙只列有懷胎生母的名字。她們早前曾向高等法院要求宣告兩人為孩子的父母,但處理案件的歐陽法官認為現行的《父母及子女條例》僅承認一名生母及其丈夫為法律上的父母,基因母親並無法律地位。但法院對她們的境況深表同情,最終透過普通法宣告她們為孩子的「普通法下的家長」(parent at common law)。她們以為可藉此判詞更改孩子的出世紙,加入基因母親的名字,但卻遭當局拒絕,認為「普通法下的家長」這身份並不足以構成更改出世紙的理由。她們唯有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高等法院高浩文法官認為,「普通法下的家長」這概念並無助解決與《父母及子女條例》的衝突問題或誰人才可享有家長的權利和承擔相應的義務,問題的癥結還是在於對條例的解釋。
在確認誰是家長這問題上,孩子的最佳福祉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孩子的家長對他的成長、教育、醫療以至身份認同皆影響深遠,誰是他的家長可以影響孩子的一生,這對孩子的福祉至為重要。但在現行法例下,一名懷胎母親的丈夫,即使他與孩子沒有血緣關係,亦不願負起家長的責任,仍可在出世紙上登記為孩子的父親,但一名與孩子有血緣關係,全心全力愛護和照顧孩子的基因母親卻不能登記為家長,唯一的原因是她的性別。法院認為這種制度性缺陷已侵害兒童及家庭的基本權益,亦沒有足夠的理由支持這制度。
在這方面,法院指出《人權法案》第14條所保障的私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權利,包括與他人建立和發展關係的權利,當中最重要的自是孩子與家長的關係。家庭生活建基於客觀事實,包括孩子和家長的關係、感情的聯繫,生活、成長和經濟方面的照顧,但並不取決於家長的婚姻狀況或性別。代表政府一方的大律師辯稱,這些家庭生活亦可透過頒下監護令而得到認可,但法院指出,監護令只適用至孩子滿18歲,家長卻是一生的關係,監護人和家長是不同的身份。由於基因伴侶和孩子有基因關係,領養令並不適用,領養令亦未能反映同性伴侶與孩子的血緣關係。
在本案中,同性伴侶家長對孩子的關懷和照顧無微不至,充分體現對孩子的愛和承擔。至於政府政策或社會對同性伴侶作為家長並沒共識,法院並不同意這可以是限制孩子家庭生活權利的理據,少數人的權利不能取決於大多數人的同意。法院亦指出並無任何證據顯示同性伴侶作為家長會對孩子的成長或福祉有任何不利的影響。一個充滿愛與關懷的快樂家庭,必然符合孩子的最大福祉。畢竟,法例的要旨是對所有孩子提供平等的保護,不會因家長的婚姻狀況或性別而有所差異。
法院引用英國最高法院一宗案件內何熙怡法官 (Lady Hale)對家庭的分析,[11]在判詞中她指出家長 (parenthood) 可以最少可包括基因家長 (genetic parenthood),即子女為父母所親生,有基因關係的孩子、法定家長 (legal parenthood),如懷胎母親而非基因母親為家長,以及社會和心理家長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parenthood),如長期照顧孩子的身心需要,但和孩子沒有任何血緣或懷孕關係的領養父母。
高浩文法官在判詞強調,家庭的觀念隨科技及社會進步不斷演變,人工生殖等技術帶來新的家庭形式,昔日視為異數的情況,如今已漸趨常見。法官直言,社會終須全面正視這社會改變,否則將持續出現法律與現實不符的矛盾。最後法官説了一個中世紀皇帝坐在海邊下令海水不能沾濕他的腳足的故事,有人認為皇帝太過驕傲,以為自己能力勝天,可以改變自然;也有人認為,皇帝其實很謙卑,以此説明即使是皇帝亦無力改變自然。潮水最後還是沾濕了皇帝的腳足,但他沒有選擇視而不見。法官似乎借此隱喻,同性關係在社會中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法律若拒絕建立制度性的框架,只會延長同性伴侶的痛苦與不安,卻無助於鞏固異性婚姻的地位。[12]
六、未來路向
《法案》被否決,並不意味問題的終結,反而是正面面對問題的開始。同性伴侶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對的困難與不公的待遇,不會因《法案》被否決而消失,政府和立法會有責任面對和解決這些問題,就如高浩文法官強調:「唯一不可行的選項,就是把頭埋在沙堆裏,假裝問題不存在。」
在策略層面上,政府或可借鏡當年將《家庭暴力條例》改名為《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而成功將同性伴侶間的暴力行為列入條例之內的的經驗,考慮調整《法案》的名稱以減低社會的敏感反應。例如,將法案改名為《同居關係及民事伴侶登記條例草案》(Registration of Cohabitation and Civil Partnerships Bill),或採用其他較中性的名稱,可能有助於減低議員與公眾對「同性婚姻」這敏感詞語的即時反應,並將焦點放在法律效果與權利保障上,或能提高《法案》獲得立法會支持的機會。
又例如研究可否修改有關器官捐贈、家屬探監、遺產繼承等方面的條例,以及在未作全面修法前以行政措施和政策落實法院部分的判詞。清晰明確的政策文件,可以為日後違反這些政策的決定提供司法覆核的基礎。雖然這些舉措未必能解決根本爭議,但仍有助社會邁向更平等的方向和提升日後再提出較全面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法案獲得支持的機會。
有鑑於立法會的取態,涉案人士亦可以考慮向法院申請其他補救,研究可有其他方法,例如透過普通法的原則或一些現有法例的解釋,盡量落實法院的判決。
本案凸顯香港在法治與憲制秩序上的一個重要挑戰:立法會在面對法院已宣示之憲制義務時,不得以政治立場或社會壓力為由加以漠視,這是法治的基礎。否決《法案》並非「獨立」的展現,而是對憲制責任的迴避。未來,政府與立法會應透過更科學和更廣泛的諮詢、更謹慎的立法策略,並在憲制框架下履行其義務。同性伴侶的法律地位議題終需要正視,掩耳盜鈴裝作問題並不存在並非選項。
註釋
[1] BBC News, “Hong Kong lawmakers say no to more rights for same-sex couples,” 10 Sept 2025,
https://www.bbc.co.uk/news/articles/c5yqeggvwgpo
[2] Sham Tsz Kit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2023) 26 HKCFAR 1.
[3]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Cap. 383)第 7 條:人權保障對一切公共機關,包括立法機關,均具約束力。
[4] John Burns, “LegCo, same-sex partnerships, and public opinion,” (民意與同性婚姻) Green Bean Media (translated version, 17/9/ 2025): https://greenbean.media/%e6%b0%91%e6%84%8f%e8%88%87%e5%90%8c%e6%80%a7%e5%a9%9a%e5%a7%bb/
[5] Centre for Comparative and Public Law (HKU), CUHK Sexualities Research Programme & UNC Human Rights Law Program, Change Over Time in Support for Same-Sex Marriage in Hong Kong, 2013–2023 (May 2023): https://hku.hk/press/press-releases/detail/26113.html.
[6] Pew Research Center, “Across Asia, views of same-sex marriage vary widely,” 27 Nov 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11/27/across-asia-views-of-same-sex-marriage-vary-widely/.
[7] CUHK Sexualities Research Programme, Survey on Marriage Aspirations of LGBQ+ People in Hong Kong (2025), as reported 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3 January 2025: Wynna Wong, “70% of Hongkonger in same-sex relationships want to get married: survey”: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society/article/3294596/70-hongkongers-same-sex-couples-want-get-married-survey-finds.
[8] 《大公報》,2025 年 9 月,社論評論立法會否決法案「證明立法會不是橡皮圖章」。
[9] 湯家驊:否決同性關係條例並非憲制危機,2005年9月17日: https://www.facebook.com/ronnytong.hk/posts/1412835613536714/
[10] K (An Infant), by his next friend R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2025] HKCFI 1974. 報道見
“Hong Kong judge rules in favour of lesbian couple seeking to include mothers’ names in son’s birth certificate” 9 Sept 2025
[11] Re G (Childre)(Residence: Same-sex partner) [2006]1 WLR 2305, paras 36-37,見法院高浩文法官的判詞第111段。
[12] K (An Infant), by his next friend R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2025] HKCFI 1974, paras 258-259.
▌[海外隨筆]作者簡介
陳文敏,前香港大學公法講座教授,2021年退休後,旅居英國,並出任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名譽教授(Honorary Profes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