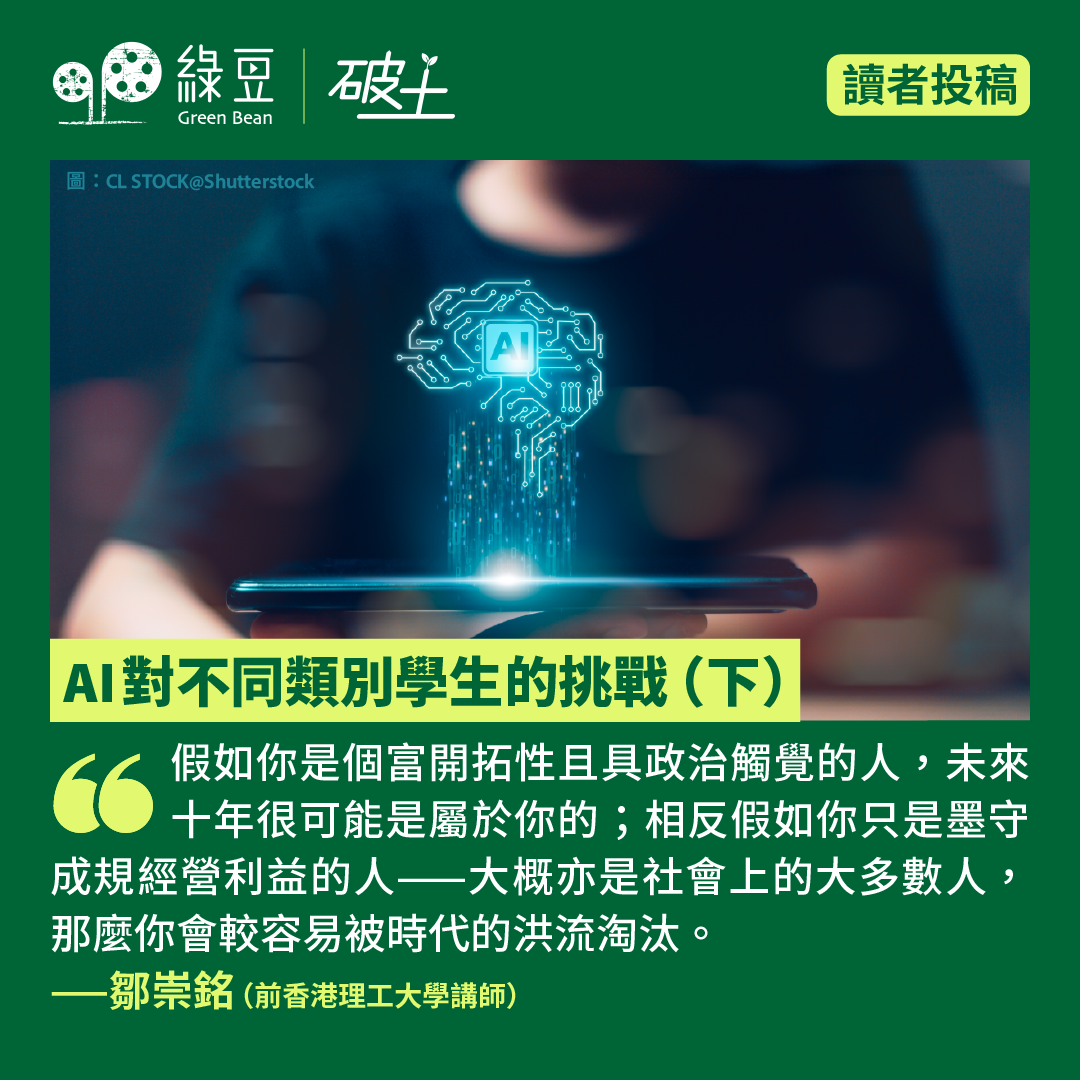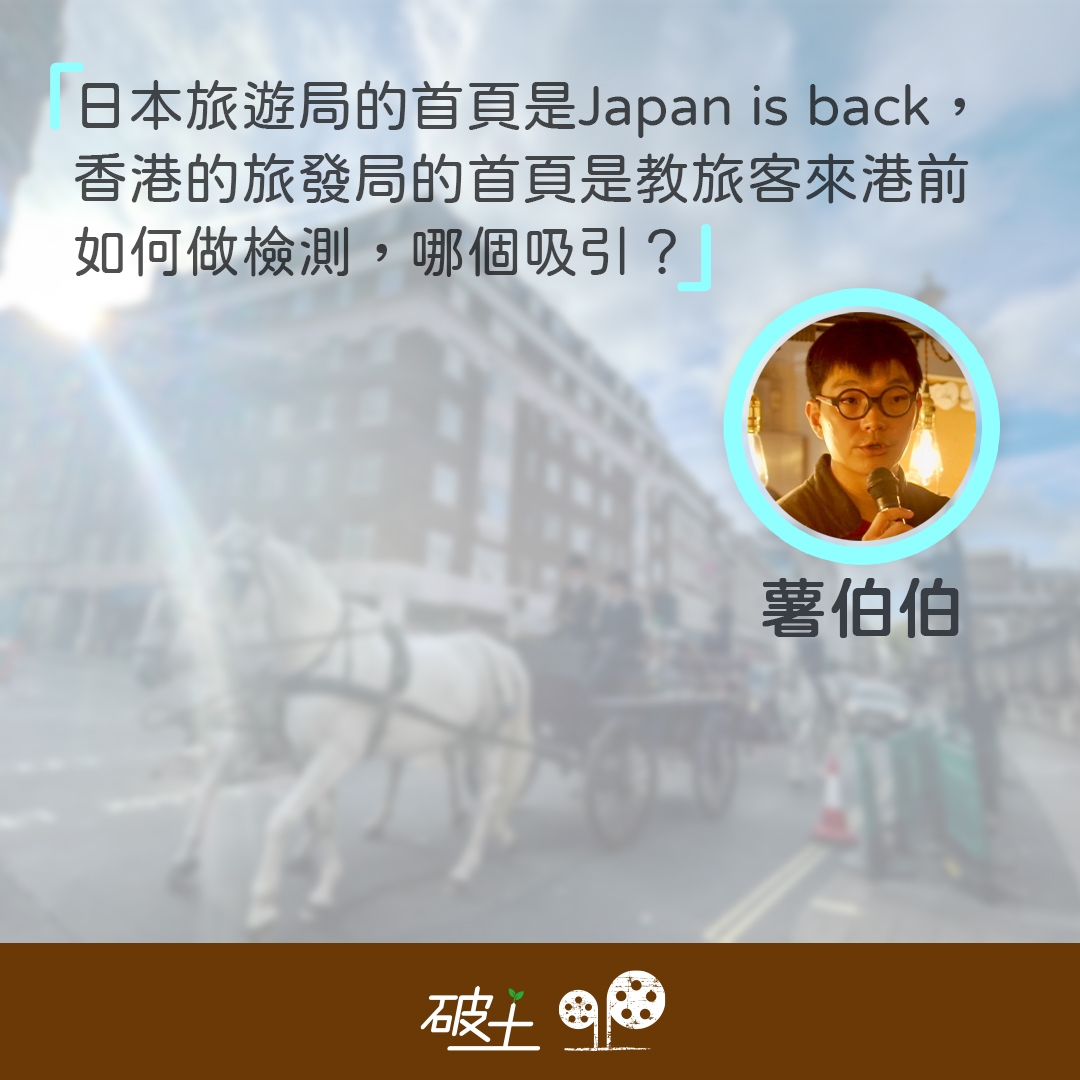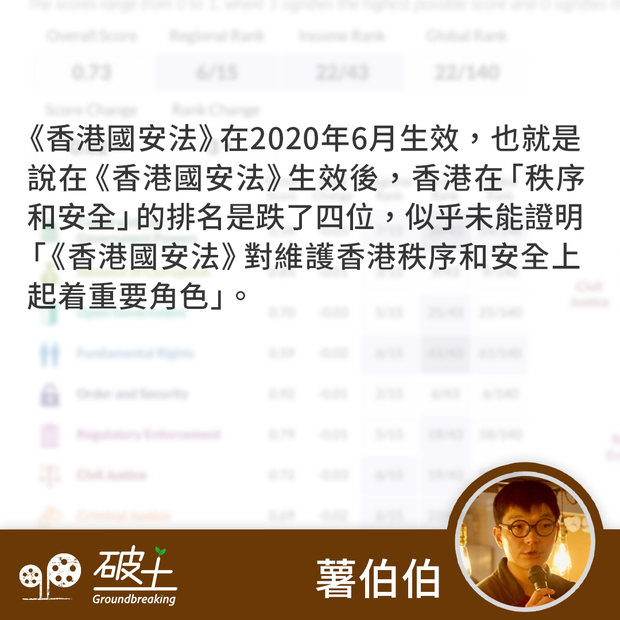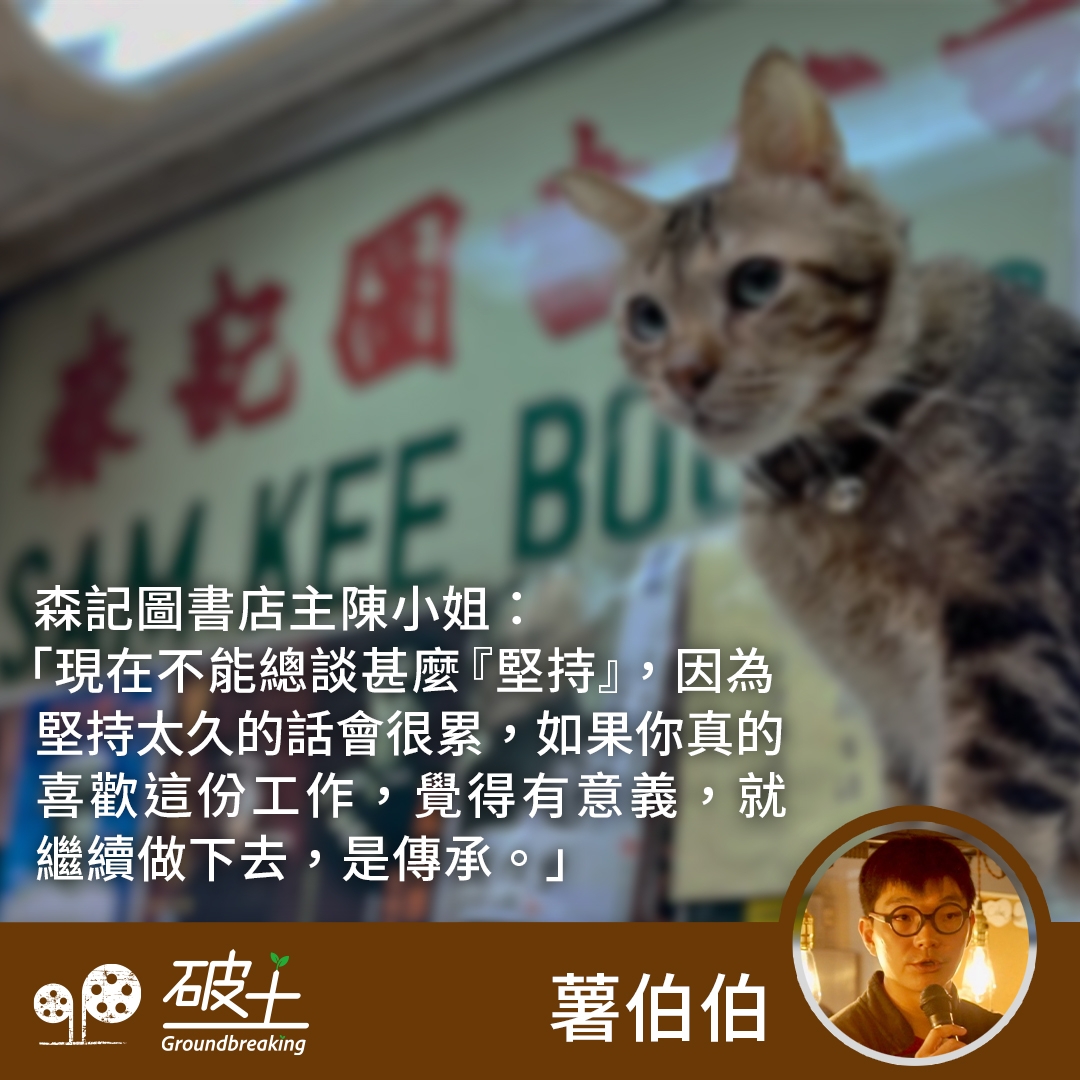懷念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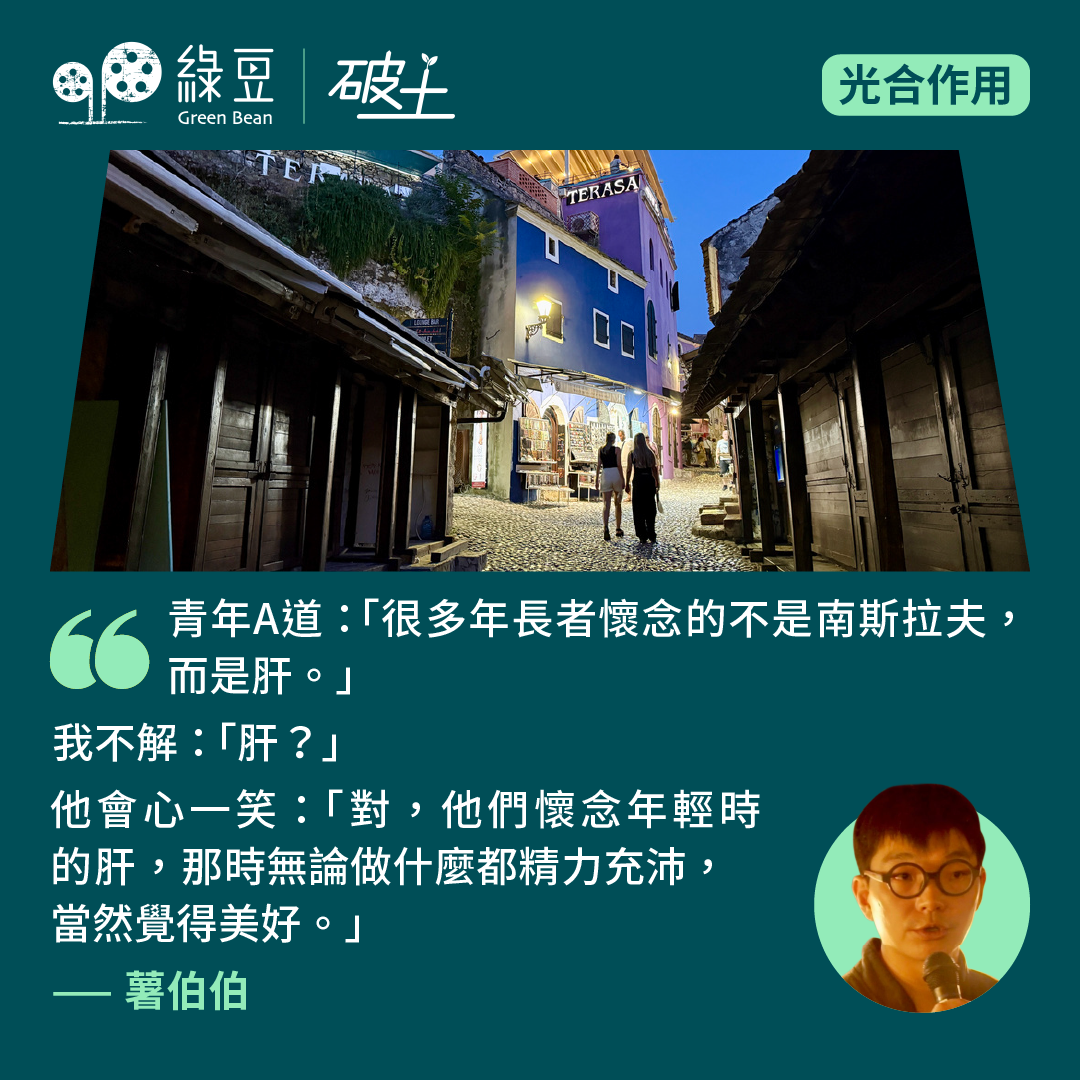
香港人對身份認同這課題,應該特別多反思,所以亦很有興趣了解他人的身份歸屬。記得一次到訪巴勒斯坦,遇上一名居於定居點的猶太裔大叔。他反覆強調當地的巴勒斯坦人其實是阿拉伯人,其後與一位巴勒斯坦友人談及此事,他坦言自己在種族上屬阿拉伯人,在土地歸屬上則是巴勒斯坦人,但他不禁質疑:「為何一個殖民者(指定居點的猶太人),如此執著於否定我們與這片土地的聯繫呢?」
忘了從哪裡讀來的一句話:「巴爾幹半島產生的歷史,遠超其所能消化。」巴爾幹的身份認同,自然也份外複雜。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的古城莫斯塔爾(Mostar),認識了 S。他看上去像伯伯,但實際居然只有48,蒼老得令我要再三確認年齡。
在波黑,人口主要分為三大族群,各族又與其宗教緊密相連:塞爾維亞人(東正教)、克羅地亞人(天主教)和波斯尼亞克人(Bosniak,伊斯蘭教)。S 生於波斯尼亞克族群,但本身不是穆斯林,而是無神論者。儘管他在文化層面認同波斯尼亞克的身份,但在宗教信仰上卻有所分歧。地域上,S 出生於黑塞哥維那的莫斯塔爾,他強調自己是黑塞哥維那人,每當他去外國時,聽到有人稱他為波斯尼亞人,會覺得不高興。
想當年
身份認同某程度上與職業相似,若能一言以蔽之,往往顯得單調乏味。那麼 S 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他說:「我就是一個『波黑公民』,這是我的法定國籍。」然而他坦言,內心最深處的身份認同仍是南斯拉夫人。南斯拉夫解體之時,他才 15 歲。
在 S 的記憶裡,南斯拉夫時期是個「多元共融」、「守望相助」及「社會福利完善」的年代。醫療、教育均為免費,護照可免簽前往 126 個國家,是最強勢的旅行證件之一。那時人人有工做,失業率低於4%,相比現今近20%,他反問:「哪個才是更理想的生活?」
後來在薩拉熱窩(Sarajevo)遇到 30 歲青年 A,卻對這番留戀嗤之以鼻。他認為懷念那個年代的多是既得利益者:「那時確實有少數人過得不錯,但稍有言論不慎就可能人間蒸發。表面和諧的背後,是言論自由的徹底缺失。這種以壓迫換取的和諧,真的值得嗎?」
他又補充道:「很多年長者懷念的不是南斯拉夫,而是肝。」
我不解:「肝?」
他會心一笑:「對,他們懷念年輕時的肝,那時無論做什麼都精力充沛,當然覺得美好。」

照片:莫斯塔爾(Mostar)的一角。
連結:https://www.patreon.com/posts/133895378
▌【Pazu薯伯伯簡介】
薯伯伯為最早一批在網上連載遊記的香港人,多年來足迹遍佈歐、亞多國,在喜馬拉雅山麓、東南亞、南亞等地區生活。著有《風轉西藏》、《北韓迷宮》、《西藏西人西事》、《不正常旅行研究所》、《逍遙行稿》,分別在香港、北京、首爾、台北出版。
作者 Patreon 頻道:https://www.patreon.com/paz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