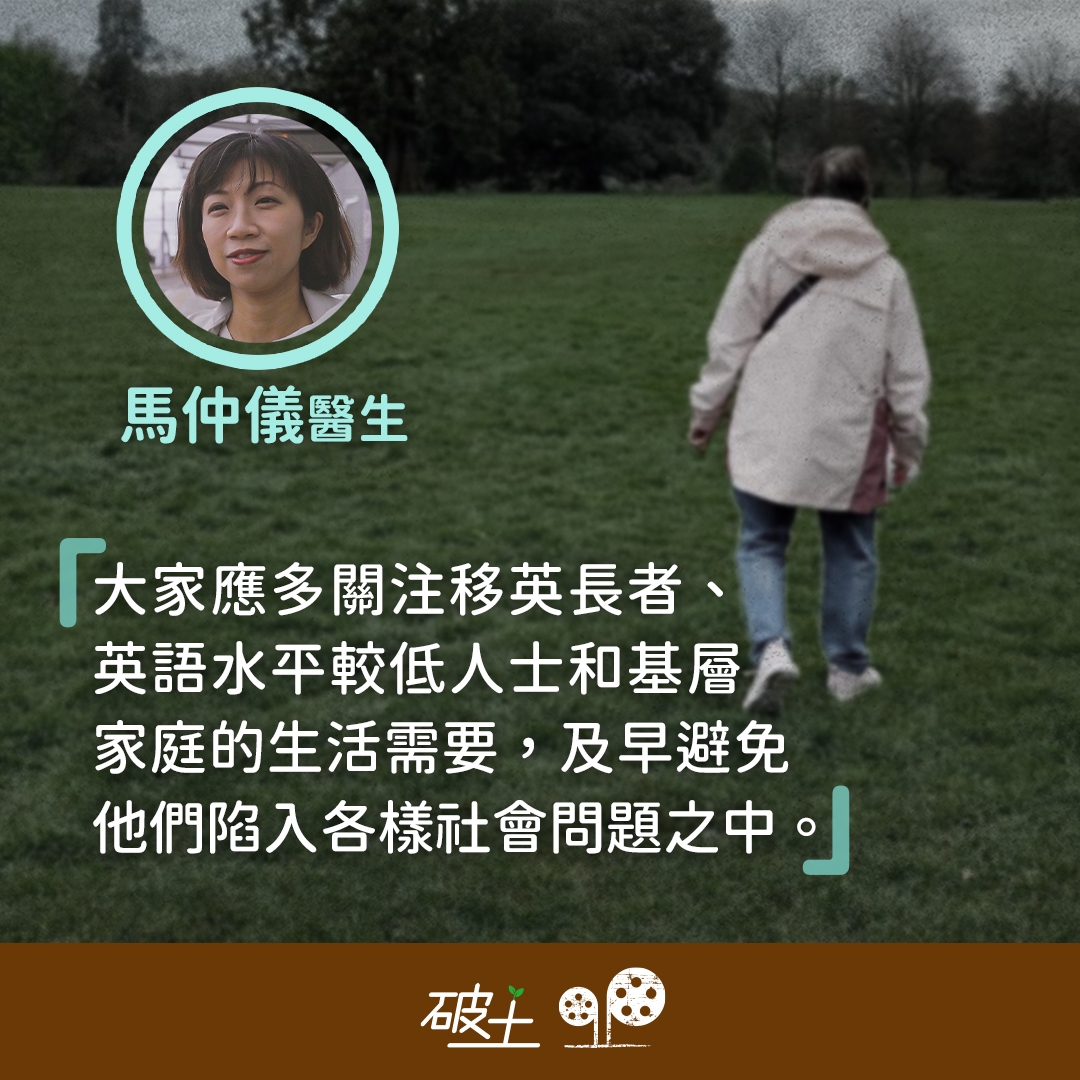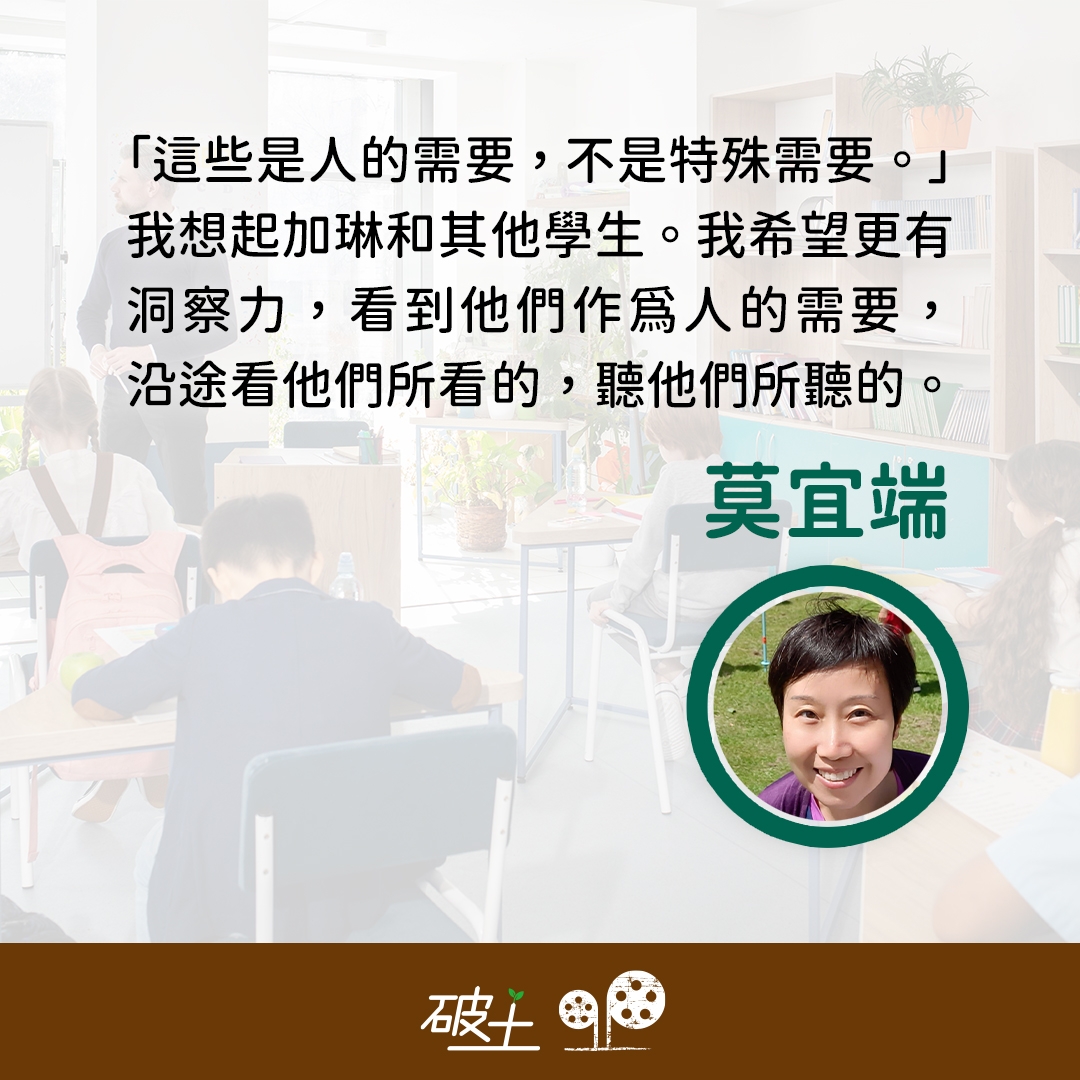選輸便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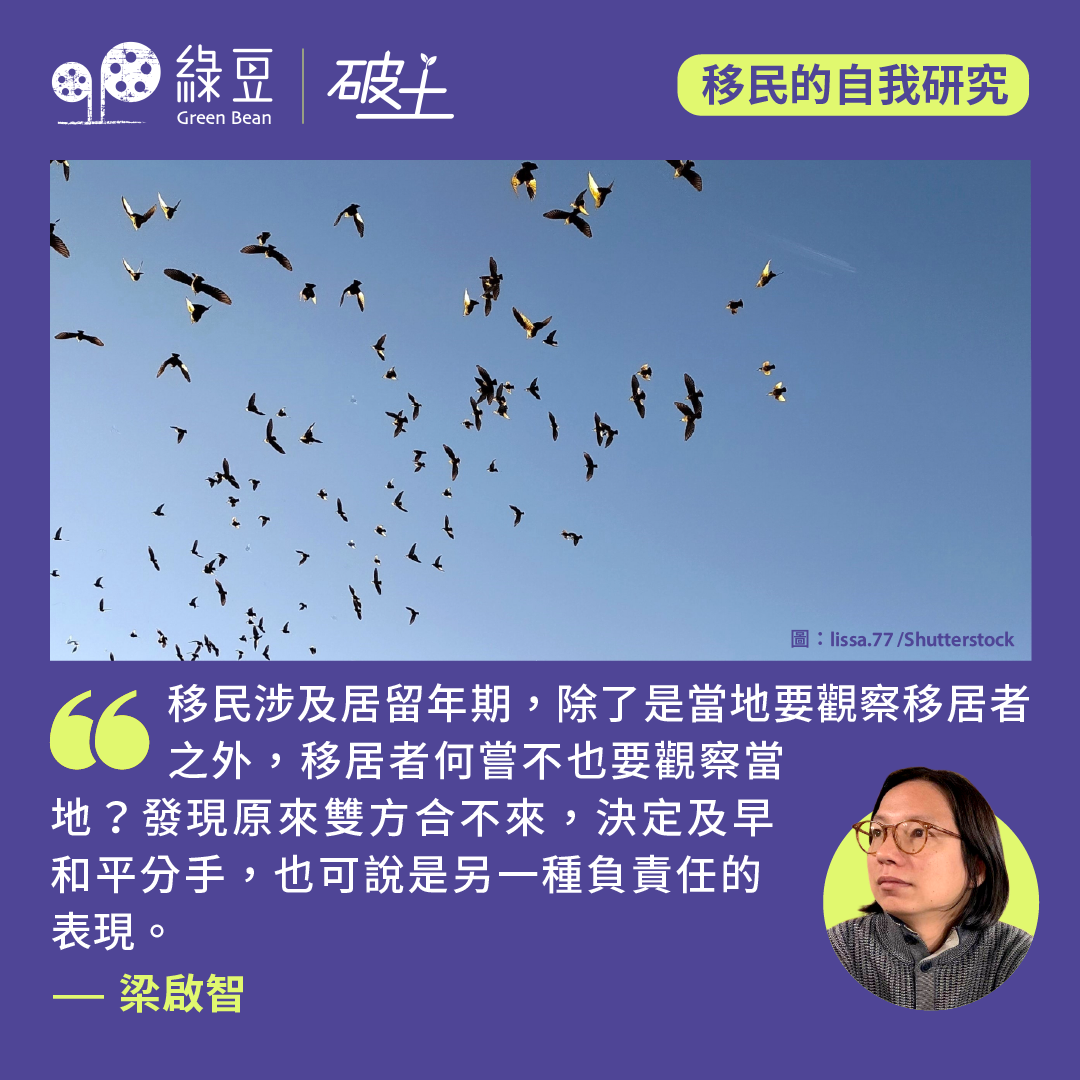
台灣大罷免首波投票以罷方大敗落幕,社交媒體見到有台灣人發晦氣說要移民離開,引發其他網民熱議。這邊嘲笑對方之前說愛台灣是假的,另一邊則號召不能只有在贏的時候才愛台灣,要愛就要同時愛她的不完美。一時之間,各種道德判斷紛紛壓下來,好不熱鬧。
身為移民,對移民這件事情本身沒有多大的道德判斷。人不能選擇自己於何處出生,如能有機會爭取自己在何處生活也算是一種自我實現,把對原生地的愛說成責任並非吾等自由主義者所嚮往。驀然發現自己和所處的社會原來格格不入,那麼嘗試尋找新的居住地亦是人性所在。
而對於本來處於社會邊緣的人群,意外的選舉結果或政治變遷很可能預示未來環境的急速崩壞,提早規劃後路實是情理之中。你總不能說上世紀三十年代末離開歐洲大陸的猶太人或四十年代末離開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是不夠義氣。而從六十年代起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移民離開香港,後面也是同樣的道理。
台灣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沒有人能夠預知。這次選舉是否預示未來情況將會急速轉壞,有風險或有能力的人是否該開始想想後路,恐怕要由未來的歷史學者回答。不過我相信這刻會說這些話的人,出發點很可能是情緒發洩;而之所以引起不滿,是因為碰上其他同樣在巨大困擾和震撼中的人群,於是引發了更多的情緒。
多少人付諸實行
現實上,要作出移民這個決定還是沒有那麼即興的。就連處於移民潮中的香港,經常見到民意調查聲稱有兩三成港人計劃移民,但到目前為止真正離港的人口百分比應該還是個位數。有時人們對媒體或調查說自己寧願移民,很大程度上是要表達對現況不滿,而非真有計劃。
那麼每次選舉之後聲稱「這社會太可怕,還是早走早著」的人,實際上又有多少人付諸行動呢?美國人移民加拿大的數據或可幫助我們回答。過去兩次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都為不少美國人帶來震撼,紛紛聲稱要移民加拿大。從數據上看,確實見到有移民加拿大的美國人有所增加。按加拿大統計局的資料,在奧巴馬任內八年,每年移居加拿大的美國居民大約是一萬人;特朗普在2017年就任後,數字明顯增加,到2019年時最高峰時超過兩萬人。2020年的數字估計因疫情大幅減少,到了2021年拜登上任後仍維持於每年超過一萬五千人的水平。至於特朗普再次就任的影響,現在為時尚早,未有數據。
值得留意的,是增長最多的原來不是美國公民,而是居於美國的第三國公民。其中一個可能是在特朗普政府下,在美的外國人擔心長遠不能留在美國,不如及早轉場加拿大。此外,注意加拿大本身有八百多萬人是外國出生,佔人口四分之一,每年新增數以十萬計,再多一萬人在比例上其實不算得上是甚麼。
中途轉場
加拿大和美國的例子倒帶出了一個和港人移民相關的問題:港人移民的中途轉場。對於許多地方來說,移民不止涉及文化融合,更是建立新的政治忠誠。港人移民如果抱有「逛商場」心態,不同地方的居留權都去拿一個來「有備無患」,有時難免引人側目。話說回來,移民涉及居留年期,除了是當地要觀察移居者之外,移居者何嘗不也要觀察當地?發現原來雙方合不來,決定及早和平分手,也可說是另一種負責任的表現。
早兩年不少赴台港人轉場英國,當中既有對定居政策混亂期的不滿,也有的是來的時候還未有BNO簽證計劃,英國宣布後便重新打算。隨台灣政局緊張,會不會再有一波赴台港人轉場?我發現赴台港人往往有三種特性:其一是本身移居計劃未定,見到台灣門檻較低便先來台灣;其二是有實際需要不能離開香港太遠;其三是確實和台灣有緊密聯繫(例如依親或從事文化界工作)。第一種我懷疑不少已經離開台灣了;第二和第三種在選擇來台灣前已知道風險所在,估計也不會有太大影響。或者那些打算送子女到歐美讀書的,現在可能會提早起行吧?
至於我自己:我想我這輩子已移動得足夠多。迎接不確定的未來還有很多種方法,各人處境不同選擇也不同,港人經歷過的離與留之爭,希望台灣不用再經歷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