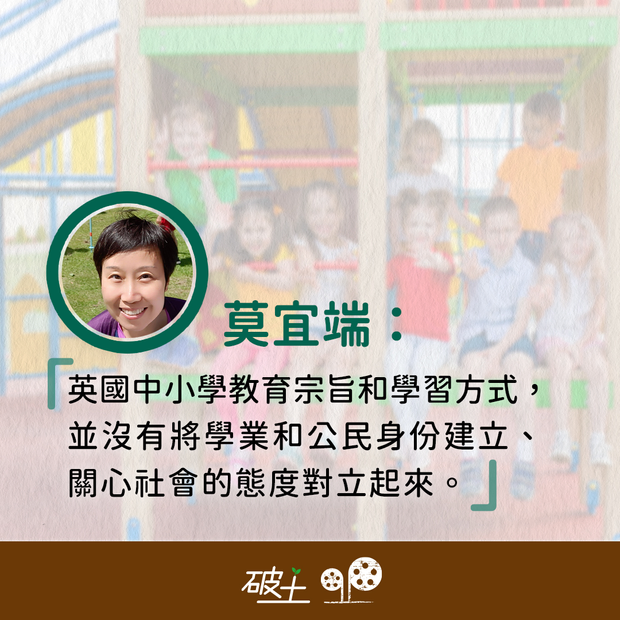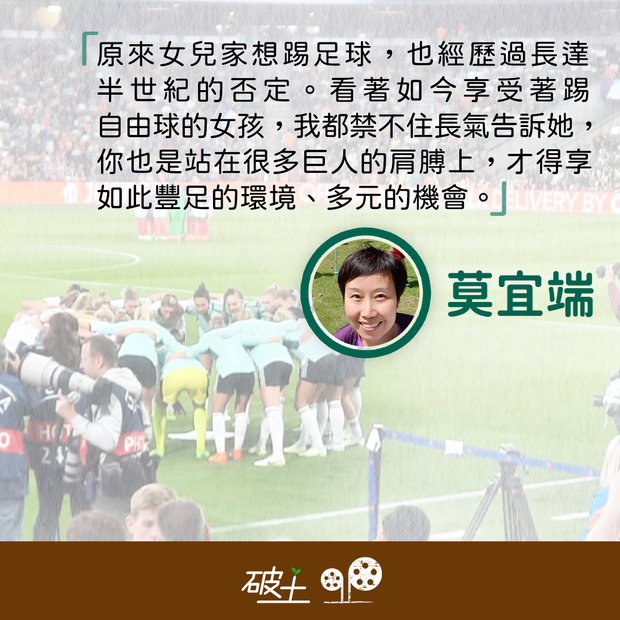講求人權的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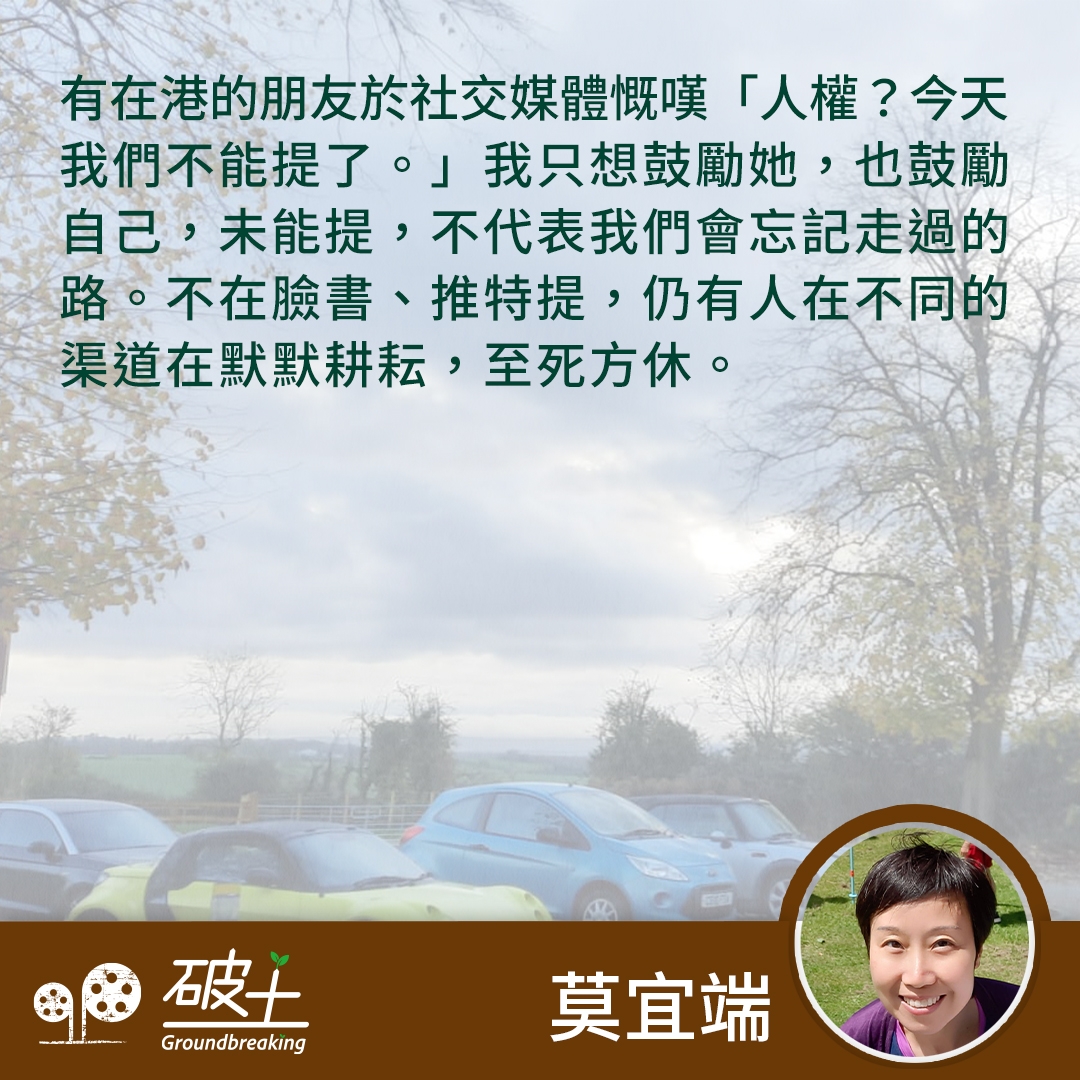
來英一年了,轉工了。能獲聘做駐校言語治療師。我的言語治療學位不是在英國大學考得,所以擁有外地專業資格的人,做治療師的頭一年要找本地資深同工做督導,督導要定期檢查一下我的工作是否符合本地學會的技術要求。在舊校做治療助理,遇過好人,也遇過「mean精」。後來因緣際會,一間特殊寄宿學校要請治療師,於是一步過完又一步,到最後,學校所屬的機構知道我需要本地督導,就告訴我絕對無問題,因為機構聘請不同的輔助醫療同工,有些都因為新畢業,或新來英國打工,需要督導監察。於是,超乎我所想所求,莫姑娘就開始在特校的新一程了。
無論有幾多汗水幾多淚水,沒有一段經歷是白費的。有了之前助理崗位的經驗,更貼地了解這兒特殊學校的運作、資源的拮据,也有人手轉變快的難題,所以到了新校,心中踏實很多。其實作為駐校的言語治療師,除了檢視學生的EHCP(Education health care plan)、之前到校同工的工作流程、資料,還要逐一觀察學生。雖然學校只得幾十名宿生,但也是非常用心力的事。幸好體育老師出身的上司和我的督導治療師都怕我太勤力,叫我慢慢觀察,不用急。

在山旮旯的學校,望出去都是田野
充滿彩蛋的新入職員工培訓
反而上工頭幾個星期,最惱人的是要不斷上 Induction training(新入職員工培訓課)。看到訓練時數:人權/照顧者權責要上兩天的課、急救課程又一天、Positive Behaviour Support工作坊要上24小時。還有機構的介紹和共融派對。每次都要上至少八小時。一看更表,對坐足幾個鐘聽講座有種莫名的恐懼。不過,原來內容好多彩蛋,真令我有返老還童之感。
有一次人權工作坊,簡直有如返到大學重讀國際人權公約般。我的上司任這科的導師,他本身在機構由體育老師做到考到社工牌再負責Behaviour Support,他在介紹Human Rights Act時,講及第二條「保障生命的權利」(Right to life)和第三條「免於虐待、酷刑的權利」(Freedom from torture and inhuman, degrading treatment)的核心人權,提醒照料受助的學童或不同能力的成年人時,一定不能鬆懈。
其他的權利,如第六條的「享有自由的權利」(Right to liberty),或會因為出於保護當事人的人身安全或其他原因而要做出不同程度的限制,但核心人權是任何情況下都不容剝奪!導師說,服務學障和身心障礙人士的人都算是手執權力的人,學校同工是否尊重學生人權,別人就會看我們是否真正尊重比我們弱勢的受助人。
在最少侵犯自由下讓受助人有自己的聲音
讀到這裏,導師拋出很多摘自真實個案的例子,讓我們分組討論究竟故事中的老師或院舍員工,侵害了人權法中哪一項?做法合理嗎?可以怎樣改進,怎樣在最少侵犯受助人的自由下,讓他們有自己的聲音,實踐自己想做的事?
有殘疾院舍的少男,因為母親逝世,好想把媽媽的英文「Mum」字紋在臂上,院舍員工應該點做?多一事不如小一事,告訴他紋身有多痛苦,千萬不要搞?抑或可將他的要求變成一個照顧者和被照顧者一同學習的機會,透過同工用他明白的語言,讓他知道紋身的金錢成本、好處壞處,再讓他為自己選擇——即是協助他做到知情的抉擇?我們有沒有盡力給予知識和技能,讓不同能力人士自行選擇?
香港防疫優先壓下了一切
我的小組中,有一位女士是院舍的夜更支援同工,她細細聲同我講,年幼時,她的家人在特殊學校,試過不斷被體罰,根本無人出聲。現在在英國生活,才體會到人權對人的尊嚴幾重要。我問她,你的家在哪?原來是1970-80年代共黨治下的捷克,即是哈維爾筆下那個無權者都有權力的國度。
我即時告訴她,我祖家香港也好不了多少,服務殘疾人士的前線員工培訓不足。若思維不轉變,難以表達所需的院友真的有口難言,甚麼人權保障都變成空話。再加上政治收緊,這幾年因防疫優先,早前很多社福前輩倡議、協助受助人為自己發聲的努力都壓了下來。例如,過嚴和前言不對後語的防疫措施,對自閉症人士和其他學習障礙的患者有何影響?亂了的邏輯和日常生活秩序,應該如何重整?因防疫而生出的精神健康需要應如何處理?或者坦白說,若有主事的人仍然把殘疾和學障人士視為lesser persons,覺得除了保他們人生安全和基本衣食,其他的心理、娛樂和wellbeing需要,在大局當前都是可以犠牲時,以上的問題,就會在業界由細細聲講,到完全不再提……
好像越講越灰,但翌日跟另一位同事聊天,提到我自己對殘疾人士權利的知識和想法是幾時開始的呢?原來,就是我成長時代的香港教我的,特別是十多年前開始認識很多學障人士家長組織、倡議團體、以前議會內議會外的社工、教師、律師教我的。還有鍥而不捨堅持報道弱勢聲音的記者。社交媒體有在港的朋友慨嘆「人權?今天我們不能提了。」我只想鼓勵她,也鼓勵自己,未能提,不代表我們會忘記走過的路。不在臉書、推特提,仍有人在不同的渠道在默默耕耘,至死方休。
真正的共融派對
另外,在學校辦公時間參加全機構同工的inclusive party(共融派對),有得食有攤位,旨在介紹機構的vision、核心價值等。我原以為只有員工才參與,怎料又是突破我的想像!大會安排了幾位唐氏綜合症的成年dancers教大家跳舞。他們是成人服務的受助人,但機構以part time形式聘請他們表演。而機構的重要文宣,都會付費給受機構資助的學生或受助人做校對,確保自閉症或其他學習障礙的人都看得明、看得懂。
最厲害的是派對開始,見到老師/助教一拖一帶宿生參加。有攤位的主題,是讓大家在連儂牆上寫下你的志願(ambition)!有學生畫了公仔,同工幫他寫「I like bicycles! I can learn to repair bicycles for people」。大堂一邊有個用黑色幕搭成的comfort zone,讓怕太大聲、害怕太多感統刺激的同學,可到那裏休息一下、躺平一下。Disco時間,幾個學生都好投入地同dancers一同跳舞。我們跟他們跳,又拍手又cheers,那種真是出於自然、像equal partners般互動,真是動人!老師要預備很多,要盡所能讓年青人參與,才能促成這事。

特殊學校學生畢業後,或有學習障礙的成年院友,可到機構在社區開設的咖啡店做學徒,甚至兼職。筆者特地到機構社企享用茶點。
我的志願:做個更好的自己
其實,我返工之後才發覺,原以為到山旮旯寄宿學校上班而已,但原來學校所屬的機構還有一系列的成人教育和訓練服務。在英國也有幾處家舍,讓剛畢業、或剛投身社會、或因緊急狀況而暫住的自閉症/學障人士,在員工支援下一步一步學習獨立生活。
活動完後,經過走廊,貼上了印度哲學家Jiddu Krishnamurti(1895-1986)有關教育的金句「There is no end to education. It’s not that you read a book, pass an examination, and finish with education. The whole life, from the moment you are born to the moment you die, is a process of learning」(中譯:教育之路無盡。不是讀完了一本書、通過了考試,就為教育劃上句號。人的一生,由你出生的一刻到你氣息斷絕的一秒,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繼續學,繼續反思,把香港給予我的底氣,再在生活中賦予新意義。唔,到我寫我的志願(Ambition):做個更好的自己。
▌[英倫筆端]作者簡介
莫宜端 Zandra, 育有一子一女,與丈夫子女定居英國,英國註冊言語治療師。曾任記者、時事節目主持、政策研究員、特區政府局長政治助理。及後進修並成為言語治療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