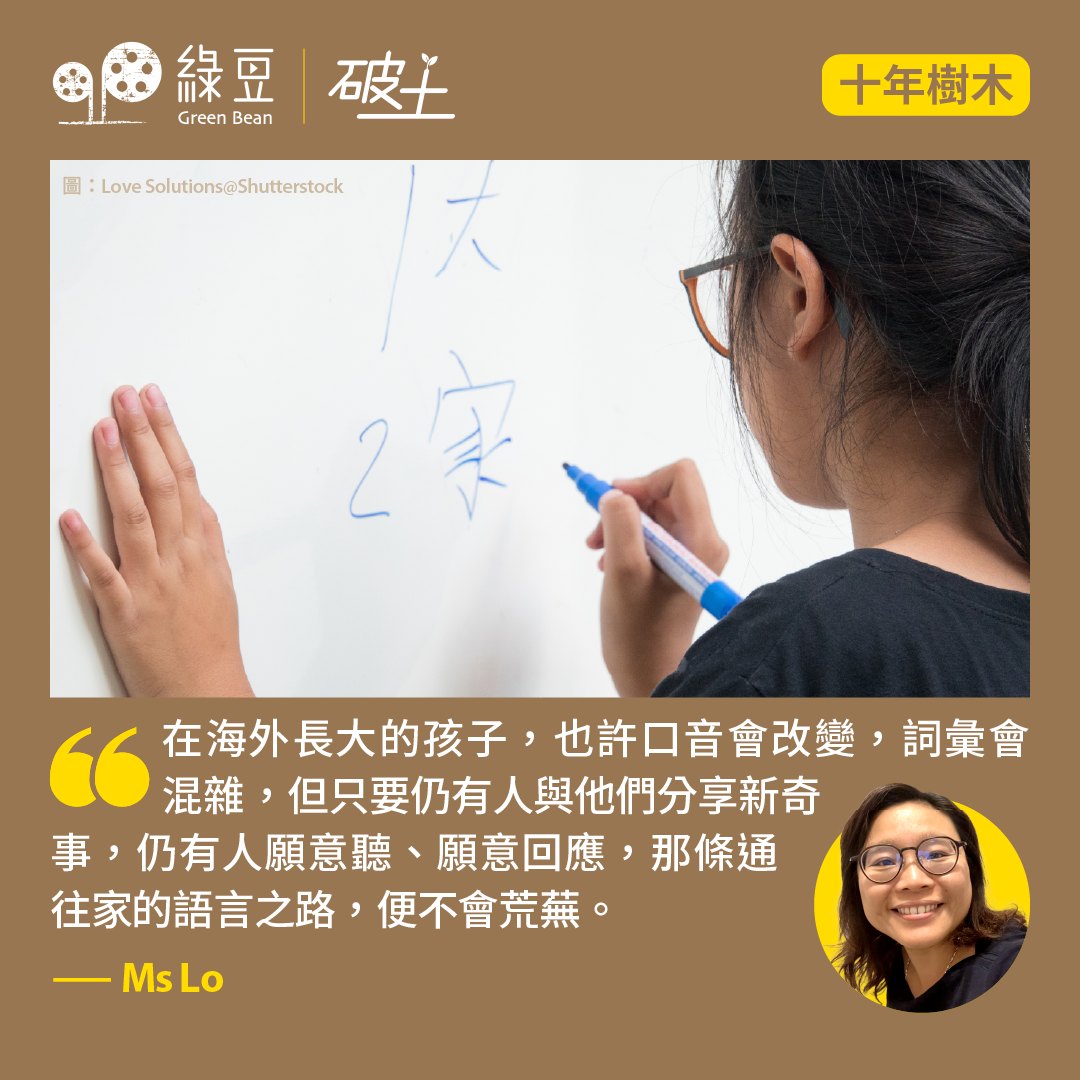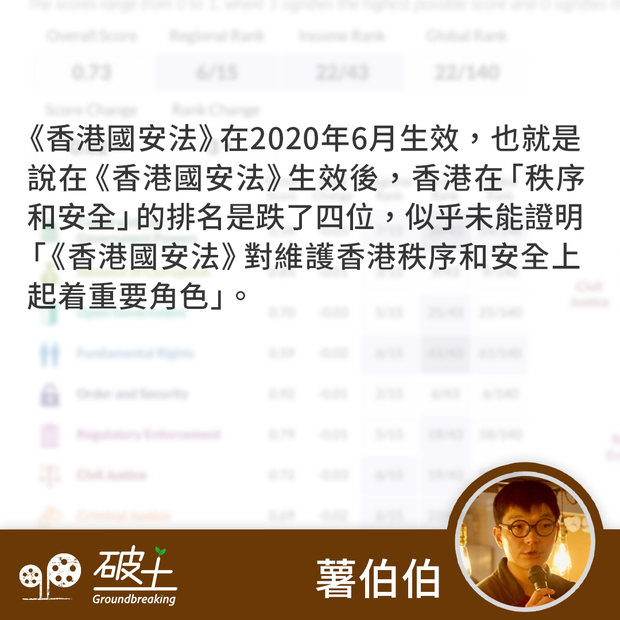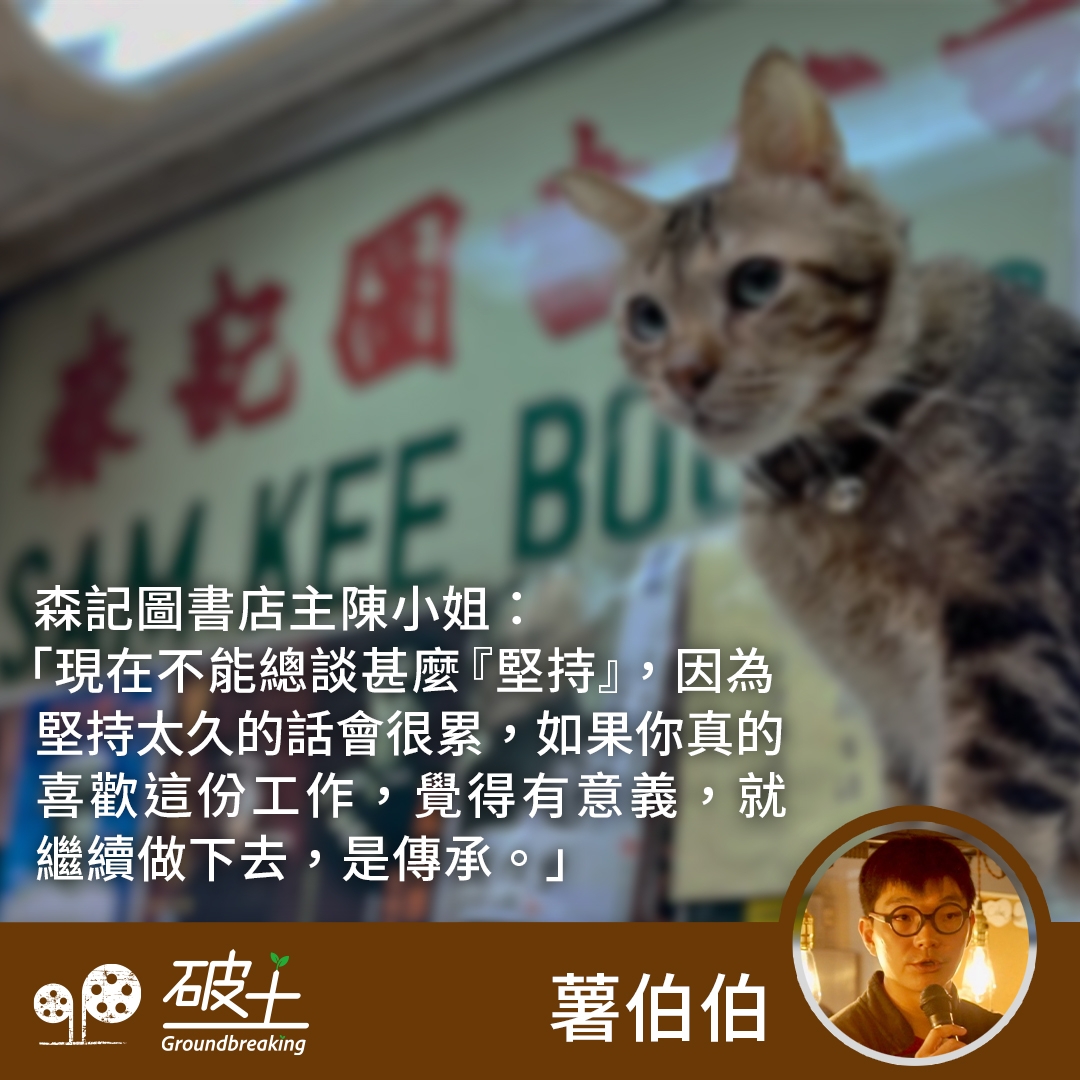談談抑鬱和自殺

(注:文章最初寫於 2015 年,是我跟舊同學之間的通訊,後來覺得有些意義,便整理成較完整的文章,並在 2016 年 3 月初發表,曾刊於《蘋果日報》。此文稍作修補,再次發布。有人問我事涉隱私,能否分享此文,當然可以,希望對你身邊的人有幫助。)
說起自殺問題,有件事從來沒有跟身邊家人或朋友說過,現在忽然一提,最熟悉我的親友,也許會覺驚訝。一直沒說,只是覺得沒必要說,大概一年半前,才首次跟最好的朋友談起這個話題,而且是談到別人的事情才順便提到自己經歷。
創傷後抑鬱
我在中學二年級時遇上交通意外,同行朋友被捲入車底,重傷死亡;我則雙腳折斷,頭骨爆裂,腦有瘀血,留院 39 天。車禍過後,有意無意之間,會想到自殺這個話題,從來沒有實行過,但幾乎每天都會想到。這種感覺維持到中四下學期就慢慢消失。現在回想那年頭,自己應該有點創傷後抑鬱。
記得車禍後的一年多,學校午飯之時,我不會跟班裡任何人去午膳,有次我獨自坐在餐廳一張四人桌,忽見三名同班同學進來,當時全場滿員,只好跟我搭枱。雖然坐在同一張枱,但我沒有主動跟他們說過半句話。
後來我看了一些探討抑鬱的書籍,當中提到斷絕自己社交圈,加上不時想到自殺,就是抑鬱的表徵。那時我根本不知甚麼是抑鬱,更不知道自己可能有抑鬱,只是覺得有點不開心。我是直到 2003 年,張國榮死後,才知道原來抑鬱跟悲傷是兩回事。
九零年代的香港,心理創傷治療,屬新鮮事,我只看過一次心理醫生。在醫院期間,我阿媽經常偷買家鄉雞黑椒薯蓉給我吃,但沒跟醫生說清楚,護士見剩飯太多,誤以為我有厭食症。心理醫生談了好一會兒,報告上說我對車禍後的生活有適當預期,狀態良好。也許她的評估是對的,因為我大概到了中四下學期之後,就沒有任何自殺念頭,只是中間還是有個漫長過程。也許是自己逐漸放開,也許是因為自己很幸運,找到可以傾訴的朋友。總之,轉變的過程很漫長,也很微妙,連自己也不為意。
抑鬱是有癮頭
每個人的情況都可能不同,所以我只是用自己的心態,去寫一些感受:
1. 記得有次另一名不太相熟的同學跟我說:「點解你成日都咁開心嘅?」也許,有抑鬱的人,表面看起來,可以是很開心,每次見面都笑,不是強顏,而是散發自內心真誠的歡笑。也許正因如此,當他們選擇結束自己生命時,才令人格外詫異。
2. 車禍之後,有些人總會用很奇怪的理由或邏輯去開解我。我心知那人好意,我真的知道,所以別人不需要再重複說別人只是出於好意之類的話。但是這些好意的說話,卻難以在我心中引起任何共鳴。車禍後兩星期,得知好友死去,我難過哭泣,腦外科病房的護士長就跟我說:「你以為自己好慘?之前有個女仔被泥頭車壓爆頭,佢咪重慘,佢屋企人咪仲慘……你要好好活下去。」這些說話,我知道他是好意,只是對我來說毫無幫助,因為我不是鬥慘。
3. 抑鬱是奇怪感覺,我知抑鬱負面,它使你忽然冷感,無故悲傷,詭異的是,好多人不知道,其實抑鬱是有癮頭。吸煙者明知抽煙不對,還是會抽;若有抑鬱徵狀,或多或少都會知道這種想法對自己有害無益,但還是會忍不住繼續去想。有時甚至每晚憑空想像,讓抑鬱感覺佈滿全身,想像身邊的人一個一個離開,想像得躲在被窩裡淚流滿面。這種負面感覺,卻又弔詭地能給我一點安慰。任何勸你停止感受抑鬱的建議,都是無效。如果有人說:「唔好諗太多」、「早啲瞓啦」、「時間會沖淡一切」、「你仲想點?」,又或者更令人摸不著頭腦的一句 ——「神自有安排」,我都覺得那人活於另一個跟我不同的次元空間。
4. 抑鬱,雖然看起來很負面,但其實會讓人有快感,不知情的人大概會覺得很變態。抑鬱的過程中,自主意識非常強烈,不是純粹處於被動狀態,很多人生的念頭、思維,都可以在抑鬱的過程裡做出深刻的反思。尼采曾經說過:「自殺的想法是很大的安慰:多虧它,人們才能經歷許多黑夜。」我有時想,如果人類經過千百萬代的演化,仍然保留抑鬱,也許它真的有存在價值。
5. 承上一點,抑鬱的過程,感覺頗像北韓領導人金日成所說的「主體思想」,即認為自己有改變命運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潛在於自身。正正因為我的意志可以隨時讓自己停止抑鬱想法,這種短暫的能力,造成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錯覺,沒意識到需要在外界尋求幫助。就像煙剷總會跟你說自己與別人不同,別人才是有煙癮,他則可以隨時 72 小時停止吸煙,所以自己沒癮,不必戒煙云云。
聆聽就足夠
6. 我與臨床心理醫生的對話,印象頗深,因為那次是車禍以後,第一次放下戒備,說一下心底感受。醫生沒評論或批判我的說法,只是點頭、聆聽、寫筆記。她成功讓我覺得,她想了解我的想法,所以想花時間聽我的話。可能她受過相關訓練,知道根本不用去開解別人,聆聽就足夠。
7. 回顧自己的轉變,算是非常幸運,身邊有些願意聆聽的朋友。剛才提到在餐廳裡同桌而不往來的三名同學,其中一人後來成了我非常要好的朋友,至今仍是(這篇文章最初其實是寫給他的 Facebook message)。中學時代,擁有最多的就是時間,煲電話粥數小時,煲到睡著了。有些人以為聊天一定是交換資訊,但那只是表象,正如北韓發射長程彈道飛彈也不一定是對外攻敵,我找朋友傾電話傾通宵不一定是聽他或與他分享故事,也許只是尋求安全感和慰藉。回想起來,在懵懂的青蔥年代,能有一位朋友願意(或不情願卻願意)跟我多晚聊至通宵,是成長中最幸運的事情。
8. 聽到別人對我訴說他的悲痛或哀傷,我的心裡也同樣覺得難過,但是因為自身的經歷,我總不願意去安慰別人,有人以為我冷漠,其實不盡如此,我只是覺得安慰沒有作用。抑鬱,雖然說有藥食,但又似乎無藥可醫。如果要幫助有抑鬱的人,或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心聆聽他們的感受,既不必覺得在幫助他,又不可以嘗試改變他,不要抱著開導他的心態,更不要分析或批判對方的想法。當對方走出抑鬱,抑鬱者也許連自己也不察覺;聆聽的過程漫長,長得你誤以為自己束手無策。但會有用,可能你幫了別人,自己沒有察覺而已。
心裡一道疤痕
以前在新聞上看到多宗學童自殺,學童母親走到殮房認屍,激動得昏倒過去,聽到這類報道,總覺非常難過。我真的很希望,看不見出路的人,能找到聆聽他們的親人或朋友,又或更重要,是起碼給別人聆聽自己聲音的機會。
數年前我打電話去車禍時死去的同學家裡,約了他媽媽出來飲茶。臨走之前,他母親忽然對我說:「我見到你去旅行,就好似見到自己個仔去旅行。」說起失去了二十多年的孩子,她還是哭成淚人。一個人離去,不論走的原因是外在還是內在,就算過了數十年,卻一直是最疼愛自己的人心裡一道疤痕。
假如離去的原因是內在,若然只是暫看不見前路,想走最後一步,可以的話,不如再多忍一會吧。
照片:突尼西亞撒哈拉沙漠的夜空(攝於 2023 年最後 2 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