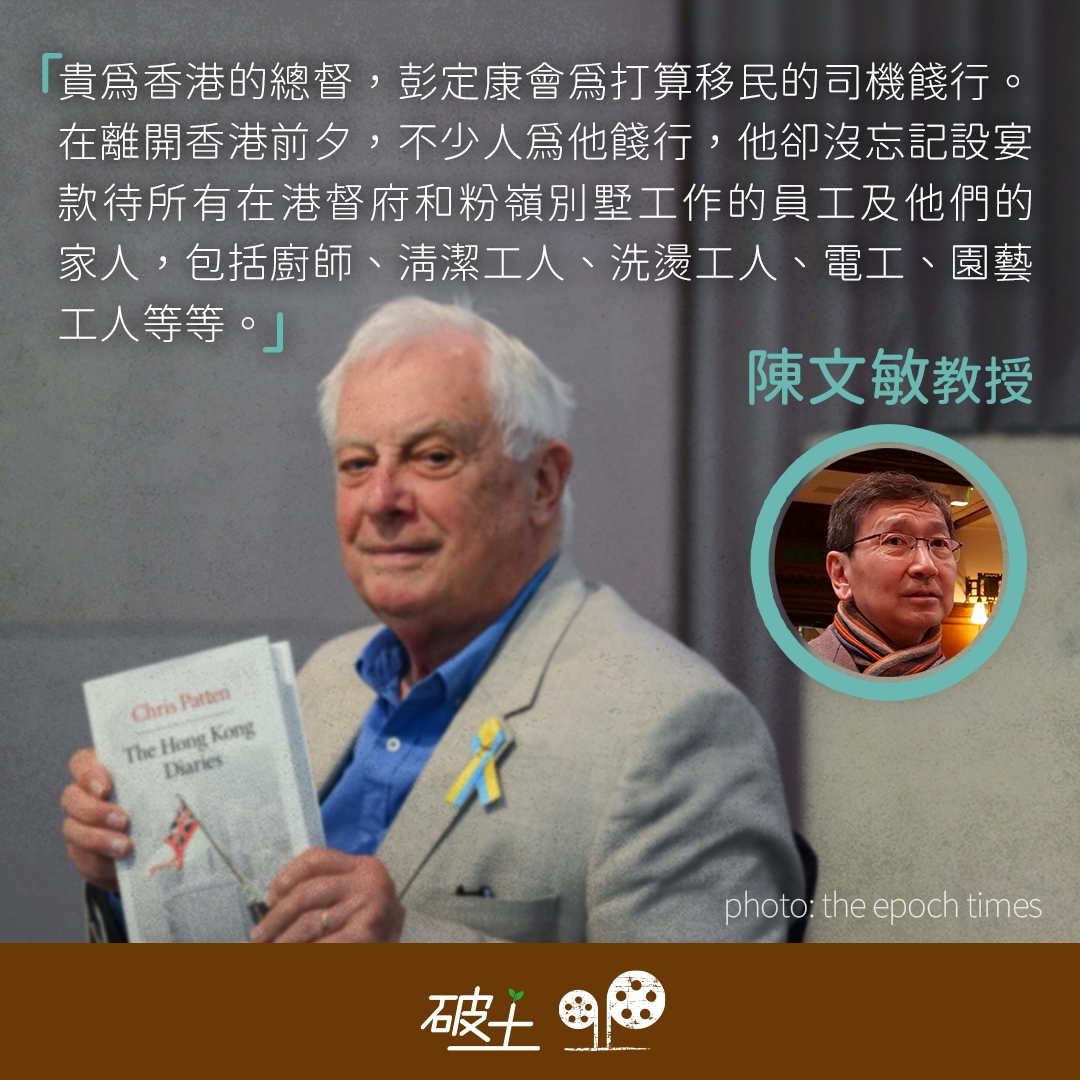評47人初選案

經過118天的審訊,法庭在多名被告被囚達1,189天後作出判決,裁定在47人初選案中不認罪的16名被告,當中14人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罪名成立。這宗案件涉及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個是較廣泛的問題,即法院如何解釋《國安法》?第二個是較具體的問題,即為何一項為《基本法》所容許的行為會構成顛覆政權罪?
這次檢控是建基於《國安法》第22(3)條,控辯雙方同意案件並不涉及任何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因此,控罪的元素是各被告串謀:
- 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
- 以非法手段;
- 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
- 而目的旨在顛覆國家政權。
於是,案件的兩個重要元素是何謂「非法手段」及這些手段如何「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這兩個問題均涉及法院如何詮釋《國安法》這法律問題。其餘兩個問題主要涉及事實的裁決,即各被告的具體行為。本文只集中討論前者的法律問題。
無限放大國家安全
從法律角度看,這個判決是令人失望的。判詞表達的強烈訊息是國家安全凌駕一切。誠然,國家安全固然重要,但國家安全是否便要壓倒一切?國家安全不等如壓制自由,但國家安全的定義愈模糊,涵蓋的範圍愈廣泛,自由和基本權利被剝奪的風險便愈高。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有國家安全的考慮,在極權國家,國家安全往往定義模糊,政府便可借國家安全之名,實行鎮壓言論、打擊異己之實;在民主自由的國家,國家安全同樣相當重要,但國家安全只是限制基本權利的一個合法目的,政府得在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基本權利之間取得平衡。在普通法國家,法院便是肩負平衡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基本權利的重任。《國安法》要在普通法制內施行,於是,《國安法》第四條便清楚明確指出,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法院亦須保障《基本法》和國際公約所賦予的基本權利。
可惜,在洋洋三百多頁的判詞中,我們只看到法院多番強調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卻連一次也沒有提到《國安法》第四條!在解釋《國安法》的時候,法院似乎忘記了這條法例是在普通法制度內執行,亦似乎遺忘在普通法內,法院同時肩負平衡維護國家利益同保障市民權利的憲制責任。當法律條文不清晰時,普通法容許法院參考行政機關在立法會引入法律草案時的説明,但這只供參考作用,法院過往亦多次提醒要小心處理這些説明:這些説明很多時只是政治言論,解釋法律是法院的權力,得客觀和根據法律原則行使這權力,過分強調政府的言論,很容易變成由行政機關主導法律的解釋。
在這宗案中,法院大篇幅引述人大通過《國安法》的說明和528決議,以支持所謂的立法原意,但這些説明背後的理念是任何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基本法》權威的行為都是不能允許的。當法院不加思索,囫圇吞棗地接受這説明,甚至將這些政治言論當作法律條文般來解釋,強調説明的英文譯本遺漏了中文原文中「任何」一詞。這種處理,已遠超普通法引用官方在立法時的説明的限制,亦自然或不自覺地全盤輸入了國家安全壓倒一切的內地價值觀念,而忘記或忽視了普通法對人身自由等基本權利的尊重和維持一個兼容、容忍和多元社會(broadmindedness, tolerance and diversity) 的價值觀。
《國安法》是國家通過的法律,本質是一條刑法,刑法的本質就是透過一個機制合法地奪去被告的人身自由,觸犯《國安法》最高可以判處終身監禁。在解釋這樣嚴峻的刑事條文時,普通法一個基本原則是刑法的範圍一定要清楚明確,在剝奪人身自由時,立法機關有責任將違法的界線清楚界定。若果法律太過含糊,法院不會越俎代庖,執行含糊的法律,而是會給予相關條文一個狹窄的解釋,以保障人身自由,這稱之為「合法性原則 」(Principle of legality)。
終審法院在2012年的A v Commissioner of the ICAC 案中,便確認和接納英國上議院法庭在ex parte Simms案中Lord Hoffmann對合法性原則的解釋:國會有權限制基本權利,但這樣做便必須使用清楚明確的用詞,合法性原則的意思是國會須面對它的作為,並為此付出政治代價。籠統或含糊的字眼不足以限制基本權利,因為在民主立法的過程中,立法機關忽視籠統用詞的全面後果的風險太大,因此,「在沒有明確的用詞或必要的相反暗示的情況下,法院假定即使是最籠統的詞語,也無意限制個人的基本權利。 」 (In the absence of express language or necessary implication to the contrary, the Courts therefore presume that even the most general words were intended to be subject to the basic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非法手段
在解釋「非法手段」一詞的含意時,法院認為「非法手段」不局限於武力,亦不局限於刑事罪行,這大大擴闊了顛覆政權罪的適用範圍。法院的理據有四點:
第一,如果法律原意是將這片語限於刑事罪行,人大大可選用「犯罪手段」,故「非法手段」當不止於刑事罪行。這論據不具說服力,若法院的解釋是正確的話,即「非法手段」包括任何不合法的手段,那前面「以武力或威脅以武力」這一句便變得多餘。
第二,法院認為同一詞彙在同一部法律內的解釋應該是一致的,「非法」一詞在《國安法》內出現了五次,包括了刑事和非刑事行為,但這只是一項普遍性的原則,還得看具體的語境。在其他條文內,非法手段都是針對特定的具體行為,例如第26條指「非法管有爆炸性物質」,或第29條指「非法提供國家機密」,這些均明顯是刑事罪行;法院引用第29(5)條以支持其結論,但這一條指「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對特區居民對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的憎恨」,這不正正就是煽動罪嗎?這些例子反而支持「非法」一詞只是指刑事罪行。再者,第22條的罪行包括四類行為,首兩類涉及推翻憲制制度和政權,第四類是攻擊、破壞特區政權機關履職場所及其設施,均明顯是刑事行為,故將「非法」限於刑事罪行,是將第三類罪行和第22條其他部分的罪行的範圍變為一致,亦對國家安全提供了足夠保障,毋須擴闊至非刑事行為。
第三,法院指若「非法」只是指刑事罪行,那顛覆罪便會出現罪中有罪的情況。但這種例子比比皆是,入屋行劫罪便包含了盜竊罪。
最後,近日上訴庭就歌曲「願榮光歸香港」發出的禁制令,要證明違反禁制令,控方便得以證明幾項不同的國安控罪,原訟法庭因此認為禁制令沒有必要,但上訴庭卻認為蔑視法庭罪中包含了國安的罪行並無不妥。最後,法院認為任何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均不能接受,故相關的行為不該只局限於刑事罪行,但這是結論多於理據,並反映了法院向內地的違法觀念傾斜的取態。
法院的解釋大大擴闊了「非法」的範圍,但若不是局限於武力或刑事罪行,那還包括什麼呢?為何民事的濫用權力一下子會變成刑事罪責?會否包括其他的民事過失?法院對後者採取了迴避的態度,說日後才算。若果法院自己也無法清楚界定刑法的範圍,市民如何守法?採納這樣模糊的解釋,令這條本已嚴苛的法例的界線變得更模糊不清,這既違反《國安法》第四條對人身自由的保障,也違反普通法的合法性原則。而這種向內地價值取向傾斜的取態,很容易導致法院成為威權政府壓制異己的工具,當內地的法律價值取締了香港普通法的基本價值,兩制的差別也會名存實亡。
基本法與國安法
與其給予非法行為一個清楚的界線,法院認為只須處理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是否濫權行為便足夠,若是濫權,便是非法行為。法院的理據有多處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法院沒有解釋為何這是濫權行為?法院指議員有責任審議財政預算案,若不理會財政預算案的內容便作出否決便是濫用職權,這即所謂的「無差別否決財政預案」。但第一,議員同樣有責任審議任何法例。在議會中,議員用否決一條法例,以換取政府在其他方面作出讓步,是民主議會中司空見慣的情況,過往亦有政黨提出若政府不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便會否決財政預算案,建制及泛民的議員亦曾多次以法例以外的原因否決法案,民主議會就是這樣運作,那是否也是濫用權力?法院並沒有闡釋何謂「無差別否決」,被告行使否決財政預算案的權力是基於政府拒絕五大訴求,並非只為否決而否決。法院認為政府無可能接受五大訴求,而且是缺一不可,但這是一個政治判斷,當日的全民退保何嘗不是遙不可及?政治上開天索價,落地還錢,本是常態,立法會本來就是一個討價還價的地方。
第二,法院指根據䆁義及通則條例,議員無差別否決政府提案以威嚇政府便是違反宣誓,但這修訂是在2021年才作出,條例沒有追溯效力。法院認為即使在修訂前,普通法也是一樣,這說法並無任何依據,亦顯得相當牽強。
第三,法院強調否決財政預算引致對政府施政的影響,但這些影響早在《基本法》的設計之內。《基本法》已預計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大法例有可能被否決,因而設計了一套制度以解決這種情況:行政長官可以解散立法會,並按上一財政年度的開支批准臨時短期撥款。即使財政預算案再次遭否決,也只是特首需要辭職,按《基本法》的規定,特首出缺,由政務司司長、財政司長及律政司長依次署任,政府仍然繼續如常運作。這些安排已盡在《基本法》的設計之中。若果依從《基本法》的設計所引致的後果會成為「嚴重干擾、阻撓或破壞特區機關依法履行職能」,那豈非《基本法》本身也違反《國安法》?
第四,法院另一項重大遺漏是並無充分考慮在財政預算案被否決後,行政長官可以解散立法會,立法會須要重選。這個設計的目的,就是讓選民作決定,而特首只會在再度拒絕順從民意的情況下才要辭職。若選民不滿意和不信任行政長官,決定以選票再次將被告選入立法議會以更換政府,這是民主社會中選民行使選票的權利,又何來顛覆國家政權?
第五,若根據法院的邏輯,被告同意以無差別否決財政預案算作為參與初選的基礎,透過預選前在7月6日及9日的新聞發布會,當選民清楚知道這是被告的共同目的,而預選是落實這個目的重要一步,但仍然決定參與投票,以行動支持這項被法院裁定為顛覆政權的罪行,那是否意味六十多萬參與預選的選民,均有可能觸犯協助被告實施第22條規定的罪行?
結語
當按《基本法》的條文作出的行為被裁定為違反《國安法》,當本來合法的行為變為顛覆政權的罪行,傳遞的信息是今天在香港,任何挑戰政權的行為已是超越底線,這是國內的法律觀念。令人憂慮的是這種觀念近年已不只一次出現在各級法院的判詞中。當這種觀念成為主流,並凌駕普通法原有的法治價值,香港和其他內地城市還有甚麼分別?
若這案件有陪審團參與,結果會否有別?由於沒有陪審團參與,這只會是臆測,但若有陪審團參與,最少兩名被判無罪的被告已可重獲自由。在普通法下,控方不能以上訴推翻陪審團的判決,但法例給修訂後,控方在法院頒下三百多頁的判詞後隨即提出上訴,給人的感覺是窮追猛打,要所有被告入罪,一個也不能少。在普通法下,控方的責任不該是千方百計將被告入罪。不過,諷刺的結果是被告亦可因而在上訴中質疑法院的判決,最後可能要到終審法院才能清楚看出法院對國安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取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