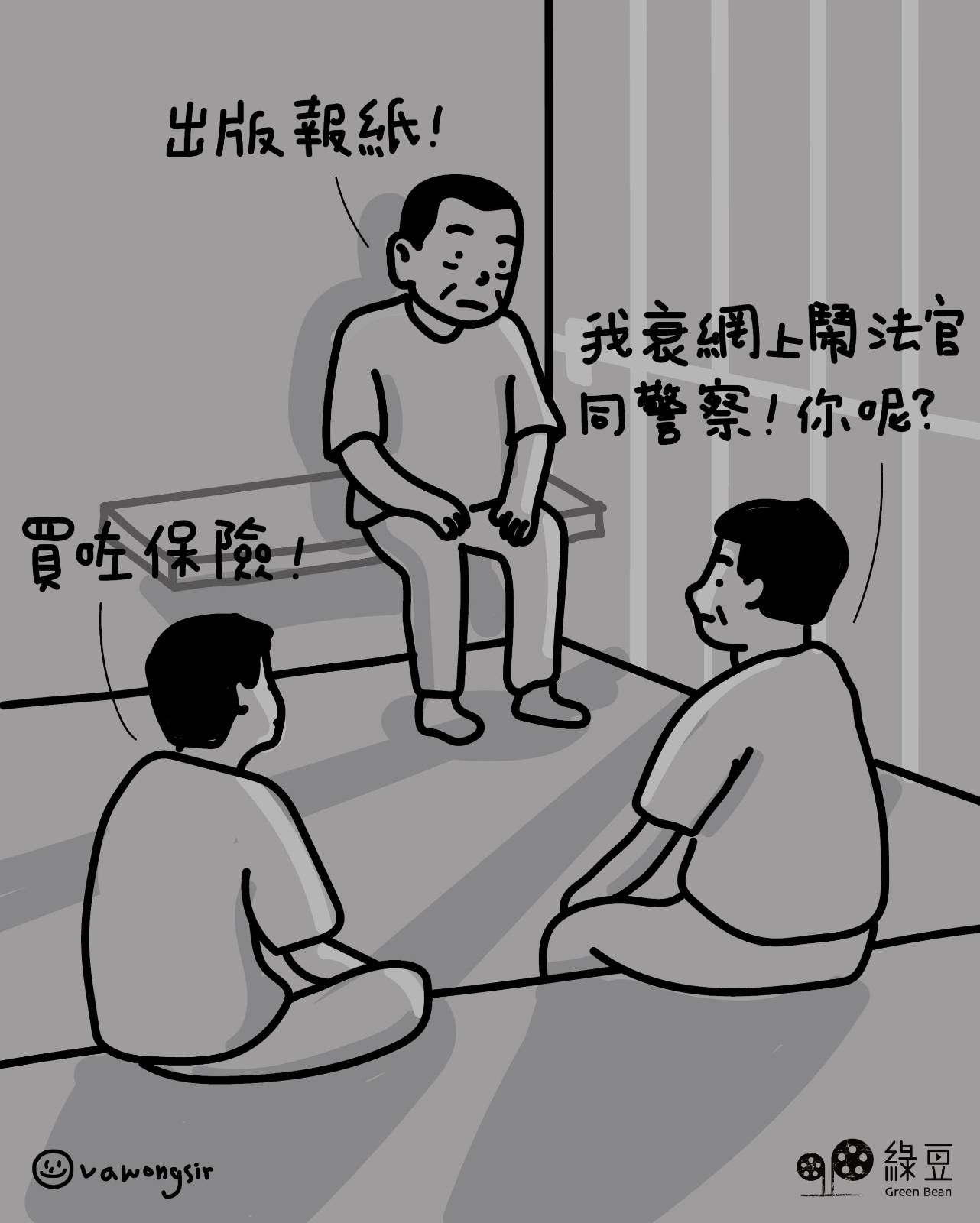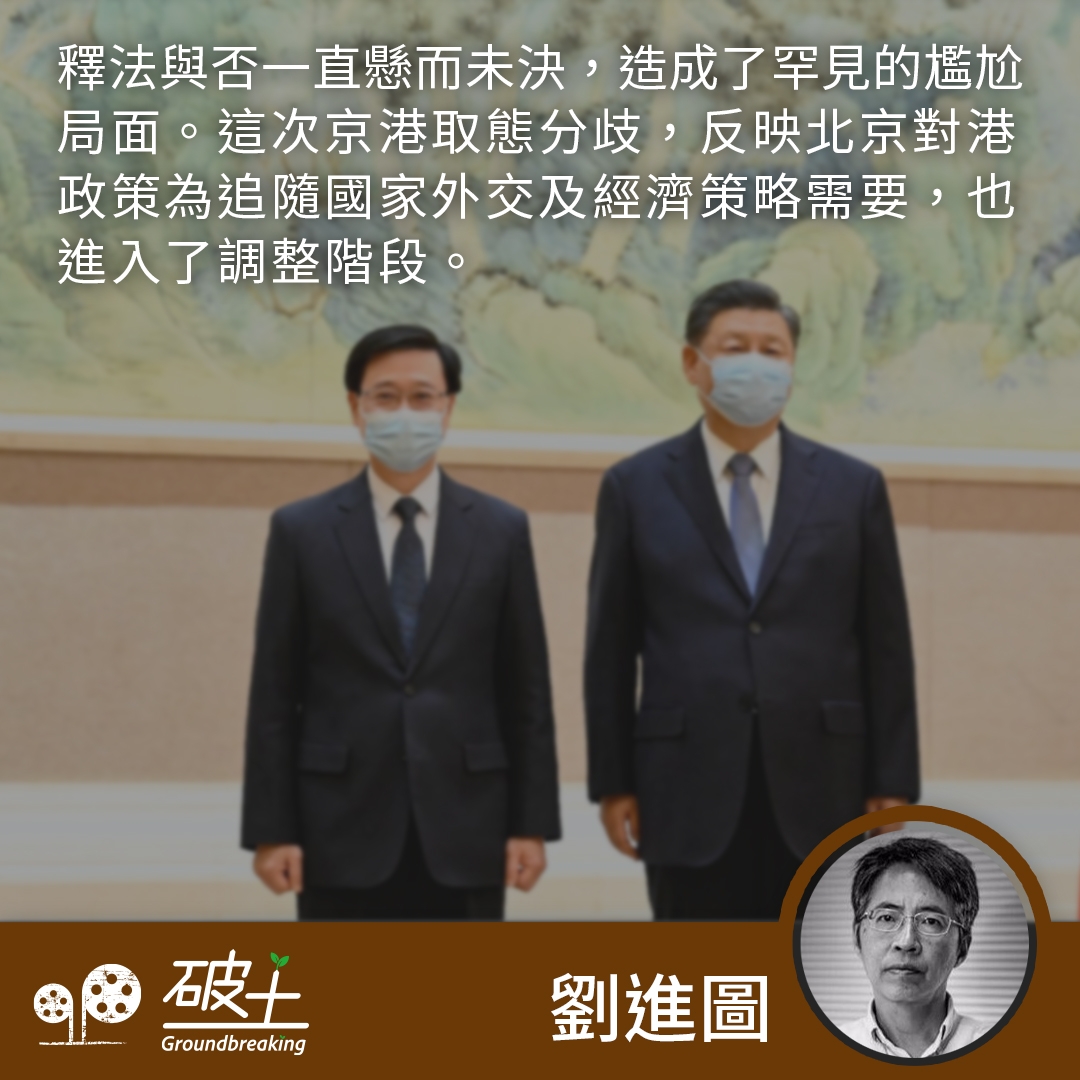記者被霸凌乃香港之恥

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要聞是香港記者協會披露會員受滋擾的調查結果,有至少13間本地及國際媒體,以及兩家新聞教育機構,在今年6月至8月發生過針對記者的滋擾事件。涉及手法相當卑劣,包括恐嚇記者的家人、僱主、物業業主等,且霸凌一方掌握了大量記者及家人的敏感個人資料,實力遠非一般民間網絡起底欺凌可比,似是集團式系統性針對獨立媒體記者的政治攻擊。
這種政治攻擊過去甚少在香港出現,其客觀影響絕不限於受滋擾的記者與媒體,若不能依法阻止嚴懲,會散播白色恐怖氛圍,成為香港的恥辱標記,加速人才與資金流失。
攻擊的幾點特殊之處
香港記者被霸凌一事,《明報》的周日話題(9月15日)有詳盡的報道,商業電台的早晨節目也有受害者詳述遭恐嚇細節。從這些報道內容來看,這一波針對記者的攻擊有幾點特殊之處,並非一般宣洩私人怨憤的網絡起底抹黑,扼要歸納如下:
1)受滋擾的對象有政治針對性,全是新聞行業內最獨立敢言的一撮,包括香港記者協會多名執委、獨立媒體(Inmediahk.net)、HK Free Press、誌傳媒(HK Feature)等,並沒有傳統新聞機構高層,也沒有親政府媒體的僱員,顯示攻擊對象是經過細心挑選的,是當權者眼中不服權威、拒絕自我審查,又沒有大財團撐腰的一群;
2)滋擾行動採取漁翁撒網式,範圍甚廣,但並非單獨一次或數次,而是因應抹黑恐嚇取得的初步反應作選擇性跟進,採取進一步的滋擾恐嚇來擴大成果,反映這些持續攻擊是有組織的、系統化的、有指揮調度的,明顯屬於集團式操作,絕非個別黑客可以做到,也有別於以往藍營與黃營之間偶爾發生的網絡欺凌;
3)滋擾行動顯示霸凌一方掌握了極多私人敏感資料,包括記者有哪些家人、
他們在什麼機構任職、租用什麼物業,甚至包括私下兼職細節、出入境行蹤等。這些資料超出了黑客入侵個人手機帳戶所能找到的資料,顯示霸凌一方神通廣大,對行事低調的普通年輕記者也能作出全方位監控,形成恐怖的威嚇壓力;
4)滋擾行動的目的具政治性,就是設法逼使受恐嚇記者放棄新聞工作,這從滋擾方多次致電受滋擾記者的對話中清晰可見。滋擾的指控內容也具政治性,例如記協主席鄭嘉如遭受的抹黑就是「灌輸反中亂港思想」。滋擾者使用手法也具政治性,例如致電時自稱是國安處人員,威脅對方若不停止新聞工作就可能坐牢;發給與記者家人有關僱主業主的信息也多涉及記者危害國安的無根據政治罪名。
5)滋擾手法經常涉及向親人施壓,具體手法是針對記者的父母、配偶和兄弟姐妹,向他們的僱主或物業業主,甚至鄰居和地產代理,散播記者是犯罪份子的謠言,作出種種毫無事實依據的抹黑,試圖令記者的親人受到巨大壓力,不勝其擾下促使記者噤聲轉行。這種向親人施壓使其被社會孤立的打擊手法,過去經常見於內地維權人士的遭遇,但在香港甚少出現,如今卻密集地用於對付一批年青記者,反映內地的政治打壓作風入侵香港,「誅九族」式政治威嚇高懸被針對人士頭上。這一點可能是最令港人側目的,文革式批鬥風潮原來可以在香港出現,如果記協不是對會員作了廣泛調查,並且部分滋擾受害人肯挺身而出作證,這股暗黑政治風潮也許至今還未暴露。
白色恐怖氛圍揮之不去
面對如此有組織有規模的集團式犯罪(刑事恐嚇、侵犯私隱),香港執法當局除了循例表態徹查,還必須以具體執法成果來向受害人及公眾交代。就算不能揪出集團主謀,最低限度要把執行監控與恐嚇的人繩之以法,否則,若任由事件不了了之,市民大眾和國際社會就會認定,香港根本沒有辦法阻止這類針對新聞工作者的政治恐嚇,白色恐怖氛圍就會揮之不去,一直籠罩香江。
這種政治氣氛的破壞力不容低估,受衝擊的絕不限於少數新聞從業員,目睹政治風潮的民眾會設法為自己和家人尋找出路;當獨立媒體集體受壓噤聲,社會上只剩下不敢批評政府或只會歌功頌德的主流媒體,倚靠獨立報道對社情民意作投資判斷的財金機構也會規避風險,把資金與人才遷移至擁有較多新聞與言論自由的地方。
不久前,英國財經雜誌《經濟學人》北京分社社長任大偉(David Rennie)離開中國,停止撰寫了六年多的《Chaguan (茶館)》專欄,他在告別篇中感嘆,近幾年在中國從事獨立採訪寫作愈來愈困難,許多外國記者被迫離開 :《紐約時報》派駐中國的記者從10人減至2人、《華爾街日報》從15人減至3人、《華盛頓郵報》從2人減至零。伴隨這些外國記者離開的,還有大量跨國企業和國際資本。當香港的政治犯罪團伙為自己恐嚇記者的成就沾沾自喜時,國際社會看到的卻是暗黑無光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