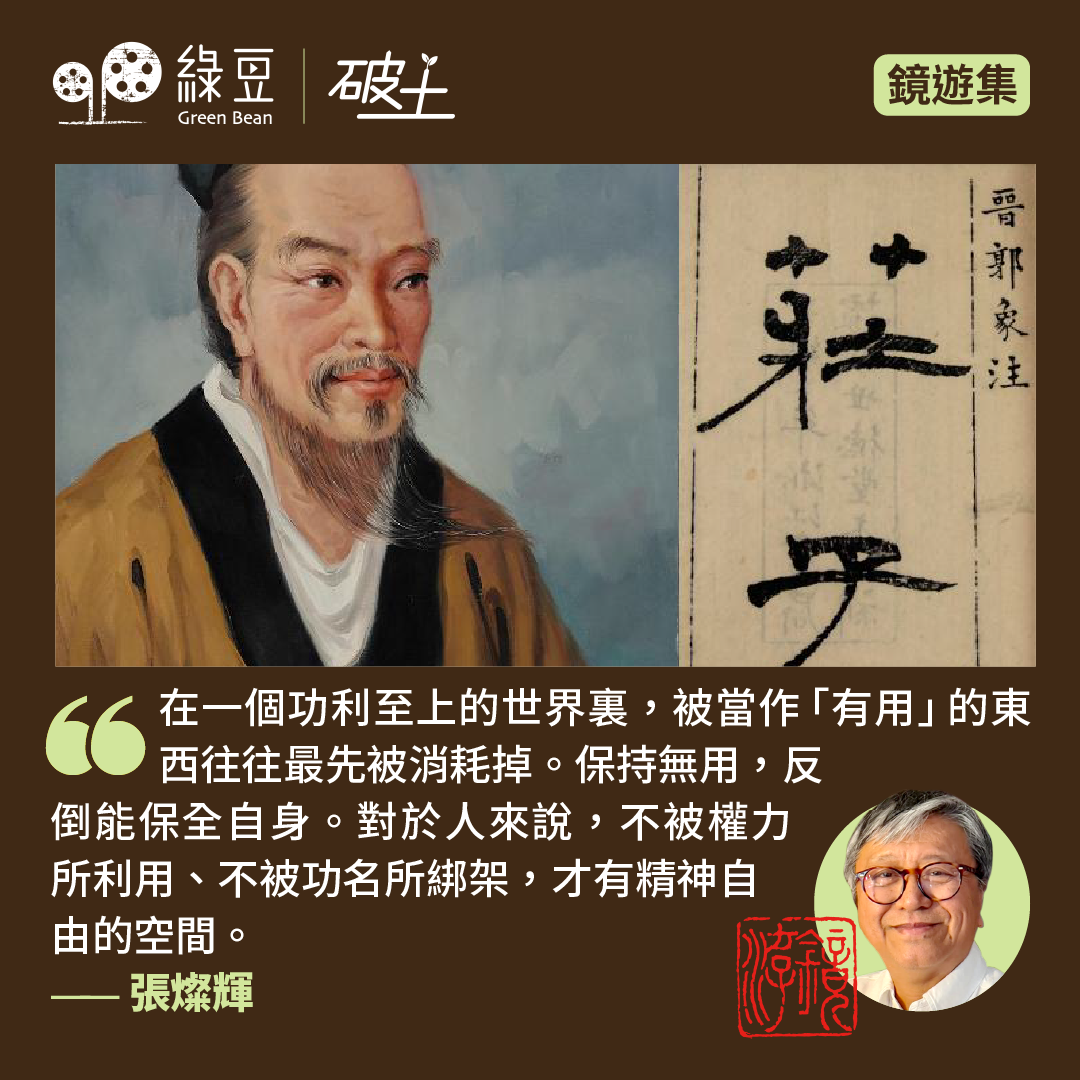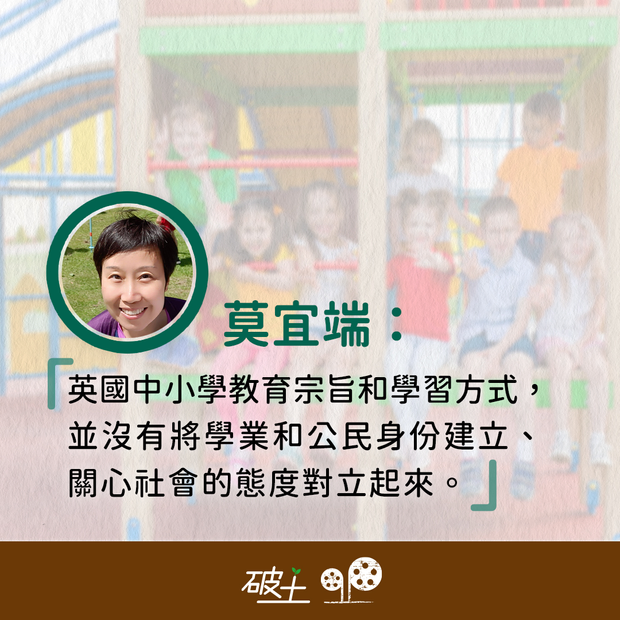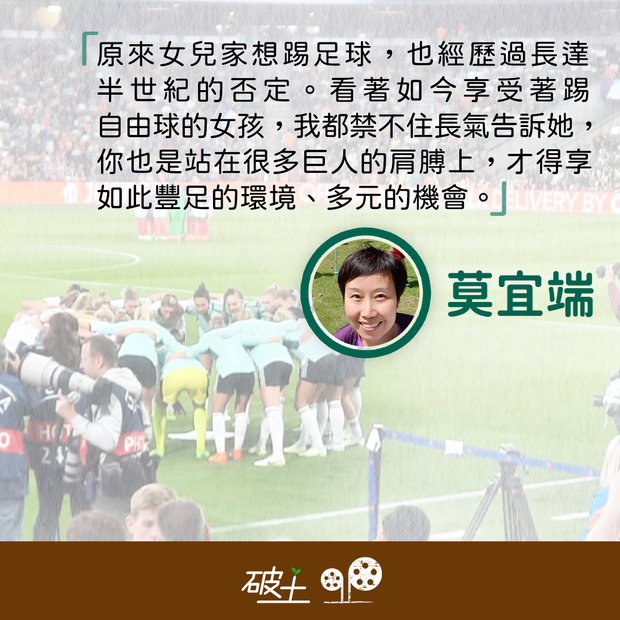被看見

新學期開始,孩子們,您們好嘛?
您們雖不多言,有些甚至未有口語,但新課室、新同學、新老師,讓你們一時反應不過來,必定不太好受,是嗎?
拓闊一點就好了
患自閉症的新生阿信(化名),因為新冠疫情輟學。世界復常了,可是15歲的他習慣了反常—— 宅在家變成他唯一接受的日常。即使是跟家人去超市,或參加他曾經至愛的SEN足球班,要他踏出家門都總是困難重重。家人照顧越加乏力,停學兩年多,阿信八月終於加入我們學校及入住宿舍。
阿信面對最大的挑戰,是工作、節目的轉變。別人眼中芝麻小事,如換了相熟的教學助理,或原本每天都做的戶外早操因天雨而取消,對阿信都可能是極大震撼。他會怎樣回應呢?阿信不會打鬧、不會大聲抗議,面對這些消化不了的要求和轉變,他總會吃吃地笑 —— 面帶緊張地笑,所以初認識阿信,會以為他害羞不說話,改以微笑回應。但其實,阿信的笑,更多時候是代表他受不了。
要減低阿信在陌生環境的焦慮,就要支援他的成人一同動腦筋。有一次,老師想阿信不再縮在他慣用的教室一角,希望他能移玉步到教室的另一邊,換換位置一同遊戲。我帶來他喜愛的玩意和填色簿。為了減少壓力,我索性請阿信到教室另一邊幫我搬椅子、抹枱,然後我們就鋪開畫冊,開始畫畫。
不過,這一招到下一次卻不管用了。
阿信這天又做「角落生物」。同工問他要甚麼嗎?但好意的提問,反而增加阿信的壓力。壓力一來,言語障礙的他更難啟齒,索性將鴨嘴帽拉下蒙著頭,不聞不問。
身心相連,壓力不容忽視。教人溝通的言語治療師,豈不是更應該先「聆聽」對方的身體語言?阿信的身體動作百分之二百正告訴我,他很驚慌、很害怕答任何問題。那就不如休息一下吧。
我在遠離阿信兩米的地下,攤開他平時喜歡的砌圖,又打開iPad一個選擇輕音樂的溝通版面,播起音樂來。阿信從他的角落偷偷看我做甚麼,我邀請他過來,選一首他愛聽的歌。就這樣,頑石移動,阿信到我這邊來,選好了歌,又八卦看我砌砌圖。於是我們就這樣,說很少很少的話,享受片刻,但交流了很多很多。他讓我知道他的音樂喜好,並且停了做「角落生物」,嘗試把自己的世界拓闊一丁點。
一丁點就好,肯嘗試就好。
每年九月,一同開學一同忐忑的,還有家長。嚴重學障兒的家長,壓力尤其大,也極其勇敢。
嚴重學障兒嘉兒(化名)的媽媽,參加孩子入學後第一次校內的跨專業會診(multi-disciplinary clinic),與會的有老師、宿舍舍監、駐校護士、特約精神科醫生,還有職業及言語治療師。我們一般都會向家長了解孩子的醫藥需要、生活習慣、情緒、溝通需要,每個參加者就從其專業角度出發,分享有關嘉兒的進步或值得留意的情況。媽媽今次是以視像形式參加,我們各人就坐滿會議室的長桌。除了嘉兒的個案,這早上還為另外三個學生個案會診,忙個不可開交。
到了下午,當我和同事埋頭埋腦寫報告時,大家都收到「腦細」電郵,原來是嘉兒媽媽的信。
開完會就收信?搞邊科?
原來是媽媽來函多謝我們一群同工。媽媽說,女兒之前的學校和求助的服務單位,因為該區資源緊絀,所以即使女兒情況很差,但學校只能提供一月一節的言語和職業治療。她有問題的話,學校通常會以電郵或電話回覆,她未有獲邀列席或出席關於女兒的跨專業會診。媽媽說,今早視像一接通,一見到十個人圍坐長枱跟她打招呼,我們又逐一報告嘉兒入宿兩星期以來的生活日常,她覺得很感激,亦很激動。她的電郵如此說:
I am being seen, being heard, being listened to. And most of all, I feel being respected. Thank you very much. (我感到被看見、被聽見、被聆聽。難能可貴的是我覺得被尊重,多謝你。)
開跨專業會議開得多,不多不少總有行禮如儀的感覺。但這位媽媽的電郵,真像荒漠中的甘泉。一位同事說:不是每一次開會都會有結論,有時面對一個辣手的個案,大家都好像無計可施。有時家長或local authority又有不適切的期望。但能在學年初,有這媽媽的鼓勵,真的有如強心針。
至少,我們彼此提醒,無論多難的個案,只要其中一直處於弱勢的一方,能被看見、覺得被聽見,不再隱形,這就功德無量了。
讓無聲者覺得被尊重,我想,這就令冗長枯燥的會議,不再行禮如儀;也會令助人專業的同工,不會變成老油條。
▌[英倫筆端]作者簡介
莫宜端 Zandra, 育有一子一女,與丈夫子女定居英國,英國註冊言語治療師。曾任記者、時事節目主持、政策研究員、特區政府局長政治助理。及後進修並成為言語治療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