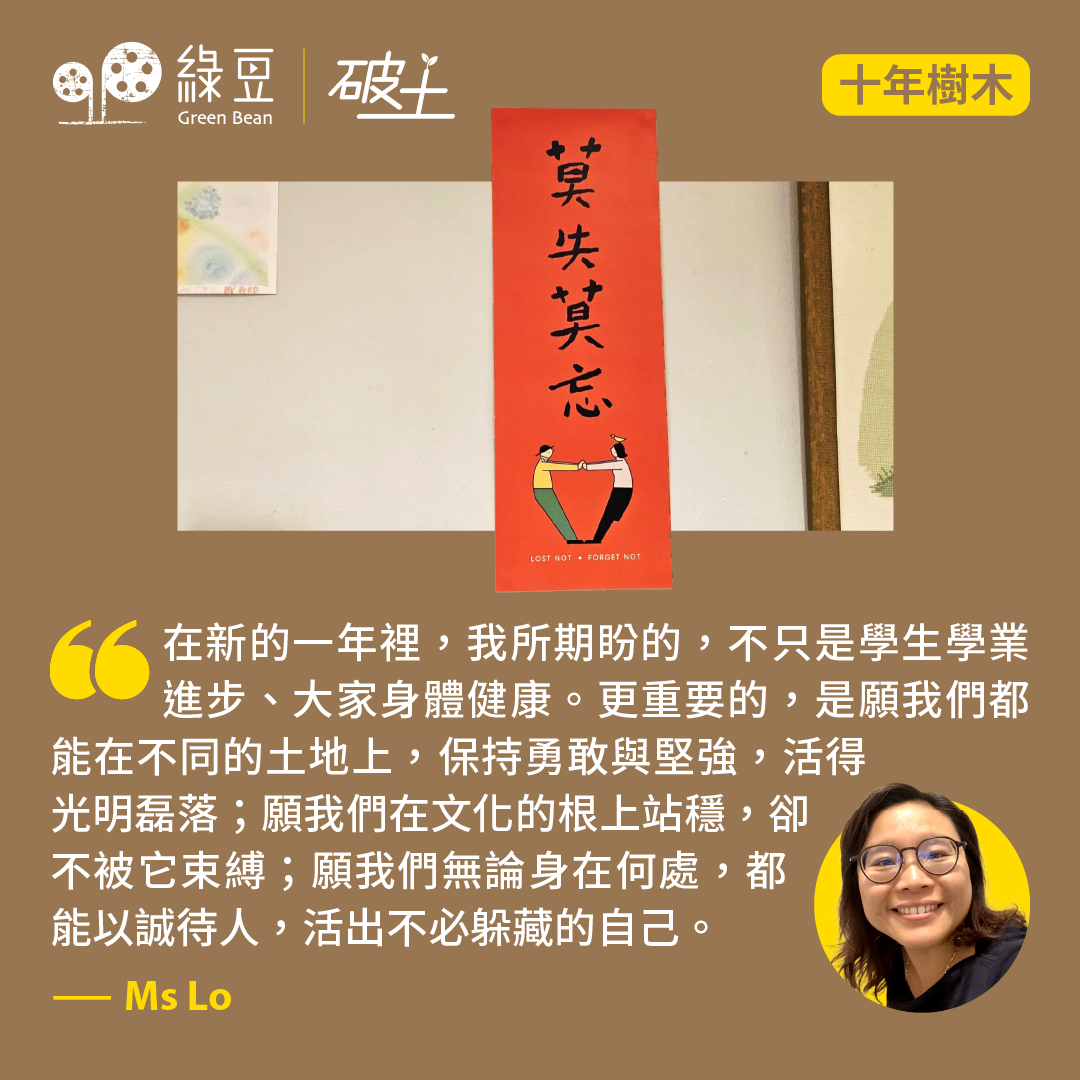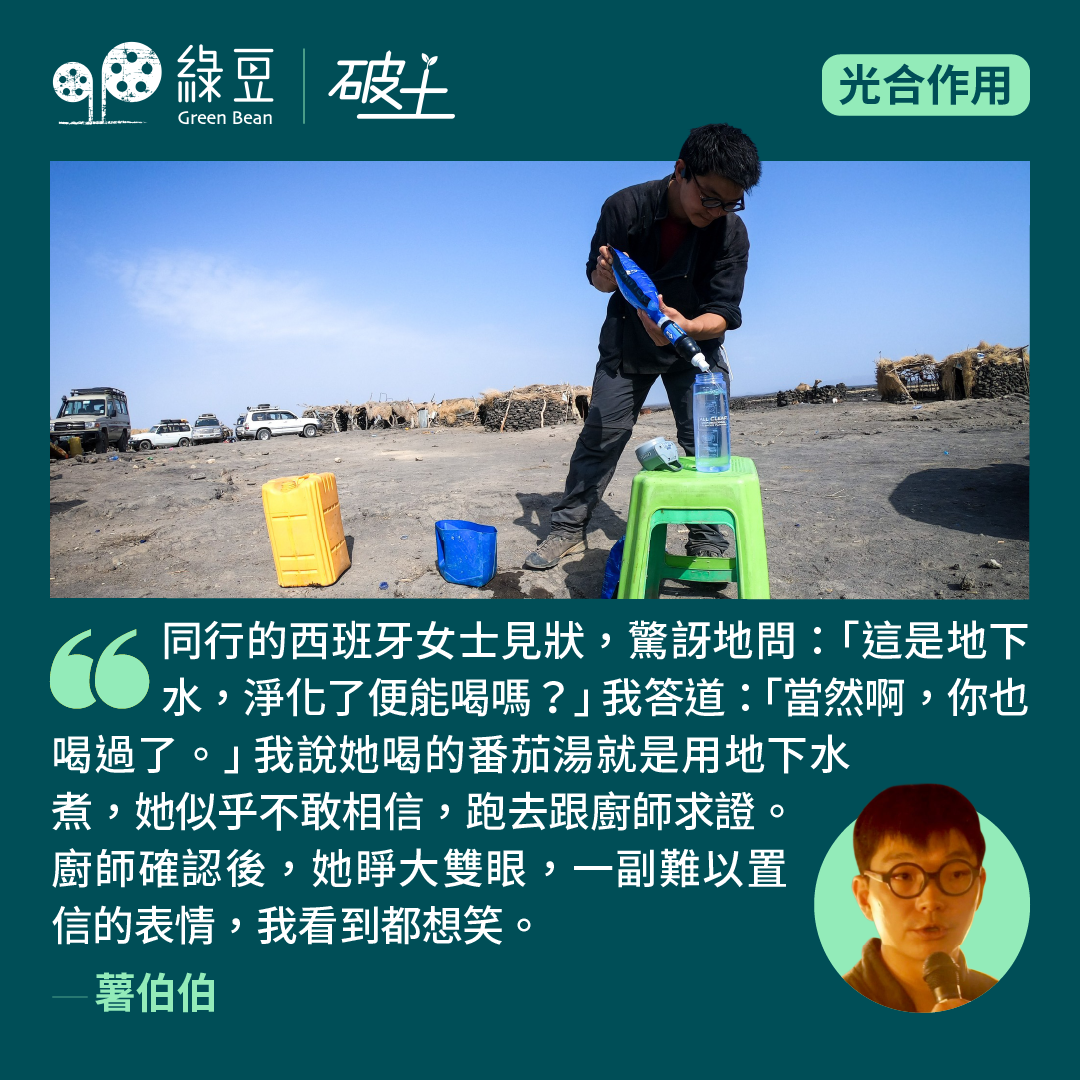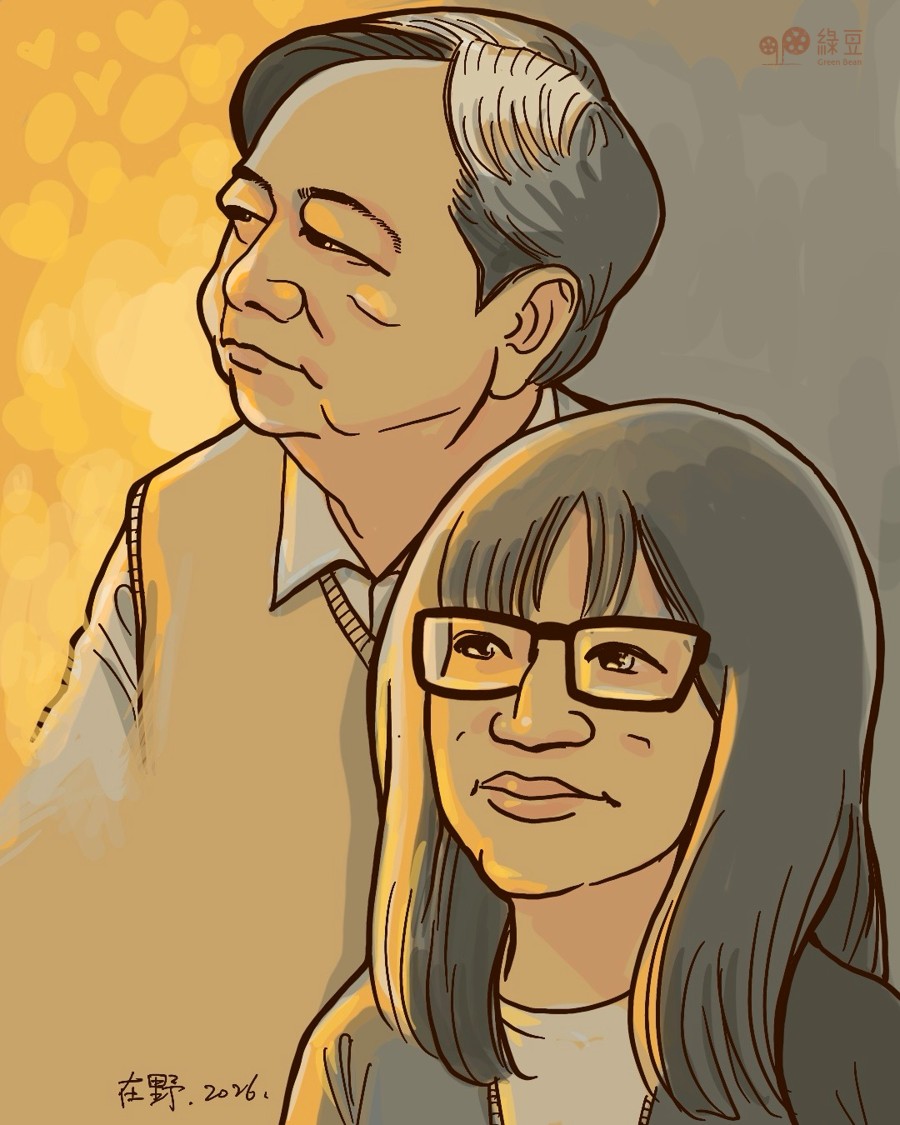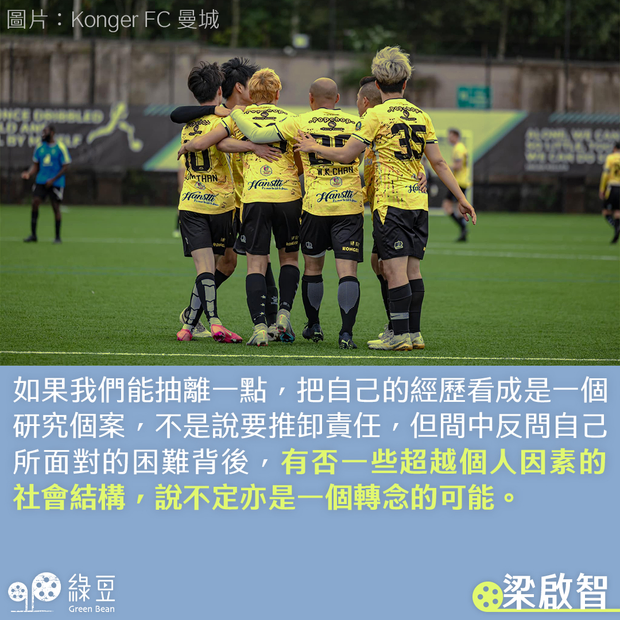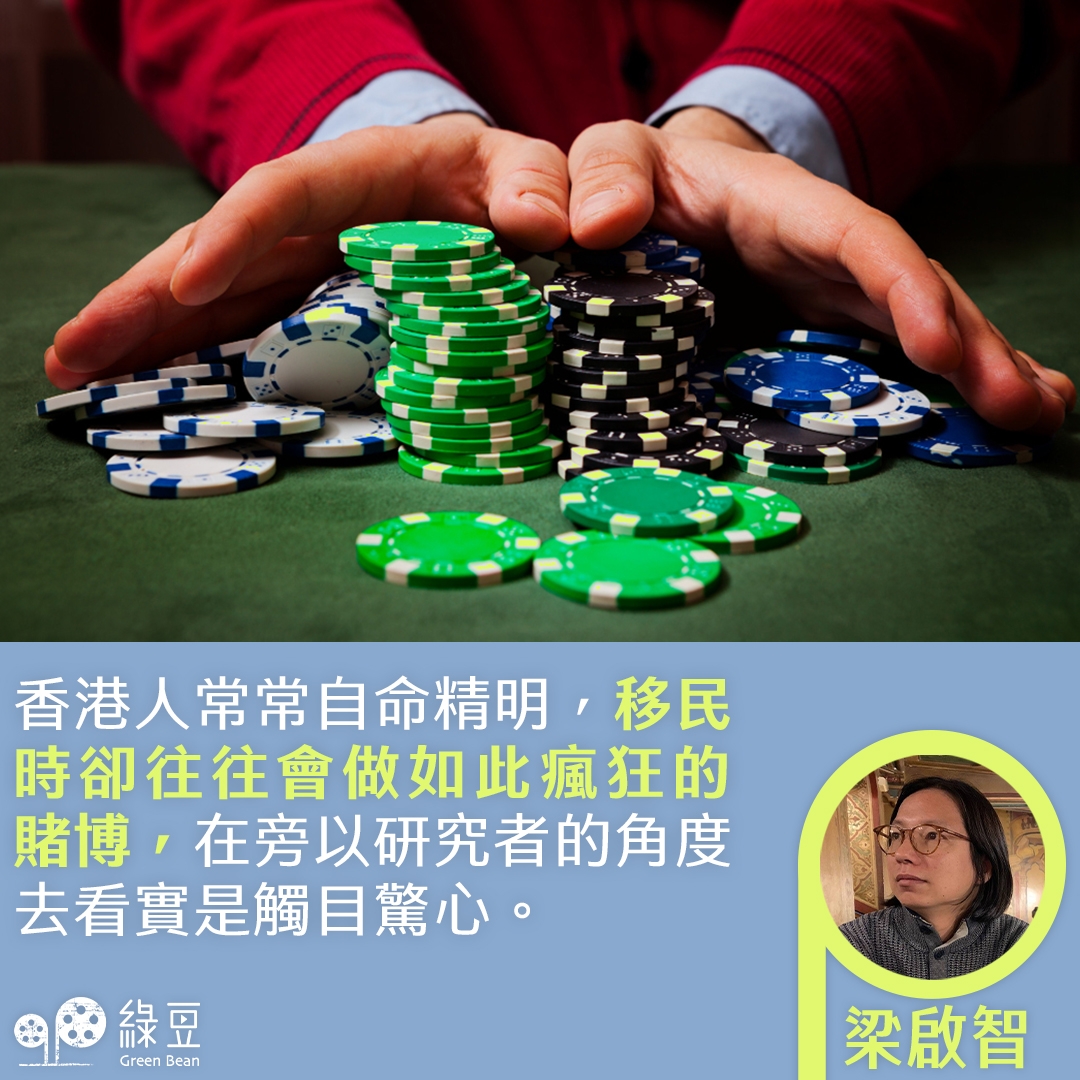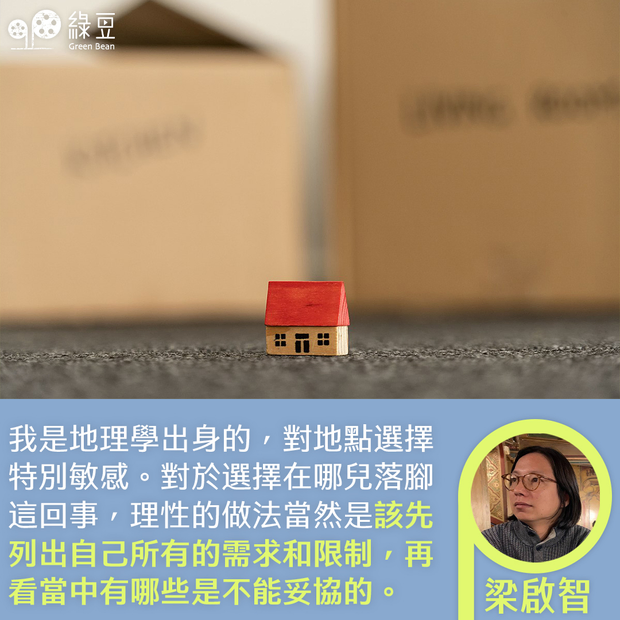移民家庭這個巨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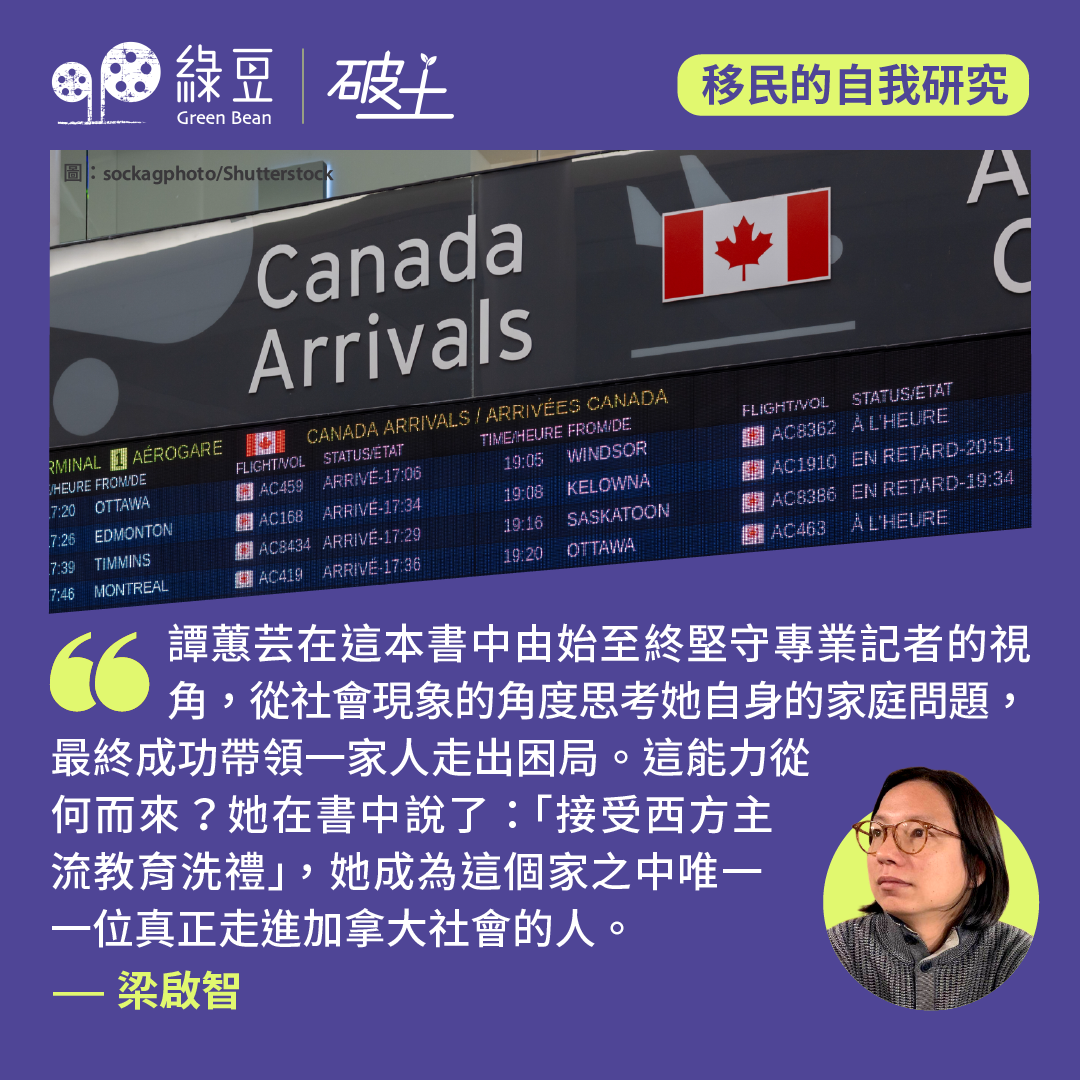
友人譚蕙芸近日出版的新書《家鎖》廣受好評,送到各書店的首刷書均被搶購一空。早前她分別在台北和東京的飛地書店舉行新書發布會,兩場活動也是座無虛席。《家鎖》的副題是「華人家庭這個巨獸」,不少到場讀者也分享了他們與原生家庭的種種糾纏,說明此主題有強大的共通性。然而在新一波的移民潮下,此書也帶出了另一個重要的主題:移民的衝擊如何擴大原有的家庭矛盾。相對於「華人家庭這個巨獸」,要直視的還有「移民家庭這個巨獸」
過去熟悉的譚蕙芸,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同事,擅長於以輕鬆活潑的方式教授新聞寫作手法。在公眾領域的她,則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以細膩的筆觸,紀錄街頭和法庭的人與事。而在這本書當中,她打開了另一個被埋藏的身份:她有中風的父親、失智的母親,還有思覺失調的哥哥。在疫情期間,當香港人都在趕緊移民離開,她一個人把全家從加拿大搬回香港,找辦法活下去。
故事的起點是八九六四後,一九九七前的那一波移民潮。他們一家過去從來沒有離開過亞洲,一下子連根拔起移民到加拿大多倫多。然而哥哥在離港前已有的徵狀,在移民後進一步加劇,結果被診斷為思覺失調。可是他的精神健康卻沒有得到適切照顧,父母把他藏起來與社會絕緣,成為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移民環境成問題催化劑
事情發展至此,固然有華人家庭中的疾病污名和社會禁忌。然而在譚蕙芸的筆下,很明確看到移民家庭的環境如何加劇了各種問題,一步一步的走到無尾巷。
精神問題和其他身體問題不一樣,不能依靠外在儀器診斷,需要患者願意告知醫生潛在的徵兆;其中首要條件是建立和醫生的信任關係,在此之前又要先跨過語言的障礙。自問在台灣看醫生,明明已是說華語,有時要描述自己到底怎樣不舒服還是覺得隔了一層;換成英語,再加上各種沒聽過的醫學專有名詞,難度可想而知。書中就提到要在當地尋找懂粵語的精神科醫生的各種障礙,即使身處港人社群聚居的大城市也不易辦到,求醫路上又帶來更多拖延。
移民也會帶來家庭崗位的改變,而這點又可以延伸出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書中提到母親對家居整潔十分執着,移民後成為退休人士,一天到晚就在大屋中料理家務。對她來說,維繫這個家的整潔成為了她的「工作」甚至是生活價值,甚至演變成某種「控制慾」;然而兒子本來已是精神緊張,家中還要有各種規條,對病情沒有好處。可是也正正因為成為退休人士,她有時間照顧兒子生活所需,真的可以把兒子從社會中隔絕起來,雖然這也同樣不見得對病情有好處。
家人有病,不能自理,應該如何解決?這就來到家庭本身的內在權力關係。一個家庭本來在香港各有各忙就算同住也不相見,到了地廣人稀的加拿大後變成獨立大屋內「困獸鬥」,潛藏的問題隨之爆發。本欄之前也寫過,移民歐美又不在市區的話,最好每個人都懂得並願意開車,因為這不止是生活問題,更可以帶來家庭問題。看譚蕙芸寫到母親不願開車,「父親掌握開車大權」、「形成了家庭內部權力不平衡的局面」,讓我想到許多相類似的移民家庭,深感唏噓。
這就是譚蕙芸筆下的家庭自述史:潛藏的危機一方面看得驚心動魄,但各種細節和骨子裏的問題卻又熟悉得讓人吃驚。
真正走進加拿大社會的人
這樣的家庭結構終於隨父親中風和母親失智而撐不下去,有如每天為變成倫常慘劇倒數。於是譚蕙芸鼓氣勇氣,把一家人帶回香港。
但我想強調的是如果移民家庭能在這故事得到任何教訓,除了「必要時回流可以是一個選擇」之外,更重要的反而是怎樣才算是與當地社會「融合」。
要回索這樣一段隱藏數十年的家庭史,很容易走歪路,變成各種埋怨或自憐。但譚蕙芸在這本書中由始至終堅守專業記者的視角,從社會現象的角度思考她自身的家庭問題,最終成功帶領一家人走出困局。這能力從何而來?她在書中說了:「接受西方主流教育洗禮」,她成為這個家之中唯一一位真正走進加拿大社會的人。在早前在東京的新書發表會中,她還笑說她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她把從西方社會學到的意識,應用到華人家庭關係當中。
港人常常自以為具國際視野,然而那是相對的;移民到歐美社會,骨子裏還是華人傳統觀念,一不合眼的習慣或訴求便視之為是西方社會有問題,大有人在。不時告誡自己有沒有畫地自限,有沒有忽視問題而不自知,是《家鎖》的重要提醒。
▌[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
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