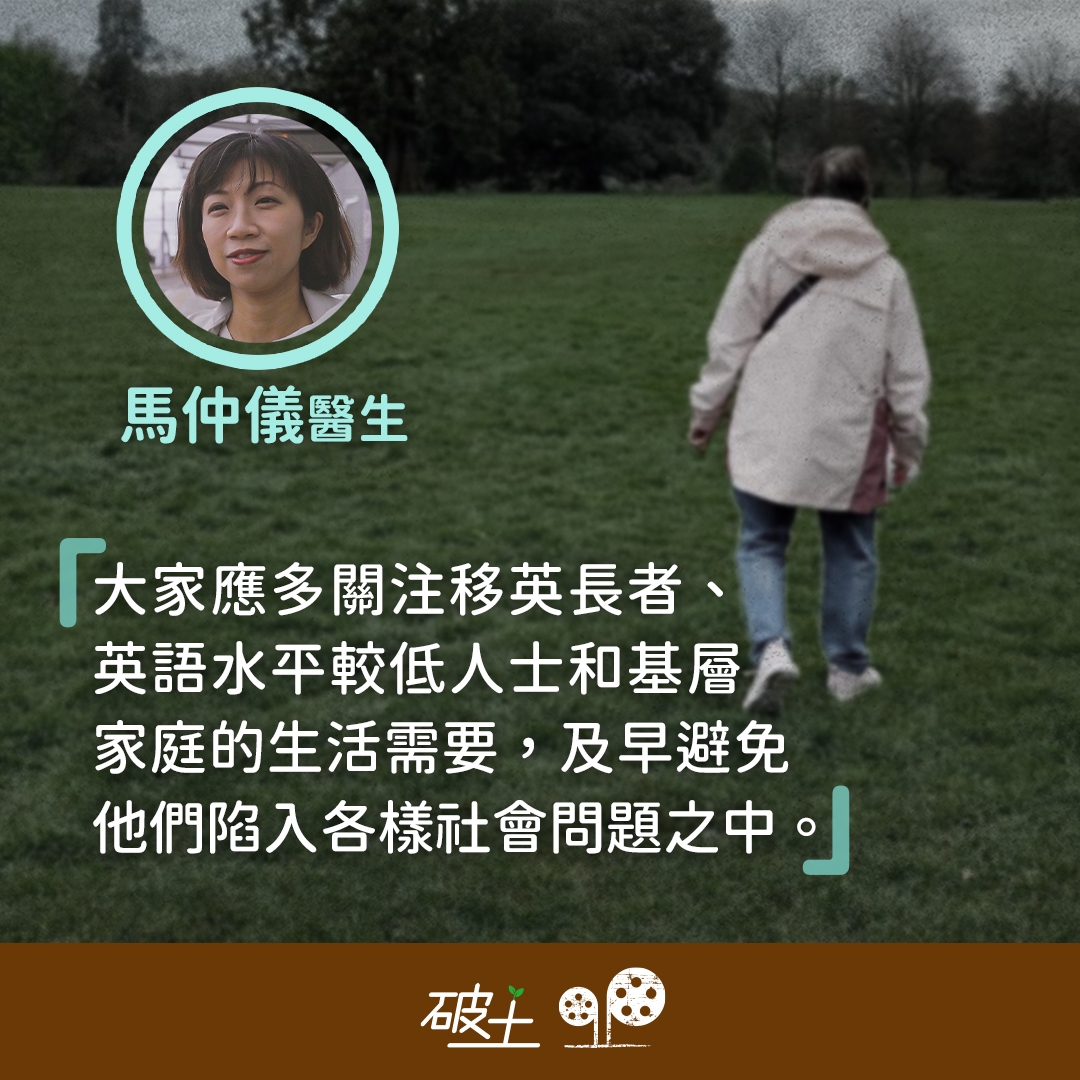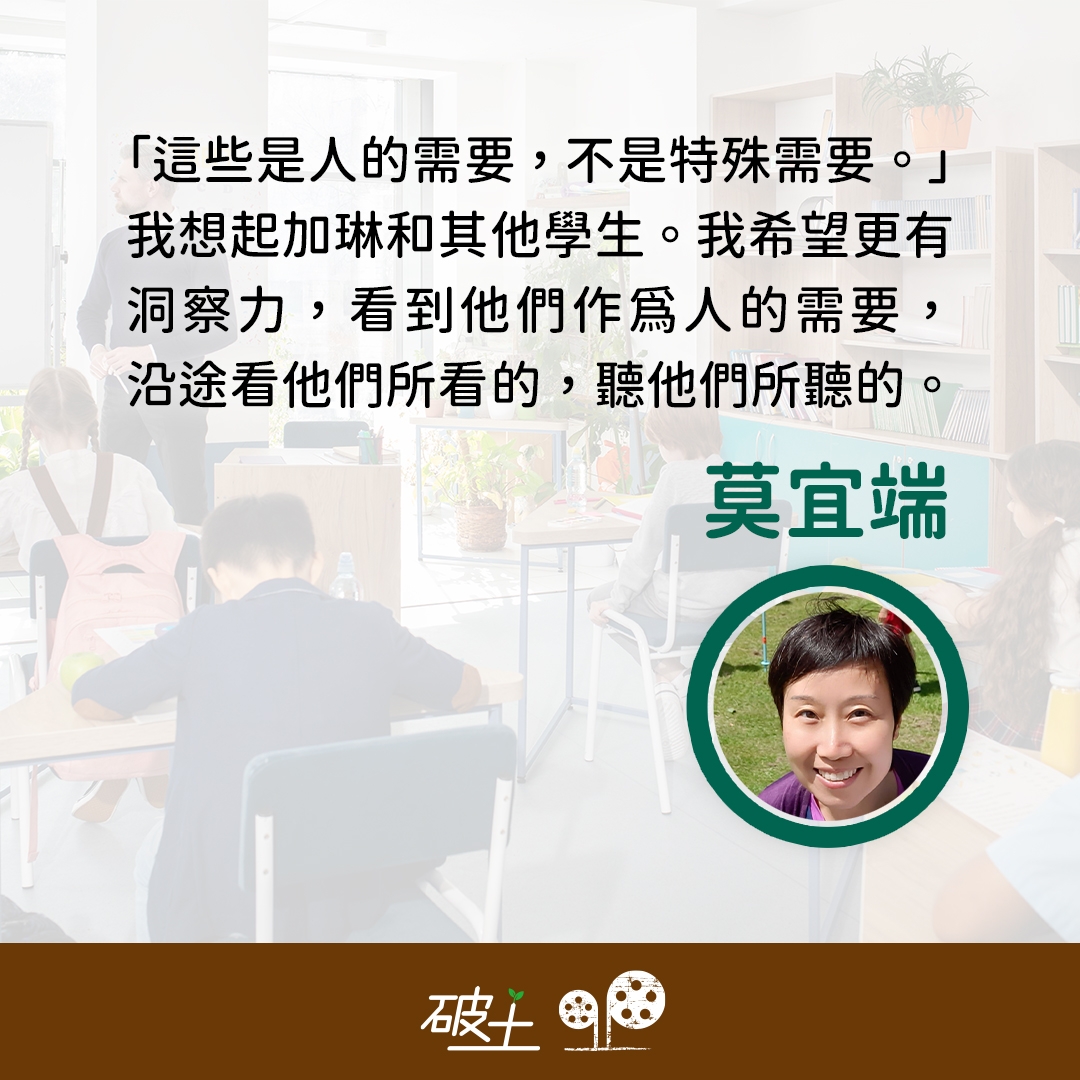為什麼要讀歷史?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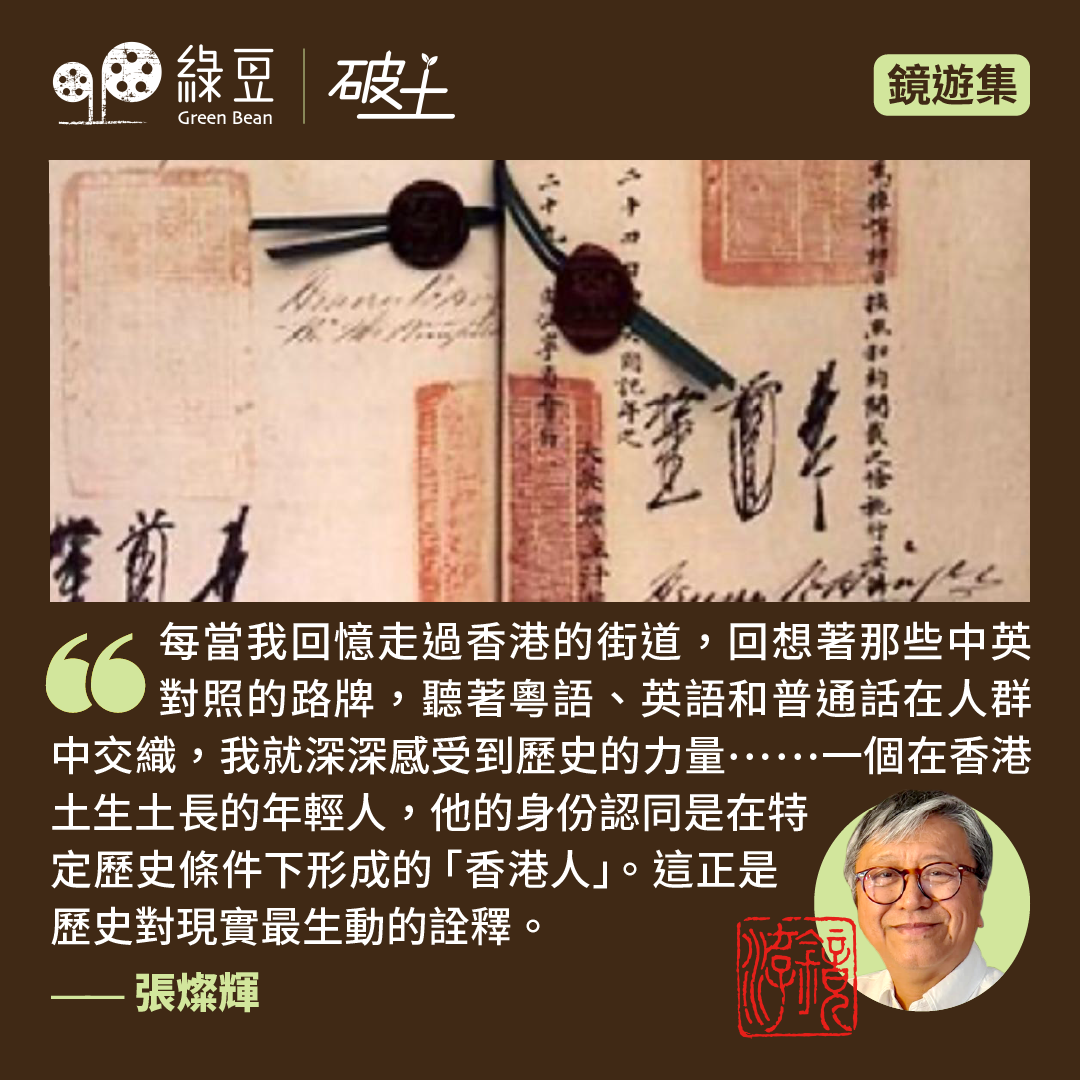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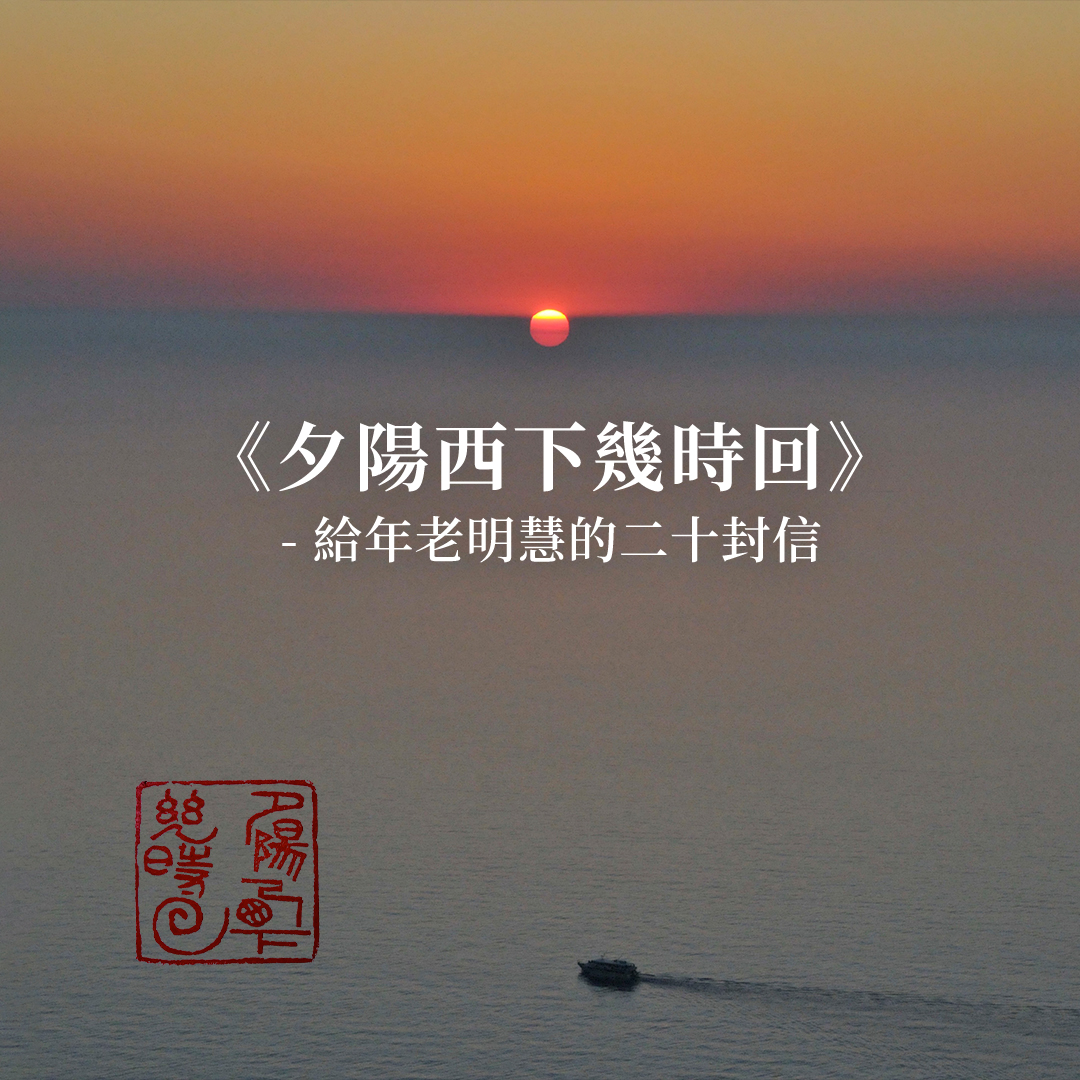
第十八封信 18.1
明慧:
當夕陽西下的光影灑向遠山,我常常沉思於時間的奧秘裡,想著我們何時才能真正明白過去的光影,並在它們的照耀下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安寧。你曾經問我:「為什麼要讀歷史?」這個問題彷彿一顆石子投向靜湖,激起了我心中層層漣漪。這不僅是一個學術的問題,更是關乎我們「是誰」的核心命題,是每一個思考的靈魂都會面對的永恆追問。
讀歷史,就像是在一面古老的銅鏡中:我們從何而來?過去的經驗如何塑造了我們的思考方式、價值觀與語言;我們是誰?對歷史的理解,讓我們在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中找到了立足點;我們往何處去?唯有明白過去的軌跡,才能在當下選擇合適的道路,並懷抱對未來的希望與憧憬。這三個問題環環相扣,就像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說的時間三重結構,共同構成了我們存在的完整樣貌。
歷史與我們的身份認同:一場永不停歇的對話
明慧,歷史並非冰冷的年代數字或單純的事件羅列,也不是博物館裡陳列的文物標本,而是深刻地融入我們日常認同的活生生的力量。它像血液一樣流淌在我們的思想脈絡中,像基因一樣遺傳在我們的文化傳承裡。香港的例子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深刻性。
1997年主權移交,並非一朝一夕的決定,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當時清朝政府在列強的壓力下,將九龍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新界地域,以及235個島嶼租借予英國,為期99年。從這段延綿百年的歷史軌跡中,我們可以理解,香港的政治制度、法律體系與社會結構,都深深根植於那段殖民歷史的土壤之中。
當我們探究這些歷史脈絡時,我們尋求的不只是「發生了什麼」的事實陳述,更是要理解「為什麼會這樣」的深層邏輯。正如那段開埠的歷史所顯示的,香港之所以會形成如此特殊的東西文化融合,與1842年《南京條約》、1860年《北京條約》以及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這三部曲的歷史安排密不可分。這種特殊的歷史處境決定了香港「一國兩制」政治框架的複雜性,也解釋了為何香港在今天會面臨如此多的挑戰與機遇。
每當我回憶走過香港的街道,回想著那些中英對照的路牌,聽著粵語、英語和普通話在人群中交織,我就深深感受到歷史的力量。這不是抽象的學術概念,而是活在每一個香港人身上的具體現實。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人,他的身份認同既不是純粹的「中國人」,也不是單純的「英國殖民地居民」,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香港人」。這種身份認同的複雜性,正是歷史對現實最生動的詮釋。
因此,讀歷史絕不是一種懷舊的消遣,而是在靜心傾聽「過去如何持續影響現在」的深刻對話。這種對話讓我們明白,我們每個人都是歷史的產物,同時也是歷史的創造者。當我們面對未來的抉擇時,歷史為我們提供了更寬闊的視野和更堅定的身份認同基礎。
海德格的時間論:存在的時間性結構
要真正理解歷史對身份認同的重要性,我們必須首先理解時間的本質。海德格在他的《存在與時間》中為我們揭示了一個革命性的觀點:「此在」(Dasein)之所以為人,關鍵在於它的「時間性」。這不是一個抽象的哲學概念,而是每個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的實在結構。
讓我們用通俗的語言來理解海德格的深刻洞察。他告訴我們,人類的存在總是同時和「過去」「現在」「未來」相連接的,這三個時間向度不是機械鐘錶上分割的時刻,而是有機統一的整體:
過去(曾在,gewesen):我們每個人都被投擲到某個歷史情境中——譬如一個特定的家庭、一段特殊的殖民史、一種獨特的文化傳統。這種「被拋狀態」並非我們自己的選擇,但它賦予了我們原初的文化背景與語言基礎。就像一個香港人無法選擇自己出生在殖民地時代,但這個歷史事實深深影響了他的世界觀和價值體系。
現在(當下,gegenwärtig):人必須在此時此刻做出選擇與判斷,這些「此刻的抉擇」正是形塑我們身份的關鍵過程。每一個決定都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回應,同時也是對未來的投射。當一個香港人選擇用粵語還是普通話與人交談時,這看似簡單的語言選擇實際上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意義和身份表達。
未來(將來,zukunftig):我們的行動總是指向某種可能性,最終指向死亡這個絕對的界限。但正是因為有了對未來的投射和期待,才讓我們在當下努力規劃與改變。未來不是一個空白的畫布,而是在過去和現在的基礎上展開的可能性空間。
海德格的哲學洞察在於,他向我們展示了這三個時間向度的內在統一性。用更通俗的話來說:我們不能割裂過去、現在與未來,就像我們不能割裂頭腦、心臟和雙手一樣。正如讀歷史能讓我們理解自己從何而來,當下的思考與行動則決定著我們將往何處去。這種時間性不是抽象的哲學概念,而是我們每個人都在親身體驗的存在結構。
更重要的是,海德格指出,這種時間性正是「歷史性」得以可能的根本條件。沒有時間性,就沒有歷史;沒有歷史,就沒有真正的人的存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理解歷史不是學者的專利,而是每個人實現自身存在的必要條件。
伽達默爾的詮釋學:理解作為歷史性存在
如果說海德格為我們揭示了時間性的存在結構,那麼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則進一步闡明了我們如何在這種時間性結構中理解歷史。他的哲學詮釋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歷史、理解文化、理解自我的全新視角。
伽達默爾的核心洞察是:「理解」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性行為。這意味著我們永遠不可能像自然科學家觀察實驗對象那樣,以一種完全客觀、超越歷史的方式來理解歷史。我們總是帶著自己的歷史處境、文化背景和個人經驗來接近歷史文本或歷史事件。
這種觀點包含著三個重要的層面:
語境決定理解:我們的語言、概念與價值觀,都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步形成。想要理解一段史實,就必須盡可能還原當時的歷史語境。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我們永遠無法完全擺脫自己所處的當代語境。這種「雙重語境」的張力,正是理解活動的動力源泉。
前見與對話:每個讀者都帶著自己的「前見」(Vorverständnis)——早已存在的理解框架來接近歷史。這些前見並不是理解的障礙,反而是理解得以開始的前提條件。真正的歷史理解,是讀者與歷史文本在「對話」中彼此調整、相互啟發的過程。就像兩個朋友的深度談話,雙方都會因為對話而改變自己的觀點。
視域融合:伽達默爾用「視域融合」這個概念來描述理解的本質。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視域(horizon),即我們能夠看到和理解的範圍。當我們接觸歷史文本或歷史事件時,我們的視域與歷史的視域會發生融合,產生新的理解。這種融合不是簡單的相加,而是創造性的重構。
讓我們用香港的例子來說明這個過程。當一個今天的香港年輕人閱讀關於1967年暴動的歷史資料時,他不可能完全擺脫自己當代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念。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無法理解那段歷史。相反,正是通過他的當代視域與1967年歷史視域的對話和融合,他可能獲得對那段歷史更深刻、更豐富的理解。他可能會發現,當年的社會矛盾與今天的政治分歧之間存在著某種深層的連續性,也可能會意識到歷史發展的複雜性和多面性。
伽達默爾的詮釋學告訴我們,歷史理解不是被動地接受既定的「歷史事實」,而是在「提問—回應—再提問」的動態循環中,持續深化對歷史和對自己的認識。這種理解活動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我們的理解也會成為後人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材料。
(待續)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