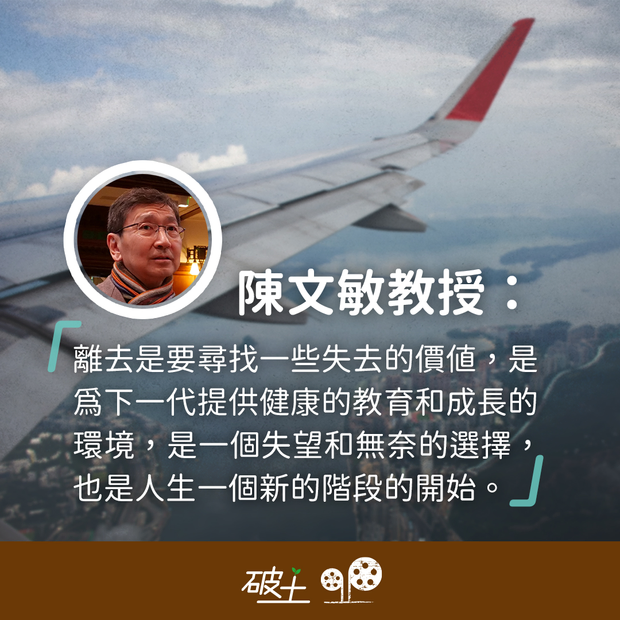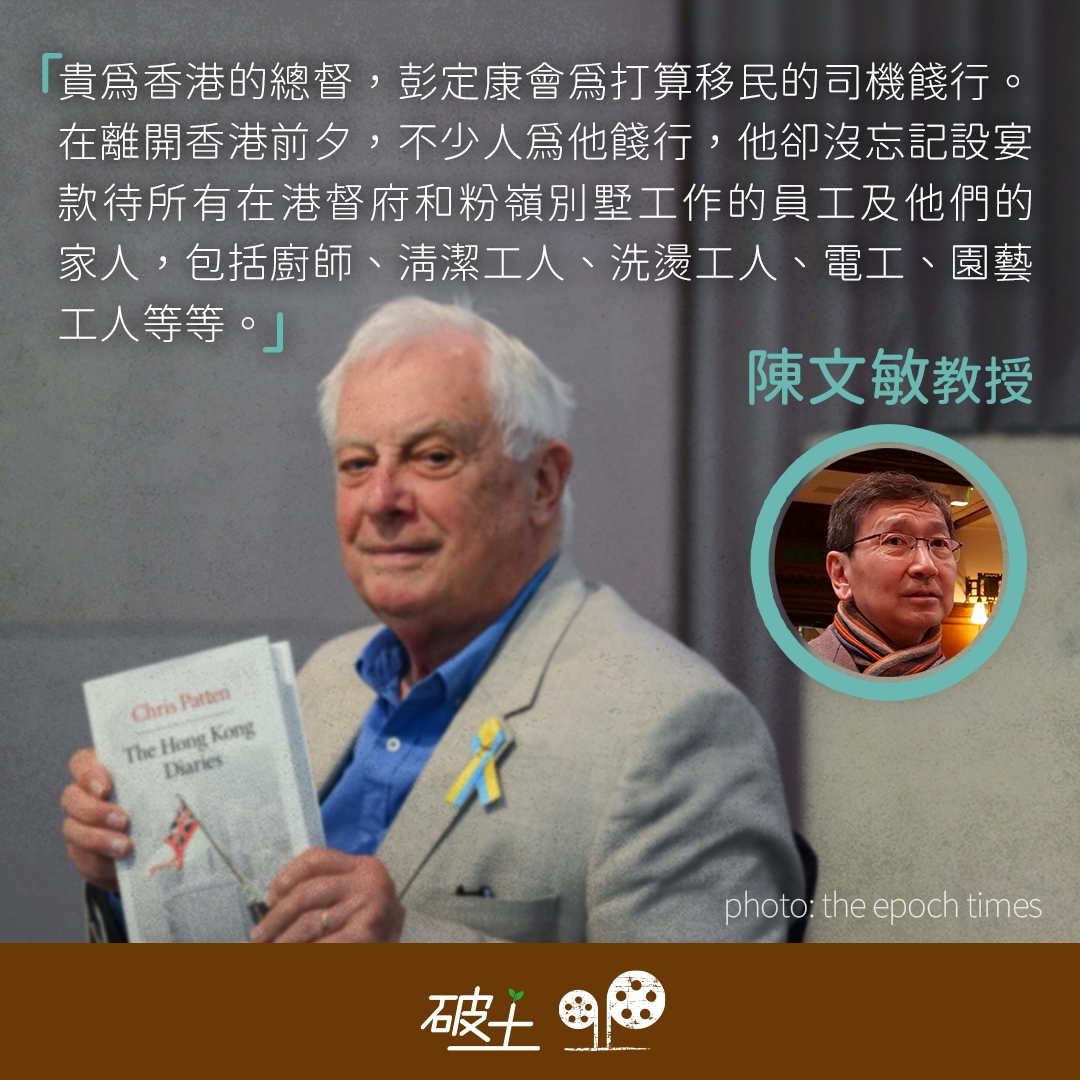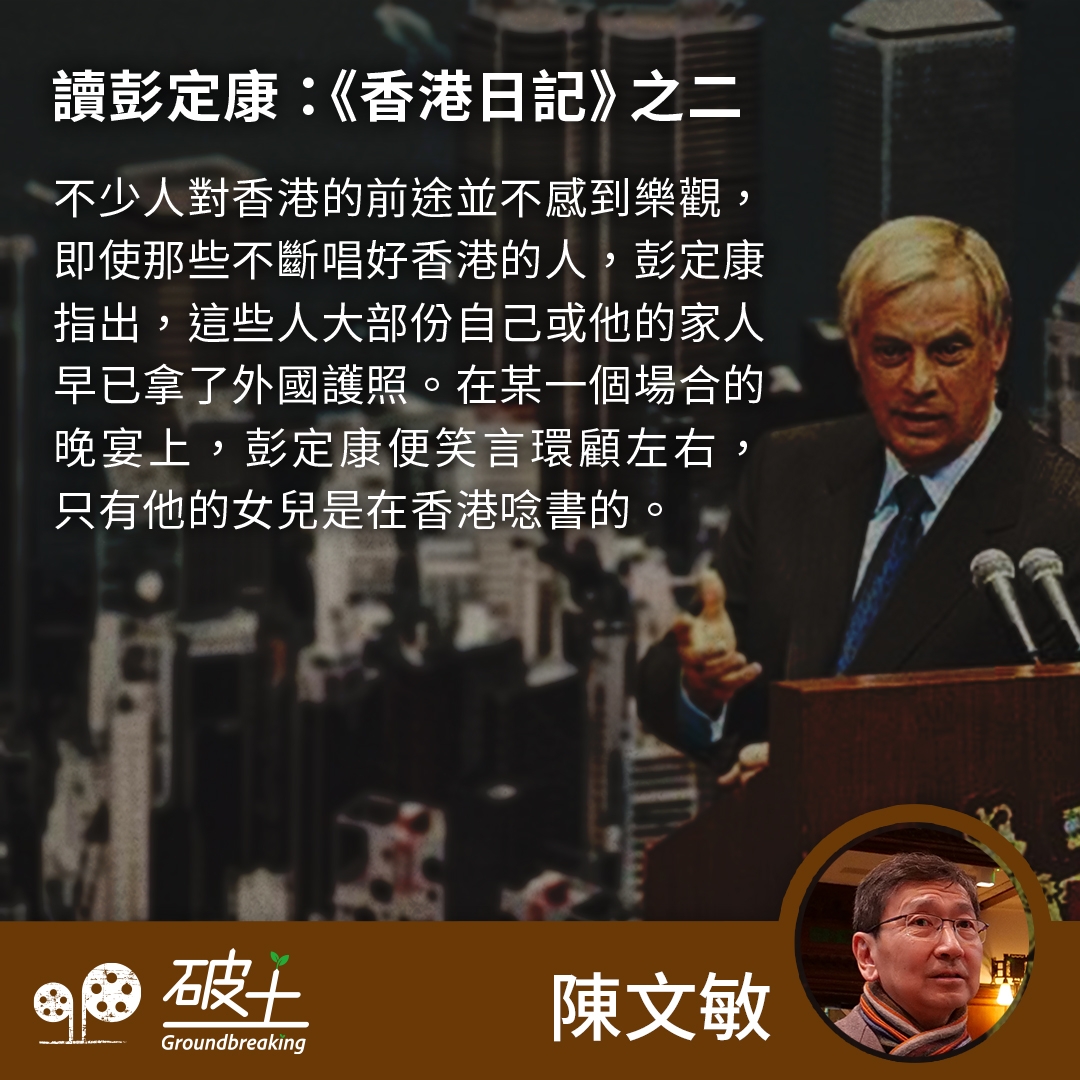兩性之間:確認性別與生理性別

英國的《性別確認法》(Gender Recognition Act)規定,任何人士獲發性別確認證書( Gender recognition certificate)後,其性別將以確認書上所載的性別為準 ,除非法例另有規定。早前英國最高法院裁定,[1]《平等法》(Equality Act)中對性別的定義只限於出生時的生理性別,而非後天經確認程序確認後的確認性別。這宗裁決在社會上再次激發起傳統性別與跨性別的爭論。網上的討論更傾向兩極化,一邊認為這是對維護傳統生理性別的勝利,另一邊則認爲這是對保障跨性別人士的一大倒退。實情究竟是怎麼?
最高法院的判決
事緣蘇格蘭政府為保障女性在公營機構的代表性,規定公營機構的董事會必須有一半成員為女性,但由於持有確認證書的女性(生理性別為男性)在法律上被確認為女性,故理論上公營機構的所有代表可以是男性或確認性別的女性,這受到一些女性團體的質疑。
For Women Scotland Ltd 向法院提出訴訟,認為以性別為基礎的保障應該只局限於出生時為女性的人士,蘇格蘭政府則認爲持有確認證書的女性應該得到和生理女性同樣的保護。這爭論背後則是經已爭辯多年的跨性別人士的地位。
法院強調它並非處理任何政策或倫理道德的問題,而是純粹一個技術性的法律解釋問題,即《平等法》中對性別的界定是指生理性別還是包括確認性別。因此,法院首先重申銓釋法律的原則:在銓釋法律時,法院旨在尋求和釐清立法機關透過法律的文字用語所欲表達的意思,法院須考慮法例的整體內容和相關條文的上文下理,至於條例以外的背景資料,例如法改會的報告書、政府發表的相關白皮書等,雖然是法院可以參考的資料,但這些文件不能取代法律條文的用語的意思,尤其是當文字的意思是清楚明確,沒有含糊的地方或出現不合常理的情況。這些原則並不具爭議,但卻突顯法院的結論是完全基於對條例文字的演譯,而非法院的價值取向。
法院從條文的的用語、上文下理、立法背景和歷史發展出發,《平等法》內多項對性別的保障,例如一些涉及懷孕或餵哺母乳的條文,明顯只能適用於生理女性。國會在2010年通過《平等法》時,《性別確認法》經已存在,但《平等法》中將「性別」與另一項受保護特徵「性別重置」(gender reassignment)並列,顯示立法者有意區分生理性別與跨性別身份。
其次,若性別包括確認性別,將會有違法律允許某些場所可以實施性別分隔安排,例如洗手間,庇護場所、監獄等。若跨性別女性(即生理男性)也被視為「女性」,則該類空間將不得排除跨性別者,進而損害(生理)女性的安全與隱私。法院認為,這種解釋將使原本旨在保障女性的條款變得形同虛設,顯然有違立法的目的 。
事實上,英國已有兩宗仍在審理的案件,一宗涉及一名確認性別為女性(生理性別是男性)的囚犯,被安排在女囚犯監獄期間涉嫌強姦一名女性,[2]另一宗在勞資審裁處的案件則涉及在國民保健計劃下一名女護士拒絕讓一名確認性別為女性(生理性別是男性)的醫生使用女性休息室。[3]
此外,法院認為,政府的解釋會引起不少混亂,在執行上亦難以實施。一些專為女性提供服務的機構,會難以分辨那些是服務對象,例如跨性別的女士(生理性別是男性)毋須接受子宮檢查手術,不持有確認證書的跨性別男子(生理性別是女性)則可接受這服務,但持有確認證書的跨性別男士(生理性別是女性)卻會被排除於這些服務之外。
蘇格蘭政府亦提出,若法例只承認生理性別,這會令跨性別人士不再受平等對待的保障,亦有違多年來的平權政策的精神。法院並不同意這個論點。法院指出,若一名被告人因某人的衣著或外表而認定她是女性,並以此作出不平等的待遇,那即使某人在法律上仍被視為男性,被告仍然觸犯《平等法》中不受性別歧視的保障,而這結論並不視乎某人是否持有性別確認證書。
再者,2024年《平等法》的修訂,亦擴闊了不受間接歧視的保障。所謂「間接歧視」 (indirect discrimination),是指被告採納某一看似中性的標準 (例如身高),但實際運作時可能有大部分某一類人士(例如女性) 均無法符合這標準。新增的第19A條規定,若受害人因這標準而受到不平等待遇,那即使他不屬於該類人士 (例如因她是確認性別的女性而按這判例法律上是男性),他仍然受到不受間接歧視的保護。
討論
法院的裁決言之成理,亦相當具説服力,從技術層面看,難以説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唯一可以爭辯的地方是該部法例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在涉及懷孕、產假、母乳餵哺等問題,將性別局限於生理性別是無可厚非,但這是否意味在整部法例多個不同領域內,性別須要作統一的解釋?普通法假設在同一部法例內,同一詞彙該有同樣的解釋,但這只是一項一般性原則,過往亦時常有例外的情況,同一詞彙在同一法例的不同章節可以有不同的銓釋。[4]法院拒絕採取一個彈性的解釋,認為這會帶來很多不確定性,亦難以和主要的保障條文相符。
法院的思考方式是先從明顯只能適用於生理性別的條文出發,繼而審閲容許單一性别的例外條款,推論法例的原意是指生理性別。法院繼而審議法例的主要保障條文,認為這些條文若包括確認性別,這將會出現很多矛盾和混亂的情況。最後法院再審視條例的保障,認為即使將性別局限於生理性別,跨性別人士仍有足夠的保障。這種推論方法是常見的,也具一定的説服力,但卻不是唯一的推論方法。
另一種思維方法是以《性別確認法》的清晰條文為出發點,該條例開宗明義指出性別一經確認後,法律上便是以確認性別為準,《平等法》中那些明顯保障生理性別的條文屬例內情況。至於《平等法》的主要保障條文,法院認為採納確認性別所引發的矛盾,其實部分源於持有和沒持有確認證書的跨性別人士之間引致的矛盾,而非生理性別和確認性別之間的矛盾。
例如法院指按照確認性別,持有確認證書的確認男性(生理女性),不能獲得分娩服務,但不持有確認證書的男士則仍被視為女性,可接受該分娩服務,這明顯不會是立法意圖,但若按照生理性別,這種情況便不會出現。法院這個例子適用於涉及生理 (如分娩) 的條文,但若不是涉及生理的條文,同樣的情況仍會出現。例如入住專為女性而設的院舍,若按生理性別,則外貌生活完全是男士的確認男性仍然可以入住女子宿舍,和其他女士一起住宿,使用同一洗手間和沐浴設施。
或以本案為例,原告擔心若採納確認性別,可以令公共機構的董事局成員為全男性 (生理男性和確認女性),但亦可以是全女性 (生理女性和確認男性);但若採納生理性別,則可以出現所有議員是全男性裝扮(生理男性和確認男性)或全女性裝扮(生理女性和確認女性),但卻符合法例男女成員各佔一半的要求。 換言之,不論採取統一的生理性別或確認性別作解釋,混亂和不合常理的情況根本無法避免,故不能以此作為支持性別需理解為生理性別的理據。
較恰當的方法是同時考慮生理性別和跨性別人士所面對的困難,在不同境況下採取彈性的解釋。可惜,法院並沒有從人權的角度出發,沒有詳細考慮將性別限於生理性別會對跨性別人士造成的困擾,從而找出一個可以照顧雙方的解釋。
非男即女變成非男非女
法院將性別局限於生理性別,令性別返回非男即女的兩極狀態,這會令跨性別人士處於非男非女的尷尬位置。這在法例內容許一些專為單一性別提供的服務或處所方面便特別明顯,跨性別人士被排除於同性和異性之間,例如向受家暴或性侵犯的女性提供庇護的場所,可以只局限於生理女性,但確認女性同樣可以是家暴的受害人,卻因這裁決而被排除於服務之外,但又沒有相關的其他服務。又例如確認女性(生理男性)既不能囚於女子監獄,但囚於男子監獄亦絕不適宜,將性別局限於生理性別,將令跨性別人士處於孤立無援的境況。
當然,這不單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涉及政策和資源的問題。跨性別的出現,打破傳統男女的二分法,但社會上仍有不少服務或措施是以男女作分野,未能處理跨性別人士的需要,不論法律上採取單一的生理性別還是彈性處理跨性別,最終仍需要訂立相關政策來支持和處理這些問題。有些問題較易解決,例如設置單一性別的洗手間,或在公共設施如泳池或健身室提供獨立的不分性別的更衣室等;有些則較難處理,例如監獄、學校等,即使可以提供專供跨性別人士的設施,但將性別分為男性、女性和跨性別這種隔離的處理方法,又是否有利於建設一個包容多元的社會?
如何確認性別
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是如何界定性別。在這宗案件,蘇格蘭政府規定公營機構的董事必須有一半為女性,女性團體擔心這些席位會給確認女性所霸佔,但背後的問題是這些女性團體並不認為確認女性是女性,這可能是出於偏見或宗教理由,但亦可能是出於對人身安全的憂慮,如女護士不願與確認女性醫生用同一休息室、或女囚犯不願與確認女性囚犯處於同一監倉內;確認性別的女性警察,可以向女性還是男性市民進行搜身?[5] 這些憂慮亦可以是基於行業特質,例如在需要體能的運動項目,一般確認女性的體能會優勝於生理女性,同場比賽便可能不公平!這些憂慮不無道理,亦需要不同的處理方法,不能以一刀切的方法來解決。
至於如何確認性別,有些地區如香港仍然以手術後的性別為依據,歐洲人權法院則認這樣的硬性規定有違對個人私隱的保障;[6]有些國家如英國則要求跨性別人士須通過一項確認程序才能獲發確認性別證書。申請人須提供兩名醫生證明,診斷申請人患有性別錯配 (sexual dysphoria),申請人並須提供證據,證明申請人在提出申請前兩年內,經已以欲獲確認的性別生活,包括荷爾蒙注射,官方書信或銀行文件的性別稱謂等。[7]獲確認性別並非強制,以致有些符合條件的人士選擇不申領確認證書,這是法院指出引起混亂的重要原因,持有確認女性證書的男性,法律上是女性:同樣一名男性,因為沒持有確認證書,法律上仍是男性,但兩者同樣以女性容貌打扮生活,同樣具男性的生殖器。對不少服務的提供者而言,亦確實難以分辨雄雌!
即使英國的確認程序需要兩年的觀察,一些較保守的人士仍認為這程序不夠嚴謹,但一些較前衞的人士則認爲這程序太過苛刻,有些人甚至提議以個人宣誓確認性別,但這會令性別變得毫無意義。不管以什麼程序來確認性別,相信都會是兩邊不討好的妥協,當生理性別和確認性別的差距越大,或確認性別程序愈簡化,社會的普遍應受亦會愈困難。
對香港可有什麼影響?
首先,英國最高法院強調,它的判詞並非針對任何政策,而只是一項技術性的法律詮釋。判詞強調一些如涉及懷孕或餵哺母乳的條文只能適用於生理女性,而在同一部法例內,對性別的界定應該是統一的。換言之,法院這個詮釋只局限於英國的《平等法》,不一定適用於其他法例。其次,法院亦強調,這判決並不影響跨性別人士不受歧視的保障。例如一位被確認為女性的人士,因被視為女性而在工作上受到歧視,他仍然受到法律上不受歧視的保障,不會因為他生理上仍被視為男性而有所分別。
香港沒有像英國的《平等法》這種綜合性的平等條例,對平等的保障散布於不同的法例如《人權法案》和《基本法》。較接近的是《性別歧視條例》,雖然香港的主流認知是《性別歧視條例》並不包含性傾向歧視,但終審法院已有一系列的判例確認性傾向歧視違反《人權法案》和《基本法》中對平等的保障,這方面的判決相信不會受英國這判例所影響。
另一項是對婚姻的詮釋。按現時的法例,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結合,早前在W案中,[8]終審法院已裁定,完成變性手術後的性別,才是確定是否符合一男一女的結合的性別,並明確否定以出生時的生理性別作為能否締結婚姻的準則,因為生兒育女並非締結婚姻的必然要素,而且在過往50年,社會對婚姻的觀念和醫學上對性別的界定均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判決建基於社會的變遷,相信亦不會受英國判例的影響。然而,法院在W案中給予政府一年的寛限期,以便政府立法處理相關做法律問題。一年寛限期結束時,立法會仍無法達成共識,處理變性人士結婚所引致的相關問題,當中一個難題正是各方無法就如何確定性別達成共識!
先前終審法院在岑子杰案中認為,[9]《基本法》中的婚姻是指一男一女的結合,並不包括同性婚姻。至於《基本法》是否可以跟隨社會的轉變而作相應的解釋,由於岑子杰一方在上訴時放棄這論點,終審法院並無就這一點作出任何判決。終審法院同時裁定,法律上沒有機制承認同性伴侶,這有違對私隱的保障,勒令政府須進行相關立法,但給予政府兩年時間立法。兩年的期限將於2025年10月26日結束,但政府在這方面的立法工作似乎相當緩慢,在2025年7月初,政府才向立法會提交討論文件,勾劃出政府的立法方向。[10]
政府將在保障現有的異性婚姻制度和傳統價值的前提下,立法確立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的關係獲得法律承認和保障。政府將設立登記機制,讓符合條件的同性伴侶進行登記,這些條件包括申請雙方已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有效註冊成為同性伴侶,以及雙方的性別相同。前者等如政府只是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若同性伴侶因財政或其他原因未能前往海外註冊,則他們的關係仍然無法獲得確認,這並未足夠符合法院的要求,亦可能仍然有違平等的保障。
建議所提供的保障亦相當有限,甚至沒有提及過往法院在房屋、遺產等方面的平權判決,雖然政府指將會繼續執行這些判決,但若建議成為法律後,這些判決會否只是適用於已登記的同性伴侶?這一點仍有待澄清。至於雙方是同性的要求,由於這立法主要針對同性伴侶,這要求無可厚非,但在決定誰人可以締結同性伴侶關係時,如何界定性別,將會是難以避免的問題。
註:
[1] For Women Scotland Ltd v The Scottish Ministers [2025] UKSC 16 (“Judgment”)
[2] “Isla Bryson: What is the transgender prisoners row all about?”, BBC, 28 Feb 2023: https://www.bbc.co.uk/news/uk-scotland-63823420
[3] “Changing room trans row nurse ‘felt intimidated”, BBC, 3 Feb 2025: https://www.bbc.co.uk/news/articles/cy8p41z972vo
[4] 見判詞,第 190-197段。.
[5] 例如在 Chief Constable of the West Yorkshire Police v A (No 2) [2004] UKHL 21,申請人成功提出司法覆核,推翻警隊以申請人不能對男性或女性進行搜身工作而拒絕聘用她的決定。
[6] AP, Garçon and Nicot v France, Applications Nos 79885/12, 52471/13 and 52596/13, Judgment of 6 April 2017.
[7] 例如在 AB v Gender Recognition Panel [2024] EWHC1456 (Fam),申請人既做了人工乳房,但又要保存男性生殖器官,確認委員會認為沒有足夠證據證明他以女性身分生活兩年,但申請人成功申請司法覆核,法院認為委員會應整體考慮申請人的生活方式而非只限於醫樂報告。
[8] W v Registrar of Marriage (2013) 16 HKCFAR 112.
[9] Sham Tsz Kit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2023] HKCFA 28.
[10]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panels/ca/papers/ca20250703cb2-1350-1-c.pdf.
▌[海外隨筆]作者簡介
陳文敏,前香港大學公法講座教授,2021年退休後,旅居英國,並出任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名譽教授(Honorary Profes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