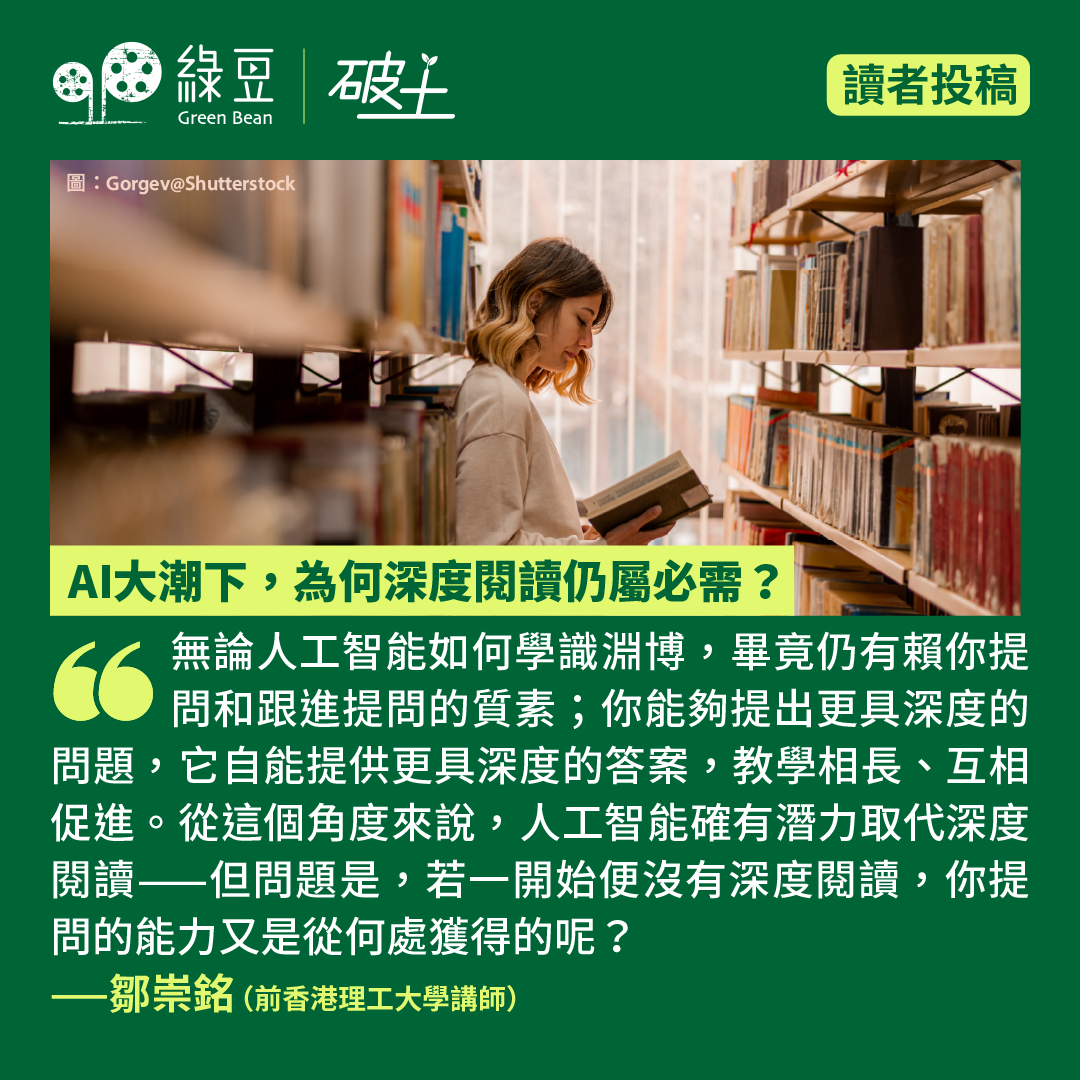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中的幸福與友誼(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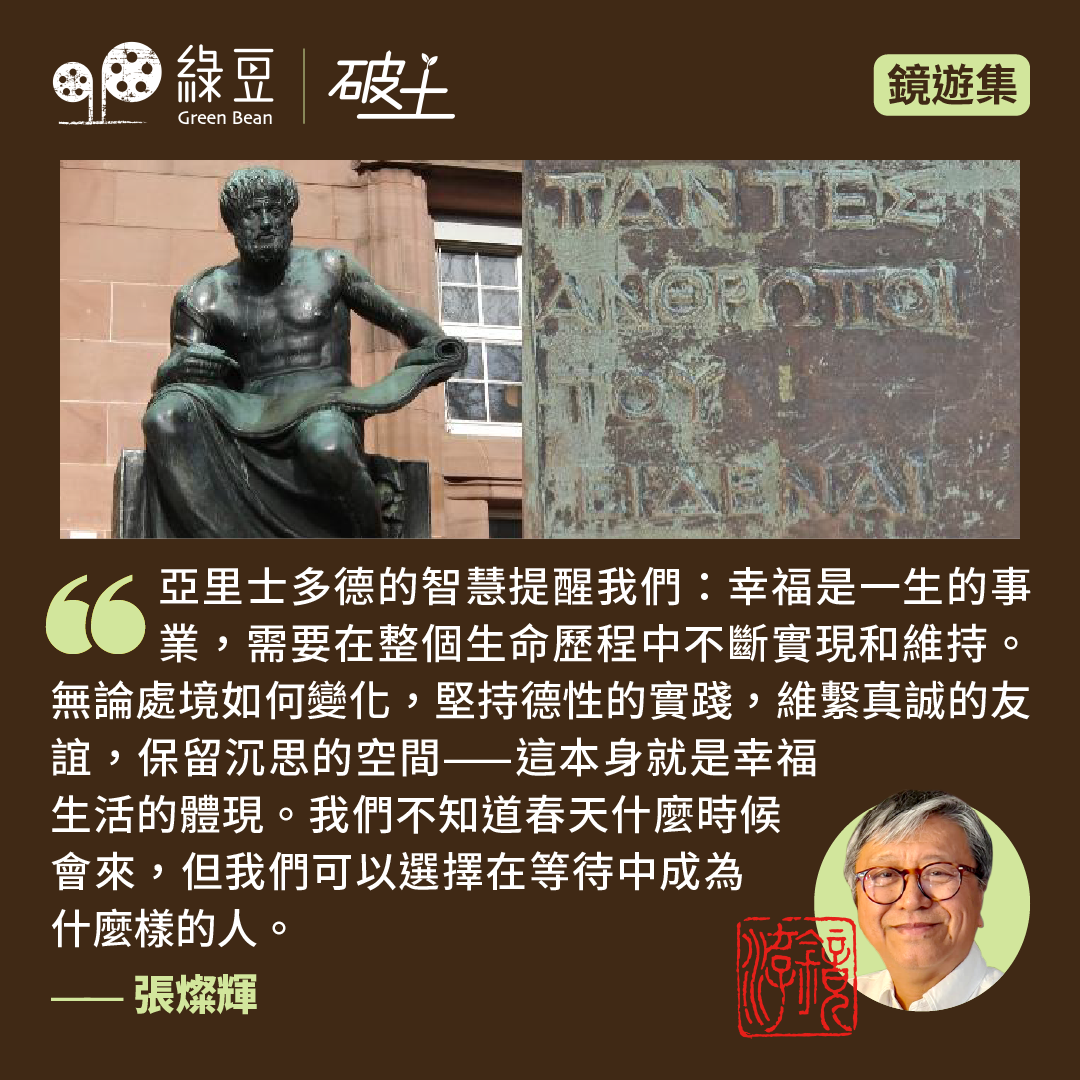
幸福與友誼的內在關聯
在理解了幸福和友誼各自的本質之後,我們需要探討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繫。亞里士多德明確提出了一個問題:幸福的人是否需要朋友?這個問題的答案對於理解幸福的完整圖景至關重要。
有人認為,既然幸福的人是自足的,他們就不需要朋友,因為他們已經擁有了善的事物。歐里庇得斯(Euripides)的詩句也表達了這種觀點:「當命運對我們微笑時,何需朋友?」然而,亞里士多德認為這個結論是荒謬的:「如果我們將所有善歸於幸福的人,卻不給他朋友,這看起來很奇怪,因為朋友被認為是最大的外在善。」
「將完全幸福的人表現為孤獨者是荒謬的,因為沒有人會選擇獨自擁有世界上所有的善,因為人是社會性動物,天性就是要與他人一起生活。」這個論證揭示了自足概念的微妙之處。自足並不意味著完全的獨立或孤立。相反,它包括了與父母、子女、朋友和同胞公民的關係,因為人天性上是社會性動物(zoon politikon)。
亞里士多德進一步論證:「善的朋友本質上對善人來說是可欲的。因為自然之善對善人來說本身是善和愉快的。」、「既然善人對朋友的感覺就像對自己的感覺一樣,因為朋友是另一個自己——如果所有這些都是真的,那麼對一個人來說,朋友的存在就像自己的存在一樣可欲,或幾乎一樣可欲。」
使自己的存在可欲的是對自己善的意識,而這種意識本身是愉快的。因此,一個人應該同樣意識到朋友的存在。亞里士多德指出:「這可以通過共同生活和交談、分享想法來實現——因為這似乎是共同生活在人類意義上的含義,而不是像牛一樣在同一片田野裡吃草。」這裡亞里士多德特別強調,人的共同生活不同於動物。人的共同生活涉及思想和言語的交流,涉及意義和價值的分享。
「如果對真正幸福的人來說,存在本身是可欲的,因為它本質上是善和愉快的;如果朋友的存在也幾乎同樣可欲;那麼朋友也必須是可欲的東西。但對他來說可欲的東西他必須擁有,否則在這方面他就會有所欠缺。因此,要幸福的人將需要有德性的朋友。」
「朋友是另一個自己」
「朋友是另一個自己」這個命題是亞里士多德友誼理論的核心,也是理解友誼與幸福之間關聯的關鍵。這個命題有多層含義。在認知層面,我們對自己往往是盲目的,對他人卻能看得清楚;朋友提供了一面鏡子,使我們能夠以比較客觀的方式觀察自己的品格和行為。在情感層面,善人希望朋友好,就像希望自己好一樣,並且是為了朋友本身而非為了任何外在的原因;朋友的幸福或不幸,會像自己的一樣牽動我們。在存在層面,正如我們希望自己存在和被保存,我們也希望朋友存在和被保存 —— 不是因為朋友對我們有用或令我們愉快,而是因為朋友的存在本身就是善。
亞里士多德特別強調共同生活對於友誼和幸福的重要性:「朋友之間最可欲的莫過於共同生活。友誼是一種夥伴關係,一個人對朋友的態度就像對自己一樣。既然對自己存在的意識是可欲的,對朋友存在的意識也必定同樣可欲。而這種意識在共同生活中得以實現,所以朋友自然渴望共同生活。」
這個觀察具有深刻的倫理意義。共同生活不是中性的,它具有塑造性和影響性。亞里士多德指出:「惡人的友誼會產生惡劣的影響,因為由於不穩定,他們參與惡劣的追求,並且通過彼此的影響變得惡劣。但善人的友誼是善的,並且通過他們的交往而增長。他們似乎甚至通過操練友誼並相互糾正而變得更好,因為他們從彼此那裡獲得他們所欣賞的特質的印記。因此有這樣的諺語:『從善人那裡得到善』。」
這揭示了友誼在道德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德性不僅僅是個人的成就,也是社會的產物。我們通過與他人,特別是與善的朋友的交往,來學習、實踐和完善德性。友誼提供了一個道德共同體,在其中德性不僅被傳授,更被共同實踐和體驗。
沉思生活與完美幸福
《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十卷提出了一個令許多讀者感到驚訝的論點:最高的幸福不在於政治生活或實踐德性的活動,而在於沉思(theoria)。這個結論表面上似乎與前面關於友誼和共同生活的討論有所張力,但仔細審視之下,它實際上是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邏輯頂點。
亞里士多德的論證從他在第一卷建立的原則出發:「如果幸福是依照德性的活動,那它應該是依照最高德性的活動;而這將是我們最好部分的德性。無論這最好的部分是理智還是別的什麼被認為自然地統治和引導我們、並且認識高尚和神聖事物的東西——無論它本身就是神聖的,還是我們身上最神聖的部分——這部分依照其固有德性的活動,就是完美的幸福。」這段話的關鍵在於,亞里士多德將目光從實踐德性轉向了純粹的理性活動——也就是沉思。
沉思之所以是最高的活動,亞里士多德列舉了多重理由。首先是其對象的卓越:「沉思是最高形式的活動,因為理智是我們身上最高的東西,而理智所處理的對象是可知事物中最高的。」沉思的對象不是變動不居的人間事務,而是永恆不變的真理——數學的規律、自然的秩序、存在的本質。這些對象本身比人類的行為和情感更為高貴。
其次是沉思的持續性:「沉思可以比任何其他活動更持續地進行。」政治活動、戰爭、慷慨施捨,這些實踐德性的表現都需要特定的情境和條件,不能持續不斷。但沉思不同——一個人可以獨自一人、在任何時候進行思考,只要他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
第三是沉思的愉悅:「我們認為幸福必須包含快樂的成分。現在,依照智慧的活動被公認為是德性活動中最令人愉悅的。哲學的追求似乎具有驚人的純粹和穩定的快樂,而擁有知識的人比尋求知識的人更能享受這種快樂,這是合理的。」沉思的快樂不像感官快樂那樣容易厭倦或帶來後悔,它是一種純粹的、自我增強的愉悅。
第四是沉思的自足性:「沉思被認為具有最高程度的自足性。誠然,智慧的人和正義的人以及其他有德性的人都需要生活必需品;但當這些得到充分供應之後,正義的人還需要他人來對其施行正義,節制的人、勇敢的人等等也是如此。然而,智慧的人即使獨處也能沉思,而且越智慧越能如此。」
第五是沉思純粹為其自身而被愛:「唯獨這種活動似乎是純粹為其本身而被愛的,因為它除了沉思本身之外不產生任何結果。」政治活動追求權力和榮譽,戰爭追求和平,商業追求利潤——這些都是為了某種外在的目的。但沉思不同,思考本身就是目的,理解本身就是報酬。
最後,亞里士多德將沉思與閒暇聯繫起來:「幸福被認為存在於閒暇之中,因為我們忙碌是為了能夠閒暇,我們打仗是為了能夠和平。」沉思是閒暇的活動,它不是為了其他目的而進行,而是在所有外在目標都實現之後,人仍然選擇做的事。
沉思生活與神聖生命
這個論證的高潮是將沉思生活與神聖生命聯繫起來:「這樣的生活將超越純粹人性的層次,因為一個人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其內在神聖成分而過這種生活的。這神聖成分的活動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我們複合本性的活動,其生活也在同等程度上超越人的普通生活。」亞里士多德在這裡觸及了人的存在的根本問題:人究竟是什麼?人只是有理性的動物,還是在某種意義上分有神性?
他的回答是大膽的:「我們不應該聽從那些勸告我們作為人只應思考人的事務、作為凡人只應思考凡間事物的人。相反,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應該追求不朽,盡一切努力依照我們身上最高的成分而生活。因為即使它在體積上很小,但在力量和價值上卻遠遠超過所有其他部分。」
那麼,神是怎樣生活的呢?亞里士多德在第十卷第八章給出了一個著名的論證:「完美的幸福是某種沉思活動,這一點也可以從以下考慮看出。我們設想諸神是至福至樂的。但我們應該把什麼樣的行為歸於他們呢?正義的行為?但想像他們訂立契約、歸還存款之類的事情,豈不顯得可笑?勇敢的行為?但設想他們忍受恐懼、面對危險,豈不荒唐?慷慨的行為?但他們會給誰?再說,設想他們擁有錢幣或類似的東西,豈不奇怪?節制的行為?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什麼?說他們沒有卑劣的慾望,豈不是貶低他們?」
亞里士多德的結論是:「如果我們逐一審視所有德性行為,它們對於神來說都顯得瑣碎而不相稱。然而,所有人都認為神是活著的,因此是在活動的——因為我們不能設想他們像恩底彌翁那樣永遠沉睡。但如果從一個活著的存在那裡去除行動,更不用說創造,還剩下什麼呢?除了沉思,還能有什麼?」
因此,「神的活動,在福祉上超越一切,是沉思的活動;在人類活動中,與之最為相近的也是最具幸福特質的。」人在沉思中最接近神,也最接近幸福。「諸神的整個生命都是至福的,人的生命在其包含某種這類活動的相似物的程度上也是至福的;但其他動物沒有幸福可言,因為它們完全不分享沉思。」
但這並不意味著實踐德性毫無價值。亞里士多德明確指出:「依照其他德性的生活是第二等的幸福,因為這些活動是人的活動。」正義、勇敢、慷慨、節制——這些德性處理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複合體」的活動,需要身體、情感和外在條件的配合。它們是好的、是必要的、是構成人類生活的重要部分。但它們不是最高的。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層次結構。第一層是享樂的生活,以快樂為目標,這是最低的;第二層是政治的生活,以榮譽和德性為目標,這是人作為社會存在的恰當生活方式;第三層是沉思的生活,以真理和智慧為目標,這是人分有神性的最高實現。一個完整的人生可能需要同時包含這三個層次,但最高的幸福仍然在於沉思。
但這是否意味著亞里士多德在前面討論友誼時說的話都不算數了呢?並非如此。亞里士多德從未否認人需要朋友、需要共同生活、需要在社會中實踐德性。他只是指出,在所有這些善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善——沉思。「當然,作為人,沉思者也需要外在的繁榮,因為我們的本性對於沉思來說並不自足,身體需要健康,需要食物和其他照料。然而,不必認為幸福的人需要很多或很大的外在善,即使沒有外在善就不能達到至福。」
沉思生活不是逃避人間,而是在充分履行人的社會責任之後,將目光投向更高的事物。一個人需要朋友,需要共同體,需要實踐德性——但這一切都是為了創造條件,使沉思成為可能。沉思是閒暇的活動,而閒暇需要和平、富足和友誼來保障。
亞里士多德倫理學與生命意義的追尋
讀完《尼各馬可倫理學》,我們不禁要問:亞里士多德究竟想告訴我們什麼?這部著作的意義,不只在於它是西方倫理學的奠基之作,更在於它直面了人類最根本的問題:人應該如何生活?生命的意義何在?
亞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多層次的。在最基本的層面上,人應該追求幸福。但幸福不是感官的滿足,不是外在的榮譽,甚至不只是德性的狀態。幸福是靈魂依照德性的活動——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持續的實踐,一種在整個生命歷程中不斷實現人的本性的努力。這個定義排除了把幸福當作某種可以獲取和擁有的東西的想法。你不能「買到」幸福,不能「贏得」幸福,只能「活出」幸福。
在社會的層面上,人需要朋友。朋友不是可有可無的裝飾,而是幸福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通過朋友,我們認識自己;通過朋友,我們實踐德性;通過朋友,我們體驗到另一個自我的存在。善人的友誼是基於德性的,因此是持久的、穩定的、令人愉悅的。這種友誼超越了利益和快樂的計算,達到了人與人之間最真誠的連結。
在最高的層面上,人應該沉思。沉思不是逃避現實,而是面向永恆。在沉思中,人超越了自己作為「複合體」的有限性,觸及到存在的根本。沉思是人分有神性的方式,是有限存在追求無限的途徑。哲學,作為「愛智慧」,就是這種追求的體現。
這三個層面並不矛盾,而是相互支撐的。一個人需要適度的外在善——健康、財富、社會地位——作為德性活動的條件。他需要朋友作為共同實踐德性的夥伴。而最終,他需要閒暇來從事沉思,思考那些超越日常生活的問題。這是一個整體的生命圖景,其中每個部分都有其位置和功能。
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因此是一種目的論的倫理學。萬物都有其目的,人的目的是實現其本性;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因此人的目的是充分發揮理性;理性的最高形式是沉思,沉思的對象是永恆不變的真理;通過沉思,人不僅實現了自己的本性,也與神聖的秩序建立了聯繫。
但這種目的論不是機械的或宿命的。亞里士多德強調德性是習慣的結果,需要通過實踐來培養。一個人不是天生就有德性的,而是通過反覆做正義的事而變得正義,通過反覆做勇敢的事而變得勇敢。同樣,一個人不是天生就會沉思的,而是通過長期的學習和思考才培養出沉思的能力。幸福不是給定的,而是成就的。
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也是一種中庸的倫理學。德性是兩種極端之間的中道——勇敢在魯莽和懦弱之間,慷慨在揮霍和吝嗇之間,節制在放縱和禁慾之間。這種中庸不是數學上的中點,而是「對我們而言的中道」——因人、因時、因地而異。實踐智慧(phronesis)就是判斷在具體情境中什麼是中道的能力。
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最終是一種關於人的整全性的學說。它不把人簡化為純粹的理性存在,也不把人簡化為純粹的感性存在。人是複合體,既有靈魂也有身體,既是個體也是社會成員,既是凡人也分有神性。好的生活必須照顧到人的所有這些面向。
這對於當代世界有什麼意義?我們生活在一個碎片化的時代。工作與生活分離,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分離,理性與情感分離,個人與社群分離。亞里士多德提醒我們,好的生活是整全的生活。它不是在不同角色之間來回切換,而是將所有這些角色整合在一個有意義的整體之中。
幸福不是主觀的感受,而是客觀的成就。現代文化往往把幸福等同於「感覺良好」,認為每個人對幸福的定義都是同樣有效的。亞里士多德不同意。他認為有些生活方式確實比其他的更好,更能實現人的本性。這不是傲慢,而是對人的尊嚴的肯定——人不應該滿足於較低層次的生活,而應該追求更高的卓越。
德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培養的。現代社會往往假設道德是個人選擇的問題,政府和社會不應該干預。但好的品格需要好的教育和好的法律。「如果不是在正確的法律下從小培養,很難從年輕時就獲得正確的德性訓練。」社會對於培養有德性的公民負有責任。
人需要朋友。在這個社交媒體盛行卻人際關係疏離的時代,這個洞見格外切中時弊。真正的友誼不是基於利益或消遣,而是基於共同的價值和相互的尊重。這樣的友誼需要時間來培養,需要共同生活來維持。沒有朋友的人,即使擁有世界上所有的財富,也不能稱為幸福。
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不是一套可以機械應用的規則,而是一種生活的智慧。它邀請我們思考:我是什麼樣的人?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生活才是值得過的?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正是在追問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我們開始過上真正屬於人的生活。
對當前香港人的啟示
亞里士多德的幸福與友誼理論,對於當前處境中的香港人 —— 無論離散海外還是留守本土—— 均具有特殊的意義。
香港人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局。熟悉的制度在改變,昔日的生活方式難以為繼,許多人被迫在去留之間抉擇。在這樣的處境中,亞里士多德提醒我們:真正的幸福不在於外在條件的穩定,而在於靈魂依照德性的活動。財富可以失去,地位可以改變,甚至家園也可能離開,但一個人實踐誠實、勇氣、正義、智慧的能力,卻是任何外力都無法剝奪的。以德性為本的幸福觀,為動盪時代中的香港人提供了一個內在的錨點。這不是說外在條件不重要,而是說在外在條件無法控制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選擇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亞里士多德區分三種友誼的理論,在離散的現實中顯得格外真切。那些僅僅基於利益或消遣的關係,往往經不起距離和時間的考驗。生意夥伴分道揚鑣,酒肉朋友各奔東西,這些都是可以預見的。唯有基於共同價值和德性的友誼——朋友為了對方本身而關心對方,而非為了任何偶然的好處——才能跨越地理的阻隔而持久。當舊日的社交網絡因遷徙而瓦解,真正重要的是辨識和珍惜那些基於德性的友誼,而非徒然哀悼那些本就脆弱的關係。
「朋友是另一個自己」這個命題,對於身份認同受到衝擊的香港人尤為重要。在陌生的環境中,在價值觀受到質疑的時刻,朋友成為我們確認自我的鏡子。透過與志同道合者的交往,我們記得自己是誰,記得自己珍視什麼。這種友誼不僅是情感的慰藉,更是存在的確認。當周圍的世界都在變,當連「香港人」這個身份都變得模糊,朋友的存在提醒我們:我們不是孤立的個體,我們屬於一個價值共同體。
亞里士多德強調朋友需要共同生活,分享活動和追求。對於散居各地的香港人,這意味著必須有意識地創造共同實踐的空間——讀書會、文化活動、社區參與、網絡連結。共同生活不必然要求物理上的接近,但必須有實質的共同行動。善人的友誼通過共同實踐而增長,朋友從彼此身上獲得他們所欣賞的品質。在艱難時勢中,這種相互砥礪尤為珍貴。不是在一起喝茶聊天就叫共同生活,而是一起做有意義的事、一起追求共同的價值。
一隻燕子不能帶來春天,一時的困境也不能否定一生的意義。亞里士多德的智慧提醒我們:幸福是一生的事業,需要在整個生命歷程中不斷實現和維持。無論處境如何變化,堅持德性的實踐,維繫真誠的友誼,保留沉思的空間——這本身就是幸福生活的體現。我們不知道春天什麼時候會來,但我們可以選擇在等待中成為什麼樣的人。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