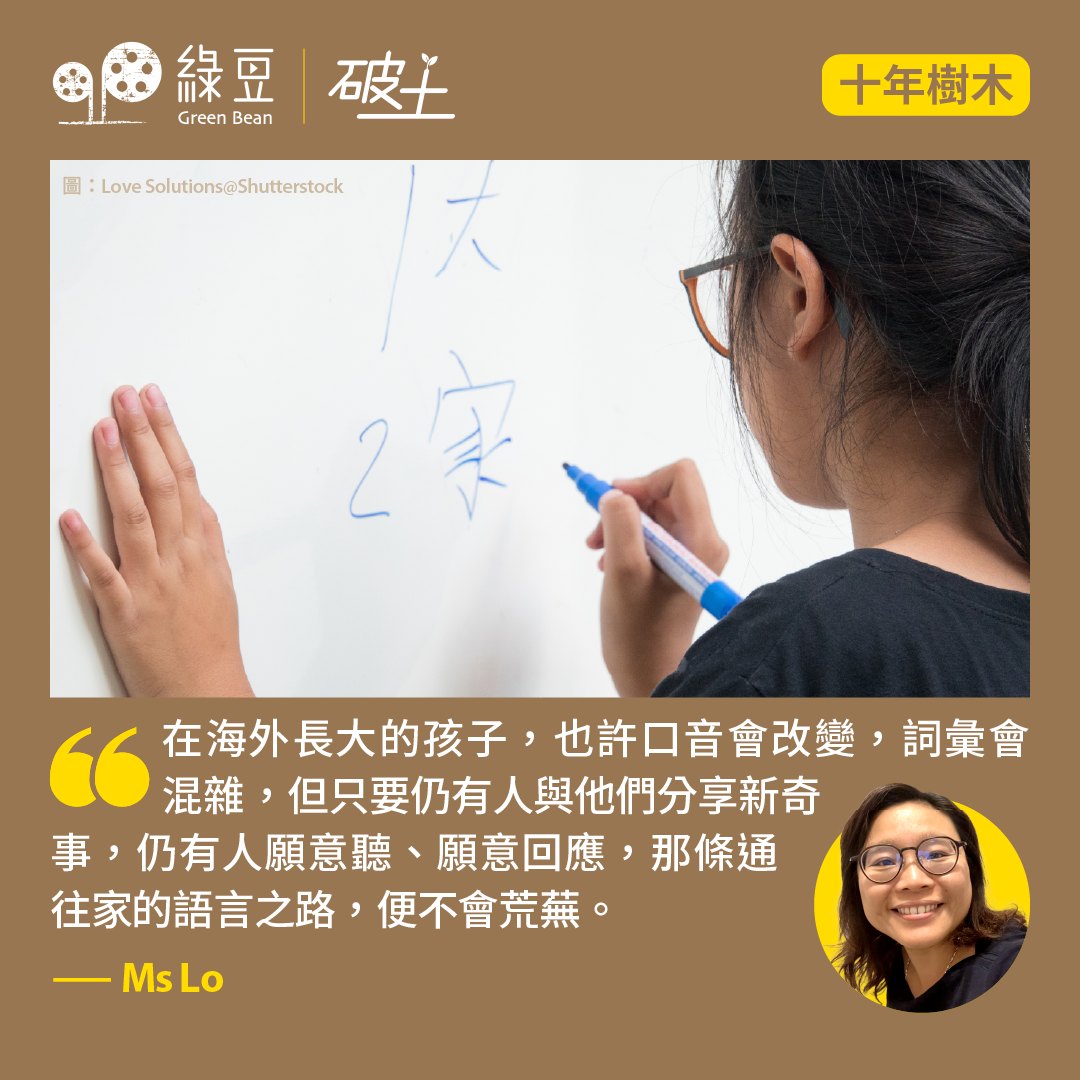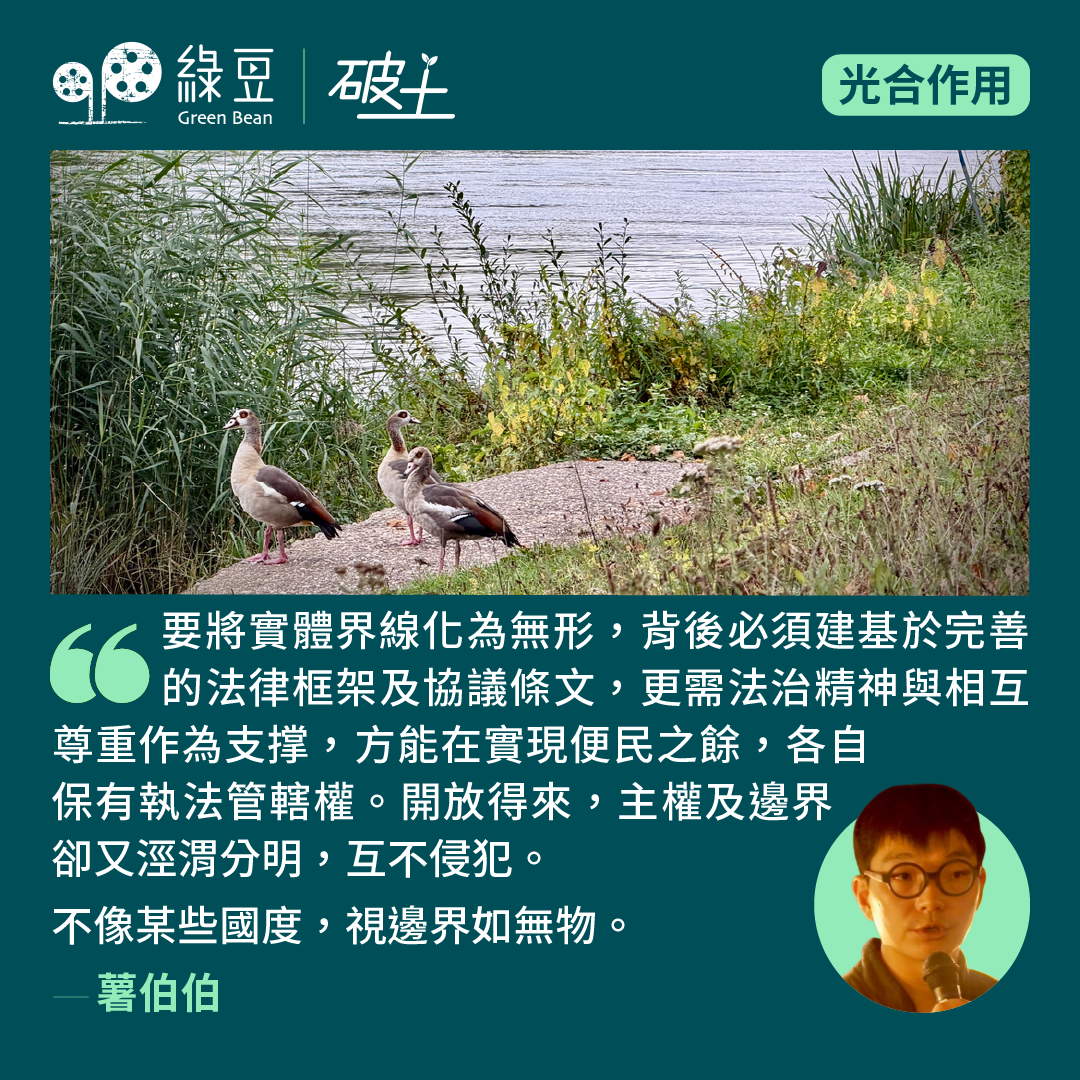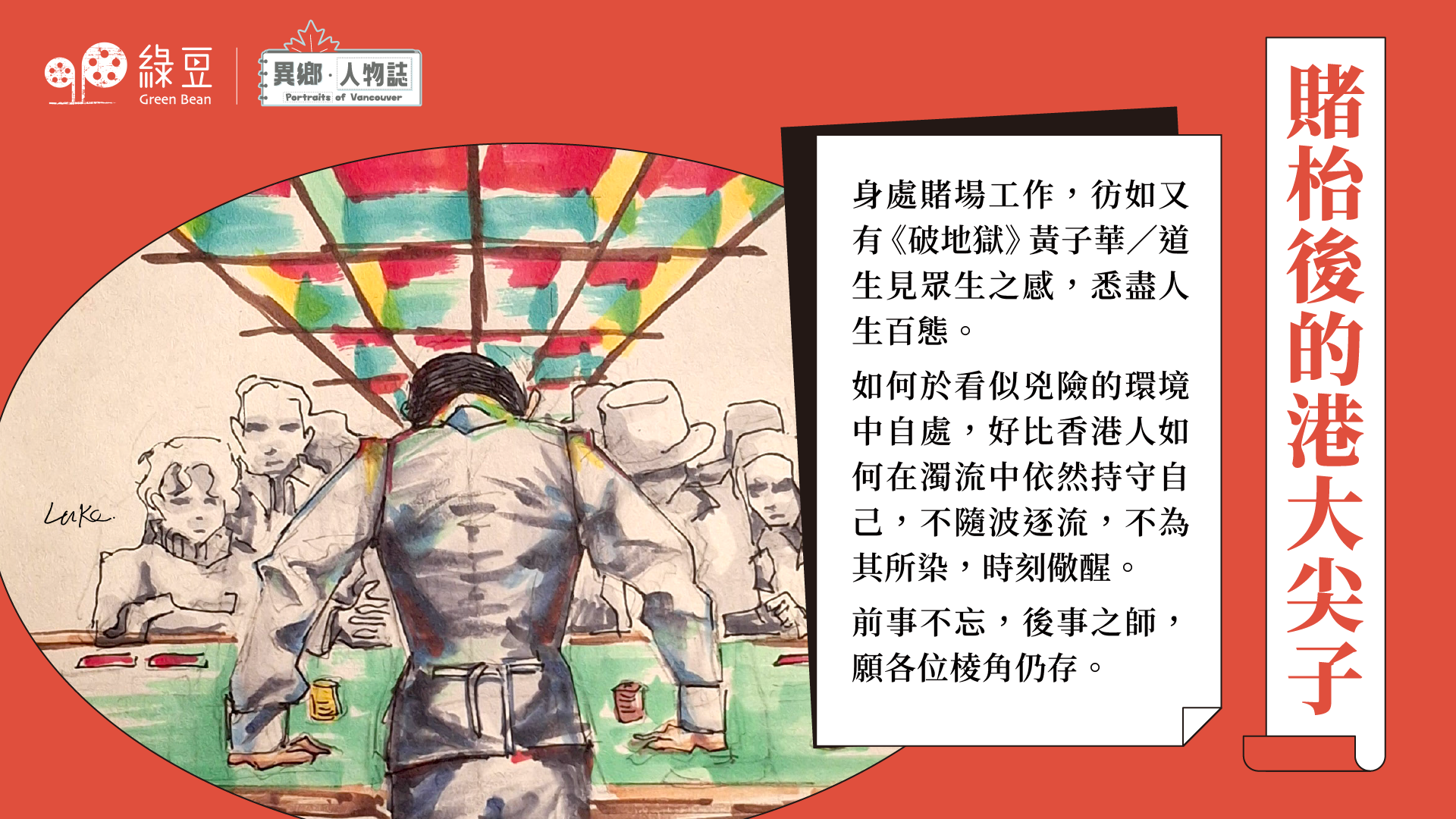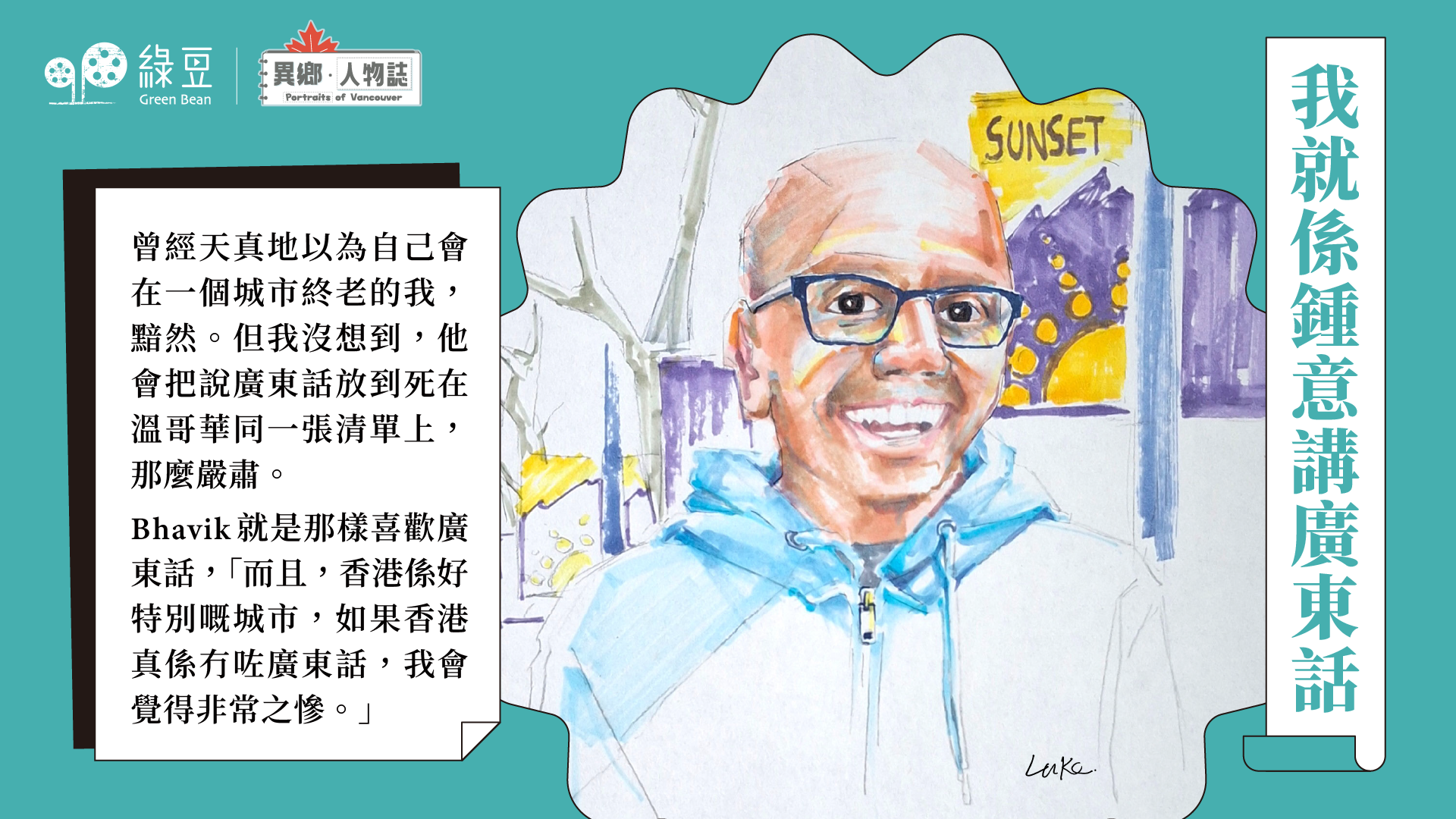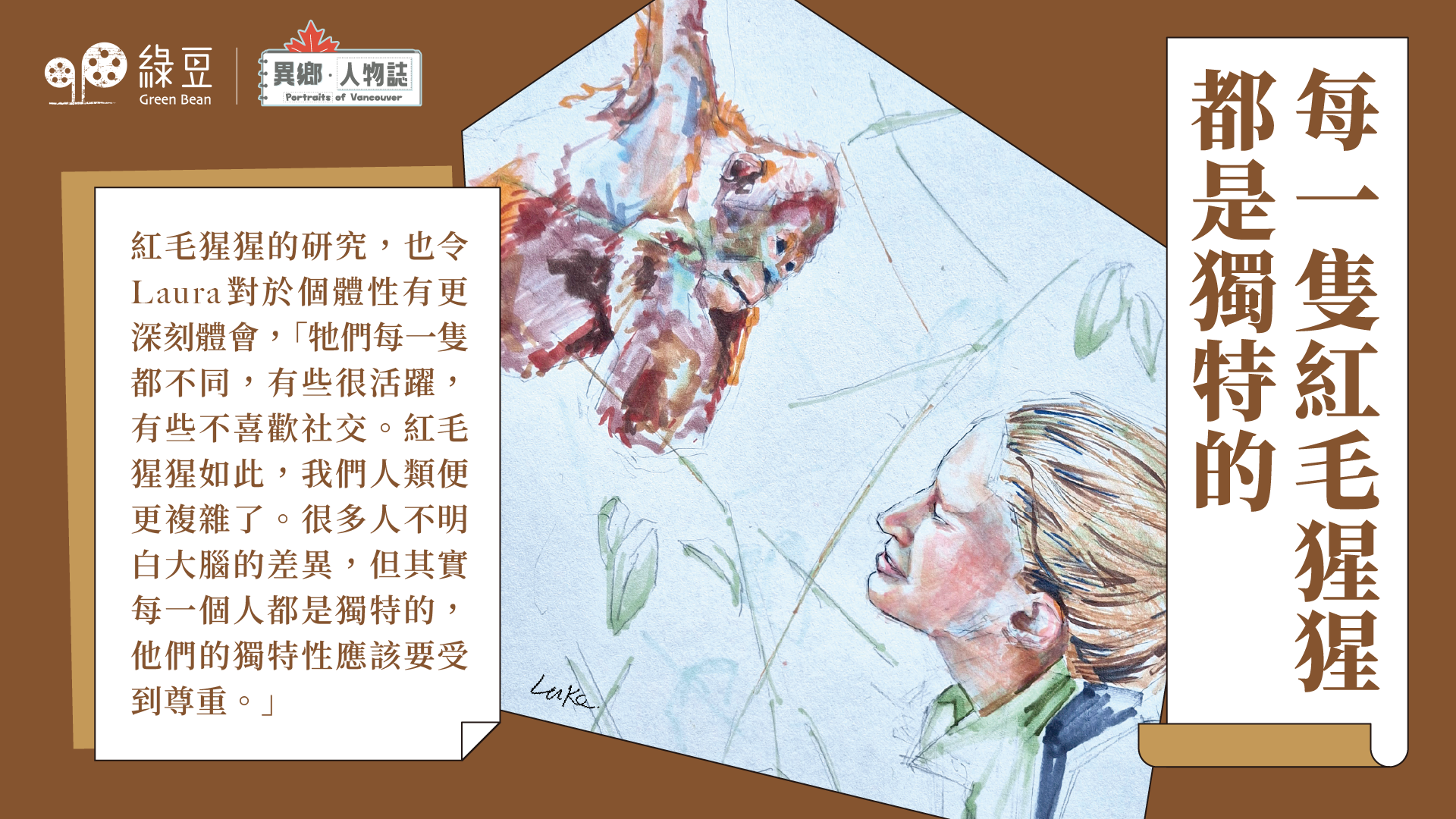二手店的快樂與哀愁


2025 年我有一個小小的個人創舉:傻傻弄不清 nickels, dimes, 和 quarters 的我,硬着頭皮當上慈善二手店的義務收銀員,花了很大力氣,收下不少挫敗之後,竟然開始有點期待每週一次的當值——天天來逛幾回的笑瞇瞇老公公、總是給準確零錢說 “I just do it for you” 的鬼馬伯伯、每次提起偷衣賊都恨得牙癢癢的義工姨姨⋯⋯
這回側寫在二手店遇到的人,也是這個社會某個角落的小小群像。

圖:二手店一隅
早上回店,門外已經堆滿舊物。雖然張貼了通告,請大家不要在關店後把舊物放門外,但那樣做的人還真不少。我和義工朋友交換完無奈眼神,便捲起衣袖,把它們逐一搬進店子。溫哥華的冬天雨綿綿,擱在戶外一整晚的雜物,已被雨淋得一塌糊塗兼重甸甸,大部分只能直入垃圾桶。
這店由義工全盤運作,除了幾個年輕女孩,成員多年過六十,最年長的足八十歲——那位滿頭銀髮的婆婆有次捧來一個烤得香噴噴的自家蛋糕,與大家分享,笑容跟蛋糕同樣甜美。
義工以白人女性為多,地牢另有一位專門維修傢俬和測試電器的男士。義工中有家庭主婦,以及不同專業的退休人士,像教師和警察等。訓練我當收銀員的義工從前當護士,上班頭兩天,我沒注意客人的信用卡扣款失敗,害店子損失,懊惱得不行,她立即說 “It happens”,然後分享自己犯過的錯。加拿大的職場文化對過錯有時包容得過頭,教人又愛又恨。但那一刻我確實被暖到。
開店了,進來的第一位是熟客——我在心裡叫他「笑瞇瞇公公」。笑瞇瞇公公小個子,背有點佝,冬天愛戴呢絨貝雷帽,話不多,總是掛着率真笑容。他是華人,十數年前隨家人從北京搬來,至今仍沒法說英文,一律用身體語言跟店裡的義工溝通。所以當他發現新來的我竟會說國語,樂透了,從此每次進來都先跟我揮手,朗朗地招呼:「你在啊!」彷彿他鄉遇故知。
「笑瞇瞇公公」報到!
笑瞇瞇公公一日來幾次,每次都挑中一兩件令人意想不到的東西,有時是小女孩氣質的別針、有時是貼了小狗貼紙的行李箱、還有已被剪得這裡一個洞那兒一個缺的真皮碎料。他有備而來——某次拿起一條手鏈喃喃地問完「這是鐵嗎?」,便逕自從褲子後袋掏出半截磁石來試。
笑瞇瞇公公看上眼的,跟他的形象有落差萌,義工都好奇,常常着我去探問他買來做什麼。他會回我一個特大笑容,豎起大姆指,用濃重京腔說:「好玩兒!」而有些「好玩兒」之後會陸續出現在他身上,像是對他來說實在太大的皮褸,已經成為他的冬日戰衣了。
我每週當值一個早上,以為笑瞇瞇公公只在這天到來,一段日子後才知道,他可是天天來的超級熟客!某回他進店見到我時,顯得特別高興,聊一會後我才明白,原來他發現其他日子的義工換了人,都沒有熟面孔了,所以擔心。我向他保證義工只是放假。這時郵差剛好進店來送信,立即跟公公熱情招呼(用不同的語言),然後詼諧地回頭對我說:“He’s my good friend! Did you know he comes to your store every day?”
我跟笑瞇瞇公公的對話很日常——他的記性有點卡,說話有點卡,而我的國語也卡,深入不來。但他不只一次,問起同樣的問題:「你老家在哪兒?是覺得香港好,還是咱這兒好?」我心裡千迴百轉——香港已經是我的家鄉了嗎?還是某種家的現在式?喜歡不喜歡香港和溫哥華,該從哪裡說起⋯⋯?最後我用最大的誠意,交出最不糾結的「局部現實」——
「難說啊。溫哥華的夏天很美,但我掛念香港的冬日太陽⋯⋯那你喜歡北京還是這兒?」
「北京比這兒冷多了,而且空氣太差勁。」笑瞇瞇公公說:「環境還是這邊好⋯⋯這邊好⋯⋯」可他那句話的尾音拖得太長,長得讓人莫名惆悵。
快樂尋寶:Forrest Gump、校徽杯子、神奇小工具
在二手店工作其中一個樂趣,是看到街坊找到心頭好;而這裡,確實藏着各樣的寶。聖誕後,應節貨品換成一整個架子的老影碟,我疑惑:大家都在串流,還有人買嗎?可沒過多久,一位中年男子便捧着一疊經典到收銀處,《真的戀愛了》(Love Actually)、 《阿甘正傳》(Forrest Gump)、 《90男歡女愛》(When Harry Met Sally)⋯⋯送給住老人院的年邁母親。他不好意思地笑說:「聖誕趕不及從美國回來,唯有新年陪她。」我想像一場溫暖的跨年電影馬拉松。
街坊的尋寶能力常常教我驚嘆,拿到收銀處的,有時是新簇簇的名牌衣物,有時是我攪不懂的奇妙小工具。一天,一位年輕男子拿着杯子來,我端詳上面的圖案,看到兩頭站立的神獸合力承托盾牌,後面還印了一個英文名子。「這是我母校的校徽,名字是我哥哥的老師,早退休了。」男子興奮地說:「沒想到在這裡碰上,太神奇了!」

圖:不少娃娃到來時一身襤褸,愛編織的義工姨姨為他們一針一針地鈎出合適的衣物。
基層生活剪影
基層街坊是二手店的重要客群,而他們自有不動聲色的生活智慧。收銀檯的小盤子常常擺着手指大小的玩具車,一元幾角,銷情不俗——有時孩子自己左挑右挑;有時是公公婆婆買來哄孫兒;但也有不少人連看都不看,隨手抱走一堆。直到一天,一位婆婆把玩具車掃清光,我才終於明白箇中奧妙——她說:「拿去社區交換站啊!放下一輛,可以換走一本書或者玩具⋯⋯」
但這裡也有令人心頭一緊的畫面——每次出現都緊皺眉頭的黑人媽媽,在店裡來來回回只挑減價貨,她拖着的小女孩有一雙惶惶的大眼睛,彷彿也注進了焦慮⋯⋯神情迷惘的老伯伯在冬天依然穿得單薄,他說剛買下的衣服不合身,坐在地上要求退貨,正在付款的姨姨也穿得樸素,但她趨前對我悄聲說:「他要的,我可代付」⋯⋯一對中年女子匆匆離開後,在試身室留下一堆扯下來的價錢牌子⋯⋯
德裔的義工姨姨拿着那堆價錢牌,一臉深惡痛絕。她討厭偷衣賊、討厭議價的客人、討厭大減價、討厭寫不清楚的政策⋯⋯因為這些都會減少二手店的收入,「等於我們為業主白打工,而不是非洲的孤兒!」一輪連珠發炮後,她忽然停住,然後像是對自己說:「⋯⋯我知道我老是在發牢騷。」
我沒料到這着,笑了。下次見面,我會想起來告訴她:謝謝你着緊。

圖:店內的標示:請支持慈善工作
快時尚之外
近年店裡生意愈來愈差。雖然我們當中沒一個人領薪,但能拿出來的善款一年比一年少。與此同時,走「快時尚」路線的時裝店愈來愈盛。那些以近乎「用完即棄」方式生產與銷售的全新衣服,價格竟和二手衣沒差多少。每次看見那些店標示的價錢,我都彷彿看到,很多速食時裝很快又會被丟到我們的小店門前,在冬雨中堆成一座小丘。
午後我下班,正要離開時,笑瞇瞇公公又來了,今日第二回。他問:「哎——你們都有時間吃午飯嗎?會不會餓着?」「我現在就回去吃!」「那快點兒,快點兒回去!」他揮揮手說。
這些點滴,正是我在二手店當義工尋到的寶。

▌ 蘇美智
記者,愛聆聽日常、撿拾容易錯過的精彩;既寫大人看的書,也寫小朋友看的書。對她來說,離散的功課,是保持自我完整,同時珍視身處的當下。作品包括《外傭——住在家中的陌生人》、《我們的同志孩子》和《神奇小盒子》繪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