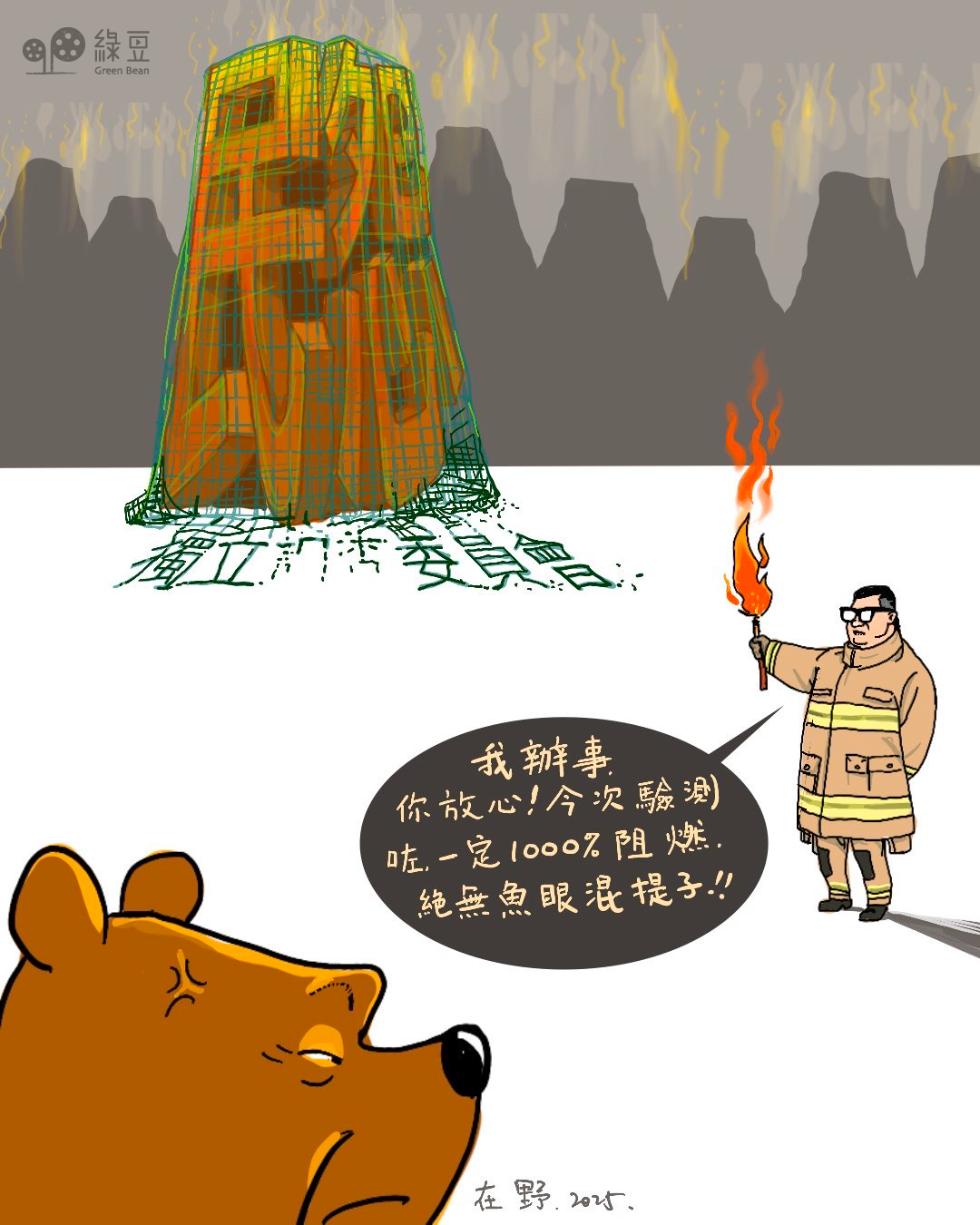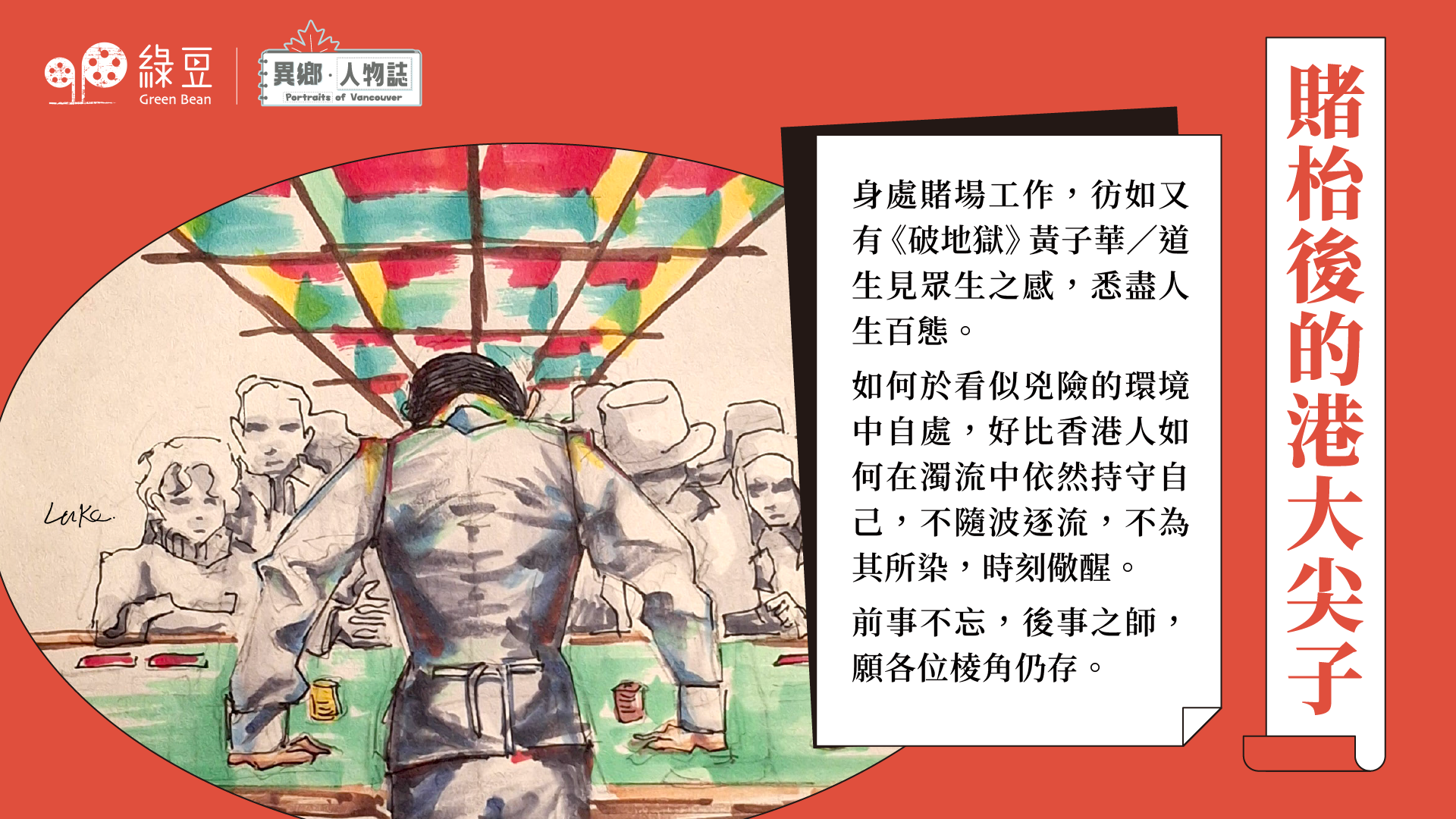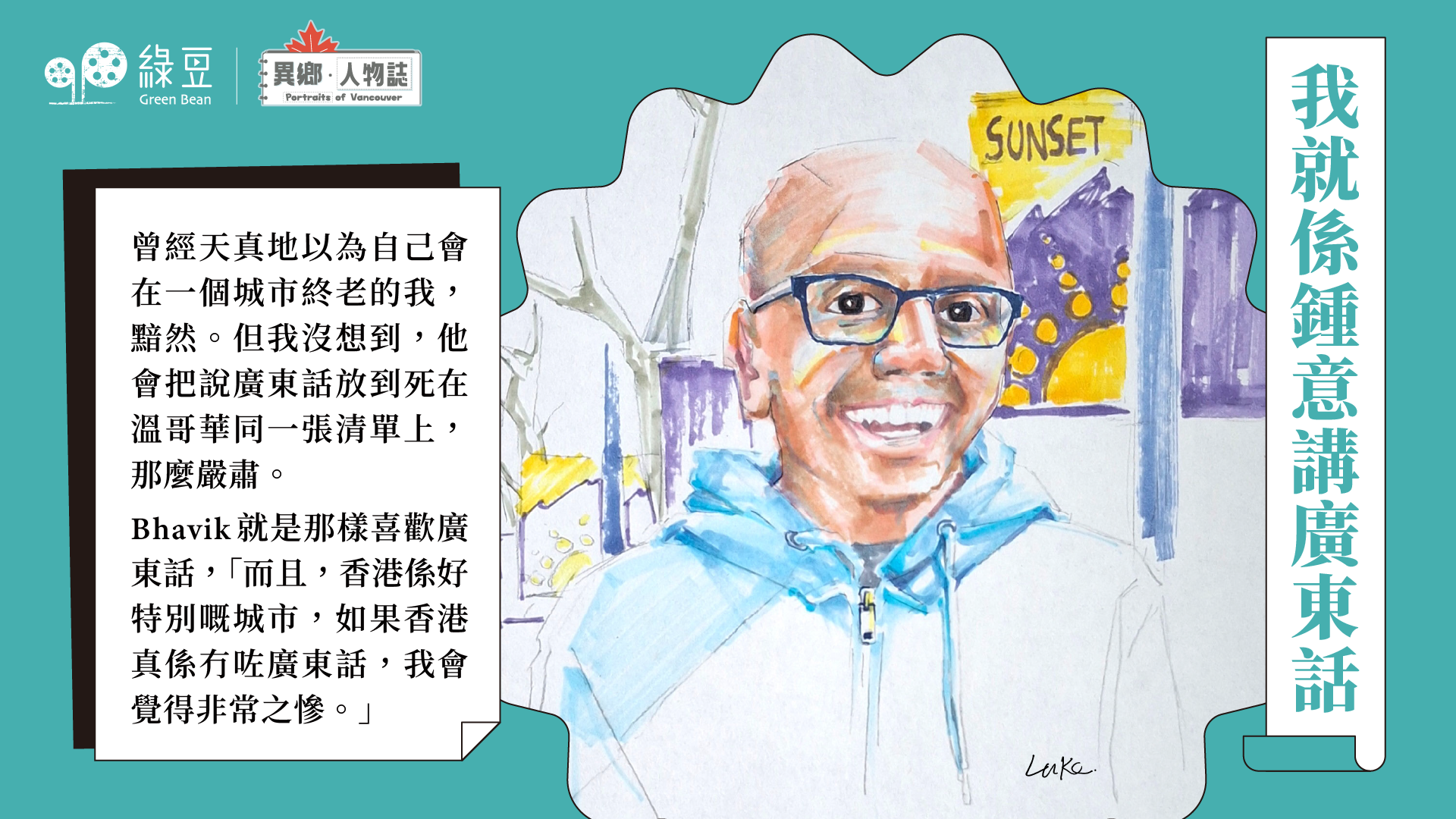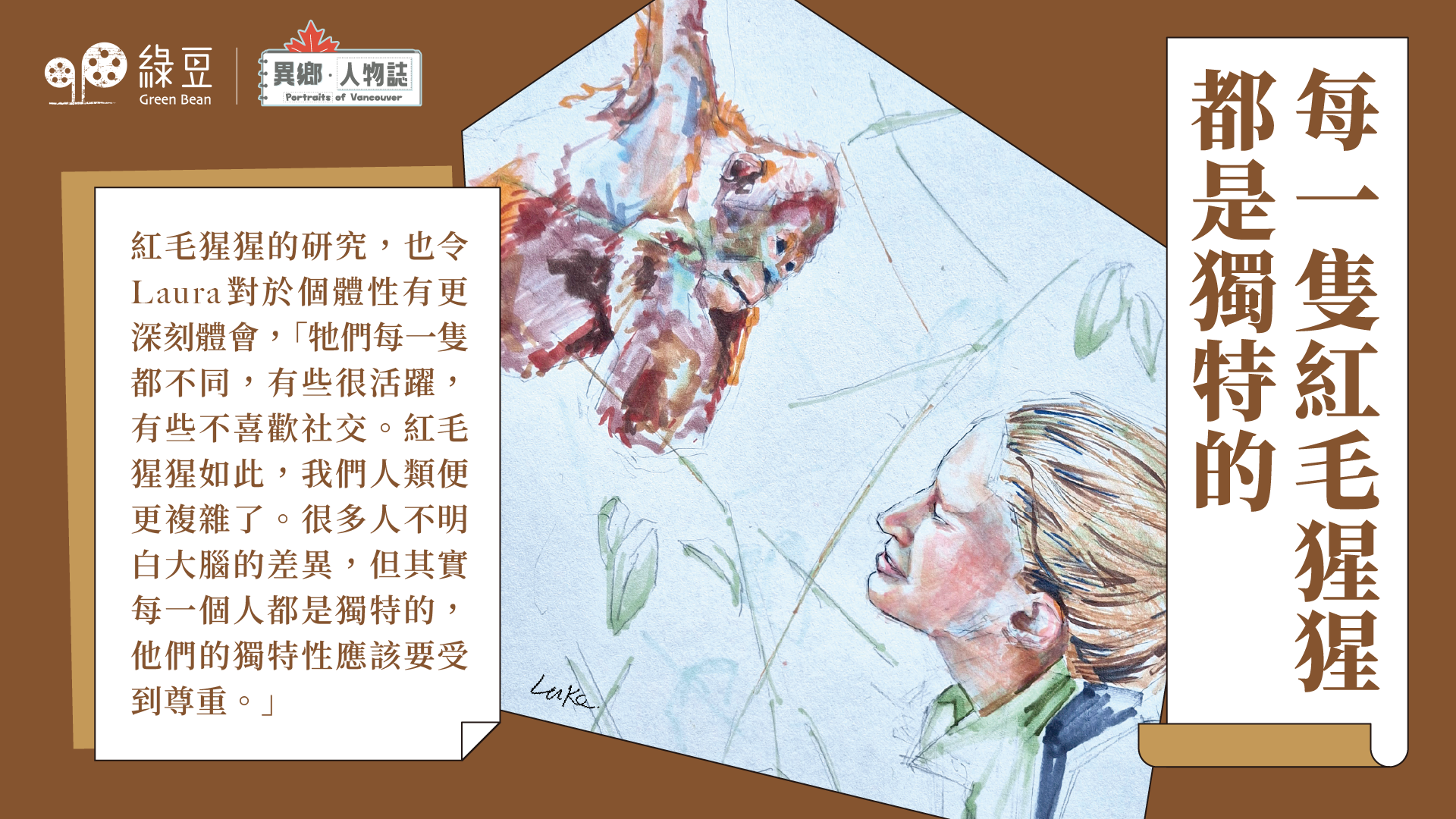粵語作為生命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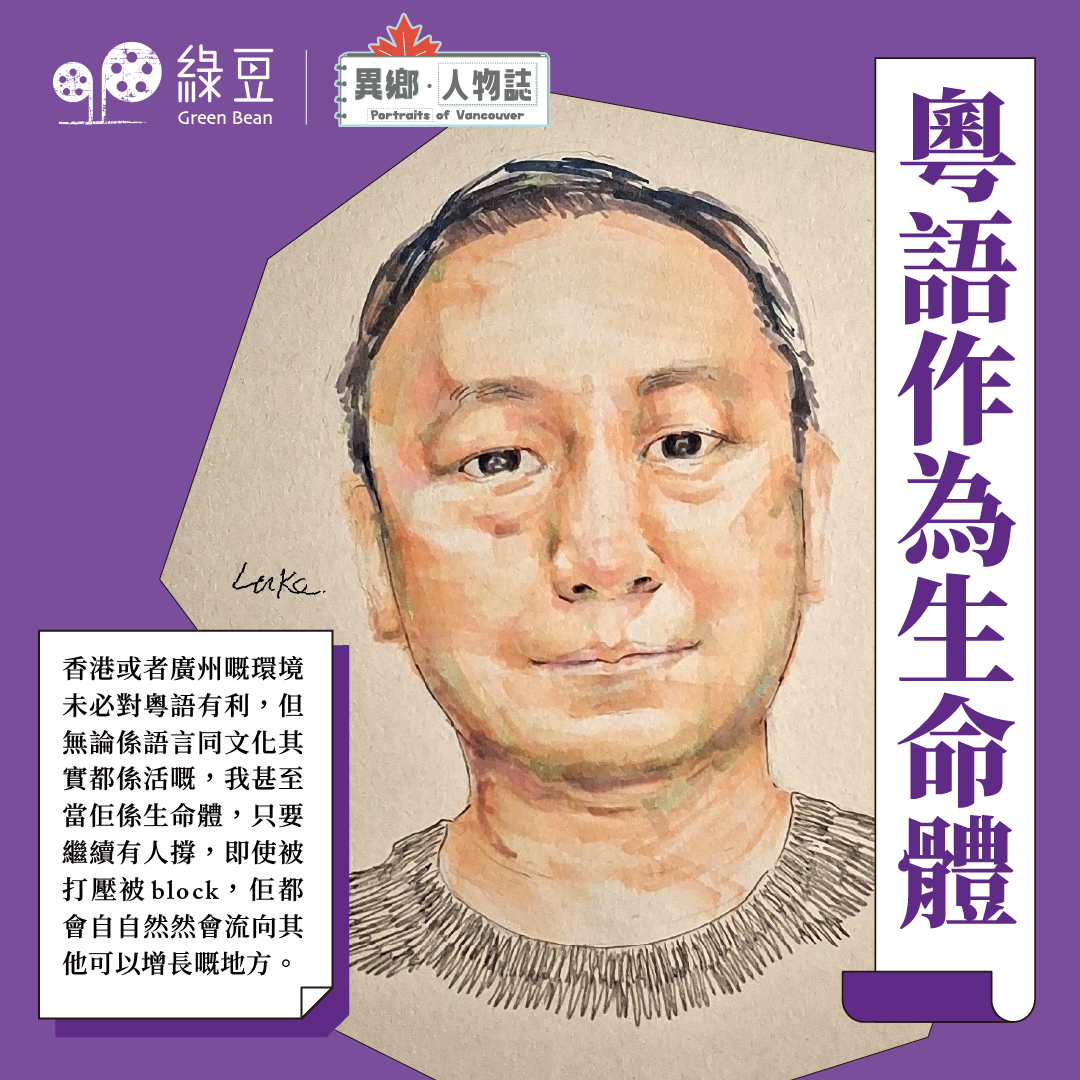
你覺得廣東話正在沒落嗎?—— 這條問題,白文杰(Raymond)十年前初到溫哥華卑詩大學擔任粵語課程主任時,已經有人在問了。那時他答:未到瀕危,但有危機。「十年後,我覺得我哋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睇:香港或者廣州嘅環境未必對粵語有利,但無論係語言同文化其實都係活嘅,我甚至當佢係生命體,只要繼續有人撐,即使被打壓被 block(封鎖),佢都會自自然然會流向其他可以增長嘅地方。」
他強調不要妄自菲薄,因為廣東話根本是國際語言,「全球有8千萬人喺唔同地方講緊粵語,多過意大利文同韓文。如果連母語者自己都睇得咁灰,仲點會有人撐?」
Raymond 生於香港,畢業於中文大學,後來到美國修讀語言學碩士,2015年獲聘到溫哥華擔任粵語課程主任。從碩士畢業到落腳卑詩大學之間的八年,他在加州蒙特利的軍方語言學校 (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 Foreign Language Center)任教普通話,那是美國軍人速成外語的地方。
在美國軍校教普通話
那時臨近畢業,他從師姐口中得知那間軍校需要大量普通話老師,覺得有趣,便申請了。這是國家級的龐大團隊,單是中文教師就有 140 人,中國大陸的求職者必須接受繁複的背景審查。至於來自香港的 Raymond,非常順利便過關了。
在軍校教授語言是特殊的體驗。「嗰度冇乜秘訣,最強係軍費同操練。佢哋六個人用一個班房,班房全部有電子觸控熒幕,人人手拎一部 iPad。師生比例係一對三,主要學口語,學讀繁體同簡體字,但唔考書寫。喺嗰度返學都係一種軍訓,朝朝操體能,之後至少要喺課室留六個鐘學中文,未計做功課同睇書嘅時間。佢哋就咁樣日日學,完全無空間處理情緒,試過有軍人喺堂上崩潰爆喊。催谷一年之後,大部分都由對普通話零認識開始,到最後能夠基本溝通。」
憑着語言學的知識,加上從其他普通話老師學到的方法,Raymond 很快便掌握要領。幾年轉眼過去,他彷彿能預視自己跟同事一樣,在同一個崗位安穩到老;但一種不甘慢慢累積。「我覺得自己需要進步,好想入大學教書。而且嗰度大部分同事嚟自大陸,我係唯一從香港嚟嘅,好體會到文化差異。」像是農曆新年,同事相約買外賣回來觀看「春晚」(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的春節聯歡晚會),「⋯⋯但呢個唔係我嘅文化。」
媽咪、夾餅、溫哥華
2013年他決定裸辭。一年後,一個有香港背景的家庭捐助溫哥華卑詩大學開設粵語課程,大學尋找有海外中文教學經驗的老師。這筆二百萬加幣捐款的消息,甚至登上了《經濟學人》。朋友對他說:「係你啦﹗」
Raymond 從沒想過自己會來加拿大生活,「難聽啲講,以前對呢個國家嘅印象,只係落後啲嘅美國」。他已過身的媽媽倒曾盼呀盼來溫哥華看看,「嗰陣好多親戚移民過嚟,個個話靚,佢一直想去睇。」2008年,Raymond 的妹妹在西雅圖行婚禮,一家人順便速遊兩小時車程外的溫哥華。當日「Raincouver」(溫哥華外號)正常發揮——天陰陰雨綿綿,風景都蒙了灰,街上人寥,而他們也跟親戚錯過了。「但我好記得媽咪走嗰陣話:我終於嚟過溫哥華一次啦。」翌年她癌症過身。
2015年,Raymond 重返溫哥華,這次獨個兒來卑詩大學上班。他聽說校園附近有港式食店,便跑去買夾餅,沒料到吃着吃着掉下淚來。「其實喺加州嗰幾年好寂寞,有時會特登開幾個鐘頭車去搵中國餐館。我無唸到呢度可以就咁行去買夾餅。」他說:「嗰一刻好感動⋯⋯然後忍唔住唸,會唔會係媽咪想我嚟呢度?」

圖說:「我喺呢度做嘅唔單只教書,仲同社區同香港結連,呢個真係我嘅 identity。我好珍惜呢種社區嘅感覺,從此愛上呢個地方,亦都慢慢同呢度嘅人同風景結連,」
學粵語不能脫離文化脈絡
卑詩大學的粵語課程隸屬亞洲研究學系,著重口語聽講而非書寫訓練,不設入門班,修讀的學生須具備一定中文底子。Raymond 這課程主任既是「開荒牛」,也是開課首三年的唯一任教老師。對於這個課會招到怎樣的學生,他起初全無把握,但有一點十分清楚:粵語課絕不能脫離於廣東話的文化脈絡之外。
Raymond 積極探索香港的文化資源,與當地導演、作家、歌手、文化學者,乃至當時的立法會議員建立聯繫,邀請交流;他亦嘗試在課堂加入戲劇元素,讓學生在表演與對話中自然學語。課程從最初的三十名學生起步,逐步建立口碑,到今日有800多名學生選修,而老師團隊亦增至六人。課程名額常滿,後面拖着長長的候補名單。
讀者或可以上網欣賞初班同學的配音功課:
https://youtu.be/HYD0irEVUDs?si=4zDUKDECIR4bJZmB
我旁聽了一堂中級粵語網課。三位同學分別用廣東話報告新聞,介紹相關生字,最後挑選一個俚語分享。聽到他們認真講解「神又係你、鬼又係你」、「食得鹹魚,抵得渴」、「吹水唔抹嘴」,我莞爾又禁不住暗暗自豪——那樣生猛的廣東話!班上不少同學操普通話口音,談到來學廣東話的原因,有人說是與朋友溝通,有人覺得唱廣東歌有型;而唯一的白人學生則分享自己在香港居住時沒機會學廣東語,沒想到在加拿大補上這一課。
這正是卑詩大學粵語課程學生的某種群像:七成學生有普通話和中文底子,但對廣東話好奇;少數非華裔學生約佔一成,他們出於興趣或人生經歷與這門語言結緣。然而,Raymond 最想接觸但報讀人數始終難以突破的,卻是那些在北美成長的華裔新世代。
帶傷學廣東話的土生華人
他把這個疑惑開展成為自己的博士生研究課題,招募了二十位有粵語家庭背景的學習者 (Heritage learner of Cantonese) ,探索這個群體的學習動機與缺乏動機,嘗試從中梳理脈絡,包括他們的身份認同、意識形態和溫哥華的文化環境等。
「我發覺好多人對學粵語仲保留住童年創傷,尤其係家長同親戚嘅態度:『你咁都唔識講』、『你好多懶音』,又或者佢哋好努力講,人哋反而用英文答。好多人放學後被迫返中文學校,抄抄寫寫,但唔知自己寫乜,覺得冇用又唔好玩。」累積下來的挫敗感,甚至影響他們對自身身份、語言,乃至原生家庭的看法。
「有趣嘅係,佢哋好多人長大之後至重新發現,原來要同屋企人溝通,最好都係用母語。但佢哋已經唔識講。」
Raymond 設定的訪問對象為「學習者」,即是那些最終重拾童年錯過了的機會,嘗試回頭連結祖輩語言的人。但在這個研究以外的溫哥華,繼續錯過廣東話的土生華人,依然是多數。
愈把課題挖掘下去,Raymond 感到愈難定義所謂的文化身份,「喺全球化下,我哋嘅文化背景愈嚟愈多元,每個人嘅經歷都係獨特嘅。我 reflect (反思) 自己嘅身份,都覺得好難單純咁講——我係香港人,但 what does it mean?我喺香港出世長大,屋企一直講廣東話,我從來冇從移民角度睇自己嘅爸爸媽媽,但其實佢哋原本係講印尼話嘅印尼華僑,至於我嘅公公婆婆爺爺嫲嫲,講嘅係福建話。」
今年 Raymond 第一次陪爸爸回到福建安溪一條很多白姓人家的村子,翻開紀錄了二十二代族人的厚厚族譜,從中找到自己的名字。這次家族旅行帶來一種震撼,他突然很想重新學習那些疏遠了的祖輩話語,除了福建話,還有親愛的媽媽從前說的印尼話。
或者,所有身份認同的複雜背後,最珍貴的其實是連繫。「雖然我哋做到嘅好少,但真係有學生多謝我哋,話佢返屋企講多咗幾句粵語,阿公阿婆已經感動到不得了。」Raymond說:「很多移民二、三代斷咗廣東話,但係咪代表佢哋完全冇動機學?我哋有冇可能畀返呢個機會同環境畀佢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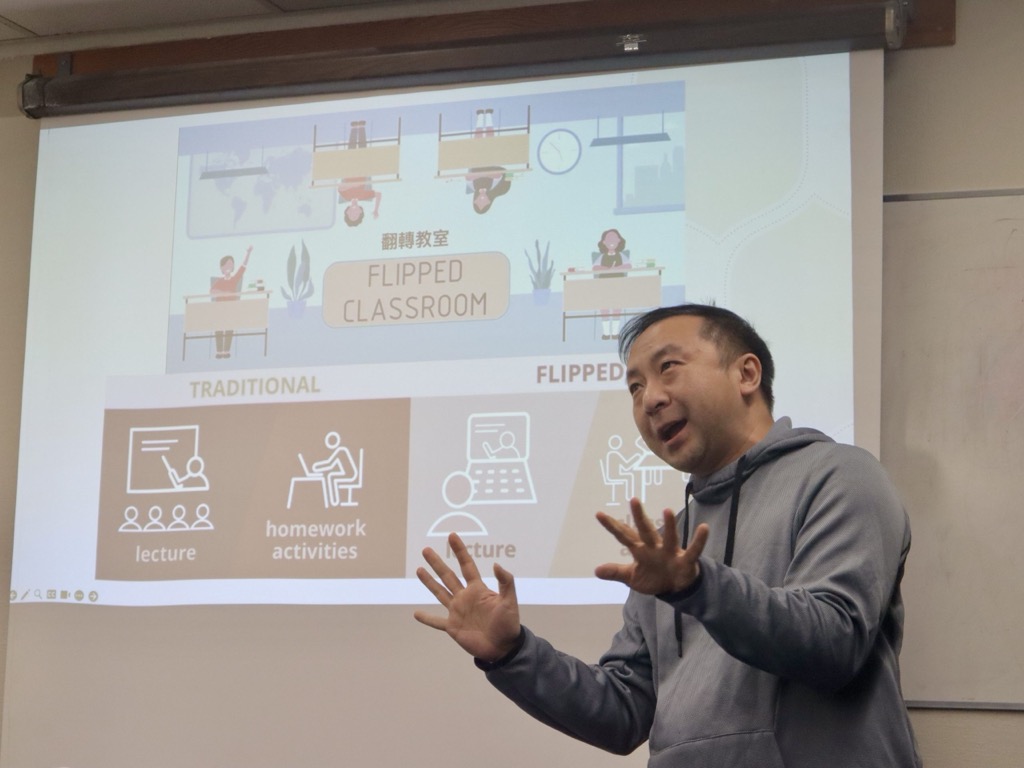
圖說:「有人問,上堂如果遇着敏感話題點算?我會冷處理——唔係唔處理,我會同同學講,你哋嚟學語言一定要有open mind,個腦硬繃繃一定學唔好,試下抱開放態度,因為同學諗嘅可能同你唔一樣。」
粵語課程十周年
今年是卑詩大學粵語課程成立十周年,標誌着新的發展階段:他們正跟香港語言學學會和一群海外學者合作,成立粵語口語水平考試;又計劃發展教師培訓,同時設計全新粵語基礎教材,希望最終能以開放源碼 (open source) 形式向全球網上發放。
擔當課程主任這些年,Raymond 對粵語教學的定位也添了反思:「曾經有學生同我反映,我哋啲教材好 Hong Kong centric(香港為中心),但佢唔係嚟學香港。冇錯我係教緊自己嘅母語,但粵語唔等於香港,教嘅時候係可以考慮埋粵語同其他文化背景人士之間嘅互動?」
今日 Raymond 期許的粵語,是一門在世界各地有8千萬人口使用的國際語言,「很多人很在意粵語喺香港嘅發展,但其實佢喺一定程度上已經係國際語言。可能我哋前線教學工作者睇到嘅同民間唔一樣,我知道世界各地有好多人教緊粵語,無論我去到捷克定比利時都聽到有人講。語言文化同人一樣係流動嘅,就好似溫哥華嘅粵語氣氛,比我十年前嚟嘅時候好,嗰時普通話比較強勢。」
「但係我哋對呢個語言嘅態度,絕對會影響大家對佢嘅睇法。即係你哋問你覺得廣東話點呀,你話就嚟絕種?所以,如果身邊有人學,你就幫下佢學,人哋講廣東話,你唔好隨便轉台,唔好介意口音,正如而家學英文都唔要求 accent free。」Raymond說:「母語者要撐自己嘅語言,如果唔係,仲邊有人撐?」

圖說:2024年11月香港歌手黃耀明訪問卑詩大學。
▌ 蘇美智
記者,愛聆聽日常、撿拾容易錯過的精彩;既寫大人看的書,也寫小朋友看的書。對她來說,離散的功課,是保持自我完整,同時珍視身處的當下。作品包括《外傭——住在家中的陌生人》、《我們的同志孩子》和《神奇小盒子》繪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