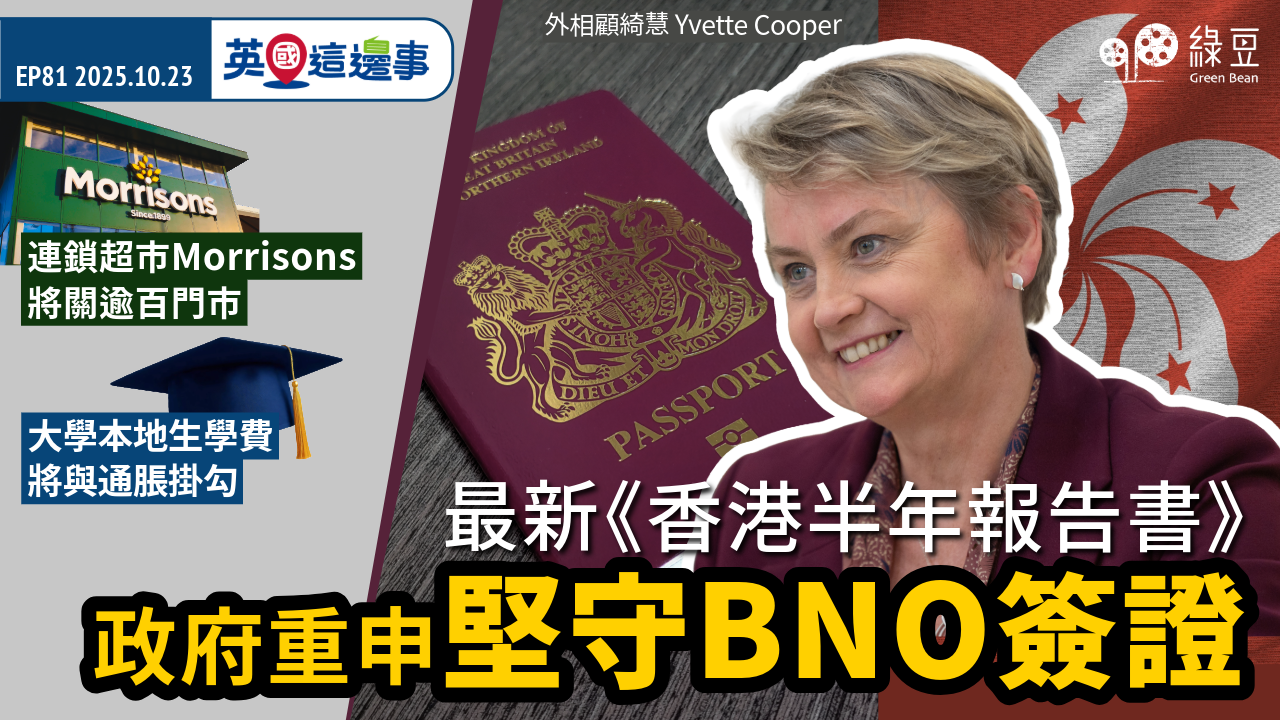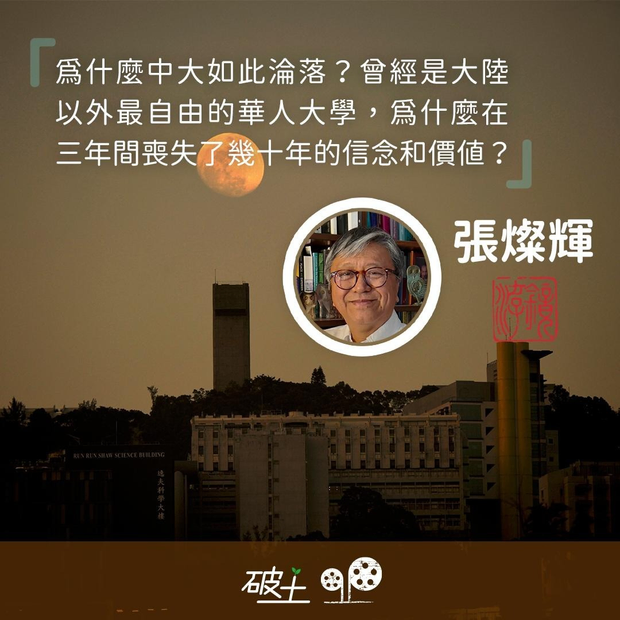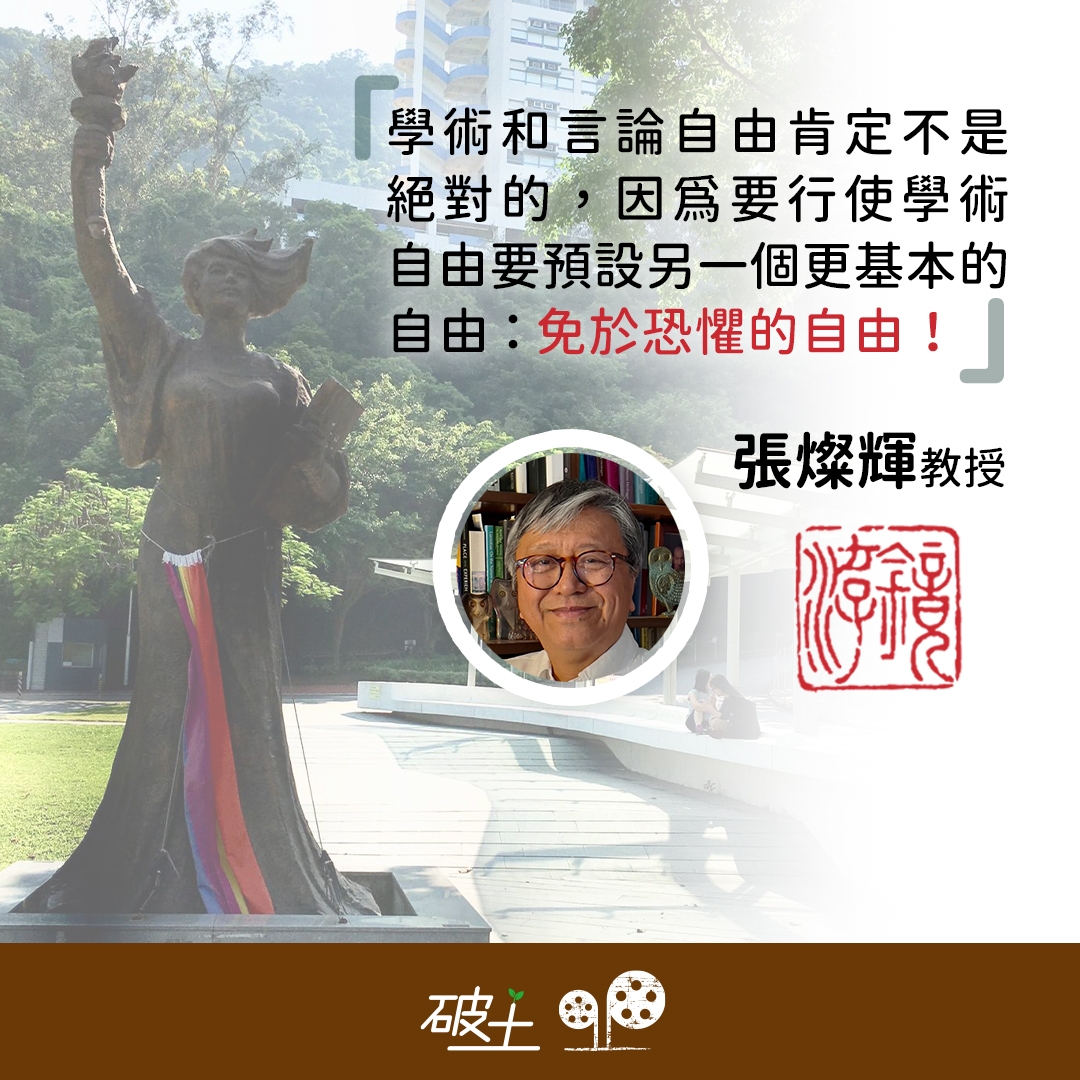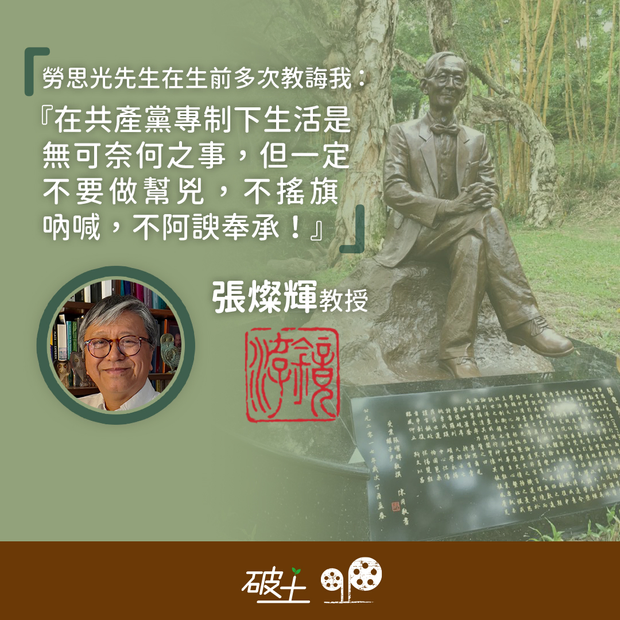生活藝術——篆刻與攝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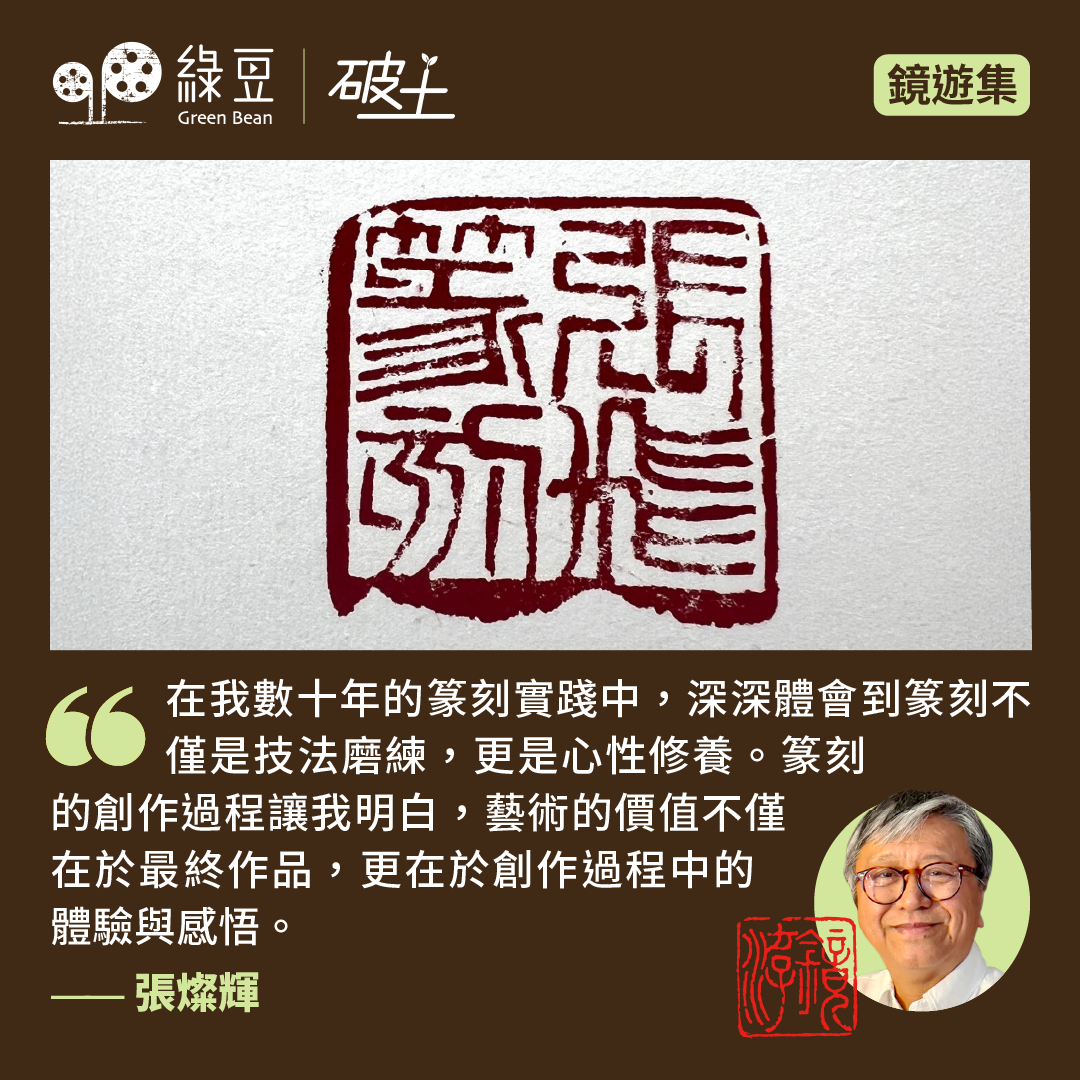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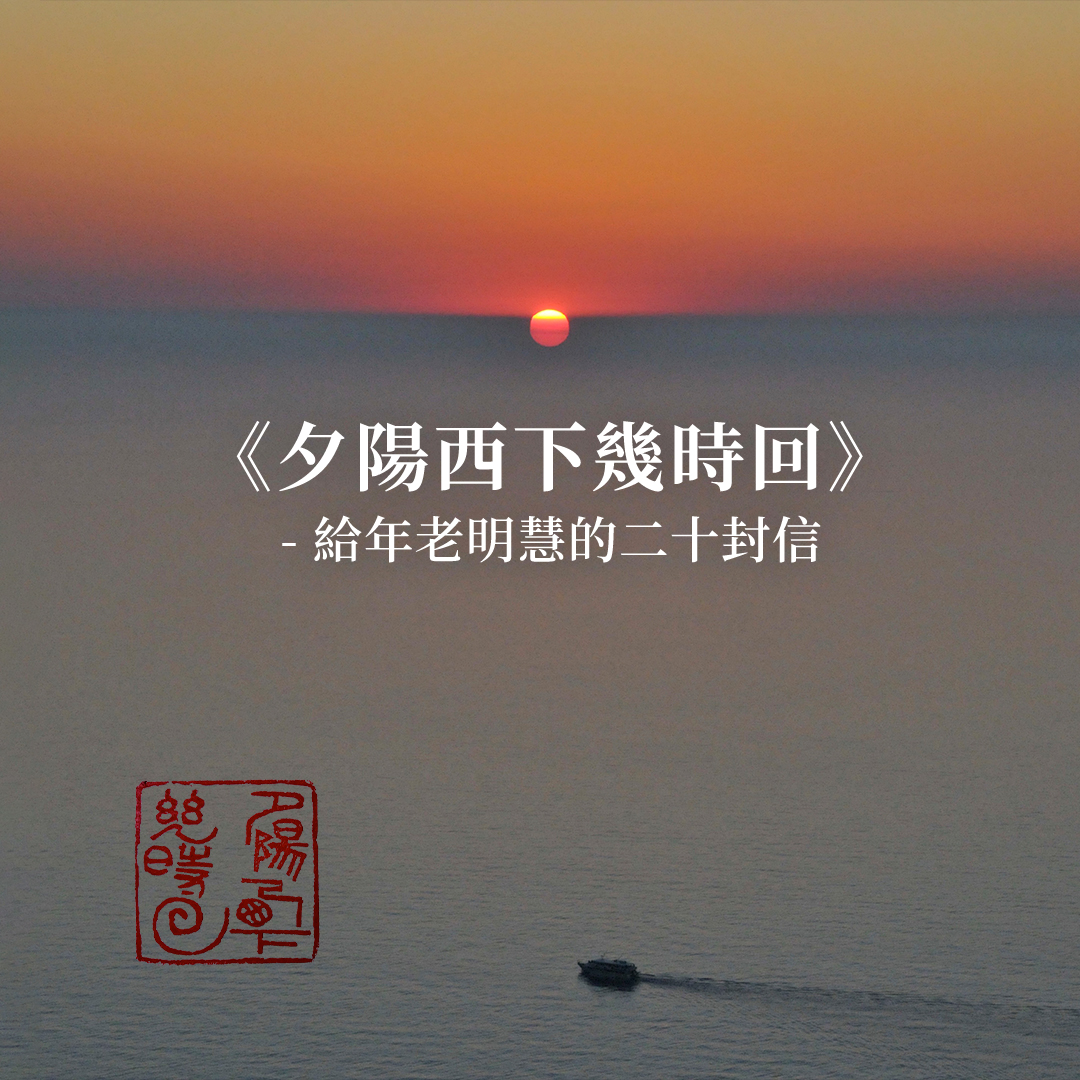
第十六封信 16.1
明慧:
當我靜坐於書案前,手中撫摸著那把陪伴我數十年的篆刻刀,凝視著見證無數歲月流轉的相機,心中湧起難以名狀的感動。這種感動既源於創作的純粹喜悅,更來自對藝術本質的深刻領悟。今日,我願與你分享我一生摯愛的兩種藝術形式 —— 篆刻與攝相,以及它們如何從平凡的日常汲取靈感,進而昇華為具有深刻意蘊的美學境界。正如莎士比亞在《李爾王》中所言:「Allow not nature more than nature needs, Man’s life is cheap as beast’s」—— 若僅僅滿足於自然的基本需求,人的生命便與禽獸無異。藝術,正是人類超越動物本能、彰顯精神高度的重要標誌。
太初無法:石濤與呂壽崑的藝術啟蒙
回憶起數十年前我在香港大學唸建築系的那個午後,呂壽崑老師踏進藝術創作第一課講堂時的身影依然歷歷在目。他並未看向我們這些懵懂的學生,而是開口便引用石濤的至理名言:「太初無法」。彼時我尚未領悟這四字的深邃內涵,亦不知眼前這位老師在抽象水墨畫領域的卓越成就,但石濤的這句話卻成為我此後數十年篆刻與攝相創作的根本指引。
石濤在《畫語錄》開篇即云:「太古無法,太樸不散;太樸一散,而法立矣。法於何立?立於一畫。」這個「太初無法」的理念實際揭示了藝術創作的至高境界——不為既有技法與規則所囿,而是回歸創作之本源,從心靈深處湧現真正的藝術表達。石濤認為:「一畫者,眾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於神,藏用於人,而世人不知。」這個「一畫」既是宇宙生成的根本,亦是藝術創作的起點。
呂壽崑作為香港新水墨運動的先驅,被譽為培育了無數香港水墨畫家的重要人物,深受石濤藝術理論薰陶。他在教學中強調的「太初無法」,實乃要我們拋棄一切成見與框架,回歸創作的純真狀態。這一理念對我後來的篆刻與攝相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讓我明白真正的藝術不在於技法之精湛,而在於能否從內心深處表達對世界的真切感受。
篆刻藝術:從無法到有法的心靈雕琢
篆刻藝術乃華夏文化之瑰寶,擁有三千多年的悠久歷史。它結合書法、繪畫與雕刻工藝,將藝術家的創造力與藝術成就表現於各式印文內容中,表達對文化、人性與自然的深切關懷。篆刻在古代凡屬於雕玉、刻石、鏤竹、銘銅的範圍,都可稱為「篆刻」,印章的刻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對我而言,篆刻的意義遠不止於技藝傳承,更是一種心靈修煉。
我從來沒有上過任何篆刻和攝相的正式訓練,完全是自學成才。學篆刻時,只能靠閱讀參考書籍,細細品味歷代篆刻家的作品與印譜,反覆思考其中的章法與刀法。攝相方面,也只是閱讀攝影理論書籍,觀摩攝影家作品,然後帶著相機到處摸索,慢慢琢磨出屬於自己的風格。篆刻和攝相於我而言,完全是娛己之舉,從未想過將作品作為商品出售。它們是我與世界對話、與自我對話的方式,是純粹的精神追求。
每當我開始篆刻創作,面對的總是最樸素的材料:一方壽山印石,數個漢字篆書,但在創作過程中,這些平凡元素經歷著神奇轉化。印石不再是冰冷的頑石,而是承載思想情感的溫潤載體;漢字亦不再僅是溝通符號,而是具有獨特美感與文化內涵的藝術形式。正如莎士比亞所說:「The object of art is to give life a shape」——藝術的目的是賦予生命以形狀,而篆刻正是將抽象的思想和情感,透過刀與石的對話,凝固成具體可感的藝術形式。
印從書出的革命性轉變
鄧石如提出的「印從書出」理念具有劃時代意義。他將自己的篆書書法直接入印,這種做法對鄧石如或許只是小小探索,但對整個篆刻史卻是不小飛躍,因為印人們終於認識到,原來自己手寫的篆書也可以拿來入印。這種從模仿到創造的轉變,正體現了石濤「太初無法」理念在篆刻藝術中的具體實踐。
「印從書出」既是學習篆刻藝術應當遵循的基本法則,也是衡量印章優劣的客觀標尺。篆刻藝術通常要遵循章法、筆法與刀法三法合一的原則。當我手握篆刻刀於印石上雕琢時,每一刀都承載著對文字本質的思考,每一筆都凝聚著對美的追求。篆刻創作形成了篆法、章法、刀法三大技術體系,主要包括篆稿、上石、奏刀、刻款、鈐印、拓款等創作步驟。
刀法與心法的統一:創作過程的深度體驗
在我數十年的篆刻實踐中,深深體會到篆刻不僅是技法磨練,更是心性修養。篆刻的創作過程讓我明白,藝術的價值不僅在於最終作品,更在於創作過程中的體驗與感悟。正如篆刻家所言:「刻印過程頗為舒壓,十分愜意」、「將感受釋放、把情緒雕刻於一枚印章上,可視為情感轉化的一種方式。」
篆刻的刀法主要分為衝刀與切刀兩大類。衝刀法運刀時,刀刃與石材呈一定角度,利用腕力直接向前推進,刻出的線條有力、挺拔,適合刻制直線或長曲線,能夠表現出篆刻的力度和氣勢。而切刀法則是主要依靠刀刃切削印面的刀法,以刀刃自右而左地順著線條的沿口切去,是一種斷續的運動過程,用切刀刻成的線條有生澀遲緩的特徵,顯得凝重蒼老。
記得初學篆刻時,每當執刀在手,內心總是忐忑不安。那方小小的印石彷彿蘊含著無窮的可能性,卻也承載著對失敗的恐懼。第一刀下去的那一刻,石粉飛濺,刀尖與石面接觸的清脆聲響,彷彿在宣告一段創作旅程的開始。隨著歲月的積累,我逐漸明白,篆刻不是對石頭的征服,而是與它的對話。每一方印石都有其獨特的質地和脾性,有的溫潤如玉,有的堅硬如鐵,需要用心感受,用刀傾訴。
在深夜的工作室裡,只有我與那方印石,還有手中的篆刻刀。燈光下,石粉在刀鋒間飛舞,彷彿靈魂的碎片在重新組合。每一刀都需要深思熟慮,因為一旦下刀,便無法挽回。這種不可逆轉的特性,讓篆刻充滿了張力和戲劇性。有時一刀下去,效果超出預期,心中便湧起莫名的喜悅;有時卻功虧一簣,只能重新開始。這種得失之間的起伏,正是篆刻創作最迷人的地方。
如同莎士比亞筆下哈姆雷特的獨白:「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 man! How noble in reason, how infinite in faculty」——人類是多麼了不起的傑作!多麼高貴的理性!多麼偉大的能力! 每一次篆刻創作,都是人類精神能力的展現,都是理性與情感的完美結合。
篆刻技法的深層體驗
隨著技法的日漸純熟,我發現篆刻刀法的運用需要因應不同的創作需求。初學者在刀法實踐中會遇到種種問題:這幾個篆字如何在方寸上佈局,線條的涩感如何表達、短線條與長線條如何處理、直線曲線圓弧等各種線條的處理,以及線條交匯處的處理等。這些細節刀法的處理,在臨習漢印的過程中將會一一遇到,遇到的時候需要仔細思量。在入石的角度、刀鋒與石面的夾角角度、刀刃入石的深度、刀刃衝切的速度、刀角入石的準度等實際操作中找到自己的方法。
每一次創作都是一次內心世界的探索和表達,都是對「我之為我,自有我在」這一境界的追求。石濤強調「我用我法」的創作精神,這在篆刻創作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我並非複製古人技法,而是進行主動創造。在石濤的理論體系中,「一畫之法,乃自我立」,這種從內心湧現的創作動力,正是篆刻藝術生命力的源泉。
(待續 )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