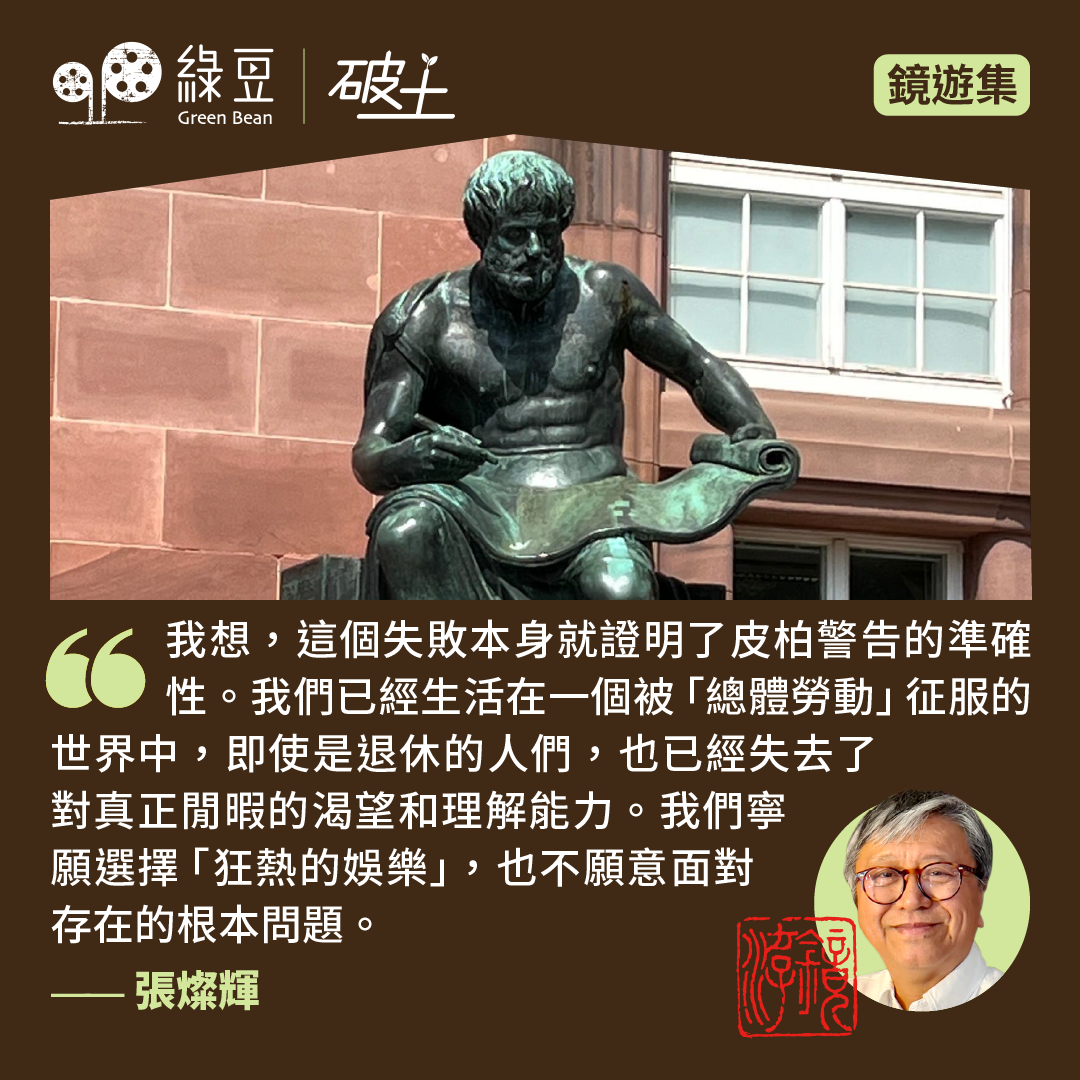《夕陽西下幾時回》- 明慧的回信 | 明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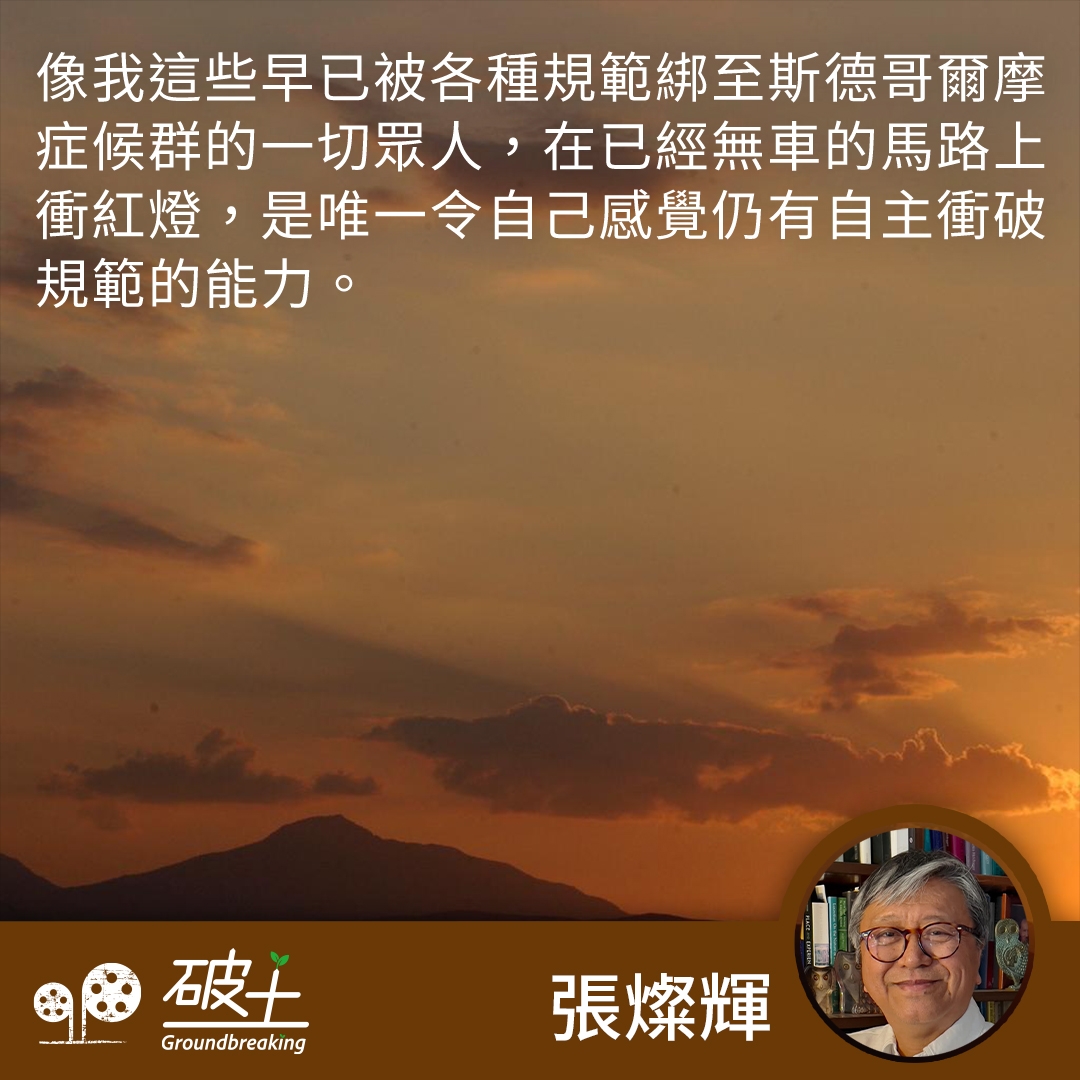
(張燦輝按:「明慧」是我的學生,一位不願意沉淪在日常無聊生活中的讀書人和音樂愛好者,也不想埋首沙堆無視當前政治荒謬的香港人。我剛刊出的第一封信,有他的認真回覆,令我感動不已。原來「明慧」是收到我信的!)

凌漸:
收到你的信,實在驚喜,也屆黃昏時候了,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甚麼鬼也好吧,也是對證曾經為人,一種回憶,不能改變的回憶,如同汪洋中一切破船上唯一的錨,作我這些不能接受孤獨的眾人的最後安慰。
也應回一下近況,雖然寫回溯的文字很不容易,尤其是我們這年紀的人。不過難寫不寫終歸寫,既是摯友之誼,亦是對自己的交代。這樣寫吧:我很好,一點也不好,如同一切眾人一樣,不用擔心。大學畢業以後,舉著理想輾轉在大型政商機構之間遊走推銷,想像總有伯樂偶會發現自己的一計半策,從此能逐漸實現想像中的理想社會。當然事與願違,才逐漸知道在已穩定的社會中,結構是由上層維持和建構的,其運行與我想像的任何理想皆風馬牛不相及。
也許《大同篇》、《正義論》是對的,但我一句也沒能推銷成功,起初同路不少,但見無人成功,紛紛改為推銷自覺更受現實歡迎的產品,不消一陣子,竟得我奮鬥終日未得之青睞與隨後的影響力。王道不行,代之霸道,霸道亦不行,代之以錢道、厚黑,至於我,只好在被看得太落魄前悄然離開,跟自己說,不是自己未盡全力,也不是放棄理想,但既已得浮桴於海,不如全身而退,韜光養晦。
沒一會竟機緣巧合浮到大機構做行政,算是存身遠害,大隱於市,組織家庭,從此過小確幸的生活。雖然其中也經歷過一些波瀾,社會的種種問題和無法接近的出路,一次又一次,理想又再浮現,我又再作馮婦,跟同齡之間越來越少的同路走進社會吶喊。只是從前的路盡閉塞了,我和同路只好走上街頭,走在義憤激起一切眾人的街上,一起流動,然後激情退卻,逐漸消散,壯闊卻無痕。
然後不知多久又一遍波瀾,繼續繼續,波瀾越疏也越平靜,我的生活也不可逆轉的歸於平靜。直至2019年,直至大廈崩塌,才悚然夢醒,以為自己是陶淵明,其實只是王衍,不只自己,還有我認識我不認識的同輩,佔盡天時地利的一輩,已屆耳順、從心之年,竟不克終,親歷桓靈、天啟之禍,徒恨亦不知應恨甚麼,奈何奈何。
這就是我的近況,乏善足陳,無所取材。既不算善,亦不至惡,這樣豈不是一切眾人的寫照?那時你送給我那本《伊凡.伊里奇之死》,我還珍藏得完好無缺,儘管跟那些波瀾一樣,隨著我的生活越來越平靜,越發疏於翻讀,但讀過的種種情節卻早化為魘。將書合上、忘掉亦無濟於事,任憑案牘勞形,家事縈心,那管終日暢飲,午夜酣眠,伊凡的尖叫總在最不能預期、最不適當的時候劃破當下。那撕人心肺、悲憤欲絕的吶喊,不能自已、無以截停的長嘯,剎那間就像自己的過去、現在毫無意義,一切希望土崩瓦解,感覺自己融解一地,散落四周,連雙腳重新集氣、站起的力量也失去,實在無能為力。
一時記起小學時聖經老師教過,還背到兩三句,求你寬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復原。但你甚麼你,明明就只得我一人,誰可代我感覺?毫無意義,醒了就睡不著,不是到廚房取酒飲,就是勉強閉眼裝睡,捱時間過至明早,起牀再忙過再行忘掉。我回憶起,當年你送我書後,我接續給許多朋友推銷過,他們的經驗皆與我相當:驚醒,不能面對的虛空和孤獨,重新入睡的努力。醉酒的無奈,裝睡的可笑──然後我終發現,人之所以沉醉於無聊且無意義的日常,不是跌倒陷入的,而是自己投江。
不只是從沒求索人生意義者在江上飄浮迴旋,更是已醒覺者因醒覺之痛苦,回蜷縮落日常之中,以沒頂之缺氧麻醉自己的痛苦。也即這麼多曾醒覺過的沉睡者根本沒睡,所以伊凡的尖叫根本無法叫醒他們,他們亦曾在第一次聽見伊凡尖叫時一起尖叫過,但跟伊凡不同,伊凡向大限去,在終見大限成為事實那刻解脫,尖叫亦在那刻停止;他們則還得繼續生活──至少他們覺得是──繼續重覆,繼續尖叫,也總得停止,唯有將經驗之鐘撥回尖叫之前。那怎麼可能?那就裝作從沒發生尖叫的經驗,並催眠自己:從此不再尖叫。就算他們真正見到大限,回復尖叫的能力和欲望,再次尖叫,亦不能免伊凡之悲劇。至於我,不過五十步笑百步,推銷給朋友的書,結果現在自己也不讀,還不知是不能還是不為,情何以堪?
近況還能提起的二事,皆是從前輕狂歲月剩下的痕跡:聽巴赫清唱劇,和衝紅燈。無法擺脫日常,日常的重覆行止,日常的言語,不能避免被甜蜜而安全的日常吸去,但回憶承載著那僅餘的自尊,卻令我始終不能閉目飄流進日常,上不至天,下不至地,無處安身,幸好還有耳機,只要一播巴赫清唱劇,聽時且安身於音樂之中,上天下地甚麼也沒關係,這音樂構築起一個世界,真實而極端強烈的七情六慾,還有永恆而絕對完美的秩序,就像人本應存在於的那個世界,還好有人寫得出來。
許多人說甚麼音樂可以陶冶性情,可以治療心病,我看這些都太複雜,純粹在聽時感到自己真實地、昂首挺胸地存在著,感到因自己的存在而感到的一絲興奮和價值,甚至一點不需原因的感動,已經很好了。
至於衝紅燈,不知說笑還是認真,不就是體現自決和自尊的最後方法而已。像我這些早已被各種規範綁至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一切眾人,在已經無車的馬路上衝紅燈,是唯一令自己感覺仍有自主衝破規範的能力。既有成功感又安全,在衝及對岸時回望,剎那竟有種如聽巴赫清唱劇的感動,正好衣冠、含著微笑、看著馬路。我想,都這年紀了,不輕狂還待何時?還要是這種無益也無害的輕狂,不過是跌在地上,聊當拾起一手沙,遲暮者衝紅燈,跟伊狄柏斯自挖雙目其實都是一樣。
亂寫一通,似乎我逐漸當寫信是種發洩,不過也是一種近況吧,望你别要介意,寫完以後,還得繼續生活。就此擱筆,期待你的回信。
明慧
13-16/2/2023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