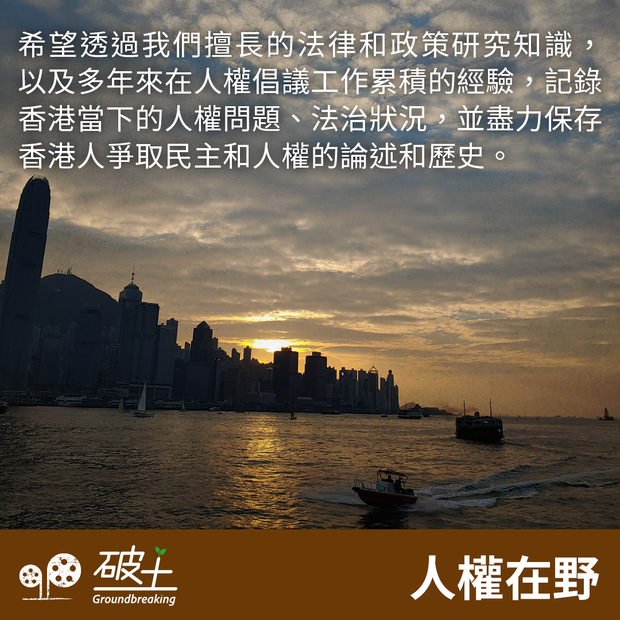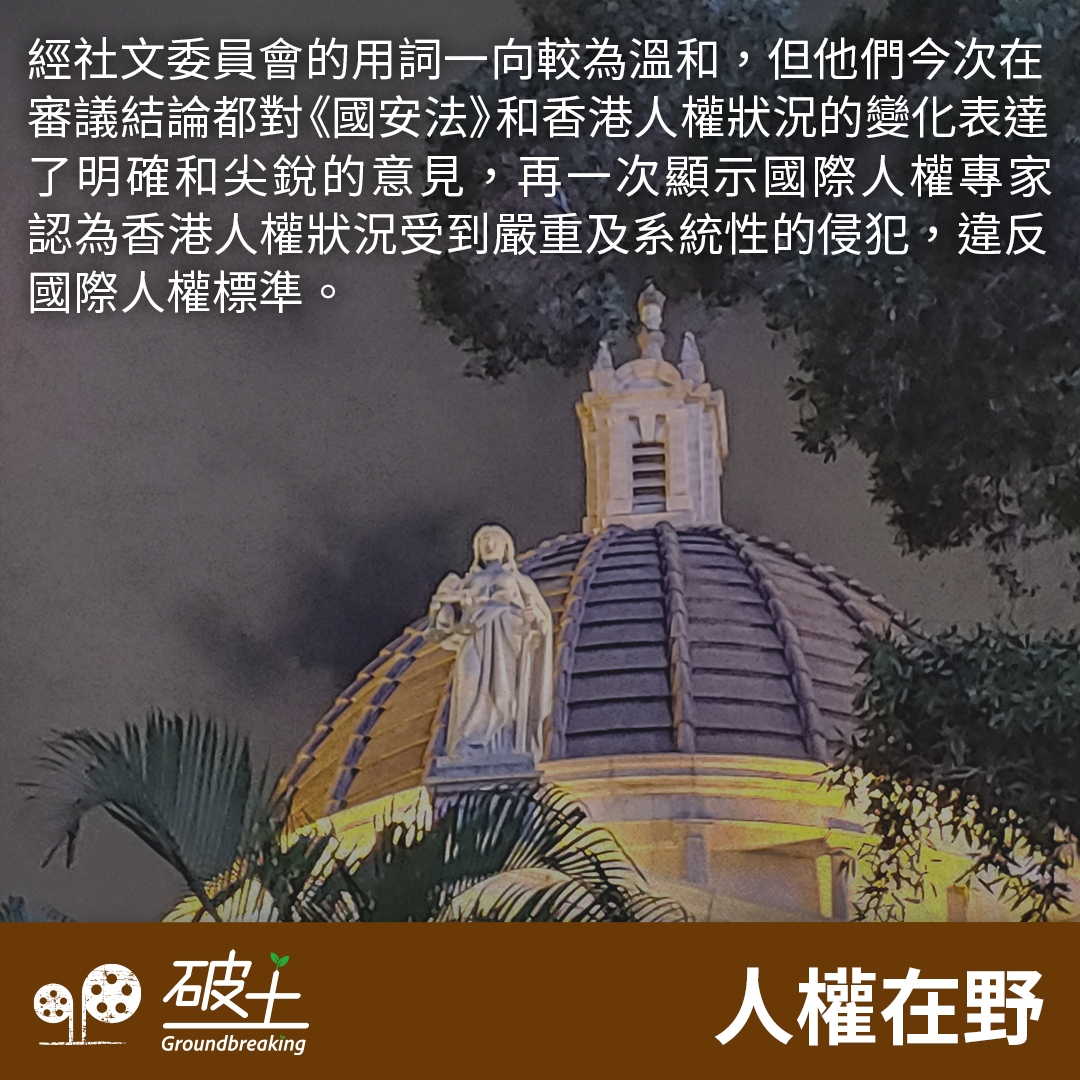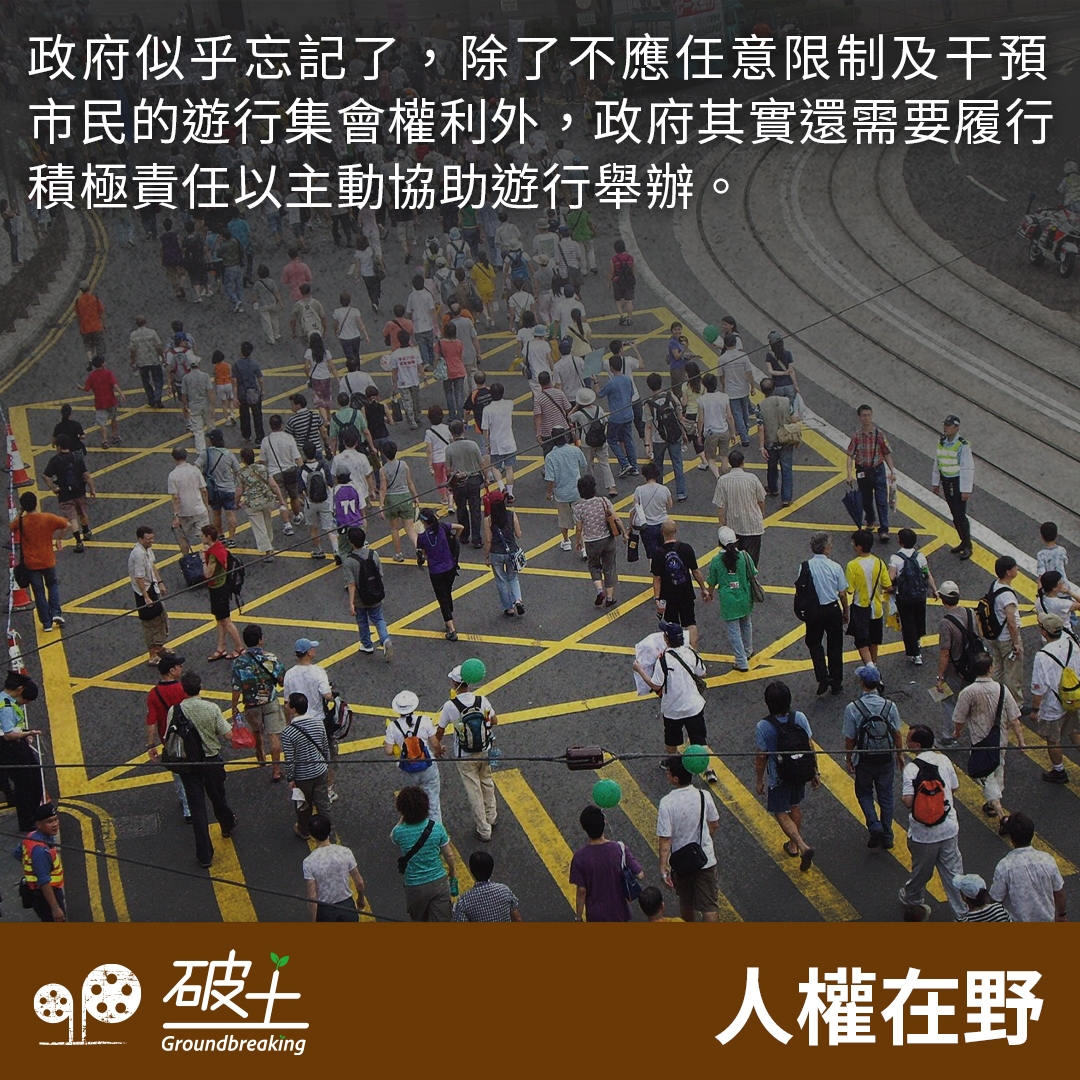暴力不能取代對話:Charlie Kirk之死的警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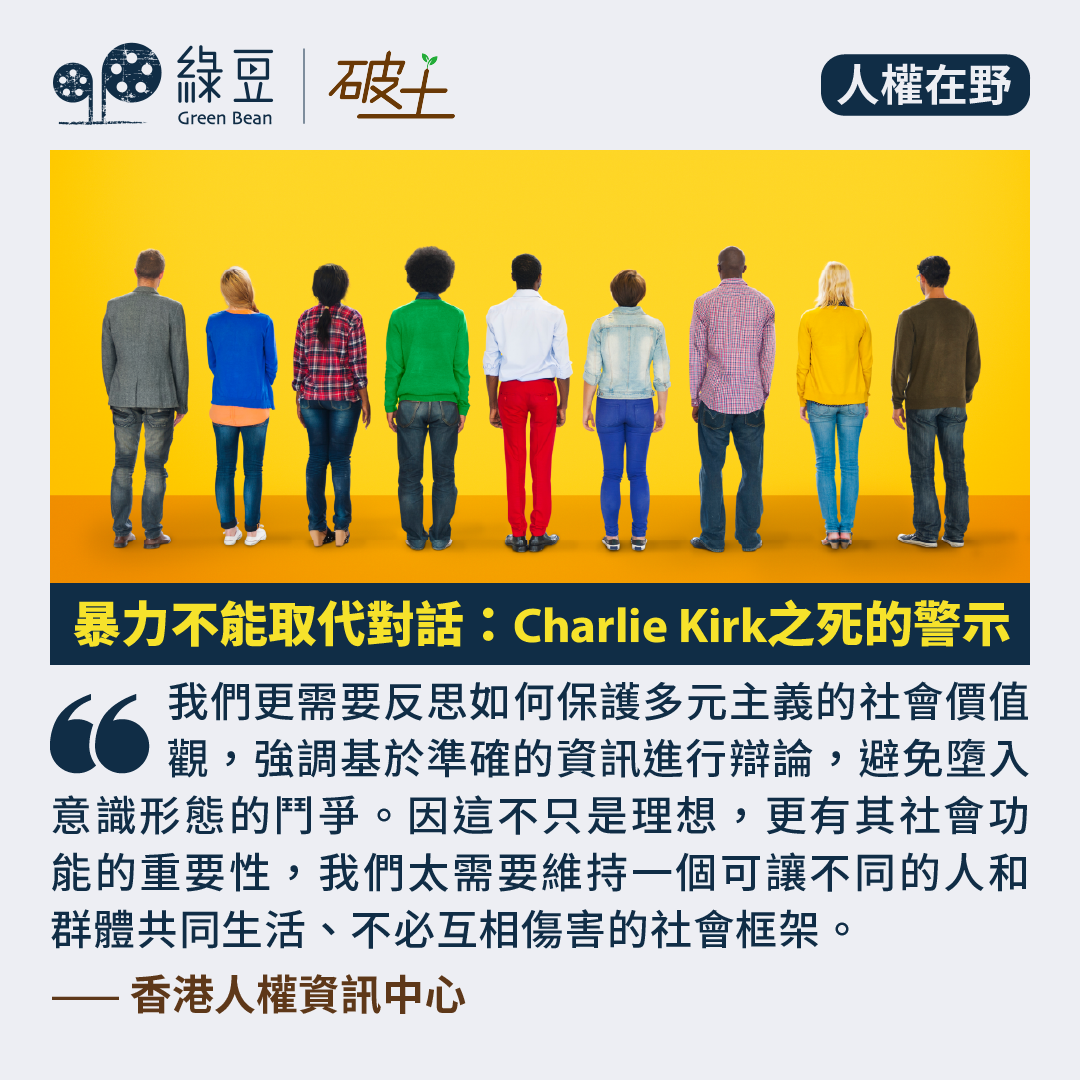
2025年9月10日,美國右翼保守派評論人 Charles James Kirk(Charlie Kirk)在猶他州一場校園演講中遭到暗殺。Charlie Kirk以言論大膽、立場鮮明聞名,生前常就種族、宗教及LGBTQ等議題發表具爭議的言論。
筆者認為,Charlie Kirk作為政治評論人,即使他的政見立場受到爭議,他在演講活動中被公開謀殺,是一場悲劇,亦是自由民主社會中不能接受的行為,刺殺的行動必須受到譴責和根據法律作出制裁。Charlie Kirk之死,亦令筆者反思我們應如何防止政治暴力、仇恨言論的擴散。
在國際人權法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19條保障言論自由,但第20條亦要求禁止對民族、種族或宗教「鼓吹仇恨、導致歧視或暴力」的言論。這代表社會必須既保障冒犯性或爭議性表達,同時亦要防止有人鼓吹仇恨,甚至把仇恨轉化為行動。誠然,這種保障表達自由與防範仇恨政治之間的張力並不容易處理,然而唯有保持持續的對話和基於實際經驗的檢討,我們才可以探索出當中的平衡點。
法律測試框架
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和人權專家在2012年提出「拉巴特行動計畫」(Rabat Plan of Action),建議了一套六項標準,協助判斷一則言論是否構成煽動仇恨,並達到須限制言論自由的程度,包括:
(一)背景:評估言論是否煽動歧視、敵視或暴力時,必須考慮其所處的社會與政治背景,因會直接影響意圖與因果關係;
(二)發表者:需考慮發表者的職務、社會地位及其在受眾中的影響力;
(三)意圖:《公約》第20條要求必須有「鼓吹」或「煽動」的意圖,僅疏忽或魯莽不足以構成犯罪,需涉及言論者、內容與受眾的互動關係;
(四)內容與形式:言論的內容與表達方式是判斷煽動的核心,包括挑釁或直接程度、論點的風格、性質及平衡性;
(五)影響範圍:涵蓋言論的傳播方式、規模、公開性及受眾數量,並考慮受眾是否具備依據煽動行動的條件,以及訊息的可及性與傳播頻率;
(六)可能性與危迫性:煽動不需實際行動發生即可構成,但須確認存在合理可能性導致針對目標群體的行動,且與言論之間具直接因果關係。
這套法律化的分析框架,保障所有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必須是例外,並須為實施限制定立很高的門檻,這可以幫助社會避免兩個極端:一是對仇恨言論完全放任,二是借「冒犯」之名去壓制異見,過度地壓制表達自由。
這套法律測試框架正被一些國家使用,歐洲人權法院在2018年的一宗涉及言論自由與仇恨言論的裁決中,亦引述了這套框架。在長遠發展下,這套測試框架可望逐步成為國際人權法的一部分。然而這套框架如何普及和發展,仍是在初步階段。香港是否可藉這套法律測試框架,平衡現時「煽動罪」對表達自由的過度侵害,值得進一步探究。
動盪社會下保護多元價值
我們現正身處一個資訊爆量、情緒能即時傳播和放大的年代,世界變得越來越碎片化與極端化。社會分裂、政治對立、網絡仇恨言論頻傳;政治、種族、移民、宗教、性別與性傾向等議題被激烈地拉扯、撕裂和抗衡。許多人感受到的,不只是言語的傷害,更擔心言論會轉為暴力,造成真實的人身損害與社會動盪。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情況已不是個別國家的問題,而是一種全球現象。
筆者認為在這脈絡下,我們更需要反思如何保護多元主義的社會價值觀,強調基於準確的資訊進行辯論,避免墮入意識形態的鬥爭。因這不只是理想,更有其社會功能的重要性,我們太需要維持一個可讓不同的人和群體共同生活、不必互相傷害的社會框架;容許並鼓勵在種族、宗教、性別、性取向、政治立場等方面存在差異,並允許這些差異在公共生活中被表達、被討論、共存,而不是被壓制、單一化或強行同化,讓不同的人在同一個社會體系內,以互相尊重與法律保障為前提,共同生活與對話。
逝者已逝,Charlie Kirk的立場和影響將交由歷史定斷,期望他的家人和朋友能早日撫平傷痛,美國的民眾亦能從中深思,避免美國社會陷入更大的撕裂。對於筆者來說,Charlie Kirk之死提醒我們保護多元價值和對話,是防止社會沉淪於暴力與分裂的必要條件。
▌香港人權資訊中心 Hong Kong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Facebook: hkchr.org |IG: hkchr_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