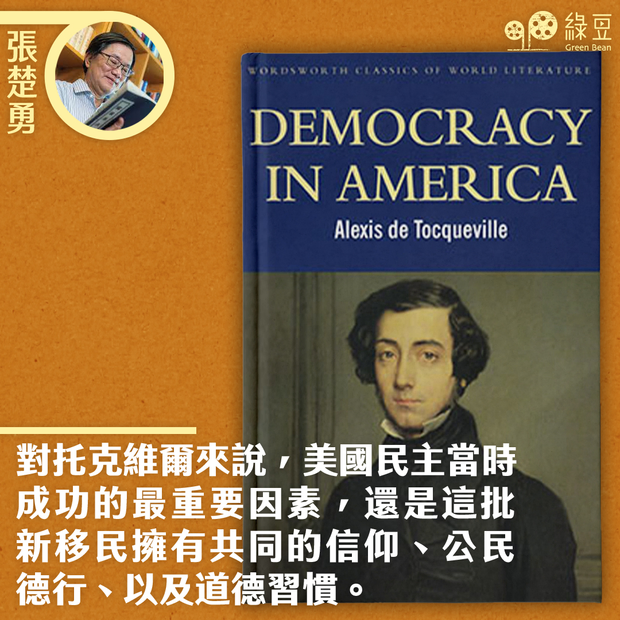寫在 《通向奴役的路》 出版80週年前夕

《通向奴役的路》(The Road to Serfdom) 在1944年3月和9月二戰期間先後在英、美兩國出版。出版後,始料不及的,是該書即時使英籍奥地利裔思想家 Friedrich A. Hayek 聲名大噪。這本討論政治社會理論的嚴肅讀本,竟然成了當時暢銷一時的書籍。
據英文版 Hayek 全集的總編輯 Bruce Caldwell 在21世紀初時說,芝加歌大學出版社估計,他們的英文版《通向奴役的路》一書自出版以來,銷售量已在35萬冊以上。
為甚麼人們還在看
《通向奴役的路》出版後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納粹德國及其軸心盟邦戰敗,國際政治秩序進入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形對峙的冷戰格局。
把納粹主義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同樣批評為是侵犯個人自由的極權(Totalitarian)制度的《通向奴役的路》,其立論雖在當時很受爭議,但它的主張在這意識形態爭持不下的冷戰年代,卻同時受到敵對的兩個陣形一致重視,至使Hayek這本書需求不斷,甚至被翻譯成多國文字,成為他最為人知和最多人閱讀的著作。
在我去年退休之前,曾在香港城市大學的圖書館的書架上隨意瀏覽一下,便找到八個不同版本的中英文版《通向奴役的路》。說這本書使Hayek聲名大噪絕不過份。畢竟,知道Hayek是《通向奴役的路》作者的人,恐怕要比知道Hayek為甚麼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多得多。
今天離《通向奴役的路》首次出版已近80年了。人們看來還在不斷閱讀和出版這本書,繼續研究Hayek的思想。究竟是甚麼原因會是這樣的呢?
讀者如果單是細讀《通向奴役的路》的文本,可能得到最深刻的印象,就是Hayek對極權政治鞭辟入裡的批評。Hayek在這本書很希望澄清當時他認為的兩大流行誤解。第一個誤解,就是西方知識界普遍以為極右的納粹主義是資本主義走向末落時的極端反撲,其政治性質被認為是與左翼的社會主義南轅北轍的。
其次,不少西歐的社會民主派政治力量相信,政治自由和經濟平等是共容的。在民主政體下,政府通過理性規劃來節制自由市場的「盲動」,以達致社會公義的結果。這樣做是既可取、又可行。Hayek的《通向奴役的路》在它剛發表的那個時代,其直接的現實意義就是試圖糾正上述這兩大流行的誤解。
二戰後重要的事
把社會主義和納粹主義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邏輯連結起來,Hayek的用意其實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納粹德國所犯下的罪行和所推行的暴政,如果簡單地把責任完全歸結到德國人的民族性或納粹主義身上,那便是毋視了德國文化同屬是歐洲的共同文化的一部分這一事實,也忽視了納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樣會產生極權暴政的可能。
Hayek在撰寫《通向奴役的路》的時候,已預期到盟軍最終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勝利。因此,如何在戰後的秩序重建中,面對根本而真正造成極權暴政的因由,更好地認識、重塑和維護自由文明所賴以茁壯的思想資源和相關的制度傳統等,便是頭等重要的事。釐清社會主義和納粹主義的關係和澄清上述的「誤解」,正是《通向奴役的路》的一大任務。
在學理上論說清楚為何維護個人自由跟維護自發的社會秩序是分不開的,以及為何不應該盲目迷信理性萬能,以為理性規劃的制度必然可以取代或優於社會上自發的調協制度(如市場、普通法、道德習俗等),正是Hayek澄清上述「誤解」的依據。
他認為依靠政府干預市場,以達致某種通過一些抽象推理預先假定的平等或公義結果,不但會破壞人類長期自發互動中累積下來的社會協調機制,更會直接干犯個人自由。在現代複雜的社會中,由於對社會互動協調的知識是散落分布在社會不同角落的個人身上,因此,在缺乏例如自由價格這類自發形成的協調機制的情況下,中央式的理性規劃根本不可能盡知相關而瞬息萬變的資訊,至使干預往往不能帶來預期的結果,反而使當權者為求目的,不斷加強干預的力度和範圍,一步步迫近全權的暴政。這便是Hayek為甚麼不同意經濟平等可以和政治自由共容,並在《通向奴役的路》對歐洲邦國內左傾的社會民主黨派當時提出的工業國有化主張不斷作出批評的理由。
至今仍有啟發意義
換言之,《通向奴役的路》之所以受到重視和引起廣泛的爭議,在當時是因為Hayek尖銳地對進步知識界達成的一些重大共識提出了異議。這本書和Hayek的思想至今仍舊在學界和知識界備受關注,是因為他的立論根據,其實是針對西方文明自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以來對理性的高度推崇的唯理主義(Rationalism)作出根本性的批評,認為唯理主義錯誤的以為,自然科學的方法可以應用到所有人類的認知範疇之上,盲目相信理性設計本身在方方面面都優於傳統智慧或實踐經驗的累積,任何不符合理性標準或理性不及的東西都是比理性低劣的事物,理應被理性取代或淘汰。
Hayek相信,現代的唯理主義是對理性的濫用,這種濫用並不單局限在例如納粹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些政治意識形態上,而是廣泛地存在於近現代歐洲文明的某些強大的思想資源之中,不斷地挑戰著歐洲文明中的自由傳統。因此,對Hayek思想的關注實質上是超越了上世紀40-50年代的時空,也超越了冷戰的年代,因為他的理論、批判和對理性、自由、社會秩序的自發協調和演變等根本問題的反省,對歐洲文明和現代性到了今天還是有著相關的意義,其立場觀點仍舊有啟發性,這就是為甚麼人們現在還在閱讀和討論他的著作。
近期一個最新的例證,便是美國紐約一位學者Vikash Yadav,今年剛出版了一本名為《自由主義的殿軍:在政治資本主義時代的海耶克》 (Liberalism’s Last Man: Hayek in the Age of Political Capitalism) 的專書。這本新著有兩個重大特點。第一,這本書的篇章(即前言、15個內文篇章、結論)是完全依照《通向奴役的路》原書的篇章的結構和題目來撰寫。書的每章主要內容除了深入討論Hayek在原著該篇章內的論點和理據外,還會對有關論說作出批評、改善、或發揮。
書的第二個特點,就是Yadav認為,在上世紀末東歐社會主義集團瓦解之後,正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邦國已名存實亡。今天自由主義面對的挑戰,和20世紀Hayek所面對的極權邦國的挑戰已經不一樣,其思想和制度上的競爭者,已是在經濟上採取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但在政治上繼續實行黨國專權的邦國。
和20世紀的極權邦國不同,這些專權黨國引入了市場機制,在經濟領域內實行全球資本主義式的競爭和生產,並以取得經濟增長來加強其統治的正當性,但在政治上這些邦國繼續實行從上而下的一黨專權,對挑戰或威脅其統治權的任何內外力量都不會容忍。Yadav形容這類體制為政治資本主義,並在書中每一個篇章的後半,把來自政治資本主義的挑戰和自由主義應有的回應和關注羅列討論。
Yadav這本書探討的,是當下一個很重要的政治經濟大課題。以後有機會我希望能與讀者分享我的看法。但Yadav在分析這個對自由主義新的大挑戰時,認為Hayek及其《通向奴役的路》,至今還是一個主要的依據,此依據讓自由思想溫故知新,以應對新的世界情勢,可見Hayek的思想仍舊很有當代意義。
Hayek在中國
Hayek的思想,對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在一些方面也發揮著關鍵的影響,近年這一點愈來愈受到華文學界的關注。周德偉、夏道平、殷海光在上世紀50-80年代的台灣,正是通過譯作和著作,有力地推介了Hayek思想的中國自由主義者。
林毓生同時是殷海光和Hayek的學生,在周、夏、殷這一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基礎上,他在70-80年代至他去世為止,一直進一步深化和推動Hayek服膺的古典自由主義如何與中國傳統開展對話,希望通過「創造性轉化」的方式,把中國傳統中可以和值得改造/重組的東西,變成有利的文化資源,使自由、民主、法治等現代價值和制度,可以在中華文化的環境下生根成長。
Hayek的理論除了影響到50年代台灣的自由主義者之外,到了80-90年代、那些親身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大陸知識分子在開放改革後,開始可以閱讀Hayek的著作。在他們讀到《通向奴役的路》時,當中帶來的,是印證了預言般的震撼。《南方人物周刊》主筆何三畏在2014年5月發表的一文章說:「[該書]在第九章的開頭,作者先引了列寧在1917年的一段話:『整个社會將成為一個同工同酬的管理處,或報酬平等的工廠。』接着,哈耶克又引了托洛茨基在1937年的一段話:『在一個政府是唯一的僱主的國家裡,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这個舊的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讀到這段話,就深深地記住了,因为它概括了我八十年代在工廠觀察的心得。」
在中國大陸思想界很活躍的秋風,10多年前也提到Hayek理論的雙重意義。首先,Hayek基於有限理性的英式自由思想,開展出對文明演化的解釋,指出了在文明內的制度和傳統做法,往往並非是個人理性或設計意圖所造成的結果;人類文明中的大多數實踐知識也是體現在那些不能以理論知識或語言完全闡明的、理性不及的制度和習慣做法之中。這些制度和做法雖然行之有效,卻不一定能為人所意識到或以理性語言完全演譯出來。
這些做法多是包含著長時間累積下來、但卻不能明言的豐富經驗和判斷。而我們去跟從這些制度和做法賴以構成的規則,正是文明得以運作之道。要創新改變,依這樣的思路推演,也只得在邊際上進行和採用內在的批評,靠同一文明內被廣為接受的做法作為標準,修正文明內在當下產生爭議的做法。如果我們以為可以有一外在於相關文明的理性標準全面地建構全盤的改革,來取代這些傳統做法,那就犯上了理性致命的自負。
秋風認為,有了對有限理性的認識,自由主義者便應放下全盤改革的虛妄,轉而於局部制度性改革的努力,尤其應在憲政制度上尋求漸進的改變。他在21世紀初時說:「在周德偉的思想典範刺激下,過去幾年中,我一直尋找……現代中國思想和政治的中道傳統。……在清末立憲者、張君勱、陳寅恪、周德偉、現代新儒家等等看似相互沒有關係的人物和思潮之間,存在著內在而深刻的關聯。我將他們概括為『現代中國的保守——憲政主義思想與政治傳統』」。他稱這是中道的自由主義,因為「與之相比,激進革命傳統固然是『歧出』,因其在政治上傾向於專制,在文化上趨向於單純的破壞。」他同時認為,五四以來中國自由主義的傳統也存在重大缺陷:「一方面是文化上的偏激,這一點與革命傳統相同;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軟弱無力,這一點又讓它敗給革命。保守——憲政主義傳統則保持了自由的革命的中道。」
要全面充分地檢視Hayek對戰後中國自由主義的影響,是一項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和理論研究中很值得去探討的題目。因此,Hayek的思想,不管在東方西方,至今還是跟我們關注的大課題息息相關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