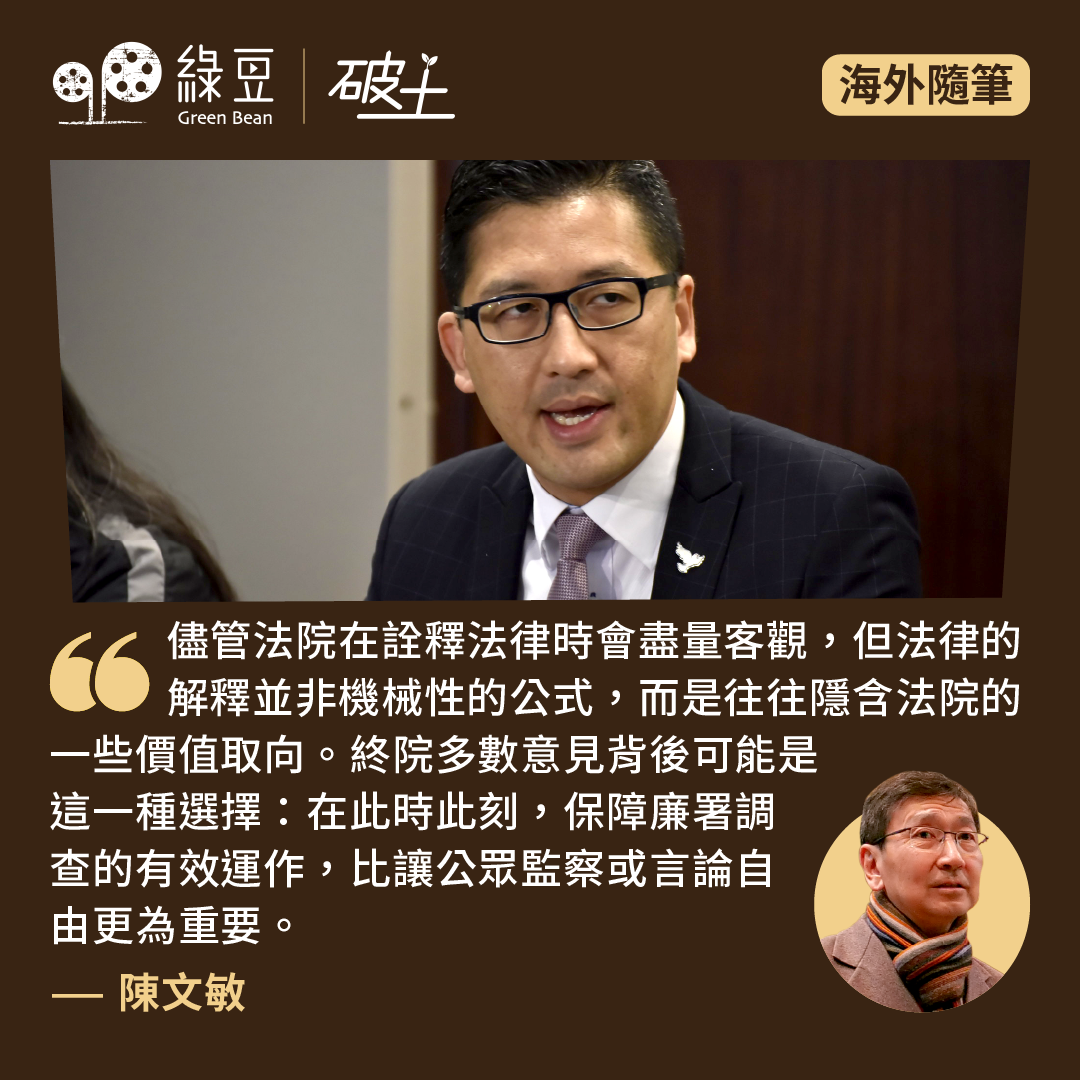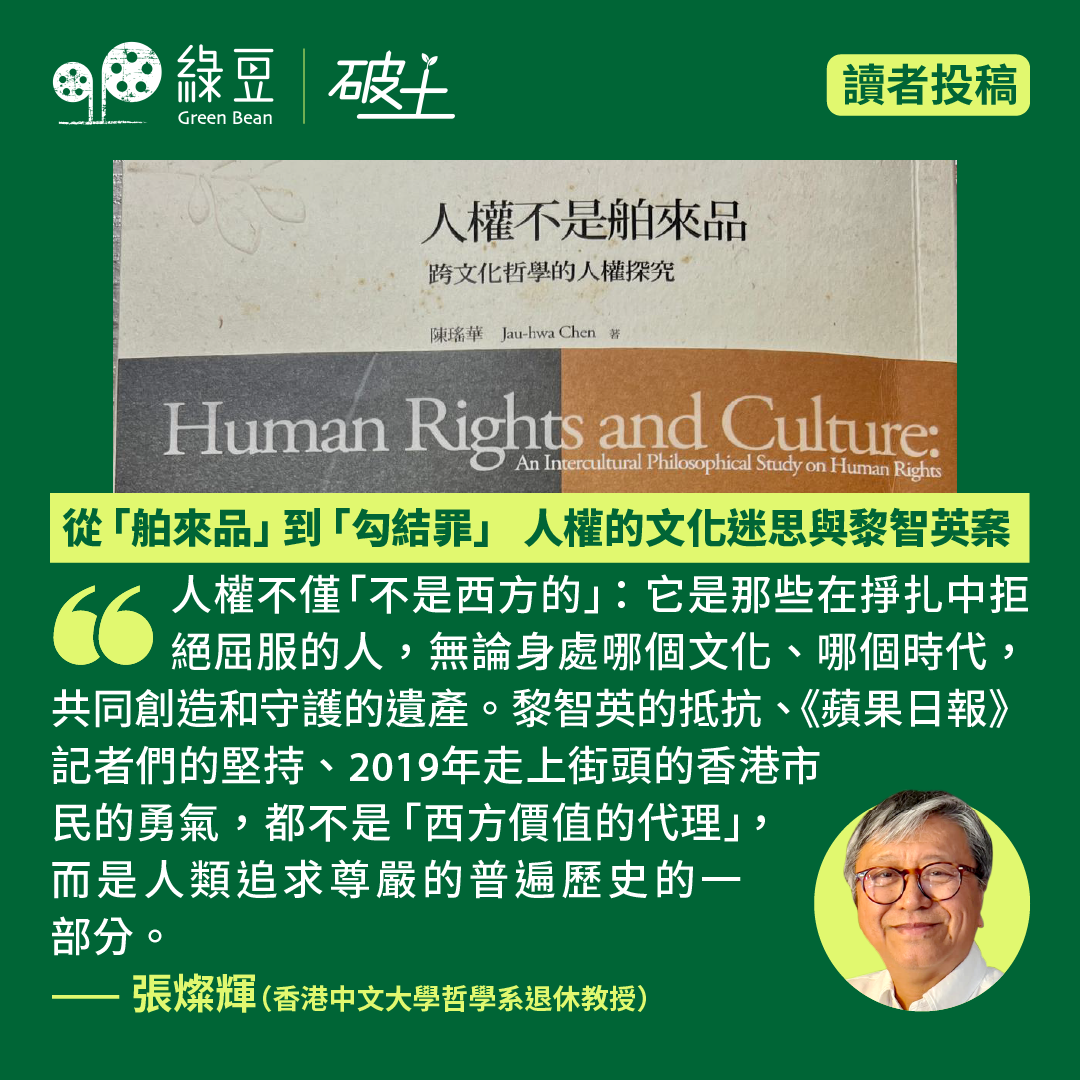制定一條法律條文時總會有一定的目的,法院在詮釋法律的時候,一方面要體現立法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偏離文字的意思。當然,理想的情況是文字準確表達了立法的目的,然而,若因為種種原因,文字未能完全表達或涵蓋立法的目的,那麼法院應該尊重文字,即使這意味立法的目的未能完全實現?還是以立法的目的為依據,勉強詮釋甚至扭曲文字的意思來迎合立法的目的? 前者可能被批評為僵化和造成法律漏洞,後者則可能混淆司法和立法的角色。這裏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兩者之間的分界可能模糊不清,而如何取捨和平衡,亦往往反映了一些基本價值的取向。 近日林卓廷披露廉署調查警司一案[1],便正好反映兩者之間的角力。林卓廷因向公眾披露廉署正就警司游乃強是否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作出調查而遭起訴,該案的焦點是《防止賄賂條例》第30(1) 條禁止披露的內容是廉署的任何調查,還只是廉署就該條例第二部分所定的罪行的調查?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並非第二部分所定的罪行,原審裁判官裁定林罪成;上訴時高院推翻裁決,認為林披露的並非第二部分所定的罪行,故沒觸犯法例;律政司向終審法院提出終極上訴,終審法院於四月初以3比2多數裁定林罪成,維持裁判法院的判罪和四個月的監禁。 《防止賄賂條例》第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