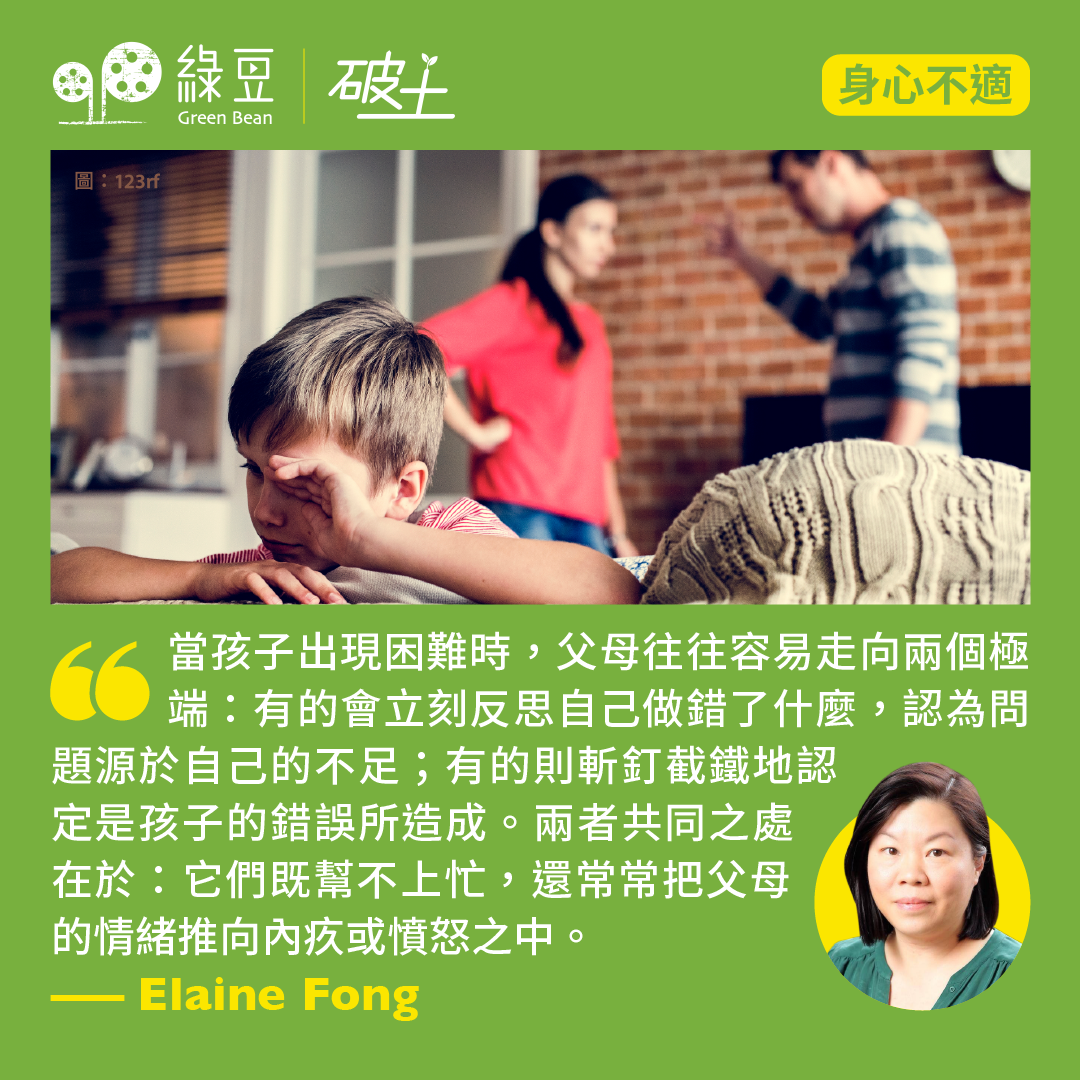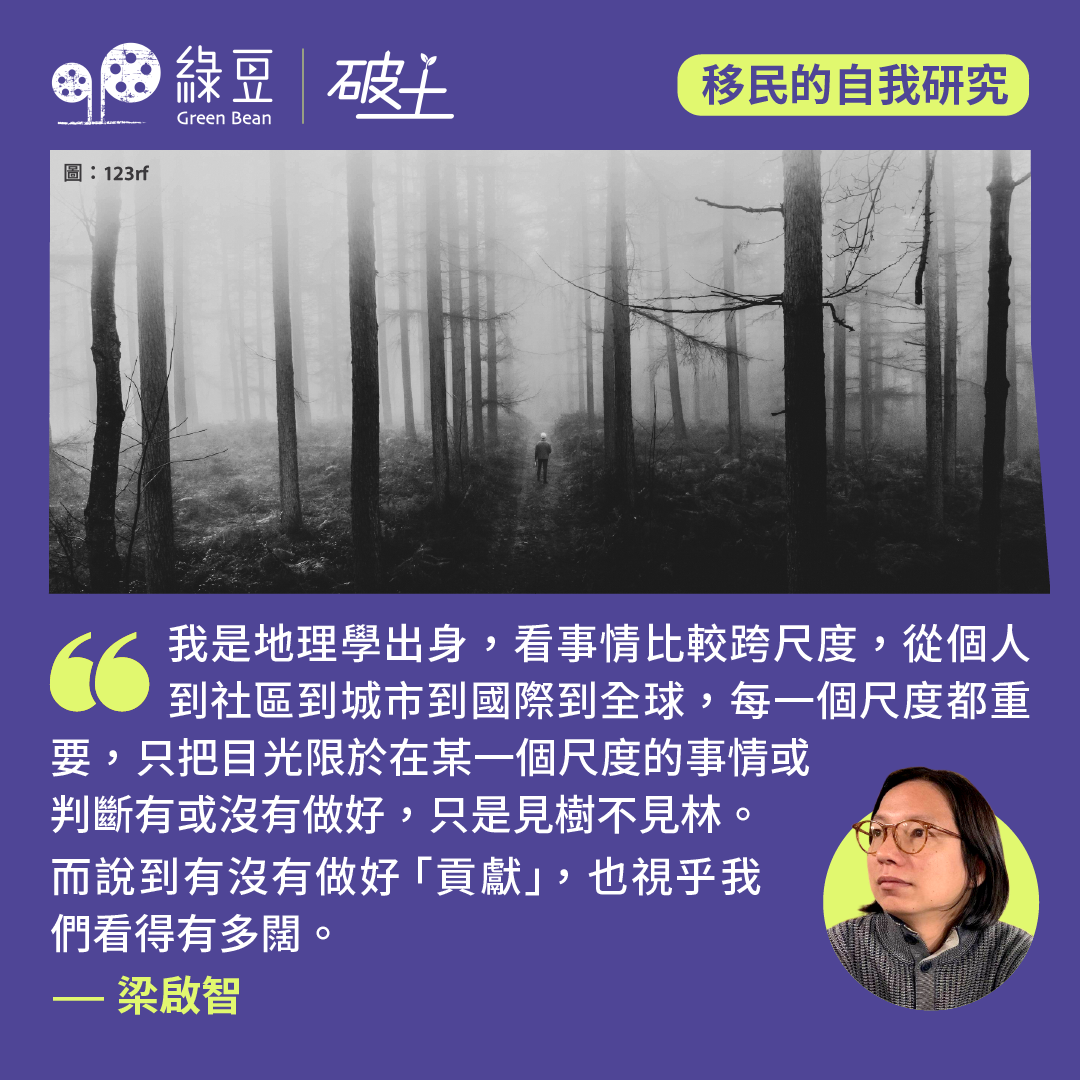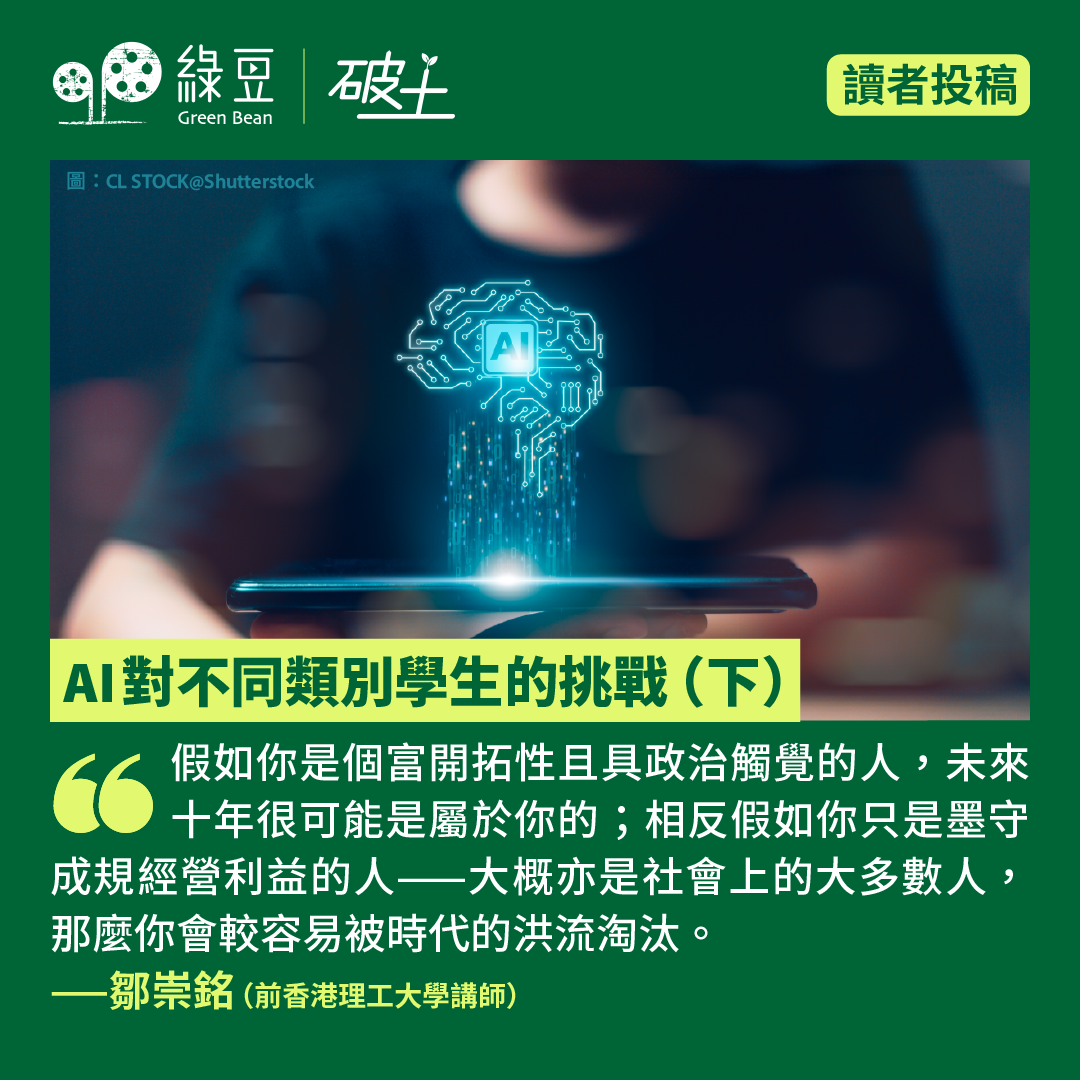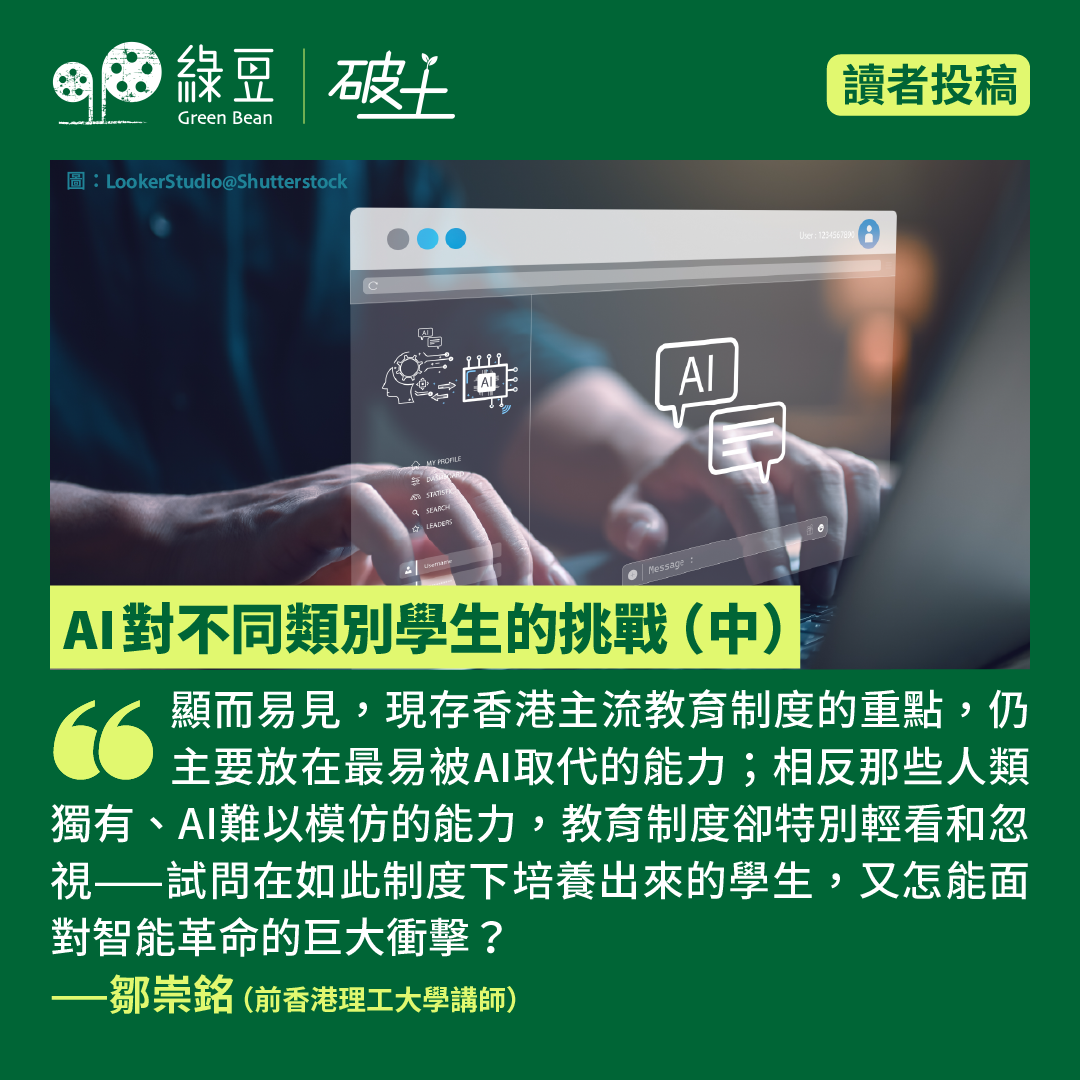( 編按 : 此專欄內容均為真實處境,旨在反映家庭、婚姻及個人之間的複雜性,以文字與大家一起走過荊棘。專欄文章經編輯在文字上修改處理,確保內文提及的人士身分保密。) 當孩子出現困難時,無論是行為還是情緒問題,父母往往容易走向兩個極端:有的會立刻反思自己做錯了什麼,認為問題源於自己的不足;有的則斬釘截鐵地認定是孩子的錯誤所造成。這兩種看法看似不同,但共同之處在於:它們既幫不上忙,還常常把父母的情緒推向內疚或憤怒之中。 15歲的Summer已經超過一星期沒有進食,父母焦急之下把她送進醫院。當情況稍為穩定,醫生建議他們接受家庭治療。第一次見面時,張太立刻說:「都是我的錯,我見Summer最近沒有胃口,就拼命煮不同的菜,催促她多吃一點。結果她不是完全不吃,就是吃到吐。我太心急了,不應該這樣做。」張先生卻嘆了一口氣:「Summer自己想瘦,所以才不肯吃。我們從沒批評過她,也不知道她為什麼覺得自己胖。」 張太深陷自責,張先生則堅持認為女兒「自作自受」。當父母各自停留在「全是我的錯」或「完全是她的問題」的思維時,他們聽不進對方的聲音。即使張太提起張先生常提醒女兒「不要吃太多,免得長肉」,張先生也立刻否認:「我是為她好,從沒逼過她運動。」...
雖然香港過去數十年來多次的移民潮或多或少也和政治局勢相關,但相對而言政治因素對當前的移民潮明顯見得更為迫切。畢竟在此波移民潮當中,不少人都是因為面對切身的政治壓力而選擇離開。而在他們離港之後,回看過去在香港並肩作戰的友人要在新的現實下過活,往往會產生「倖存者內疚」(survival guilt)。曾在各地與不少過去活躍於香港公民社會的朋友見面,發現儘管程度上和表現上或有差別,潛藏的相關情緒原來相當普遍。 所謂「倖存者內疚」,一般是指對自己「活下來」的愧疚感,或覺得自己不配「過得較好」。這感覺源於在創傷事件後的相對比較:自己能繼續生活,其他人卻沒有。這兒說的創傷事件可以是指戰爭、天災、疫情,或政治打壓。離散社群的成員考慮到自己離開了原居地受壓或受苦的群體,也會產生同類的情緒反應。 港人社群中的三種表現 我在港人社群中遇過的,通常有三種表現的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羞愧,覺得自己的離開是一種背叛。特別是見到有留下來的人選擇「慷慨就義」,主動迎接因為政治參與而帶來的苦難,這時候離開了的人往往會責怪自己是否做了逃兵,未有如對方一樣能通過自我犧牲來發熱發亮。...